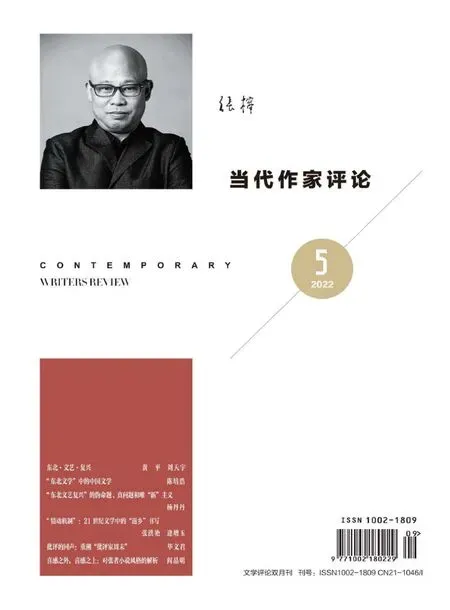从“探求者”到“美食家”
——兼谈陆文夫与《苏州杂志》
朱红梅
作为当代文坛“回归”的一代,陆文夫的创作生涯几经沉浮。20世纪50年代,因为《荣誉》《小巷深处》的发表,青年陆文夫惊艳文坛,成为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组成员;1957年,“探求者”事件发生,他被遣送回苏州机床厂当学徒;60年代初,经济调整,文艺复苏,他又返回南京当上了专业作家,《葛师傅》等作品的发表让他获得了茅盾的关注,后者专门撰写评论《读陆文夫的作品》并发表于《文艺报》;1964年,陆文夫因专写“中间人物”,“坚持‘探求者’的老观点”再次被批,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苏北的黄海之滨,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苏州;粉碎“四人帮”后的8年间,他的创作进入井喷期,发表了约4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4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贡献了《美食家》这样的新时期文学经典之作。陆文夫曾总结道:“从二十五岁起开始写小说,用了二十五岁的时间跌倒爬起,三起两落,最后才落定了作家这个并不美好的职业。”①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2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三起两落之间,风云变幻,物是人非,也有些东西历经磨难始终如一,例如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对于办刊的热衷。纵观其跌宕起伏的创作和编辑生涯,有着无法忽略的互文关系。
一
陆文夫一生办过两本刊物,一本是文学刊物《探求者》,一本是文化刊物《苏州杂志》。确切地说,筹办于20世纪50年代的《探求者》并未正式创刊,充其量只是成立了一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成员包括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陈椿年、梅汝恺、曾华等一批当时的江苏青年作家。众人推举陆文夫起草组织“章程”,高晓声起草“启事”。后来,《“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亦作为“反右”斗争批判对象在1957年第10期《雨花》全文刊发。
“章程”开头第一条:本月刊系同人合办之文学刊物,用以宣扬我们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②《“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明确了《探求者》系同人刊物,以示与机关刊物的区别。第六条第九点又说,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③《“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这条旗帜鲜明地反对机关刊物的“面面照顾”和“拼盘杂凑”,认为这样的刊物缺乏独特的见解和艺术倾向,无法树立起自己的风格来。他们还在“启事”里强调:“这种拼盘杂凑的杂志内容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编辑部战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艺术思想的混乱。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①《“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又说:“我们这样来办杂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我们也竭诚地寻求同道,但决不面面照顾。对于来稿,合则来,不合则去。我们期望以自己的艺术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②《“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
《探求者》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出于对江苏的文学期刊《雨花》的某种不满以及对当时办刊风气的自觉纠正,一群文学界的理想主义者集结到了一起,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创办一份有特色的新刊物。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期刊林立,同人刊物鳞次栉比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苏州的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通俗文学耆宿,编创了各种各样的文人期刊,在市民阶层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前人的成功经验坚定了“探求者”们以刊物创流派的目标与决心。
在创作手法上,“启事”声明:“我们认为现实主义在目前仍旧是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方法”。“启事”的观点和“章程”的表述彼此呼应:“(刊物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漫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③《“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在后来的“反右”批判中,“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都成为“探求者”的罪名而遭到逐一批驳。④周根红:《“探求者”文学社团的酝酿、批判与平反过程》,《钟山风雨》2011年第6期。“探求者”事件令陆文夫等历经坎坷,损失了十数年的写作光阴。晚年的陆文夫回忆: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浪漫主义者,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只是经过了“反右”和“文艺整风”之后,才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把浪漫附托于想象中。⑤陆文夫:《致陈村的邮件》,《苏州杂志》2008年第4期。
那么能否据此推断,他年轻时“探求”未果缘于不切实际的浪漫,花甲之年经营《苏州杂志》就是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呢?似乎也不尽然。《苏州杂志》创办于1988年。陆文夫撰写的“发刊辞”短短千字文,却是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体。浪漫主义体现在刊物定位上:办刊人要把《苏州杂志》办成一本文化杂志。人文荟萃的苏州古城给了陆文夫这样的自信,“苏州的优势不在于单项冠军,而在于团体总分。文化古城的特点就是文化的各种门类齐全,都有传统,都有积累,都有发展……目前的各种期刊都统称杂志,但真正的杂志却并不多见,苏州可以杂,因为它有那么多的内容可志”。⑥陆文夫:《发刊辞》,《苏州杂志》1988年创刊号。《苏州杂志》讲究格调,追求高雅,所以在追求理想的同时,陆文夫也以“谁爱风流高格调”自况,对这本杂志的命运做了现实而清醒的预判:“《苏州杂志》的诞生,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目前的期刊已多得目不暇接,何况它的封面上没有‘赤膊女人’,标题又不‘吓人大怪’,不可能畅销,一定要赔本,既无公费可吃,只能靠向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化缘’,随缘乐助,功德无量。”⑦陆文夫:《发刊辞》,《苏州杂志》1988年创刊号。在他看来,办刊是一件值得文化人为之献身的“傻事情”,并以“武训行乞修学”来勉励杂志社同人。
浪漫也好,现实也罢,可以视作陆文夫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应对策略。如果说“探求者”的受挫源于逆时而动,而新时期办刊则是一种顺势而为。以同为“探求者”的方之创办《青春》为例:“方之兴致勃勃地向我宣传刊物的方针,说是要办一所文学的中小学,一座苗圃,让文学青年在这里成长,长大了可以升大学,可以从苗圃里移栽到高山上去。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当年,老一辈的作家和编辑也曾经办过青年刊物培养过我们,可我也知道办一个刊物很不容易,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人马、经费、纸张、印刷、组织稿件,困难一大堆。”⑧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96-9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这是1978年的秋天,陆文夫坦言那时尚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方之却已经在和斯群发起筹备工作,并将人生最后的一点精力花在了《青春》的筹备上。“方之对他的身体状况也并非是毫无预感,他曾对我说过,最多只想活五年,把一个刊物办起来。把几篇想写的小说写出来,然后再见马克思去。”①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97、29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陆文夫惋惜方之最终没能把想写的写出来即匆匆谢世。但是对于方之这种“把自己的生命为别人做了路基”的精神,他是感佩和敬仰的。而前者的“路基”精神,与他自己办刊的“献身”精神,几乎如出一辙。
二
1988年的陆文夫,已经写出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作品《美食家》。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主持一个地方文化刊物《苏州杂志》,可谓大材小用。何况,他还有着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划。叶兆言在《苏州杂志》第200期纪念文章中提及:“就在我们家,陆文夫先生对我父亲说,他准备弄一本刊物,名字就叫‘苏州杂志’。给人的感觉,好像也就是很洒脱地随口一说。父亲并未当真,私下里对我嘀咕,你老陆叔叔向来不怕事,弄什么杂志呀,吃力不讨好。”②叶兆言:《珍惜》,《苏州杂志》2022年第1期。好友叶至诚的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一方面,他既是“探求者”同人,又主持着《雨花》编辑工作,对于办刊的条条框框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其时纯文学遇冷,办刊无疑要面对人才、经费、组稿、印制等各方面的困难和压力。对于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陆文夫来说,确实“吃力不讨好”。
那么,陆文夫又为什么要迎难而上办杂志呢?时任苏州市委副书记的周治华在回忆文章里说:“苏州人才济济,办刊之人有的是……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我们的第一人选是陆文夫,争取他出山,是为上策……于是,我登门求贤,找上老陆了。他认为刊物一定要办,由他来办,要考虑考虑以后再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登门找了老陆。他表示,一定要他办,就一定要办好。他坦率地说,由他当主编,要答应他两件事:一是编辑部人员,由他提名;二是编辑内容,由他定。说句实话,当时办个文学刊物,最大的担心,就是不能‘出格’。老陆已久经磨练,是个成熟的文化人,大可放心。我当时表示同意,也向他提出两条:办刊地址自己选;经费原则上自筹。”③周治华:《怀念陆文夫》,《苏州杂志》2008年第4期。
可见,陆文夫对于刊物的态度还是明确的:一要办;二要办好。对于办刊,陆文夫绝不是凭着一股“傻”劲就赤膊上阵,对于“怎么办”,他是有着通盘考虑的。第一是确立《苏州杂志》地方文化刊物的定位,规定“所言之事所述之人,都必须是和苏州,和苏州的文化、风貌有涉,无关者留与他人评说”。④陆文夫:《十年树木》,《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他承认这对于刊物是一种局限,但是,“刊物的局限性也就是它的个性,也就是它的特色,没有特色的刊物在当今期刊林立之中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我们坚决不开百货公司,只开一爿苏州文化的专卖店”。⑤陆文夫:《十年树木》,《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这样的办刊理念与其创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将保持特异性作为首要追求,“一个创作文学而不是创作流派的人,并不希望大家都流到一起去,甚至于还害怕别人和自己流到一起来”。⑥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97、29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之所以不将《苏州杂志》办成纯文学刊物,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许多四大块(小说、诗歌、理论、散文)的文学刊物已摇摇欲坠了,何必再添一个替死鬼!”⑦陆文夫:《发刊辞》,《苏州杂志》1988年创刊号。第二是要求地方文化刊物也要办出高格调。《苏州杂志》不登广告,不刊“吓人大怪的文章和赤膊女人”,办的是民俗、风俗杂志,写的是世俗、世情故事,而世俗、民俗与风俗之俗,并非庸俗和媚俗。不迎合市场而降低刊物品位,不允许广告经营来插手编辑业务,就是俗中见雅,特立独行。第三是持之以恒。陆文夫主持《苏州杂志》17年,出刊整100期。“《苏州杂志》创刊时,市委、市文联的领导者集思广益,为杂志定下了‘当代意识,地方特色,文化风貌’的十二字方针。我们把这十二个字印在每期的刊头,认认真真地加以执行。”①陆文夫:《十年树木》,《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这里体现了陆文夫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人”的自觉,相对于高屋建瓴的办刊方针,他关于“开一爿苏州文化的专卖店”的提法其实更具体、鲜明、深入人心。他在创刊10年絮语中总结,《苏州杂志》能取得一点成绩,应该归结于两点:一是办刊的方针明确;二是明确了以后就不要东张西望,要坚决地、富有韧性地认真执行。②陆文夫:《十年树木》,《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
从《探求者》“启事”到《苏州杂志》发刊词,可以读出两个时期面目迥异的陆文夫。这样的变化无法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简单概括,只能从时事变迁中梳理线索,寻找其合理性及必然性。《风雨中的一枝花》写于1987年,首先,主编《苏州杂志》的陆文夫不再坚持“开专车”“创流派”了,认可刊物就是公共交通工具,“把一些人的灵魂送到一批人的灵魂里面去”;③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101、102、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另外,肯定当时《雨花》《青春常在》,作为“一条客流量不太大的基层路线”的方向,理由是“人人都想干大事,那小事儿由谁去干呢?小事儿干多了,再由办大事儿的人把它汇集在一起”。④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101、102、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晚年的陆文夫是务实派,对于文学和文化艺术上的纯粹性,他一以贯之地追求,而在其他方面,他有着处理现实问题的精明和妥协。
1995年,长篇小说《人之窝》发表后,陆文夫停止了小说创作,“年逾七旬,疾病缠身,精力不济,老骥伏枥,主要是休息,能写则写点,不能写就做一点写作之外、力所能及的事情”。⑤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101、102、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这“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办《苏州杂志》,并且办成了一份集腋成裘的事业。从1988年至2005年的17年间,陆文夫在《苏州杂志》上发表了6篇文章。包括《发刊辞》(1988)、《谢吴中父老》(1994)、《五十而立》(1997)、《十年树木》(1998)、《关于更正》(1999)、《一滴何曾到九泉——悼念凡一同志》(2000),除了最后一篇悼念文章,其余都是出于办刊所需的“吆喝”文章:《发刊辞》用于创刊号,《谢吴中父老》写于办刊5周年,《五十而立》是期刊50期的应景之作,《十年树木》为了纪念创刊10周年,《关于更正》主要是针对编校、印制质量所作的专门说明。2005年第3期是期刊整100期,当时陆文夫已经卧病在床,无力再撰写相关文字。从这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苏州杂志》是陆文夫晚年主要精力所系。从《探求者》到《苏州杂志》,如果说50年代办刊面对的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压力;新时期以来,期刊需要承受的则是迫近的经济压力和市场考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稿源不济、人才流失、刊物后继乏力等问题。期刊的兴衰也从某种角度预示了“回归”一代的创作命运和前景,他们在不同时期承担了不一样的时代压力。
三
从作品的创作数量和影响力来综合考量,《美食家》发表的1983年可以视作陆文夫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同年发表的《围墙》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美食家》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曾有论者认为:“1984年,陆文夫刚获得新的身份和标识——被称为‘陆苏州’的‘小巷文学’代表作家,此后的写作便难以为继……实际上,自从陆文夫发表《井》(《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以后,‘小巷人物志’系列名存实亡。”⑥刘新林:《“巧干”的作家——论八十年代文学场中的陆文夫》,《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3期。论者将陆文夫创作衰退的主因归结为“小巷人物志”后期作品的模式化效应。“难以为继”和“名存实亡”的论断是否确切,还有待商榷,但是1984年以后,陆文夫中短篇小说创作势头出现明显减缓的迹象也是事实:1985—1994年,他共发表4个中篇小说、3个短篇小说,以及少量散文、创作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1988年以后,他将主要创作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创作上,创办《苏州杂志》也占去了他一部分精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主观反思作用下创作理念的变化。
“糖醋现实主义”作为陆文夫小说创作的标识,“在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时处理好了紧张与妥协的关系”,①王尧:《重读陆文夫兼论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使得他80年代的创作不处于任何潮流之中,显得从容笃定。但这一代“归来者”对于现实的关切,对于文以致用的追求与实践,是一以贯之的。在《有用与有趣》一文中,陆文夫承认当年在与“苏州三老”的交往中得到不少教益,但创作思想却各异:
有一次,我和周瘦鹃先生闲聊,偶尔问起,“你创作时首先注意的是什么?”
周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有趣。”
“你呢?”周先生反过来问我。
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用。”②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293、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两代“美食家”,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文学旨趣和审美取向。熟读《美食家》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作者一段时期内与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相处的耳濡目染,但是陆文夫《美食家》的主旨,却与“鸳鸯蝴蝶派”的意趣有着天渊之别,他心中始终背负着历史的责任和现实义务,探索着文以致用之道。在新时期的第二次文学跋涉中,“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进行了十多年的冲刺,我把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人与事,一一加以审视,对受难者寄予同情,对卑劣者进行讽刺”。陆文夫也是在对自身批判现实的反思中,慢慢停下了笔,“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他不能包写一切”。③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第293、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作为一个少产多思且坚定的现实主义写作者,陆文夫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他自我解构了文学的“特别法庭”,越过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学有用论”。
陆文夫在一次访问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围墙》、《井》等都属这类作品。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像唱昆曲的艺人、帮人家办酒席的‘挑高蒌’、做丧事的‘桥头’,都是很特殊的。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再不出去做访问、找资料,这些人都要死光了,苏州就有年纪大、绣得一手好刺绣的妇女,被召到皇宫去织缂丝,故事丰富极了……”④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陆文夫说这段话时不过60岁,和汪曾祺复出时年纪相当。
这段话充分表明陆文夫对于有别于“糖醋现实主义”的另一种文学的向往。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小说家陆文夫,会将《苏州杂志》办成一份反映民俗民风、乡土乡情的文化期刊。首先,一份好杂志当然需要独树一帜,人无我有;同时,这种出人意料之举,亦喻示了陆文夫在文学创作理念上的思考和新变。在晚年致友人信中,他又强调:“总觉得一个作家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要想跨越一个时代很难。”⑤陆文夫:《致陈村的邮件》,《苏州杂志》2008年第4期。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但他仍然尝试着要从自己建造的“法庭”出走,走到更为广阔的“民间”去,与小人物打成一片,而不再是置身事外的“审判官”。
从“探求者”到“美食家”,陆文夫始终在不单纯的文学创作环境中,探索受限的创作方法,以达到自己文以致用的理想。晚年创办《苏州杂志》,有着从伴随创作始终的“文学有用论”驱策之下“出走”的打算,但因为精力等问题,终于无法再发起自己写作上“新一轮的冲刺”。陆文夫的文学之路,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与现实不断冲突和妥协的路。从“探求者”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唯一模式开始,到探索“糖醋现实主义”成为闻名遐迩的“美食家”,再到对于文学以外的民俗文化的一些思考和延伸,都表明了他几经沉浮,仍能在局限中打开局面的探索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