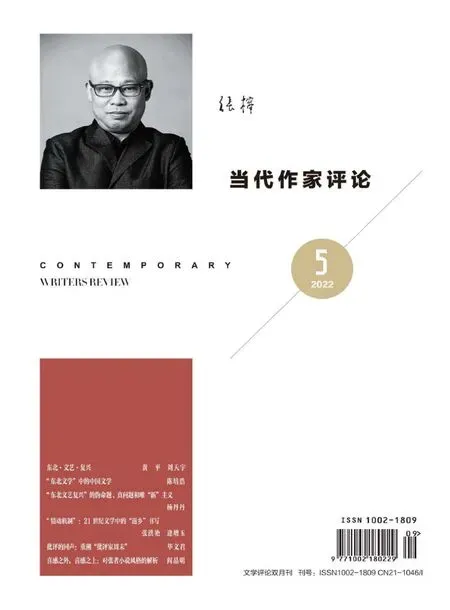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 张清华
主持人的话在北京以南的郊野,有一个幽静的园子,俗称“湾子”,这里住着隐士张者。
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张者并不总是住在这里,只能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隐居”于此,其他时间他就“孔雀西南飞”了。当然,张者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除了这一点外,说他是隐士,并非夸张。因为这个园子太幽静了,近乎幽闭,喜欢热闹的人没法在这儿待住。那树木遮天蔽日,那碧水四周环绕,城市和喧嚣,在这儿立刻便成了远方,甚至梦境。
当然,风景是没说的,除了冬天是照例的萧索,其他季节可谓是桃李芬芳,春色满园,尤其到夏秋,树上的各种果子竞相招摇,晃得人眼花缭乱。
可是这么好的地方,却很难有人可以常住,除非是真隐士,假隐士不行。和张者住对门的李洱就是,每次去,兴之所至,半天足矣,侍弄一下他的菜地,他的花木,就吵闹着要回城;若住一天,必须要有一伙朋友陪着,否则便会觉得静寂难耐。来时路上还大讲京城之拥堵闹心,到走时,便又高叫大隐隐于市也。
但没有李洱的湾子也不好玩。太安静了,确乎会让在城里面住惯了的人心里发慌。张者安稳如山,很少开玩笑,和李洱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庄一谐,一静一动,而他们对门而居,亦算择邻佳话了。没有李洱,张者纵有定力,也不免寂寞;而没有张者,李洱也决然不能在这幽寂之地待一天。所以他们两人这么一对门,一不小心便把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门派”搬到了这里。
什么门派?李洱曾经戏称之为“雄安文学”,言从“建安到雄安”的文学史,有了一个新地标。我以为,“雄安文学”倒还未必,因为这湾子实则还在北京的边儿上,离那水乡泽国的白洋淀还有一百多里地呢,压根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但至少,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知识分子小说,在这儿倒是落定了两个重镇。李洱过去还只算是个“影子人物”,出了《应物兄》之后,便属真人物了,可以标立门户了,算是主将;张者呢,虽然还没有李洱那么炙手可热,但自世纪之交以来陆续推出的《桃花》《桃李》《桃夭》“大学三部曲”,怎么也确立了他“副将”的位置了吧。一正一副,那是在写小说的角色方面,但要论在生活方面,张者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先说说作为园丁的张者,作为“桃李”的手植者,可不是白混的。你如果有机会来他湾子的小院,那就算是开眼了。门前盛放着玫瑰、月季、蔷薇,玫瑰丛旁边是芍药,芍药旁边是葡萄架,葡萄架下是菜园,菜园里种着紫色的玫瑰甘蓝,甘蓝旁边是一小畦地瓜,地瓜旁边则架着黄瓜、西红柿,再边上,便是茄子、辣椒,更远处的墙外,是硕果累累的南瓜……
这还只是他园子外面空地上的景观。穿越欧式花墙间的院门,来到他的园子中,才会看到更多景致:一座中式的亭子居于对角线上,中间是品茗乘凉的茶座,亭子两侧分列着各种果树,有桃树、李树、枣树、石榴树,花园中种着欧月和绣球,墙角下是花团锦簇的秋菊……我原来所着迷的陶渊明式的“采菊图”,现在活脱脱换成了张者的形象,除了缺身行头,要论风骨气度,舍张者又有其谁耶?
张者的园子里,真个儿是桃李争妍,生气勃勃,屋子内更是一尘不染,满室书卷之气。张者好客,来湾子的朋友的第一客厅,当然是张者家。每次他都会把好茶拿出来,并且留大家在他家吃饭。张者雇有专门的帮手,一边喝茶一边大将风度地指挥着,他一般不亲自下厨,有关键的招牌菜时,才会亲自掌勺。
而这时李洱也大显身手,他的拿手好戏是“李氏烤肉”。羊肉、孜然、辣椒粉,还有木炭,都是从专卖店精挑细选的,烤炉和工具一应俱全。每次先把木炭引燃,去掉烟气之后,才会把亲自扦插好的肉串,码放到火上,这时油烟和香气便弥漫开来。李洱一边哼着小曲,扇着扇子,在烟熏火燎中大呼小叫着。而这时,张者便会端着茶一边伺候着,嘴里面还要口称“李大师”,生怕这“主烤”寂寞偷懒儿,把火候弄过了。嘴里面不停地夸着,这手艺,若是有“茅盾烤肉奖”,那也是非洱兄莫属了。
那时候我就会感慨:这两兄弟都是误打误撞地穿越到了当代,他们即便不是兰波和魏尔仑的再世,也应该是元稹与白居易的托身了。
前面说,张者是候鸟,一到深秋时节,他就展翅飞往嘉陵江畔温暖的山城重庆,去当他的“重庆市专业作家”。那时,湾子才真正地枯寂下来,开始度越它漫长的寒冬。那时,“雄安文学”便真的只剩下一个苍白干燥的词语了,因为张者走了,李洱也不会再来。想让它重现生机,要等到来年之春,张者如同候鸟一样飞回来。所以,有张者在的湾子才是真正的湾子,那儿才有地气和灵气。这时你再去湾子,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去处,一个有足够的生气和活力的地方。
了解作家生活的,一般都知道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活动半径大,没有足够的地理和物理跨度,不会对生活有特别深的感受;二是定力强,虽满世界跑,但真正写作时都是要坐得下来,耐得住寂寞才行。而像张者这样有如此大的半径,又有这般坚韧的定力的,还是不多。
要问张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模式,那就要从他的身世说起。他的生活轨迹,大概已作为一种“无意识”融入了他的血液。他祖籍河南,出生不久,父母就从老家信阳支边去了新疆,张者在外祖母身边长到六七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时,跟表舅一起坐火车去新疆寻找父母,在那里上了小学、中学。1984年他考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从那儿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就是独立在京城游弋打拼,开始去了新华社,后来跳槽到《南方周末》,然后又从媒体回归文学,因为创作成绩突出,被重庆作家协会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当了专业作家。
有了这么一个足迹,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者能够在这座空旷的园子里悠然自得地居住下来了。他有孤独的童年,独立成长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自然也就有了这喜欢享受宁静和僻远的性情。
说完了隐士和园丁,还要说说作为作家的张者。张者似乎并没有在最早的“新生代”名单中占到地盘,但从他90年代开始写作迄今,也差不多接近30年了。张者一直是作为创作界的闲云野鹤或独行侠存在的,但从写作本身看,他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新生代群落中的零余者”,只是他因“‘桃’之三部曲”(阎晶明语)而声名鹊起时,已错过了被收纳的时机而落了单。
这次下决心把张者“强拉”到“新生代”的阵容里来,大约不只是为了借此重盘概念,也是试图代历史“偿债”。因为张者确乎为一个写作谱系做出了贡献。阎晶明的文章说得好,从鲁迅到钱钟书,到王朔,凡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都带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喜感。他说出了神韵和关键。这个喜感,说穿了是一种“有意味的批判”。中间似乎还可以把某个阶段的王蒙,把英年早逝的王小波,还有世纪之交以来的李洱,都放进去,他们共同生成了一个具有先锋气质的谱系,一个具有思考加讽刺意味的写作群体。这个群体,我个人以为也当然是当代先锋文学的一个锋面,其核心是王朔与王小波,后继者则是李洱与张者。
这正是我们重新看待张者的理由。在这个谱系学的意义上,张者也成了“新生代”写作的一种典范:既传承了先锋文学中固有的实验性、批判精神,同时又将那些比较极端和观念化的倾向,适时引向了现实的地面,“软化”并放大了它们。但从文化与美学精神的内核上看,他又一以贯之地传承了应该传承的东西,比如说幽默的、诙谐的、亵渎的、叛逆的那些风神。在当代的意义上,在我看来,根本上便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置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场域中,是最合适的:知性的、欢谑的、神经质的、形而上学的、斗嘴皮子的、充满弦外之音的……总之都有不可预测的衍生性与增殖的可能。
这也就不难理解,“‘桃’之三部曲”中的那些言语的机锋、情感的一惊一乍、夸张过剩的力比多、一夕三变的爱恨情仇、翻云覆雨的人生哲学;不难理解,那些本可以避免却非要发生的悲欢离合。
张者的大学系列,确乎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景观。很多人试图讲这一人群的故事,但因为“度”的把握尤难,要么没意思,要么不真实,而很少被人记得。而张者将他们适时地放到了时代和时间的洪流之中,让他们的生活获得了“历史的现场感”,以及敏感的“文化意味”,并且因之而获得了存在的根基,以及真实性与意义。当然还有风格意义上的成功。张者有适度的诙谐,节制的俏皮,并不泛滥的荒诞,这很大程度上降解了“二王”那恣意欢谑的经典手法,变成了更接地气的时代性景观,并且也成为了张者自己。
当然,张者是丰富的,他截至目前的创作至少显现了三个界面,知识分子生活,属于他父母亲的兵团生活,再就是其他的历史虚构。关于这些,我就不必啰唆了,因为接下来的几位研究者,都会比我说得更精细和靠谱。我的任务仅仅是,给予张者在这一栏目中一个必要的理由,一个“木已成舟”的说头。
当然,我最着迷和嫉妒的人,还是李洱,不是嫉妒他的才华,而是嫉妒他的运气,因为他与张者对门而居,便有了一个最靠谱的兄弟。任何时候只要敲开他的门,都有好茶喝,有满园春色以供玩赏,如果赖着不走,便有酒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