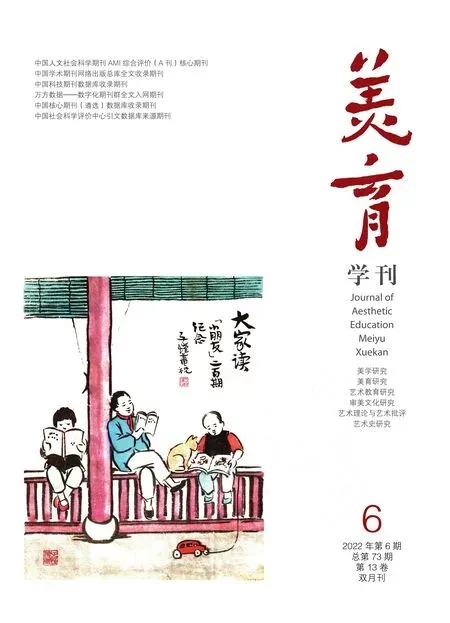从“古雅”到“无弦”:历史语境中苏轼琴学思想的变迁
郎耀辉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苏轼是北宋时期政坛、文坛双领袖,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又成就超然。在政治生涯中,他泾渭分明、恪守原则,有三次在朝为官后遭外放再被贬的经历。在文学艺术领域,他诗词俱佳,绘画、书法、音乐造诣皆深。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代表,苏轼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诸多政治理念与文艺观点相互呼应,显示出矛盾与交融的独特面貌。
相较于诗词、书法和绘画,苏轼的音乐成就往往不为人所知。事实上,他不仅音乐活动异常丰富,如蓄伎唱乐、品笛鉴乐、度曲作乐等,还写下了十分深刻的乐论。在诸多音乐形式中,苏轼对古琴情有独钟,不论是早年意气风发还是晚年落魄失意,始终与琴为伴。他一生咏叹的古琴诗词共计八十余首,更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了古琴传统、丰富了琴学理论,奠定了后世“淡”的琴学审美旨趣,并大大推进了陶渊明以来形成的“无弦琴”传统。
关于苏轼的音乐美学研究已日臻成熟,学者们结合苏轼的生平,将其音乐美学思想大体归结为:早期的“乐教”思想,外任时期的“泛美”思想,“乌台诗案”后的“悲美”思想,二次被贬后的“淡美”思想(1)此说参考南京艺术学院衡蓉蓉博士学位论文《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此外,成容在《苏轼“淡美”音乐思想的行程轨迹》(《四川戏剧》2020年第4期)一文中将苏轼音乐思想分为早年“尚美”、中年“和美”、晚年“淡美”,亦在此框架之中。。总体上看,这是中肯的。具体到苏轼的琴学研究,学者们或从音乐学、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苏轼琴论的特征、成就等,或将苏轼的琴学放在其音乐美学思想的范畴内加以考察,探讨其琴学的儒释道根源、审美旨趣等,为苏轼研究开创了崭新的面貌。但上述研究尚未将苏轼琴学放在他整个政治生涯和文艺生命中加以比对,既缺乏纵向的琴学思想变迁脉络研究,亦缺少横向的与苏轼同时期其他乐论的对比研究。
实际上,苏轼琴论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在早年强调琴具有“千古寥落”(《舟中听大人弹琴》)的古雅美,却在中年被贬黄州之后写下《琴非雅声》,认为琴是“古之郑卫”之声;他在谪居黄州时为琴乐《瑶池燕》填新词以表达“闺怨”之情,却在《听僧昭素琴》中强调琴乐“至和”“至平”的审美特性;他追求古琴演奏的“指法之妙”(《文与可琴铭》),却屡次三番作应和陶渊明的诗词,表达自己对无弦曲意的向往。上述矛盾,仅从苏轼音乐美学角度考量,显得错综复杂,很难找到强有力的阐释方案。
近年来,宋代音乐史研究出现了以“新史学”为范式的崭新思路。在方法论上,诚如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强调的,要采取“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将个人的思想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作观察”。[1]这种方法注重对历史语境的重建,并“强调人与社会的互动,在历时上强调思想的形成及其制度化、常识化、风俗化的过程”[2]。苏轼琴学思想的矛盾和变迁恰恰可以在此种“新史学”研究范式中获得合理解释。
综观苏轼的一生,其琴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而这种矛盾恰恰伴随着他人生境遇的改变而发生。他从学生时代至从政早期,坚持琴的“古雅”论,认为琴应当为礼乐制度服务;首次外任期间,逍遥而寂寞的生活使他有机会纵情交游,这时他开始重视琴对生命的滋养,将“平和”“清亮”视为古琴的审美标准;“乌台诗案”后的一段时间,他认为“琴非雅声”,消解了琴的政治功能,以创作琴诗寄托个人情感;晚年,他被贬惠州、儋州,一心归隐,琴学思想走向淡漠,向往陶渊明“无弦曲”的意境。
一、“古雅”论:苏轼早期琴论的政治意蕴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父子一行自家乡抵达京师,应举考中。在第二年的省试中,他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梅尧臣、欧阳修的称赞,但为避嫌而屈居第二。其后的殿试,他以《春秋》对义获中乙科。他又在最具权威的“贤良科”考试入第三等,受到当朝大臣和皇帝的赏识。当时的制科考试,第一、二等通常虚设,甚至这个第三等在苏轼之前也仅一人得过,足见分量之重。从省试、御试,到院试、秘阁试,苏轼名震京师,一举展示了他的政治思想,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苏轼早期的政治思想中,对乐教的讨论占有重要地位。嘉祐年间,苏轼参加了京都部务和“制策”考试,后者要求针砭时弊,他呈上了二十五篇策论文章。在《策略三》中,苏轼主要探讨了立法与任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3]797。社会行为虽受法律约束,但仍不免有行凶作恶之人,就好比世间音乐形式众多,“淫乐”有自身存在的土壤。禁止“淫乐”正如杜绝违法一样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社会需要依靠贤者的引导,才能法治康明、礼乐和谐。在《策别十二》中,他进一步认为,“王治”中“安万民”的第一要义在于“敦教化”:“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飨,而谨之以冠婚丧祭,民是以目击而心谕,安行而自得也。”[3]811教化首推礼乐,通过学校教育,结合婚丧嫁娶的礼仪,百姓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感染,便能各行其是、安守本心。反观当时天下,“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3]839。礼乐价值缺失,学校教育缺位,礼乐断没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3]786,核心在于乐教。
乐有雅、俗之分,在苏轼的早期政论中,尚未指明施行何种乐教。通观他的策论,可见鲜明的价值取向。他在谈及《大雅》《小雅》时说:“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3]841《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又素有诗家和乐家所传之分,诗家以孔子为代表,重诗之义,乐家以周太公为代表,重诗之乐。[4]苏轼评价季札观看周代雅乐,认为《大雅》《小雅》的区别在于《大雅》取辞宽广却不落流俗,《小雅》取辞狭小却并不局促,表明其尤重雅乐。
苏轼对雅乐的态度也落实在琴上。嘉祐四年(1059年),年仅23岁的他丁母忧归里,服满而随父亲和弟弟从家乡眉山沿岷江经三峡到江陵再转陆路至汴梁,在船上作《舟中听大人弹琴》一诗。该诗阐释了苏轼对古琴音乐的理解,表达了他对古雅意趣的追求。他认为,自从郑卫之声扰乱雅乐,演奏雅乐的乐器大多散佚,唯琴独存。琴是雅乐的象征,寓示“古意”。但时人竟容不下雅乐,强行为琴谱写铿锵的新曲,使之“声浮脆如笙簧”[5]524,改变了琴的审美旨趣,古器尚在、古意全无。面对此情此景,苏轼只得恳请父亲弹奏《文王》以追思。显然,苏轼视琴为雅乐的象征,不赞成时下“铿锵”“浮脆”的琴风,认为琴应当以“古意”为旨趣。
如果说策论是为制科考试而作,其阅者是皇帝和朝堂大臣,那么返程途中的诗作则为抒怀,表达了苏轼的审美意趣。结合二者可见,苏轼重视礼乐,强调乐教,尤其重视雅乐。可惜演奏雅乐的乐器大多散佚,只有琴能重现雅乐,因此琴不应当演奏流行乐曲,而应追寻古意。琴的审美意趣也不应当是“铿锵”和“浮脆”的,而应当是古雅的。
彼时,意气风发的苏轼胸怀家国天下、壮志凌云,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怀有远大抱负,对音乐和琴乐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乐教功能上,尚不含人生况味。嘉祐六年(1061年),他被认命为大理评事,在凤翔府充任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嘉祐十年(1065年),解除官职的他返回京都,在史馆任职,有机会饱阅名家字画和珍本古籍,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治平三年(1066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兄弟立即辞官,将父亲和苏轼妻子的灵柩运回故里,丧居共两年零三个月。熙宁元年(1068年)腊月,苏轼兄弟二人携家眷从陆路返京都,于次年到达。等待他们的,既有各自政治抱负的实现,更有一场激荡的社会变法运动的冲击。
二、“平和”“清亮”:外任时期的琴学审美原则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33岁的苏轼与司马光、范镇一道反对变法。苏轼三次上奏折,洋洋洒洒万言,直陈政治主张,痛斥变法给百姓带来的伤害。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从“判官告院”一职改任“权开封府推官”,以一道乡试考题《独断论》彻底激怒了王安石,立遭罢黜。七月,他携家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通判有联署和监察官吏之权,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但实则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6],除了审问案件外并无重要任务。因此,他有了更多闲暇与人交游、纵情山水,创作了大量诗词。杭州当年已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大城市,“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6],这一时期,苏轼听琴、赏琴,并以琴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对琴的看法发生了较大改变。
熙宁五年(1072年),36岁的苏轼写下《听贤师琴》,自注云:“欧阳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韩愈《听颖师琴》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非琴诗。余退而作杭僧惟贤诗,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5]525韩愈琴诗是音乐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琴声是否可以“奇丽”。苏轼以《听贤师琴》表达对欧阳修的支持,认为琴声当以“平和”为准,不能追求琵琶声的“奇丽”审美效果,表明了嘲韩派的主张。他写道:“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叩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5]525苏轼认为,就古琴音色而言,大弦(较粗的弦)应如春日般温润柔和,大弦的取音标准首推“平和”;小弦(较细的弦)声音显劲直,应以“清亮”为标准。“平和”与“清亮”的标准符合琴的发声规律。大弦较粗,声音易闷浊、迟钝,若取音“平和”,则可避免,并使琴声韵味有佳。小弦较细,声音易吵显噪,若取音“清亮”,则可使琴声既有较强的旋律性又张弛有度。蔡仲德先生注释:“此诗以琴为雅而以笛筝为郑。”[5]525认为苏轼坚持了琴为雅乐的原则。若干年后,苏轼在黄州写就的《杂书琴事·欧阳公论琴诗》中重新引用了此诗,并强调琵琶音的“恩怨”和“轩昂”是与琴声格格不入的。很显然,此时苏轼对琴乐本身有了更深的体会,通过与琵琶音的对比阐释,建立起“平和”“清亮”的琴乐审美观。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又在杭州写下《听僧昭素琴》一诗,纵深推进了其琴学思想。苏轼于此再次强调“平和”为琴乐审美的总原则,指出“平和”的琴声有“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5]526的重要作用,首次将琴声与生命滋养相联系,指出琴乐不单单是外在的旋律,更是疏解内心郁结、平气和心的方法,从生命哲学的高度阐释了琴乐的意义。这与自东汉以来形成的琴人“禁邪僻、忿欲之情,养中和之气”[7]的传统观点契合,主张以琴静气、养心。
值得注意的是,从熙宁五年到熙宁七年,仅隔两年,苏轼便绝口不提琴乐的“清亮”原则。如前所述,在《听贤师琴》中,苏轼分别对大弦和小弦音色的“平和”与“清亮”作出审美界定,二者中“清亮”更倾向于琴乐的旋律性特征。到《听僧昭素琴》一诗,苏轼对琴乐的体悟逐渐开始超越旋律。他说,最“和”的琴声右手不施“攫醳”(即拨挑),最“平”的琴声左手不加“按抑”,从而否定了琴乐的音响性。但从实际出发,琴只有在手指运动下发声才能奏出乐曲。如果取消声音本体,通过琴乐才能体悟到的“微妙”便无从而来。《礼记·乐记》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8]。苏轼诗句的言外之意是,最微妙的琴声并不来自乐器的音响,而来自人之本心。散去“不平气”,洗去“不和心”,才能得到“至和”“至平”的琴声。自此开始,苏轼琴论一步步消解了琴乐的旋律性特征。
概而言之,在杭州外任的几年间,苏轼的琴乐审美观逐步建立:就旋律而言,他认为“平和”“清亮”是琴的音乐美;就生命境界而言,他更追求“平和”乃至没有声响的“微妙”琴声,目的在于“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以求涵养“此心”。从琴声的“平和”到内心的“平和”,苏轼琴论揭示了外在旋律直抵内心的功能与意义,将古琴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修养生命的高度。
三、“琴非雅声”论:“乌台诗案”后的情感皈依
元丰二年(1079年),任湖州知州仅三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以“文字毁谤君相”罪被判入御史台牢狱三个多月,史称“乌台诗案”。在狱中,苏轼每天被逼迫交代先前所作诗词用典的出处,饱受身心折磨,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后,他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既不得擅离,又无权签署公文,没有薪俸。苏轼的文学创作因生活境遇的急转直下而改变,感物伤怀之作大增,风格悲伤、抑郁。在此段时间,苏轼对古琴的看法也随之转变。
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在黄州会挚友陈季常,陈氏带着精美的笔墨纸砚求其创作,恰逢同行客人中有善弹琴者,机缘巧合下苏轼作《杂书琴事》十条,概括和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琴学思想。
《杂书琴事》的第四条是《琴非雅声》,在此条中,苏轼一改早年在《舟中听大人弹琴》中的看法,认为琴并非雅声。他说:“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5]531苏轼首先明确亮出结论:当世以琴为雅声的观点是错误的,琴其实是古代的“郑卫之声”。为了阐释清楚,他区分了当时和古时郑卫的区别。在“华夷有别”的语境下,“郑卫之音”其实是胡人之乐,而古时“郑卫之音”又是中华之声。苏轼在这里将音乐分成“胡乐”和“中华之声”两大部分,“中华之声”又分“郑卫之声”和“雅乐”。在他看来,琴乐的定位是“中华之声”中的“郑卫之声”,并非雅乐。
苏轼写《琴非雅声》之目的究竟何在?蔡仲德认为这是“崇雅斥郑进而肯定中华之声,否定‘胡部’即一切少数民族音乐”[5]531。龚妮丽则认为苏轼区分雅俗音乐的目的在于将论点转移到对“今乐”的分析上,“维护正统的‘中华之声’才是他真正的用意”[9]。两位学者均认为《琴非雅声》的核心价值在于巩固“中华之声”的正统地位,肯定苏轼维护“中华之声”的决心。但此说不足以解释苏轼对“琴为雅声”观点的颠覆,因为琴在苏轼早期观念中恰恰是雅乐的代表。值得探究的是,苏轼不仅肯定“中华之声”,还将其分成“雅声”和“郑卫之声”,并更看重“中华郑卫之声”,认为从古至今的琴乐当属“郑卫之声”。为了巩固这一论点,他还探讨了时人对琵琶的争议,悬置了琵琶演奏原本代表“中华郑卫之声”的地位,只肯定了古琴演奏“中华郑卫之声”的地位和价值。显然,《琴非雅声》的宗旨在于排除“胡部”音乐,将“中华之声”分为“雅声”和“郑卫之声”,突出以琴为代表的“郑卫之声”在“中华之声”的重要地位。“郑卫之声”主要与自西周以来的雅乐相对立,在政治功能、情感抒发诸方面都与雅乐不同。苏轼把琴乐从雅乐中排除出去,归到“郑卫之声”的范围内,旨在强调抒发个人情感为琴之要义。
首先,相较于青年时期,中年的苏轼对雅乐的重视程度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黄州谪居五年后,苏轼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变。宋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以母改子”,苏轼先是被恢复了太守的官职,官阶至礼部郎中,随即被召回京,做了中书舍人,后至翰林学士知制诰(通常由名望最高的学者担任),官居三品,为皇帝草拟诏书,成为真正的“大学士”。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为省试出了关于古乐制度的考题,如问:“法之二三,乐不可正,后世虽欲淳天下风,美天下俗,将何以哉?”[3]217法度不统一、乐律不标准,后世想风淳俗美,以什么为依据呢?苏轼如此关注乐律的统一问题,盖源于宋朝雅乐制度的复古倾向。
有宋一朝,曾先后历经六次大规模的雅乐改制,《宋史·乐志》记载,“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10],希冀恢复三代的雅乐传统。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范镇新制雅乐,虽最终未得到官方认可和推行,但苏轼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在《延和殿奏新乐赋》中先阐述了改制乐律的原因,“郑卫之声既盛,雅颂之音殆息”,而后提到“用稽《周官》之旧法”“验太府之见尺”,表明此番改制的标准和手段完全效法上古,最终达“天地之和既应,金石之乐可奏……律制既立,治功日新”[3]657。值得注意的是,论及雅乐的具体乐器,苏轼提到了“钟磬”和“笱簏”这类“磬管”。宫廷雅乐只有打击乐和管乐,却没有琴这样的弦乐,这是不同寻常的。据《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述,祈天地、祭鬼神的礼乐中就有琴的地位,如“云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龙门之琴瑟”[11]等诸多记载中所述。宋朝在“三礼”中首推《周礼》,一心复古的苏轼对此不会一无所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苏轼大力支持恢复雅乐制度,但绝口不提琴在雅乐中的地位,想必有特殊考量。
其次,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填词《瑶池燕》(2)《苏轼文集》卷七一《琴书杂曲十二首赠陈季常》之十二即为《瑶池燕》。据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证,词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题解说:“琴曲有《瑶池燕》,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显然,他听琴曲《瑶池燕》之后,萌生闺怨之情,遂填新词,寄给季常:“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揾,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鬟,眉峰敛晕。娇和恨。”[3]603从曲到词,苏轼借“偷啼自揾”的琴女,寄托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感怀,以“娇”“恨”自况被贬黄州的惆怅。在苏轼看来,琴不仅可以涵养生命,更能直抒胸臆。琴史上,以“闺怨”表文人的怀才不遇是琴曲的一大传统,如《长门怨》,借“金屋藏娇”的典故抒发文人似阿娇一般失宠的幽怨。
因此,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乌台诗案”后,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被贬黄州又被起用)使苏轼彻悟生命,既在官言官,坚持青年时期对雅乐制度的推崇,又在个人情感方面寻求琴的寄托。他将琴排除在雅乐制度之外,并不违背雅乐复古的核心——乐律的制定,又为琴乐抒怀给出理论支持。他的“琴非雅声”论使琴从“雅声”到“非雅声”,从朝堂宗庙的礼器到寄人情思的乐器,进而成为安放心灵之所,标志着苏轼琴论的一次重要转折。
四、“无弦曲”:苏轼晚年琴论的淡漠归旨
元祐三年(1088年),蜀洛党争,在朝为官的苏轼被卷其中。第二年,他自求外调,出任杭州太守。重新出仕杭州的他疏浚西湖,修建湖堤,兴办医院,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回朝任吏部尚书。八月,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他写下《听武道士弹贺若》一诗:“清风终日自开帘,凉月今宵肯挂檐。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合爱陶潜。”[3]408全诗以“清风”和“凉月”的意境开场,强调琴要如古淡的《贺若》(3)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琴曲有《贺若》,最古淡。”,诗定合恬淡的陶潜。自此,苏轼确立了以“淡”为美的琴乐旨趣,并向往“无弦琴”的旷达自适。
“无弦琴”的典故来自陶渊明。据南朝梁萧统《陶靖节传》:“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12]陶潜以琴寄意,言“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此后,“无弦琴”成为一个意象,历代文人借以“表示自己远离尘寰,不求荣达的高洁品性”[13]。至宋代,“无弦琴”这一意象更是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文人反复引用并讨论,成为“音乐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14]。
苏轼历来喜爱陶诗,在《破琴诗》之前,他虽偶有提及“无弦”,但多借此表达逍遥闲逸,如在首次任杭州时作《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写道“人生飘若浮”,因而要得意尽欢,所以“主人有酒君应留”,酒足饭饱后,“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3]74,一副沉醉肆意之态。随着境遇的变化,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和神往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绍圣二年(1095年),他完成了应和陶渊明的124首诗作。
被贬惠州乃至儋州后,苏轼论琴大多不离“琴枕”与“无弦”两个意象。此时,听琴、弹琴已不足以表达他对琴的嗜爱。他还用不适合做笛子的竹材制成周长约一尺的“袖琴”,也就是琴形的寝具“琴枕”,“轮囷濩落非笛材,剖作袖琴徽轸足”[3]542,连睡觉也要以琴为伴。在《琴枕》一诗中,苏轼更是奇思妙想,欲将琴枕装上琴弦,奏出动人乐曲,“斓斑渍珠泪,宛转堆云鬒。君若安七弦,应弹卓氏引”[3]542。可见,苏轼爱琴已臻痴境,至于琴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已经不重要了。
晚年,苏轼谪居于海南岛北部沿岸。当地居民大多为黎人,处中国文化的藩篱之外。在如此蛮荒之地,接触音乐的机会和场合十分有限。苏轼涉及音乐的文字自然较先前大为减少,且几乎看不到音乐旋律的元素。如果说苏轼在《破琴诗》中追求“无弦曲”的与世无争而抨击“与世好逐”的“流俗”,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愤懑,那么此时苏轼的诗作则只借陶渊明的“无弦琴”表达隐逸与淡漠之情。在海南,苏轼写下《和陶东方有一士》,自解“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3]517,显然也为应和陶渊明所作。在诗中,他描述自己“瓶局本近危”的处境,意识到早年追求华美的“楚弓”“越冠”实则对生命并无益处,仿若忽然间明心见性,顿悟了“殽潼失重关”才是自己该走的路,为此纵是崤山和潼水的万重关隘也挡不住他。苏轼追随陶渊明,“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岂惟舞独鹤,便可摄飞鸾”,借无弦琴,不演奏,而幻化成“独鹤”,架着飞鸾羽化登仙(4)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还将岭茅瘴,一洗月阙寒”,南方多瘴气,每年夏秋之时,茅草黄枯瘴气更胜,苏轼非但不畏惧恶劣的自然环境,遨游月宫,还要以茅瘴之毒,一洗仙境的寒凉。苏轼透过陶诗参得真如本性,笔下展现出彻悟生命后的大无畏精神,无论世间境遇若何,或摇步青云或遭贬蛮荒,都可上九天揽月。“无弦琴”在此作为一个审美意象,成为苏轼追慕陶渊明生活的符号,表达了他摆脱世事纷争、“归田园居”的生命向往。
至此,不能奏乐的“无弦琴”成为苏轼“归路”的伴侣,也成为他遁世的生命寄托。苏轼晚年将“淡美”的审美思想落实到琴上,使琴论超越了单纯的音乐审美,亦超越了抒情的艺术功能,上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
五、结语
中国古代尚“淡”的思想在先秦便已出现,“淡”被看作“道”的重要表征。《老子》言:“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15]老子把“淡”直接与“道”相联系,确立了“淡”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到魏晋和唐朝,文人逐步将“淡”的意趣视为个人趣味的一种,但还未赋予其丰富的内涵。直至宋哲宗元祐年间,晚年的苏轼在诗文中系统阐释了“淡”的思想,建立起以淡为美的审美标准,“淡美”遂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理想,“在诗歌、散文、绘画、书法、园林、音乐等多种艺术中实现出来”[16]。苏轼之后的琴学理论,都给“淡”很高的审美地位。例如,宋成玉磵《琴论》中说“盖调子贵淡而有味,如食檄榄”[17];源于南宋历经元明两代的浙派、创立于明代的虞山派,都主张清淡的琴风,虞山派“清微淡远”的琴乐追求,被后世琴人视若圭臬。古琴美学的集大成著作《溪山琴况》将“淡”列入琴乐二十四个审美范畴(即二十四况)之一,详细深刻地阐述了尚“淡”思想,指出“夫琴之元音本自淡也,制之为操,其文情冲乎淡也”[5]601。需要提及的是,上述琴论中的“淡”只承接了苏轼“古淡”的琴乐审美,并未上升到生命哲学境界。
苏轼不仅是“文人画”的提倡者,还是“文人琴”的重要代表人物。“文人琴”视琴乐为修身养性的法门,强调抚琴人自得自适,对琴的旋律不做过分要求,进而消解了琴的音乐性,追寻“无弦琴”的境界。苏轼的“无弦琴”思想上承陶渊明,下启元朝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弦指忽两忘,世事如商参”[18]的琴学理想便是对苏轼《题沈君琴》“匣中”“指上”琴声的回应。进一步说,中国文人千百年来对琴乐的持续推崇得益于“文人琴”的审美理想。在演奏水平上,文人士大夫与职业琴家一般存在较大差距,但从不以此为然,认为琴艺之要绝非于“指上”,而在调心,强调以琴平心静气,追求琴声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李泽厚先生评价苏轼的作品有“人生空漠之感”,认为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19]。
本文通过采取“新史学”范式的研究方法,厘清了苏轼琴学思想的矛盾变迁——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从音乐性到去音乐性,而且以琴这一独特而又清晰的视角,更加全面地呈现出苏轼琴论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为研究苏轼及后世琴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历经时代和境遇的变迁,苏轼的琴学思想从以琴阐述政治主张,到借琴抒发胸中情感,再到携琴归于内心淡然,走向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