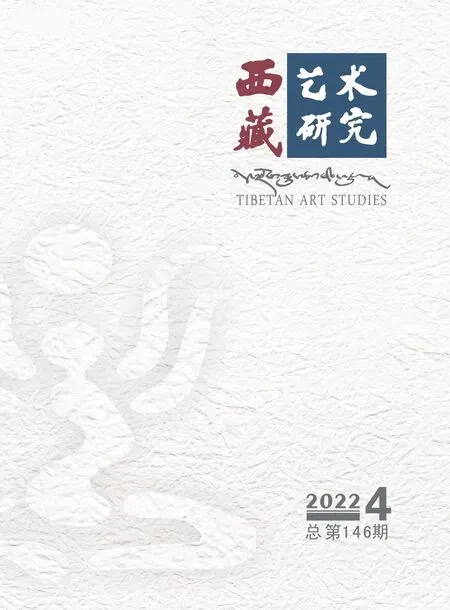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类学田野反思
白玛措
人类学的田野,对远方的书写总是很多。这是一门以研究陌生人社会为己任的学科①赵丙祥.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J],社会,2019年第一期,第39 卷。。即便笔者生活工作的城市离田野不算远,然而我的田野点“牧区”在书写中依旧还是那个远方。当我们不在远方田野的时候,还有一片田野却被忽略了。那就是“自己的日常和这日常的附近”。
人类学家项彪曾提出现代社会都有一种趋势,就是消灭附近。自己身边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一个场景。②“项飙:我们在没有“附近”的世界里生活”https://xw.qq.com/cmsid/20220617A029K800.其实这个“消失的附近”对人类学学者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不但形成了人类学家对远方田野的理解和思考,也构筑了人类学学者从远方田野归来后如何呈现那片空间的叙事过程。研究者时而在田野的剧中更多时则是在田野的剧外,故而怎么能不去凝视这片附近的田野。借用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于我,田野的意义必定也在田野之外。
梦境
最不被纳入的附近就是人类学学者的“梦境”,这个奇思妙想完全源于我的一次阅读经历。2022年,我在偶然阅读多尔斯·艾根(Dorothy Eggan)发表于1949年的一篇文章叫做《人类学对梦境研究的重要意义》③The Dorothy Eggan,“Significance of Dreams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American Anthropology,Vol.51,No.2,1949,pp.177-198.,艾根在这篇文章中提及了他所记录的印第安霍尔比人的梦,以及梦者对其梦境的文化解释。作为人类学家的艾根认为这个他者社会有着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解读梦境的文化体系,艾根甚至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佛洛依德关于梦和象征性的那套理论。艾根的文章让我突然想起一个和我人类学学者身份有关的梦境,霍尔比人会怎么解释我的梦境?这个梦境对我如何呈现“远方田野”的思考和“田野归来”的写作一直产生着奇妙的影响。
梦境中的我走在一片雾气弥漫的草原上,此刻我完成了一次田野访谈,正在赶往去下一个牧场的路上。雾气弥漫,让我有些害怕,心想着万一遇到坏人,应该怎么应付,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我手上还握着一份自己写好的文章,这是一篇草原生态系统存在Naga 的论文。此刻,天色渐黑,寒风袭来,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影子。我纳闷着在这空旷无垠的草原上,会不会是放牧的牧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近这个影子。是一位老人。他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文稿便已通读完内容,与此同时他用意念在我文稿里写进了他想象的几个概念。接着老人递给我一杯水,让我喝下去,我在完全无助的状态下喝下了这杯水。顷刻之间,周围出现了几个张牙舞爪似人形的东西欲置我于窒息状,我用沉默奋力挣扎。另一个我告诉自己“你被老人投毒了”,因为这个老人认为没见过Naga,Naga 就是不存在的。而且老人一直以投毒延续其影子存在的状态。那一刻,我好像从历史的时空看到无数这样飘荡着的影子。我不由得担心自己会不会就这样凭空消失。前方,我看到有一条阳光铺洒的小径,准备走向那里,一个看不见的声音说被投毒之人不允许进入。
梦境里没有空间界定,犹如一个剧场,一个舞台。此刻,我身处在一个环形剧场中。舞台中央是一位拉二胡的老太(有点像某县春晚那个拉二胡的何伯伯)。我旁边的艺术家告诉我,她就是传说中的“魔音小公主”。“小公主”可能是看到我和艺术家低声细语,突然指着我说:你留过学,不能坐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个圆形剧场中走动着类似《盗梦空间》中的那些防卫者,他们负责在潜意识的梦境中审查我残存的意识。我摸了摸头顶,醒了过来……
荣格认为梦可以将我们带到人类文化的昔日状态,就是潜意识。情结以人格化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情结是我们梦中的行事人,面对他,我们束手无策。荣格认为这些情结是我们在意识状态下那些感觉不到的,被否定的,被压抑的意识(记忆、或者创伤的记忆)①【EP146 梦! 潜意识的神秘语言! 荣格心理学维蕾娜.卡斯特-哔哩哔哩】https://b23.tv/k9epmK0.。
我很希望这个梦境就是电影《全面回忆》中那个植入的回忆,但无论如何这个梦的情结显然在意识状态下左右着我行走远方田野的思考以及呈现田野场景的写作思路。因为,非梦场景下的我,在田野期间会下意识的想起那个影子,而在思考如何呈现田野的写作过程中,“魔音小公主” 也会时常飘过我的脑海。
梦是不是一种经验? 我想起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逻辑的那句话“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污名
人类学学者从远方的田野回来,再进入书写话语的那个过程中,脑海中会时常闪现出一个模糊却又挥之不去的背影。但是,你无法去聚焦这个背影,因为田野始终你都没有能够接近这个背影。但它会以非常清晰的轮廓成为田野经历的一部分。我依旧如此清晰的记得草原上的那个轮廓,那位被称为“疯子”的人,那个我始终没敢前去说过一句话的牧民。
初入田野点,我的资讯人就善意的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疯子”,有时会有点“危险”,所以要离她远点。资讯人进一步提供了“危险”的合理性,说周围的人一般都不会接近她。所以让我不要指望和“疯子”有正常的交流,更不要抱有访谈的幻想。
“疯子”是一位70 多岁的牧人,总是一个人窃窃私语,周围人听到过她描述她眼前看到的幻觉,偶尔也出现过攻击性行为。平常,她总是独来独往,天不亮就会背着一个很沉的行囊,拄着拐杖远途,傍晚才回到居所。
在田野地蹲点的几个月,我和“疯子”没有过一句交流,离她最近的几次社交距离就是从她的居所前疾步路过。关于她的故事,需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详述,在这里我要写下的是田野归来我一直在反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走近“疯子”,没有试着去访谈她。这个疑虑让我在田野之后又重读了人类学的污名研究的文献。自己在挪威卑尔根那个细雨连绵的冬季读过的戈夫曼的《Stigma》,前言中那位因面部缺陷而被排斥在正常社会关系之外的16 岁女孩①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现在回想起来,“疯子” 被我列入访谈对象之外的原因竟然与这位女孩非常的类似。当资讯人警告我远离“疯子”时,我的脑海中就下意识的将这个“疯子”和“危险”分类在了一起②Emile Durkheim,Marcel Mauss,Primitive Classification,Rodney Needham(Tra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这一分类是我的本能,还是后天习得中社会建构给我的信息(social information)? 戈夫曼认为社会会建构一套关于“疯子”的信息,让“疯子”这个名称本身代表着不名誉的特征,使它具有超越常规和规范可能性的特征。我同“疯子”周围的人一样,将她的症状(窃窃私语、幻觉描述、过激行为)视为规训之外的行为,将规范化的社会关系对“疯子”封闭起来,无形之中进一步强化其异类特征③Douglas 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Class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66.。这种标签让我在田野始终惧怕“疯子”会冲破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而对我产生危险,危险感让我将“疯子”排斥在了访谈对象之外④Goffman Erving.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Prentice Hall,1963.。我不由得想起北京大学郭金华博士在精神病医院做田野调查时,以及在与那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伟华进行对话时,内心是否曾产生过一丝危险感⑤郭金华.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J].学术月刊,2015年,Jul 07,第47 卷。,我对那些在精神病和艾滋病污名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同行心生敬佩。
2022年,我回访了生活在“疯子”周围的一位资讯人。关于她的信息依旧零星破碎,但其中的一些只言片语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位“疯子”被污名的过程需要从时间的纵向纬度理解她,将她放置在游牧社会史的纵向视野才有可能展示这位污名化主体的具象化呈现⑥郭金华.污名研究:概念、理论和模型的演进[J],学海,2015(02):10.。因为,我想到了自己附近的一位人类学学者被污名化的经历,以及自己附近的那些污名的田野案例都有着时间纵向纬度的原因。
一位人类学者因为用故事解释人类学理论而被冠以“脑子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污名如果从时间的纵向纬度思考,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一直存在的对话鸿沟,人类学的研究因为没有数据和模型的推理论证,故而在“不正常”和“非科学”的分类中①白玛措.撞死一头牛:民族认同在西藏民间的故事[J],中国藏学,2019(1).。
人类学家涂尔干和莫斯认为人类是通过分类建立起一套秩序,并通过这套秩序认识自身和周围熟悉的环境。例如,城市通过分类建立起了一套秩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则通过这套分类熟悉秩序中所包含的意义。在熟悉的城市环境中,面对熟悉这套城市秩序的人,我们的兴趣点通常都会集中在个体上,而一旦面对不熟悉这套秩序的行为或面对不符合我们通常社会习惯的人,我们的兴趣点就会从个体的人转向区域、偏向于群体②Sapir,Edward.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Culture and Personality,edited by David G.Mandelbaum.Berkeley(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赵丙祥,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J],社会,2019年第一期,第39卷:57.。这种兴趣点的转向过程中就有可能将时间纵向角度中已有的偏见叠加在污名化的产生过程中。如,在拉萨乘车,我不止一次听到不同的司机抱怨藏E 车牌的车。在拉萨街头如果看见藏E 开头的车牌号代码,“E”不仅表示所在地的地市一级代码,暗含着在路中央会车时停车聊天,以及其他不遵守城市交通规则,还象征着牧区、牧民等诸多信息。这一信息的叠加过程应该产生自现实生活中驾驶藏E 车的人在城市驾车的行为方式越过了城市秩序之外,这对于那些熟悉这套秩序的人而言,这个越轨的藏E 车司机就代表了他所属的那片区域和所属的牧民群体,于是兴趣点从越轨的司机转移到了区域和群体并完成了污名化的一个微妙过程。
印象派
评论家路易·勒鲁瓦在1863年说:那是一群根本就不懂绘画的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完全就是凭印象胡乱画出来的,其他人也附和着说,这些画家统统都是“印象主义”。在人类学的田野经验中,难免不会遇到类似路易·勒鲁瓦和附和他评论的人,我称之为印象派人类学田野经验。
我的最近一次的印象派田野经验是在2011年,也是我的一次生活在场的“田野经验”③彭兆荣.‘我’在‘他’中[J],读书,2022年2月9:105.。这年,从一次远方的田野归来后,我写了《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这篇文章的田野经验,我自诩为“印象派人类学田野经验”。
这个经历让我想起在游牧世界的柏柏尔人中从事田野工作的拉比诺。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反观田野工作,在其《摩洛哥田野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1977)重新思考了田野工作者和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升了资讯人在田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人类学家与资讯人之间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呈现④盛燕.反思田野作业-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15:197.。然而拉比诺的这种反思,并未得到其导师格尔兹的认可⑤张海洋.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VOL.30,NO.1.。不管拉比诺的观点是否落入了人类学自说自话的内卷空间⑥《悼念: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2021年4月7 号https://tyingknots.net/2021/04/sahlins-rabinow/,至少,格尔兹让拉比诺感受到是人类学专业领域中的“印象派”。
《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 中的主人公曲英多吉是我的资讯人,与曲英多吉的官方接触则要感谢一位知道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的boss,这位和蔼可亲的领导疏通了官方层面的沟通。这一疏通比起那种单打独斗的人类学田野进入,节省了人情时间和枉费的精力。然而,如何获得资讯人和资讯人周围群体的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对象怎样凝视田野工作者。于是,我有了两条并行线的角色:角色A 是要对得起boss 对我的信任,拿出一份沾满田间地头泥土味的田野报告①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角色B 是通过对牧民的理解,绕道来理解作为本土人类学者的我。
远方的田野归来,我完成了递交给boss 的田野报告,也完成了一份突出资讯人在田野过程中发挥重要性作用的文本。
那份递交给boss 的田野报告,非常接近于格尔兹所述:田野作业中从最细微的对话、日常繁琐的事情着手,期望达到更为广泛的解释,力图做到“事实材料”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也是之后)对“事实”的选择、理解、分析和解释②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7.③彭兆荣.‘我’在‘他’中[J],《读书》,2022年2月9 号:101.。Boss 对这份田野报告倒是很满意,当它转到了具体的分管者手中,便开始了我的印象派人类学田野经验。这份田野报告被“降维打击”(借用刘慈欣《三体》 中语)(仅仅是沾满泥土味的第一手资料,并不至于降维打击)。很显然,专业人类学者倾心完成的田野报告如果在非人类学的权威那里一锤否定,且一旦有人给人类学这门学科贴上“资产阶级学科”的标签。本土人类学者终有一死,人类学是错的。也许犹如萨林斯曾打趣过的那样不幸言中,“至少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我们终有一死;二,我们都是错的”At least as far as Anthropology goes,two things are certain in the long run: one is that we’ll all be dead; but another is that we’ll all be wrong④Marshall Sahlins.Waiting for Foucault,Still.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⑤赵蕴娴编辑|黄月.告别“行动着的理念人”: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本周相继离世,界面新闻,2021-04-0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432050468993624&wfr=spider&for=pc)。即便如此,我依旧感谢带我走进“人类学” 这门学科的中国民族学界前辈学者和我的人类学同行2009⑥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基于1978年以来的总结与反思[J].西北民族研究,2009,(03):16-32。“2004年第16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邀请两位民族学家讲课和胡锦涛主席在学习会上号召全党全国都要加强学习民族学知识的讲话,说明中国政府和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已经认识到民族学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27.。
降维打击后,面对凝视着我的资讯人和他的群体,我得有一份文本交代。我想起了那些在权威艺术沙龙落选的画家,却在“落选者沙龙展”中获得了认可。这激发了我将更为抽象的分析放在《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文本中。
《大地艺术家》文中主人公曲英多吉于我类似那个引导拉诺比进入摩洛哥阿拉伯牧民社会的阿里,作为游吟诗人的曲英多吉也是漂泊在“我文化中”的“他者”,也是这次田野过程中我得以进入和了解北方游牧文化最直接的、具体的观察和体验对象⑦彭兆荣“.我”在“他”中[J],读书,2022年2月9 号:98.⑧克里福德·格尔茨.事实之后: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M],林经纬译,2011.。田野的“事实”不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终点,而是这个“事实”之后的“解释”成为田野工作的某一个终点⑧。故而,文本中我通过资讯人展开了对他所处的游牧文化的一种解释:游牧群体面临着当下社会共有的症结:一种与过去社会意义的被割裂和主动的割裂①维克多·弗兰克尔.追求意义的意志[M],司群英,郭本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我不由得想起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的观点:研究的直接焦点不再是我的主观过程的意向对象(曲英多吉和他的牧人社区),或者说甚至不再是个人经验的象征表现(我的田野经验),而是全部书写话语的一个领域,一种文本和类似于文本的领域②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M],J.B.汤普森编译,洪汉鼎译,2021年8月。。
这份文本应该是和牧人的感受对上号了③“21世纪的社科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产,跟百姓的感受对不上号。”谷雨实验室:“独家访谈著名学者项飙:在海外“讲解中国”,拆解中国年轻人的痛点”,2022年8月。,我的资讯人和他的牧民群体、人类学同行、艺术界、文学界朋友的认可中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的“落选者沙龙”,让我经历了一次饱满的印象派人类学田野经验。
2021年,彭文斌教授来拉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曾问过我:“你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怎么活下来的? ”人类学前辈的提问都是幽默中充满深意!那个午后,我猛然对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有了哲学意义上的理解。
……
人类学学者的“田野”除了远方,还不应遗忘附近和日常。因为,这附近和日常往往会影响如何最终呈现那远方的“田野”。戈夫曼以剧场延伸的人类学理论中将社会活动分为台前台后④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我将田野的最终呈现理解为台前的那部艺术作品,而台后则可能有一连串与台前行为不相关的事件,附近和日常的田野就好比这些发生在台后的事件,但它们也影响着最终呈现给读者的那个远方的田野。在这个整体的田野过程中,那些萦绕人类学学者的灵感、那些让荒诞黯然失色的生命意义便是希望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