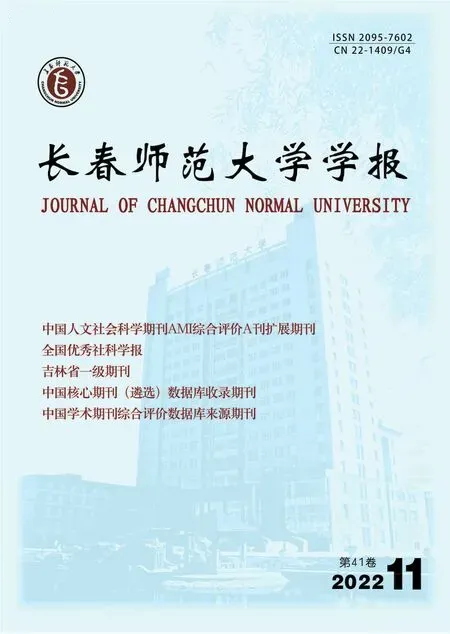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深度翻译的实现策略
王 玉
(太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认知语言学是基于人脑思维过程以及认知模式,对语言的了解、习得、应用等方面进行探索的学科。它是融合了认知心理过程的语言学学科细目分支,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遵循认知学派的理论逻辑。认知语言学与深度翻译具有融通之处,这为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展开深度翻译的探索提供了基础[1]。一方面,深度翻译更侧重于从感性层面对翻译效果进行衡量,缺乏相对理性的量化衡量标准以及方法论框架下的规律总结,而认知语言学对认知过程的探讨在一定的弹性之余讲求范式的摸索与总结。由此,认知语言学为深度翻译的方法论探索提供了参考,深度翻译的研究为认知语言学的深化研究提供了议题,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注重从不同路径对同一认知过程进行研究,为深度翻译的策略提供了更多的切入思路。换言之,深度翻译的实现需要结合认知语言学丰富情境,进而达成翻译目的。因此,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借鉴其研究范式与逻辑框架探索深度翻译的实现策略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一、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深度翻译现状
在认知语言学架构下,深度翻译包括两层内涵:一是达成翻译语言转换的基本目的,二是对“深度”的追求。在深度翻译的内涵中,深度不仅是对程度的形容,更包含最终结果的衡量标准,即需要摆脱字面直译的生硬,站在沟通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高度下使译文读者真正理解原语言表达的真实内涵[2]。目前国内外有关深度翻译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入手。
一是停留在概念辨析与内涵挖掘层面的研究。该类研究对深度翻译“是什么”有一定程度的阐释,回答了深度翻译“从何处来”的问题。深度翻译与人类学与翻译学均有渊源,可以说深度翻译是以翻译学为工具探索人类学中沟通表意的本质,抑或可以解读为人类学为深度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撑,而翻译学为深度翻译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是结合文学作品探索深度翻译效用的研究。首先,此维度的深度翻译充分关注翻译特征中内隐与外显的区别,在翻译中注重对内隐含义的挖掘。其次,此维度下的深度翻译开始意识到文化异质性对翻译的桎梏,在深度翻译过程中考虑结合文化差异进行更贴切的表述。此外,此维度下的深度翻译在表意准确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通过异质文化的陌生化审美再现达成更生动的呈现效果,即在译作当中,深度翻译不仅注重理解的达成,也不断深入探索将丰富多彩甚至译作读者不曾接触的世界进行更生动的呈现。因此,此维度的研究对深度翻译的实际操作方法有一定的理论探讨,但仍浅尝辄止[3]。
三是从反向维度切入的研究。此维度不回答深度翻译的效果意义以及“如何做的”具体操作性策略,而主要以批判性思维指出当下深度翻译的局限。该维度的研究认为,深度翻译最典型的局限在于过多依赖进一步的解释以达成翻译,这容易让翻译本身成为解说而磨灭语言本身的魅力。通过脚注、尾注、附录、参考文献等种类繁多的注解完成翻译,让无论何种文种的翻译都形成学术论文式的标准,精准有余而韧度不足。
二、基于补足缺位的深度翻译
(一)补充类符概念
在深度翻译过程中,补充类符概念的目的在于直接通过相关信息的激活完成缺位补足。首先,需要厘清类符及关联概念。从本质上讲,类符概念是相对于形符概念而存在的。形符,顾名思义,即把象形直接作为符号代表的内容,在翻译中通常表现为内容的本体性含义。无论是原文抑或译文的读者,通常对形符有一定的先验直观了解与认识,形符以客观实体投射在可以为个体所觉知的意识层面。在此基础上,类符的含义不言而喻。与形符相对应,类符的意义表达通常不以直接的字面形式出现,而是具有更突出的象征指代意义,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更深层的因素。类符的缺位补充对深度翻译实现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一方面,类符的有效补充能够使深度翻译更到位,在逻辑上进一步联通前因后果,促进读者对描述对象性格、情感态度等深层次因素产生更多共鸣;另一方面,类符的补充使得文字的表达更加委婉有深意,为读者预留更广阔的思考想象空间。形符的表达是单面体,而类符的表达是多面体,同一形符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下对应的类符可能有所差异。类符的补充和点明既使读者摆脱了盲目猜想,也为读者的深度思考和想象指明了方向,搭建了整体框架,有助于读者对译文进行更深的加工领悟。
类符的补充方式灵活多样。首先,最直接便捷的方式是通过副文本形式展现类符内涵。此种方式对原文和译文所对应的读者之间文化背景或经验层次差异较大的情况较为适用,能够将有效信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补充到位[4]。同时,对形符与类符之间差异较大,较难依托读者自身经验进行探索想象的情况也较为适用。其次,可以通过形象启迪补充类符内涵。如老虎,在中英文语境中形符均指向某种猫科类食肉动物,对应形符的生物学属性;类符中老虎的含义指代其在捕食等行为中展现的行动迅猛、力量雄厚。因此,在深度翻译中,只要可以构想老虎的外形与动态,对其力量性内涵的把握自然水到渠成。同时,深度翻译中通过定语等形容修饰成分的加入,老虎“攻击性”等类符含义也进一步引申补充到位。此外,更高明的深度翻译中,还会通过谐音等进行类符补充。如例1采用补充缺位的方法进行深度翻译,用柳树柔软随风的形象表现漂泊无依,并以与柳同音的“留”表达挽留惜别之意。
例1 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漪。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王维《柳浪》)
a.Willow Waves
Lacy trees, touching in separate rows,
Reflect in clear ripples upside down.
Do not copy those by the royal moat
That suffer from parting in the spring breeze.
b.Willow branches were commonly snapped when parting from a friend, “willow”(liu)
being homophonous with “stay”(liu).
(二)补充隐喻意义
形符与类型的相对概念通常以词语断句为主,而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中,常有蕴含在整句乃至篇章中的寓意,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类比引申实现深度翻译。最常见的是文化典故中的隐喻意义。隐喻不同于修辞手法中的比喻,通常以达成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为目的,其更侧重对不可言明的倾向性态度进行表现。隐喻的介入能够提升内容的呈现效果。一方面,隐喻的运用使文本呈现出对仗、押韵等表现效果,从而提升语言表达的艺术性,这在汉语古诗文中最为常见;另一方面,巧用隐喻打造内部沟通语言,有利于节约文本篇幅。隐喻能够用简短的语言象征指代某些情况,而无需再次赘述前因后果,只有对原文文化背景及历史典故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才能明确其中的真正含义。
在深度翻译中,隐喻意义的补充方式较为灵活。一方面,深度翻译中可绕过表意直译而直接体现隐喻的真正内涵,如杜甫诗歌“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并非表现在东面庭院内踱步又在南面城楼上远眺的表层意思,而是通过刻画晚辈跟随父辈学习开拓视野的回忆画面,表达作者对父亲的回忆与怀念。据此,可在翻译中直接表达子承父教、怀念先祖的隐喻意义,而无需再从东、南的物理空间位移角度进行生硬的直译。另一方面,深度翻译中对隐晦的内涵进行拆解,使隐喻以相对浅显的类比形式出现,也是常见的隐喻意义补充方式。如杜甫诗“谬知终画虎,微分是醯鸡”中表意为“虽然愚笨,但仍然画出了老虎”。如此翻译容易让读者一头雾水,更难以与上下文进行衔接[5]。究其原因,在于中华文化中“画虎类犬”的典故在外文中并未对应概念,而虎和犬的形态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在生物学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与界线。因此,采用“画虎类犬”的降维比喻自然能够使读者明了想象与真实的鸿沟以及能力与实力的差异,进而达成深度翻译。
三、基于框架建立的深度翻译
认知语言学中强调以图式为认知的基本单元,即在语言理解中,读者往往将文字所对应的形象转化为头脑中某个类别的概念,并激活与之相关的概念而形成整体认知。而读者的个体认知往往随其生活经验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产生动态变化,在将新概念纳入认知框架后,相应的图式也会发生同化并不断完善。当图式的改变程度较大以至产生质变时,认知框架会发生层次性调整而达到顺应。在深度翻译中,经典著作原文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被译为多语种传播,这导致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的认知框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两者的基本认知图式难以匹配,认知框架难以接洽,理解自然也存在偏差。据此,需要基于译文读者的认知框架进行搭建与重塑,以促进深度翻译的实现。
(一)激活框架要素,理顺框架逻辑
认知图式的构成具有层级性,在主概念下由细分类目进一步组成认知框架节点。翻译理解中的阻碍部分源于译文读者对概念的认知存在差异,从而造成某部分图式框架节点匹配错误,影响对后文乃至全文的理解。深度翻译正是需要通过认知图式中框架要素的激活实现“画龙点睛”,促进框架逻辑的理顺,帮助译文读者把握理解关键点。
在具体的实现策略中,深度翻译通过打通认知矛盾点激活框架要素。如“安可辞固穷”一句中,采用反问质疑的语气表现出对穷困潦倒现状的坚守。其中,“安可辞”是“怎么可以辞去”的意思,而“辞”表意为“推辞、告辞”,有主动摆脱现状之意,反问的语气进一步强调了对穷困的坚持,甚至表现出对主动请辞的责备。在外文化的读者眼中,此处与个人主义框架下的认知图式难以匹配,在崇尚自由追求自我的理念下,对摆脱穷困的苛责让人疑惑。而实际上,深度翻译正需要通过阐释文化根源回答这一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难题,击破理解矛盾点。深度翻译中需要点明“固穷”在儒家文化中是作为君子品格而存在的,由此打通集体主义文化认知框架搭建的要素,理顺逻辑思路。解决了此矛盾后,全文的理解更为通顺,译作读者对作者在彷徨中的坚守与选择更能够产生共情,对贯穿全文但是以君子大义为根基的文化情感也有更深的把握。
(二)联通框架要素,建构框架整体
原著作品的精髓往往不能仅由只言片语体现,深度翻译还致力于促成上下文框架要素的联通,以此构建整体性认知框架,进而促进译文读者在更高视野下领略文本要义。
深度翻译联通上下文中同类要素建构框架在许多作品中均有体现。如杜甫的《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原著作品刻画主体人物并流露敬仰之情,以此表达希望得到关注与提携的投诚之意。而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的译作读者面对全文对主角的描述,而无一笔点透作者自身,可能仅感受到原文对主角的赞美褒扬,难以体会更深层次的诉求。深度翻译则细致刻画注解了主角描写中提到的“高朋满座”“笔耕不辍”等内容,同时用美玉、亮剑等比喻主角的人品与文辞,使主角的形象更加生动立体。通过上下文多次联动,读者在通读全文后逐步搭建了用溢美之辞以扬所求的认知框架,对作者立场的诉求更容易有进一步的理解。至此,在下文提及“桃阴想旧蹊”之处,深度翻译中联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自然让渴求赏识、一展抱负的内涵跃然纸上,水到渠成。
四、基于内涵凸显的深度翻译
(一)以转喻凸显内涵
如果原著中运用比喻形式表现内涵,但译文文化中直译比喻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化意象,直译喻体便无法承载形象化功能。因此,深度翻译中常采用转喻形式,以期在最大限度还原原文修辞韵味的同时,将喻体转换为更容易被译文读者所处文化接受理解的对象。转喻的使用并不是比喻的简单降维,所转换的意象需要与原文保留一致的情感态度,保障阅读的顺畅。杜甫诗歌的深度翻译对转喻的运用炉火纯青,如诗人用对比手法讽刺小人当道、人情冷暖,以此反衬自身处境的凄凉。但在译文的文化语境中,原作所用的南山豆苗、儿童项领等寓意均无对应意象。因此,深度翻译中借陶渊明诗歌转喻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以本该培育的豆苗稀落衬托杂草的繁茂,表现鸠占鹊巢的无奈以及本心的背离。
(二)以隐形概念域凸显内涵
翻译中常有同一认知概念域包含不同层次内涵的情况。显性概念域的点明较为容易,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画隐形概念域的内涵,则颇考验深度翻译的功底。“仙李盘根大”一句中,仙李盘根错节,翻译中通过对现实场景的描写很容易表现植物繁茂的视觉画面,但实际上“仙李”的隐形概念域中还指代盛唐王朝的李家天下。在深度翻译中通过注解挖掘这一原本隐形的概念,才能真正让译文读者读懂原著。
(三)以深度语境化凸显内涵
翻译的魅力在于实现不同文化语境下语言符号的转换及内容思想的互通。相同的文字中哪怕标点、语气等有细微差异,也可能让理解谬以千里。深度翻译中内涵的凸显可以通过深度语境化达成[6]。一方面,厘清语境,缩小概念域,能有效促成深度翻译。如“文理”一词本身囊括的内涵较广,通过注解缩小其概念域,可以使某一应用语境下“文理”的内涵与关系得以清晰。另一方面,减少偏离性解读也能从深度语境化角度促成深度翻译。此方式更侧重从反向排除角度凸显真正内涵。如“鹤”意象在中华文化中常喻指长寿,而深度翻译中通过对此寓意的排除,表明在某篇章中“鹤”仅指代自由无拘的活动,由此有效缩短读者的理解路径。
五、结语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深度翻译内涵精深,探索及丰富其实现策略对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从整体视野探讨了深度翻译的研究现状,并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讨了补足缺位、框架建立、内涵凸显等具体的深度翻译策略,以期有效消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差异,实现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互动。
——以“人”“彳”字部为例
——以满洲里学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