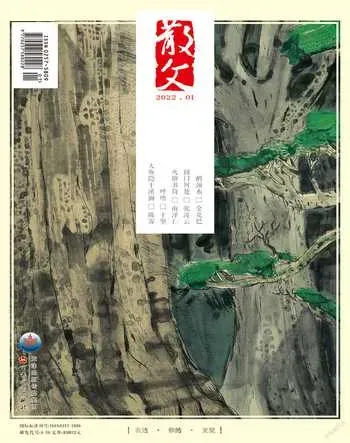鹅颈水
金克巴
鹅颈水是茅洲河一条支流,遇见它纯属意外。因为平日里,我大抵只沿茅洲河的岸边走走,对它的支流一直知之甚少。我住在茅洲河上游,探访源头自然不是问题,但行到水穷处却是另一回事,我总是顺流而下,半途而返。即使那样,我还是感受到了王子猷雪夜访戴的那种意兴,并最終意外地踅入了鹅颈水,邂逅了燕处于鹅颈水与茅洲河交汇处的鹅颈水湿地。半年来,我在这个小小的泽国“收获”了一百多种陆生植物、三十多种水生植物,事实上决然比这更多。还有数不胜数的飞鸟鱼虫。
就在几年前,这条支流还饱受訾议,因为它实在丑陋得令人生厌,河道里充斥着垃圾和浊水,刺鼻的气味令行人不得不匆匆逃走。
直到有一天,人们良心上有所发现,拯救鹅颈水便提上了日程。接下来不仅仅是拯救,且还着力于把它打造成风光旖旎的湿地公园,依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叫鹅颈水。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是悠远的农耕文明的一个写照,那时,还没有人造的毒液源源不断地汇聚、横流。时光的钢铁河流固然不会倒流,但我还是憧憬那消逝的次第能够重现。
我的生活便这样停留在暂栖的“鸽笼”与鹅颈水之间:一个是位于十二层的空中楼阁;一个在两河交汇区,浓缩大地的诗情画意。白昼,我在空中楼阁中筑梦;傍晚,我自然不放过去观察月相变化的机会。面积并不太大的鹅颈水,是一方匠心独具的所在,汇聚了许多我所挚爱的草木。水,依然是它的主题。水,也是生命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们逐水而生,最后连感情也浓缩成喜悦或悲伤的泪水。
水真好。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在我看来,水具有非凡的治愈效果。这些日子里,一泓水总让我通体澄澈,时时浮想联翩。
老子珍视各种消极和不利的因素,譬如:反、无、无为、静、虚、下、后、曲、贱、少、枉、无知、无欲……如果是死水,或许它真的能开出灿烂的花来。那就是昔年我在茅洲河的塘下涌段所看到的:水面浮泛的凤眼蓝纵情地绽放,似乎要让此地即便在地球史上某个稍纵即逝的时刻,也绝不被丑恶独自开垦。在老子看来,所有消极和不利因素都意味着已经播下了反转的种子。正因为如此,才“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当然,低洼也一定意味着丰盈。试想,如果这个夏天是我人生的洼地,是否也意味着七月流火之际,我会迎来一种别样的丰赡。
我开始从心底铭感这些惘然无措的日子,是天地间至为玄妙的缘分把我带到这个安谧的暴风眼,喧嚣在小小的泽国之外席卷一切,我大可以将身心搁置于清流潺潺、蛙声阵阵之中,足以抚慰过往的遗憾。
湿地,而且是人工的,这是一个有些许遗憾的存在吗?除非在这个生命之火延绵不绝的星球上还存在全然原始的湿地。但我相信,在工业文明还不曾侵入这片土地的肌体时,存在着相对原初的湿地:野草在沵迤的原野上蓬勃生长,河流在大地上纵情流淌。鹭群无比庞大,当西天铺满瑰丽的巨幅晚霞时,它们就回到倚门倚闾守望着的大树上,不时发出低鸣——那是惬意的心声哦。时至今日,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南国海滨城市,在人们悉心保育之下,得以幸存下来的相对原初的野地已俨然是最具魅力的宝藏。所以,在我看来,即便人工湿地,也是弥足珍贵的,它意味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也许有一天,人们蓦然回首,就会发现,二十一世纪之初,倡导与建设生态文明是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纪最可称赞的理念之一。但还剩下一个玄秘的问题:地球的生态是否可以由人类牢牢地掌控?谁能保证人类的陟罚臧否,能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对我来说,步入鹅颈水,是惊喜的,惊喜于意想不到的景致。但我不敢睥睨一切,从而认为眼前的月地云阶,一切理所当然。对于鹅颈水来说,人们曾是加害者,现在依然不能尽释嫌疑,人们所能做的,唯有加倍赎罪,祈求美好的生态回归。步入鹅颈水,我是晏如的,我终于发现,当人们放低姿态,怀揣一份美好与自然万物真诚相处时,也必定会收获美好。人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应是暴戾恣睢的施虐者,而应是谨慎的建设者。接下来还可以重新定位,将自己视为民胞物与的偶在者。
因为民胞物与,在生存权上,我并不比一只巨型的蜗牛更重要更理直气壮。多雨时节激活了它们的生机,它们不时横穿赭红的透水混凝土步道,是去幽会,还是访友?大概不会像初出茅庐的李白一样,寻人不遇,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蜗牛世界,岂止是惆怅,还有着须臾难测的祸福,一次远行,或许就意味着快速滑向末路。总有一些蜗牛无辜受难,硬壳亦不足以保护它们。当我慢跑时,会尽量避开不断漫行的蜗牛,温柔地对待它们,一如这个季节的南风凉爽地迎着我。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这个世界,是奇妙的。同样奇妙的,还有淡淡的愁绪,轻轻地吹拂着我,就像一块明矾,让我的心澄净下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如老子所珍爱的那些不利的或消极的因素,把我带到了安谧的妙境。悲伤如一块小小的明矾,当其被投放到我身上,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让我脱离了自己的身体,想到一些形而上的问题。
我蹲下来,观察一只非洲大蜗牛的走向,从名称上我大概知道,它来自遥远的非洲,来自于不经意的挟带,从此便在东方大地上顽强地生存和繁衍,现在几乎把足迹撒遍了这个南方的绿色襞褶。正因为其寻常可见,我曾在一个公众号上收获提示,不要随意触摸这种非洲大蜗牛,因为它携带着多种病菌。我眼前这只大蜗牛,迟缓、坚定,似乎顺应着某种召唤,向另一片草坪进发。生存和死亡,从来都不会使它耿耿于怀。因此在我看来,它的行动既盲目又可敬。但它绝不会苟同人的文化心理和视角。我和它,还有周遭林林总总的生物都生活在各自的平行世界里,拼凑成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
我会记得,这个令我怅然若失的、怀着失路之悲的夏天,在人生旅途的洼地里,在一个叫鹅颈水的地方,喜获了一沓草木笺。它们是构成这片湿地的有机部分,坚定地站在天下至为柔弱的水的一边,巧妙地与一切恶浊作战。我认出了它们:大花美人蕉、香蒲、水葱、千屈菜、黄花鸢尾、再力花、风车草、灯芯草、菖蒲。它们在表流湿地上颇有仪式感地列队,让我想到一个文友的水彩画,在画面中,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整齐地向上竖起,充满了生命的力度,具有一种向上的风容,简洁而不失优美。
我迫不及待地向一丛香蒲靠近。它们是我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我在儿时就跟它们相识。其时,它们悠然地生活在村庄附近的一小片泥淖里,那是真正的湿地,不种庄稼,鱼在在藻,依于其蒲。我总讶异于香蒲那形似蜡烛的肉穗状花序。不用说,它是山里孩子取自天然的玩具,不須各种电路连接,只是充满了野趣。奇怪的是,这种蒲草虽然美其名曰“香蒲”,其实闻起来并不香。被归入香草之列的蒲草名为“菖蒲”。
在我看来,菖蒲堪称横空出世,拨开野草卓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古人为了表达对菖蒲的由衷喜爱,遂将它人格化,还为它过生日。“四月十四,菖蒲生日,修剪根叶,无踰此时,宜积梅水渐滋养之,则青翠易生,尤堪清目。”我揣想,菖蒲生日正是它新生的开始。从那天开始,它就缓缓走进文人雅士心里,成为他们的案头清供。
岂止是案头清供,还是古代的神草。每逢端午,菖蒲就被人拿来与艾蒿扎在一起插于门上,据说辟邪驱疫。在我儿时,这是一种寻常可见的习俗,让我的周遭都浮荡着独特的灵氛。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并非是一种蒙昧,而是人世不可全然沦丧的虔敬和慎独。只可惜,在我有生之年的上阕,端午插艾蒿和菖蒲的习俗业已消失。这种神草有水陆之分。苏东坡酷爱这种香草,毕生为它写下三十多首诗。
二十九岁那年,苏东坡在关中的山中邂逅了一株野生石菖蒲,见它虽然出自瘠土,但细叶芊芊,有着一种令人挪不开视线的鸿渐之仪,从容而淡然。苏东坡将最好的褒词献给它,誉之“千岁灵物”。自此,苏东坡再也没有让它从自己的世界走失。他曾经写下《石菖蒲赞并叙》,惊叹于石菖蒲只需一点清水、一块石头就可以生趣盎然,也不知其生存玄奥之所在。在他看来,长于石隙的草木,一般都需要些许土壤以固定根须,像石韦和石斛虽然用不着土的供养,可一旦挪到别处就生机尽丧,“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五十七岁,九月,他被流放到风物殊异的岭南,继续饱尝文章憎命的酸甜苦辣,而进入晚境,那种滋味更加浓酽。既然命当如此,那么就乐天知命,生寄死归。当然,犹不失对命运的玄秘和荒诞的理性省思。倘若我们能够善待一切众生,尊重它们独有的神秘特质,自然也可以对人类命运的神秘性有所启迪。途经广州蒲涧寺,泉石膏肓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放过那一方神奇所在,前去寻幽探胜。人称“苏海”的苏东坡自然知道,此地是安期生隐修的地方,鬼出电入的安期生以菖蒲为食,最终飞升成仙。在这里,苏东坡又见到了酷爱的菖蒲,留下了“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的诗句。
九百多年后,我在岭南一个叫鹅颈水的地方遇见菖蒲。在“欣逢”中,似乎也与苏东坡相遇,因为我的那股心流亦源自眼前这种香草。王羲之说得妥帖极了:“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相信吗?我们这些被抛入隔世的人,将以灵犀相通等各种奇妙的形式在某个时刻相遇。因此,即使生命已经完成,那一脉气息依然长存。
在侘傺无聊的日子,大自然的尤物慰藉着我,它们欣然地簇拥着我。不用说,这个绿色的王国一定少不了高大的乔木,人们请来了木棉、菩提、榕树、玉蕊、黄葛树、紫花羊蹄甲……还有一些本在灌木之列,得益于南方旺盛生命力的勖勉,一不留神就长成了小乔木,比如含羞树。我宁愿相信那只是一种误读——人往往有一种谵妄的习惯,总是用文化心理去看待周遭的一切,以至于让我以为,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澹然和陶然的意味也是我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某个时刻,我沉湎其间。李易安所谓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对我来说,就是时而惊动几尾游鱼,惊飞会飞的花朵——蝴蝶。那种动态也让我有所触动,原来即使身处人生洼地,我跟世界依然还保持着互动,微妙而和谐。我感到自己还没有全然沦为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这个世界中并没有局外人。希望这不是一个自负的错觉,而是实况。我不是自己命运的局外人,我是它的亲历者,我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时间没有失去,只是已经完成。而我尚未完成,还将继续撮盐投水,投入喧嚣的渊潭。
傍晚,西天早早就升起了上弦月。我站在鹅颈水一个圆形的荷塘边。鱼在水里游来游去,蜜蜂穿梭在由荷花与美人蕉构建的妙境里,池边的玉蕊树上长长的花梗已经挂果。走在栈道上,成片的再力花,纤纤花茎擎起紫色小花迎来了许多蜂鸟鹰蛾,暮光中,它们伸出长喙勤勉地探寻着花粉……它们都沉湎于各自的世界——在我周遭,存在着无数的平行世界,与我的世界并行不悖。只是,它们并非如自作多情的人所以为的那样,把人视为万物的唯一尺度。
没有谁是谁的中心。每个生命都有一部无法置身事外的生命史。只有执笔者才能决定它是丰赡还是贫乏。
记得几年前,我在茅洲河一侧的田寮暂栖下来,其时,这条河已经被恶浊的工业污水给扼住,一旦靠近,就只能掩鼻而走。那时我哪能料想得到,有一天她竟可以出落得如此清丽。意外中的意外还有,河的两岸都为之蝶变,沿途都是怡人的景观,这才有了鹅颈水湿地。在溶溶月色之下的鹅颈水荷塘边,我再一次想到老子,他从不排斥不利因素,因为他知晓,卑微其实难掩高贵,低洼也许意味着丰盈……
老子能够打动我的,除了对于柔弱的青睐,还有他耄耋之年下落不明。在我看来,那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迷局,而是整个人类的终极之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据说,老子过关并未走远,而是隐居在秦国或陈国。出关时,特别尊崇老子的尹喜极力挽留老子,央求他为世人留下一部大作。担任过皇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并不悭吝,洋洋洒洒地写下五千言。幸运的是,获得真言的尹喜并未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据为己有,而是对自己的职位毫不恋栈,从此一心追随老子。后来他也在自己思想的藤蔓上结出了硕果,他的“贵清”是早期道家最主要的思想之一。
水往低处流,水是深壑与低洼坚定的支持者。正是水成全了这里,让它挹着一泓清澈,有了深度,闪烁着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