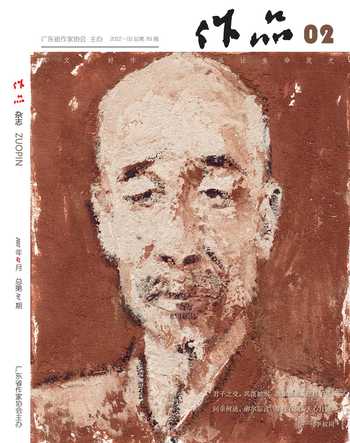浅醉北疆(散文)
储冬爱
2018年年初,辣妈们着手策划俄罗斯暑假游,群里欢欣雀跃,熟悉的苏联歌曲轰炸数日后,有了不同的声音,“俄罗斯小偷多”,“世界杯人满为患”,更有甚者担心美、俄大战!最后妥协的结果: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改为“新疆烤全羊”,似乎在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一样可以看到“三套马车”,了却“山楂树”之愿。
“烤研”5人组
“大美新疆”“大美青海”之类的赞美在朋友圈泛滥成灾,在我看来,若不是偷懒者的行为,便是词语匮乏的表现。神州之大,哪里的夕阳不绚丽?没有良友,没有新朋,风光再美,终究只是一趟乏味的苦旅。
6~8人组合是我们“3861”团的固定自由行模式,2017年普者黑之行5位“大妈”单独成团,一路莺歌燕舞,把酒言欢,一度招徕了正在厨房“kaoyan”(烤羊)的彝族厨师,“烤研”的梗神一般地被带到了新疆。
多年路上的磨合,“吐槽”的套路彼此心知肚明,焦点往往是司机,既要拿他开心,又要讨他欢心,这可不是一己之力能办到的,所以分工明确:话题常常由“八卦姐”Y主任抛出,貌美能干的P团长更新、补充,我专事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最贤的妻L老师长于“补刀”,往往神来一笔,庄重自律的W总能在关键时刻把握方向,把我们拉回正道,“吐槽大会”戛然而止,也完美收官。
当然,正事我们干得一点不差,经P团长和亚伯兰庄园谢庄主多番筹划,“烤研之行”既能沿独库公路线且行且止,看山河变色,也可入天山腹地,叹人间烟火,9天行程满满当当,完美无憾。
第一次见司徒是在乌鲁木齐机场,我们刚到出口,一个刀郎模样的汉子便准时出现在接头地点,休闲帽、双肩包、黝黑的皮肤都是户外达人的标配,这是庄主口中的“老帅”无疑了。没有握手,没有寒暄,咧嘴笑了笑,便拉起离他最近的行李箱大步流星往前走。大家在后面紧赶慢赶,手上拖着箱,心里都压了一块石头。
行程第一站: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大巴扎。一路上,大家都一反常态地矜持,小声嘀咕时都要递个眼色,坐在副驾驶位的Y姐晕车症还没发作,偶尔能和司徒闲扯几句,刀郎的歌声(好在有刀郎)若隐若现,音量小到只有司机位能听分明。司徒认为刚下长途飞机的乘客仍需要在车上睡一觉?
大巴扎传说已久,但百闻不如不见,完全没有让人驻足购买的欲望,倒是风格浓郁的建筑式样和装饰让人耳目一新,置身其中,仿佛闯入阿拉丁的神话,我们这些中土的汉人成了真正的少数民族。
离了方向盘,司徒还是那个司徒,少言少语,与我们若即若离,但只要见我们谁摆POSE,他立马端起相机,抓拍、“偷拍”,一路上的风情全在他一手掌握,这么称职的摄影师叫人没法不喜欢。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相处渐入佳境,虽不曾对过话,但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对号入座,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是时候把话题撩到他身上了。
“庄主在家安逸,你干吗要出来奔波?”
他嘿嘿一笑:“我没本事,只能给庄主打工。”
如此高明的冷场没几个人能应付,但我们不甘心。去八卦城的路上,我们规定轮流放歌,司徒也不能例外,他说车在盘山公路上唱歌危险,这道理我们哪里不懂,不过是想逗他开心,谁会当真呢?驶入平路后,他竟主动唱了半首摇滚歌曲,把辣妈们全惊呆了。
在夏塔古道,司徒陪我们中的一个骑马,其余4个坐区间电车巴士,维吾尔族司机热情得“不靠谱”,原本只是想请他帮忙拍个合照,他对我们的姿势“指手画脚”,还混入我们的队伍,勾肩搭背,载歌载舞。司徒前来会合时,我们假装责怪:“你都不管我们,万一遇上坏人咋办?”
司徒朗声大笑:“遇到你们4个,我倒是替这位维吾尔族兄弟捏一把汗啦!”
所以,任何时候,不要低估一个貌似沉默的理工男,他可能只是想做领队里最好的司机。
行走独库公路,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风景,而是尼勒克县一座直插云天的纪念碑和布满墓碑的陵园。筑路十年,168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因为雪崩,有的因为塌方,年龄最大的牺牲者58岁,最小的18岁,2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因放不下長眠于斯的战友,复员回家的老兵陈俊贵返回天山,自愿看护乔尔玛陵园,义务讲解30多年,风雪无阻。时机不巧,当天没能在纪念馆见到那位情深义重的老人。
陵园位于纪念碑旁的小山上,谈不上荒草丛生,但也足够简陋,穿行其间,只恨自己身无一物,不能像旁边那位中年游客(或许是战友?)敬上一根香烟,彼时彼刻,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身体民俗学仪式感的重要性。
所谓“最美公路”实是躺下的丰碑,任何小资小调都显得不合时宜。在纪念馆内,牺牲者一般都有生平详细介绍,但仍有几位只写了“情况不详”,一位“籍贯广东”的年轻士兵,信息寥寥,至今没能找到家人的下落。
山上的野花开了又败,何时能盼得亲人来?
琼库什台,一个哈萨克族的小村落,借“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光环,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农家乐,虽在天山深处,游客不至于蜂拥而来,但干净整洁的民宿还是抢手,我们歇脚的地方有一间“树上的房子”,全村别无二家,必须提前预订,老板是能干帅气的哈萨克青年阿杰,和司徒完全反着来,热情泼辣,见招拆招,看我们第一眼,就冲着司徒说:“老兄这团带得不容易吧,全是漂亮大姐啊!”你看,这样的店家不火谁火呢?阿杰还有个得力的表妹,切菜、洗碗、下厨一脚踢,汉餐手艺相当不错。
休整一晚后,我们打算徒步后山,俯瞰全景,但没走多久,遇到各种牵着马匹的牧民,操着当地特色的普通话:“骑马má?”“骑马mà?”,直直望着你,诚恳、急切。最后我们挑选了一老一少,大叔身高腿长,略有佝偻,小男孩结实黝黑,眼睛澄澈入水,都是让人没法拒绝的主。
8岁的阿德热斯,家有良马20多匹,拿过赛马冠军,哥哥生病去世后他升为老大,既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帮家里挑大梁,利用假期赚外快。他显然见过“世面”了,十分健谈,不像一般的孩子只停留于一问一答,让我们了解他的情况后,他会主动抛出问题,比如“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有孩子吗?”W总逗他:“想不想去广州读书?有个阿姨很喜欢你哦。”他让阿姨指认:“哪一个?”然后,以非常老到的口吻说:“这个可以。”“你去问问我的爸爸。”我一阵狂喜,翻出儿子8岁时的相片,两相对照,竟有几分相似。我试探性询问能否去他家做客,他连连点头,策马飞奔,说回家报告父母,迎接不速之客。
阿德热斯一骑绝尘,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穿越一个大草场,来到另一个更大的草场,最高处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我暗暗为自己的鲁莽后悔,不知该不该把一个8岁孩子的话当真。到达后,疑虑全消。阿德热斯家新添了一台打草机,他爸爸和一群男人正围着新家当热火朝天地讨论,对我们的到来一点不意外。马奶、点心、水果早已备好,就等客人入座了。他妈妈满脸羞涩地示意我们进屋,自己忙进忙出,让阿德热斯在屋内陪客,传话翻译,中间还当着我们的面给了儿子一个极亲昵的吻。虽然陈设简单,卫生粗糙,但温馨溢满了这个小康之家。回来的路上,阿德热斯成了我们“吐槽”的热点,如果不是对牧民生活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想象,又怎么会生出之前那样的非分之想呢?
告别琼库什台村,我们匆匆赶赴下一站,当晚,阿德热斯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段语音,邀请我们再去骑马:“我妈妈说不收你们的钱。”
阿不都·哈米提,那个热情得“不靠谱”的司机,以前跑南闯北,普通话在遇到的维吾尔族人里算最流利的了。当天与我们厮混几个钟头后,当即邀请大家次日去他家吃午饭。鉴于阿德热斯家的经验——大人之间语言不通,实在不便久留,我第一个表示谢绝,他执意相邀,为表示诚意,晚上给我发来多个视频,画面里他胖胖的夫人忙里忙外,一副杀鸡宰羊的架势,看起来似乎正在做待客的各种准备。
第二天,我们在解忧公主墓逗留的时间久了些,超过了与哈米提约好的时间,他打来多个电话,说夫人在村口恭候已久。如此盛情,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哈米提的家位于夏塔古道旁,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村落,一家一戶,沿马路整齐排列,完全不是汉族传统村落那样前水后山或依山而上错落有致的布局,更像内地一个小城镇。正苦于没有门牌号码时,遇到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热情地把我们簇拥到哈米提的家门口,胖太太果然在门口张望,我主动上前与她拥抱,这就算是确认过身份了。
进了院子后,哈米提的电话再次响起,邀请我们入屋就座。夫人似乎接到了指令,拿着一段比手腕还粗的小绳子,追赶院子里的老母鸡。看来,我大大会错了晚上的视频,所谓的“都准备好了”,不过是他和太太两颗热情的心。既来之则安之,在我和P团长的帮助下,最大的老母鸡顺利落入魔掌。
故事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了,如果每一个家庭主妇都必然有巧妇的样子。但这位维吾尔族主妇望着老母鸡一筹莫展,恰好两个邻人从后门路过,过来帮忙切喉放了血,“开膛剖肚”时,她一直在喘气、叹气,目睹她手撕鸡翅、鸡腿的全过程,直让人怀疑她是否干过家务。贤惠的L老师实在看不过眼,出手相助,母鸡才得以顺利下锅。
鸡肉微香的时候,这位太太出了一趟门,回来时,手上多了几个土豆和一个大西瓜。下午三点过后,我们终于吃上了哈米提家的土豆焖鸡,虽然手抓饭半生不熟,虽然全程除了我们自说自笑,但一点不妨碍我们和语言不通的女主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五个小时。
其间,我又以搭讪术成功进入马路对面的邻居家,与从农机站退休的大叔唠嗑一个多小时,与他家的孙子孙女们打成一片。晚上,我们已入住昭苏县城,邻居家的大叔打来电话,邀请我们第二天一定要去他家吃饭。
面对这样热情似火的维吾尔族朋友,我们到底该守信还是失约呢?
广州IT人变身新疆农民,驴友圈里流传着司徒、谢芳夫妇的故事,前往伊宁亚伯兰庄园的“朝圣者”络绎不绝。
2010年,喜欢自驾和徒步旅游的谢芳和朋友相约去了新疆,同行的一位新疆人自费充当向导。一行人从喀什出发,开车穿越漫天的尘土到了吐鲁番,决定坐火车到伊宁,不料,最后一头沉醉在9月的伊犁。
不得不说,9月的伊犁颜值(在新疆)最高,吐鲁番已过葡萄成熟的暑假旺季,街道人少,干净,小摊上的哈密瓜真的很甜,吃完必须刷牙。
当时,深圳人在喀什买房,如买白菜一样。司徒脱口而出:不如买块地,自己盖。同行的新疆人有心,后联系了他的同学,11月介绍了一块农地。司徒又飞来一次新疆,被一个快散架的桑塔纳拉到了目前的农场:亚伯兰庄园前身,一片被几百、上千年雪水泄洪冲刷的荒地。同行的新疆农民表示愿意回来种地。当时他天真地以为:种地很简单,没文化的人都会。便买下了眼前约500亩的土地,开始开荒种地。
庄园周边满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闲散牧民。边地民族及时行乐,拿了薪即刻走人,“用工荒”随时叫人挠头。更多的操心等在后面,赌上全部身家却颗粒无收。“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夫妇俩请来当地农科院的专家,对荒地重新考察评估,优化了水稻品种,在旱地改种苹果、蟠桃、棉花、小麦,投入第六年后终于有了收获,庄园自产的口碑效应也在圈内圈外扩散——“花城农夫”借助电商平台为客户打造“农特超级管家”。庄园业务分工明确,男外女内,能干、果敢的谢芳主理庄园,寡言、踏实的司徒带团徒步或自驾,司机、导游(加摄影)双肩挑。
庄园是我们北疆之行的最后一站,白天假装牧民,喂马劈柴,顺便周游旷野,等待天黑。夜晚来得迟,鸡羊归笼,繁星登场,密密麻麻,几乎触手可及,比起白日更纯净更辽阔。晚风袭来,透着几丝寒意,八月末的庄园,蜜瓜、蟠桃当令,秋意深浓。我们一群短衣帮,自夏天来,习惯了广州屡屡的入冬失败,对秋天完全脱敏了。奶茶、啤酒上桌后,维吾尔族雇工古丽和“神仙会”的客人们腼腆告别,司徒依然闲不住,收收拣拣,偶尔过来搭腔:“你们不是要求住宿三星吗?你看,现在要几星有几星,我没骗人吧!”回到庄园,果然还是那个司徒。
三个月后,庄园将转入休耕期,也是候鸟南归的日子。亚伯兰的“牧羊人”回到广州,休整到来年的2月底,再重返庄园,南来北往,刚好抓住了两头的春天。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