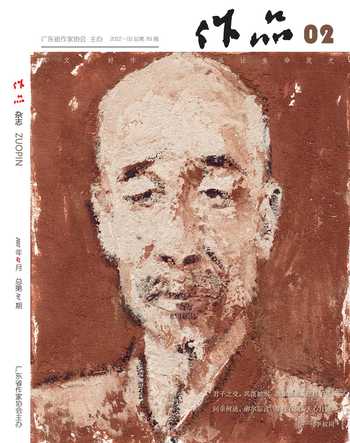黑色雪片(短篇小说)
盛可以
这些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也许存在误解、偏差、添油加醋,但熟悉A的人都认为整个故事没有脱离基本真实,大部分内容众所周知,和A关系亲近的人提供了某些情节细节,心理活动部分由具备生活经验的人,以洞察人性的天赋加以完善,合乎逻辑的揣测推断属于文学性质的虚构,使其血肉丰满。
有人认为,A悲剧性的根源可能是文学,可能是生理缺陷——镶嵌在眼眶里的那只狗眼珠并不能美化他那张毛孔粗糙的脸,也不能使他横肉丛生的面部变得柔和,这个畜生的器官仅仅是填补了一个实际的黑坑,却制造出无形的心灵空洞,影响了A通过眼睛向同类传情达意的功能。也许这扇心灵的假窗户导致了交流障碍,使他不得不借助肢体和语言暴力。
人们以为A习惯了那只狗眼,直到他在第一次结婚的第十个年头当众发飙。那时候A已经遇上贵人,这个表现出写作才华的农民,当上了电视台记者,继而被推荐到某大学作家班深造,发表了几篇小说之后,脱胎换骨成了作家。文学附体,A脸上那只狗眼依旧死灰,但神情举止与从前不同,人眼微醺,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走路时下巴抬起来,头略偏左肩,像是憋着一股劲——没当作家之前,那颗脑袋在脖子上倒是规规矩矩的——直到某次A在酒桌上向自己的狗眼开火,人们才意识到,他过去在乡下艰难成就的婚姻就像一身破旧的衣服,在如今金碧辉煌的殿堂中显得灰暗寒碜不合时宜。在场的人数年后仍能逼真地模仿出当时的情形,A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摘下眼镜,手指自己的狗眼珠,说:“我这个样子,哪个会要我?”
作为一个贫穷和戴假眼的农民,A在大龄时终于结了婚,那个随他迁城入户,没有文化的妻子大刘——朋友们习惯以大刘和小刘来区分A的两个刘姓女人——做姑娘时和已婚的村支书发生关系,此事尽人皆知。姑娘的处女膜和A的狗眼被灵巧的媒人分放天平两端,意外地使一对男女半斤八两门当户对。A原本就为脸上的狗眼自卑,清除了家里任何照得见人脸的东西,婚后又增添了妻子被别人破身的羞耻,这根暗刺扎在心头,疼得他挺不直腰。随着身份转化阶层上升,这根刺越来越清晰尖锐,双重屈辱的煎熬,使这个在小地方混出头面的A脾气更加暴躁易怒。
不管A对他的女人多么粗糙,他的背叛、抛弃、暴力、性虐、自私、悭吝等诸多不太美好的品行都获得她们无限的宽容。这一点颇为令人费解。A被他的女人视为玉石,她们心甘情愿地呵护奉献,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擦拭打磨。这块玉石在女人们手中流转,浸染她们各自的体温、汗水、眼泪、生活,经年累月,其质地不但没有变得温润通透,反倒模糊不清暗影重重,而她们被玉石粗糙的部分弄伤,没有人怨恨,更没有人反目成仇,惹人艳羡。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读者最好不要刨根问底,不妨将此事完全看作虚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发表过一点东西,因文学的加持而意满志得的男人,获得本市文学奖酒足饭饱后横尸街头,连同体内的酒精欢娱荡漾春情一起摊在冰冷的马路中央。
原配大刘没有特别之处,普通得连描述她的外貌都显得多余。不管她年轻时有过何等痛楚的感情经历,终归在“伤风败俗”的道德评判覆盖之下,直到婚恋形式多样,人们见怪不怪的时代,A却仍然没有达到社会的宽容度,对那事依然耿耿于怀。没有人知道村干部对大刘的情感属于哪种类型,总之没有任何谴责的言语落在村干部身上。多年来大刘和村干部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村干部的父亲过世,大刘特意回乡参加葬礼,A大怒,痛打了大刘一顿,喊了多年离婚的口号付诸行动,谁劝都不管用。此時他们的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为了给A冷静的时空,大刘去了北京和女儿生活。顺带提一下A和女儿的感情,父女俩的隔阂是从做父亲的听护士恭喜他得了千金时掉头就走开始的。A想要的是儿子。当女儿在离婚问题上公然袒护大刘时,A声称要断绝父女关系。
A在大刘腾出的时空里并没有自我反省,相反立刻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揽到怀中。女记者是个文学青年,对A的仰慕填补了他的生理缺陷以及他异于常人的性情。她知道好些伟大的作家,在他们伟大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私生活丑陋的一面,赌博、吸毒、淫乱、情妇、私生子、自私、负心等等,她说得出一长串名字,而且她认为中规中矩成不了好作家。女记者具有城里姑娘的大方洋气,旁人也觉得大刘没有哪一处比得上她,虽说对于始乱终弃嘴上有道德上的评判,心底里却是羡慕A的,因此A真正办理离婚手续时,不再有人劝阻,而大刘也安静地——也许是绝望地——成全了他们。
女记者并没有使A获得新的创作灵感,相反进一步激化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按道理她根本不应该看得上他。他怀疑她嫁给自己的动机是想要在电视台里站稳脚跟,调进这个单位来。他也怀疑任何和女记者有联系的男人,老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甚至觉得这事情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只有他还蒙在鼓里。人们在聊天,看到他走过来就闭上嘴巴,他认为那是在议论他和他年轻老婆的风流韵事。他越是恼怒性欲越是强烈,而性交这件事让他感到自己的地位与强大,他从后面揪住记者的头发,或反钳住她的手,打她的屁股,咬她的奶头,把她弄得到处青紫。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在大刘身上,只不过大刘把这当作夫妻间的隐私,或性生活里合理存在的一部分。A的悭吝、自私、酗酒、暴力等品行,在女记者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她将这些视为A的独特之处,正因如此A才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不幸的是,女记者婚后不久查出绝症晚期,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之后,永远离开了A。
这段由死亡终结的婚姻仅存在了一年多,没有留下子嗣,时间迅速抹掉了女记者在A生活中的痕迹,人们也淡忘了她。就像是被一阵骤雨淋击过后的植物,在短暂的萎蔫后重新舒枝展叶,抬头挺胸,A倒掉酒杯里的愁苦,满上自由欢愉,在饭局上无节制地畅饮,被蠢动的性欲带到某个暧昧的房间,尽情消耗肉体。他同时开始着手写人生第一部长篇,一部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关于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南洞庭湖区的垦殖史和人世沧桑,他打算把自己经历的爱、死亡,以及种种失去巧妙地糅合进去,野心是要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媲美。
听说A在写世界名著,大刘悄然回来,照顾A的起居,洗衣做饭。A坦然接受她的伺候,仿佛天经地义。大刘怀着虔诚之心做好的食物,像下酒菜点缀搭配A那杯“写作”的香醇美酒。这模式过了一阵,好心人便劝A复婚,说于人于己都是桩善事。A和大刘已重新进入婚姻模式,但两人都没有提出复婚,随后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出世,人们也觉得血脉的延续比一张婚纸更有说服力。大家都以为A投身到伟大的创作当中,这艘颠簸的船最终停泊在大刘宁静的港湾,用不了多久,他将鸣响文学的汽笛,那部史诗般的大作也必然将他重塑。
但随之而来的艰难超出人们的想象。A总是因为创作瓶颈大量喝酒,每次都要呼朋引伴,拉人陪喝,喝起来无休无止。朋友们起先还觉得陪A喝酒散心,多少算是参与创作名著的方式,将来没准混进著名作家回忆录里,沾点荣耀与谈资,于是最初也是喝得心肠滚烫,笑语欢声,经常持续到深更半夜。但很快有人觉得不太对劲,A似乎是打着写名著的幌子喝酒,拍桌子骂粗口,透支未来的名气与威望——渐渐地只剩下一两个人肯陪他吃饭喝酒。
大刘的厨艺长进,她奉献出伺候伟大作家的全部虔诚与敬重,赢得了在A身边的生活。外人看来这个家庭之前的挫折都是有价值的,一如风雨过后水落石出。然而石破天惊,大刘在一个昏黄的下午知悉A得了一个儿子,她是在洗碗时听到他在电话中向亲戚报喜,显然是有意让她听见——他甚至都不屑于当面跟她谈,此后也没有。据大刘自己讲,她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掉进黄河浊水中,不能呼吸。A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强调儿子的生辰体重,如何健康可爱,丝毫没有提到那个婴儿的母亲。在A把母子俩接回来安顿前,大刘什么也没说便去了北京,且制止了女儿愤愤中打电话的冲动,叫她不要破坏她父亲的喜悦。
也就是过了一个冬,油菜花开的时候,A联系大刘,说他儿子没人管了。大刘于是知道,那个女人是个菜花癫,油菜花一开,她就背起旅行包要去中央开会,商谈国家大事,A阻拦多次,她最终还是半夜跑了。用不着A放下姿态恳求,大刘立刻就回来了。无人知晓大刘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盘弄这个比她外孙还小的婴儿,似乎她所品尝到的滋味是甜的。这白白胖的小男婴在大刘怀中笑,爬行、站立、学步,几乎是一夜间就满地奔跑。他长得聪明漂亮,机警伶俐,A到哪儿都带着他,仿佛在胸前佩戴一枚战争勋章,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荣耀。A的精神面貌变化巨大,整个人印堂发亮眉目舒展,一个温柔细腻体贴负责的父亲替代了那个酗酒打女人的野蛮汉,他对儿子的耐心无人能比。
这是A最忘我的时期,他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和情欲,至少四年人们没有看到他沾上别的女人。他也没有出去寻找孩子的母亲,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人们也不知道A是怎么和她发生关系的。她算得上神秘。人们在A未来的遗作中能看到她的影子,他将她比作蒲公英,风一吹就飘扬,种子落到土里就发芽。也许这蒲公英飞遍了全国各地,落下了无数的种子。既然飘扬是蒲公英的天性,A也就心安理得,儿子是他唯一在乎的事物,甚至覆盖了他与马尔克斯媲美的文学野心。
A的创作瓶颈消失了,至少没有人再看到他为此苦闷。他和大刘以及这颗蒲公英种子变成的男孩构成一个颇为奇怪的家庭。说奇怪,自然是旁人的感觉,人们的想法肯定因素复杂,且带着某种评判。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回A的生活无论如何上了正轨,人们称赞他的慈父形象,没有哪一个父亲比得上他的称职与牺牲,人人自愧弗如。
不幸的是,随着儿子的白血病诊断结果,A胸前这枚勋章瞬间失色,他的世界随之坍塌,彻底被击溃在瓦砾堆中。他在这片废墟上长久地挣扎,寄望于科技、医学,以及人类的知识智慧,在梦想与现实间时醒时昏,但始终笃信人类发明了“奇迹”这个词,就有可能用在他的命运中。他每晚睡在儿子的病床边,将年过半百的身体放进那张狭窄的行军床,很难说他真的睡过觉。有人看见他,几乎认不出来,脸上肉都掉没了,腮部放得下鸡蛋,连那只暴突的假狗眼也有了感情,隐隐闪现人间的悲凄。那时离那孩子死去还有两个星期,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定局,他连奇迹的气味都没嗅到。人们不再背地里嘲弄A,他们眼中的悲剧父亲、英雄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了整整八个月,唯有深夜膝头上的笔墨承载他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煎熬,他遗作中最感人肺腑的部分就是在医院写的。
按道理,在经历不幸与人生低谷时,人对周围的事物会涌生珍惜之情,容易做出平时不做的抉择,比如一个原本对婚姻犹豫不决的人,某次空难余生后马上向相处多年的女友求婚。人们以为A会和大刘复婚,相依为命。事实相反。A很快弹回原形,酗酒、打女人、骂粗口,变本加厉。他是否继续性虐大刘,这事只有大刘知道,当然大刘不会说,她认为这是夫妻关系中的一部分。不过人们很快知道小刘的存在。这个生过两胎的女人按政策结扎过,到城里生活多年蜕去了乡下人的壳,自己在小区开了个文具店,她的口头禅是“吃了没读书的亏”,言下之意,她要是读了书是要成大事的。这个女人乐观健壮,经常面色潮红——或许是处于更年期,或许是因为A的缘故——大白天将她拽离工作岗位上楼弄一把是常有的事。
无论如何人们对A的行为更加宽容,还有什么比中年得子、得而复失更悲怆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子女,根本不需要多加解释,即便A做出杀人放火大逆不道的事情,人们恐怕也会将之归结于他所经受的痛苦并垂怜于他。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未来会比失去的儿子重要,谁也没有资格要求A坚强振作,忘掉不幸,甚至都不敢打断他舔伤口的行为。这件事影响了整个朋友圈的氛围。人们跟A相处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有人拿他开玩笑,将他放进某个段子里取乐。在他拍桌子骂政府说大话自贬自嘲狂妄自负等情绪交织时,大家现场配合扮好听众角色。大刘再次黯然赴京,人们也没有对此做出评判,或许是习以为常,或许是早有预料,A的历史毫无障碍地翻到了小刘这一页,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结成了夫妻。
小刘独自带着两个儿子,日子原本过得不坏,因为对文化和读书的崇拜促使她注重教育,她生活中唯一跟文化沾边的事就是卖文具,各种笔墨纸本的价格能张嘴就来,根本没想过某一天会和A同床共枕,尤其是这个A正在写一本世界名著,这部作品极有可能在她的气味中画上句号。她没少想象自己作为作家夫人挽着他的手臂出现在某类颁奖场合的情景,巨大的满足感抚慰着她。至于A本人的各种毛病,包括连柴米油盐钱都不掏一分出来,小刘也从不计较。然而A一点都不爱她的孩子,总想将他们支开,蜜月期过去很久还是一样。孩子的外公外婆觉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有意拒绝照看孩子,他们不在乎A是什么身份,只看重人的基本責任。这么一来,A与孩子之间的矛盾仿佛水落石出,那坚硬而突兀的存在无法视而不见。
通常来说,一个痛失孩子的父亲,心中的父爱需要给予,需要倾注的对象,但A不同,他只爱自己下的种。不过人们也早该想到,这个对大刘的情史终生耿耿于怀,时刻担心妻子不忠蒙羞,看重处女膜,对女人贞洁毫不松懈的男人,绝不会喜欢妻子与别人生下的孩子,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料到,他对这两个孩子几近厌恶。他们在客厅里吵闹,尖叫,奔跑,弄得嘭嘭作响,他儿子以前也是这样,但那些噪声让他幸福愉快,涌动着莫名的骄傲,而这两个孩子弄得他烦躁不安,他想拎起扫把揍他们,永远轰出门去。但理智屡屡阻止了他,火窝在心里越憋越烈,最终火舌舔向小刘,一些莫名其妙的暴力行为几成常态。
小刘对读书人文化人的崇信在A这里彻底瓦解已是两年后的事。这期间她经历了几番情感波折,婚姻之船颠簸摇晃,她眩晕并尽力稳住船舵,直到她明白A与孩子之间的冲突是他们婚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放弃周围因她高攀了A而闪烁的羡慕眼光并不容易,这虚荣一度让小刘以为自己突破阶层,进了上流社会,然而所有这一些,包括这次婚姻的荣耀与作家夫人的头衔,都无法排挤孩子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小刘在处理婚姻问题上的表现反倒像文化人,她先是表达了自己对这段婚姻的感激,从这里她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得益于A的文化熏陶,但从A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她和她的孩子是拖了后腿的,他们严重影响了一部世界名著诞生的节奏。对于那双年纪正值“八岁九岁狗都嫌”的儿子,她毫无办法。经过深思熟虑,她认为分开对彼此都好。
倒不是离婚的事情多么突兀,也不是离婚本身让人难以接受,A只是惊愕于离婚的发言权竟然落在一个女人手里,而这女人将自己的意图隐藏得滴水不漏,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起的心,没有半点征兆。与其说A不愿离婚,还不如说他不愿女人占上风,大发脾气之后分居,之后由他正式提出离婚,这事才算和平了结。
大家意识到,没有什么能填补A丧子的虚无,写作也无法照亮他生活的黑洞,至于女人,也許他没有真正遇到与灵魂匹配的。人们搞不清他要什么样的女人。当大刘仍然对A抱有幻想,谁也没去为大刘当说客,主要是不忍看她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待遇,倒是有人劝大刘放弃A,别再遭他的罪。不过这种说法也许是一个旁观者的偏见,没准当事人觉得挺好,大刘早就适应了A阴晴不定与暴风骤雨的气候,一旦掌握了他的规律习性,她那柔软宽阔的胸膛就有足够的空间给他电闪雷鸣。
话又说回来,还真没人能列出A卑鄙无良行坏使恶的劣迹,他也只是个普通人,和大家一样,要说遭罪,哪一个不在各自的婚姻里遭点儿罪呢?要是遭点罪就散伙,哪里会有白头到老的?有人认为大刘有大智慧,她就像放风筝一样,任A满天空飞,她心里头的线绳总是绵延不尽。一些为大刘抱不平的人,仿佛被大刘照见自己的促狭,闭上了多情的嘴。但依旧有怒其不争的,认为大刘活得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在一个装了只狗眼珠的男人的轻视与欺负下生活,打都打不醒。
这个乡下妇女到底是智慧还是蠢钝,人们还没来得及理出一点思路,A的生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新的女人大家都认识,多年前嫁到几十公里外的省城,退休后经常回小城探亲访旧。平时都管她叫骆嫂,原是和大刘同村,据说她俩过去很要好,无话不谈,各自离乡后疏于联系。这事说起来真像讲故事一样。年轻时骆嫂在村里当广播员,播读政策文件表扬奖励之类的东西。那时A的写作才华还没被外界发现,还在种田养猪生孩子打老婆。他后来才知道,他婚后的生活早就夹杂在大刘和骆嫂的私房话中,他的性活动细节被一个不相干的年轻姑娘熟悉,多少年以后,这个不相干的姑娘在年过半百之时抛夫弃子跟了他。
让人们困惑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究竟哪里来的激情与勇气,促使她做出这种几乎惊世骇俗的举动?化学物质、激素、情欲……这些都不足以发动一个机能衰退的女人身上的发动机,而A本人似乎也不具备令人疯狂的魅力,最后人们锁定一个东西:文学。骆嫂老早就从杂志上读过A的小说,她有非凡的解读能力,她能复述每一个故事,而经由她说出来的故事往往比A写的更有趣更富深意。他们没有注册婚姻,只是同居,但比任何人都更像夫妻,甚至人们认为A找到了灵魂伴侣,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他的拳头与暴躁。A的生活貌似开始静水深流,世界名著正缓慢无声地攀爬向终点,一如他本人的生命。
因为A,大刘与骆嫂重新搭上线。某一次大刘像职员交接工作般,交代了A的生活习惯以及注意事项,诸如蒸鱼不要加醋,保护好茶杯里的黑垢,睡觉打呼噜不要弄醒他,和朋友聚会时不能打电话……骆嫂是否执行不得而知,反正她没有像当年的大刘那样对她无话不说,也许是到了这个年纪,男女之事的确也没什么可讲的。她们在电话里聊得挺不错,大刘一点都不介怀。她留在北京带外孙,或许是过于操劳,人们在A的葬礼上看到她明显老了,双目潮湿浑浊,皮肤上开出大朵大朵的老年斑。
当晚A是往回家相反的方向走到肇事点。一辆桑塔纳撞烂了他的脑袋。那只让他终生自卑的狗眼珠脱离了他的躯壳飞弹出去,被车轮熨成了薄片。终结A生命的地方,离斑马线五十米远,也许是抄近路去对面的暗娼街,他惯于在陌生女人身上寻找愉悦,尽管他正和他的灵魂伴侣同居。也有人说A在那条街上有一个相好的,他不定期造访。无论如何,这个年满六十,经历过生命中至暗时刻的A,手持被打碎了的人生圆镜,始终四处寻找修补的地方。
有人说他过马路时正给大刘打电话,此说法未经证实,因为没有人去问大刘。不过这引起人们的好奇,假如这是真的,A在获奖当晚酒足饭饱之后,走在空荡荡的夜街,为什么会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刘打电话,他对她说了些什么?
在A生命中浮出水面、并为大家熟知的五个女人,除了因病去世的那位,以及蒲公英一样飘荡无影的,大刘、小刘以及与A同居中的骆嫂都参加了A的葬礼。她们相聚一堂,用各自情感成分不同的泪水与A告别。此时此刻,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与身份匹配的悲伤是一门学问,外人也可借此观察她们与A感情的深浅。大刘扑倒在A身上,以乡村妇女不加修饰的嗓门断肠号哭;骆嫂只是不断擦泪擤鼻涕,攥紧变得脏污的纸巾堵住嘴巴;改嫁了的小刘除了在几个特定环节红了几下眼圈,还能平稳地抚慰大刘与骆嫂。她们像亲戚般团聚在A的遗体周围,共同的失去使她们捉住对方的双手,从另一个女人的手心感受A的存在,想象A与他人亲密的情景已毫无醋意。她们的A躺在那儿,一张丝绸被单盖住了整个躯体,包括那张无法修复的脸。在这个抽象又具体的符号象征面前,她们是那么的海阔天空,如此的亲如家人。
当骆嫂将A的遗作放在死者胸前,人们才知道A真的完成了一部史诗巨著。书于翌年出版,并在A的周年忌日举行了作品研讨会。大刘、小刘和骆嫂闻讯而来,她们坐在主桌外围,每个人都经过精心打扮,面色虔诚地听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没想到被主持人邀请发言。她们从各自的角度讲述她们和A的生活细节,以及他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情景。她们的声音充满赞美与怀念,听起来更像是她们参加A葬礼时应该讲的,那时她们谁都没有说话。
根据她们的表述,人们总结出一个结论:A其实是个相当温柔善良的男人,只是在文学上走火入魔,有意塑造与作家身份匹配的不同寻常的一面,以掩盖其平庸的个性特征及生活经历。也许这是女人们对A的人格的集体粉饰,也许A的确在刻意塑造“作家”的传奇色彩,不过这已经没人去求证,人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中年丧子和横尸街头等意外不可能在A的设计之中。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