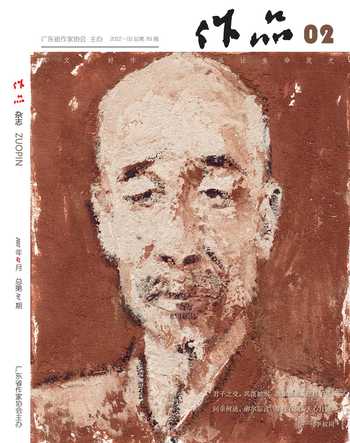瞳中客(短篇小说)
许龚燕(复旦大学)
张怡微(复旦大学)
许龚燕的小说《瞳中客》,写了一个杀妻的故事。男主人公因性无能寄情互联网世界的美女小瞳,渴望被关注、被感谢。她的妻子则是务实的助产保姆,负责养家。两人的生活本来平淡乏味,因为男主人公眼疾的加重,和妻子发现他精神出轨而有了波澜。小说的心理描写细腻动人、引人入胜,夫妻两人因生计结合却因精神上的疏离而诱发极致愤怒的设计,事关难以言明的性压抑,有些像麦克尤恩的名篇《立体几何》。包括男女主人公和女主播的名字,似乎都意味着看见、识别、照亮和希望,但他们的生活却是一点点被剥夺希望的过程。小说的场景其实有两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女主为了了解男主的生活,也曾登录过这个象征情感满足的虚拟世界中加以观看,繁复的人性和欲望被处理为夫妻之间的羞辱,令人期待作者对于两性关系、对于两重世界的复杂认知。美中不足的是,结尾的恶性事件还是缺少足够的动能,过于突兀的结束令小说原有的悬疑气质降落为通俗故事中常见的嫉妒和暴力元素。对女主情感需求压抑的表现还可以更加充分。
明尔旦第一次见到小瞳,是在一个睡不着的夜里。
吴桐陪护的孕妇产检时羊水不足,当场便入了院,她也提前结束难得的休假,匆匆收拾行李赶了过去。助产保姆这份工作虽说时薪诱人却也磨人,但她总怀有一份过人的诚挚热情,每天有那么多的婴儿在出生,她也就停不下来,从一个产房辗转另一个产房,忠诚地做着阴道口的引路人。这也许是种逃避,明尔旦心里清楚,他不能给妻子作为女人的幸福,她只好跳过这一步,无休止地去体验成为一名母亲的快乐。
日子怎样不是过,至少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的夜晚。只是隔壁的小情侣正闹分手,摔砸打骂声时断时续,隔一堵薄墙整日扰人清静。他拿着手机胡乱戳,戳进一个直播间里,恰好看见小瞳拈着两朵粉玫瑰哼唱,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好老的歌。她原本是低头浅笑着看花的,他进来后便去看他,抬眸时一束光正巧含进她浅棕色的瞳孔里,眼波流转,歌词唱到“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女声低柔的尾音细微上扬,和上挑的眼尾一起,看一眼又羞涩地歇一眼,勾得他久久停在这个页面,真的忘了要去哪。
那晚小瞳便进了他的梦,梦里手机方正的屏幕塌了棱角,无边的黑色不受控制般流淌开来,将他包裹其中。亮着光的那头,女人举花朝他招手,他身子一轻,盯着视线中那抹飘摇的粉色便随她而去。直播的小房间,他看见摄像头背后是一片广阔的玫瑰海,女人温热的鼻息喷洒在他肩头,小瞳在他耳畔低语,她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谢谢你照顾我。”
一股陌生的力量席卷自下腹,汹涌而来。直至轻盈的身体渐渐落入实地,欲望注入四肢,他才后知后觉,欣喜万分。雄性的本能,那未曾体验过的原始冲动充斥着所有的意识,他激动地不停颤抖:原来自己真可以做个男人!这念头叫他无法控制自己,只好不顾一切将女人压倒在身下,贪婪地舔舐她脖颈处的芳香。然而双手却丢了力似的,怎么也撕不开薄薄的衣衫,他几乎要哭出来,趴伏在小瞳柔软的胸口处不断哀求:“你帮帮我,你快帮帮我。”
小瞳依旧是微笑着望向他,双手滑过他的眼睛。两人身旁的花瓣忽然猛烈地纷飞起来,迷乱住他的视线,他想再去抚摸女人的脸,亲吻她鲜红的唇,但右眼处的刺痛却唤他回了现实世界,回到漆黑一片的房间中央。
在堆满衣物的床上缓缓直起身来,他揉了揉模糊的右眼,眼睑处的细微水声润泽了干涸的视线,几秒后世界才稍稍回复清明。亮起的手机屏幕上闪烁着系统自动更换的壁纸,从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变为温馨的室内景象,干净的欧式餐桌上是色泽明亮的水果与说不上名字的精致饮品。
屏幕下方浮动着一句话: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2:03,还不算太晚。
身后传来模糊的声响,女人抑不住的低喘声和床板吱呀摇晃的声响持续好一阵。他捉摸不透从争吵到做爱之间曲折幽深的距离,但那带着阳刚之气的律动却一下又一下用力撞击着他的脊柱。一墙之隔,另一个男人,尽管他完全知晓那人的无辜,却还是控制不住将头痛苦地埋进双膝间,任空虚的夜一点点吞噬他的躯体。
吴桐回来后,明尔旦迫不及待拉着她试了一次。
妻子虽对他突然的热情感到诧异,但还是顺从地解开内衣扣,双手绕过脖子在他背上来回轻柔安抚,这是她工作时的小习惯。身后的手裹挟着晚间凉风的寒气,还带来几分消毒水的味道。阴暗的房间里,明尔旦觉得自己像母亲肚中焦躁不安的婴孩,即将滚落人间,独自去面对这空旷辽远的陌生世界。
吴桐总叫他想起母亲。不光是因为她的职业,他想起每次犯错被板着脸教训时,母亲也会这样拍拍他,叫他下次考好些,叫他想想清楚,叫他加油,叫他年纪大了,也该定下来,叫他对媳妇好一些,有点丈夫的样子。他老是忍不住想起小时候自己在房间里偷着看影片时母亲突然闯入的场景,她压低脚步声,从背后悄然出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按灭显示屏,叫他穿好裤子。他记得母亲冷静到没有一丝温度的言语,她说:“脏不脏啊?”
漆黑的显示屏兀自播放没有暂停的视频,脚边的音响还在持续震动着,传出一些黏腻放荡的声音。那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炽热的阳具,却羞愧地哭不出声。想起母亲,一切便失了味,于是他的人生也如胯间那物一般,颓颓地软下来。
吴桐是个好姑娘,母亲的眼光向来不会出错。唯一的缺陷便是脸上遮不住的一大片暗红胎记,否则她也不会屈尊嫁给他,在魁梧高大的妻子面前,自己依旧瘦弱得像个孩子。她大概生来就有种照顾人的天性,连搬家这样的事都用不着他插手,在一个个出租屋间奔走时,全靠了她和房东们打交道。若说收入,吴桐的工资虽不固定,怎么算也都比在工厂上班的他要多上许多,明尔旦心里对妻子的亏欠越多,在床上就越发无能,可偏偏他在床上越发无能,他的妻子就越发要照顾他。
正如此刻,吴桐在他耳边轻声说:“别急啊,你慢慢来。”
结束之后,两人都有些舒畅而满足。吴桐难得露出一副小女儿姿态,靠在他肩上沉沉地睡去了,发出熟悉的阵阵沉重鼾声。怀里的女人有着丰腴的肉体,两人第一次同床共枕时,吴桐腰间的赘肉压住自己的肋骨,让他做了一整晚孙悟空的梦,梦里的五指山上空响彻着母亲冷冷的声音,她说:“吴桐是个实在的好女孩,你要和她好好过。”
这回他是真的决心要和吴桐好好过。趁着假日,他跑去商店为妻子挑了好几件套装,又听从店员的建议,去一楼的美妆店买了支口红,据说是清新的豆沙色,当季卖得火热,女人应当都喜欢。
原本是很开心的事,但衣服的尺码不对,吴桐穿上身后,提口气都费劲,鲜嫩的粉色短裙显得她更臃肿了,像是菜场案板上耷拉着的猪肉。她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高昂的兴致渐渐冷淡下来,在他递给她口红时,只说工作时不能化妆,拿去退了吧。
当天晚上吴桐没有留在家里,说是临时要顶同事的活。明尔旦没有挽留,在妻子走后照例点开LULU,直播间里的小瞳一身蓝色淑女裙,长发绾在脑后,绕成蓬松的卷,露出线条优美的下颚与颈部。她总爱唱些旧旧的情歌,今晚是《亲密爱人》,缱绻绵延的调子。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每时每刻把你梦。”
既然是天意,就不能违抗。他想,也许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是一件以后想起来不必矛盾和纠结的好事。还是原配好。她曾经说过。每次在一起面对他的为难甚至是显得虚妄的希望时,她总是这样泼冷水。显然,他们不再是狂躁的孩子。她不会因此离开家庭,虽然因为寂寞她接受了他的追求,并且全身心地享受着这份另类的激情。而他显出的虚妄多是在她矛盾愧疚的时候出现。我是好女人吗?会遭到唾弃吗?等高涨的潮水退去的时候,突兀的岩层理性地裸露出来。于是,在她无序的自责中,他会挺身而出,骑士般地说,不要等下辈子了,让我这辈子就娶你吧。我什么都可以舍得。
她唱“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唱得他不住心神荡漾,右眼一阵阵地跳。他在直播间洒下一场又一场花雨,LULU的世界里,他是“明小明”,小瞳开心时叫他明明,心情一般时叫他小明,嗔怪时则称呼他明先生。这个晚上,她永远“明明”“明明”地喊他,双唇向外拉扯时,总能看见白净脸颊上那一对深深的酒窝。他不知道那张小小的唇涂了什么色调的口红,但手旁的豆沙色应当也适合,优雅而温柔的颜色,像她。
他和小瞳的关系是量化的可以累积的亲密点:一个星星棒十个亲密点,一场玫瑰花雨五十个亲密点,如果是一艘潜水艇,则是一百五十个亲密点。“明小明”的账号攒满了十级,整整一千个亲密点,他终于可以向小瞳发出好友请求。这意味着,她的生活将在他面前完全敞开。
他们的对话不再拘谨在日常的问候与感谢里。如果他留言紫色好看,第二天他便会看到身着紫色包臀裙的小瞳开启直播。他喜欢她听话的样子,从眼线上扬的弧度到穿着打扮,每天唱的歌,甚至下一顿午餐或晚餐,都可以听他安排。他无数次幻想小瞳是自己妻子的样子,于是他在床上愈发动情地呼唤着瞳瞳,隔着吴桐肥硕的肉体去拥抱小瞳柔软的腰身。
小瞳的朋友圈满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好喝的咖啡馆,美食街小摊上的美食,某一刻的心情,诸如此类。他热衷于他们之间这种巧妙的解谜游戏,他像一个侦探般搜寻出暗藏在图片与文字里的所有线索,组合完毕后,去换取她惊喜的一句“你怎么知道”或者“我也一样”。说这些话时,她眼眸中总有水光流转,像是一颗石头投进平静湖水中央时荡起的涟漪。
有一次她发了一张看展的照片,照片里是线条抽象的画作与女人纤细的背影,她穿着棕色的风衣,配文是:朋友请我看展,好开心。带了三个荡漾的波浪号。他有些嫉妒那个没有名字的“朋友”,嫉妒他拥有注视着她背影的机会,尽管看展从不是他会做的事,但他却确实找到那个展去看了。毕加索,只在学生时代的课本里见过的名字,反正画的都是些他看不懂的画。
他记得两张,一张是画家的自画像,另一张据说也是画家的自画像,上面画着一个叫塞什么纳的老妓女,她的右眼被厚厚的白翳覆盖,忧郁的深蓝底色下,这一点病态的白显得更加诡异,老夫人身着一袭黑衣,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没有看他,视线穿透了他的身体,望向未知的地方。在画作前,他抬手捂住右眼,站了很久很久。
大概便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眼疾开始迅速恶化,点点白翳从眼角向瞳孔攀附延伸,越来越近。吴桐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眼翳,却还不到开刀的程度,只需要滴点眼药水。然而再多的眼药水对他来说好像都于事无补,明尔旦只好放任右眼结出一张模糊的网,工厂的活不得不停了,他休养在家,吴桐又接了更多的活。
他为小瞳每天的直播定好了闹钟。那天,闹钟响起的上一秒,他还陷在柔软的梦里,梦见他变得很高大很高大,是一棵参天的大树,而小瞳成了他脚边的一株柔柔的小草,承蒙他的荫庇。他飘飘乎俯视着世间万物,为自己的小草挡去一切风雨。
而此刻盖着窗帘的房间里一片惯性的昏暗。他凭记忆描绘出桌角、衣柜、燃气灶的轮廓,临街的喧闹声如大雨倾盆,直击耳膜。拉开电脑桌前的椅子,按下主机上发着微微红光的开机键时,他才觉得自己终于从遥远的梦境落回了真实世界,着陆在这间狭小的出租屋内。
刷新了几次页面后,右下角的通知栏出现那条熟悉的消息:您关注的主播瞳瞳爱吃饭已经开播啦,快进入直播间660352看看吧!顺着链接溜进屏幕里熟悉的小屋,满目是温馨的暖黄色调,架子上一堆毛茸茸的玩偶,他认得最上层的大眼公仔,一周前他在医院检查完时寄出去的。和公仔一起送到的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你的眼睛会说话。”卡片费了些力气,他先用铅笔打了遍草稿,再小心翼翼用水笔描上去,奈何撇捺间生硬的粗细变化还是泄露了他的紧张与游移。如果可以,他多想将自己那颗为她跳动的心一起打包快递出去,告诉她,第一次见面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是爱情的俘虏。
散着黑直长发的女人正微笑着打招呼,小瞳说今天去换了个新发型,来得有些晚了。下方的弹幕滚过一堆“晚上好”,他也顺手在键盘上敲“新发型不错”,很快她便注意到他的光顾,轻轻将耳畔的碎发别至脑后,朝他挥了挥手。
欢迎明先生,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他暗暗回复。他注意到小瞳并不高涨的情绪,也是,最近忙着在医院里做各项检查,确实好几天没有看直播了,她有些生气也是应当的。屏幕里飘起他送的气球与玫瑰,昂贵的告白套餐,鲜红的花瓣正代替他的手指抚过女人的面庞与身体,那属于他的每一分每一寸。他继续在弹幕里解释。
明小明:最近眼睛不太好,去医院了。
明小明:想你了。
明小明:小瞳,想你了。
明小明:对不起。
一串串文字从屏幕中女人的身体前飘过,于是他又听见自己的名字从那张微启的红唇中说出,女人开口时嘴角微微上扬,这次她叫回他明明,多了几分亲昵。
她说:“明明的眼睛怎么了呀,严不严重?”
他回复了一句没关系,又送上两场花瓣雨。小瞳照例感谢,谢谢明明送的花瓣雨,谢谢你一直以来对瞳瞳的支持。她停顿了一会,加上一句,还是要保重身体呀。明尔旦被安抚得服服帖帖,早忘记一开始是他想要道歉。他露出满足的笑容,身后却突然传来房间门重重关上的声响,循声回头,只见吴桐面色铁青站在她身后,手中拎着一塑料袋的东西。
她淡淡开了口,脸上的胎记随着面颊的肌肉轻微扭曲开来:“你在家的时候,就在干这个?”这语气和多年前母亲质问他时一模一样,那时母亲说:“你才几岁,就看这个?”
“瞳瞳,你听我解释……”他听见年幼的自己颤抖着嗓子:“妈妈,我没有……”
“明尔旦,那是我挣的钱,你就这样白给其他女人?”吴桐和母亲的声音一同响起:“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学读书,不是让你学这个的!”
吴桐走近了屏幕,直播间里瞳瞳的声音还在继续,大概是谁送了礼物,她唱了几句后又停下来感谢:“谢谢这位大哥对瞳瞳的支持。”吴桐愣了愣,想必是意识到了什么,冷笑道:“瞳瞳?她是瞳瞳,还是我是瞳瞳?”
她将手中那一大袋子东西重重砸在他胸口,“明尔旦,你活该瞎一辈子!”说这话时,暗红的胎记张牙舞爪地扑挤过来,他下意识向后仰倒,塑料袋里的东西溅到脸上,刺刺地疼。他认出滚落的某种中药药材,大概是吴桐前几日打听到的偏方,治眼睛的。
接下来的几天,明尔旦的眼翳更加严重了,右眼已经完全不能视物,那层白翳甚至在向外伸展,吞噬着眼睑与眼周,他的眼睛像结了层厚厚的冰,眨一次眼,就要费劲地解一次冻。这事消磨了他的睡眠,也就此罢免了他与小瞳交流的权利。吴桐想必是幸灾乐祸的,因为当她打开阴阴沉沉的房门时,他分明看到她脸上划过的嚣张笑意,那笑意太过明显,叫他想忽略都不能。
吴桐过来拿行李,她要回娘家住。这房间里属于她的东西本就不多,散漫堆着的,永远是他的杂物,她总把自己的东西好好收在衣柜一角,维持着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模样。收拾完行李,她却不着急走,拿起餐桌上的水果刀削了个苹果吃,边吃边与他闲聊。
“你最近应该看不了直播吧。”
他点点头,也不看她,视线在房间里逡巡,落不到一个固定的焦点。
“我前两天看到新闻,说是一个女主播骗了自己的粉丝,原来她长得又老又丑,粉丝还以为她是白白净净的美女,整天给她打钱。结果直播的时候,美颜突然坏了……你说好不好笑?”
“直播……美颜?”
“我还试了试,真的神奇,像换了个头一样。这么大的红斑都能给我遮了,脸比鸡蛋还小。”她翻出手机里的视频给他看,里面的吴桐果真没了硕大的胎记,整个人像年轻了十岁,若不说是她,他是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你说你的那个瞳瞳脸上会不会也有我这样的斑?”
他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视频还有虚假的可能。恍惚间,他看到手机里妻子的脸颊长出红豆大小的斑,那斑越来越大,逐渐吞噬掉她整张脸,只剩下空洞开合着的五官,记忆中小瞳的脸也被这样的红斑逐渐吞噬,酒窝与微翘的唇角枯叶一般脱落下来,那斑点传染病一般,也吞噬掉母亲苍老的面颊,他的世界里只剩下吴桐那尖锐刺耳的声音:“真的,我也去看了瞳瞳的直播,她一晚能收入小几千呢。唱唱歌张张嘴就能赚钱,世上还真有这么容易的事嘞。早知道这一行来钱这么快,我说什么也不去做保姆啊。”
“我也给她送了点礼,你猜怎么着,她和我说:谢谢小叶子的礼物,谢谢你对瞳瞳的支持。哈哈哈,她确实该谢谢我,你给她送的钱,有多少都是我赚的?谢我也是应该的,对吧?”
他没想到吴桐竟去看了小瞳的直播,那明明是他的专属领地,小瞳樱桃似的小嘴只能用来呼喊他的名字,如今却叫她玷污了。明尔旦的胸膛猛烈地上下起伏着,呼吸越发粗重。
吴桐终于达到目标,止不住笑起来,起身拎住了箱子。临走前,她还嫌不够似的火上浇油:“我看你在那女的面前也不怎么重要啊,人家还有郑先生熊先生许先生献殷勤呢。昨晚郑先生还中了她的大奖,共进晚餐,哈哈哈……”
一束光从未拉紧的窗帘间照了进来,细细的一条缝,从窗台通往餐桌,指示明尔旦拿起尽头处发着亮光的刀。
陌生的力量又一次主宰了他,欲望让他不受控制。在那个有些阴冷的午后,当刀锋划破妻子雪白而脆弱的脖颈,喷射的鲜血灼烧着他右眼的坚冰,硫酸一样腐蚀掉了片片白翳。
换个头就好了,他想,换个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