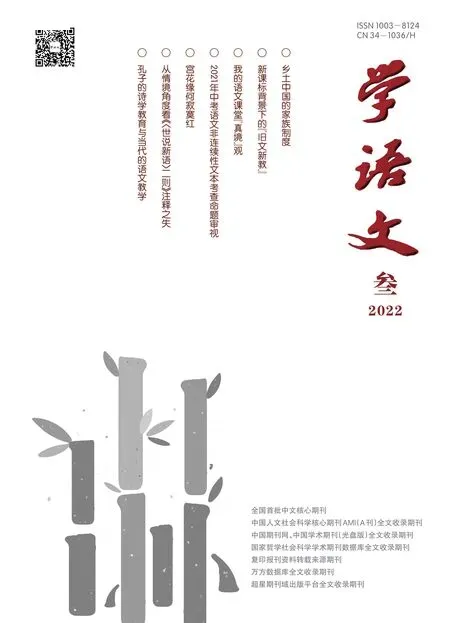《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的双线说理技巧*
□ 刘劲凤
《寡人之于国也》这篇文章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对话。梁惠王困惑于自己“尽心焉耳矣”却“民不加多”,孟子在正面回应梁惠王使民加多、称霸天下的策略要求的同时,又想借机指出梁惠王扰民、不顾百姓生死的残暴,对其进行一次行“王道”的“教育”。两个目的一表一里,一明一暗,贯穿孟子的整个说理过程,形成了孟子在本文的双线说理技巧。
一、说理的明线:层层递进献策
孟子的话是说给梁惠王听的,他说什么、怎么说就必然由这个特定的对象决定。根据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考证,孟子五十多岁才来到魏国大梁,梁惠王当时在位已经五十年,年纪也在七十上下。可以说《寡人之于国也》其实是两个老人进行的一次关于政治理念、社会理想的交流和探讨。虽然都想使民加多,但两人的根本目的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梁惠王使民加多的目的是增加兵员、打仗,孟子的目的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道不同,注定了谈话的不易。所以在梁惠王表述观点后,孟子明知其错误并没有点破他、批评他,而是另起话题,从梁惠王爱听的说起。
孟子开言第一句“王好战”,在权势与暴力被推崇膜拜,攻伐征战被视作合情合理的战国时代,估计不仅仅是对梁惠王的治国困惑的解答,更能勾起梁惠王英雄般戎马生涯的回忆。否则,梁惠王不会对孟子的“战喻”回答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坚定,如此之自信。
接着孟子说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此处孟子设喻取譬的目的不仅能使说理生动形象,还能让谈话不涉及原话题,以避免尴尬或刺激。这种委婉的方式比直接批评梁惠王不懂得质与量的关系更易于接受。
说了故事之后,孟子仍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判断。而是故意反问了一句:“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意在投石问路,这个问题就是他投的石头,以此探探梁惠王的态度。待对方回答后,孟子才表态。论辩中只有充分、准确了解对方的思想动态才能对症下药。相信,假如梁惠王不是如现在所答,本文的行文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
得到预期的答案后,孟子这才顺势直接点出梁惠王不能“使民加多”的原因。“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在说,你民不加多是有原因的,不值得奇怪。这句话是孟子说理的第一个层次的总结句,第一次正面回应让梁惠王困惑的民不加多的问题,分量很重,可以直接唤醒梁惠王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但这句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建立在孟子对梁惠王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孟子层层推进的说理策略上。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还有引出下文的作用。这句话完整的理解应该是: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还坚持原有的观念或做法,就不要指望百姓比邻国多了。这种基于语境而省略的内容,对说话双方来说,不言自明,启发了梁惠王从理论上的知道错误到行动上的做到改变,从渴望使民加多的心动到实行正确的使民加多的行动。两人的谈话聚焦到“做到”“行动”这个问题,自然引出下文。
下面孟子就开始宣讲自己“使民加多”的要义,即怎么做才能使民加多。孟子提出的实行“王道”后的社会图景也是层层递进的,非常契合梁惠王的心理预期。
“不违农时”一段是指广义的粮食生产,是为了“有的吃”,从而迅速改变战争带来的穷困局面,解决温饱问题。“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百亩之田”“七十者衣帛食肉”具体讲发展农副业生产,是能“吃的好”,描述的是小康社会的富裕局面。“谨庠序之教”描绘的是文明社会的状态——安宁、有序、仁爱、有礼。
孟子循序渐进地为梁惠王描绘了从温饱、小康到文明的社会发展蓝图。这样的社会,百姓自然归顺,民必加多。这一番美好的愿景,相信梁惠王也一定心驰神往吧。
就在梁惠王沉醉在愿景中的时候,孟子抓住时机,趁热打铁,立即指出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君王不关心百姓的行为进行了批判。面对“狗彘食人食”“涂有饿莩”的极度不平等、极其悲惨的现实,王公贵族们“不知检”“不知发”,冷漠无情,置百姓生死存亡于不顾,何谈为国“尽心”呢?这就把梁惠王从理想拉回现实,思考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解决百姓的贫困温饱问题才是当务之急。为了进一步引导梁惠王从主观上找问题,孟子又举了一个推脱责任的例子:杀人者刺人而杀之之后,貌似很无辜地说“非我也,兵也”,这种荒唐可笑的说辞无疑增强了批判意味。
在此基础上,孟子总结说,“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年成,实行王道,才能做到真正对百姓“尽心”,老百姓看到国君真正爱民,民也会爱君,就会归附国君。最后一句总结全文,照应开头,第二次正面回应梁惠王“使民加多”的策略要求。
二、双线交织,不露痕迹
孟子“王道”的内容有很多,如“与民同乐”“民贵君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为了实行王道,孟子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沉重的赋税等。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孟子在回答梁惠王“使民加多”问题的同时,始终围绕战争带来的后果和休战带来的好处去论说。孟子这种双线说理技巧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说理艺术,如果说“使民加多”是一条外在的显性的逻辑线,那否定“王好战”这条逻辑线所承载的信息只能藏在暗处,不动声色,不易察觉,却时时处处要传达给好战的梁惠王。
对“王好战”的否定态度,为什么只能藏在暗处呢?除了和梁惠王之间王道和霸道的对立立场外,孟子面临的更大的困难是当时各诸侯角逐武力,以“好战”为英雄之举的社会现实。刘向《战国策·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对“王好战”的否定态度只能藏在暗处,见机行事,然后不露痕迹地传达给戎马一生并以此为荣的梁惠王,从而巧妙地对好战的梁惠王完成一次价值观的更新和引导。
(一)反驳“尽心”论
梁惠王的话语中,原文用“焉耳矣”三个语气词强调“尽心”;用“无如……者”排除一切人,骄矜得意之情可见;邻国百姓“不加少”,自己百姓“不加多”,对比中流露出深深的不满和困惑。可见,梁惠王自以为很爱民,治理国家很“尽心”,所以“民不加多”的现实,令他心里很不平衡,很委屈,很困惑。面对迷信武力征伐且自以为是的梁惠王,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时,不得不兜兜转转,但他始终抓住梁惠王的“尽心”论做文章。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在说,你民不加多是有原因的,不值得奇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从句子本身的结构看,应该是代词“此”指代的内容。“此”代指上面的“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所蕴含的道理——不可用五十步、一百步的不同的量来代替逃跑这个相同的质,即不能以量代质。把这个道理迁移到梁惠王身上,孟子想说的是,你以为“移民移粟”就是“尽心”了,认为自己为政就比邻国好了,其实你和邻国为政的本质是一样的。因为移民移粟是治标不治本,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出了大问题时的应付,“应付”和“尽心”是不同的。“尽心”是梁惠王认为自己应该使民加多的重要理由和依据,孟子在此紧紧抓住“尽心”这个“核心概念”进行内涵的阐释界定,从而顺理成章得出结论——你并没有尽心,你是在应付百姓,那么老百姓当然不会依附你了。在巧妙反驳梁惠王的观点的同时,自然引发梁惠王的疑问:“真正的‘尽心’是什么呢?”孟子接着就和盘托出自己的王道策略。表面上,孟子在为梁惠王谋划“使民加多”的策略,实质上孟子始终在暗示“使民加多”的前提条件,要“尽心”,先“止战”。
(二)暗示“好战”扰民
孟子在论述“使民加多”的措施时,在描绘实行“王道”的图景时,始终暗示“好战”扰民,始终委婉告诫君王停止“好战”。
“农时”就是农业耕作的时节,老百姓该种地时种地,该收割时收割。“违农时”就是老百姓不种地,不收割,老百姓都到哪里去了?春秋战国时代打仗是常态,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老百姓去服劳役,去打仗了。“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是说不要过度提前食用和使用。为什么会提前用呢?在当时主要还是因为打仗。一打仗,要保证粮草武器的供给,吃的用的就会无休止增加。不够用了,就只能不该用的也提前用了。大鱼没有了,就吃小鱼。大量的木材急需,就滥砍滥伐。同样因为君王好战,民不可能顺利养生丧死,七十者不可能衣帛食肉,颐养天年。结合前面梁惠王“民不加多”的疑问,孟子实际上在说,因为打仗过分消耗,又耽误农时,致使物质匮乏,老百姓缺衣无食,怎么会归顺你呢?所以不能过分动用民力,不能老打仗,这样老百姓有粮食供养活着的人,同时有人力又有财力物力为死去的人办丧事,如此爱民养民,百姓自然就归顺了,民自然就加多了。
孟子积极拥护“井田制”,拥护“耕者有其田”,有了自己的田,百姓又能自己做主,土地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五亩之宅”是宅基地,宅基地本身是用来住的,现在也要利用起来,种上桑树。百亩之田是耕作田,耕作田只要按时耕种劳作,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都不会挨饿的。老百姓能全心全意生产,还可以养点鸡鸭猪狗,作为农业生产之外的副业,日子就更好一点了。而这些都是在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所以这既是以美妙的图景吸引梁惠王,也是在规劝梁惠王改弦更张,不要好战。
孟子用词精当,“违”是“违背”,“夺”是“强行改变”,“失”是“错失”,都含有主观、人为、任意导致的后果之意。是谁导致“违”“夺”“失”它本来的时节?“好战”的君王。
文章中“无失其时”“勿夺其时”,与前面的“不违农时”一样,都是说不要耽误它本来的时节,如此反复,论述的内容并不重复。“不违农时”是指广义的粮食生产,是为了“有的吃”,从而迅速改变战争带来的穷困局面。“无失其时”“勿夺其时”具体讲发展农副业生产,是能“吃的好”,描述的是社会的安定局面,“违”“夺”“失”有主观、人为、任意导致的后果之意。如此反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强调实行王道必须做到不要人为任意地“违”“夺”“失”其时,要让耕作、生产、生活都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只有在正常的状态中,才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文明社会。
(三)谴责“罪岁”
从原文“非我也,岁也”“罪岁”可以看出:梁惠王不关心人民疾苦,面对“途有饿莩”的悲剧现实,只是一味“罪岁”,推委责任,把百姓痛苦遭遇的根源,归结为年成不好这个客观因素。
那么到底谁是“狗彘食人食”,“涂有饿莩”这种悲剧现实的罪魁祸首呢?是残暴“好战”的君王发起的无休止的战争。君王真正对百姓“尽心”,是不可能好战的;君王好战,置百姓生死存亡于不顾,又何谈为国“尽心”?为了增强批判意味,强化自己对“王好战”的否定态度,孟子又举了一个战争中杀人者怪罪于兵器的例子来类比。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对于好战,并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梁惠王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变相的敲打!
孟子最后总结说,“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年成,要从主观上找原因,停止好战,实行王道,百姓自然就会归附国君。
理解至此,我们回头看孟子开言第一句的“王好战”就特别耐人寻味了。它一方面投梁惠王所好,拉近了情感距离。另一方面指出了梁惠王好战的事实,为后面论述“好战”恰恰是梁惠王的“民不加多”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做了铺垫,从而开启了孟子双线说理的序幕。
孟子的“王道”思想的核心是爱民之道,“王道”的矛盾方是梁惠王奉行的“霸道”。孟子认为,要想使民加多,只有先停止“好战”的霸道,才能实行真正“尽心”爱民的王道。在孟子的论辩中,王停止“好战”和“使民加多”两条逻辑线是条件和结果的关系,两者一表一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它们共同支撑起孟子严谨、周密的说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