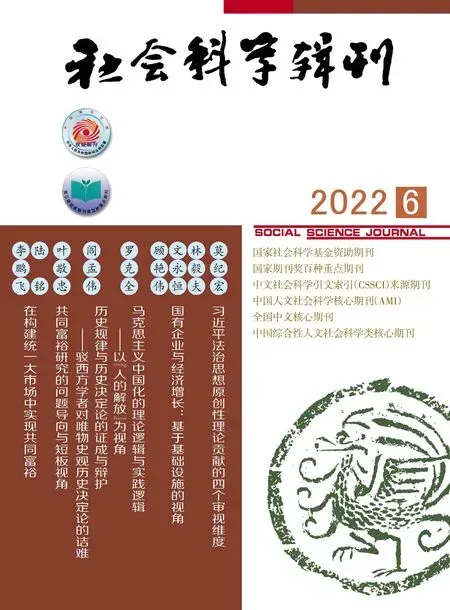器物“陈设”美育功能的中西方思想述论
李钧
人是伴物而在的,人的所有物是人的客体化形式。伴随的物品,有的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有些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也就是所谓“身无长物”的“长物”。有意思的是,后者虽然无用,但却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甚至附带产生了“收藏”“博物”“玩物”等社会活动。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兴起过多次收藏高潮,近几十年随着国力增强、文化自信以及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增长,从事收藏活动的人数已达六七千万之多,形成了一个新的收藏时期,同时收藏也成为国人重要的生活方式。收藏以及非有意识收藏性的对“无用”之物的汇集行为意义何在?收藏动机是多元的。最简单的动机是投资,但藏品的真正价值并不主要在于价格增值;动机的另一极是研究,对于古代器物、艺术品或文物进行收集,以实物探究和佐证古代名物制度。这种动机亦是以实用态度对待器物。此外还有怀旧、体会文化、欣赏艺术等其他动机,这些动机逐渐靠拢于器物无用性里隐藏的一些深层价值,但大多语焉不详,具体的理论根据与路径,在诸种博物与收藏理论中鲜少见到。因此,有必要对生活中这一普遍现象进行理论探讨,也即追问器物就其本身而言对于人的非实用目的的意义何在。
在这个思考中,器物在其对人非实用性的陪伴中,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器物大多是通过“陈设”而伴人的。这里说的陈设或摆设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似乎是人对于物品随意、自主地安放,它体现了主体的一种心境和意蕴投射,呈现出意向不同和境界高下。这是一种看起来最无意义的行为,但也是生活最普遍和平常的行为。在这种几乎意义透明的行为中,也许我们能找到人之伴物现象中一些较为深层的意义。当然,讨论陈设也要先区别一些并非完全是一种自由的摆设行为,比如制度性或寓意性摆设行为,比如旧时厅堂家具的固定摆设或“终身平静”(厅堂神台上座钟、帽筒、花瓶等器物的固定摆设)的器物搭配。自由摆设是器物包括收藏古物最基本的意义呈现。古今中外,其实有不少著述正题或非正题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表达了通过“长物”的设立把器物的功利性和特殊性转换为非功利性和整体性,从而将器物艺术化,而艺术化的器物给人带来对于世界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领悟,从而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带来精神境界的提升。这个互动过程,建立起了博物行为与现象最基本的价值。
一、规定与座架:精神的实存与进步方式
在西方,少见对陈设行为的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多和博物研究联系在一起,并不成为一个专题。随着近代博物馆的兴起,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其本身隐然含有对于展示物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几乎被人忽略的意义,直到以揭示意识形态深度建构为重点的黑格尔这里才被注意到。而且,它的意义,被黑格尔直接与作为真理——“事情本身”的“精神”的实际存在这一本体论过程联系在一起。精神不仅直接实存为具体事物,并且它还以某种方式把异化着的自己表现在实存物中。这种表现,需要实存物摆脱具体的实用约束,更深地表达它的建构过程,也因而表现出与其他实存物的系统性与历史性联系。只有这样,实存物才脱离狭隘的限定性,启示出精神的整体性。在黑格尔看来,要达到这种超越,某种方式具有优势意义,那就是博物馆式的系统的、历史性的陈设与展览。在这样的方式中,出现的不仅仅是具体特殊的器物或者艺术品,陈设本身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实存的整体,提供了历史。这种历史,当然是客观世界的历史,但由于它是人的创造,它更是精神的“内在”性的历史,是精神的自我的直接历史,是主体性的客体化。它对于人提升自我、看见自我、实现自我具有根本性意义。这种看法,直接赋予了陈设行为最深的形而上意义和理论基础。
黑格尔清晰地表达他对于陈设的重视,是在1828年冬季学期进行的第四次美学讲座中。在这次讲座里,他提到柏林将有一个新场所适合绘画鉴赏:“适合研究和欣赏的陈列是顺历史次第的陈列。这样一种按历史安排的绘画结集我们不久将有机会在建立在本地的皇家博物馆的绘画廊里欣赏到。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比珍贵的绘画结集,不仅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技巧发展的外表历史,还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内在历史的本质性的发展,包括各流派之间的差异、题材及其构思和处理的方式。”〔1〕黑格尔在这里提到的是将于1830年开幕的柏林老博物馆。这座由洪堡建议、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设计的王室博物馆,收藏着普鲁士王室多代的古代艺术品积蓄,不仅体现帝王家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对广大的市民阶层进行文化教育。博物馆采取古典风格,内部空间模仿罗马万神殿,有高大的穹顶、整齐的科林斯式石柱,柱间各种方格里的古代雕像及绘画等各种艺术品面对着观众的凝视而泰然自处。
黑格尔对于柏林博物馆画廊的期许并非讲座中随意偶然的言谈,因为“画廊”竟然是这位大哲学家在其庞大理论体系建立中对于理念或精神的最高展现方式的隐喻,并且看来这个隐喻在他心中持续了几十年。在此前20多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阐述了他的认识论。精神在意识层面表现为现象和知识,知识在不断进步,精神也一步步地在意识里呈现出自己的真相和整体,最终,精神达到了自己最高的形式:概念。因为这种概念不是抽象以及与对象对立的主观的,所以,这种概念是以所有的非概念的意识或者对象为内容的,这个概念的形式就是内容,概念就是意识和对象,它是自我否定的,不停留在自己抽象的形式的,是能够“回复”和“外在化”的。简言之,精神最初是一个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进步,最后达到最高的意识形态:概念,而由于这种概念的科学性和完全性,这个概念又不是固守在一个僵化抽象的形式里,它反而又同时表现为那些它一步步走过的意识形态。当然,此时那些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曾经的样子,它们已经脱去了其当下的狭隘,而在整个概念的自我把握中与整体联系在一起,获得了必然性,从而与其他意识形态发生了一种不再是有限视角而是新的整体性的联系。与此同时,概念虽然把自己等同于这些意识形态(形式等于内容),但是它不再是最初的茫然探索自己的等同,而是已经把握了自己整体的等同,所以,它不再“现时存在”地是这些意识形态,而是在“回忆”中拥有这些意识形态。不仅拥有一个,而是拥有所有它走过的形态,在回忆中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明明灭灭,相互交替。在这个变化中,精神的概念拥有自己的呈现(黑格尔称之为“启示”),并且,这种呈现是时间性的/接续性的,所以,它是“历史”。也就是说,精神在回忆中外化自己为历史。因为被外化的意识形态已经脱离了它在迷茫探索中当下浅层的牵绊,在更高的境界里被更新,被赋予了一种整体性的环节意义,所以,那些意识形态被黑格尔比喻为“画”,具体事物脱化为一种回忆的藏品。于是,就有了《精神现象学》里这个最高也最著名的隐喻:“(精神的变化过程)呈现一种缓慢的运动和诸多精神前后相继的系列,这是一个图画的画廊,其中每一幅画像都拥有精神的全部财富……它抛弃了它的现时存在并把它的形态交付回忆……这个被扬弃了的定在——先前有过的然而又是从知识中新产生出来的定在——是新的定在,是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精神形态。”〔2〕
在黑格尔看来,时空中存在的事物都是被规定的。起初,这些事物最显然地是在人的意识里被规定,并且伴随着认识这种行为。随着认识的发展,把所有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的精神或理念被认识到。事物的被规定,也由被人规定转而被认识到是由这个普遍整体规定,甚至,认识主体这个主动者,也成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环节,成了这个整体自我认识、自我规定的一个自我意识和自我确定。精神通过自我的规定产生一系列意识形态,在精神还没达到自我认识的最高高度时,这些事物仅仅是这些事物;但当精神的自我认识达到最高高度时,那些曾经作为精神当时的自我认识和规定的事物,就脱离了它们狭隘的环境和实用性,成了精神最高认识的一种外化,它们被精神物化了的主体收拢,和这个主体一起体现为连续变化、传输转让的历史性。这种“画廊”隐喻深刻地表现了精神的整体性自我认识的状态和活动。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重点是一种整体性的“自我规定”,即精神把自我设定为一个存在物的这个设定行为本身,只有这种体现精神本身的设定(规定)本身才能把自己的不同形象脱离特殊实用性、特殊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从而在更高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关系中陈设在世界中。形象在陈设模式中的缤纷和变化,才能体现这种所有具体规定行为的整体和本身。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看到这一点,也必须犹如黑格尔所说的在主体认识水平上达到最高的、与对象合一的高度。对此,黑格尔反过来也指出,艺术品的涌动和铺陈,它们集合成一个“万神殿”,成了最高精神出现的“条件”〔3〕。因此,黑格尔的这种表述,表达了一种人类生活中本体性的行为,是对于伴物而在的生活现象对于人的精神提升和必然性意义的深刻阐述,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可以是一种物的生活以及博物理论中的形而上部分。
黑格尔这个潜藏在理论大厦里的深邃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未被人重视。但它在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那里却得到了呼应和发挥。
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哲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存在者,都体现着“存在”这个根源,存在是存在者的依据和真理。不同的存在者有不同的内容,这内容是同一个存在在不同的处境中的体现。这犹如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规定或者定在。因此,存在者的真理,应当是打开自身,把自身作为存在在特殊的处境中的自我设立展示出来,也因为此一缘故,海德格尔称真理为“无蔽”。任何一物,自然物、工具或者艺术品,其第一个本质就是无蔽。物是一个无蔽的凝聚,而更具体地说,无蔽又是以这个物为视点的一个这个物的世界的打开。《艺术作品的本源》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与艺术是存在打开与流行理论的重要文本。在其中,他说:“真理……即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也是早就开始规定着一切在场者之在场的东西。”〔4〕物之“无蔽”,就是物坚硬黑暗的形态融化透明了,把它内在的生命世界展示出来。正如凡·高的绘画《农鞋》,农鞋之实现,在于它融入和助成农妇的生命与劳作,借农妇这个主体打开了它的世界。当然,这个作为一个世界的物的真理,必须要有一个和打开世界的日常视角不同的打开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个世界“建立于其上”的东西。这个世界之所依据和来源,作为这个世界的相对部分,也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世界里,于是,“世界”就变为“世界—大地”的二元模式,“无蔽”就变为“无蔽—遮蔽”的二元模式。那么,在具体的现实中,这个“大地”和“遮蔽”对应着什么呢?那就是把这个真理的世界创造、制造以及呈现和设置出来的环节。因此,它可以是艺术行为中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可以就是包含着这个世界的物的“物性”,也可以是一种“陈设”:“要是一件作品安放在博物馆或展览厅里,我们会说,作品被建立了。”〔5〕总之,一切使物、作品里的世界打开,使那个物与自己根源相联系的命运呈现的行为和方式,都是“大地”的维度。海德格尔也把这种依托性称为“形态”,他说:“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真理之被固定于形态中。……这里所谓的形态,始终必须根据那种摆置(Stellen)和座架(Gestell)来理解;作品作为这种摆置和座架而现身,因为作品建立自身和制造自身。”〔6〕这也就是说,物的内容和世界是和它的形态外形重合的,而物的外形就是它的建立和设置的体现。当然,这是一种穿透人们日常对于物、工具和艺术品的理解,是对于一种物的真理、命运以至于世界整体真理、天命的理解。在这种视线里,有一个行为被呈现出来,也被强调地把握住,那就是“座架”。这种座架,是各种具体的座架本身,具体的座架改头换面隐藏为事物的具体实用的样子,但所有这些特殊之用的根本依托在于存在运动的创生与托举。在海德格尔理论里,“座架”是非常重要的范畴,他用它来思考“技术”的本质和拯救,它是“存在”和“真理”的基本模式。
海德格尔的理论与黑格尔其实是高度契合的,在这两位近代以来最重要思想家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世界本体理解里一些特别强调的东西。一种纯粹的设立、摆设,这普通的生活行为,其实也可以深化为一种本体模式。我们注意到这两点:一是设立的行为就是设立的东西,设立要体现在设立的东西上。二是设立的东西必须超越日常地呈现,否则,那本体性的设立行为就会被埋没僵化,而不能体现出它的整体性和本体性。因此,设立之物是脱离实用与功用处境的,它只为一种超然的看而存在,这种超然的看呈现出事物超越功用的形式,这种形式体现出事物整体性和本体性的存在运动和存在形态。为此,它们会呈现出不同于实用处境的空间关系方式。同时,设立之物还是缤纷并陈的,它们在视线变化中隐显,展示隐含在形态中的时间与空间、历史和世界。
如果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领悟到我们生活中某些基本的、无用的日常行为的深刻意义,也让我们注意到那些惯常关注的理论中人们不太注意的价值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空间,不仅潜藏在西方思想中,在中国古代有关生活审美和收藏的理论中,有着虽然简略但却更为深刻的体现。
二、“古雅”说:探寻艺术的本源
相对于西方,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于陈设其实具有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陈设赏玩器物,也在其中领略文化和历史,这种雅兴行为,是中国人的日常。以较为明确的审美与历史意识甚至形而上的意识来进行器物收藏与陈设,从而获得精神性提升和陶冶,至少在宋代就开始了,而在明代达到顶峰。因为各种感悟性表述较多,往往湮没了很多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性较强的深度思考。前文对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性视角,可以更好地寻索中国人在美育意义上理论性思考陈设行为的踪迹。
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中国古典审美理论的总结与转型人物王国维的某些观点。王国维的《古雅之在美学之位置》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及多重阐释的名文。在此文中,他借助西方美学理论话语来试图建立中国古典审美活动中熟悉而难以言说的“古雅”范畴。一般来说,“古雅”论首先是主要关于一般物的审美价值的讨论。他并不讨论专门的艺术品,而是一般的“玩物”,原本是实用的东西,如果加以玩赏的态度待之,那也可以纳入考察。王国维特别注意这个“无关于利用”“超出乎利害之范围外”的“缥缈宁静之域”。这个“域”具体立足在哪里呢?王国维根据他对于康德美学的理解,认为如果“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如果是美的,那么它要形式化,脱离狭隘的功用。那么,事物靠什么出脱为“优美”或“崇高”的形式呢?他说:“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种第二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7〕让事物出脱为形式的是另一种形式,名为“古雅”,“古雅”是让事物呈现其纯粹化的无形的“第二形式”。这个无形之处正是那个“缥缈宁静之域”,是中国古人对于物的独特的玩赏行为的施展之处。他继而指出,这个无形的东西,不仅使原本美的东西的美得以展现,甚至“虽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茅茨土阶与夫自然中寻常琐屑之景物,以吾人之肉眼观之,举无足与于优美若宏壮之数,然一经艺术家(若绘画,若诗歌)之手,而遂觉有不可言之趣味”〔8〕。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具有一种创造性,它创造性地显示了事物的缥缈之域,这个领域被利用所遮盖,但又是事物一切利用之依托。它在创造性的展示中和这种事物本体性的根基融为一体。
当然,王国维其实具体地指出了这种“古雅”是“修养”或者技术积累,同时,在具体示例中,某种程度上对于“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的区分并不是很严密,比如说绘画的布置是第一形式,绘画的笔墨使用是第二形式。如果按照现代叙事学理论强调故事与叙事之区别的话,他说的许多“第二形式”仍然是“第一形式”,从而使他对于“第二形式”的建立有含糊之处。但是,王国维此文的理论价值是巨大的。首先,他把千百年来东西方人类生活中一种非常熟悉但又被忽视的审美行为和领域标举出来,那种制造“古雅”的行为确实是一种独立而富有价值的行为。其次,他把这种几乎无形的东西形式化、范畴化,犹如亚里士多德因对世界的“惊异”而把“存在”标举出来一样。第三,最为重要的,这种无形的东西被称为“形式”,是对于“第一形式”也就是一般事物的形式里面存在或者真理运行的洞见。也就是说,他洞见到了一般的形式里的形式本身,感受到了一般形式需要建立和被托举,而这种建立、托举与一般形式其实是本质关系,因此,他将之称为“第二形式”或“形式的形式”,也就是形式的本体、形式的形成与建立。这一对事物内在东西的把握,是这篇论文最有价值的东西。尽管王国维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样偏重于解读形式建立的形而上学内涵,但他对于这个领域和现象的理论敏感度是令人惊异的。
尽管王国维没有把“古雅”与陈设行为联系起来,但我们看到,王国维看到了一种使艺术成为艺术的深度的东西,固然,这种东西可以有种种解释和阐明,但这个“雅”字确实也指引人们关注古代生活方式中“雅”的行为,包括使器物进入某种特别光晕中的陈设行为,指引人们对它们在审美活动中的意味进行思考。
在该文中,王国维还特别提到“古雅”的美育功能。他说:“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9〕他认为,古雅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并非如天才那样不可传输,经过修养,这样的基本技术和视野、品味是可以获得的,因此可作为美育的手段。从某种角度来说,“雅”是可以提升人的境界的、在所有人这里皆可具备传输的能力。这是这个论题里富有新意的见解,我们在其中隐隐可见康德用以建立“文化”而实现“教化”的“共同感”理论的影子。
三、“闲”与“长物”的生活形式对于器物的转换
从王国维的“古雅”出发,在前文所提的引导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包括诸如博物、收藏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构建,或者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构建的内在动机以及理论意义,凸显出中国古代美学一种独特的取向。这就是关乎物品的趣味性陈设、玩赏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典籍中是常见的,但也是常被忽略的,人人都知道玩物之有趣,但这种趣味立足于理论之何处、具有何种理论意义、在生存和本体论中具有何种价值等问题其实是并不显明的,也因此,它们也就成了玩物理论中的一种大而化之的部分并不被人深究。博物与收藏典籍被大量论述且重视的,是“学问”或“考据”部分,如事物的来源、辨伪、收藏源流、品鉴题记的内容,更高级的也是用于考古、名物制度佐证的材料。
这种玩物领域的义理性与辞章性结合、本体论性质的理论构建,滥觞于宋,主要流行于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特色。但因为缺乏理论掘进,后来沦为一种关于博物的基本性但又缺乏深度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在对其考察中我们看到,其实在生活的这个领域刚被打开时,前人即抓住了这个空间里虚无缥缈的部分:“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殊不知我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10〕赵希鹄提出的“清福”,依托于古物的“罗列”与赏玩。罗列即是赏玩,而玩者之称为玩,仅因其无涉实用,但这种创建雅趣的行为,所给予的“清福”却是阆苑瑶池也比不过的大用。在“骨董”的罗列中,人之生存已经化身为流连于罗列中的时光,这时光不是空虚与抽象的,而是凝聚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的物品,这物品不是静默无聊的,而是在光影中诉说着自己的命运。但中国古代理论对于这些“清福”的“为什么”,大概多以心灵相契来交流,并不多做分析或对之做系统性、理论性范畴建立与勾连。不过这种隐含的动机,推动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发展,它的“怎么样”到明代发展到非常精致的地步,产生了诸如《遵生八笺》《长物志》这类著名的论述。
《遵生八笺》要推出的是“闲”——“孰知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斯得其闲矣。余嗜闲,雅好古。”〔11〕《长物志》则加推一个“长物”:“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12〕无用而多余的人生与事物的这个部分与方面,具有一种深长的意义蕴含。它们在玩味中化身为无用的部分,而其玩味方式,可以以综合动、静方式的“陈设”作为基本模式。这里面,“骨董”化的诸般事物是以古物为核心的,即高濂的“好古敏求”〔13〕,古物在此具有内涵丰富的历史与家国命运,而关键在于其已经脱离当时的牵萦处境,在落闲之处,面貌可以摆脱狭隘的功用线索,呈现它被掩盖着的、更深的、看起来是无用的作为整体生活与历史环节的内涵。从古物方面来说,玩味者沉浸于其中的是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生命延伸。但是,用以“养性”的,并不仅仅是时间性的东西,同时也有空间性的东西。说起来,玩物是有“制”“度”以及“经”“目”“风”“味”等细节划分的〔14〕,这些制度,并非主要是传统使用中的规矩,更主要的是陈设玩味中的美学的考虑以及时空感的引发。这两部著作尽管有大量的名物介绍以及考订内容,但其突出而显明的内容,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审美范畴(似乎可以名为“古雅”)的发挥。它们分为几个层次:一是浅层的审美享受。陈设讲究搭配,这种搭配不仅是形式和色彩的讲究和配合,还有器物本身意蕴的选择以及生活、历史意蕴的配合。事物本身的形式呈现给人以愉悦的感受。其次是深层的审美感受。在对事物的玩味中,主体精神性的意向得到抒发。比如:“观古法书,当澄心定虑,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自然强作。”〔15〕如果说前两个方面还都是以主体为主,引发应和主体的审美旨趣,停留在“才”“情”〔16〕层次,那么,第三层次则是对于“道”之领悟,走在审美自我超越和提升的极致边缘,“一洗人间氛垢”〔17〕。在这种层次上,陈设玩味的意蕴就比较隐含,比如在古物中领会“唐虞之训”或“宣尼之教”〔18〕,或者依照节气陈设不同的物品。表面看来是应时与修养,更深的是对于充实着历史与生存的时空的体味。
四、“藉物”说建立的陈设的形而上学
传为董其昌所作的明末论述《骨董十三说》(以下简称《骨》文)①本节未标明出处的引用均出自《骨董十三说》,不一一注出。〔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2集第8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92-1195页。对于骨董的形而上意义做出了直接的论说,在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论说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它和前述西方思想家在关于陈设问题的看法上,具有富有意味的共鸣。在《骨》文中,作者揭示了“陈设”绝非无足轻重的习惯,它在看起来含混不清的雅兴举动中具有对于这个鉴赏活动的奠基性意义。陈设本身正是所有陈设之物的本意与隐含指向,所有陈设之物,最根本地就是表达陈设,而陈设也因此体现为形而上的创造、托举,是使器物超越自身的特殊化从而艺术化同时使欣赏者领略到自身以及道之力量的线索和根源。
在《骨》文看来,一般人认为骨董是无用的,但是,“唯贤者能好之而无蔽”,能够别具只眼的贤者,可以在对骨董的赏玩中“得事物之本末始终,而后应物不失大小轻重之宜,经权之用,乃能即物见道”。同时也能“进德修艺”,使骨董能够发挥“大用”。究其原因,该文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骨董的外在表意中。所谓“骨董”,整体意义是杂陈,但杂陈不是没有意义的,该文开篇指出:“易曰:杂物撰德。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文生于杂,有自来矣。文德修而人道立,非入德无以明道,德何以入?总其别,同其异,名消实化,繁兴大用,突焰飞光,莫可测识,乃有骨董一句,用举形上之道也,不可以训诂论说通之者也。”杂物形成文明,在这纷繁里能够领略到文明之变化和各种呈现,进而总合融化而体悟“德”与“道”。比如:“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迹,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
但是,纷繁的领略和学识并非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体悟形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具体化为纷繁的,但它又潜藏于纷繁中,是需要透视的,这种透明的东西才是该文要着力揭示的。这个道,体现在“骨董”的内在蕴含里。首先是“骨”,“去肉而骨存,故云骨”。人天然喜爱感官的享受,但内心却也能感悟到“声色臭味”之后的“平淡”与“清虚”,这些“无声无臭”之物,“即为万声万臭之大本”,是后者“有赖以存”的东西。“骨”即是万般缤纷剥落之后留下的内核,正如器物在生活与历史应用之后残余的符码,坚硬沉默又围映着过去的幻影。它指示着一切变化的依赖和根基。声色呼应感官,而“骨”则呼应“心知”,心知之物才能“可永我乐”,“得我安生立命之地”。但更深的含意还要从“董”字来继续发掘。“董”是治理控制之意,骨董如何会有这个主控性的意义呢?“董”字从草从重,所以其意要从草如何重要去寻找。它说:“读易曰:藉用白茅。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于是征其文有合于董治之义也。凡置物必有藉之以成好,薄如草茅,用之为藉即重。重其物,即重其藉物也。制器物者,亦用以藉我养生供物之用耳。”茅草虽然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但它总是用来作为器物保护凭藉的材料,它们保护着器物,守护着器物,其实正是器物所赖以在世间有用的可靠性的来源,因此,它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器物之用的基础和主控者。当然,草之为物藉,只是一个引子,它只是指示事物是具有发挥自己、呈现自己的基础的。“骨董”正是这样一个基础,是诸般事物的凭藉:“骨董古之垫物多,凡物必有垫,所以藉之也。……藉之即所以治之使成其用也。求古人之服食制度不可见,见藉服食之器而贵重之。”在玩物行为中所玩之器物,总是一种“垫物”,即用来装东西的器物,或者泛指某些用处、某些表达所在其中的器物,相对于应用或意义,器物总是“藉物”。“藉物”本身就是那些意义,意义是被“垫”出来的,是有“藉”的,在意义被“藉”的过程中,“藉”以适应于意义的方式铺陈出意义,“藉”就是意义的形态,因此,世界是意义的交织,其表现为各种“藉物”的杂陈,变现为各种“藉”的方式的运行。这是《骨》文最着力强调的意义:“然物藉之以存焉者也,而物又莫不相藉也;食物以器藉之,器物以几藉之;几以筵藉,筵以地藉,而地孰藉之哉?能进而求知藉地之物,则天人交而万物有藉矣。……则天下皆藉之矣,天下一大骨董也。人皆画于小而遗其大,特未之思耳。”这论述里体现出来形上思辨是令人钦佩的。天下是一个互相凭藉的网络,这网络又在一个根本的凭藉中各自走出呈现意义的线索。对于骨董的玩味,不在于表面器物的声色润美,而在于对于其后生产的追寻;不仅追寻它们后面各自的命运,更在于视这些命运为一个整体的运行设立的“道”中的各个环节,并且在这些环节的杂陈中透视到“道”,这才是不拘于器物形式和内容的“小”而把握其“大”的玩物之道。
《骨》文此理论,与前述王国维的“古雅”有一致的地方,它把无形的“大”揭示出来,而且在思路上也是以把握、呈现来立论的。它和前述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相契之处,“规定”“座架”与“董”“藉”,都是复杂的事物背后无形而容易被忽视的“骨”。而对于“骨”这种几乎不会以正题被人关注的陈设本身的关注和领悟,呼唤着人整体性的生存以及形而上的生存。古今中西,人们都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审美性地伴物而在,但是,人们多不会追问为何这种方式会具有如此力量和必然性,只是在它潜在的作用下,孜孜以求。这些论说的意义,正如王国维把“古雅”言说出来因此赋予它有意识的存在那样,把这个基本动力提取出来,使我们沿着这个启示,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