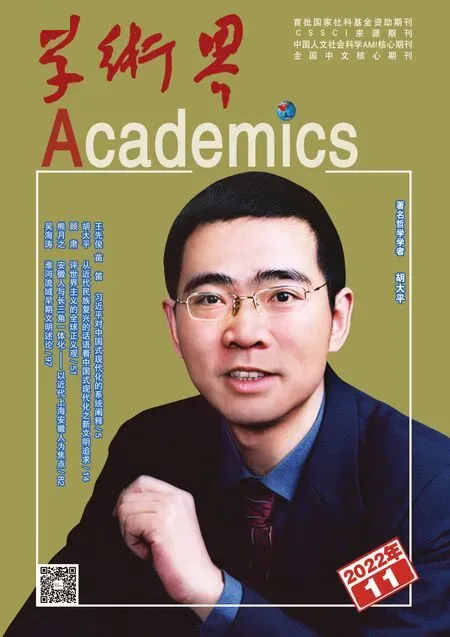国际海底区域环境补偿基金的制度困境与纾解〔*〕
周 江
(西南政法大学 海洋与自然资源法研究所, 重庆 401120)
一、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制度生成
环境保护一直是海洋治理的重要议题。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专门规定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近年来,随着“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逐渐被提上议程,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保护问题亦愈发受到各国的重视。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于2015年7月发布的《构建“区域”内矿产开发规章框架》(Developing a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ineral Exploitation in the Area,以下简称“2015年7月《开发规章框架》”)中,环境保护问题是其管理规章计划的重要内容。“区域”环境补偿基金制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一)“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中环境污染的责任缺口
目前针对海洋环境保护主要有两个向度的考量:其一,是事前预防,即尽力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即是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其二,是事后治理,即针对易产生的海洋环境损害迅速展开补救或对责任人进行处罚。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29条允许就海洋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提起民事诉讼程序。但是,现实中的海洋环境污染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无论是航行活动还是海洋资源开发活动均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因而事后对海洋环境的恢复和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这一问题很早即为国际社会所关注。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即斯德哥尔摩会议)中,与会国就进一步促进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该会议明确指出应当考虑制定对各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人承担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国际法规范。〔1〕及至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第235条亦对国家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中的责任予以了明确,要求各国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国际义务,并根据国际法规范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中,“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侵权有特殊性。海洋环境污染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导致传统侵权行为的救济手段不一定适合解决海洋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往往较一般侵权行为的后果更加严重,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救济方式。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对“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损害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9条和第215条只是明确规定了应当根据第十一部分制定国际规则、规章和程序,以及根据各国相关国内法以明确“区域”内活动的环境污染治理和责任归责问题。目前,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制定的规章仅面向“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并未涉及资源开发,且相关规章的环境保护措施仍是以事前防治、减少污染为主。例如,《“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第5条仅要求探矿者采取“预防性办法和最佳环境做法”,“同管理局合作制定实施方案”,对于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失探矿者主要承担书面通知义务。相关规定未对探矿者规定较为严格的责任,可能是考虑到“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活动对“区域”内生态破坏程度有限。但是,随着深海采矿技术的发展,“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采作业也逐渐提上日程。如果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5条之规定具体到“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活动中来,责任人的范围极可能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根据该条规定,作为公约缔约国的承包者母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考虑到“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合同本质上是一个私法行为,因而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承包者亦负有相应的责任。
于承包者而言,即使不考虑最低效力要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9条之规定,当“区域”内的污染对特定国家的受害人造成损失时,依特定国家之国内法要求承包者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仍然可能无法全面覆盖“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对整个海洋环境造成的真实损害。除此之外,这种当地救济的方式需要考虑到对承包者的判决或行政决定的承认或执行,在缺乏相关国际条约或互惠承诺的基础上,承包者作为责任人的责任履行极有可能无法及时到位。于担保国而言,首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作为缔约国的承包者担保国(通常是承包者母国)只在没有履行其对承包者遵守环境保护的监督、确保义务,并由此造成了相应的海洋环境损害时才应承担责任,且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这种责任承担不仅以“实际损害”为上限,而且还可因国际海底管理局责任或对相关活动具有管辖或控制权的国家所负之潜在责任主张减免。其次,担保国仅对承包者的海洋环境损害行为承担补充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当且仅当承包者履行赔偿责任且其无力对全部损害进行赔偿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就剩余部分承担责任。最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担保国所承担的义务只是一种关于确保承包者履行环保义务的“行为义务”,而不是杜绝此类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而,从私法的角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9条来看,如果担保国已经尽责履行其行为义务,即使因承包者的原因造成海洋环境损害,其也无须承担责任。〔2〕由此,“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极有可能因为上述责任缺口而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解决。
(二)补缺责任缺口的“区域”内开发活动环境补偿基金制度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以下简称“争端分庭”)曾于2011年2月1日就“区域”内担保国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承担提供了一份咨询意见。争端分庭在该咨询意见中指出,争端分庭虽然承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等方面的努力,但前述责任缺口之填补无法通过诉诸担保国在习惯国际法中的赔偿责任,因为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无法要求担保国在满足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对环境损害承担责任。是以,争端分庭建议国际海底管理局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5条第3款的制度框架下设立一个用以支付未能得到覆盖的损害赔偿的信托基金。〔3〕事实上,早在1979年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就有提案强调了对污染海洋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应当保证迅速而适当地给予补偿,其中即包括了类似强制保险或补偿基金等措施方案。〔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5条第3款明确指出,各国应当进行合作以保证对污染海洋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迅速而适当的补偿;该款规定还明确了“拟定诸如强制保险或补偿基金等关于给付适当补偿的标准和程序”等规定。
于国际海底管理局而言,即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对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规定,但是依据公约规定,其仍有权力制定相关规则以建立一个用以覆盖“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的补偿制度。加之争端分庭的建议使其开始慎重审视环境补偿基金制度,在起草“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时候,海底管理局即以环境补偿基金为中心制定了一种专门用于填补环境责任缺口的第二顺位补偿制度。该项制度在国际海底管理局2015年7月《开发规章框架》、2017年1月的《制定和起草“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环境问题)的讨论文件》、2018年4月的《“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4月《草案》”)、2018年7月的《“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7月《草案》”)和2019年7月的《“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7月《草案》”)中均有所体现。
环境补偿基金本质上是一种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方式,这一方式在目前的学界备受推崇。〔5〕于“区域”内环境污染问题而言,采用社会化救济途径可能更适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区域”的制度设计之目的。首先,在“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案件中,将承包者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人或许并不合理。虽然将相关环境损害的责任归因于承包者于法有据,但是,当承包者通过与海底管理局签订合同而从事“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时,其不仅满足了个人利益,同时也因相关行为符合“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而具有社会公益性。因而,将某些通过环境保护计划或合规行为无法完全预防的环境损害责任完全归于承包者承担,或有失公平。其次,“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不仅有直接受害人,还因为海洋作为生态系统的非封闭性,相关损害可能会对不特定国家抑或全人类有长期性的影响。因此,针对“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损害更应该体现补偿性而不是惩罚性。再次,海洋环境污染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可能使作为污染结果的不利影响具有隐蔽性和时间上的断层,因而在技术条件很难实现污染源追踪的情况下,某些实际由承包者造成的影响可能难以归责于承包者和担保国。最后,由于“区域”内开发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无论是污染范围还是污染程度),如果最终风险得以实现,使承包者的责任承担远低于其预期利益,那么潜在承包者尤其是因技术能力不足而具有先天缺憾的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承包者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6〕通过海底管理局实现对“全人类共同财产”的开发利用将会遭受阻碍。因此,作为社会化救济途径的环境补偿基金制度更适应“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
二、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制度设计
在海底管理局关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方案设计中,环境补偿基金制度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在2019年7月《草案》中,环境补偿基金的制度略显简明,其中的主要部分为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方向和资金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关文件未明确环境补偿基金的支付程序,但是该基金亦应在现有的海底管理局财务体系下运行。
(一)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
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方向在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具有连贯性。从2018年4月《草案》、2018年7月《草案》一直到2019年7月《草案》,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并未发生变化。一方面,草案规定回应了这一基金设立的最初目的,即填补争端分庭在咨询意见中指出的“无法通过诉诸担保国在习惯国际法中的赔偿责任”的环境损害责任缺口;另一方面,其是超出这一最初目的的,由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所确定的,与“区域”内环境保护相关的其他基金使用范围,这又包括促进“区域”内环境保护领域科学研究、组织相关教育与培训项目,以及恢复和修复“区域”内环境。
事实上,在2015年7月《开发规章框架》中,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使用方向确实仅针对潜在的“区域”内海洋污染之责任缺口。〔7〕与此同时,海底管理局还设想过一个平行于环境补偿基金的“海底采矿可持续发展基金”(Seabed Mining Sustainability Fund)制度,该项基金专门致力于支持“区域”内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研究,以及资助有关海洋保护机构的自身发展。其主要目的在于:(1)促进对深海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2)增进国际社会对“区域”内活动可能造成的海洋环境影响的了解;(3)加强对“区域”内特定环境问题的监管;(4)研究与“区域”内活动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5)加强对利益攸关方传播相关研究成果;(6)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技术支持和援助;(7)从事“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之修复技术的研究等。〔8〕虽然“海底采矿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制度构想仅仅停留在框架性文件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较为正式的规章草案文件中,海底管理局对环境补偿基金与“海底采矿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功能进行了整合,后者的大部分功能被吸收进了环境补偿基金,从而使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用途有了较为宽泛的方向。
(二)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是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重要内容。由于在海底管理局的财务制度中,单项基金具有独立账户,因而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不能与海底管理局持有或管理的其他资金账户或基金项目混同。这就要求为环境补偿基金开辟单独的资金来源。从2019年7月《草案》来看,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有两个向度的来源方式:其一,是从海底管理局持有的其他资金账户中进行挪用,例如,从海底管理局收取的一般性费用或罚款性质费用中提取。其二,是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例如,海底管理局在具体争端中胜诉所得收益、对环境补偿基金进行投资所得收益,以及根据财务委员会建议向资金转入的专项资金等。
由于规章草案文件并未对前述由海底管理局收取的费用等资金来源进行进一步细分,除因基金运营产生的资金以外,其他资金构成部分均可以按照国际海洋法体系中有关“区域”内管理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现行规定进行判断。目前,海底管理局向其成员国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行政开支和周转费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60条第2款第(e)项和《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一节第12条第(i)款,海底管理局的行政开支在其从其他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之前,应当由其成员国根据“按照以联合国经常预算所用比额表为基础议定的会费分摊比额表”缴纳。其中,其他来源包含了海底管理局从事商业活动或接受捐款所得之资金。2020年,海底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名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成本回收基金》(Cost Recovery F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的公报,该公报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成本回收基金”,意在通过收取与海底管理局收到的预算外捐款和自愿捐款有关的,被视为可支出收入的间接费用和直接费用的成本回收项,以确保公平补偿海底管理局所消耗的资源。〔9〕根据“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规章草案文件,相关资金应当也可作为环境补偿基金的提取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关于基金的资金构成中并不包含承包者或者担保国缴纳的专门性费用。事实上,从目前的规章草案文件中来看,海底管理局似乎无意增加承包者和担保国的上述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包者和担保国不会对环境补偿基金产生间接的支付责任。根据2019年7月《草案》,海底管理局因“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活动而向承包者和担保国所收取的费用,其主要是根据矿产资源开发的合同类别项下的特许权使用费率所确定的,合同项下的开发区内已经出售或尚未出售但已经回收的含矿矿石之特许权使用费、固定年费、年度报告费、申请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费等。其中,年度报告费和申请费均有其专门用途。但除前述两项费用的其他费用,尤其是特许权使用费和固定年费本身即具有商业费用的性质,应当属于海底管理局在商业生产中的获利。因而,从这两项费用中抽取合适比例或特定数额的费用作为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亦无不可。诚如我国政府就2018年7月《草案》所提的评论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源于“区域”内资源开发的收益充分体现了惠益分享与环保间的密切联系。〔10〕
(三)环境补偿基金的支付程序
支付程序应当作为环境补偿基金的重要内容。但是,在2018年4月《草案》、2018年7月《草案》和2019年7月《草案》中均未明确规定环境补偿基金的支付程序,仅指出基金的规则和程序将由理事会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制定。但是不难判断,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支付应当包括一般性支出和特定性支出两种情况。如前所述,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用途具有多样性。其中,用于科学研究、技术支持和成果传播等目的的支出属于一般性质的,因为相关目的的实现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而用于填补责任缺口的支出则属于特定性支出,因为因“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具有不确定性,其属于一种风险,因而只有当相关风险确定发生之后才会产生真实的成本负担。当然,风险管理亦可能产生相应的成本,但是这一成本的负担并不在环境补偿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应由海底管理局的行政费用、承包者所缴纳的“环境履约保证金”,以及承包者和担保国应履行的环保义务所产生的日常管理费用所吸收。
有关环境补偿基金的支付程序作为一项财务内部支出项目,应当遵循《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和《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细则》(Financi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的规定。根据相关规定的“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规则,所有资金的使用必须经秘书长授权,认证人员核准款项预算或分款项有关的账目,审批人员核实与合同、协议、订购单和其他承诺形式有关的债务和支出是否符合规定。上述一般性支出或经常性支出可以通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和《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细则》的框架下实现基金款项的拨付。但是,作为环境补偿基金最不具争议的且最核心的功能,填补责任缺口的资金支付则要额外考虑应急性。环境补偿基金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性质的基金项目有所区别,其功能是保障性的和补偿性的。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性质的基金,其支付相关资金后通常具有代位权人的身份,可以向实际责任人进行追偿。因此,侵权损害赔偿性质的基金项目其支付行为通常发生在侵权责任关系已经较为明确之后。但是,补偿性质的基金如环境补偿基金,其并不需要明确责任的划分,只要损害结果产生,即应当考虑对相关损害的修复和控制。事实上,这也符合当下解决“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之现实的、应急性的需要。
三、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制度困境
环境补偿基金的制度设计仍具有不合理之处。一方面,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使用方向决定了该基金的目的实现,但是现有设计下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方向较为宽泛,其中大部分资金使用方向的设计已经脱离了该项制度的设立初衷。另一方面,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缺乏稳定性和可行性,相关安排可能难以使环境补偿基金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应用的效果。
(一)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
过于宽泛的资金使用目的不仅会使环境补偿基金的核心目的受到稀释,同时还会因为环境补偿基金在其他事项中的资金投入过多,而使“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责任缺口缺乏足够的资金予以填补。事实上,环境补偿基金多元化的适用方向在很多利益攸关方的意见中并不被认可。多数利益攸关方认为,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方向及其制度目的应当限于2011年2月1日争端分庭发布的咨询意见,即仅用于填补因“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件中可能出现的责任缺口。〔11〕例如,澳大利亚政府曾提交意见文件称,“根据争端分庭之建议引入环境责任基金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其职能和目的应当局限于解决争端分庭确定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缺口之填补,与该目的有较大不同的事项应当通过其他方式提供资金”;〔12〕深海管理倡导组织认为,环境补偿基金应当专门用于解决无法从承包者和担保国收回成本的因“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补偿;〔13〕牙买加政府则指出,如果将环境补偿基金的目的规定得过于宽泛,可能反而会削弱该项制度在实现共识目标方面的效果。〔14〕
从环境补偿基金的结构上讲,首先,“促进研究可减少‘区域’内开发活动造成环境损害或破坏的海洋采矿工程方法和做法”与“资助对恢复和修复‘区域’的最佳可得技术进行研究”,二者本质上均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针对科学研究,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在2006年第12届会议中就已经设立了“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用以促进和鼓励在“区域”内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资助。〔15〕根据海底管理局的财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5月22日,“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的资本为350.3567万美元,累计利息收入为70.2463万美元,有关“区域”内活动的海洋科学研究支出为58.2617万美元,可用资金(利息结余)11.9845万美元。〔16〕从前述财务数据可以看到,有关“区域”内活动的海洋科学研究仍能够在现有的预算安排和财务结构下有效推进,并不需要通过环境补偿基金来弥补财政空缺。
其次,“与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教育和培训方案本身”的定性就较为宽泛,且与环境补偿基金制度建立的最初目的相去甚远。事实上,在有关“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制度设计中,海底管理局就已经考虑到了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和实施。此外,不考虑市场导向而将“区域”内环境保护相关教育和培训完全视为海底管理局的责任,不仅缺乏效率,而且相关费用即使利用环境补偿基金也难以覆盖。因此,在2019年7月《草案》中海底管理局将教育和培训列为承包者的义务之一,根据该文件第37条的规定,承包者有义务制定培训计划,并对海底管理局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持续开展培训。这一规定本质上即是将市场需求与“区域”内环境保护的公益需求相结合的产物,相关成本主要由市场主体进行吸收,无需再于环境补偿基金中寻求资金覆盖。
最后,“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并有最佳可得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恢复和修复‘区域’”虽然与填补因“区域”内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责任缺口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但是,根据草案文件的制度设计,对“区域”环境所行之恢复和修复本来就是承包者在关闭计划时所应当作出的承诺。当然,“区域”内活动产生的海洋环境污染也可能在承包者已然按照良好行业做法、最佳环保做法、最佳可得技术和相关准则保持了关闭计划的实时性和适足性的情况下发生。如果承包者已经严格执行了其关闭计划,“区域”内环境仍然受到了损害,那么这些损害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归责于承包者,亦无法通过“环境履约保证金”制度予以弥补。而此时所产生的责任缺口之填补可以被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核心任务所吸收,因而无需另外开辟一个有别于责任缺口填补的专门目的。
(二)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具有不稳定性
如前所述,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构成主要包括海底管理局所收费用、罚款或所获补偿即赔偿,承包者和担保国提供的费用支持,以及受捐助所得和投资所得。但是,罚款、接受补偿、接受捐赠和投资所得的资金来源存在不稳定性,作为稳定资金来源的海底管理局所收各类费用亦可能无法完全满足环境补偿基金的现实开支需要,而有关承包者和担保国所应当提供的费用,其制度也并未得到完善。
根据海底管理局的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海底管理局已有56个成员国拖欠相关费用两年以上,其中,未缴纳的摊款数额与海底管理局年度预算下的月度开支基金持平。相关财政缺口已经累及海底管理局秘书处的正常运行,以及其对事务方案的投资实践。〔17〕此外,作为保障海底管理局在成员国摊款所筹金额仍不足以满足其日常预算支出需要的“周转基金”(working capital fund)亦无法向环境补偿基金提供所需资金。一方面,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章程》第5.3条规定,“周转基金为预算拨款提供资金而预支的款项,一旦有了用于此目的的收入,应尽快偿还给周转基金”。因而,“周转基金”向行政费用所支出的款项属于预支性质,环境补偿基金无法在成员国为筹措“周转基金”所缴纳的费用中按比例或特定数额提取金额。另一方面,从海底管理局2019年的年度预算来看,“周转资金”已有款项总额并不足以完全实现该基金的目的,至少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0万美元。〔18〕
相较于从海底管理局的行政开支中截流费用,从承包者和担保国所缴纳的费用中开辟专门的开支项目可能更加可行。但遗憾的是,特许权使用费和固定年费的具体缴纳方式及数额仍在讨论当中,因此无法准确计算环境补偿基金应从中抽取的具体比例和数额。此外,根据规章草案的制度设计,承包者可能因承担环境履约保证义务和强制保险义务而需要支付相应的资金。其中,“环境履约保证金”的款项使用方向涵盖了提前关闭开发项目、移除任何设施和设备、关闭开发项目的后续环境影响残留的监测管理等,且在“环境履约保证金”的退回方面,即使承包者按开发合同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海底管理局仍可留下一部分。而在承包者的强制保险义务中,虽然承保人的支出也可填补责任缺口,但这种商业保险性质的支出需要以特定的商业保险为准。通常的保险合同中,承保人的支出通常亦是以被保险人的责任份额为限,试图在保险合同中突破该限度实现责任缺口填补显然具有难度。
四、环境补偿基金制度的制度完善
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或将逐步发掘这份来自“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价值。从2018年7月《草案》中的“环境责任信托基金”(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rust Fund)到2019年7月《草案》中的“环境补偿基金制度”(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 Fund),均是为平衡在该区域内的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而生的开发辅助制度,但囿于该草案中相关规则的模糊性以及粗糙度,导致该基金在适用范围上过于宽泛难以实现其设立目的,其资金来源途径问题难以保证可持续性,故为促使人类更为审慎和合理地开发相对有限的资源,需要关注且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中的各项不足之处。
(一)限制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
事实上,无论是2018年7月《草案》第4节所规定的环境责任信托基金,还是在2019年7月《草案》第5节中所规定的环境补偿基金,其针对的客体都是以下五个具体方面:“第一,供资用于实施任何旨在防止、限制或修复‘区域’内活动对‘区域’造成的任何损害,其费用无法从承包者或担保国(视情况而定)回收的必要措施;第二,促进研究可减少‘区域’内开发活动造成环境损害或破坏的海洋采矿工程方法和做法;第三,与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教育和培训方案;第四,资助对恢复和修复‘区域’的最佳可得技术进行研究;第五,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并有最佳可得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恢复和修复‘区域’”。〔19〕
一方面,在2018年和2019年草案文本的规划中,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维护主要从事前预防、事后兜底和适用条件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事前预防主要体现在上述草案具体条文中的第二点、第三点和第四点中。其中第二点和第四点又主要针对的是科研方面的投入,即环境补偿基金可用于改良相关海洋采矿工程方法和做法,资助对于修复相关“区域”的技术研究。而第三点表明,草案规划环境补偿基金可在事前用于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教育和培训之中。故以“减少开发活动造成环境损害或破坏”为目的,加大对相关技术研究的投入,无疑是希望通过事前的有关技术革新以更好地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与生态,而对于开发活动中“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教育和培训方案”的资金投入,也主要体现了该笔基金事前预防的特点。第二,关于该基金使用的事后兜底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上述条文中的第一点。供资用于实施任何旨在防止、限制或修复“区域”内活动对“区域”造成的任何损害,其费用无法从承包者或担保国(视情况而定)回收的必要措施。此即该基金产生作用的主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该基金以“应急性”和“补救性”为特色所创立之初衷。第三,上述条文中的第五点则表明了环境补偿基金适用的前提和条件: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并有最佳可得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恢复和修复“区域”。即在恢复和修复相关区域的时候,该笔基金的投放需要遵守“可行”和有“最佳科学证据支持”的前提。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该点之规定是在该基金“事后兜底”下的环节之一,但由于其在适用过程中的前置性地位,以及为该笔基金在相关环境问题产生之后的基金投放标准作出了规定,使得其在众多笼统的规定中呈现出一定的实践价值,故单独列出予以说明。
而另一方面,虽然在2019年7月《草案》中关于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规划基本围绕“事前预防”和“事后兜底(包括适用条件)”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但现行条文中关于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方向存在相对宽泛的疑虑,故建议可对其适用范围予以限缩以明确环境补偿基金之主要功能。
首先,关于2019年7月《草案》第55条第(b)(c)和(d)款,建议在环境补偿基金相关条文的规定中,删除该部分对于促进研究相关开采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对保护海洋环境的基金投入之规定。在2019年7月《草案》第5节之规定中,第55条关于该笔基金的“适用目的”规定主要分为“事前预防”和“事后兜底”两部分,且“事前预防”主要体现在对相关科学研究的投入和对有关人员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培养。但如前所述,其一,关于上述所提及的科学研究,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在2006年就已成功设立了“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且根据其运行的情况来看该笔基金在海洋科研方面仍有结余。因此,不建议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基金投入在规则上出现交叉。若是相关基金之间针对同一问题存在重复规定,在未来具体实行层面恐会招致适用上的困难,并将难以发挥其实效。其二,虽然事前对于相关开采人员海洋保护意识的教育与培训是海洋环境保护体系中一项明显的事前预防手段,但考虑到2019年7月《草案》中海底管理局将教育和培训列为承包者的义务之一,且根据该文件第7节第37条的规定,承包者有义务制定培训计划,并对海底管理局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持续开展培训,此即为承包者的必备义务,无需在环境补偿基金中重复规制,故建议该部分应随海洋科学研究部分一同删除,即建议删除2019年7月《草案》中的第5节第55条第(b)(c)和(d)款与其他基金和规定间存在重复的内容。
其次,2019年7月《草案》第55条第(e)款项下的环境补偿基金使用范围可以被认为是环境补偿基金适用范围的兜底性规定。但是,这一环境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实际上与第55条第(a)款项下的使用范围发生了重叠,其本质是对第(a)款的补强性规定,其中,“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以及“最佳可得科学证据支持”既可以被认为是该兜底性规定得以适用的具体要件,也可以被看作是具体支出金额的评价标准。由于环境补偿基金的偿付程序和财务规则需要由“理事会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制定”,而这一规则在海底管理局的规章制定过程中并未得到落实,因而第(a)款项下的适用范围在实际操作中必然面对认定标准欠缺等问题。是故,可以将第(e)款作为对第(a)款偿付前提的规定,将“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以及“最佳可得科学证据支持”作为环境补偿基金在第(a)款项下进行支出的金额认定标准。
最后,通过对在现行2019年7月《草案》第55条关于环境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之规定的研究和分析,为强化该基金“补救性”和“应急性”之定位,故建议删除原条文(第55条)中第(b)(c)(d)款与其他基金适用范围和其他相关规定存在交叉和重复之规定。
(二)完善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
环境补偿基金设立之目的在于补救由承包者开采等人类活动对于区域环境生态的破坏,但其目的之实现必然有赖于其资金“源头”的存在和可持续性。因此,探索环境补偿基金机制的设立与运行的关键之一是保障该基金有可靠的且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首先,关于2019年7月《草案》第5节第56条之规定,环境补偿基金的供资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构成:(a)向海底管理局缴纳的费用中按规定百分比或数额提取的部分;(b)向海底管理局缴纳的任何罚款中按规定百分比提取的部分;(c)海底管理局通过谈判或因与违反开发合同条款有关的法律诉讼程序而回收的任何数额资金中按规定百分比提取的部分;(d)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按理事会指示存入基金的任何资金;(e)基金通过投资属于基金的资金而获得的任何收入。
具体而言:第一,向海底管理局缴纳的费用中按规定百分比或数额提取的部分。在《协定》附件第1节第12(c)段中具体规定了作为海底管理局临时成员的国家和实体,负有“按照会费分摊比额表向管理局的行政预算缴纳会费”的义务。此外,在2019年7月《草案》中,关于海底管理局征收的费用中,主要有第8部分规定的“年费、行政费和其他有关规费”,且“年费”这一项具体涵盖了“年度报告费”(第84条)和“固定年费”(第85条),而其他的则涉及“申请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费”(第86条)和“其他有关规费”(第87条),且关于“其他有关规费”的具体内容,被详细规定在该《草案》的附录二中,例如,涉及申请核准工作计划、开发合同续签、转让开发合同利益和核准的工作计划、使用合同或核准的工作计划作为担保、商业生产暂停、工作计划的修改、核准经修改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等各环节计划被分别设置具体需要向海底管理局缴纳的费用。第二,向海底管理局缴纳的任何罚款中按规定百分比提取的部分。根据2019年7月《草案》第80条之规定,以第103条第6款的规定为条件,理事会可对本部分规定的违规行为处以罚款。而该《草案》第103条第6款规定,如果发生违反开发合同的情况,或不再适用第5款所规定的“暂停”或“终止”,理事会可对承包者施加与承包者违反行为严重程度相称的罚款。结合上述两条之规定,当承包者有违反开发合同有关规定等情形时,对于该行为的惩处将以理事会为主体,对相关承包者予以惩罚。除此之外,在该《草案》附录三中也详细规定了对承包者进行罚款的情况和对应的处罚金额,如对承包者少报或少付特许权使用费的罚款、对未提交或未提供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的罚款、对虚假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和信息的罚款、对未提交年度报告的罚款,以及“其他”(如环境和其他事故等)。第三,海底管理局通过谈判或因与违反开发合同条款有关的法律诉讼程序而回收的任何数额资金中按规定百分比提取的部分。即当承包者违反开发合同后,海底管理局通过谈判或者在历经法律程序而回收的款项应当作为环境补偿基金的组成部分。第四,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按理事会指示存入基金的任何资金。关于该供资来源或可理解为一种类似于海底管理局执行机关——理事会对于海底管理局所掌握的资产的财政分配。第五,基金通过投资属于基金的资金而获得的任何收入。即允许通过建立可靠的投资方式将环境补偿基金的孳息纳入基金的资金来源中。可见,根据该2019年7月《草案》第56条之规定,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海底管理局所收费用、罚款、承包者违反合同的资金回收、理事会指示划入的专项资金和由该基金的投资收入各自按一定比例提取而构成。
其次,由于可将上述五种资金来源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固定供资和不固定供资,不固定供资在资金来源渠道的数量上呈现出更大优势,故易导致保障环境生态维护的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供应水平面临较不稳定的结果。如前所述,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一定比例的海底管理局所收费用、罚款、承包者违反合同的资金回收、理事会指示划入的专项资金和由该基金的投资收入构成。而在上述五种供资来源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仅海底管理局收取的费用属于一种固定资金来源。根据《协定》附件第1节第12(c),各缔约国按照行政预算缴纳会费是一项公约义务,以及2019年7月《草案》的第8部分“年费、行政费和其他有关规费”的规定中存在年度报告费和固定年费等固定的收入来源;与之相对,其余4种供资来源实际上都依赖于一定的随机性,例如承包者违约时的罚款和资金回收、靠基金投资收益作为基金的新增收入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若仅从供资来源渠道的数量类型划分层面来看,固定资金来源仅占总体供资结构的20%,剩下更能影响该基金体量的80%的资金来源都建立在一些随机性事件之上,因此,环境补偿基金的供资水平极易产生波动,此或将不利于环境补偿基金的有效运用。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即便是在固定资金来源中也存在着大量会员国家拖欠会费的现状,导致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有固定供资来源的规定,但恐将在实践中面临实际难以将相关资金流动分配到环境补偿基金的可能性。即从规则制定层面,虽还有20%的固定资金成为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构成,但鉴于实际因素的影响,对于保障开发区域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维护,理应另寻一些更加切实可行之措施保障以保护海洋生态和环境为唯一目的的海洋环境补偿基金机制的有效运行。
最后,鉴于开发过程中对相关区域生态和环境的不可偏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故建议可以在环境补偿基金的机制构建中采取更为大胆和激进的措施。第一,该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不从行政费用中支出,而是要求会员国另行支付,即在会员国支付会费之余开设一项专设基金。但为了避免类似相关费用的征收面临大量拖欠的情况,同时也为照顾不同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和维持相对的公平性,从而提高相关建议的接受度,该笔相关资金的支付或许可以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并要求开发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开发区持有较多的国家可以按照比例多承担一些责任。第二,考虑到要求会员国额外支付一笔费用的实际操作难度不小,另建议从对相关资源开发有较高兴趣的承包者切入,强化其在勘探开发过程中对于环境保护和维护的责任。例如,由于开发活动将对相关区域的海洋生态和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故建议尝试将承包者拟缴纳的“环境履约保证金”按一定比例纳入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这样,既保证了环境补偿基金的资金构成有了最低保障,同时还可设置相关环境评测机制,即在相关承包者若对环境的影响超出了平均值或者标准值时,将调高由环境保障金纳入环境补偿基金的比例,即实际将由其一方出资的环境保障金实质转化为全体成员国共用的环境补偿基金,从而强化相关承包者在开发过程中的责任感,乃至或可成为倒逼其技术精进的影响因素之一。第三,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在第二点建议上平衡相关承包者权益,考虑是否可以从企业部收益或承包者收益中收取一部分作有期限的信托资本,作为环境补偿基金的补充资金来源。
尽管草案仍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但是有关“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的规范性要求已经具有比较清晰的轮廓。在已有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底管理局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在利益攸关方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对“区域”内活动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的事后兜底,环境补偿基金既符合现实需求,也具有理论基础。但是,一方面,它适用方向、功能追求较为宽泛,会影响该项制度核心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它的资金来源从目前海底管理局的财政状况来看并不可靠。因此,限缩该基金的使用目的,并构建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是保障这项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
注释:
〔1〕United Nations,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Stockholm:UN,1972.
〔2〕高健军:《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
〔3〕Seabed Disputes Cha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dvisory Opinion),Hamburg:ITLOS,2011:66.
〔4〕Shabtai Rosenne,Alexander Yankov,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Vol.IV:Articles 192 to 278 Final Act,Annex VI),Dordrecht,Boston and 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pp.411-412.
〔5〕韩立新:《我国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与制度构架》,《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
〔6〕李志文、吕琪:《国际海底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理想和现实之协调》,《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
〔7〕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Developing a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Deep Sea Mineral Exploitation in the Area,Kingston:ISA,2015:36.
〔8〕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Discussion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rafting of Regulations on Exploitation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Environmental Matters),Kingston:ISA,2017,pp.72-74.
〔9〕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Cost Recovery F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28 January 2020,ISBA/ST/SGB/2020/2.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评论意见》,https://www.isa.org.jm/files/documents/EN/Regs/2018/Comments/China.pdf。
〔11〕Concil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Comment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ISBA/25/C/2),Kingston,2019:8.
〔12〕Australia,General Comments from Australia on Draft Regulations on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Kingston:ISA,2018:10.
〔13〕Deep-ocean Stewardship Initiative,Commentary on Draft Regulations on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ISBA/24/LTC/WP.1/Rev.1),Kingston:ISA,2018:8.
〔14〕Jamaica,Submission of Jamaica Comment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s,Kingston:ISA,2018:22-23.
〔15〕Assembly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Resolution Establishing an Endowment Fund for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Area(ISBA/12/A/11),Kingston:ISA,2006:1.
〔16〕Financ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Status of the Trust Fu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Related Matters(ISBA/25/FC/6),Kingston:ISA,2019:1-2.
〔17〕Financ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nd Related Matters (ISBA/25/FC/3),Kingston:ISA,2019:1.
〔18〕Financ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Status of Working Capital Fund (ISBA/25/FC/2),Kingston:ISA,2019:1.
〔19〕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The Mining Code(ISBA/25/C/WP.1),Kingston:ISA,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