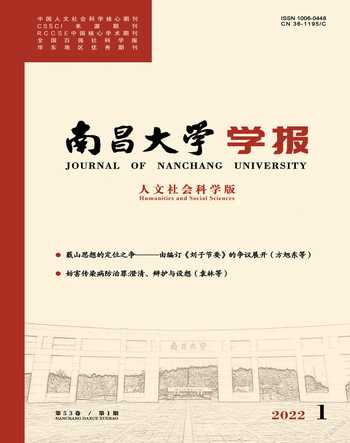参与式文化:实践拓展与理论聚焦
摘 要:“参与式文化”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历了“电视剧粉丝文本”“网络用户泛文化”的生产阶段,正进入“文化的社会化生产与参与式的社会建构”阶段。“参与式”实践和研究议题不断泛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实践和分析的重要框架。作为一种显著不同的文化—社会生成模式,该领域的研究应更聚焦于其“社会化生产”机理与核心价值,就公益与私利、开放与垄断、权力与正义等问题展开论证,以便在政策规划和实践中尽早规避由于社会化生产而出现“文化公地悲剧”,以及因资本、权力等导致文化的结构性异化,进而讨论如何建构开放、公平、正义、有序的参与式文化生态,不断优化其作为文化与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参与式文化;粉丝文化;用户生产;文化社会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2)01-0089-10
文化与社会总是相互建构的,需要“以一种对文化,特别是对艺术新关系的生产的思考,来创立新的社会形态,观察和评论当代的生活的形态”[1](P1)。表现在理论视域中,“大众媒体—大众文化—大众社会”的系列理论即是前一阶段社会主流文化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分析的宏观框架。因而,是否也可以找到某种类型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当代文化生产的特质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当代文化生产最显著的特征是“网络化”,互联网不仅扩容了传播渠道,复杂了传播结构,改变了内容生态,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模式与生产能力,由此也有“网络社会”的当代特征概括。然而“网络媒体—网络文化—网络社会”的概括虽然显化了当前文化、社会的结构特征,却未能充分揭示其机理。相比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专业化生产,“参与式”机理不仅是网络文化内容生产的最大特色,而且逐渐形成了高度依赖普通用户“参与”的全新的以各大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文化经济模式,“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也在当前文化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这种“自觉”有无道理,原因为何?这一概念能否准确概括当下文化发展的机制特征?有必要在文化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维度进行历史性梳理与考察,从而判断其作为“文化—社会”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以及发展趋势研判的可靠性。
“参与式文化”是一个概念提出近三十年仍在发展的实践和理论领域,有着广泛的“多元内容研究以及不同传播理论与其内在关系的解读。”[2](P14)鉴于互联网具有超越传统的媒介属性,影响已扩散到社会乃至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网络参与式文化也早已不囿于狭义文化层面,甚至延展到了雷蒙·威廉斯所指的“全部生活方式”层面。本研究将参与式文化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分為三个阶段:(电视剧)粉丝的文本生产阶段、网络用户泛文化生产阶段、文化的社会化生产与参与式的社会建构阶段,以期基于对不同阶段实践发展和理论重点的分析,探讨何为参与式文化最核心的机制及其理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一、粉丝世界的盗猎者潜能
1993年,亨利·詹金斯研究了美国电视剧粉丝基于原文本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将其总结为“参与式文化”概念,以指涉“一种邀请粉丝和其他消费者积极参与新内容创作和传播的文化形式”[3](P290)。
(一)电视剧粉丝的创作
在此概念最初提出的时代,粉丝文化已经开始挑战“观察主体的意识形态地位”,身份边缘、流动、分散、地下,不被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虽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无法统计其数据,但却是一种具有显著传播性的社会事实存在。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其真实规模已极为庞大,也出现了极为显著的文化行为特征与积极的文化作用。以科幻文化为例,科幻粉丝的生产与聚集最早可追溯到雨果·根斯巴克创办在《惊异故事》(Amazing Stories)上的信件专栏。正是因为作者、编辑和粉丝之间丰富的互动使得科幻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成为一种极为独特的题材。由这一文化发展而来的世界科幻大会自1939年创办至今,已成为科幻粉丝圈存在和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类似的粉丝创作被冠以“同人”之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给同人艺术提供技术支持和评价的指南性读物也开始出现,如有关同人音乐的《APA-同音》(APA-Filk)、同人绘画的《艺术论坛》(Art Forum)、《数据志》(Dataine)等。各种媒体粉丝大会内容逐渐多元化,有同人视频播映、同人文本阅读会、同人艺术家研讨会等,也为粉丝艺术家展示、销售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市场平台,粉丝画被拍卖,杂志被出售,表演被上演,录像被放映,各种杰出成就奖的设立等。
(二)粉丝研究三大框架
早期理论在文化的生产主体、内容形式、生产方式三大方面框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当时此类文化的生产主体为电视剧粉丝及其群体,因为只有“粉丝”才对原文本有极其深入的了解、期待、意见,有迫切地表达,或将“观看转化为某种文化活动”的冲动,“与朋友分享对节目内容的感受和想法”,加入同兴趣“社区”的行动。相比传统受众,“粉丝”有着显著的身份认同,往往基于身份而传播集体信息,共同创作或解决问题[4](P41)。就内容形式而言,参与式文化是基于大众媒体所生产文本的再创作。正是某种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激发了粉丝们对节目的不同创意改写和文化制作[5](P87),原文本成为他们自己文化产品的原材料,也是他们社会互动的基础。
文本盗猎(poaching)是最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粉丝作为“漂流者和偷猎者,总是在文本之间穿梭,愉快地创造新的互文连接和并置”[6](P67),其方式是复制原文本内容,并将其运用到新作品的创作中,他们试图在商业流通文本的空白和边缘地带建立自己的文化。所谓盗猎指一种相悖于主流或体制化版权规则的行为,这构成粉丝作品创作和传播的主要矛盾。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可能性,粉丝作品不能通过大众传播渠道或其他合法的市场渠道进行传播,仅在小众的粉丝圈内传播。即便粉丝发展成为同人艺术家,也被禁止作品的商业流通,因而进入主流专业媒体艺术世界的机会非常受限[7](P46),这表明粉丝创作实质性参与生产的机会很少。大多数人都没有深入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的机会,无权决定大型电影院的播放日程、广播的内容或者大型连锁书店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因此对于制作方信息“完整性”的尊重带来的后果往往意味着消灭或边缘化那些反对的声音。经济和社会壁垒阻隔了粉丝文化进入文化生产方式的途径,大部分粉丝“在主导表达状态中都处于‘未标志、不可读解且无法象征’的地位”[7](P25)。
(三)参与的可能性与潜力
可见,詹金斯最初提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时的重点是分析粉丝生产的逻辑——“盗猎”和“文本”,并不是严格的“参与”和“文化”。虽然书中对“参与”机理的研究仅集中于“盗猎”,但这一概念敏锐地查觉到了某种文化发展结构性变动的潜在力量,并对此进行了极为精准的概念提炼。因而,这一阶段全部理论价值可以归结为“受众生产力的发现”。粉丝不再是大众文化中“被动的受众”,也不只是被动地消费媒体,或“无声的生产”,而是媒体内容积极的批判者和参与者,对大众文化进行适当地改造和延伸,生产出新的文化和新的社区,文化生产逻辑从“观众文化变成了参与式文化”[4](P60)。粉丝基于原文本的创作,形成了作者和读者间对文本所有权、对意义阐释的控制权的争夺[7](P23)。随着同人文化的发展,也打破了在“职业”和“业余”间明显的分界,消费生产者(Prosumer)的出现和身份的变迁意味着文化生产结构的松动。这种受众生产从一出现即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低门槛,艺术表达和公众参与的空间增加了;因为身份认同和社区化,参与式文化在某种形式上能够将知识从最具经验的群体传递给新手们的非正式指导关系的文化[8](P3)。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粉丝成为同人艺术家,从业余转为专业人士,粉丝文化成为一种“‘转型的专业性时刻’,粉丝文化生产本身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它作为一种专业出版训练基地的作用”,可能是“从媒体提供的符号原材料上建筑起来的整个文化体系”[7](P47)。
电视剧时代尚处前数字化文化阶段,粉丝除了通过胶印和摄影术等之外,不太可能拥有专业的图形和视频制作工具,传播主要依靠邮寄和参与粉丝大会的方式。在传播分享方式、可再处理的文本内容、可用的媒体工具、专业的图形和视频制作工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受众文本再生产,真正在互联网时代才实现更大的突破,从受众拓展至用户,超越盗猎而真正参与,从文本发展成为文化。
二、网络世界的文化生产泛化
进入网络时代后,参与式文化突破了“粉丝生产”,以及“基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文本再创作”的具体指向,成为网络社会中文化生成的主流模式,研究的视野也有了极大扩展。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文化生产,参与式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参与式文化对传播的实践影响,以及基于相关学科对网络参与式文化进行的理论性批判等方面都展开了极为丰富的研究[9](P27)。如果从文化事项和形态出发分析相关实践历程,可见有两种类型的文化实践相交织演进的并存:一类是粉丝文化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即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狭义的文化创作行为;另一类是Web2.0之后的各类用户网络参与行为,其意指已扩展到一切经由互联网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实践。
(一)粉丝文化在网络空间的繁荣
计算机技术使得参与式文化开始“数字化”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架构,互联网生成了一种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以从空间的任何位置访问和输入的媒体环境。特别是web2.0阶段之后,作为一种文化,粉丝吸收并回应新媒体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普通消费者有了更为便利的方式对媒体内容进行保存、注解、挪用和再利用[10](P8)。
粉丝文化、粉丝社区的网络化发展开始于1990年代末,初期通过网络论坛和电子公告板等形成了定性清晰、有界,且结构化的网络,方便了粉丝的创作、分享、传播、交流[2](P7),使粉丝文化生产在量和质方面都全面提速。粉丝创作的同人小说、同人漫画、同人音乐,以及粉丝组织间协作都快速发展。据再创作组织OTW(The 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资料显示,2013年其平台“提供了超过380 000个任何可能来源的粉丝小说作品供粉丝在线阅读、下载、评论、分享和讨论”[11](P543)。
粉丝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的现象,它邀请了多种形式的参与和不同层次的参与[12](P2),例如,许多音乐网站允许用户创建和共享音乐播放列表,依靠已创建的音乐作品,定制特定风格的电台。网易云音乐歌单一栏中每天滚动更新的歌单数约在1 295个左右,且不乏收藏、播放、转发过数百万的私人歌单。由于专业生产的内容始终是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原素材,这类基于某一文本的内容再次创作依然是网络空间最大规模的文化形态。游戏网络直播行业即是游戏玩家在原游戏基础上创作的攻略、技术解说、游戏评测等相关内容。圍绕电影产业也延伸出较多的粉丝再创作类型,以字幕组、电影解说、电影杂谈等各类片段剪辑和再创作为主。由此可见,互联网时期粉丝基于大众文本的再创作行为已极为普遍。同时这类成果绝大部分制作成本极低,多采用非直接售卖,免费收看吸纳大规模受众(流量)以实现二次售卖或流量变现的方式运作,巧妙地避开版权困境,甚至部分地实现了合法化。随着网络技术和文化生态的发展,这一形式的文化生产门类式样越来越多元,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甚至极大限度地调整了“大众文化”和“新媒体文化”的关系,实现了大众文化的专业生产与粉丝文化实践的相互借力和共存。
(二)作为广义内容生产的网络实践
网络正不断消解文本创作中原本清晰的各种边界,文本被无限次、多层级引用、演变,原本的粉丝因再创作成为新的偶像,网络空间的文化概念很快超越了传统意义所指,摆脱了对大众文化的“成品文本”依赖,不再局限于使用大众文化中的人物、情节来创作相关作品,其实践已超越了狭义的文化创作,囊括了一切普通用户生产分享传播的各类型内容,包括碎片化的个人观点、言论,任意文字、图片、视听内容,即使是自拍这类日常行为,虽然只有“与社区或群体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才能够被认为具备参与性”[8](P11),但也是普遍意义上的参与式文化形式。
互联网空间的参与量之大是超乎想象的,形式包括电子邮件、网络搜索,以及Facebook、Instagram等各类社会化媒体的网络行为与内容上传。与传统社会和大众社会的文化生产相比,“参与性”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互联网,尤其是Web2.0之后网络文化的主要特征,因而成为互联网文化生产传播中最具解释力的框架。各类数字及在线文化类研究都有所展开,内容极为多元,成果也较为丰硕。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粉丝圈等亚文化社群的文化生产活动,而逐渐与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乃至赋权现象相连,社会化发展和运作机理变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三)社会化机理:从雪球文本到集体智慧
网络空间的文化生产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运作机制——雪球文本和集体智慧。“雪球式”机理是指围绕着特定题材或者内容,把相关的跨媒介叙事和散落的文本碎片滚动整合到一起,形成超越原意义的全新文本。在许多现象级传播事件中,以及“爆款”推文、视频等个案中,都可见雪球式文本创作和传播的机制。“雪球”的制造过程直观地体现了粉丝与创作者身份的相互融合[13](P135)。由于生产与传播的提速,从内容生产到新偶像形成都从盗猎式进入了“雪球模式”,经典文本如漫威系列、哈里·波特等不断被利用重写,核心IP会如雪球越滚越大。这种逻辑在偶像与粉丝的互动结构中同样存在,表现为粉丝在文化再创作中成长为偶像,不断滚动累积粉丝,持续滚动生成更大的粉丝—偶像群体。这种机制是高度社会化的,普通人可能因一个不经意的文本及传播事件而快速成为一个很多粉丝关注的“草根偶像”。
另一模式被皮埃尔·列维描述为“集体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由于媒介消费中的接入点正是粉丝参与媒介文本再生产的生长点[14](P101),每个人作为知识链中的一环,一起工作,共同分类、组织、建立信息,以一种自发的协同机制深度参与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去[15](P18)。世界正在被参与式的知识文化所改变,基于网站平台的词条、百科、知识共创、共同编辑、共享类型的知识生产不断更新,以认知、合作和协同三种维度的参与式文化为基本架构,成为当代知识生产最主要的机制。“Yahoo Answer”“新浪爱问”、网络百科、词条创建、编辑等内容生产,显示出了巨大的社会性知识生产能力。
雪球机制和集体智慧都表明文化生成的社会化机理已成为主流,印证了实践中网络空间文化生成在工具、技术、生态等维度的全面社会化趋势。为了鼓励参与式文化生产,互联网平台在技术层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社会化改造。平台提供技术方便用户内容生产的实例普遍存在,各类搜索引擎不断丰富可接触资源的多样性,实现了文字、图片、影视、音频资源的全覆盖,这种便利的可检索性极大方便了资料内容的准备。例如美图、快剪辑等各类图像、视频、音乐制作、音频编辑软件、配音小程序同时提供有大量的素材,使非专业用户的文化内容创作更为便易。这甚至引发了一场新的创造性资源发掘和争夺的竞赛,网易、虾米等音乐平台不断推出音乐原创扶持计划,Bilibili等视频网站的剪辑大赛等,进一步推动了参与式文化的实践。倾向于水平整合的媒体集团的经济趋势表现为鼓励图像、思想和叙事在多种媒体渠道之间流动、共享,并鼓励更活跃的观看模式,许多文化机构认识到公开可访问的数据资源(公开数据)可能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与机会。英国广播公司(BBC)后台项目“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允许公众参与开放数据的重用和重组,鼓励人们利用BBC发布的公开数据进行二次创作。
参与的社会化正颠覆着传统文化经济学模式,形成了抖音、Bilibili等为代表的高度依赖网民直接参与生产的互联网文化模式及相应的平台经济,围绕参与度这一核心竞争力,各类平台以数据为资源,以“数字劳动”为生产力建构了新的产业结构及盈利模式。特别是大量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出现,标志着由普通生产的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向更为专业的生产体系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开始新的整合。
三、生活世界的社会性建构
互联网不只是内容平台,也是一切社会信息联结的媒介,文化创作的征集、对话、沟通、交流、发布、分享、传播等一切环节都必然地利用网络资源,经由网络或向网络集结。以网络为基本交流沟通工具的线下艺术及文化创作、传播等行为自然地出现了结构上的网络化。文化生产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使得在网络空间高度发展的参与式机制不仅对现实的文化生产、传播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着作为社会意识的广义的文化生成,参与式机理真正从文本层面和网络空间全面进入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层面。
(一)参与文化专业性生产
参与式机理正广泛应用于传统专业化、制度化的文化生产领域,并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全面改造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机制。参与式使当代文化生产实现了逻辑倒置,粉丝生产将文化从专业生产逻辑转向非专业生产逻辑,普遍的参与机制又将这种非专业生产逻辑全面引入文化的专业生产领域,部分复原了大众文化之前文化生产的最初样式和传统。
网络文学是最早和最典型的社会化、网络化文化艺术创作的类型。在很多国家,互联网推动了诗歌复兴运动和文学创作的转型。我国网络诗歌也经历了1998-2004年的“诗歌网站和诗论坛”阶段,以及2004-2008年的“博客诗”阶段,甚至45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驻站创作者数量已达1 400万,其中签约作者数量达68万人,47%为全职写作[16](P9)。网络文学类型极为多元,而且以IP授权模式为核心,在与电影、电视剧等产业的互动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模式。
新闻领域的变化表现为传统新闻机构与微博等社交媒体用户内容生产之间的合作,使生产、复制、发行等环节都大大简化,这导致对媒介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专业人士的手中,正将新闻、出版等行业“大规模业余化”。美国甘内特报业旗下90家报纸编辑部甚至以“众包”形式展开与读者的合作。
全球草根文化运动中,互联网既是连接、交往、传播的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生產关系模型。许多文化艺术项目从设计之初就融入了参与式的生产机制,通过各种形式的众包或参与设计其作品。经由激浪派(Fluxus)的偶发艺术和行为表演予以理论化的观众“参与”,开始变成艺术实践的常态,艺术作品已经完全融入互动的文化中,艺术家探索着社交性与互动的秘密……,尝试建立足以生产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样式[17](P22)。
参与式文化生产逻辑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再显活力。詹金斯在观察桑巴舞时指出,民间艺术家早已掌握了一些参与式学习的核心原则——创造性的表达方式被融入日常实践中。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普遍存在,赛龙舟、藏族锅庄等传统文化正以各种方式激活和挖掘各类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被大众文化打断的民俗文化的某些部分,在电子文化时代开始回归,“不同形态的文化能够导致或实现不同方面的参与性”[8](P8)。
参与式文化引发了文化经济学的深层转变,见证着参与式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加速发展[18](P3)。参与式机理在制度化维度开始探索解决“版权困境”,以及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放资源、合理使用(Fair Use)等理念正在更大范围内被接受与实践。一些以用户内容为主的网络平台正在探索集体购置版权,以提供给用户再创作。平台或网站为便捷和保护用户生产,正在探索个人版权保护的有效机制,例如微信公众号版权方面的特别条款,以及国外部分网站对用户创作版权提供的相关法律、咨询、谈判等业务。社会性生产的投资、收益等模式也在探索中,各视频网站的流量分成以及内容变现机制也随着业务类型的不断丰富而在持续完善之中。
(二)社会建构的参与式显化
参与式文化的外延正从狭义的文化层面,向雷蒙·威廉斯所界定的“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层面拓展,呈现为当前文化和社会的“参与性转向”[19](P267)。参与式文化作为“当代知识建构的社会本质”,通过改变公共记忆的形成方式以及某类政治事件的运作模式等,初步彰显了其显著的社会建构能力。
参与式文化的社会建构能力源于其本质,即它是一种有着紧密社会性联结的文化类型。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粉丝看似私密的观看行为具有实质性的社会维度,有着极强的社会可见度(social visibility)。粉丝阅读本身即是一个社会过程,独立个体通过对原文本的解读、再创作和传播,形成身份认同和社群及圈层,使意义的生产不再是单独、私人过程,而是社会化的公开行为,是一种互动共生性的新型文化生产形式[7](P251)。社会性经个人阐释和与其他读者持续的互动而逐渐成形并加强,社会影响更在于它突破领域划分,成为社会生活的日常文化,重新诠释着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与各层次的社会表达和社会诉求高度同构。
参与式文化理论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与公共记忆有关,特别在建筑和博物馆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由于社交媒体造成了遗产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性,被社交媒体塑造的参与式文化可用于深入分析人们如何在不断的交流中生产、组织和分享各种内容、观点、信仰、依恋,甚至抵触,从而继承经验,建立新的记忆和身份[20](P461)。2011年奥地利举办的“参与式文化时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全球研讨会即为代表。“众包”模式被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中,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报纸数字化项目曾发动公众对数字化内容进行转录、校对、改正、评论、添加标签等。
由于粉丝与网民特殊的连接方式,从公共关系领域到政治参与领域,参与式文化都呈现出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2016年“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中,粉丝在践行政治话语时具备主动参与性、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媒介素养,以及强大的集体认同感,而上述特质与他们参与偶像明星形象建构与维护的日常网络实践直接相关[21](P327)。“参与”一词在文化研究和有关参与性政治的政治学和哲学研究之间搭建了桥梁。一方面,网迷群体的实践已经取代政治,成为中国人日常价值的中心[22](P46),年轻人通常直接采用来自流行文化的語言,通过参与文化启发下的机制和实践来表达他们的社会愿景,获得“感官共振”的沉浸体验[23](P96)。另一方面,社会化工具越来越多地让群体具有生长在一起且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24](P234)。因此,詹金斯直接将参与性政治界定为“出于政治目的的文化参与机制”[8](P161),认为融合文化中的媒介粉丝借助集体智慧形成的知识文化将改变“民族国家的运作方式”。对此,雷蒙·威廉斯甚至乐观地认为,“技术是漫长革命征途上的当代工具,我们正在走向有文化素养的、参与式的民主”[25](P151),应通过消费、批评、生产、参与,以及社会联系,将文化参与的机理发展成为更有意义的公民参与、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更好地参与式生存。
四、理论向文化社会化生产聚焦
通过对参与式文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三阶段梳理可见,“参与式”用以广义的文化分析,表明“参与式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重要工具。然而,无论其适用范围有多么广泛,其被采用的出发点都是对“社会化生产”价值、机制的发现和运用。因此,文化—社会的“社会化生产”实践仍存在较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路径优化才是应当聚焦和深入研究的理论重点。
(一)文化、社会、参与的关系理性
对于“参与式文化”理论的讨论焦点在于将“文化”的意指拓展至社会层面,切入社会这一广义文化视角的实践理性源自当代文化社会发展的同构性。
一是文化与社会同构。文化是现代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在文化接触和文化生产方面都极为显著。人们从来都是通过文化接触行为来建构个人身份和社会定位,差别在于由文化生产主体差异而形成的文化类型差异。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生产和大众社会的专业文化生产都显著地作用于社会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生产与社会的互动逻辑中,生产与接受有显著的分割,生产始终决定着接受。互联网生态中的“参与”性实践,突破和消解着生产与接受之间的分割,在文化与社会互动中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
二是参与即社会定位。在“参与式文化”研究中,参与是层级化演进的。接触和涵化作为文化过程的完整环节,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文化本质上都应该是参与性的。在文化生产小批量、精英化阶段,文化接受的可达范围、速度等都不影响其“卖方市场”格局,受众在文化生产全过程中的参与度对整体并不重要。内容与渠道双双扩容后,文化生产呈现为“买方市场”格局,受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单纯的购买、收看等初级参与度决定着特定文化价值的完成和实现水平。粉丝文本以盗猎式进入大众文化生产体系,在网络时代实现部分合法化,向传统艺术领域渗入,真正参与到现代文化生产的制度化格局中。当文化内涵扩大到社会层面,成为当代记忆建构、意识凝聚的主场,这种文化逻辑参与的是社会建构、实践的真实维度。由于文化与社会、生产与接受的同构,当代人“如果无法对公共生活和文化做出贡献,也很难在社会中找到让自己满意的位置”[8](P25)。这即是过去被认为是“社会的”问题如今被认为是“文化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三是概念可相依界定。正是基于二者的关系本质,参与—文化—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在其概念的重新界定中已清晰可见其依从度。在当代,参与的概念更多被解释为“人们能够进行集体的或个人的选择进而对共享经验产生影响的文化属性”[8](P12)。由此文化被重新界定为“一个社区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的一套共同假设”[26](P156)。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文化可以分为参与性和非参与性两种,一种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越明晰,参与性越低,社会分层现象越明显。
由此可见,“参与式文化”的理论价值需要在考察对象的泛化中不断地回溯,聚焦于“参与内核”,进而真正发现“社会机制”。在各门类文化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参与式文化”概念理论的应用正在不断普遍化,可见其对文化—社会的当下及可预期未来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二)关注社会化幻象和障碍
在“参与式文化”研究的早期,曾有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各种乐观判断,其机理被很多政府、机构所实践。然而,现实中对于什么是有意义的参与以及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参与尚缺乏共识,也存在很多文化社会层面的失序情况,需要形成一套更成熟的治理体系来调整参与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壁垒。
一是加剧的场域斗争。参与式文化的美好构想是普通人突破文化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的边界,实现个体自由表达,推动文化社会化的进程。然而全面开放的全民参与仍然是一种理想,资本、技术、利益的极化与集中,使得文化生产领域本身存在的地域性资源竞争、民间/主流话语权争夺、权力/权利分配、文化能力/资本差异等矛盾都显著放大,“参与鸿沟”(participation gap)正在不断修正“数字鸿沟”,可能更进一步加剧文化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资本的绝对优势。大众传播时代少数媒介机构的文化垄断被互联网时代普遍的文本盗猎行为冲击,普通人文化生产相关的部分权益基本在旧框架中已实现了大多数免责,甚至部分合法化。但这不代表真正公正、合理的文化生产权益结构业已成型。在参与式文化发展的早期,粉丝和媒介之间彼此独立,网络时代的用户依托于平台,版权问题不仅更为复杂化,而且与文化相关的权力已被独立出版商、视频共享网站、合作维持的知识银行和粉丝创造的娱乐所篡夺[18](P3),新媒体集团已经直接将粉丝和受众的参与行为资本化了,“饭圈”从文化形态变为乱象即是典型一例。
三是技术的隐匿控制。参与式文化实践领域的资本权力被技术逻辑所隐匿,正以一种技术无意识的状态建构社会。媒介技术与算法自“首次生产”的步骤开始,就已然通过用户的参与完成了对整套文化体验的形塑,是带有后霸权主义特征的权力自组织形式[27](P996)。经由互联网的文化与社会的公共参与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营利性的共生模式,但参与主体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与广大用户相对的平台越来越集中,在技术、资本、管理权限等方面都存有优势,而生产大量内容的用户甚至将其日常生活实践都变成了平台的利润之源,这将导致参与式媒体与文化的实践开始趋向封闭。
四是价值的公私之争。参与式文化改变了利益结构,需要更为审慎考量其中的价值悖论和价值取向。作为个人创作,参与式文化有大部分出自个人表达的动机,宣泄個人情绪,以个人化的标准传播个人价值,这就可能使这种文化“陷入仅满足于个人情绪需求但效率低下的行为模式中”[26](P178)。暗含“隐喻表达和心理需求”[28](P175)的个人创作因传播量大而获得经济利益后,其文化价值可能让位于市场和资本利益。然而,文化在社会范围的传播,其社会动机、公用价值和公共价值更为重要,参与式文化框架内,原本个人化的创造性拥有了公共的属性,却多被用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可能成为“文化公地”,社会性生产的认知盈余中可能获得仅是公用的价值(communal),但对公民(civic)和整体社会并无益处。
(三)优化社会化参与机制
作为期待,参与式文化“包含了一系列针对社会实践该如何促进学习、赋权、公民行动和能力构建的理想”[8](P185),有着深远的时代价值,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仍在发展中,需要充分发展其核心机理和社会创新,保持开放、对话和可持续性,使其更好地“塑造社会共识和认同”[29](P117)。
一是重构开放式架构。参与式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文化生产、社会建构的社会化,因此应基于公共利益与私有价值的平衡而优化其开放性。参与式文化突破了传统的“把关人”模式,从先筛选后出版到先出版后筛选,形成了更合理的创作环境和平台筛选机制。同时创造大量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机会,这种模式需要更细致复杂地考虑传播控制的中间环节,如果只进行简单发布平台端的删除,就会出现原文本不断被网民戏仿、接力传播的社会文化怪象。
二是理顺治理逻辑。“在线参与平台中的各种力量应该从一种开放的符号学治理维度去理解”[30](P91),需要进一步优化参与式机理,发掘创意社会中商业逻辑与文化逻辑间交融的可能性,调整理顺综合性治理的逻辑。文化创新往往出现在没有普遍意义上利益关系的时候,一旦成为某种利益的实现与分配的时候,文化创新就会被垄断,多数人的创造性行为就会转变成少数人的文化权力[31](P465)。在草根和参与式文化被资本收编的同时,能看到大量用户利用商业实现的牟利行为。参与式文化治理不能简单地割裂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虽然大部分文化和知识生产在本质上是更偏向社会化而非商业化,但是,文化社会化生产实践中的商业化现象从生产性机制保护、可持续条件创建的维度看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三是赋能社会化工具。基于参与式逻辑而搭建的社会化工具应进一步综合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开放存取(Open Access)等协议共识,不断优化参与式文化的技术实现。社会化工具使得社会生活具有高可见度和可搜索性,成为新的社会契约达成、社会资本累积的重要因素。参与式和分布式协同优化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只有足够多的用户想把某一工具或平台视作协调性资源,才可能共同参与;因为共同的参与,其内容才可能真正地成为共享和协调性平台。因而,作为社会工具的参与式平台和媒体,需要不断更新开放与参与的软件和机制,才可能跨越话语、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既有的工具化分割与限制,不断更新社会文化生成过程中参与的视野拓展、品质提升、模式更新、机制优化,以更深刻地定义“参与式文化”建构的意义,更高效地实现内容赋权赋能。
四是深化素质类教育。文化品质优化与可持续性问题会挑战参与式文化的发展价值。参与式文化在不同阶段都有低俗化的倾向,其整体水平的提升更是一个社会长远的发展问题。因为粉丝文化的发展必然通过更大粉丝群体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美学惯例(aesthetic conventions)、解释协议(interpretive protocols)、技术资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和技术能力(technical competence)来形成的[32](P43),因此参与式文化应该从内容生产、作用机理等多维度进入政策设计规划和职业教育体系。同时,更广义的文化和社会素养的提升更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基于参与式机理制定、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
五、结语
不可否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实践已开始自觉启动了民众参与机制,创建自媒体平台,合理利用网络活跃群体为地方文化、经济、社会服务,但还远未进入前置价值取向并展开总体规划和引导的层面。参与式文化作为当代最为显著的文化生产与社会建构模式,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化力量服务于文化和社会的优化,成为当代文化社会治理的重大议题。政府作为公共价值协调控制主体,需要调控、纠正各种力量对社会性文化生产的不良控制以及结构性扭曲,应尽可能规避新文化与社会意识建设中的“公地悲剧”,在保证公共价值的前提下统筹开放性与可持续性能力,建构公平、正义、有序的参与式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1]尼古拉·布里奥.后制品:文化如剧本[M].熊雯曦,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2]Bennett Lucy.Tracing Textual Poachers: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n Studies and Digital Fandom[J].Journal of Fandom Studies,2014 (1).
[3]Jenkins Henry.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4]Jenkins Henry.Fans,Bloggers,Gamers:Media Consumers in a Digital Ag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5]Jenkins Henry.Star Trek Return,Reread,Rewritten:Fan Writing as Textual Poaching[J].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88 (2).
[6]Duffett Mark.Understanding Fandom: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edia Fan Culture[M].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3.
[7]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亨利·詹金斯,伊藤瑞子,丹娜·博伊德.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M].高芳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9]谢新洲,赵珞琳.网络参与式文化研究进展综述[J].新闻与写作,2017(5).
[10]Jenkins Henry.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M].Boston:MIT Press,2009.
[11]Lothian A.Archival Anarchie:Online Fandom,Subcultural Conservation,and the Transformative Work of Digital Ephemer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3(6).
[12]Jenkins Henry.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Participatory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2.
[13]赵宜.从“文本盗猎”到“媒介雪球”——青年文化承诺下的IP进化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14]赵丽瑾,侯倩.跨媒体叙事与参与式文化生产:融合文化语境下偶像明星的制造机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6).
[15]Surowiecki James.The Wisdom of Crowds[M].New York:Doubleday Publishing,2004.
[16]陆健.《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7)》发布[N].光明日报,2018-05-21(9).
[17]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M].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18]Delwiche Aaron,Henderson Jennifer.The Participatory Cultures Handbook[M].New York:Routledge,2013.
[19]Jenkins Henry.Rethinking “Rethinking Convergence/Culture”[J].Cultural Studies,2014(2).
[20]Smith Laurajane.Heritage and Social Media:Understanding Heritage in a Participatory Culture[J].The Museum Journal,2013 (4).
[21]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2]朱丽丽.网络迷群体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编辑学刊.2012(2).
[23]喻发胜,张玥.沉浸式传播:感官共振、形象还原与在场参与[J].2020(2).
[24]克莱·舍基.人人社会: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25]Williams 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M].London:Fontana,1974.
[26]克萊·舍基.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M].胡泳,哈丽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7]Beer David.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J].New Media & Society,2009 (6).
[28]陆晓芳."震惊"与"沉浸":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J].文艺理论研究,2021(4).
[29]陈世华,李玉荣.公共议题中符号的表征与传播[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
[30]Ganaele Langlois.Participatory Culture and the New Governance of Communication:the Paradox of Participatory Media[J].Television & New Media,2013 (2).
[31]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2]Hellekson Karen,Busse Kristina.The Fan Fiction Studies Reader[M].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4.
Participatory Culture:Practical Expansion and Theoretical Focus
DUAN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Guang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Communic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 Zhou 510420,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in the Internet era,so that the UGC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 of Internet cultural production.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od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participatory mechanism again.Ba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to adjust individual value and social valu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Only in this way we can avoi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tructural alienation caused by various interests contention.At the same time,an open,fair,just and orderly participatory ecology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that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n truly become a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culture;fans culture;UGC;socialized production of culture
(责任编辑
陈世华)
收稿日期:2021-09-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人口结构变迁与文化产业互动机制研究”(18BXW103)
作者简介:
段莉(1977-),女,甘肃兰州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文化产业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