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到底好在哪里?
谭保罗

春节前后,2021年的城市经济数据出炉,给人一种“洗牌”的感觉。
一线城市的四大金刚之中,北京和上海超过了4万亿,分别为4.03万亿和4.32万亿,成为我国最先晋级“4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同样保持了稳步增长,GDP分别达到2.82万亿和3.07万亿。
四座城市经济体量稳步提升,充分显示了中国一线城市经济的韧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每一位兢兢业业,同时忍受着城市扩张所带来巨大通勤成本的工薪族,无不为城市经济总盘贡献了微小而不可或缺的份额。
现在,一种观点认为,从体量上看,一线城市的传统格局可能已经过时。
首先,北京和上海晋级“4万亿俱乐部”,明显拉开同广州、深圳的差距,可以说独为一档。同时,后面的重庆和苏州也追了上来,其GDP分别达到了2.79万亿和2.27万亿,和广深的差距并不大。因此,一线城市的阵营未来是否应该加入重庆或苏州?
然而,一线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量化的概念,它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了GDP。
城市的GDP数据到底是多少,和工薪族,特别是白领、中产阶层的关系并不大,真正关系的巨大的是GDP数据中的服务业(第三产业)状况。
服务业到底有多重要?它让你的生活更有品质,因为有更好的生活服务提供给你,一出门就有按摩店、理发店等。显然,这些只是对服务业的字面理解。
城市服务业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决定中产阶层是否可以在这座城市安身立命,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合适伴侣、组建家庭和安居乐业的概率。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很多GDP数据非常可观,甚至有着晋级一线之势的大工业城市,年轻白领面临着严重的择偶难。择偶难,在一线城市不是很普遍吗?大家要求高而已。不过,在一些大工业城市,择偶难则是真的难,不是矫揉造作。因为在于,无论线下撮合,还是通过交友软件、相亲网站等线上方式,可以选择的“合适约会对象”并不多。
长三角的苏锡常和广东东莞、佛山无不是著名的工业强市,我曾和其中某座城市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交流,他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线下有人介绍对象,那么对方极有可能在另外一座城市,需要坐着高铁,穿越半个省去约你;如果自己去网络征友,更会发现,如果某座工业城市GDP是某座一线城市的1/2,那么这个地方可供选择的适龄青年的数据库规模,可能只有那座一线城市的1/5,甚至更少。
这并不让人吃惊,造成这种不成比例差距的原因,在于城市的服务业。
在工业城市,社会是一种M型结构,即低收入者(工厂务工的劳动者)和高收入者(工厂老板、拆迁受益者等)占据多数,他们是“M”字母的两个尖端,而中间的中等收入者(写字楼白领、公务员和工厂管理层)群体则出现塌陷,处在“M”的中段,向下凹陷,数量少得可怜。
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中等收入者希望和高收入者进行婚配,然后实现了财富的阶层跨越。但现实情况是,择偶除了财务因素之外,意趣相投也很重要,所以,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者都愿意和这里的高收入者进行婚配。于是,中等收入者必然出现择偶难。
在一线城市,社会则是一种橄榄型结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两头小,中等收入者则数量巨大,犹如橄榄球的腹部。这种健康的社会结构,功臣就是发达的服务业,而绝大多数白领的工作岗位都在服务业。
在一线城市,社会则是一种橄榄型结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两头小,中等收入者则数量巨大,犹如橄榄球的腹部。
我们看一组2021年部分城市的服务业数据:2021年,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202.89亿元,深圳为19299.67亿元。苏州的GDP为2.27万亿,约为广州(2.82万亿)的80%,深圳(3.07万亿)的74%,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却只有11655.8亿元,几乎只有广州的一半、深圳的六成。
这是巨大的“断崖式”差距,远比GDP差距大得多。当然,苏州是非常优秀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工业的“支柱城市”之一,但它毕竟属于工业城市,和一线城市并不处在一个范畴之內。
服务业有很多种分类,我们以传统的两分法来看,它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前者是指那些直接给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往往同时、同地发生,比如按摩、餐饮等。生产性服务业则是不像消费者提供直接效用,而是为工业生产提供“配套”的服务业,比如金融、物流、商贸和信息服务业(包括互联网)等。
一般来说,产生中等收入者的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但两种服务业也是互相促进的,只有中等收入者足够多,那么才会消费畅旺,消费性服务业才会发展。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又反过来证明城市的工薪族收入殷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错。因此,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数据,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群体结构,无疑有极其关键的参照价值。
服务业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关乎到城市社会结构中的公平正义。
2016年,城市经济领域发生一桩不起眼的大事。当年,我国首次突破1万亿(10089亿)大关。其中,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总和超过4000亿元,在全国的占比竟然达到了40%。要知道,四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不到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高薪来自高端服务业在一线城市的集中。
在国民经济的统计概念中,所谓高端服务业并不是一个常用概念,只是通过人们的约定俗成,让它逐渐开始指代某一些对提升城市能级很重要,对其他产业影响很深、很广,同时也产生高薪岗位较多的服务业。它们也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包含互联网)两大“天王”。
2020年,中国最洋气的本土投行中金公司高层的总薪酬,约为1.7亿元。中金一直都以高薪著称,也因此引来了不少议论。但和腾讯比,中金还是差点意思。同样是2020年,腾讯公司13位高层总酬金大约31.64亿元,之前的2019年,这一数字约为26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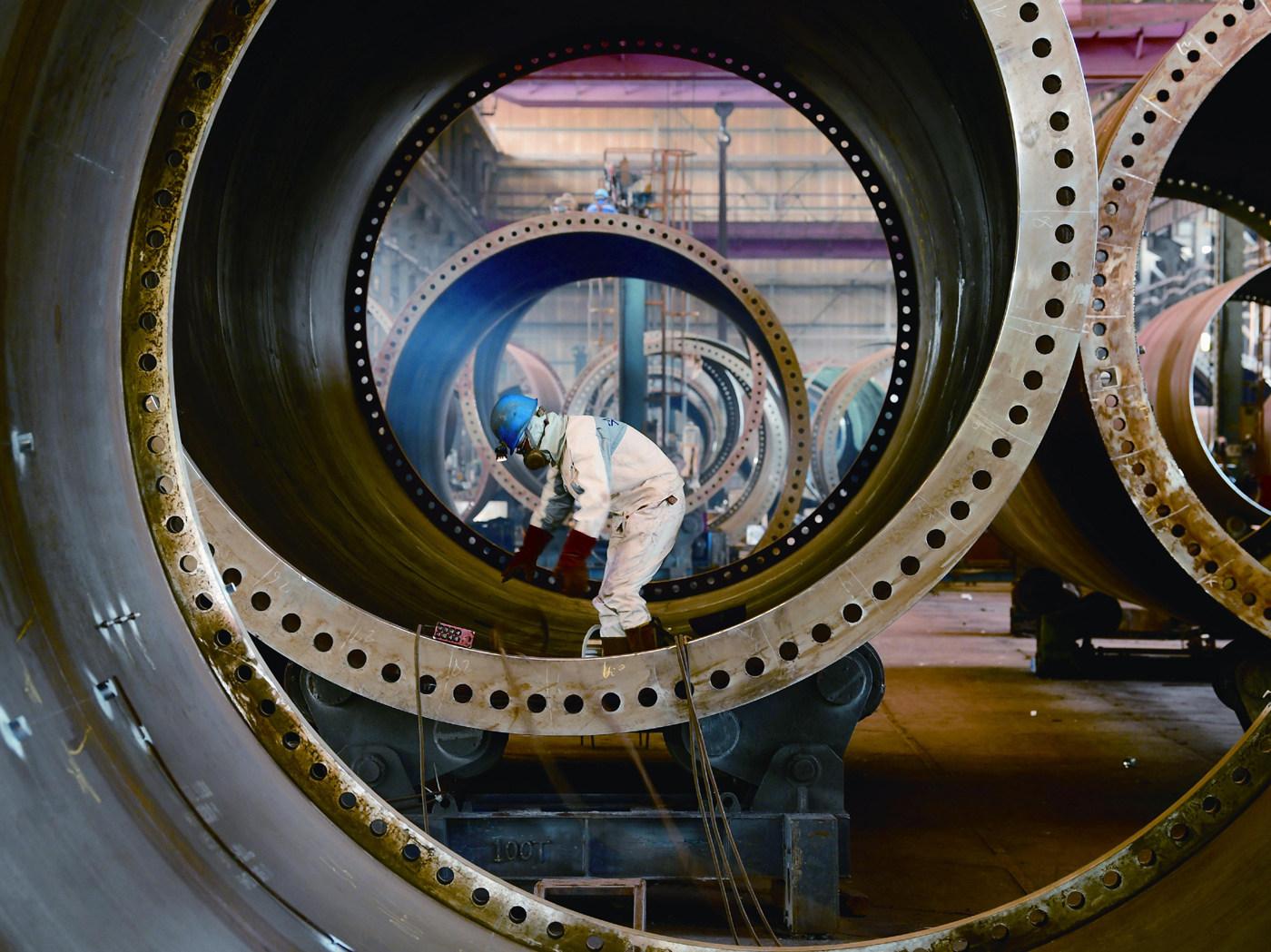
中金特别是腾讯的薪酬,无疑是高端服务业中的“极端现象”。它说明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越是“高端”的服务业,在分配上,越是会对劳动者有利,而后者主要就集中于一线城市。
在这些行业,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而是一种基于共赢的新型分配模式。此外,由于股权激励制度的广泛存在,资本和劳动者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腾讯的总裁刘炽平的年收入最高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而且,他还持有腾讯的股份,虽然不到1%,但在股价的高点,市值达到了330亿港元(腾讯在香港上市),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280亿元。
高薪,它最能代表一個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钱,毕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撒谎的一种存在。当然,炫富式超高薪是另外一回事,并不值得提倡,并要坚决打击。但适当的,足以维护劳动者体面居住、舒适生活和教育子女需要的薪水,的确可以体现劳动者的地位和价值。而且,有足够的,有着体面薪酬工薪族的存在,也是一个城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最好体现。
在工业城市,显然是另一种情形。资本在分配中会占据绝对的优势,超高收入的工厂厂主(提供的资本是机器和厂房)和拆迁受益者(提供的资本是建设工厂、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是最富裕的阶层,他们决定或影响着分配机制,而工厂工人作为劳动者,在分配机制的构建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对而言,在高端服务业集中的一线城市,劳动者在分配上往往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也是对劳动者最友善的城市。
除了以上这种市场化的分配,另一种非市场化的“分配”—公共服务,也是一线城市的独特优势。公共服务的底气来自城市的财力,而一线城市显然不可能输。以深圳为例,2021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7.76亿元,人均财力位于全国所有城市的头部,这比苏州高出一大截,远远超过了两座城市的GDP差距。究其原因,既有税收体制的因素,也有两座城市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经济“含税量”有差异的原因。
基于雄厚的财力,以及财力带来的对基层管理者的激励和充裕的公共资源,再加上本就相对高的地方治理水平,一线城市能提供中国第一流的公共服务,越来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冠大流行的这两年,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线城市远远不止于GDP数据,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心理期待,投射到城市领域的一种符号,它指向了一种和谐的社会结构,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品质,一种可以冲破固化并出人头地的可能性。
对工薪族来说,一线城市无疑最适合奋斗。当然,这些思考都排除了资产价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