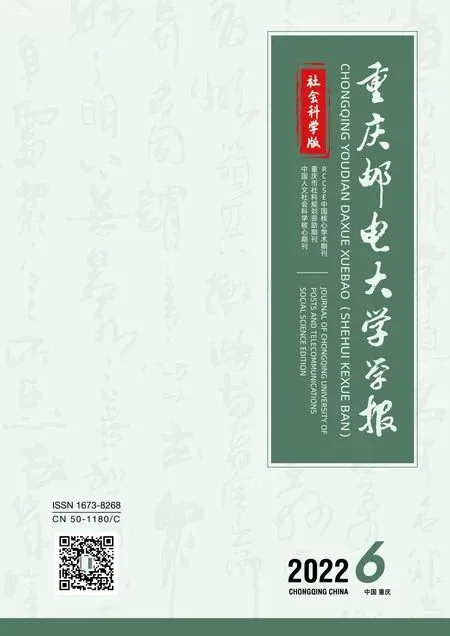鸳鸯蝴蝶派的游园与城市消费空间再生产*
李 斌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范伯群等人对鸳鸯蝴蝶派研究的深入,其评价从基本否定转向基本肯定并形成共识:他们是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通俗文艺流派。该流派的代表著作有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等,他们提出通俗文学应与精英文学同生共存、比翼齐飞的观点,阐述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性”[1]。总体而言,近些年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因循了已有结论,并且仍然多集中于文学领域,并无太大突破。笔者借助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空间生产、权力等理论来观察鸳鸯蝴蝶派的转型与从周边城市到上海的空间变化的对应关系,进而探寻鸳鸯蝴蝶派“作品价值”之外的“空间价值”。正如韩悦涵认为的那样,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群体“用自己的休闲行为占领、争夺和重新表述城市公共空间”[2],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创作之余的行动与在生活中开辟的生活美学空间对当下建构适应美好生活追求的城市消费空间颇有启示。“园”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发生着空间变化,其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提及的“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也即园伴随着空间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形态:具有江南文化特点的古典园林、伴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而从古典园林发展而来的营业性私园和大量兴建的城市公园。本文所指的“游园”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狭义即鸳鸯蝴蝶派围绕“园”发生的游览过程;广义则包括鸳鸯蝴蝶派围绕“园”发生的游历与游离的空间变化过程,主要包括从乡园到新城的生存空间转型,从城市的亭子间、报馆到园子的游玩空间转移,在不同类型和不同城市的园子里游历以及离开上海这个超级城市重新回归家园的一系列空间实践,在后者中蕴含着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空间抵抗。他们对上海的空间抵抗将他们的审美特征深深嵌入20世纪城市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中,示范了美学感的空间在消费空间里成形的轨迹,对当下建构与美好生活相适应的城市消费空间具有借鉴意义。
一、城市消费新空间的生成与鸳鸯蝴蝶派的空间转移
福柯认为,20世纪是一个“空间时代”[3]。作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必然产物,彼时发生的空间变化并非只指地理空间的改变,还指伴随着地理空间变化而引发的人们的表意实践、快感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城市消费空间孕生于这种空间变化中。周边城市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不断聚拢到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中,进而在其中塑型出带有消费主义特征的空间,并逐步挤占其他实体空间(包括传统文化空间)的容量。
(一)成为城市消费新空间的园
喧嚣的现代公共园林取代了荒疏的古典园林,与之对应的是普通市民的游乐空间取代了士绅阶层的交往空间,“园”的空间变化成为社会转型的缩影。在空间变化的过程中,古典园林、非营业性私园这种更符合江南文化风韵的空间被现代资本遗弃为边缘空间。营业性私园与城市公园逐渐成为公共娱乐的主流空间,并且与市民的工作空间、居住空间、室内娱乐空间等活动空间一道化作了以同质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空间,在这些园中的游园也成为借助便利交通、低廉票价与现代设施得以实现的消费行为。园是“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塑造的产物”[4],受到了行政与资本力量的双重规制。前者通过为游园活动增加政治意义来塑造城市发展的秩序感,后者则将游园变作可盈利的生意,不但向游客兜售商品,而且将游客变作商品。正如20世纪30年代一句城市建设口号说的那样,“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5],行政规训隐藏在游园规章、园内教育场馆建设、宣传标牌、游戏活动等中得以进行。得到行政力量支持的消费文化空间的权力空前壮大,摇身变为城市主流空间。由此,园成为具有行政力量的“教化功能”与资本力量的“消费功能”的城市消费新空间。
政府在园的建设中引入了商业法则,表现为交通设施的便利化、景观设计的标准化和入园价格的低廉化。公路建设便利了市民的游园活动,如徐园“地虽僻西,公共汽车直达于门,交通颇称便利”[6],申园“位于康瑙脱路胶州路口,占地六十余亩,与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为比邻。自南京路南路口以公共汽车往,但需铜元二十余枚,交通良便,以汽车往,则许时可达矣”[7],园被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拉进了城市消费空间中。现代之园的设计以便利游览为鹄的,景观设置并非为了凸显意境,而是通过打造自然的替代性空间,加速游客的身心修复。这种功利的设计导向体现出消费主义的特征,直道阔景、大开大合的现代设计取代了山水野趣、曲径通幽的古典设计,目的是容纳更多的游客入园,佛兰西公园“拓地可三百余亩”,景物被置于广阔的地理空间中,“无边碧草平如褥”[8],沪西徐家汇的濠乐园,“入园即为广场,芳草铺茵,繁花簇锦,迎面乃见廊子”[9],大华花园在西化设计的路上走得更远,“地广约十亩,清洁胜旧式花园倍蓰,亭台不多,位置得所,中有喷水池,以水门汀制成”[10],绿色草坪、高大树木、宽广池塘组成的标准化空间既能容纳更多游客,也在设计上花费较小,吻合商业成本控制的理念。
这些现代之园适应了现代城市定时作息的工作机制,从设计、设施、活动上都体现出平民化的特点,其中价格是体现平民化的重要指针。彼时有人这样说公园门票之便宜:“这是全上海最便宜的消遣地方,花一百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小本门票,一共五张,全上海十三处公园任何一处都可以通用。”[11]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财力改扩建道路及建设新公园,但却设置了低廉的入园价格,这背后不排除有获得长远收益的商业目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套路大抵都是以低价吸引客源,从而为二次消费引流。低价门票只是引导人们入园的诱饵,涌入的人群将成为能够带来更大资金流的消费主力。列斐伏尔认为,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是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12]86。游客们通过程式化、标准化、同质化的游园实践快速修复身心,同时成为大众消费经济的对象而被嵌入到整体性的城市消费文化空间中,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就此意义说,园不是游客的消费客体,游客反而是园背后的消费主义势力控制的客体。园不仅是城市公共服务空间,而且是城市文化消费空间。
(二)鸳鸯蝴蝶派的转型与空间移动
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鸳鸯蝴蝶派的家居空间、职场空间与休闲空间发生了转变,这种空间转变形成了他们开放的认知结构与身份的重新定位。他们移居上海后,与平民合租于嘈杂拥挤的亭子间里,根据上海市政府1936-1937年的居住情况调查显示,彼时每一户接受调查的房屋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改建,整体住房环境是比较杂乱的,一般都只有一个厢房,“厢房朝东,后轩有窗”[13],因此这里的居住环境与他们自小熟悉的“家家礼乐,人人诗书”的故园环境大相径庭。鸳鸯蝴蝶派工作的报馆也多处闹市区,他们通过耗费心力的文字工作和迎来送往的应酬积极拓展着自己的职场空间。与此同时,他们的休闲空间得到了充分释放,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广场里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总之,他们告别了风雅家居生活,告别了熟人社交圈层,告别了单一刻板的休闲方式,这些皆代表着他们“从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14],这种转型在空间上的体现就是从故园的“小园香径独徘徊”的环境,向着上海这座超级城市里的亭子间、报馆、茶馆、咖啡馆等多元空间的转变。
鸳鸯蝴蝶派通过游园将居住空间(亭子间)、工作空间(报馆)与休闲空间(园)贯通起来。与空气憋闷的室内休闲空间相比,园是一个更贴近自然的具有生态属性的公共休闲空间。尽管此时的园与鸳鸯蝴蝶派熟悉的古典园林有所差异,但大体来说满足了他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需求,是以游园成为鸳鸯蝴蝶派缓解身体疲倦与精神焦虑的仪式化的休闲活动,这从他们的游园体会中可以感知到,“歌场舞楼徒足招烦增恼,又安能慰人寂寥。顾舍此尘俗场,又无高尚娱乐之地,堪助人清兴,心窃憾焉”[15],“这三月来,我因为心绪太坏,一天到晚的做事,弄得头晕脑涨,也谭不到什么顽耍,本来上海没有可去的地方,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南头的半淞园好”[16],“十一月二十七日为星期日,孤室闲坐,益增无聊……驱车至半淞游焉”[15]。此时的游园不再是擢升精神境界的活动,而成为缓解“城市症候”的工具,是现代城市发展获得可持续性的健康人力资源的前提。
政府将园作为延展的规训空间,采用的规训方式是隐秘的,如设置专门的公园管理部门,并颁布一系列规章,规范公园管理机构组织、游客游园、公园商业经营和公园出产采销等[17]。鸳鸯蝴蝶派对这些规训的服从与遵循表明他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适应与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如许廑父与徐枕亚游览宋园时,对无人遵守公园规章的现象就颇有微词:
既入,门有小屋三楹,建于门口,悬规行数条,大抵与普通游园规例相似,惟第一条游客须赴签名处签名云云。余谓枕亚既至,此间规则不可不守,乃觅所谓签名处者不得,既而晤一园丁,询之笑答曰,向见规牌上书此,然自我来此数年,未见有人签名者,更不闻所谓签名处果何在也。余等为之嗟讶久之。以此小事,然园规十数条,一事如此,则一切胥成。[18]
在逃离促狭人际空间、舒缓工作疲劳的需求上,鸳鸯蝴蝶派与普通市民并无二致。从报馆、亭子间到园的空间移动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主要方式,也成为他们体认公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途径之一。
鸳鸯蝴蝶派对游园规则的遵循可视为他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蕴含在其背后的规训权力的服从。只要有机会,他们仍然会基于自身的审美体验、快感和文化身份展开对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生产”的控制性关系的抵抗。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再生产者,在现代城市的消费空间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成为核心,“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12]410。福柯用“权力”概念进一步阐述了“空间生产”中的控制性关系。在福柯看来,权力指的是一种统治关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施的强制性控制。人们可以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挪用与意义表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另一位美国大众文化学者费斯克明确地提出,文化是通过意义的争夺来形成的,“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它要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的分配及其再分配”[19]。旧园融入新城消费空间的过程也是鸳鸯蝴蝶派建构媒介作家新身份的过程,伴随新身份建立的是他们在居住、工作与休闲生活上适应现代城市的过程。这种适应在游园中的体现,就是他们一方面接受消费主义浸染的游园活动,并视之为现代生活的必备仪式,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对古代士子审美化游园活动的情感依附。本着崇尚“自然”之境界、追求“个性”之精神的美学思想,他们对消费文化影响过甚的游园逐渐生发警惕,进而从初始对游园生活的接纳到后来借助古代士子的游园传统对园这一消费空间中的资本权力开展抵抗,最终实现“文化主体性的表达”[20]。
二、游牧式游园:时刻、方式与消费的选择
游牧是德赛尔托、费斯克等大众文化学者用以表述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方式。德赛尔托认为,读者是文本盗猎者,他运用“盗猎”的比喻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21]。费斯克对德赛尔托文本盗猎理论持肯定态度。在“游牧主体论”中,他将在大众文化工业中制造出反抗的群体命名为“创造性大众”[22]。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鸳鸯蝴蝶派属于费斯克所说的“创造性大众”的行列,他们借用游园活动这一空间实践来抵抗城市消费空间神话的做法,正契合福柯所主张的“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23]26。
(一)清静悠思的古典时刻
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的上海之园中充斥着喧嚣的人声,这与古典园林求静尚雅的格调大相径庭。园成为市井化空间的延伸与全球化乐园的东方版本,经营者希望通过阔大的空间设计、世俗的活动安排、低廉的入场票价等方式请三教九流的人群入园以扩大游园消费市场。这种经营理念与鸳鸯蝴蝶派对审美化游园的期待有所抵牾,使得他们对眼前这个被消费资本操控的园怀有抵触情绪:“向日来游类多俗伧,杂沓喧笑……公共场所,我能来彼亦能来,耳目之官何若今日清静。”[24]作为费斯克所说的“创造性大众”的一员,他们对资本权力的抵抗策略之一是“躲避”,费斯克认为这种躲避式的快感具有产生能量与赋权的可能性[25]66。鸳鸯蝴蝶派试图避开嘈杂喧嚣的游园活动发生的主要时间,通过选择清静悠思的时刻营造出与喧嚣嘈杂的世俗之园的空间区隔,并在躲避过程中重新生产出园与自我的新关系。一般而言,白天游园者较多,而夜晚游园者较少,他们通过游览夜园错开人群,以逃避喧嚣嘈杂的环境。徐园的“夜游”就吸引他们前往游览,当然,徐园开放“夜游”的目的并非营造他们期待的静谧的审美化空间,而是通过占有劳动者晚上的时间将游园效益最大化,是以夜园的嘈杂渐渐不输白天,或者变成另一个白天:“摩托十数已先吾而至,南道中电炬通明,照眼生缬”[26],被电灯照得亮如白昼的园中,游玩者摩肩接踵,“游众之衣香鬓影,明妆新声,几滞我人之魂”[27]。在乡村型传统社会中,夜晚是一个宜于静思的天人神交的独特时刻,而在灯具的照耀下,夜晚静谧、漆黑的特质被抹除,时间和空间出现了双重变质。不夜园作为上海这座不夜城的一部分,为游客提供了24小时循环的休闲消费。夜晚这一被鸳鸯蝴蝶派选中的审美化时刻被强行收编进歌舞升平的狂欢化消费体系中,沦为只适合消费的平庸时刻。
鸳鸯蝴蝶派选择人烟稀少的时间与空间去游园,就是故意对抗资本逻辑,站在消费社会的对立面。当夜晚被资本占据后,他们只得另选时间,这反而增加了他们掌控游园时间的主动性,即便这种时间选择与身心放松的一般性游园目的相去甚远,他们也宁愿借此来表达对精神幸福的追求,如他们选择雪天游人渐散之时去游园:
晨大雪纷飞……污秽恶浊之上海,顿成清洁世界……约王董谢华沈顾诸子……携酒挟□冒雪上道……既至,则择饮于池旁小亭之上,亭颇湫隘,然开窗面山,挹雪拥云,则室虽陋而雅绝也。饮次,众以踏雪为乐,遂各爱其爱,各乐其乐,余与赵王诸子四五人,跨山穿桥,探雪穷谷……园中无游客,路皆积玉,深可没踝。[28]
天寒地冻的冬园中已无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这时鸳鸯蝴蝶派行到园中,体验超越身体愉悦的精神快感:“春夏有花木之胜,及冬则一片萧条,无足观已。雪代夕阳,其色转明,冻雀无声,游人三五。”[29]借用费斯克的“快感”理念,他们借助依托传统游园文化衍生而来的精神快感,对被资本权力操控的游园的时间进行选择性置换,重构出具有枯寂的审美意味的新空间,用自由、个性、超迈不群的“逸”文化[30]抵抗以成果与效率为导向的消费文化,从而将园改造为溢散他们审美化主体性的反消费空间。
(二)意趣盎然的雅游之乐
正如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在资本的渗透与推动下,上海之园被建设成为较竞奢靡、追求感官享乐的全球乐园,其中的游乐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西式文化特点,如卫乐园的中央为跳舞场,四周是木条构成的跑道,用作自行车比赛[31]。凡尔登花园则引入了马戏团娱乐表演,“黄发女子走钢绳、女子马上舞蹈,俄国莫斯科歌舞、鹦鹉戏”[32],半淞园的“枪击游戏”,“毛线气枪射红的得中有赠彩”[33],及来自西方的游戏项目——溜冰,“溜行如飞”[34]。赛狗这种西方休闲活动更是流行一时,申园就常举行赛狗活动,“入门,即闻犬吠声狺狺然,一若迎客也者,电炬通明中,烛见广场一片,范以白漆之护栏,栏以内为草地,即赛犬骋逐之所”[7]。这些典型的感官刺激消费给游客们带来了释放本能的快感,而不是高层次的精神愉悦。
鸳鸯蝴蝶派并不排斥这样的消费性游乐,甚至常常浸淫其中乐而忘忧。如周瘦鹃就是半淞园的常客,在游园时常被人认出:“五时许觅途出,忽邂逅周君瘦鹃。谓将访张王二君于人群中,第斯日在园中寻友侣,非预约在何许,恐不易找得也。”[35]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流露出中国传统游园文化的深厚底蕴,更看重精神愉悦而不是感官娱乐,所以他们会选择契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活动来替代喧嚣鼓噪的娱乐活动。他们选择的游乐活动既汲取了传统游园文化的风雅特质,又符合现代生活轻便明快的节奏。如在陈氏耕读园中游玩时,他们采用“记物”“答问”的“滑稽问答”方式助兴:“忽而号筒之声连作,相将同坐,陈遂康君提议作滑稽问答,如答案与问句中之答案相吻合,则奖香蕉一枚。”[36]这种“滑稽问答”的游戏沿承了古代士子雅集中把酒咏文的传统,同时灵活地变赋诗作对为滑稽问答,使文学游戏做到了雅俗共赏,在意趣盎然的雅游中,他们在马戏、魔术、赛狗盛行的园中重置出一个具有风雅审美趣味的新空间。
花木清赏是文人游园的必备项目,它受制于时间、地点、环境、品相、形态,也要求赏花者具备足够的文化素养[37]。当时不少公园举行过花展,无论是参展的品种,还是展出的方式,都与传统的花木清赏相差较大。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就记载了西方花卉品种和中国的差异:“沪地自通商后,洋舶带来各国花卉,奚止百数十种。名目甚繁,未能翻译备载。其花卉颜色虽各极鲜艳,而绝无香气,殊不可解。草本最多,藤本花皆千叶。唯玫瑰一种,花蕊倍大于中国,香气亦终不及耳。”[38]在这些园中,各式品种植于阔大开朗的草坪空地上,构成壮观“花海”,旨在壮大客源流量,而非营造艺术欣赏意境,重“花境”而忽视“花意”[39]。与之不同的是,在一些营业性私园的花展中,经营者借鉴了古典园林的花卉摆放、花器配置、空间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强调园景、器皿与花卉的和谐措置与隽雅幽深的艺术风韵,吸引了鸳鸯蝴蝶派的目光。半淞园的兰花展就利用环境建筑制造出“暗香浮动”的意境,将兰花这一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的名花衬托得愈加淡雅迷人:“今观此兰,不禁为之感喟,亦未知余家中所爱之兰,今日为何如耶。顷者沪上艺兰家,既各出其精品以比赛,其平时培植之功,为不少矣。余与友人分笺默坐,对花写生,惟觉香气环绕于笔墨之间。”[40]小观园的梅展则利用不同款式、模样的梅花构造出视角多元的“赏游”格局:“陈列梅花甚多,古本梅,枝干苍老,古雅绝伦……或曲叠万状,花生满枝,或枝干稀疏,清芬扑鼻,朱红碧绿。”[41]鸳鸯蝴蝶派避开了普通公园的嘈杂花展,徜徉于私园的展厅领略天人合一之美,用花木清赏带来的精神愉悦取代了喧闹乐游带来的感官刺激。
作为艺术雅集、花木清赏等雅游活动的主要群体,鸳鸯蝴蝶派的游园偏好无疑也激发了更多的营业性私园开展类似的风雅活动,使得“乐园”之中逐渐形成具有传统风雅之美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三)园林雅市:传统文化消费新空间
费斯克用“外置”的概念来表述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所谓“外置”,就是被支配者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资源和商品中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和方式。费斯克指出,权且利用(making do)就是这样一种“外置”方式,也就是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25]27。鸳鸯蝴蝶派在游园中利用的现有文化资源就是他们熟悉的传统文化,他们通过对契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传统文化消费的选择与利用,在园中开辟出传统文化消费新空间。
在集聚了各类收藏家、书画家、赞助家、文化人的上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国古典艺术群体和艺术市场。据统计,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由1919年的12个飙升至1933年的105个。相比封闭的公司、楼宇而言,园为这些艺术展以及后续的艺术消费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到舒心畅神的开放空间,游园与书画、古玩等传统文化消费的结合提升了园作为消费空间的文化品质,彰显出园在传统文化产品的销售、流通与消费中的独特作用,游园与逛街的结合打造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消费空间。澄园是一个未开放的私园,但主人潘澄波借助高级职员与私园园主的双重身份,以澄园为舞台密切开展着与政治、外交、文学等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沟通。就在澄园的一次聚会上,出现在座上的就有“戏曲家尚小云小翠花朱素云,新文化家胡适之,法律家卢谢二公,外交官冯总领事,词人赵叔雍,都凡数十人”[42],可见澄园已是一个兼具传统和现代因素的“杂交空间”,这样的空间容易成为有别于现代消费的传统文化消费空间——园林雅市。所谓园林雅市,就是利用园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打造适应产品售卖的营销环境,以促进产品的消费。澄园变作雅市的缘起是园主即将卸任经理职位前往欧美旅行:
潘丈澄波,任怡和轮船公司华总理,数十年矣,刻因年老,不胜繁剧,缘将公司事授与文郎志铨,己则拟作长期之欧美旅行,所有葛罗路二号澄园内,历年购置之古玩珍物,珠玉陈设,拟一并出让,以便轻身首途。[43]
潘澄波通过《申报》对此次拍卖进行了宣传,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售卖传统文化产品的园林雅市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澄园从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私园变为一个开放的古玩市场。
“在现代性语境下,人们的生产逐渐由消费所引导,人们的消费也从物质商品的消费演变到文化消费”[44],审美与消费的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之途。作为主要消费者的鸳鸯蝴蝶派的游园方式也从单纯地赏玩传统景观演变为购买传统文化产品,进而形成了一股消费新潮流,推动以审美消费为主要特点的传统文化消费空间的生成。在民族企业的参与下,园更是成为他们延续文化传统与展示民族意识的消费政治表达的新空间。海上国货厂商联合会在徐园举行规模空前的“七夕花灯赠品大会”,参加者既有厂商,如“三星棉织厂、五洲大药房、华生电器厂、香亚化妆品公司”等,其中作为参与者之一的“家庭工业社”的创办者正是陈小蝶。诚如前文所言,在近代化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曾经的闲逸雅致的园被卷裹入消费文化的洪流,成为市井街道的延伸和现代集市的组成部分,如当时有人这样形容一些园林:“杂货骈至,百戏喧闹”[45],“园中水木清华,溪山明秀,在此软红十丈中,已非易得,惟小摊林立,为状乃□,游戏场未免为园林之玷。”[46]鸳鸯蝴蝶派向已经充斥着各种消费的园中注入了具有风雅性、民族性的传统文化消费新内容,通过对园的消费内容的调换,丰富与提升了园的消费层级,绵续了重精神审美的传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鸳鸯蝴蝶派从承载他们繁忙劳碌的文化传媒工作的亭子间、报馆来到园中休闲消遣,借此表达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与对新身份的认同。当他们意识到园在消费资本操控下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后,开始生发对逝去的古典空间的怀旧,通过对游玩时刻的选择、游玩方式的替代与消费内容的挪用等空间实践,对园中的庸俗消费性开展了游牧式抵抗,重新生产出了与自己审美趣味相契合的新空间。
三、重返、跨域与回乡:美学化生活空间的重置
上海在开埠后逐渐发展成中国乃至东亚首屈一指的超级城市,园也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象征性空间。如福柯所说,在园中同样存在“权力运作”以及“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的游园者[23]28。身为游园者的鸳鸯蝴蝶派通过选择、占有与挪用园的空间以抵抗消费空间霸权的支配,其特殊性在于他们将游玩过程写成文字发表,使得他们的游园成为一种“被凝视的流动”,有助于生成时人对城市中不同空间及上海与周边城市关系的新认识,进而开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民主化”进程。
(一)重返私园:鸳鸯蝴蝶派的新游园
上海在发展成超级城市的同时也产生了现代空间与传统空间的分裂。一方面,上海不断汲取周边城市的资源进而壮大为现代空间,另一方面,大力改造实质上也就是祛蔽包括园林在内的传统空间。如上海既有交通便利、设施完备的公园,也有地处偏僻、没有充分开发的园林,后者仍然保留着“清空远渺,别成异响,而空庭鹤唳断续,木叶渐脱,已无蝉喧”[47]的清高出尘的生态景观。这种空间断裂是现代资本的有意为之,因为资本要求空间是可盈利的,园只有进入市场化、大众化的轨道后才能产生更多的增值机会。与之对应的场景是,获得了资本投入的公园变得人头攒动,而在园主个人经营下勉力维持的私园则日渐荒芜。尽管私园和公园在交通抵达、设施配套上有差异,但私园带给游人的诗美体验也是公园不能比拟的。鸳鸯蝴蝶派对此深有感触。他们在深受消费资本操控的公园中无法体验他们所期待的风雅之美,所以他们克服交通的不便,纷纷前往郊区未开发的园林游玩,以感受久违的精神愉悦。这些未开发的郊外古园没有让人意乱神迷的现代装置,唯有依照园主审美情趣设置的由古玩、书画、花木构成的古雅氛围,如鹤园主人庞蘅裳就将园子设计得逸趣非凡:“自出心裁以修葺之,亭榭竹石,池塘花木,莫不饶有逸趣。”[48]风雅脱俗的景观无法直接创造市场价值,但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所以才受到他们的青睐。郑逸梅曾专门到位于南翔镇的葛氏园赏玩:“入门右折,抵雪影轩。藉以品荈憩息。轩侧植梅数十百本。园主人因取昔人冲寒有客寻春去,移得晴窗雪影来句,即以雪影二字为□,惜予来已迟。”[49]
鸳鸯蝴蝶派在地处僻远的私园中不但享受到古意盎然的景观之美,而且重温了现代消费社会里难觅踪迹的风雅生活。私园的主人们多半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怀有文人的气质、情怀和旨趣,交往的主要群体也是文人。如亦园的菊花盛开后,园主邀请一众文人前往赏菊,“邀邑中耆宿及书画名家”,“一时裙屐连翩,好不欢畅”[50]。与公园里的陌生人交往不同,园主与前来的文人多半是师徒、好友或同道,他们多通过结社的方式建立联系,而社团活动的地点往往安排在自己的园中。他们借助与园主的私人关系进入园中,此时他们的身份不再是游人,而是贵客。吴闻天、徐碧波、顾明道等星社同仁就常常在鹤园赏月,鹤园主人庞蘅裳也是星社成员,“践同社之约,夜饮于鹤园”。庞蘅裳的周到款待令众人倍感愉悦:“赏心于兹月色,自觉其分外明也”,“座中虽无管弦丝竹,顾觥筹交错,极宴酣之乐事”[48]。小观园在江湾分园的园主杨瘦莼也在园中举行了聚会,“以园中桃李盛开,仙客来又在争妍斗丽之际,尚足一骋游赏,特于星期日,设筵园中”[51]。当时一些私园请来戏曲名家表演,但这些表演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园主和表演者私交甚笃,因而更像好友聚会。如楚园园主刘介鲁请来京剧大腕谭小培、荀慧生到园中表演,饮到好处,主人和戏曲名家会同台唱戏,气氛十分融洽:
与公鲁合歌长生殿一曲。袁去小嗓,刘去大嗓,二翁素以昆曲声著。语冰唱寄予一叚,公鲁唱捉放宿店一叚,复与语冰先后唱捉放行路一大叚,可谓谭拉谭唱。后由舍予操琴,小培唱盗骨一叚,末由慧生唱不日将演之新玉堂春牢中梳妆一叚……罢,各尽兴而散。[52]
游园成为园主与鸳鸯蝴蝶派交往生活的方式,这时的园不再是旅游空间,而是风雅生活的空间。他们通过游园活化了摩登娱乐空间之外的精神审美空间,使其虽被现代消费空间所遮蔽但不至于消散。他们的游园活动尽管沿承了古代士子的雅集方式,但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情势。如园主邀请的游园者中不只有文人,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雅集内容也不只是诗文酬唱,也有国事品谈。这时的雅集更像面对社会上流阶层的高端文化沙龙。如梓园园主“无不钦其高旷异世也”,但并不妨碍园主“大宴宾客”,有一次请来吴俊卿、李平书、虞洽卿、陆伯鸿、池子黄,“皆警务中重要人物,与谈国事”[53]。为适应时代特点,一些私园的布置也变得更加洋派,如从一次夜宴中可看出,澄园的设计已运用了不少现代技术:“旋由潘公子夫妇导客鱼贯入一精室,金阁银灯,锦堆花密,主人制西餐……席之中央,置喷水盆,烂漫如云雨。席间穿花成带,缀以彩电,宛疑万点明星。”[42]鸳鸯蝴蝶派在私园里的漫游并非意在做回消极避世的士子,而是通过私园里的风雅生活展现传统文化空间的独特审美价值,确认自己城市生产流水线上零件般的“物质身份”之外的高扬主体性价值的“精神身份”。
(二)从上海之园到长三角之园
由于交通运输业的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尤其活跃,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为促进这一地区各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苏浙皖沪区域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使得长三角一体化的轮廓渐显。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中,上海是绝对中心,其他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流向上海,巩固着它作为超级空间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从上海抵达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便利交通促成了上海的发达,但反过来也使上海的资源可以便利地流向各地,造成了去中心化的可能。鸳鸯蝴蝶派的自发结伴出沪旅游就开启了去中心化的空间“游牧”。1929年,无锡章百煦邀请秋英社、兰陵社同人游览梅园。周瘦鹃热情响应,先期一天抵达无锡。此次出游的人数众多,大致分为:先到一天的,有张珍侯、胡伯翔、王汝嘉;从苏州来的,有李浩然、费左荃、徐涵生、谢公展、钱云鹤、汪英宝、杨清磐、邓春澍、施啸岑、孙洁人、沈杏荪、马万里、吴竹屏、汪英石、洪如、时敏;无锡本地的,有裘公歧、胡汀鹭、朱梦华、陆辅仁、荣鄂生、谢介子、王亚南、荆梦蝶等。上海、苏州、无锡的鸳鸯蝴蝶派几乎集体出动:
章百煦对周瘦鹃可谓十分尊敬,待之以贵客之礼。梅园之游后,他写了一首诗寄给周瘦鹃:“胜景孤山似,登临绝点埃。琴调新月上,客至万梅开。一酌花邨酒,三更蜡炬灰。明朝挂帆去,极目望苏台。”[55]期待周瘦鹃在苏州举办邓尉山雅集,这样大家可在苏州再聚首,从中可见鸳鸯蝴蝶派从上海到周边城市的跨域旅游并非偶尔为之,而是接连不断。他们频繁地跨域出游向时人宣告:作为旅游目的地,上海是可以被周边城市替代的。无锡、苏州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弱于上海,但在这些城市的园中能体验到在上海体验不到的诗美享受。他们往来出游塑造出的上海通向其他城市的游园路线,正是对上海作为游乐中心的空间神话的解构。
尽管从上海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空间游动并非始自鸳鸯蝴蝶派,也非只有鸳鸯蝴蝶派参与,如1936年,两位青年旅行家陈翼和沈霖穿着童子军服自上海国际摄影社门口出发,就开启了苏浙皖公路骑行的旅途。与他们相比,鸳鸯蝴蝶派的跨域游园伴随着旅游书写,向市民们展现出一条更加生动、更易记忆的去中心化旅游的媒介化路线,从而建构出便于公众感知的长三角旅游新空间,引导更多的市民通过在中心空间与周边空间的旅游路线切换享受主体自由。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城市问题》一书中所说,空间不只是物理因素的堆积,还包容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运作与人类实践的表达[56]。鸳鸯蝴蝶派的游园空间转换实际上建构出了双重空间:在上海,他们尽情享受现代消费带来的视觉享受和感官刺激,而一旦需要精神愉悦和审美慰藉,他们就会前往周边城市的园中寻找。与上海相比,周边城市的游园空间更加阔大,游园姿态更为放松,游园生态更加丰富,进而通过在不同城市的园之间转换满足了多样性的审美需求,因此他们不再受制于单一空间及单一的游园方式,而是在空间转换中采用与空间契合的游园方式,从而远离消费空间的支配而成为空间的主人。
(三)与超级城市的脱嵌
另一种对上海空间霸权支配的抵抗方式是逆行,也就是与从周边城市到上海的迁移路线相反,从上海离开到周边城市定居。拥有宽广人脉资源与一定经济基础的鸳鸯蝴蝶派并非没有能力留在上海,而是从内心抵触上海的浮华与喧嚣,选择主动离开上海这个超级空间。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常常表露出对藏污纳垢的上海的厌恶,发表了不少影射上海黑幕的小说,如郑逸梅的《银灯琐志》、周瘦鹃的《凤孤飞》、严芙孙的《我与萧郎》、徐心芹的《玫瑰花香》、胡润光的《影场血痕》、蒋吟秋的《影戏场中》、胡天农的《秋波》、林丽琴的《银幕下的单恋者》等小说。这些小说隐喻了只有离开上海才能寻获纯洁的主题。程小青、周瘦鹃、范烟桥等人相继离开上海到苏州买宅定居,与他们一以贯之的对上海的心理疏离感有关。程小青1923年就在苏州天赐庄附近的寿星桥畔购地并营造房屋十多间,周瘦鹃1931年也在苏州买下前身为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裔孙何维的“墨园”的紫兰小筑。苏州既有地近上海之便,又无上海之嘈杂,所以他们毫不掩饰对苏州的喜爱,刘铁群将之解释为苏州情结:“这批以苏州人为主的江浙文人毕竟不是真正由近代上海都市文明培养起来的都市儿女,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由那个苏州式的江南古城所塑造成的气质、情趣、爱好以及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他们表面上似乎融入了上海的市民社会,但内心深处却有着挥不去的苏州情结。”[57]程小青的茧芦、范烟桥的邻雅小筑、周瘦鹃的紫兰小筑,这些在园林城市的园林住宅,才能真正慰藉他们漂泊的心灵,满足他们风雅安居的理想,成为他们散养身心、逃避浮华的终极家园。
园成为鸳鸯蝴蝶派反思上海这个超级空间的非宜居性的入口。他们通过游园化解城市焦虑,或按照园林风格装饰家居,以此抵抗消费主义的庸俗化。但游园只是游览别人的园子,而家居装饰得再古典,也无法厘革家居之外的城市消费空间的嘈杂,无法扭转他们在基本人格类型上与上海的整体不适应。他们只能通过策略性的空间选择、调整与躲避来加以抵抗,而不能颠覆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消费空间,因此他们选择了终极抵抗方式:离开上海。从表面上看,他们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循环:从最初离开园到城市,现在又从城市回到园中,实质上这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他们在游园中寻获了从去中心角度反观上海的契机,进而通过对园的空间选择、挪用、占有与脱嵌完成对消费主义空间的解构,在长三角周边城市重建以诗意生活为导向的生活美学空间。他们终于回到乡邻关爱、朋友酬唱的风雅生活中,回到洋溢着生活美学的小园之中,从而回到人本身。他们离开上海既是对美学化生活的选择,也是对优雅人格的重构。
四、审美现代性的空间探寻与价值体现
鸳鸯蝴蝶派在游园中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了对于“生活审美”的强调。游园对他们而言不止是一种普通的娱乐习惯,更是一种文学活动传统。他们继承了明清以降江南士子在园林雅集的嗜好,将游园视为增进感情、巩固交往与表达意趣的主要方式。他们不断拓展游园的空间广度,呼朋引伴、遥相呼应地去长三角周边城市游园,同时也在园的不同空间中进出,如从热闹的公园走向静谧的私园。借由同道和社友的特邀,他们得以从现代的公共空间走回传统的私人空间,从而深入江南空间中体验不被世俗打搅的天人合一的风雅生活。在视游园为审美化生存重要方式的层面上,他们类似于波德莱尔所说的都市里的“浪荡子”。波德莱尔解释说,浪荡子不会设立既定目标,但却极具想象力,追求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包括世界的道德机制所具备的性格精髓以及微妙的智力,但同时也追求冷漠[58]。他们在游园中对空间的选择、规避以及再生产表达了特殊的审美体验方式,的确如波德莱尔说的,一方面突出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心理,另一方面讲求审美化生存,从而借助游园的空间实践而不只是文学实践,表达出了对于人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鸳鸯蝴蝶派借助游园的空间实践回应了早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空间的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关系。他们极力主张以传统游乐内容补充与丰富上海之园的游园内容,而当时不少园子的游乐内容都是西方化的,这让他们倍感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半淞园举办的龙舟赛就显得夺人眼球:“既而锣鼓声起,乃绕道至湖心亭畔,见龙舟一双,荡漾湖中,鲜艳夺目……二舟或相向而行,或相并而赛。”[59]这场龙舟比赛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门前车榖相并,俨然列处,以挤,抱向隅者孔多。但见林林总总之人头与草帽,作幙幌摇动之状”[35]。龙舟赛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化的娱乐方式在半淞园成功举办,这说明当时不少营业性私园经营者处理空间的做法与他们的空间观是契合的:平衡园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在游乐内容上的比例是园的空间良序开发的前提。由此亦见,鸳鸯蝴蝶派对传统文化空间的倡导并非孤声独白,而是得到了不少商人、政客、市民的齐声和鸣般的支持。其次,空间的庸俗化与审美化的关系。他们在“游牧”式游园中对游玩时刻、方式与消费的选择的背后有助于园(主要是公园)的景观设计、赏玩内容的审美化提升。与他们的倡导相呼应,不少公园的确在曲墙、廊院、亭阁、山涧步道的设计上做出了改变,部分复原了古典园林的“居游结构”[60]。一些公园在游园内容上模仿营业性私园的做法,恢复了传统文化赏鉴活动,如大华花园举行许十祺的字画作品展吸引游客[10]。他们在世俗化的消费空间重建审美化空间的倡导得到现实的呼应,审美化空间的雅气、清气、秀气逐渐消解了消费主义空间的俗气、浊气和戾气。最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从进入上海谋生到20世纪40年代集体离开上海,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因素等外部环境的作用,也是鸳鸯蝴蝶派自入沪以来对上海空间霸权支配进行抵抗的产物。如果说他们频繁从上海到其他城市的游园呈现出上海之外的周边城市消费空间的价值,那么他们最终离开上海选择到周边城市定居则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空间的中心化的决绝解构。然而这种解构并不是分裂,而是提供了以诗意化审美生活为导向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新可能。
鸳鸯蝴蝶派游园所面临的空间困境呈示出工业资本主义转向“审美资本主义”过程中审美文化的“两难困境”,他们对园的空间再生产是对操纵大众的感性需要与生命意识的审美资本主义的突破与反击。由此,他们的游园体现出了“审美现代性”的真正意义:既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也作为现代性的重建者。在新时代人们对共享发展成果的生活、自由平等的生活、优秀文化的生活、公平正义的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充满热情和期待的背景下[61],他们对建构契合生活美学的城市消费空间的历史经验理应获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