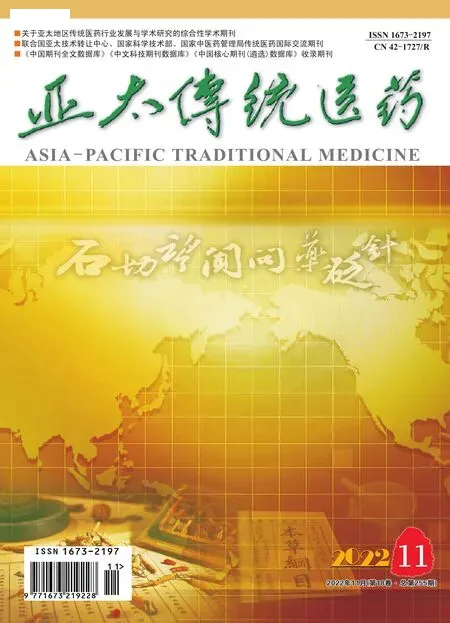古代防疫措施及其对现今传染病防治的启示
赵玉升,吴佳姝,屈会化,赵 琰*
(1.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2.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早在甲骨文中即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记载,《周礼·天官·冢宰》更是直接指出“四时皆有疠疾”,可见,抗击瘟疫自古有之。由于年代久远、著书不易、民众意识不够等原因,许多详细的瘟疫记录难以留存下来。
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1]仲景因此“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1],故凝聚毕生心血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均对瘟疫有所论述。至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应用,许多瘟疫记载才有所留存,至明代吴有性精研瘟疫,著成《瘟疫论》这一瘟疫专著,尔后瘟疫专著逐渐增多。本研究通过查阅古代文献记载的瘟疫并结合相应的史实,总结古代的防疫措施,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也希望能够对未来某种疫情的预防与研究起到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1 隔离
隔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病人的单独隔离,二是少聚集。最早的防疫措施即为隔离,《汉书》就记载有汉代“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景象,明确描述出当瘟疫发生时,腾空房屋以隔离患病之人,并医治之。可见,隔离是防疫的重要措施。晋代的《神仙传》记载麻风病人要求“生弃”以防传染家人,避免造成“世世子孙相蛀”的惨剧。唐代《释道宣续》有“收养疠疾,男女别坊”的记载,宋代更是产生专门的病坊来收容无处可归的病人。清代时,天花流行,无论皇宫内外皆受其害,《北游录》记载“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可以看出天花的危害以及民众对该病的惊惧,故传染病最首要的防疫举措即为隔离。
此外,隔离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少聚集。元代《为政善报事类》直接指出“群聚有疾疫之虞”,可见,元代人们即有减少聚集以防止疫情传播的认识。实际上,大量的隔离措施主要集中于具有明显病状的染病之人,而“少聚集”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由携带者或瘟疫初期病人传染的可能性。无论是病人的单独隔离还是减少聚集,均是为了减少人传人。可见,古人对于隔离防疫的认识已达很高程度。
2 巫术
由于早期民众对于疾病的认识程度不够,医疗卫生手段较为匮乏,导致人民患病后祈求诸鬼神。故而,在医疗的发展史上,先有巫后有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大聚篇》记载有“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可见巫术与医药在古代密不可分。很长一段时间,瘟疫都被认为是由疫鬼所致,杜甫有诗言“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韩愈的《谴疟鬼》中更是记载了“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展现出符咒治疗瘟疫的景象。从疫鬼导致瘟疫,到寻求巫术治疗瘟疫,总体包括驱傩和符咒两种。
2.1 驱傩
驱傩是一种驱逐疫鬼的民俗活动,《后汉书》记载了“大傩,谓之逐疫”这一汉代驱傩活动,具体步骤为:“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浅……以逐恶鬼于禁中。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2]唐代孟郊在《弦歌行》中写出“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的仪式场景,更有“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的热闹场面。可见,古人认为驱傩可减少疫病的发生,这与过年放鞭炮驱赶年兽有共通之处。
2.2 符咒
随着巫术的发展,道术应运而生,故在巫术防疫流行的情况下,产生了符咒防疫。据唐代《酉阳杂俎》记载,在门上画虎头,写‘聻’字,可以“息疫病”[3]。至清代,《鼠疫约编》仍有“黄纸朱书⨁乙三字悬之,可以避疫鬼”的记载[4],《松峰说疫》还单独列出各种符咒,包括赤灵符、避瘟神咒、禦瘟符咒、送瘟疫时灾吉凶诗等[5]。可见,符咒防疫深入民心。
实际上,历代医家对于鬼神致疫大多持否定态度。唐代孙思邈认为霍乱“皆因饮食,并非鬼神”,摈弃了疫鬼之说。元代也有破除迷信的记载,如《运使复齐郭公言行录》指出南安大疫不衰的原因是“其俗尚巫,事鬼摒医弃药”,故而建议医生当众治疗疫病,以使人民破巫信医。然而,尽管历代都大力提倡破除迷信、否定鬼神,但巫术防疫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直至清朝仍不衰。
3 医药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有可辟瘟逐疫的药物,如升麻可“辟瘟疫瘴气、邪气虫毒”。随着医药防疫的逐渐盛行,在长期与瘟疫的斗争中,医药防疫的方法变得五花八门,如出现了佩戴药草、洗药浴、饮屠苏酒等,不过这些医药防疫方法总体上还是分为内服与外用两种。
3.1 内服
内服药物大抵可分为三类:一是寻常药物制成的丸、酊、汁、汤、散、饼,或泡入井水中内服,如《肘后备急方》的朱砂蜜丸、《备急千金要方》的屠苏酒与芜青汁、《外台秘要》的豉汤方、《证治准绳》的崔文行解散、《景岳全书》的福建香茶饼、《种杏仙方》泡入井水中的赤小豆;二是以普通饮食作药,如《调疾饮食辩》载鱵鱼“夏秋食之,不惟无疫”,《本草纲目》载《肘后方》中鲍鱼头“烧灰方寸匕,合小豆七枚末,米饮服之,令瘟疫气不相染也”[6];三是以野味类作药,《本草汇言》载蚺蛇肉为“辟瘟瘴之药也”。实际上,寻常药物与普通饮食很难进行区分,如蒜既是寻常饮食也是一味有效药物。同时,对于古人而言,并未有野味一说,动物炮制后皆可入食入药。以上所载,均为经消化吸收的内服药物。
另外,也有内服催吐的用法,如《松峰说疫》中记载远志去心煎水服用后涌吐可致“疾疫不生”。
3.2 外用
历代关于药物防疫的方法众多,包括佩戴、悬挂、烧熏、涂抹、塞鼻、点眼、洗浴,共七种。《神仙济世良方》记载佩戴大黄可防瘟疫,《松峰说疫》指出女青挂帐中“能避瘟”,《古今医鉴》所载神圣辟瘟丹焚烧后可“辟一岁瘟疫邪气”,《万氏济世良方》载麻油涂鼻孔可使病人家“不相传染”,《医方考》以大蒜塞鼻防染,《验方新编》用人马平安散点眼以“不沾染”,加桃枝煎汤洗浴可避疫。除这些用于人身上的方法,还有一些较为猎奇的记载。如《本草纲目》载:“正旦朝所居处埋鼠,辟瘟疫也。”[6]通过在住处埋鼠从而避疫,但这种方法缺乏理论根基,与巫术法门类似,相关记载较少。
4 疫苗
疫苗是一种通过控制感染程度以预防重症感染的防疫手段。两晋时期已有疫苗的雏形,如《肘后备急方》记载:“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7],明确指出以患有狂犬病的病犬大脑敷伤处可治狂犬病。之后的抗疫过程中,古代医家未能发现疫苗的作用,可能是由于对直接传染源认识不明确,如对于霍乱、痢疾等疫病的流行,虽知道致病因素,但不能明确找到类似狂犬这种明确可见的传染源。
直至水痘即天花的盛行,医家们才开始寻求疫苗法以预防天花。据《牛痘新书》记载:“考世上无种痘,诸经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8]书中明确指出鼻苗种痘法始于唐朝开元年间。《痘疹定论》也记载有种痘治疗这一方法[9],但多为二手史料,缺乏旁证,故而关于水痘疫苗的起始一直难有定论。乃至清朝,种痘术逐渐成熟,《医通》中便记载了多种种痘法,如痘浆、旱苗、痘衣法。种痘术的出现,可能是医家们对生活、疾病观察的结果。虽然古代对于疫苗的认识程度不够,但运用疫苗防疫仍是当时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5 饮食
饮食防疫是通过控制食物、水源的方法来预防饮食所致传染病的防疫方法。战国时期《管子》记载有“抒井易水,所以去玆毒也”,讲究用水清洁。汉代的《吴越春秋》中亦有冷藏保鲜食品的记载:“休息食宿于冰厨。”可见人们已意识到食品需冷藏保鲜。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食注“饮食相染,随口入侵”,明确指出食注这种传染病源于饮食不当。明代《梦溪笔谈》载有“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10],指出饮乌脚溪之水皆易罹患瘴病。清代王孟英于《霍乱论》中指出“广凿井泉,毋使饮浊”,以预防霍乱。《喻选古方试验》中也有“不食牛马犬肉者,不染瘟疫”的记载。这些均是谨慎饮食以预防瘟疫的佐证。
6 洁净
洁净主要目的在于保持洁净,是防止接触、飞沫、空气传播等导致传染的措施,包含清洁、消毒、防护、通风这四个方面。洁净与隔离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播而减少未染病之人与具有传染性的人、物、气等接触。然而,隔离是对于染病人所进行的预防措施,目的在于减少传染;而洁净是一种通过对未染病之人进行个人防护,以减少传染的预防措施。
6.1 清洁
清洁包含住所清洁以及个人清洁两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礼记·内侧》中即有对于清洁洗漱的记载“鸡鸣初,咸盥漱”,还有 “洒扫室堂及庭”的记载。足见人们对清洁的追求由来已久。宋代的《针灸神书》[11]记载了全套去患瘟疫人家而不染病的医师辟疫法,其中即有“如出门回家……至长流水边,浣口、洗手”的记载,虽未明确指出疾病由脏污所致,但已认识到洗手可预防传染病。清代《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指出“扫除洁净”,这是一种住所清洁的方法,可用来预防霍乱的发生。无论是住所清洁还是个人清洁,均是为了减少接触传播。
6.2 消毒
明代更是发展到对病人的衣物进行清洁消毒,《本草纲目》中记载有“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6],之后大量记载多延用此说,认为蒸法可以消毒预防传染,并不只是简单的清洗病人衣物。
6.3 防护
防护是指通过减少直接接触以防疫的方法。宋代《针灸神书》[11]中即有“立不中门,坐不靠壁,卧不解衣,盖被不可近口。凡有饮食,务自己气吹过,方可吃”的记载,明确指出通过减少接触以防疫病传染。另一方面,古人认识到疫病可从口鼻而入,故叶天士有言:“温邪上受。”清代《杂病源流犀烛》中更有详细的说明:“于是更增一种病气死气相渐染,犯之者从口鼻入。”[12]无论是空气还是飞沫传播,古人认识到疫病可从口鼻传染后,产生了相应的口鼻防护措施,如佩戴口罩。《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献饮食于大汗之人,有大臣数人,皆用金绢巾蒙其口鼻,俾其气息不触大汗饮食之物。”[13]这是关于中国人使用口罩的最早记载。直至清末发生的哈尔滨肺鼠疫中,伍连德制作伍氏口罩,明确以佩戴口罩的方式预防肺鼠疫感染。
6.4 通风
从口鼻而入的病气往往与空气、飞沫传播密切相关。《验方新编》记载:“凡云、贵、两广等省地方,忽有一股香味扑鼻,即是瘴气,断不可闻,以免生病”[14],明确指出空气可致疫病,因此,大多防疫措施讲究勤通风。清代《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载:“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15],提出以通风来预防霍乱。通风有利于保持空气新鲜,从而减少空气、飞沫传播疫病的概率。
7 灭源
灭源即消灭传染源,一方面指消灭直接传染源,如驱赶传播狂犬病的病犬、驱逐传播瘟疫的苍蝇等;另一方面指消灭间接传染源,如焚烧病患的尸体、物品等。
7.1 消灭直接传染源
春秋时期《左传》记载了“国人逐瘈狗”一事,描述了一段人民群众驱逐狂犬的场景,很可能是因为狂犬伤人,为避免更多人受伤,故而驱逐狂犬。这种驱逐狂犬的行为可视作消除传染源以预防狂犬病蔓延的防疫措施雏形。清代《松峰说疫》记载了逐蝇去疫法:“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古籍中关于消灭直接传染源的记载较少,这很可能是因为直接传染源多为不洁的饮食,只需注意饮食即可。
7.2 消灭间接传染源
早在晋代的《肘后备急方》中即有关于“尸注”的记载,明确指出此病“死后复传之旁人”,已经意识到尸体也是瘟疫的传染源之一。唐代开始即有掩埋瘟疫尸骨的举措,虽然这种措施主要出于对死者的悲悯,而非意识到防疫需处理尸体以减少传染,但仍起到了实际的防疫作用。直至清末,伍连德明确主张焚烧肺鼠疫病人的尸体、物品以防二次传染。实际上,焚烧传染病病人的尸体与物品是消灭间接传染源的有效方式,之所以直至清末才有人实施,与中国自古以来尊重尸身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再者,古代疫情常在贫苦群众中大量传播,死者众多,焚烧需要的条件并不具备;同时,底层群众物资很匮乏,不会贸然焚烧病人的物品。
8 启示
通过对古代防疫措施进行梳理,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一是防疫措施来自于疫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二是找到明确病因是防疫的重中之重;三是外用中药防疫适用于长期或反复的疫情。
8.1 古代防疫措施是对疫情的有效应对
从有限的知识中,古人发掘出了各种防疫手段。从巫术防疫到医药防疫,从饮食感染现象观察到饮食防疫、灭源防疫。从惧怕传染产生隔离防疫,从发现接触不洁导致传染产生洁净防疫,又可能因为少量接触感染后有了免疫效果因此产生了疫苗防疫。不难发现,古代防疫措施都是通过观察疫情发展规律而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
纵观历代抗疫历史,防疫措施不外乎隔离、巫术、医药、疫苗、饮食、洁净、灭源这七种,几乎包揽了现代防疫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病人隔离、少聚集,疫苗研发,饮食检疫,保持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的良好习惯,还是消除传染源,都是至今防疫的主要措施。今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需要观察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总结出相应的防疫措施。
8.2 明确病因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由于古代医学发展程度不高,不能将对瘟疫的认识深入到细菌、病毒等层面,故而许多防疫措施只能针对表面的病因,如对于饮食所致的疫病就谨慎饮食,对于空气所致的疫病就佩戴口罩,对于瘈狗所致的疫病就驱逐瘈狗,对于青蝇所致的疫病就驱逐青蝇。病因即疾病的源头,古代医疗能力有限,因此医家十分重视源头控制,通过消灭或者隔离病源来防治疫病。这也启示了防疫的关键是要明确病因,从而从源头上消灭疫情。
9 结语
现代社会对于疫情所采取的中医药应对措施远不及古代丰富。当然部分防疫措施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会受到抛弃,如巫术防疫,既不合理、又不科学,应该破除这种迷信。但是,很多中医药的防疫措施仍有其积极意义。其中,内服中药防疫虽不是很普及,但仍有不少拥趸,并有逐渐发展壮大之势;而外用防疫却乏善可陈,难以成为主流。众多瘟疫都有反复出现的特点,针对于疫情的此起彼伏,现有的许多防疫措施,如停产隔离、时时测温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观古人的防疫方法,如佩戴、悬挂、烧熏、涂抹、塞鼻、点眼、洗浴等这些防疫措施往往卓有成效,在古代医籍中有大量的成功应用经验,似乎更适用于长期防疫。当然古典经验需要现代科学的验证,这些方法是否适用于今天,仍需进一步的科学实验研究来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