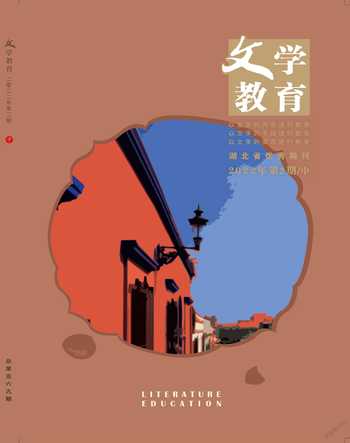与众不同的吴老师
甘娭毑
第二天,日上三竿,小孩醒了。他睁开眼,这是哪里?山冲、树木,小路、石板变成了蚊帐、被子、床。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了,撩开帐门一眼见到一个男人站在面前。
“醒了,还记得我不?你昨夜吃了我的东西,又睡在我的怀里,之后我就把你带回来忒。”颜永农见孩子一脸的疑惑和恶意的眼神,忘了这个孩子是个哑巴,一个劲地提醒孩子昨夜发生的事。
他意在消除这孩子的敌意,从而让这孩子知他的恩。
小孩依稀记起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当时天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概形模、说话的声音有些熟,也记起吃了他的东西,偎在他胸前睡觉。
不过他更清楚地记得带他出来的那个让他叫叔叔的男人也给了他好吃的东西,也把他抱在怀里。后来那家伙把他丢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害他见不到父母;害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害他夜里宿在树兜下、田坎下。天啦,黑夜里鬼叫狼嚎把他的魂都吓跑了。
“信不得眼前这个人,这个人也不是个好家伙!得赶紧跑!”小孩想着猛地从床上跳下来往外跑。
颜永农连忙拦住:“你这是到哪里去?这里山冲岔路多,又跑丢了怎么办?先吃饭,吃饱了我带你去找你爹娘,好不?”
小孩见这个人拦着不让走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拼命地往外冲。颜永农拦到左边他就往右边冲,颜永农拦到右边他就往左边突,颜永农就双手一张双脚一叉,孩子就从他胯下钻过,颜永农连忙又把两膝盖合拢。
就这样一个要跑一个要拦像在玩杀羊游戏,当小孩左冲右突挣脱不掉时,索性往地上一滚,大哭大闹起来。
他声嘶力竭地叫喊:“爸爸、妈妈救我!你这坏蛋,赶快放我走!”(普通话)
嘿,原来这孩子不是哑巴,能说话呀,还打生呢!颜永农大吃一惊。仔细听听除了能听懂“爸、妈”外,其余的“叽叽嘎嘎”半句也听不懂。
这不是拖木埂的孩子,而且还不是本县的,颜永农完全可以肯定。
他做木工时到过本县很多地方,什么沙坪语、大元音、金沙调他都能听懂,并能学说几句。可这孩子说的话叫他听着陌生,简直闻所未闻。
捡个别处孩子,这就是急死人的事,语言不通怎么跟他沟通呀?怎么了解这孩子的来历、身世?又怎么送他回家?颜永农一片茫然。
得找个翻译,否则无法跟这孩子交流,颜永农打算。
可是村里除了几个当过兵的人越过省界再也没有越过县界的了。这年头你有面子当上兵就不用呆在深山沟里了,现在到哪里找个懂别处话的人呢?
颜永农想呀想到底还是想到一个人,他是村小学教书的吴老师,从省城里下来的。听说他在省城读过师范,原先在省城里教书,不知犯了啥法打成右派被遣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他刚来时说话口里像含个骚萝卜,缠齿夹舌。
村里人听得懂山上的鸟叫声就是听不懂这人说的话。具体颜永农也没听过吴老师说的话,因为吴老师来的那年他正带着未婚妻逃亡在别处。
拖木埂像一个封了口的坛子,这里的人固步自封、封建老旧不说,排外欺生是他们的本能。吴老师这个外来佬如若不是稍微开明的村长时不时拿只眼睛射他一下,非被大家嫌出绿眼屎出来不可。
的确这个吴老师做的事很不像话,看了的人不是摇头作呕,就是笑掉腰子。
他是来接受劳改的,是来跟泥土打交道的,而他一副书生作派,戴着白纱手套、穿着雪白的鞋袜下地,仿佛要跟泥土划清界线。
这时的人除了冬天几乎不兴穿袜子,事实上热天里男人们几乎清一色打赤脚,只有上山干活时才穿鞋子。
所以说在田畈里穿袜子跟在大街上打赤脚一样格外抢眼,让人极为不齿。
“假马(扮洋气)算你的,有那么好的命就在石板大街上住着莫下来。(当时人们心目中石板街是最好的生活环境)。”有人当着他的面这样说他。
反正他听不懂,就算能听懂也无所谓,他本身就是一个坏人,行为不正就该说,这种修正主义思想行为不该接受批评吗?把他划成右派没划错人,还死不改悔还得作正经接受批斗。
在吴老师刚来拖木埂时,一生产队的队长一把抢了他去,像这样不要公分又能当牛当骡子一样使唤的劳动力来一百个都要得。
不过后来的事实改变了队长的初衷,又改口说像这样的劳动力半个都多了。
一开始队长安排他去锄草,他分不清哪是苗、哪是草,常常把社会主义的苗挖了留下资本主义的草。
他锄草比别人翻地使的劲还要大,要斩草除根,把长草那一大坨土翻个低朝天,连带着把庄稼苗的根系扯斷或是让根巴不到土,太阳一晒苗子焉了干了。
这完全是搞破坏呢,于是一顶“反动派”的帽子加在“右派分子”上。
大家把大干社会主义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转到开他的现场批斗会上来,会议地点就在他们地边的一棵大木梓树下。
他被罚站在大日头底下,劳动群众都集中坐在大树下阴凉处。大家口诛笔伐、上纲上线对他进行严厉的批斗,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打倒反动派!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远不得翻身!”
可怜他给晒得“油”直滴,羞愧得魂都出窍了。
从那之后队长再也不敢冒险让他搞这类破坏活动了,又叫他去担大粪。
人们晓得他担不起一满担粪只给他舀半担,也料到这粪水在他肩上的桶里要兴风作浪,因为大家对“满罐不荡半罐叮当”深有体会,于是在每一只桶里放上一片大南瓜叶。
然而他担大粪的那个相简直让人看不完,扁担在他肩膀上前后不是平的,前头老爱翘起来,为了摆平扁担他双手死死攀住前头。这时他的背弓成个犁辕摇摆着向前。
有人指点他把扁担居中,腰挺直,他虚心接受教导也照样做了,可是扁担的后头又翘起来了,他又用双手死死顶住扁担前头。
在平路上勉强保持平衡,上岭就把持不住,这时扁担往后溜人也往后倒,他就成了一棵庄稼给浇了粪。
粪泼了桶破了他也急死了,心想又该遭批斗了。
居然把改造的工具都毁坏了,这不是消极怠工,对社会主义不满吗?
这粪桶摔破了事小,大家晓得他是一个无用之物,舍不得给他好工具用的。人们心痛的是这泼了的粪,粪是庄稼的营养,村里这一大片的土地上的庄稼全靠农家肥来养,哪里养得过来呀?
看那一株株庄稼长得黄皮寡瘦的,严重营养不足。
村里还专门派劳力外出捡狗粪,捡粪人一手提着土箕一手拿着耙子沿着屋堂附近的田埂转着圈儿找狗屎,一天到晚捡不了一吊担碗。
看,这样一担粪一家伙就给他泼了,这粪要浇多少棵庄稼,要减少多少收成啊!
在他作好了挨斗的准备时结果人们赦免了他。人们似乎对他有所原谅,没有哪个坏蛋搞破坏不保护自己反而严重伤害自己的。
更何况他是那么洁癖的一个人,平时泥巴粘到手上当作梅毒巴上了,肥皂洗了几遍还要在清水里濯了又濯,现在给粪浇了个透估计他非要把皮都剥了。
吴老师的自虐解不了人们心头之气,人们气不过骂几句:“看得卵见,无作用,只噜(吃)得干饭。”
他不是来休养的,不能因为他这也不会那也干不得一天三餐吃饱了闲着。
队长又安排他去割草,这种农村小孩都会干的活,然而偏偏他干不好,镰刀不割草偏要割自己的手指,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的让人看了发怵。
“天啦,莫作孽呀!他不是干农业的料,只当得相公。”有人说,这话表面上鄙视他实际上带点同情味。
队上实在没有他能做的事,刚好那放牛的老头病了,队长让他放牛去。
他欣然接受了这项活儿,他带上白色的口罩,白色的手套,高筒的雨鞋进了牛栏房。他把牛赶到河边,先用水把牛浇个遍,然后打上肥皂,用鞋刷子满身刷,把头牛刷得白泡直翻。
给牛洗澡还打洋碱(肥皂),这是农村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看热闹的人来了,队长也来了,老远就叫:“天啦,叫你放牛就只要找个有草的地方把牛放着吃,你给它洗个什么澡呢?它本是邋遢东西,你一天给它洗一百遍还不是邋遢?你做好事哟!水牛是水里捞的东西,一天到晚浸到水里没事,可这黄牛挨不得水,感冒了没药治。”
队长气坏了,说什么都不要这个人,只要哪个队要不光白送还倒贴一年饭钱。
一株这样的毒草,一匹这样的害群之马,一个这样的活宝,人们避他唯恐不及,恨不得把他丢到那老山林中的庙里去住,哪个队要他呢?
村长念他是个文化人,不是做三呵(外面的体力活)的料。就让他到村小教书,把肚子里的“货”抖些出来,烂在里面实在可惜。
因他读了师范,这学校的校长也不过高中毕业,在村小文化水平属他最高,校长让他带高年级语文。
这个吴老师真有点幼稚,脑子里偏出个不结合实际的念头来,要在这里推广普通话,让拖木埂的孩子不说自己的家乡话而说他的家乡话。
他用普通话给孩子们上课,本来他可以用蹩脚的方言上的,学生们的反映大了,说他们听不懂吴老师讲的课,不知他叽叽呱呱说的哪番邦话?家长们闹到学校把他从讲台上拉出来。
校长只好叫他去带一年级,哪晓得一年级他都教不了,第一节课他教了“上、中、下”三个字就教白了两个,“上”在本地发“桑”;“中”在本地发“灯”。
村长就不信,堂堂一个师范生就教不了小学,他的这个师范是拿屁股眼读出来的?他找吴老师问情况:“小吴,你怎么把那么简单的字音都教白了呢?你是有意吗?我让你教书可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不懂的要向其他老师请教,你不要在我脸上抹黑呢!”
吴老师很委屈:“村长,我确实没教错,不信我可以查字典给您看。”
“我也不相信你教得错,可是你教的音跟别的老师教的就是不同,学生们就是听不懂。”
“我教的是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将来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不用普通话行不通,普通话跟你们的方言有很大的区别。”吴老师说。
“你就不用想那么长远,方圆百把里说的话都差上不差下。我们的孩子能走出去多远呀?学了那外地话来说给山上的草木、地里的庄稼听,还是跟牛羊、鸡狗对话去?倒是你,既然你住在这里就要随乡合乡、随曲合曲,要不你教书这碗饭吃不成。”村长说。
吴老师只好改变自己,随乡入俗了。现在他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拖木埂”话来。
后来吴老师不仅以高超的教学水平赢得了家长、学生的信任。他越来越多的智慧、优点显露出来,很受大家的喜爱。
他尤其吹得一口好笛子,拉得一手好胡琴,姑娘们、小伙子们空闲时找他学。
他满腹经纶,说起“唐传三国”来口若悬河,空闲时人们喜欢到学校里去听他讲古。
虽然他的“右派”帽子还带在头上,管他右派、左派,这里的人连“政治”两个字都不认得,哪里还弄得明白“右派”的含义?通过长时間的接触人们只知道他是个正派的人。
这里附带说一句,像吴老师这样头上顶着“右派”帽子没摘的人全国都没有几个了,说不定他是最后的一个。因为这地方太过封闭,国家的政策、形式传进来时外面恐怕早就过身了。
“是的,吴老师一定能帮得了自己。”颜永农坚信。
甘娭姆,本名甘望明,现居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