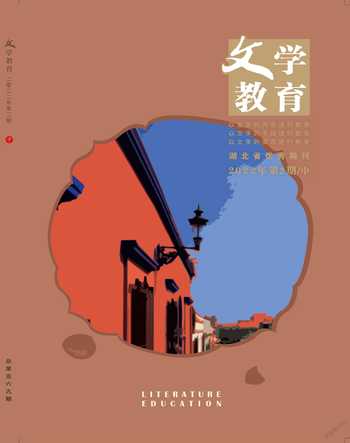说文
鸽子
文学是个非常奢侈的东西,没有大把时间和精力是玩不起的;有大把时间和精力也不一定玩得好,弄不好把一生都搭进去了也还是个打酱油的。当然,除非你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写着写着“一不小心”成了名家,混到了字字如金的地步。否则别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了,就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还写个啥!
在这个以实用主义为基调的人类社会,文人自古都不怎么受人尊重,“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古代的九流十家,“小说家”也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即便到了今天,文人照样也不怎么被看重,还是逃不出“然并卵”的尷尬困局,远没有有权有钱那么受人待见。甚至远不如昔。不信看吧,如若主席台上排位,管作家的机构绝对排在上、中、下九流开外三九二十七位之后!而且文人自己也轻视同类,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之说——这虽然指的是瞧不起他人的文学水平而敝帚自珍,但谁又说自己骨子里面没有对“文弱书生”的鄙视呢?可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文人志存高远、怀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种自欺欺人的清高。
毋庸置疑,最成功的人生莫过于名利双收。而这除了做官,似乎文学也可以成为通往这个目标的一大捷径。尽管在“利”的方面远不如做官那么容易变现,但至少在“名”上是文人还是不逊于官的,甚至比做官更能流传千古。只要有了名气,终归也能被人高看一眼。也许正因为不能像做官那样轻易获取利益,反倒索性把利看得轻一些;有的甚至矫枉过正,故意显出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来,以致许多人弄假成真,最终成就了自己一生的清贫。
言归正传。本打算是名利双收的,而现在只剩下“名”了,所以文人就把这唯一的东西看得很紧,平时如若有人哪怕在面上虚情假意一番,奉承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什么的,心里便很是受用;倘或称其“大才子”、“大作家”时,那就更是心花怒放了。当然,也有装一把的,认为这太俗气,故而做出不屑的状态来抵制媚俗。但心底里却是非常享受这种被吹捧的滋味,说到底是装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来赚取更大的名气。著名作家晓苏在《粉丝》里刻画了一个叫韦敬一的人物,这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教授倒是“不屑于”别人的吹捧,甚至不屑到“反感”,但后来被人慢慢吹到点子上了,“吹”得舒服了,居然也对别人的“吹捧”上了瘾,不也离不开“粉丝”了么?
许多人就为了“作家”这么一个虚名,常常把大好时光浪费在文学的折腾上,耗尽一生,陶醉于虚妄的精神世界里不能自拔。因此养成了清高、孤傲和自我的一身臭毛病,除了“穷”和“酸”,也就剩下“一无所有”了。
所以文学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你得像屠格涅夫《门槛》里的那个女郞一样做好牺牲和奉献的准备;非要坚持下去,你就得有一份维持生计的职业。大凡成名的作家,绝多是有赖以生存的职业的,他们不为稻粱发愁才能心无旁骛地玩下去,没有后顾之忧地玩下去,因此玩着玩着,有的才玩成了气候。
文学的路虽然不好走,但仍然有许多狂热的写作者前赴后继。因为作为一门与生活密切得无法分开的艺术,她实在是太迷人了——至少对于热爱她的人来说。而她的门槛又太低,但凡有点想法又识点字的都可以进来。所以这条路上拥挤的人实在太多,而真正成为名者、尤其能成为“文曲星”照耀后世的人又实在太少。正像前面说的这是个非常奢侈的行当,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搅起几朵浪花来。尽管貌似有慧根者在这方面有了些许突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冒了个泡泡,好不容易冲进三流四流作家的门槛,但再往上也就冲不上去了。所以虽然他们在某一域、某一隅算是冒尖的,有了些许名气,然充其量也只是小河沟里的鱼虾,只能在眼巴前儿的溪水里游弋。一旦离开了小河沟,到了大江大河乃至于大海呢,照样渺小得几近于无了。
当然,实话实说如果你有维持生计的稳定收入,或者什么事不做依然衣食无忧,玩文学倒也不失是一种高雅的选择,因为文学作为精神寄托或信仰,可以使自己变得高雅而又充实。而且文学可以净化心灵,在净化社会和他人——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同时也在净化自己,因此可以说爱好文学的人大多是心灵高尚的人。
但要奉劝那些痴迷于文学却至今仍无大成的人,切不可把这事太当回事。作为爱好,业余时间玩玩票可以,但要适可而止,不可陷得太深。也许你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能够改变命运——至少能改善你生存质量的大事要做,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雅趣”而顾此失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说白了也许你本可以成为你所从事的行业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业界耀眼的明星,就因为“误入歧途”而导致一生平庸,最终黯淡无光。
更要奉劝那些没有生活来源却梦想把文学当作谋生手段的人,别指望文学能养家糊口,更别做名利双收的美梦,除非你有王朔的天赋和韩寒的异禀,否则一定会把自己输得连底裤都没有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