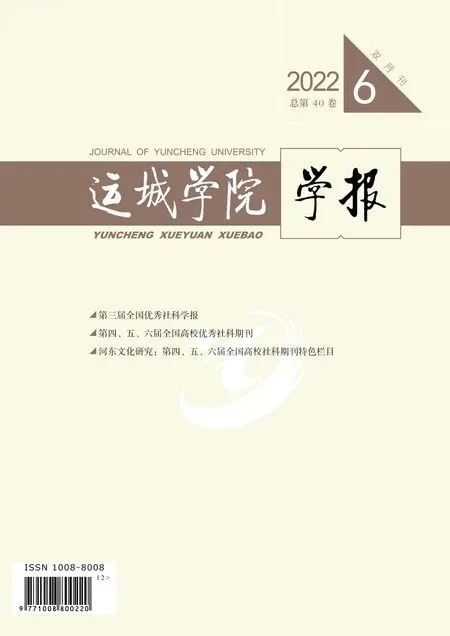论“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之共通面
李 慧 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美学及文艺思想中的两大范畴——“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其中蕴含着深厚的生命哲学思想。“日神精神”遮蔽人生的苦难本质,使人沉浸在世界与人生的美丽外观中,从而放弃对人生本来面目的探求,这显然不能回答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因而,尼采用“酒神精神”来弥补“日神精神”的缺陷。“酒神精神”是尼采美学与文艺思想最核心的范畴,它强调破除世界与人生的美丽外观,使人直接与其苦难本质相对。“酒神精神”虽然承认生命的悲剧性,但它并不否定世界与人生,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肯定人生的态度。正是出于对世界与生命的肯定,“酒神精神”反对权威与理性主义精神强加给生命的束缚,它使人在酣醉狂放的状态中与世界生命本体相融合,在悲剧的陶醉中达到对苦难人生的超越。
在我国魏晋时期,儒学式微,玄学兴盛,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皈依。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器范自然,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为上都追求“自然”的境界,逐渐形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风流”。“魏晋风流”也叫“魏晋风度”,它蕴含着魏晋士人独特的生命哲学思想。“风流”是基于痛苦人生的体认,然而,魏晋士人并不否定生命,而是肯定并执着于现实人生,并且追求对苦难人生的超越。另外,“风流”还体现在对传统权威与理性的颠覆与超越。可见,“魏晋风流”与“酒神精神”有着诸多相似与共通之处。
一、基于悲剧人生的体认
“酒神精神”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尼采对生命悲剧性的体验与认识。尼采本人的生命历程就充满了悲剧色彩。幼年之时,父亲与弟弟相继离世,这使尼采过早地看到了人生的阴暗面。成年后的尼采又长期遭受着病痛折磨,陈鼓应在《悲剧哲学家尼采》一书中对此有过一些表述:“强烈的神经痛、失眠症以及消化不良种种病苦缠绕着他……因用功过度而旧病复发,甚至几临于死亡的边缘。”[1]而对于尼采来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晚年的精神失常。从他在意大利都灵市疯掉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实际上,除了病魔的折磨,成年后的尼采还遭受着事业与失恋等带来的精神折磨。悲哀不幸的生命体验影响到了尼采悲观厌世的思维倾向。
如果说痛苦的人生经历奠定了尼采悲观主义思想的基础,那么叔本华的悲剧人生观则加速了他悲观主义思想的成熟。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正如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所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2]既然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那么任何试图摆脱痛苦的行为都是徒劳。叔本华作为尼采的精神导师,他的悲剧人生观对尼采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尼采的悲观主义思想在叔本华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加强。
“酒神精神”的提出实际上正是基于尼采对生命悲剧性的认知。尼采在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下,最终确认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然而,他认为要战胜和超越生命的悲剧性,基于此,他提出了“酒神精神”。尼采认为,“酒神精神”象征着一种深度的悲剧情绪的宣泄,这在酒神秘仪中有着明显的体现。酒神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与狂欢之神,同时也是亲自经历个体化痛苦的神,而酒神秘仪就是庆祝酒神的新生而举行的宗教仪式。在酒神秘仪中,人类在“酒神精神”的笼罩下抛弃了传统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滥饮大醉、放纵性欲,回归到了一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悲剧性情绪得到了极大宣泄,个体也在与世界本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获得极大快慰。
同样地,我国的“魏晋风流”正是基于魏晋士人对悲剧人生的体认。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除了西晋灭吴至晋武帝去世,“八王之乱”爆发前十年相对和平外,这一时期的其余时间基本上可以用战火连天来形容。然而,魏晋时期除了战乱,旱灾、洪水、瘟疫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天灾人祸的横行使得当时的人们常常过着一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死亡成了这一时期笼罩在华夏大地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曹操在《蒿里行》一篇就曾对这一时期的人间惨状进行过描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3]625
民间的悲苦强烈地冲击着魏晋士人的心灵世界。然而,这一时期带给他们心灵冲击的远不止这些。魏晋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还遭受着政治的打击。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的混乱使得魏晋士人的命运变得飘摇不定。这一时期很多的文人士大夫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比如何晏、嵇康、潘岳等。除此之外,魏晋士人还面临着信仰的失落。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它对我国古代文人发挥着规约与指导作用,然而,魏晋时期的儒家思想逐渐被司马氏集团所操控和利用,成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和工具。正统儒学的式微使魏晋士人逐渐失去长期以来的价值信仰,心灵失去凭附。
现实的种种不幸带给了魏晋士人刻骨铭心的痛楚,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4]92而觉醒后的魏晋士人开始反叛已然变质的价值信仰:“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4]92在反叛传统的同时,魏晋士人又在道家思想中寻求新的精神依托。正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开始追求“自然”的人生境界,行为上不拘小节,精神上超脱旷达,形成了后世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流”。由此可见,“魏晋风流”正是魏晋士人基于痛苦的生存现实而寻找到的新的精神出路。
二、肯定生命的意义
尼采的“酒神精神”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基于他对生命悲剧性的认识,但他并不否定生命,而是肯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尼采的“酒神精神”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肯定人生的态度,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就是对生命原力的肯定。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对“酒神精神”下定义时就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5]101
按照叔本华的观点,世界意志是徒劳挣扎的盲目力量,而人生是这意志的现象,由此出发,他彻底地否定了人生。然而,尼采对叔本华所说的“世界意志”进行了重新解读,对叔本华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生观进行了颠覆。与叔本华不同,尼采认为世界意志并不是盲目的力量,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作为现象的人生或个体生命总是短暂易逝的,然而生命意志是充沛的、强盛的,个体生命不断毁灭的同时又不断地产生新的生命。从世界总体生命来看,个体生命恰恰处于一种永恒的轮回当中。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尼采肯定生命的酒神世界观影响到了他对人生中的痛苦与不幸的看法。个体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是固然存在的,然而尼采并没有否定这些消极成分,相反,为了肯定人生,他连同人生的缺陷都一起肯定了。按照尼采的观点,生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与阻碍,而人们在克服这些困难与阻碍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痛苦甚至是毁灭。从尼采的这一观点出发,人生的痛苦和毁灭就获得了合理性。另外,尼采还认为,虽然人生中难免有痛苦与不幸,然而这些痛苦与不幸并不只有消极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还是创造的条件、新生的前提。
我国的“魏晋风流”也是一种肯定生命的文化精神。魏晋士人的“风流”是他们基于痛苦的生存现实而作出的行为与思想上的反馈,而“风流”背后表现出的更是魏晋士人对现实人生的肯定与执着。“魏晋风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视真实感情的自然抒发。魏晋士人常常通过文艺作品抒发他们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慨,比如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3]628曹植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3]763阮籍有:“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3]821这种对生命的悲凉慨叹成为了魏晋时期的典型音调,然而,“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4]92
除此之外,魏晋士人的情感也有着昂扬向上的一方面。魏晋士人不乏一些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直接表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文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珍视。比如曹操的《短歌行》,全诗洋溢着高昂的情绪,蕴涵着应该及时努力的思想。再比如他的《龟虽寿》,其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3]634一句作为千古名句更是提醒着人们要把握有限生命,实现人生价值。魏晋士人类似的作品还有曹植的《白马篇》、孔融的《杂诗二首》、陈琳的《游览诗》等,这些作品都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绪,蕴含着作者对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渴望。
魏晋士人的“风流”有一个重要的表现——纵欲享乐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短暂多艰的现实人生激发了魏晋士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用纵欲享乐的方式来对抗这苦难的现实人生。纵欲享乐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追求感官欲望的极大满足以及追求物质占有欲的极大满足。魏晋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彻底颠覆了我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正是从侧面表现出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对现实人生的绝望,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生命的执着。
三、颠覆权威与理性
尼采的“酒神精神”对权威与理性有着强烈的颠覆与反叛色彩。西方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估价活动,比如,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等,这些估价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贬低和否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尼采的“酒神精神”则充分地肯定与重视生命价值。正是基于对生命的这一肯定的态度,尼采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认为生命才是价值的根源。尼采基于这一观点对基督教神学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精神进行了彻底地反叛。颠覆权威与理性就成为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颠覆与反叛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基督教宣扬“个体不朽”说和“另一个世界”说,这些学说给苦难人生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然而它把人类的幸福和希望寄托给了神灵,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人生,也剥夺了人类生活的根本重心。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宣扬“原罪说”和“禁欲主义”。“原罪说”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对原罪的救赎,而“禁欲主义”则彻底否定人的自然欲求。因此,尼采认为基督教神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敌视现实人生和生命的,于是他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对基督教神学教义进行反叛。
其次,颠覆和反叛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精神。苏格拉底有一个重要的哲学公式:“理性=美德=幸福”,它意味着人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理智、清醒、明白。苏格拉底用他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和颓废作战,然而尼采认为:“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生活,本身仅是一种疾病……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与本能相等。”[5]18-19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使人的自然本能受到压抑,本身就是生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因此他反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而“酒神精神”就意味着理性束缚的挣脱。在酒神状态下,人们的情绪系统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生命本能可以得到尽情地释放。
我国的“魏晋风流”同样是一种颠覆权威与理性的文化精神。魏晋以前,人们的言行举止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制约,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开始“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为上简傲任诞,不拘礼法,挣脱了传统经学权威的束缚。对此,《世说新语》一书有着大量描述。比如对刘伶纵酒裸裎行为的描写:“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6]631赤身裸体在大庭广众之下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显然属于越礼行为。再比如写阮籍:“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6]632醉后与妇人同睡一张床,阮籍置封建男女大防于不顾的行为显然更为直接地冲击了封建礼教。
觉醒后的魏晋士人认识到了名教对自然人性的戕害,反对矫揉造作地附庸经学传统,追求真性情的展示,也因此发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比如在《世说新语》的《伤逝》就有一篇魏晋士人“学驴叫”的故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合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6]549-550无独有偶,在《任诞》一篇中还记载了魏晋名士阮咸“与猪共饮”的故事:“诸阮皆能饮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6]634学驴叫、与猪一块喝酒,魏晋士人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完全颠覆了传统中谦谦君子的形象,对经学传统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极大的颠覆。
除了颠覆传统的经学权威与封建礼教,“魏晋风流”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反理性,其表现就是重情。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强调理性对待感情,然而魏晋士人则强调强烈感情的自然抒发,他们的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广度。阮籍在葬送母亲之时“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6]632悲伤到吐血的程度,足以见其对母亲的感情之深。然而,魏晋士人的深情不仅表现在人伦关系中,比如《世说新语》的《言语》一篇中说:“桓公北征……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6]102在这里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的深情已经扩展到了自然界,山水草木也成为了他们的情感对象。
四、对苦难人生的超越
尼采的“酒神精神”在本质上就是对苦难人生进行超越与拯救的文化精神。按照叔本华的观点,人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因而是不可救赎的,而尼采则用他的酒神世界观对悲剧人生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进行了超越与反抗。尼采认为,个体化状态是人一切痛苦的根源,而酒神经历了肢解并获得新生则象征着个体化状态的解除。对于个体来说,解体是最高的痛苦,然而经历解体之后,个体将在和世界本体融合的过程中感受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与坚不可摧,进而产生一种充满幸福的狂喜,获得生命的超脱。
在超脱苦难人生的途径上,尼采提出了“艺术拯救人生”的命题,而酒神与日神正是作为人生的两位“救世主”而登上尼采美学舞台的。然而,日神与酒神对人生的拯救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的。从日神方面看,神话、史诗等都是日神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些艺术用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来神化世界与人生,用这一方式达到对痛苦人生的超越。而从酒神方面看,悲剧是酒神艺术的典型代表。与神化人生的日神艺术相反,酒神艺术破除了人生的美丽外观,使人直面人生的痛苦与毁灭。而正是在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过程中,使人感受到世界生命本体生生不息的力量,进而获得超越性的快慰。
实际上,无论是日神艺术还是酒神艺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人生所作的审美辩护。在尼采的观念中,人生与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审美能够担负起为人生与世界进行辩护的使命。在尼采的酒神世界观中,只有把人生与世界当作审美现象来看待,它们才有充足的理由。正是出于对世界与人生作审美化、艺术化的处理,尼采主张把世界看作是酒神宇宙艺术家,把人生看作是这个宇宙艺术家聊以自娱的艺术品:“用审美的眼光去看世界意志的创造活动,把它想象为一个宇宙艺术家,把我们的人生想象为它的作品,以此来为人生辩护。”[7]站在宇宙艺术家的角度再来审视个体的痛苦与毁灭,人们不仅不会再沉溺于悲观消极的情绪中,反而能够获得一种审美快感。
超越苦难人生同样是“魏晋风流”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士人对超脱人生境界的向往基于他们对痛苦生存现实的体验,而这一精神追求同时也植根于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道”,而“自然”是“道”的基本特征。按照胡适的解释:“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8]“自然”也就意味着事物按其本来面目呈现,按其自身规律发展。魏晋士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之道,追求一种无所阻滞、超脱飘逸、自由自在的“逍遥”境界。而“自然”“逍遥”的境界,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我”“忘我”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生存带来的痛苦与不幸都将获得消解与超越。
魏晋士人对超越洒脱人生境界的追求付诸在了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纵酒。《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士人饮酒、纵酒的故事俯拾皆是,比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6]630再比如:“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此生。’”[6]639短短的几个片段性的描写便足以看出魏晋士人对酒的痴迷与钟爱。而魏晋时期的文人之所以嗜酒成风,根本上还是缘于酒对现实的超脱作用。由于痛感现实的无奈与焦灼而又无力改变现状,魏晋士人就开始发挥酒的麻痹作用。他们借助酒的作用进入一种“醉态”,用“醉态”来对抗清醒而又痛苦的人间,从而暂时遗忘痛苦的现实,获得一种短暂的超脱。
除了饮酒,魏晋士人还追求在自然怀抱中获得超越痛苦人生的力量。魏晋时期,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游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气。《世说新语》的《言语》一篇就对这一时期的山水游览有着大量记载,比如:“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6]127再比如:“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6]128自然界之所以成为魏晋时期人们独立的审美对象,其根源便在于它带给人的超越感与自由感。自然山水按照自身规律如其所是地存在,这与久处“樊笼”的人类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如此,自然界的山水花鸟、草木虫鱼等都在向人展示着宇宙充盈的生命力。当人类置身于自然界中,自然界的自由精神与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无不激荡着人的胸怀,个体的痛苦与不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也将逐渐得到消解和超越。
五、结语
“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作为两种重要的文化精神,在学界已经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两种文化精神都是在对生命苦难的体认基础上形成,都承认生命的悲剧性本质,然而同样肯定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对生命的肯定,两者都反对权威与理性对自然人性的束缚,并积极寻求苦难人生的超脱之道。然而,“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因此,必然存在着差异之处。具体而言,尼采是西方文化转型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提出的“酒神精神”是一种对西方文明形态进行彻底反叛的精神,而“魏晋风流”虽强调冲破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对个体的束缚,然而对于传统并不是彻底地否定,对于传统,魏晋士人有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另外,两种文化精神在气质上也有所不同。“酒神精神”更像是一种硬汉精神,强调征服一切、超越一切、摧毁一切的力量,更像是一种硬汉精神。相比较而言,“魏晋风流”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价值取向,这反映出了时代主流思想,即道家思想对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除此之外,两者虽有着表现形式的相似性,然而,灌注着不同的内容。总之,“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虽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然而有着“神”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