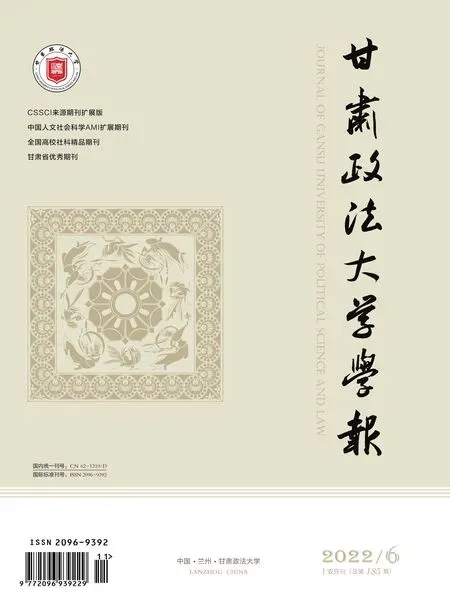定作人侵权制度适用的司法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从用工活动定性问题切入
任九岱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实践中,与定作人侵权纠纷相关的案件数量持续激增。通过在法律数据库对此类纠纷进行检索,可以发现相关的案件数量已经超过25000个,最近五年的民事案件数量则超过16000个,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案件数量均超过3700个,同时,二审、再审案件数量多。(1)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作为关键词,以“裁判理由及依据”作为搜索限定范围,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的民事案件总量为25484个,最近五年的案件数量为14607个,二审的案件数量占比为18.97%,再审的案件数量占比为1.76%。《民法典》实施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民事案件数量为883件。最后检索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该类案件中受害人往往非死即残,且多为青壮年劳动力,这对于受害人本人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应当说定作人侵权纠纷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问题较为突出的纠纷类型,理应受到重点关注。但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对定作人侵权制度的研究中,鲜有关注或者论及该司法现状,更遑论去探究该现状背后的症结所在,并进而反思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是否存在缺陷。换言之,定作人侵权纠纷和定作人侵权制度目前在学术研究中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
在这数量众多的案件中,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用工活动的定性问题,这不仅是各方当事人诉争的焦点,也是裁判者法律适用的难点,同时也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二审、再审案件。如在“郭智育与艾孜艾则木江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新40民终2000号民事判决书,伊宁县人民法院(2019)新4021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官认为受害人与用工主体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的从属关系,而应为承揽合同关系,由于无证据证明定作人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则认为,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考虑到受害人存在过错,雇主承担50%责任。在“卢龙强、李群玲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6741号民事判决书,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5741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受害人与用工主体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用工主体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承担60%的责任,受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承担40%的责任;再审法院则认为,由于用工主体不在现场,不存在指挥、安排、监督和管理行为,双方应定性为承揽关系,同时因定作人存在选任过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受害人自身存在严重过失,应承担70%的责任。在“时虎、刘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再15号再审判决书,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792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2016)皖1202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刘军与受害人时虎存在雇佣关系,利达公司与刘军存在承揽关系。刘军作为包工头未提供安全防护设施,应承担90%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公司明知刘军没有消防工程承包资质和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仍发包给刘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以事故现场不在刘军承包消防工程范围内为由,认定在工程施工中刘军与时虎均受雇于利达公司,由利达公司单独承担90%的责任;再审法院则认为,刘军与时虎之间在施工时成立雇佣关系,利达公司与刘军成立承揽合同关系,而利达公司存在选任过失,且在施工中提供错误水压信息,因而由刘军承担50%责任,利达公司承担40%责任。
通过对前述案例的梳理可见,伴随用工活动性质认定的改变,用工主体与受害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和责任承担也随之发生显著差异,可能从不承担责任到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从承担主要责任转变为承担次要责任,而且这样的案例数量并非少数。这种司法现状无疑将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诉讼周期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受害人救济的及时实现;裁判歧见明显,使得当事人无法形成稳定的法律适用预期,不利于激励用工主体事前的风险预防;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当事人陷入对用工性质的争夺战,不仅占用和消耗了司法资源,也难以起到息诉服判的效果。
由此,值得思考的是造成定作人侵权制度适用陷入用工活动定性困境的原因何在?目前司法实践又是如何处理该用工活动的定性问题的,其所采取的模式是否有效?如果有效,为何司法实践中频频发生因用工活动定性问题而导致的二审、再审案件?如果该模式存在失灵之处,那么造成这一司法现状的深层次原因为何?并进而追问是否存在解决这一困境、改善当前的定作人侵权制度适用现状的其他制度方案?
二、对现有综合要素区分模式的检视
我国《民法典》第1191条至第1193条,在区分不同用工活动性质的基础上,集中规定了不同类型的用工型侵权制度,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关于用工型侵权制度的微型体系。(5)为行文的简洁和论证的方便,本文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等不同用工活动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统称为用工关系,将这些活动统称为用工活动,这与部分学者仅在“雇佣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用工关系”这一概念存在不同。《民法典》第1191条和第1192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和个人劳务接受者侵权责任,在学理上统称为用人者责任,与定作人侵权制度法律效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用人者责任区分用工活动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对外,用人者对第三人承担无过错替代责任;对内,对于工作人员遭受的损害通常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适用工伤保险制度来救济(6)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页。,对劳务提供者因劳务受到的损害,则适用过错责任和与有过失制度(7)参见张新宝:《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而定作人侵权制度虽然同样区分承揽用工活动的内外部性,但是定作人对内对外承担的侵权责任是一致的,即定作人在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错时,承担相应过错责任(8)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309页。,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9)参见张新宝:《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页。。显然,定作人是用工型侵权责任制度中侵权责任负担最轻的用工主体。
由此,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用工型侵权责任制度的重心就在于对这些用工活动性质的界定,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用工型侵权责任制度的适用,进而会对各方当事人注意义务范围的划分、过错的认定、受害人损害赔偿不能风险的分配以及最终的侵权责任承担范围等均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司法实践和学术界关于用工活动性质区分的具体模式予以梳理和检视,并探究其是否可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一)现行用工活动的定性模式:综合要素区分模式
在“王珍、许明利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10)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3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指出,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合同主体的差异,是否对劳务者的资质、设备、技能提出特殊要求;二是合同的内容不同,承揽合同的目的是通过独立的工作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承揽人对工作完成的进度、时间等享有高度自主性,而在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方对接受劳务方一般具有人身依附性,接受劳务方的管理;三是人身专属性不同,承揽合同中承揽方可以将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而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者以自己的劳务完成劳务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四是报酬的给付方式不同,承揽合同多为一次性结算,而劳务合同多为按月持续性结算。在“桂建华与奎屯法兰斯堡布艺店承揽合同纠纷案”(11)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终137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提出了区分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四个要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二是合同的目的是劳务给付还是一次性的工作成果交付;三是工作场所由谁指定、劳动工具或设备由谁提供、工作时间由谁限定;四是报酬的给付方式。在学理上,诸多学者同样采取为谁的利益、控制力强弱、是否交付工作成果、设备或工具的自有性、工作的灵活性等要素对两者予以区分。(12)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487页;李超:《非典型承揽合同的判定及定作人过失的责任承担》,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4期。由此不难发现,无论是裁判者抑或学者通常采取多要素综合判断的方式来完成此种区分工作(此种区分模式可被概括为“综合要素区分模式”)。当然在对用工活动性质进行具体认定时,裁判者并非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会对前述全部的判断要素进行逐一甄别,可能会存在个案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文所梳理的案例中,与承揽关系相区分的用工关系主要为雇佣关系或者劳务关系,换言之,综合要素区分模式主要适用的场景为承揽与雇佣或者承揽与劳务相区分的情形。此种现状的形成与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用工活动性质的界定存在直接关联。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用工活动大体上呈现“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的三分格局。如果从谱系化的视角来观察此种三分格局(13)关于系谱化的观点,参见雷磊:《法的渊源理论:视角、性质与任务》,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4期。,不难发现的是处于该谱系两端的用工关系易于界分,因为劳动关系和承揽关系在《劳动合同法》和《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中有专门规定。而处于劳动关系与承揽关系中间地带的“劳务关系”,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其概念外延则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伴随社会生活实践的变迁,承揽活动的形式也在深刻发生变化,例如在定作人支配或者控制的场所进行的承揽活动、定作人为承揽活动提供工具、网络平台经济中的如外卖送餐、同城快递、代驾等也带有鲜明的承揽特征(14)参见王天玉:《超越“劳动二分法”: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等,这都构成对典型意义上承揽关系在程度上或实质上的偏离,定作人也从完全独立于承揽活动的完成,到可以逐步介入甚至可以部分控制承揽活动完成。由此,这些典型形态之外的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势必会存在交叉或者重合的情形,这也可以初步解释为何司法实践中有关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区分的案件类型较为常见。
至于为何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区分的案件也较常见,首先需要对雇佣关系这一法律概念作出界定。具体来说,在我国“独立劳动——从属劳动”二元立法框架下,我国的用人关系(雇佣关系)具体又可细分为受劳动法调整的用人关系类型和受民法调整的用人关系类型,如劳务关系情形。(15)参见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适用》,载《法学》2019年第10期。这就表明,学理上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上位概念或者说统称概念。因此,当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作比较时,究竟是在劳动关系型雇佣关系的意义上进行的比较,还是在劳务关系型雇佣关系的意义上进行的比较,是需要明辨的,毕竟两者存在明显差异,不能简单等同视之。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是指劳动关系型雇佣关系,则其与承揽关系易于区分,而如果属于劳务关系型雇佣关系,则同样会面临区分的困难。质言之,在司法实践中和承揽关系区分困难的雇佣关系主要为劳务关系型雇佣关系。这也进一步限定了对用工活动定性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对承揽和劳务关系的区分问题,需要关注的也是综合要素区分模式对于二者的区分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对综合要素区分模式的评析
首先,综合要素区分模式中,工具由何人提供、工作场所在何处、报酬支付方式、是否存在对特殊技能或资质的特殊要求等,均属于描述性概念要素,并非认定或者区分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必要条件,起到的至多是补强论证的作用。
其次,以是否交付工作成果作为判断要素的论证力同样薄弱。将“交付工作成果”作为界定承揽合同的重要标准,可能与现实不符,因为并非所有的承揽合同都需要交付工作成果(16)参见宁红丽:《〈民法典草案〉“承揽合同”章评析与完善》,载《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 第1期。,而且合同所约定的标的是否仅为劳务抑或包含成果,也常常存在疑问,而且还存在既具有成果关联性,又具有行为关联性的合同。(17)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因此,这一标准对于区分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并非决定性要素,而是仅起辅助说明作用。
再次,是否存在控制关系则是区分这两种用工关系的核心判断要素。但就控制力标准而言,由于控制形式的多样,受雇人和独立承包商(承揽人)之间的划界往往并不明确和清晰。(18)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页。在劳务关系中,用工活动的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两者之间的控制或者支配很松散、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存在隶属关系(1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属于一种弱的控制和从属模式。而在某些类型的非典型的承揽活动中,例如在定作人支配的空间进行的承揽活动,定作人在承揽活动进行现场予以具体指示或者监督时,很难说此时定作人对承揽活动毫无控制力,也很难仅凭控制力标准将其与劳务关系作清晰的界分,毕竟两者的控制强度相似或者仅有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说,独立或者自主处理事务规则与控制规则总是在具体案件中呈现出混合的信号,形成一种混合图像,区分并不容易,没有一个因素或一项证据起支配作用。(20)参见[美]丹·B.多布斯:《侵权法》(下册),马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1页。
一言以蔽之,这种综合判断模式是在传统的大工业劳动者的惯性思维下形成的,反映的是大工业劳动、经营组织程度较高的用工关系的特点,当其适用于大工业劳动者以外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时,其有效性是需要明辨的,尤其是在就业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形下,就会产生相当多边际事例。(21)参见田思路、贾秀芬:《契约劳动的研究——日本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页。而诸如 “是否交付工作成果”“工作时间长短”“工作场所的差异”“报酬支付方式”等区别要素,大多属于对典型承揽关系与劳动关系特征差异的描述,是通过合同特征类比来识别概念的归纳推理模式,并未回答两种合同的本质差异(22)参见唐波涛:《承揽合同的识别》,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4期。,并不构成实质性区分标准要素。至于所谓的“控制力标准”,在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交叉重合的模糊地带,此种区分的意义同样较为有限,可能只是存在程度之别。当然这并非全然否定综合要素区分模式在用工活动定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对典型形态的用工活动仍具适用价值。但是当下面临的困境是在用工关系存在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下,综合要素区分模式存在失灵之处。然而,我国的用工型侵权责任制度的适用又依赖于对用工活动性质的有效界分。这使得本应关注行为人注意义务、过错认定的侵权案件似乎蜕变为一个主要关注合同性质认定的合同法问题,无疑会导致定作人侵权制度适用的“失焦”,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为了消除因用工活动定性困难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综合要素区分模式或许是一种思路,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一方案是在维持现行制度模式下进行的探索,预设了现有的用工型侵权制度的区分与设置是完善的。但如果前述负面效应实际上是由该制度的自身缺陷所致,继续陷入用工活动定性区分的泥淖,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因而有必要转换视角,从制度层面重新去审视导致目前定作人侵权制度司法适用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反思现有的定作人侵权制度是否存在缺陷,并由此探索完善定作人侵权制度的可行方案。
三、从制度层面探寻该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层面对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进行反思,无疑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溯源研究。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是借鉴普通法中的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的产物(23)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第181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309-2310页。,因而有必要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予以审视。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是普通法国家所普遍承认的侵权法制度,美国、英国等国均在其侵权法中确立了该制度。这些制度的模式、内容大体相似,为避免行文重复,现主要就美国侵权法模式进行详细梳理,对英国法模式进行简要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侵权法著作对定作人侵权制度的比较法研究较为薄弱,未对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未注意到该制度的新发展。同时,需要对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与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之间的概念术语对应关系进行简要说明,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中的雇主对应于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中的定作人,独立承包商大体对应的是承揽人(当然普通法中的独立承包商的范围更广,不限于承揽人),独立承包商的雇员大体对应的是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即承揽人通过雇佣或者再承揽招揽的工作人员)。
(一)美国侵权法中的雇用独立承包商责任制度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15章第409节明确了雇用独立承包商责任的一般规定,即除另有规定者,独立承包商的雇主对该承包商及其雇员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给他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不承担责任。美国侵权法在该一般规则之外也确认了大量的例外情形,这些例外情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因为雇主自身存在过失而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第二类为即便雇主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应对因独立承包商侵权造成的损害承担转承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的情形,前者被称为雇主的直接过失责任(direct negligence),后者被称为雇主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non-delegable duty)而产生的转承责任。(24)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 comment a.此外,美国侵权法对受害人的类型作出了区分,专门讨论了在独立承包商的雇员遭受损害时的法律救济问题。
1.直接过失型例外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实体和精神损害责任》(以下简称《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5节、第56节对雇用独立承包商者因直接过失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本侵权法重述所规定的过失原则的特别适用。(25)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 comment a.具体来说,就雇主注意义务的范围而言,其包括:(1)依据《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5节的规定,因雇用独立承包商从事一项会造成实体损害风险活动时,雇主所负有的一般的注意义务;(2)依据《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38节至第44节,雇主所负有的积极性义务(affirmative duties),具体包括基于施加保护他人义务的法律所规定的积极义务、基于导致实体损害风险的先前行为所导致的义务、基于与他人之间特殊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基于控制他人而对该他人的义务等;(3)依据《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6(b)节的规定,行为人将工作委托给独立承包商但仍对该工作的任一部分保留控制时,则对控制部分负有合理注意义务。
而就雇主直接过失的具体类型而言,《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5节并未采取对直接过失的类型进行具体列举的方式,而是借助该重述第3节的规定来认定,即雇主对前述义务未实施合理关注,即被认定存在过失。而《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10节至第415节对直接过失的类型进行了明确列举,具体包括:指示过失、选任过失、未对交付工作中危险进行警示的过失、未行使合理关注去发现土地上危险状况,未消除或者改善那些已知或者经过合理关注应当发现的危险状况、以及未对行为人保留控制工作的任何部分行使合理关注等。同时,根据《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官方说明,这些规定在《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5节所包含的过失原则的一般规定之下,不受限制,仍可适用(26)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 reporters’ note e.。
2.转承责任型例外
自19世纪末以来,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重述,美国侵权法已经摒弃了独立承包商的雇佣者不对独立承包商的过失承担转承责任的规则,相反,均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其施加转承责任。(27)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 reporters’ note a.《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58节至第65节规定了雇主对因承包商侵权行为造成的实体损害承担转承责任的情形。依据该规则,即使雇主自身不存在过失,仍要对因独立承包商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28)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comment a.这些例外规则在美国法中被统称为因雇主违反不可转托义务(non-delegable duty)而承担转承责任的侵权法制度。
这些公认的例外情形大体上可以归类为如下情形:(1)雇主负有执行或控制工作的法定义务,(2)基于合同而承担的特定义务,(3) 拥有或者控制场所的雇主负有为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提供安全工作场所的义务或(4)将工作分配给独立承包商,而雇主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该工作涉及固有的特殊危险或雇主本应预料的危险等。(29)Rosenberg v.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595 N.E.2d 840 (N.Y.1992)此外,由于不存在单一的定义或者确定的标准(30)Kleeman v.Rheingold, 614 N.E.2d 712, 715 (N.Y.1993),不可转托义务的类型和范围并不是固定和封闭的,法院会基于原则性和政策性的理由,在特定领域、情境下承认新类型的不可转托义务。(31)参见[美]爱伦·M.芭波里克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第3版》,许传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页。
当然,转承责任型例外规则并不意味着不可将工作委托给独立承包商,而是表明即便是在雇用独立承包商进行工作时,雇主所负的义务不因此而移转,不会因对独立承包商的选任不存在过失而使得这些义务消灭。(32)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comment b.其背后的制度考虑在于独立承包商无力赔偿的潜在可能性(the potential for insolvent contractors),可能无法保障受害人获得足额赔偿,而且无力赔偿的承包商可能也没有行使合理注意义务的足够激励。(33)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comment c.而不可转托义务的引入将有助于提升工作的安全性和质量水准,激励雇主不去选任经济上不能担责的承包商(a financially irresponsible subcontractor),督促承包商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34)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 The Non-Delegable Duty--Some Clarifications, Some Questions,29(2)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500,513-514(2017).
3.雇主对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损害的侵权责任
虽然《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条文中并未对独立承包商的雇员遭受损害时,雇主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该重述的官方评注以及判例法中有对该问题的专门讨论。
首先,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主流的观点是雇主不对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承担转承责任,这一观点也为《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所采纳。雇主之所以不对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承担转承责任,主要是因为美国法中的工人赔偿制度的存在,该制度削弱了借助转承责任改善安全或增加独立承包商的雇员获得伤害赔偿的必要性,而且由于承包商的安全记录会直接影响工人赔偿保险费的缴纳,这更激励承包商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35)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7,comment d.相反,如果扩张转承责任的适用,则可能会削弱工人赔偿模式的威慑效应和风险分担功能。(36)Zueck v.Oppenheimer Gateway Properties, Inc., 809 S.W.2d 384, 387-388 (Mo.1991).
其次,关于是否可基于直接过失制度要求雇主对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承担侵权责任,在美国判例法中并未形成共识,也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因而,《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14章对此并未作出一般规定,而是选择留给司法裁判去进一步发展。(37)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5,reporters ’note h.支持适用的法院认为,如果受害方能够举证证明雇主的过失与损害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则允许受害人基于直接过失侵权要求雇主承担侵权责任,尤其是在雇主对承揽工作保留部分控制而负有注意义务的情形下。(38)Madler v.McKenzie County, 467 N.W.2d 709, 711 (N.D.1991).而反对适用的理由则主要在于,受伤的雇员经由工人赔偿制度可以获得赔偿,直接过失制度并无存在必要,而且这也不会提高对雇主的威慑,因为雇主通过向独立承包商支付报酬,已经部分分担了赔付的成本和与之相关的保险费用,如果允许此种情形下由雇主承担侵权责任,对雇主而言并不公平。(39)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5,comment h.而且即便不能通过直接过失制度要求雇主承担责任,根据美国工人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如果雇用独立承包商者满足了“法定雇主”的构成要件,例如为独立承包商的雇员购买了工人赔偿保险、行为人雇用承包商从事 “属于该雇主贸易或业务的一部分或进程”的工作,并在其控制的房舍内或房舍周围进行等,则会被认定为“法定雇主”,通过直接适用工人赔偿制度来赔偿受害人。(40)Restat 3d of the Law, 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 55,comment h.
通过前述梳理不难发现美国侵权法中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具有如下特点:雇主所负担的注意义务的来源具有多样性,雇主过失以及侵权责任的认定具有层次性,注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作等。具体来说,首先,判断雇主是否尽到因创设给他人造成损害风险而负有一般的注意义务,如果没有创设此种风险,则需要判断雇主是否尽到了积极义务。雇主未尽到前述义务和合理关注,即被认为存在直接过失。其次判断应否基于不可转托义务,要求雇主对因独立承包商侵权造成的损害承担转承责任。对于独立承包商的雇员所遭受的损害,应否由雇主承担侵权责任,则需要结合美国“工人赔偿制度”综合作出判断。
最后,需要简要说明的是,英国侵权法中的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就其制度框架而言与美国法大体相似,均在雇主通常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创设了一系列的例外情形,既包括雇主存在直接过失的情形(41)Edwin Peel & James Goudkamp ,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 ,Thomson Reuters ,2014,21-043.,也包括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情形(42)Edwin Peel & James Goudkamp ,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 ,Thomson Reuters ,2014,21-044.。不过就不可转托义务的范围而言,基于不同的法政策考量,不可转托义务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就雇主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所承担的侵权责任而言,美国法使用的是转承责任的概念,而英国法则认为其不属于转承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转承责任”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但是就规则内容、具体适用而言并无实质差异。
(二)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与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的比较
虽然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继受自普通法中的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但是通过前述的比较法梳理可见,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存在明显的部分继受的情形,而且具有鲜明的自身制度特色。
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同样采取定作人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例外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架构。只在定作人存在定作、指示、选任过错时,才承担相应的过错侵权责任,而这三种过错类型大体上只相当于美国侵权法中直接过失型例外制度中的一些特定类型而已,由此可知在我国的制度模式中,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形较为有限,定作人的注意义务范围、过错认定范围均较为狭窄。至于普通法国家普遍承认的雇主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形,无论是原《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0条还是《民法典》第1193条均未对此作出规定。此种制度的部分继受究竟是便宜之计,还是被无意识遗漏,不得而知,但是缺失这些制度又会对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适用产生何种影响,则是需要关注和评估的。此外,美国侵权法模式对受害人进行主体类型划分,区分为作为独立承包商雇员型受害人和其他受害人,并对前一类型的受害人在结合美国既有的“工人赔偿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不同的救济规则,反观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则欠缺对第三人类型的有意识区分,一体适用《民法典》第1193条的规定,欠缺其他制度的辅助与配合。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法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同样面临雇佣与独立承包关系的区分难题。对于究竟属于被雇佣人还是独立承包商的争论,并无绝对判断规则,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至于主要的控制力判断标准具体为何,则存在个案认定的差异。(43)Raymond A Nowak, Th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Rule and Its Exceptions in Iowa,24(3) Drake Law Review 654,656-657,(1975).而且法院也承认在工作不同部分或者不同阶段的控制权程度会存在差异化,可能导致潜在的双重性质或者关系,有的会被认定为雇佣关系,有的会被认定为独立承包商关系。(44)Cowles v.J.C.Mardis Co.192 Iowa 890, 181 N.W.872 (1921).而且也有学者坦言,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用工形态将发生深刻变迁,这种二元区别将更加困难。(45)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 The Non-Delegable Duty--Some Clarifications, Some Questions,29(2)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500,501(2017).虽然同样面临法律关系区分与认定的难题,但是由于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例外规则的丰富性、层次性,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而产生的转承责任,以及工人赔偿制度的辅助,使得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制度与雇主责任制度的法律适用效果不至过于悬殊,而且即便是被认定存在独立承包商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对于受害人救济的有效实现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只不过实现救济的规范路径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可能不需要借助这两种侵权制度即可实现对特定类型的受害人的有效救济,这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淡化因为用工活动区分困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过比较研究可见,虽然面临相同的用工活动定性难题,存在相同的雇主责任与雇用独立承包商制度的界分,但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却面临严重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这体现在制度内容过于单薄,缺乏相关制度的协作与配合等。单薄的定作人侵权制度自然难以应对因复杂的用工活动实践所带来的挑战,因而,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弥补缺陷,而只是将注意力置于如何完善综合要素区分模式,如何有效界分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这不过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
四、探索完善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
改善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司法适用现状的关键在于解决该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因而有必要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探究可行的完善方案。
(一)不可转托义务型例外:无必要引入
就因违反不可转托义务而承担转承责任的制度而言,我国现有的定作人侵权制度中并不包含该制度,是否有必要将其纳入,值得探究。首先,普通法中关于不可转托的义务并无固定的界定和明晰的判断标准,其外延存在动态性、开放性。其次,目前普通法国家中普遍承认的适用不可转托义务的场景,主要包括高度危险活动,雇主对雇员、医院与病人、学校或者当地教育机关与学生等存在特殊关系的情形。针对这些情形,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已设置专门的章节或者条文予以规制,通过适用侵权责任编相关制度即可应对,另行引入不可转托义务制度似无必要。再次,普通法国家在雇用独立承包商侵权责任中确立不可转托义务型例外制度,其背后的法政策考量主要是为了确保受害人能够获得充分的救济,避免雇主借助独立承包商制度逃避应负的义务,而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并不必需借助不可转托义务制度。此外,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实践中并不包含此种例外情形,缺乏相应的规范基础和司法经验,贸然引入可能会平添法律适用的成本。综合考虑前述因素,目前缺乏将此种例外情形引入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中的必要性。
(二)直接过失型例外:扩大定作人过错的认定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中定作人的注意义务的范围以及过错的认定范围均相对较窄,因而对于是否应扩大定作人注意义务的范围和定作人过错的认定范围,有必要予以探究。
1.裁判实践的现实需要
在“大连湾民丰修理部修理合同再审纠纷案”(4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938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定作人委托民丰修理部(承揽人)修理渔船,承揽人在未经渔港监督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派遣电焊工上船维修,违反规定进行明火作业,应自行承担相应风险。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定作人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错,定作人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再审申请人则认为承揽人的工作人员是在定作人指定的场所进行作业,施工现场完全处于其的实际支配之下,作为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定作人有义务防范因场所或加工物具有的某种危险因素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风险,负有保障他人人身安全的义务,或正确指示承揽人避免、排除危险的义务,但是该抗辩未被采纳。在“尤换生与屈海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47)参见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忻中民终字第8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定作人将墙体拆除工作交付给没有资质的承揽人,对此应按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定作人存在未提供安全措施和未尽告知义务等主张,则未予考虑。在“高庆丽等与济南铭凡包装有限公司等健康权纠纷案”(48)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鲁01民再74号民事裁定书。中,再审法院则以该承揽活动无需资质要求为由,认定二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但同时认为定作人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案涉房屋的结构、材料、问题、隐患等最能掌握相关信息,却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20%的过错责任。在“张海舰、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再审纠纷案”(49)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冀民申5047号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张海舰作为发包人负有为承揽人提供安全工作场所的义务,其在应当知道施工现场上方有高压线并且该高压线距离施工地点的高度对施工人的安全构成严重隐患的情况下,未能采取请求供电公司临时停电的保护措施,为承揽人提供的工作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也未提示施工人员注意触电危险,存在过失,应对受害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
通过对前述案例的梳理可见,目前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对定作人注意义务范围和过错范围认定存在明显分歧。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对定作人的过错类型作了限定性列举,致使部分裁判者在认定定作人过错时,目光只聚焦于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错这三种类型,对于不属于这三种典型过错形态所对应的注意义务的情形,则通常不予审查。 这在承揽活动完全由承揽人掌控,承揽人享有高度独立性时,并无太大问题,因为承揽人对承揽工作的方式和手段享有控制力,在风险和预防措施的了解方面拥有优势,而定作人通常对承揽人控制下的承揽活动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合理关注水平的实际能力(50)参见[美]爱伦·M.芭波里克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第3版》,许传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页。,由定作人承担有限的注意义务是妥当的。但是当处理的是非典型承揽活动中的纠纷时,例如当承揽活动是在定作人控制或者支配的场所进行时,此种制度模式可能会不当窄化了定作人的注意义务范围,甚至导致部分法院机械、僵化适用定作人侵权制度,而无视受害人正当合理的诉求。虽然有法院明确定作人在某些承揽活动中负有告知义务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等义务,但是并未成为主流观点。不过这也表明已经有部分裁判者逐步意识到,将定作人的注意义务范围仅仅局限于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错所对应的范围未必妥当。可以说,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扩张定作人注意义务范围、扩张定作人过错认定范围的现实需要。
2.扩充的注意义务类型及其法理基础
结合对前述裁判案例的梳理以及比较法经验的介绍,有必要在既有的定作人三种过错类型的基础上,承认定作人负有对承揽工作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承揽工作对象中的危险情况进行事前告知或者警示,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义务,并在定作人未尽到该注意义务时,认定其存在过错。换言之,应将此种注意义务类型固定下来,作为认定定作人过错的独立判断要素。
就其正当性而言,首先此种可能致人损害的风险是由定作人开启的,依据侵权法过错责任的一般法理,定作人通常应对此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次,从风险预防的角度看,应由能够以最低成本预防风险的主体来承担侵权责任,定作人对于由自己支配或者控制场所中所潜藏的危险状况,是知悉或者应当知悉的,由其对进入该空间的承揽人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风险提示、危险告知以及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并不会加重定作人的负担,却能有效地防范风险的发生。再次,此种类型的注意义务也存在比较法经验的支持。其不仅为美国侵权法的直接过失型例外模式所囊括,即认为当承揽活动是在定作人的工作场所时,雇用独立承包商者应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确保该场所处于安全状态,在发现危险状况后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予以消除或者就所涉风险进行警告(51)In Greenwell v.Meredith Corp.189 N.W.2d 901 (Iowa 1971).,而且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中亦设有专门条文对此予以规定,如“劳动基准法”第63条第1款、“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6条(52)参见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第63条第1款:“承揽人或再承揽人工作场所,在原事业单位工作场所范围内,或为原事业单位提供者,原事业单位应督促承揽人或再承揽人,对其所雇用劳工之劳动条件应符合用工法令之规定。”“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6条:“事业单位位以其事业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揽时,应于事前告知该承揽人有关其事业工作环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关安全卫生规定应采取之措施。承揽人就其承揽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揽时,承揽人亦应依前项规定告知再承揽人。”,同时依据“劳动基准法”第63条第2款、“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事业单位如未尽到事业单位的安全督促义务、危险情况的事前告知义务、采取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必要措施的义务等,致承揽人或者再承揽人所雇用之劳工发生职业灾害时,应与该承揽人、再承揽人负连带补偿责任。
3.民法规范上的实现路径
在论证完扩充定作人注意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后,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现行法中找寻到妥当的规范适用路径。一种解释路径是扩张解释“定作过错”的内涵,将未履行危险告知义务或者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等视为存在定作过错(53)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87页。,进而适用《民法典》第1193条的规定要求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另外一种解释路径是基于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兜底功能,对于未被定作人过错典型形态所涵盖的过错类型,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作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同样可适用于定作人侵权的情形,《民法典》第1193条可以说只是对定作人特定过错类型的部分列举而非封闭列举,两者之间实为特殊与一般的法律适用关系。
应该说无论适用何种解释方案,都不会影响到最终的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承担。不过第一种解释方案将定作人未对危险情况予以告知、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涵摄到“定作过错”的概念下,这未必符合多数人对“定作人过错”的通常理解,而且在裁判实践中也并未被广泛认可,论证负担可能较重。而第二种解释方案符合民法典体系解释的要求,论证负担相对较轻,而且有助于明晰《民法典》第1193条与第1165条第1款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打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定作人过错范围认定过窄的偏狭认知,避免裁判者机械、僵化认定定作人的过错,大有裨益。而且根据比较法经验,定作人的注意义务范围是丰富的、具有可拓展性,既不限于定作、指示、选任过错这三种类型,也不会止步于本文所明确的定作人的危险告知和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很可能会随着承揽用工活动的发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演进而不断扩充,显然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解释方案更能满足未来法律实践的需要。
(三)区分受害人的类型:完善配套保险制度
就承揽人工作人员遭受损害的情形而言,《民法典》第1193条并未对此作出专门规定。实际上,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未对因承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作出类型区分,没有注意到“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型第三人”(54)关于承揽人工作人员型第三人,具体是指承揽人组织、安排的从事到承揽活动的工作人员,两者之间可能为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亦可能为承揽关系等,对此不再具体区分。与“陌生人型第三人”存在实质性差异。就“陌生人型第三人”而言,受害人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通常与定作人的承揽活动毫无关联,对其保护涉及对一般公众人身、财产利益的救济,而“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型第三人”的主体范围则具有相对确定性,指的是实际从事承揽活动的劳动者,存在受定作人管理或者控制的可能性,对其保护则关涉对劳动者的安全保障和用工风险的预防。有鉴于此,有必要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第三人,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予以救济。
在美国侵权法中,对于独立承包商雇员遭受的损害主要是依靠“工人赔偿法”来解决。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中,事业单位以其事业招人承揽,如有再承揽,承揽人或者中间承揽人,就各该承揽部分所使用的劳工,均应与最后承揽人连带承担雇主应负职业灾害补偿责任。其制度目的在于在职业灾害发生时,使得劳工或其家属多一层补偿保障,避免因转包或者再转包后的雇主无力补偿而失去保障(55)参见林丰宾:《劳动基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87-288页。,当然而此种职业灾害连带补偿模式又是建立在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反观我国的司法现状,目前绝大多数有关定作侵权纠纷的案件,受害人多属于“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型第三人”,由于没有其他制度的协作或者分流,此种纠纷主要通过定作人侵权制度来处理,而单纯凭借侵权法来实现受害人救济显然是不敷适用的。可行的制度方案是,对于因承揽活动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型受害人”逐步借助保险制度予以救济,探索符合承揽型用工关系的保险类型,丰富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途径,借助保险制度来分散受害人可能面临的损害赔偿履行不能的风险,逐步改变过分依赖单一侵权制度实现受害人救济的现状,实现相关定作人侵权纠纷案件的分流,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因用工活动定性问题导致的司法困境。
结 语
我国定作人侵权制度在法律适用中所面临的司法困境是由于用工活动的定性困难而导致各方主体陷入对用工活动定性的争夺。该困境固然与用工活动定性问题的复杂性有关,但是通过对比较法经验的梳理和对照,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的定作人侵权制度过于单薄,存在制度缺陷。其主要体现在定作人过错认定范围过窄,没有注意到不同类型受害人的显著差异并进行恰当的类型化区分,缺乏相关的保险制度的辅助,也没有妥当处理和其与用人者责任之间的区分与协调关系等。因而,有必要扩充定作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和过错认定范围,明确当承揽活动是在定作人控制或者支配的空间时,负有对其中的危险情况进行风险提示、告知,以及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义务等。当定作人因违反该注意义务而存在过错时,应当通过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规定,要求定作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虽然扩充定作人的注意义务的范围,增加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形,有助于弥补定作人侵权制度的制度缺陷。但是理想的方案,还是在扩充定作人注意义务范围的基础上,区分受害人的类型,探索和完善相关的保险制度来解决“承揽人的工作人员型受害人”的赔偿问题,通过民法、社会法以及保险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运用多种制度工具,实现对此类用工活动侵权纠纷的综合治理,最终更好实现受害人救济、侵权行为预防、提高用工安全水平等价值目标的协调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