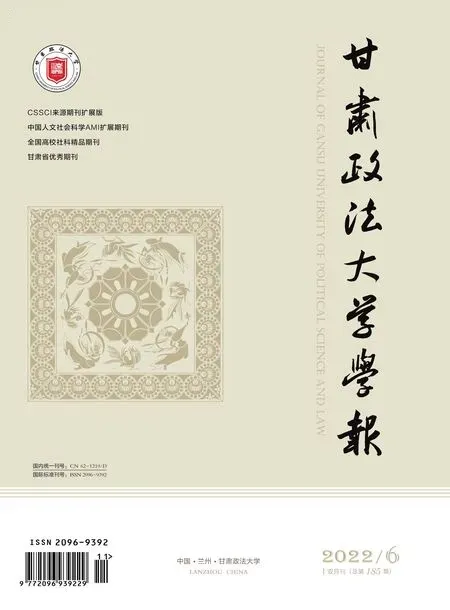“完全赔偿”抑或是“损伤参与度减责”:特殊体质侵权中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李 鼎
一、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时是否应当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
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时,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是否应当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原则,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24号排除了“损伤参与度减责”,但司法实践中“损伤参与度减责”仍被适用。指导性案例24号中,受害人荣某因加害人王某驾车不慎撞到遭受损害。鉴定意见认为,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其中受害人个人体质的因素占25%。加害人认为其不应当承担因受害人个人体质因素所造成的25%损害。对此,法院认为,事故责任认定荣宝英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虽然荣宝英年事已高,但其年老骨质疏松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而加害人应当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认可这一看法,将该案遴选为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摘要中表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结合上文所述特殊体质的评价体系,以及该案法院所表示的“荣宝英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裁判摘要中所指的“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实际上其核心原则是“过失相抵”。也就是说,第一,如果加害人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二,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即使存在特殊体质,也不能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那什么是“损伤参与度减责”呢?损伤参与度来自鉴定意见,指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伤害的贡献程度。“损伤参与度减责”就是指在确定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额时,减去因受害人特殊体质导致的损害额,减轻其赔偿责任。在指导性案例24号出台之前,“损伤参与度减责”的要求普遍被法院支持。(1)参见龚海南:《特殊体质受害人之侵权赔偿刍议》,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8期。但纵观我国制定法,并无“损伤参与度减责”的规定。这一减责事由是在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既有评价体系之外另立的,是对既有评价体系的补充。指导性案例24号否定了这一补充,拒绝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指导性案例24号虽然有效遏制了“损伤参与度减责”的适用,却没能将其消灭。从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部分法官认同指导性案例24号的观点,否定“损伤参与度减责”。这些法官认为,由于缺少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此不能仅因为受害人特殊体质参与损害的发生而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2)如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53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205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民终1562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10民终926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反,部分法官仍然认同“损伤参与度减责”。(3)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7民终1364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再31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03民终2000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5036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4258号民事判决书。
由于“损伤参与度减责”实际上是在现行法评价体系之外另行创设减责事由,为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评价补充了一个新的大前提,因此法官应当为该减责事由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但此时法官的论证理由并不在于“损伤参与度减责”本身合理与否,而聚焦于待决案件是否应当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24号,所以这并不能证明“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正当性。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指导性案例24号针对的是体质问题,而待决案件中涉及的是疾病问题,二者应予以区分,因此不能参照适用;(4)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7民终1364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再31号民事判决书。另一种认为,指导性案例24号涉及的是机动车侵权,而待决案件是医疗侵权,二者应予以区分,因此不能参照适用。(5)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03民终2000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5036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4258号民事判决书。是否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24号只是法律适用的结果,不包含其理由。实际上这种法律上“相似”或者“不相似”都是法官评价的结果,因而并不能提供评价依据。(6)参见孙光宁:《司法实践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以指导性案例24号为分析对象》,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4期。例如,“体质”与“疾病”的二分停留于语言,并没有深入讨论其背后的法律理由。同样属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体质”与“疾病”到底有何不同,如何影响了法律评价,才是应当揭示的重点。
机动车侵权和医疗侵权的区分也与此类似。纵然两种案型在一般情况下适用不同的法律,但在损伤“损伤参与度减责”的问题上,是否仍然保持这种不同?这需要进一步揭示案型不同与“损伤参与度减责”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在过失相抵之外,还需要另立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损伤参与度减责”,则必须限制指导性案例24号的参照适用范围,在该范围之外对这一减责事由予以证成,即“损伤参与度减责”是否具备正当性。出于立法者的权威,文义表述所直接指向的规则,其背后的权衡结果具有“初显性优先”,应当充分予以尊重。(7)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原则的结构》,载雷磊编译:《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在没有任何证明的前提下,应当首先推定指导性案例24号所确立的规则具有“初显性优先”,否认“损伤参与度减责”。如果想要证明“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正当性,就必须证明现行法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评价存在漏洞,需要新的减责大前提予以填补。在没有任何证明的前提下,司法实践突破指导性案例24号的做法就值得反思。那么,既有理论是否具有相关证明呢?
二、既有研究无法证明“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正当性
(一)“损伤参与度减责”的规范语境
所谓特殊体质,就是某人具有的不同于常人的体质。在侵权法上,只有当受害人不同于常人的生理或心理状况(即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共同造成了生命权、健康权等被侵害或在损害发生后扩大了损害后果,侵权法才需要对之做出评价。(8)参见程啸:《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 24 号指导案例评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可见,受害人具备特殊体质本身只是一个生活事实,是客观存在,并不一定发生法律意义。什么时候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可以被视为“与侵权行为结合”,结合之后如何进行评价,才是法律关注的重点。以不同规范涵摄受害人特殊体质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加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少赔偿责任,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法律规范。“损伤参与度减责”只是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众多规范之一。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在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时“损伤参与度减责”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才能更清晰地揭示其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逻辑关联。
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前提是认定特殊体质存在,但实际上这两个环节并不能完全区分。生活事实的性质决定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认定应当结合具体的规范。存在特殊体质,主要是相对于“一般体质”“正常体质”进行的修辞性描述。受害人具备特殊体质只是一个待涵摄的事实,并不必然对应某种法律后果。单是考察受害人所具有的疾病,进而与“正常体质”进行比较,不能提供有效标准是来说明“特殊体质”的。(9)这一思路见松居英二「素因減責における公平 素因に対する加害者の認識について」判例タイムズ1109号(2013年)75-82頁;中武由紀「交通損害賠償事件における非器質性精神障害をめぐる問題(1)——因果関係論及び素因減額等」判例タイムズ1377号(2012年)10-28頁参照。切断了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关联,就不能判断何为“正常”,何为“特殊”。在援引不同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的情况下,由于规范目的发生了变化,“特殊体质”的判断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在《民法典》的框架内,受害人特殊体质可以在过错、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和过失相抵四个规范下进行评价。(10)这一体系已经有学者提出,参见程啸:《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 24 号指导案例评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受害人特殊体质与过错判断
受害人特殊体质可能会影响到加害人过错的判断。如果加害人明知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仍然从事侵权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当然存在故意。过失的判断取决于是否存在注意义务违反。注意义务应当结合具体个案情形中理性人的能力和知识进行判断。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个案情形的一部分,可能会影响注意义务的判断。存在特殊体质的事实会影响到行为人是否应当对受害人承担更为严苛的保护义务。或许由于行为人存在先行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也可能是行为人获知了有关特殊体质的信息,能够及时避免损害,受害人特殊体质可能施加给行为人额外的注意义务。这就会提高其注意义务标准。相反,如果行为人并不对存在特殊体质的受害人承担保护义务,受害人特殊体质不会提高其注意义务标准,行为人只承担针对一般社会公众的保护义务,注意义务标准不能被提高。
例如,受害人在清洁工作过程中摔倒受伤,送至医院后突发肺栓塞和脑出血,持续昏迷,家属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意见,持续昏迷的损害后果是固定手术治疗后出现肺栓塞,因肺梗塞行溶栓治疗并发脑出血,继而出现昏迷导致。法院认为,目前术后出现并发症与患者特殊体质有关,是目前医疗水平下难以避免的。因此,医院不存在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1)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628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医院不存在过错,是因为医院只需要提供一般符合医疗标准的服务。并非所有人在固定手术治疗后都会出现肺栓塞,并在肺栓塞治疗过程中并发脑出血。因此,患者所存在的特殊体质不能提高医院的注意义务标准。
2.受害人特殊体质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判断
出于自己责任的要求,只有因加害人行为产生的损害才能归于加害人。如果损害由受害人特殊体质产生,并非产生于加害人的侵害行为,就没有事实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即使构成事实因果关系,还会通过“相当因果关系”与“规范保护范围”来限缩事实因果关系,控制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如果没有上述法律因果关系,加害人也不需要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特殊体质既可能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存在影响,也会对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存在影响。(12)See Sarah Green, Causation in negligence, Hart publishing Ltd, 2015, p.33-36.
例如,高中生王某自身存在特殊的精神状况。后因难以教育,被学校转至“思想道德提高班”进行严格的道德教育。随后,王某于第二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监护人认为是学校错误教育所致。法院认为,致病原因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复杂认证过程。综合王益虎患病前性格、家庭教育、在校表现、思想道德提高班教学方式,以及王益虎短暂进班学习时间、学校教学管理行为以及原告所提供的全部证据等,均难以确定王益虎患病系被告办思想道德提高班所致,所以,否认了侵权责任。(13)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6民终3393号民事判决书。这就通过受害人个人的特殊精神状况(特殊体质),否认了事实因果关系,进而认定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3.受害人特殊体质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自然世界的因果关系是无限延伸的。加害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必然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但法律不可能让加害人承担无限度责任。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前者目的在于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后者目的在于侵权责任成立。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同样涉及“相当性”与“规范保护范围”两个侧面。如果认为某种类型的损害是受害人特殊体质的结果,就可以否认其与加害行为之间的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加害人不对此种类型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4)See Sarah Green, Causation in negligence, Hart publishing Ltd, 2015, p.36-38.
例如,身体孱弱的受害人与他人吵架诱发心脏病的案件中,受害人在治疗心脏病时进一步诱发了低蛋白血症、尿路感染、带状疱疹。吵架一般可以诱发心脏病,但很难导致低蛋白血症、尿路感染、带状疱疹。损害后果并非全部由加害行为所致,更多受到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影响,不能要求加害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法院认为,加害人只对诱发心脏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5)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4民终1995号民事判决书。
4.受害人特殊体质与过失相抵
在确定损害范围之后,可以通过过失相抵进一步对损害数额予以调整。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存在过错,就可以据此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首先,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可能会影响受害人过错的认定。如果受害人明知自己存在特殊疾病,体质更为孱弱,出于不真正义务的要求,应当承担保护自己的义务,提高预防损害的注意程度。其次,因过失相抵的适用可以将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由双方当事人分摊。受害人参与了损害的发生与扩大后,由于过失相抵的适用,所有损害被按比例分担。分担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加害人所能造成的一般损害,而且包括了受害人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例如,在8周岁儿童骑自行车与患有骨质疏松正在晨练的受害人相撞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受害人从绿化带拐角处进入直行道时,未注意观察两边来车,存在过错,据此减轻了加害人20%的责任。(16)参见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10民终1786号民事判决书。由于所分担的20%责任针对的是加害人造成的全部损害,受害人特殊体质所造成的损害实际上也被双方分担了。
在这一评价体系下,针对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确定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后,只能通过过失相抵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一规则被称为“蛋壳脑袋规则”,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具化。“损伤参与度减责”在《民法典》中并没有依据,它并不在这一原有法律评价体系内,而是在这一体系外另立了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规范。如果认为这一体系是完美的,那么就不需要对规则进行修正,从而排斥“损伤参与度减责”。因此,指导性案例24号并没有创设新的规则,而是强调了上述既有的评价体系,排斥因特殊体质的存在另行创设减责事由。如果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不能被过失相抵所涵摄,那么就不能减轻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相反,如果能证明在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时“蛋壳脑袋规则”可以被突破,另立减责事由,那就有可能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填补这一减责规范。问题的关键在于,“损伤参与度减责”背后是否存在足够的理由支持。本文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二)学理上无法证明“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正当性
虽然没有使用“损伤参与度减责”的表述,但学理上同样试图突破现行法体系,在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时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加害人无法预见到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让加害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有失公平。由于信息的缺乏,加害人也无力预防损害的发生,因而应当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17)参见孙鹏:《“蛋壳脑袋”规则之反思与解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在加害人只具有轻微过错时应当因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存在减轻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此时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压倒了加害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18)参见徐银波:《侵害特殊体质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谈起》,载《法学》2017年第6期。另有学者认为,如果受害者特殊体质对损害结果的贡献具有相当性,应当承认“原因力减责”,通过类推适用过失相抵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19)参见郑永宽:《医疗损害赔偿中原因力减责的法理及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也有学者认为,特殊体质是否能够减责并无确定规则,应当根据动态系统论予以确定。(20)较为典型的可参见王磊:《特殊体质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审视与方法更迭》,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徐洁、李遵礼《个人特殊体质介入侵权责任影响的类型化分析——基于最高法院 24 号指导案例适用情况的考察》,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江秋伟:《特殊体质受害人的权利保障之司法证成——以指导案例24号为对象》,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这些学说本质上都是在过失相抵之外因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存在另行创立一个减责事由,虽然没有采用“损伤参与度减责”的表述,但实质上一脉相承。不过,这些理由均不足以在现行制定法体系外另行建立大前提,创设新的减责事由。本文将逐一论述。
首先,最常见的理由是因受害人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超出了加害人的可预见性。该观点认为,从自己责任出发,加害人应当只对自己能够预见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要求加害人对不具备可预见性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应当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21)参见孙鹏:《“蛋壳脑袋”规则之反思与解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实际上这一观点来自对可预见性规则的误解。可预见性规则的标准有很多。从预见的状态来看,可以是行为人现实的预见,也可以是应然的预见;从预见的内容来看,可以是对损害类型的预见,也可以是对损害数额的预见。(22)参见徐建刚:《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下的统一损害赔偿》,载《政法论坛》2019第4期;海尔姆特·库奇奥主编:《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比较法的视角》(第二卷),张家勇、昝强龙、周奥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48页。采取不同的标准,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这种观点认为加害人不能预见受害人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实际上采用了加害人事实上的可预见性作为标准。
但可预见性主要是指规范层面上的可预见性。重要的不是行为人事实上预见了什么,而是规范要求一个理性人应当预见什么。因此,可预见性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融入了原则、政策和价值判断的规范问题。(23)See Leon Green, Foreseeability in Negligence Law, 61 Colum.Law.Review.1401 (1961).可预见性规则只要求加害人预见到损害的类型,而不包括其具体数额。重要的是因受害人特殊体质所造成的损害类型是否能够被理性人所预见,进而以此判断加害人的责任范围。如果能够预见,则加害人就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不能,则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不应当获得相关类型的损害赔偿。(24)See D.E.Buckner, Comment Note.—Foreseeability as an element of negligence and proximate cause, 100American Law Reports.2d 942 (1965).这一判断与加害人事实上能否预见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即使加害人事实上不能预见到受害人特殊体质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减轻其赔偿责任。
其次,通过“原因力减责”也不能证成“损伤参与度减责”。“原因力减责”实际上是“损伤参与度减责”的学理表述,扎根于比较法上的“部分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如果加害人行为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了不可分的损害后果,只是造成损害的众多原因之一,那么加害人对全部损害结果只具有“部分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既然受害人特殊体质介入了损害的发生或扩大,那么加害人就不应当对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贡献的原因力承担赔偿责任。(25)小賀野晶一「割合的解決の定着(3)割合的因果関係論——議論の沿革と判例における割合的判断の定着」判例タイムズ847号(1994年)59-64頁参照;加藤新太郎「因果関係の割合的認定(交通損害賠償の諸問題17)」判例タイムズ633号(1987年)14頁参照;孙鹏:《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侵权责任之影响》,载《法学》2012年第12期。
然这一观点并不合理。从造成损害的原因来看,永远是多个原因共同存在的。只不过大部分原因归于“背景环境”,从而突出了加害人“行为”在因果链中的作用。除了加害人的行为之外,受害人的行为、自然力、第三人行为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损害的发生有所贡献。这些贡献是否都应当被识别并据此减轻加害人责任呢?如果需要限制原因的种类,哪些原因需要考量,哪些原因不需要考量,为什么受害人特殊体质就一定可以作为一个减责原因呢?(26)窪田充見「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原因競合の問題——寄与度減責論の批判的検討」判例タイムズ668号(1988年)22-33頁参照。
此处预设了一个前提: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应当由受害人自身承担,不得转嫁给加害人。(27)張韻琪「過失相殺の原理と構造に関する学説史的考察-現代的課題への対応のために」有斐閣(2007)法学協会雑誌134巻11号2281-2366頁参照。但这种预设与法律评价体系是存在冲突的。在评价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已经将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纳入法律的政策判断中了。经过这一阶段检测,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已经被转移到加害人处,不再由其自身承担。(28)See Sarah Green, Causation in negligence, Hart publishing Ltd, 2015, p.40.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不构成过失相抵,那么就不再对特殊体质承担风险。此时要求以“部分因果关系”的方式再次衡量受害人特殊体质,实际上是进行了二次衡量,这对受害人并不公平。
最后,是否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有学者转而求向方法论的证成。通过素因(特殊体质)重大性、参与度、违法性和有责性等多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动态系统论”,进而放弃作为一般规则的建构,诉诸在个案当中寻求减责与否的妥当性。(29)较为典型的可参见王磊:《特殊体质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审视与方法更迭》,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徐洁、李遵礼:《个人特殊体质介入侵权责任影响的类型化分析——基于最高法院 24 号指导案例适用情况的考察》,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江秋伟:《特殊体质受害人的权利保障之司法证成——以指导案例24号为对象》,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该理论以法学方法论特别是法律论证学作为依托(30)参见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其实却是最不符合法学方法论精神的。法学方法论的目的是弥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空隙,在尊重规范效力的基础上尽量实现个案正义。(31)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如果想要运用法学方法论软化规则甚至改变规则,只有法官通过充分的说理论证,澄清反对规则适用的理由以“击败”规则适用背后的理由。即便是通过法律论证,也必然是在法律的规则体系之下予以实现。没有形式依据的支撑,不能提出有效的法律论证。(32)参见[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103页。“融贯性”检测标准就是最好的证明。“融贯性”要求法官作出的法律决定必须是从一个高度融贯的前提集中推理而出的。(33)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策尼克:《论法律与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3页。也就是说,法官作出实质性判断后,必须在形式上最大程度符合法律体系。而将“动态系统论”运用到特殊体质的法律问题上违背了这一假设。如前文所述,现行法评价体系由“责任构成”“责任范围”和“过失相抵”组成,本身有稳定的弹性规则和教义学支撑。以“动态系统论”消解这些规则只是解放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失去了法律基本的稳定性。引入“动态系统论”最早针对的是损害赔偿的责任基础,是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过错、危险范围)(34)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并无明确的判断标准,就法官行使裁量权具有立法者明确的授权。此时,在空洞的形式化标准之下加入了各种要素之间的协动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限缩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今已经存在明确的风险分配规则,而将其用来消融法律规则,其实是实现构成要件的弹性化。(35)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系统论》,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在误用“动态系统论”之后,会进一步产生逻辑悖反。消融规则之后,实际上是无法确定什么是“特殊体质”的。特殊体质的“特殊”之处必然是结合待适用法律规范的结果。可能是过错、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可能是过失相抵。如果没有这些规则,就无从判断特殊体质,进而无法评价其特殊程度。
“动态系统论”唯一的优势就在于解放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解放很难说有效解决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评价问题。事实上,之所以避开“特殊体质减责”与“特殊体质不减责”的规则建构,转而走向方法论,就是因为学者无力将特殊体质减责的应然案型构成要件化,从而寻找到减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特殊体质与减责之间的稳定联系并没有被找到,逻辑关节没有被打通。“动态系统论”退而求其次,将可能影响到案件结果的全部因素都囊括进来,在不明确正当性的前提下依靠法官以个案情势进行裁量。但如果对某一论题进行专业化研究的学者尚且不能发现特殊体质减责的正当性依据,明确其适用范围,又如何能够要求法官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于裁量权行使未必总是按照学者的想象,结果未必总能实现公平,这样做反而会影响形式正义的实现。相比学者,法官唯一的优势在于掌握个案当中更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到底如何影响到“减责”或“不减责”,仍然是不清晰的。
在不能另行证立“损伤参与度减责”的前提下,司法实践和学理都仍然坚持这一尝试,源于法官和学者对现有损害分配规则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直觉,尚未完全被理性所正当化。如果这一直觉能够被理性验证,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则应当承认更广泛的受害人特殊体质减责事由(如“损伤参与度减责”);如果这一直觉无法被理性检验,那么只能是个人的情感价值,不能影响法律适用,应当被法律所修正。本文欲先通过反思完全赔偿原则,寻找这一直觉的来源;然后对这一直觉进行检验,寻找问题的应对路径;最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本土化解释论依据。
三、“损伤参与度减责”存在的客观原因: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困难
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生活事实,只可以被法律规范所涵摄,其本身并不会导致法律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不公平的直觉,必然是某个或某些规范涵摄受害人特殊体质后导致了不公平的裁判结果。问题的症结仍然在规范层面,只是受害人特殊体质案件较为典型,将缺陷充分暴露出来。本文认为,正是因为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使得有关受害人特殊体质案件的裁判产生了公正感上的不适。
(一)“蛋壳脑袋规则”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具化
将问题溯因于完全赔偿原则,主要因为“蛋壳脑袋规则”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具化。完全赔偿原则主要是指,只要归责要件具备,加害人就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大小不受加害人主观可责性的影响。(36)Vgl.Hein Kötz, Gerhand Wagner, Deliktsrecht, 13, Aufl., 2016,S.29.根据完全赔偿原则,加害人要么承担责任,填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要么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法官必须在有和无之间进行抉择。(37)Vgl.MüKoBGB/Oetker, 8.Aufl.2019, BGB § 249 Rn.133-135.只要损害赔偿责任成立,赔偿数额就根据受害方的情况确定。加害人无权要求将损害赔偿责任限缩至侵害健康受害人的程度。(38)Vgl.MüKoBGB/Oetker, 8.Aufl.2019, BGB § 249 Rn.142.通过完全赔偿原则涵摄受害人特殊体质,就产生了“蛋壳脑袋规则”。该规则要求,即使受害人相比一般人更为脆弱,甚至拥有“蛋壳头盖骨”,加害人也要对此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蛋壳脑袋规则”只要求加害人能够预见损害类型,不需要预见损害的具体数额。(39)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Harm (Basic Principles) § 31 TD No 3 (2003)加害人之所以要对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因为他的侵权行为碰巧被存在特殊体质的受害人所承担,源自于自身的“运气不佳”,不能请求减轻损害赔偿责任。
美国普通法上最早确立这一规则的是的Vosburg v.Putney一案。该案中,受害人之前因为雪橇事故而大腿受过伤害。在一年后与其他人发生争执时,加害人击打了其胫骨,造成了受害人终生下肢残疾。法院认为,即便加害人不存在故意,不能完全预见损害的严重性,仍然需要为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40)See Vosburg v.Putney, 50 N.W.403 (Wis.1891).英国法根据Dulieu v.White & Sons一案确立了该规则。在该案中,加害人骑马冲进了一个酒馆,致使怀孕的受害人因惊吓而得病,最终早产。法院表示,如果加害人主张受害人存在薄头盖骨或者脆弱的心脏,本应当受到更轻损害,进而减轻其赔偿责任,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41)See Dulieu v.White & Sons, [1901] 2 K.B.669 at 679 (Eng.).一般而言,攻击他人胫骨并不会造成终身残疾。受害人大腿曾经受伤(特殊体质)也是导致终身残疾的原因。但根据“蛋壳脑袋规则”,恰巧一个大腿曾经受伤的受害人遭受了加害行为,是加害人自身的运气不佳,并不能减轻赔偿责任。同样,惊吓他人并不总是会导致早产。只有惊吓孕妇才会导致早产。但加害行为的对象是一般人还是孕妇,应当归于加害人自身的运气,不影响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因此,“蛋壳脑袋规则”所针对的只是赔偿范围的确定问题,与过错的判断无关。(42)See § 206.Foreseeability required: extent of harm, Dan B.Dobbs, Paul T.Hayden and Ellen M.Bublick, The Law of Torts § 206 (2d ed.).“蛋壳脑袋规则”并不要求加害人必须对存在特殊体质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责任受到过错要件的控制。加害人可能对特殊体质受害人不存在注意义务违反,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蛋壳脑袋规则”不涉及侵权责任构成问题,只涉及损害数额的判断问题。“蛋壳脑袋规则”只是重新强调了完全赔偿原则:在侵权责任构成后,只要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加害人就应当对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43)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Harm (Basic Principles) § 31 TD No 3 (2003).
(二)以完全赔偿原则评价受害人特殊体质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对完全赔偿原则的批评中寻找现行规范存在的问题。对此,学者们指出,由于以自然损害的“差额说”为前提,加害人的责任可能会漫无边际。(44)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完全赔偿原则以补偿功能为价值导向,偏向受害人,这并不能对加害人产生有效的威慑。该原则在发展与适用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例外。(45)参见郑晓剑:《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载《法学》2017年第12期。完全赔偿原则分离了责任要件和责任后果,加害人可能因为轻微过错而承担无法忍受的庞大债务。(46)参见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完全赔偿原则是一种形式体系,不反映背后的实质权衡,不能满足“非定式评价”的需要。(47)参见王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机制》,载《法学》2021年第4期。这些批评通过蛋壳脑袋规则,自然会折射到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评价中,从而成为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潜在理由。(48)参见徐银波:《侵害特殊体质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谈起》,载《法学》2017年第6期;郑永宽:《医疗损害赔偿中原因力减责的法理及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孙鹏:《“蛋壳脑袋”规则之反思与解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王磊:《特殊体质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审视与方法更迭》,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
但这些批评并非都能站得住脚。首先,完全赔偿原则并非单纯的自然损害,而是经过了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过滤。在确定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时,会考量到加害人应然层面上的可预见性。如果造成的损害过于异常,理性的加害人也无法合理预见时,可以通过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否定加害人对部分损害的赔偿责任。(49)Vgl.MüKoBGB/Oetker, 8.Aufl.2019, BGB § 249 Rn.138-140.因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限缩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妨碍完全赔偿责任的实现。“完全赔偿原则”和“蛋壳脑袋规则”只排斥仅因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而再次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所以,通过可预见性判断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是“蛋壳脑袋规则”和“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前提,因此加害人的责任并不会漫无边际。
其次,完全赔偿原则的确以补偿受害人为前提,但并不排斥预防功能。由加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承担侵权行为造成的全部成本,当然会对加害人造成威慑,激励其预防损害的发生。认为完全赔偿原则完全没有预防功能,肯定是错误的。纵观该观点支持者的论述,其所攻击的内容主要指向完全赔偿原则与过错程度的脱钩。(50)参见郑晓剑:《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载《法学》2017年第12期。因为损害赔偿责任的大小与加害人的可责性并不匹配,不能保证预防功能的完全发挥。在受害人受到相同损害的前提下,如果加害人可责性很强,则可能产生威慑不足;如果加害人可责性很弱,则会导致过度威慑。但实际上完全赔偿原则是贯彻侵权法预防功能的必然选择。并非每一次过错行为都会导致损害的发生,过错的存在只是提高了损害发生的概率,但不一定带来损害结果。每一次赔偿责任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没有带来损害的相似过错行为。如果责任范围和过错相适应,就只能评价带来损害的过错行为,而不能评价那些没能带来损害的过错行为,最终或导致预防水平不足。而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就可以避免这一缺陷。可责性较高意味着给受害人施加的风险更高,过错行为带来损害的概率(P)更高;可责性较低意味着给受害人施加的风险更低,过错行为带来损害的概率(P)更低。在损害发生后,加害人对全部损害(L)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是通过损害发生的概率(P)平衡了可责性和损害数额之间的关系。在将损害赔偿总额平摊至每一次侵权行为时,如果损害发生的概率(P)较高,则加害人每次侵权行为承担的成本就高;如果损害发生的概率(P)较低,则加害人每次侵权行为承担的成本就低。完全赔偿原则在总体上平衡了损害的预防成本,赋予加害人以足够的预防激励。(51)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293页;Louis Kaplow & Steven Shavell, Fairness Versus Welfare, 114 Harvord.Law.Review.961, 1333 (2001).只不过由于随机性的存在,如果行为没有积累至一定数量,行为的频率和损害赔偿义务可能并不完全匹配。这种不匹配性可以通过保险来矫正。(52)参见[美]杰里米·沃尔德伦:《片刻疏忽与巨额损失》,载《侵权法的哲学基础》,张金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相反,如果放弃了完全赔偿原则,那么由加害人承担多少责任才能提供足够的威慑呢?这会带来无法解释的难题。(53)参见[美]马丁·斯通:《侵害与受害的意义》,载[美]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编:《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81页。
最后,完全赔偿原则虽然有时会让从事同样行为的加害人承担不同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仍然是公平的。民事赔偿责任以“损害”为构成要件,这一标志要求决定了并非所有加害人的可责行为都会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出现了损害,并认可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之后,加害人才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会产生责任过重的“错觉”,主要是将目光限制在加害人造成损害的一次过错行为上。因此,并非每一次加害人行为都会受到损害赔偿法的评价。很多时候,加害人可以从抽象的危险行为中获得不正当利益,但由于没有产生损害,就没有获得法律评价。而在损害发生之后,加害人所施加于受害人的抽象危险被现实化了。此时虽然应当就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损害赔偿背后并非这一次致害行为,而存在着多次过错行为。通过完全赔偿责任,加害人每次给受害人施加不适当风险的行为都受到了评价,使得双方获得了同等对待。(54)参见[美]杰里米·沃尔德伦:《片刻疏忽与巨额损失》,载《侵权法的哲学基础》,张金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
(三)“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使完全赔偿原则有失公平
唯一站得住的批评就是完全赔偿原则“全有或全无”的刚性思维方式,但这是获得客观化计算方式的必然结果。实现客观化就要求法律适用的规则化,规则的适用必然是“全有或全无”的。(55)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5页。通过这样的刚性设计,法官必须在构成要件的满足与不满足之间选择,进而决定规则的可适用性。这种适用必然是“全赔或不赔”,强迫法官在“有”和“无”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制度设计高度依赖于“有”和“无”的清晰边界,但现实中,这种判断并非总是存在边界,而存在很多困难。(56)作为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的判断困难,参见[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王仰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因果关系的判断困难见下文。事实认定中证据存在“确信”或“不确信”的问题,法律适用中同样也存在“构成”与“不构成”的问题。从概率论的角度能够将这种困难明确地展示出来。在事实认定中,人类不可能完全发掘沉寂在历史中的“真相”,而只能根据现有证据有逻辑地推理。对证据的采信和关联实际上都只是一定的概率,徘徊在绝对有(100%)和绝对无(0%)之间。法官最终选择采信与否,实际上是双方可能性比较的结果。如果概率大于50%,则形成优势证据,认定事实存在;反之则认定事实不存在(这一判断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要求不仅仅是优势证据)。(57)参见陈聪富:《“存活机会丧失”之损害赔偿》,载《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小賀野晶一「割合的解決の定着(3)割合的因果関係論——議論の沿革と判例における割合的判断の定着」判例タイムズ847号(1994年)59-64頁参照。同样,在适用法律时,规则的“适用”和“不适用”各自代表一个前提集,两者互相竞争,最终的适用结果则依赖于互相竞争的规则适用在法官心中的强弱比较。只有支持规则适用的理由大于不适用的理由时,才会选择适用规则。(58)[荷兰]雅普·哈赫:《法律逻辑研究》,谢耘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19页。这无疑是概率论的一种翻版,将证据心证的“确信度”改为了法律适用的“确信度”。
如果判断是绝对随机的,那么在取平均值之后,仍然大致能够形成有效率的社会后果。以因果关系的判断为例,这意味着对于同一项损害,只有被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是相等的,总体上才会达成有效率的结果。例如,如果A和B都从事了同样的行为,造成了同样的损害后果。假设此时法官在判决相当性时存在困难。法官可能判断为“存在相当性”,也可能判断为“不存在相当性”,而且两种结果都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概率为50%。如果A的行为被判断为“存在相当性”,B的行为被判断为“不存在相当性”,则等于两者在行为时都要承担50%的成本,形成均衡。每个加害人在从事相同行为时,都会预见自己将会承担50%的成本。
这一解决方式首先面对的是分配问题。虽然作为整体的加害人获得了足够的威慑,但对各个加害人之间的损害分担是不充分的。在上例中,由于A的行为被判断为“存在相当性”,将会实际上承担100%的损害,而B承担的损害为0。从事了同样的行为,却需要承担完全不同的后果。加害人个人的福利水平没有获得足够的考量。法律后果判断的多样化程度越高,这种加害人之间的分配不公越明显。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将全部加害人看成了一个整体,只处理对整体加害人行为的预防问题。而加害人之间的福利分配并没有被纳入考虑之中。这一分配问题可以通过设置责任保险来缓解,但并非所有的侵权人都能够购买到相应的保险。
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规范意义的赋予,实际上这种概率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以50%的“黄金线”作为判断标准,会导致结构性的“漏网之鱼”。有些行为与损害之间被判断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总会低于50%。虽然它们对结果具有原因力,但在比较时总是存在“劣势”,无法通过“全有或全无”的检验,总是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同样,有些行为与损害的概率总会高于50%,则总是在比较中“处于优势”,虽然与损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达到100%,却总是被认为“存在”。于前者,会导致“威慑不足”;于后者,会导致“威慑过度”。两者都不能达成有效率的结果。综合来看,将“近似有”都判断为有,“近似无”都判断为“无”,也有违“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原则。49%、50%和51%在概率上相差不大,却在法律后果上存在天壤之别。
特殊体质的评价,特别是医疗纠纷当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难题。司法实践中认为医疗纠纷和交通肇事应当区别对待就源自两类案件判断“全有或全无”时难度不同。交通肇事最大的特征在于,交通规则的确定性带来了此类案件法律适用的高度确定性。特别是交通肇事以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事故为主,更简化了判断的难度。所以,不论是过错(包括受害人过错)的判断还是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都是非常清晰的。相反,作为实践理性,医疗行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尊重医生的自主判断。而医疗事故的受害人往往都是自身已经存在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个轻微的医疗事故,只提升了损害发生的微小概率,就导致了病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此时,不论是判断过错还是因果关系,对法官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
最为典型的是因物理侵害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结合,导致严重精神疾病的案件,尤其是非器质性精神障碍。由于医学上难以明确其中的作用机理,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持,完全由法官主观判断“相当”还是“不相当”,“在保护范围”或“不在保护范围”,就会引发上文所述“全有或全无规则”的弊端,产生偏重一方利益的结果。例如,因司机中途急刹车导致受害人头部受伤,进一步发展成为精神障碍。台湾“最高法院”否认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为不存在“相当性”。(59)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241页。但这种裁判结果会挑战一般人的公正直觉。任何精神疾病的产生必然存在受害人的个人原因,可能是遗传因素,也可能是家庭、工作的不当压力。但如果没有加害行为作为诱发因素,是不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因此,完全由受害人自己承担精神疾病的后果是不正当的。(60)J.Stanley McQuade, The Eggshell Skull Rule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Recovery for Mental Harm in the Law of Torts, 24 Campbell L.Rev.1, 1-2 (2001).损害必然是作为诱发因素的加害行为与患者本身生理、精神的特殊状况结合的结果。如果认定加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则会感觉加害人被施加了过重的赔偿责任,仍然有失公平。那么,到底加害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还是不承担赔偿责任呢?这势必是一个难题。
出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希望修正甚至取代完全赔偿原则。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生计酌减和公平酌减修正完全赔偿原则;(61)参见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有学者认为,应当以过错为基准,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确定赔偿范围;(62)参见郑晓剑:《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载《法学》2017年第12期。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动态系统论,确定损害的弹性化机制。(63)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1期;王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机制》,载《法学》2021年第4期。在特殊体质案件中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实际上是只是软化甚至放弃完全赔偿原则思路的延伸。
四、完全赔偿原则的修正方法:三值逻辑
(一)“全有或全无”判断是形式理性的必然选择
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是否可以减责,关键在于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如何进行分配。如果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完全由受害人承担,那么就不能转移给加害人,应当另立减责事由,如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如果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完全由加害人承担,那么就应当由加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减轻。如果只片面追求个案公正,结合个案状况进行划分当然是最合适的,动态系统论就是典型。但这种划分方式与法治思维存在抵牾之处。
在打破血缘和部落的纽带,迈向近代社会之后,由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急剧增多,法律迫切需要处理“双重选择问题”。为了实现稳定、长期的投资,必然需要对他人抱有一定的信任,对陌生合作伙伴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预期。法律承担了这一化繁为简的系统功能,通过规范世界构建了所有行为人的预期。(64)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71-79页。这一任务的完成必然是以稳定的规则建构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法治思维必然是一种“形式思维”,以三段论推理和稳定的大前提建构为基础。(65)参见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因此,法律的运行模式中,以形式理性对法官裁量权的限缩是第一位的,对个案裁判合理性的追求是第二位的。不能仅仅因为个案公正就放弃形式理性,这样就完全打破了规则的抽象性,变成了个案判断。同时,法官不能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的适用者。动辄侵入立法领域进行政策判断,是与司法的功能相违背的。立法的合理性是通过立法程序予以保障的,例如公开征求意见、投票、表决等,但司法裁判没有经历这一过程,容易将法官个人的判断施加给整个社会。(66)See Allan Beever.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Hart publishing.2007.p.18.因此,特殊体质的风险如何分配,应当首先尊重立法者的决定,司法者不能径自根据个案情况衡量决定。批评刚性的完全赔偿原则,进而以弹性化机制进行评价,就溶解了形式化的规则。与上文所述“动态系统论”的缺陷相同,这样的思路实际上违反了法律形式理性的特征。所谓以“权衡模式”达成“非定式评价”(67)参见王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机制》,载《法学》2021年第4期。,实际上是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代替了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只有原则的适用才是“权衡”的,可以调整每个原则的实现比例;而规则的适用必然是“全有或全无”的。(68)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原则的结构》,载《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但原则的适用充满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必然带来法律的不确定性,无法为行为人提供有效的预期。加害人到底可能承担多少责任彻底成为未知数。
完全赔偿原则就是立法者根据多个原则权衡的结果。这既是自由和安全之间的一种协调方式,也是填补和预防功能的有效折衷。这些原则通过立法者的权衡,被具化为了完全赔偿原则这一规则。实质的价值衡量通过完全赔偿原则被形式化了,法官不需要再对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权衡,而可以直接涵摄。法治思维所需要的形式理性就通过这样的普遍化规则而建立起来。
相反,即使废除完全赔偿原则,由司法者进行权衡,也无法改变“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不论是自由和安全之间的权衡关系,还是补偿、预防和惩罚三者之间的权衡关系,都是规则背后的原则。原则想要适用于个案事实,必须具化为规则,否则缺少可以涵摄的大前提。(69)参见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废除完全赔偿原则之后,即使适用原则,法官也必须首先权衡多个原则之间的实现关系,然后将其具化为可以涵摄的大前提。法官最终适用的必然是一个规则,也必然是“全有或全无”的。就是没有完全赔偿原则,也必须有其他具备一般性的规则予以代替。废除完全赔偿原则并不会改变“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之所以此时能够兼顾个案情势,并不是因为“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被突破了,而是因为法官能够根据个案状况自行创造用于裁判的大前提,但这种裁量权的行使是存在问题的。法官考量的内容必须能够超出个案,在裁判理由中获得一般的正当性。如果不能超越个案,具化的规则就完全是任意的,违反了平等原则,没有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70)参见[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因此,完全赔偿原则仍然应当坚持。“全有全无”判断的困难并不是废止完全赔偿原则的理由,而是形式理性的必然代价。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可以通过修正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创设例外规则的方式予以实现。在特殊体质案件中,这种“全有全无”判断的困难虽然被更为清晰地揭示出来,但这种判断困难只能通过制定法体系予以修正,不能转而消解完全赔偿原则。
最后,完全赔偿原则实际上维护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抽象平等。从制定法的风险分配来看,主要分为两次风险转移。首先,根据“受害人自担风险”原理,受害人应当自己承受所发生的不幸。如果不存在任何风险转移事由,不能将损害转移给他人,由受害人独自承担特殊体质造成损害的风险。其次,根据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判断,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可以发生转移。如果经过了因果关系、过错等检测,侵权责任成立,则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风险就转由加害人承担。(71)See Sarah Green, Causation in negligence, Hart publishing Ltd, oxford publishing Ltd, 2015, P.33-36.最后,制定法还为损害赔偿额的调整提供了工具。通过过失相抵,能够将已经转移给加害人的风险再转回受害人。此时,受害人仍需部分承担特殊体质的风险。(72)窪田充見「被害者の素因と寄与度概念の検討——不法行為法上の損害賠償額決定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判例タイムズ558号(1985年)臨時増刊37-65頁参照。通过制定法规定的两次风险转移,特殊体质风险能够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有效分配。每一次风险转移都是确定的法律规则,都是“全有或全无”的。完全赔偿原则是第一次风险转移,将损害由受害人转移至加害人处的法律后果。在这一判断之前,确定加害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都同样是“全有或全无”的。如果说完全赔偿原则以受害人处的情况为标准,有利于受害人,那么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判断以加害人处的情况为标准,则有利于加害人。两个“全有或全无”的规则结合,正好维持了足够的平衡。
如果弹性化机制只适用于损害赔偿范围,并不包含责任成立,也不能减少“全有或全无”适用的弊端。作为完全赔偿原则前提的过错、因果关系判断仍然是“全有或全无”的。如果在侵权责任成立时采用“全有或全无”判断,却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采用弹性化机制,则使得加害人获得了优于受害人的地位,有碍于平等原则的实现。除此之外,风险第二次转移的判断还可以进一步修正完全赔偿原则。通过过失相抵,能够将部分损失转回给受害人,由此完全赔偿原则还可以获得修正。因此,仍然应当坚持以完全赔偿原则评价特殊体质案件。
(二)通过“三值逻辑”可以软化“全有或全无”判断
即使继续坚持完全赔偿原则,也不能对其弊端置之不理。那么,应当如何在维持形式理性的前提下尽量追求个案公正呢?这一弊端的解决方式只有软化“全有或全无”的评价方式。事实上,由于“中间地带”“灰色地带”的普遍存在,以“适用”和“不适用”为纽带的“二值逻辑”开始被“三值逻辑”所取代。(73)参见[德]乌尔里希·鲁格:《法律逻辑》,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在既有评价体系下另立一个例外的折衷规则而实现的。
“三值逻辑”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应当受到制定法的限制。“三值逻辑”的存在方式也可能威胁到形式理性的存在,完全变成“和稀泥”的工具。上文提到的“部分因果关系说”也是“三值逻辑”的表现,但突破了制定法体系。“部分因果关系说”提供了一个调整损害赔偿数额的大前提,从而在认定加害人是否存在损害赔偿责任较为困难时,先确定责任,然后以减责的方式调整赔偿额。(74)橋本佳幸「損害賠償額の割合的調整、原因競合事例を中心に」NBL1056号(2015年)39-46頁参照。但这种方式就缺乏制定法的支撑,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泛滥。
在医疗事故中广泛存在的“损伤参与度减责”就是“三值逻辑”侵犯形式理性的例证。如上文所述,我国医疗纠纷中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往往非常宽松(75)参见满洪杰:《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陷阱及其化解——兼评法释〔2017〕20号第12条》,载《法学》2018年第7期。,同时,大多承认“损伤参与度减责”,(76)郑永宽:《医疗损害赔偿中原因力减责的法理及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这种裁判方式在日本也存在。面对医疗纠纷中过错、因果关系的判断困难,日本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先认定因果关系存在,进而适用“寄予度减责”“类推适用过失相抵”等方式,减轻加害人责任,以谋求利益衡平。(77)中武由紀「交通損害賠償事件における非器質性精神障害をめぐる問題(2)因果関係論及び素因減額等の」判例タイムズ1378号(2021年)14-28頁参照。例如,在昭和63年4月21日的判决中,因为轻微的追尾事故而造成了受害人严重的精神障碍。日本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损害明显超出了一般的程度。考虑到受害人自身精神因素是损害产生的重要原因,应当类推722条过失相抵的规定进行寄予度减责。(78)天野智子「素因減額の考慮要素」判例タイムズ1181号(2005年)72-91頁参照。平成4年6月25日所作判决也与此类似。该案中,受害人在案发前曾在车内开着空调睡觉,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轻微脑部受伤,后因不影响日常生活出院。但在随后的追尾事故中,导致了严重的脑部障碍,发生痴呆、理解力严重下降等问题。日本最高法院同样认定了因果关系存在,然后以“由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平”为由,类推适用722条过失相抵减轻责任。(79)天野智子「素因減額の考慮要素」判例タイムズ1181号(2005年)72-91頁参照。这正是“三值逻辑”适用于“中间地带”的表现。
但这种“三值逻辑”的适用方式脱离了制定法的规则,其合理性有赖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论,因此仍然存在法官将个人判断施加给整个社会的风险。在论证法律结论时,应当进一步区分为形式理由与实质理由。前者指向特殊体质减责的制定法依据,后者指向特殊体质减责的合理性。除了上文对该说的批评外,“部分因果关系”构筑了实质合理性,却没有足够的形式合理性。日本法上运用的“类推适用过失相抵”的确是其适用的形式理由(80)長谷川貞之「被害者の素因と722条2项」法学セミナー通号600号(2004年)24-27頁参照。,却非常牵强。过失相抵的规定本身就是一个概括条款,其行使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概括条款进一步类推,将会使形式要件空洞化,带来滥用裁量权的危险。
事实上,这一作业并非要放弃制定法确立的体系。可以在保留完全赔偿原则的前提下,创设例外规范予以修正。例如,对差额说进行修正就是一种补充完全赔偿原则的方式。作为完全赔偿责任具化的损害计算方式之一,差额说以未发生侵权行为的假设状态和已发生侵权行为的现有状态两者之间求取差值计算损害。该计算方法最为依赖对未发生侵权行为状态的假设。如果待决案件中,这种状态的构想非常清晰,则差额说的适用就不存在困难;如果这种构想非常模糊,那么适用差额说就会遭遇困难。不论是精神损害赔偿、假设因果关系还是使用可能性丧失,并不是法律所意图的填补功能发生了变化,而是差额说遇到了技术困难。此时,不论是“客观损害说”还是“规范损害说”,都是通过补充一个规则,对差额说进行修补,最终实现个案正义。(81)参见徐建刚:《民法典背景下损害概念渊流论》,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2期。此时,完全赔偿原则不会被废止,而是以修正差额说的形态进一步合理地展现出来。
而类似差额说的确定规则,最大的贡献在于为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提供了高度客观化的依据。(82)参见徐建刚:《民法典背景下损害概念渊流论》,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2期。放弃差额说,就等于放弃了确定的、可涵摄的规则。而保留差额说,可以用新的例外规则来修正差额说,弥补差额说的不足。差额说的修正虽然提供了诸多例外,但在不动摇规则确定性的前提下,维护了形式理性。虽然例外的数量增多了,法律体系因此变得复杂,但由于新规则的加入,裁判结果的合理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时,法律提供的仍然是可涵摄的规则,形式理性仍然可以被保证。法官不需要动辄进入权衡领域,进行政策判断。而且,通过裁判经验和学理研究,这些例外可以被进一步发掘,并且逐渐实现规则化。如此,则形式理性和实质正义之间就能获得有效平衡。
五、“三值逻辑”在特殊体质案件裁判中的应用方式
“三值逻辑”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应用于不同情形。但为了避免裁量权泛滥,“三值逻辑”必须与制定法结合,受到制定法秩序的限制,只能在制定法提供的大前提下努力追求个案正义。如果这种追求失败了,个案正义就被法治所牺牲,但仍然应当首先维护法治的稳定性。具体到特殊体质问题中,“三值逻辑”既可以针对第一次风险转移,又可以针对第二次风险转移。既可以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损害计算体现“三值逻辑”,也可以在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阶段,以过失相抵实现“三值逻辑”。本文希望通过这一解释论方式解决特殊体质的评价难题。
(一)通过损害类型化技术限缩责任范围因果关系
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主要是解决加害行为与各个损害项目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法律解决的不再是“有无因果关系”,而是“哪些部分存在因果关系”。这样就可以在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否定部分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从而调整损害赔偿额,达成“中间路线”。上文已经论述过特殊体质对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影响,此不赘述。如果适用完全赔偿时难以抉择“全有或全无”,可以因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减少加害人的赔偿范围,达成“三值逻辑”。但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受制于损害的“类型”,即只能判断某一损害类型是否与加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二)通过对损害计算方式的修正
修正损害的计算方式主要针对差额说。如上文所述,差额说提供了客观化的损害计算方法,但学说上一般允许对其进行部分修正。假设因果关系就是这一修正的典型。所谓假设因果关系,是指由于其他原因的存在,如果没有加害行为,损害仍然会发生。例如,加害人烧毁了一幢房子,随后发生地震。事实证明,即使加害人不烧毁该房子,地震也会损毁该房子。一般认为,即使存在假设因果关系,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仍然存在因果关系,只是应当在损害赔偿责任中对假设因果关系予以考虑。(83)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09页。
如果受害人特殊体质构成假设因果关系,适用差额说就存在评价困难。差额说需要假设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受害人应有的状态。而在假设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此时没有侵权行为,损害仍然会发生,即所谓的“差额”可能为零。除差额说外,尚有“规范损害说”,但其实际上并无固定计算方法,只是意图解放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劳动能力丧失的赔偿来看,以两种原因发生存在时间间隔计算是一种可取的方法。(84)参见程啸:《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 24 号指导案例评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如果受害人存在疾病,其后如何发展、蔓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存在侵权行为,何时可能出现损害结果?这一时间差必然是难以明确的。能够确定的是,具备特殊体质,特别是严重疾病的受害人,的确要比一般人的预期寿命更短,损害未来自行出现的概率更大,完全按照差额说以一般健康人的方式进行计算有失公平。(85)窪田充見「被害者の素因と寄与度概念の検討——不法行為法上の損害賠償額決定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判例タイムズ558号(1985年)臨時増刊37-65頁参照。此时,法官既要诉诸“差额说”,寻求技术性操作的稳定性;又要应对假设因果关系的存在,对裁判结果进行修补。特殊体质问题只是这一普遍问题在特定问题域内的再现。
具体到有关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问题时,所谓“疾病”和“体质”的区分就体现出了假设因果关系在评价时的重要性。即便是比较法上最为青睐“素因减责”(损伤参与度减责)的日本法,也主要将其限缩至受害人特殊体质构成“疾病”的情形。在日本最高法院昭和62年6月27日的判决中,一个脖子较一般人更长的女性在追尾事故中受伤。事故后发生颈椎病,并发视力下降等症状。一审、二审均以“脖子长”为由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最高法院认为脖子长属于个人体质特征,不属于疾病,不能减责。(86)森健二「交通損害賠償における「あるがまま」素因減額を中心に」判例タイムズ1326号(2010年)38-53頁参照。同样,在日本最高法院平成6年4月22日的判决中,受害人本身患有“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在十字路口的追尾事故后,受害人存在颈部活动受限、颈部疼痛和神经障碍。加害人认为受害人特殊体质参与了损害的发生,应当减责;而一二审法院都认为颈椎病是现代常见疾病,不应当减责。日本最高法院认为,由于本案撞击猛烈,交通事故前也没有出现这些严重的症状,最终否定了减责的要求。(87)森健二「交通損害賠償における「あるがまま」素因減額を中心に」判例タイムズ1326号(2010年)38-53頁参照。
“疾病”与“体质”作为生活用语,本身是互相贯通的,难以划分界限。但在规范意义上,其区别在于,不论多么特殊,仅仅作为“体质”存在本身不会给受害人带来损害,最多只是损害发生的诱因。而如果受害人特殊体质构成“疾病”,则即使没有加害行为,损害也仍然会发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不能作为减责的事由。并非“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不属于疾病,而是其不能单独带来全部损害结果,不具有损害赔偿计算的意义。同样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就是针对老年群体“疾病”的认定。针对高龄受害人,年龄越大,对特殊体质的宽容度越高,越难认定为“特殊体质”。(88)北河隆之「素因減責論の新展開」判例タイムズ947号(1997年)64頁参照。这不仅仅是因为高龄受害人的“老年化疾病”本身已经变成了体质的一部分,更是因为这些疾病不会对差额说的计算方法产生影响。在计算损害赔偿时,普通的老年疾病往往以预期寿命的方式被计算过一次了。在平均寿命中就已经蕴含了对老年疾病的考量,不应当再次进行计算。
在构成假设因果关系时,我国司法实践经常适用“损伤参与度减责”来修正差额说。例如,陈某入院时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二尖瓣疾病”,在经过四零四医院治疗后,形成左右脑栓塞。这一损害结果虽然与医院没有使用足够的抗凝药物存在因果关系,但自身疾病发展也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法院经裁判认为医院只承担20%的赔偿责任。(89)参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7民终1617号民事判决书。再如,因车祸导致颈椎病加重的案件中,受害人自身患有的常年颈椎病也可能带来相同的损害结果。车祸本身作为诱发因素,加速了这一过程。法院减轻了加害人90%的赔偿责任。(90)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内民申1870号民事裁定书。再如,受害人本身具有“肛管恶性肿瘤”,经手术治疗后因不当放射性治疗,致使肠道出血。由于“肛管恶性肿瘤”本身就可能导致肠道出血,法院减轻了医院30%的赔偿责任。(91)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1民终5238号民事判决书。
除此之外,差额说可能被定额化的计算方式所取代。此时,对损害计算方式的修正也可能针对定额化的计算方式。例如,我国在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中采用固定标准,通过受害人所在地人均收入的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这样导致了不论受害人死亡前具体情况如何,都按照固定标准予以计算。但如果受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疾病,可能寿命并不能达到20年,按照这样方式计算出的损害赔偿金和实际的损害就会存在较大差距,显然有失公平。为了尽量消除其中不公平的因素,就可以在按照定额化公式计算损害赔偿之后,减去受害人原本具有的损害。例如,在“刷漆案”中,七间房小学给暖器刷漆维护后通风两日继续上课。某就读学生后患有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并且医治无效而死亡,其法定代理人认为是学校使用油漆后晾晒时间过短所致。二审法院更是明确指出:“再生性贫血障碍病因极为复杂,发病机理尚不明确。药物,化学毒物、电离辐射、病毒感染、免疫因素、遗传因素等都存在着造成再生性贫血障碍的可能。……损害后果系多种原因所致”。据此减轻学校70%的赔偿责任。(9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字1928号民事判决书。再如,在受害人住院时就已病危,医治无效死亡的案件中,法院认定医院只承担25%的赔偿责任。(93)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03民终2000号民事判决书。这都是对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修正。
(三)通过扩张适用过失相抵
面对完全赔偿原则“全有或全无”的判断困难,更为彻底的调整工具是过失相抵。过失相抵针对的是“同一损害”,能够在某一损害类型内部进行进一步调整。通过受害人过失的认定可以将受害人特殊体质所造成的损害由双方承担,已如上述,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由于“受害人过错”是不确定概念,其本身并未指明行为义务,所以在判断是否存在受害人过错时,法官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受害人过失”主要是指对损害发生存在的过失,并不是对损害诱因的过失。(94)See Andrew Chiang, Two to Tango: Rethinking A Unilateral Duty of Care, 46 Ohio N.U.L.Rev.83 (2020).但通过对“不真正义务”的扩张,可以囊括对损害介入因素(特殊体质诱因)的存在具有过错的情形,缓解完全赔偿原则“全有或全无”的判断困难,实现“三值逻辑”的适用。作为介入因素的特殊体质部分是可以通过医学治疗予以缓解甚至治愈的。如果受害人本身存在疾病,应当按照医生的建议积极治疗,但讳疾忌医,消极对待导致疾病恶化,最终因侵权行为诱发导致更大损害的,可以适用过失相抵。(95)See Andrew Chiang, Two to Tango: Rethinking A Unilateral Duty of Care, 46 Ohio N.U.L.Rev.83 (2020).例如,在Martinv.Owens-CorningFiberglasCorp(96)Martin v.Owens-Corning Fiberglas Corp., 528 A.2d 947 (Pa.1987).一案中,长期吸烟的原告后因为石棉侵权而患有肺癌。由于其极度不良的吸烟习惯,拒绝了医生的建议,被认定存在过错。这就是对介于因素存在的过错,而不是对损害发生或扩大的过错。我国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在两家争吵诱发其中一人心脏病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刘玉芬患有心肌梗死10年,未下支架,也未按规律服用药物,且其对自身特殊体质没有履行足够的注意义务,而是与姜维家争吵,进而出现情绪激动等症状,导致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据此减轻加害人20%的赔偿责任。(97)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4民终1995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明知自己存在心脏病,却未接受相应的治疗,就是对损害诱因的过失。
但这种调整必须受到“受害人过错”要件的控制。如果认为,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不应当外出行走,甚至不应当活动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过失相抵的“客观化”和“柔软化”(98)窪田充見「被害者の素因と寄与度概念の検討——不法行為法上の損害賠償額決定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判例タイムズ558号(1985年)臨時増刊37-65頁参照。,无异于将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减责事由。如果没有“受害人过错”要件,却仍然认定过失相抵,实际上是上文所提到的“类推适用过失相抵”,本质上是一种“损伤参与度”减责,是不正当的。不论是如何扩张解释“受害人过错”,都不能将特殊体质存在本身认定为过错,或者要求受害人自我隔绝于社会。这完全脱离了“过错”一词本来的规范含义,不利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法律的误用。
结 语
特殊体质的评价难题来自完全赔偿原则“全有或全无”判断的困难。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这种判断困难可以利用现行法中的评价体系予以软化,达到“三值逻辑”。但这一追求是存在限度的。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差额说的修正和过失相抵都存在修正的形式边界,对裁量权存在构成要件的限制。只有在这一限度内实现“三值逻辑”才是可取的。如果将这些工具运用到最大限度都不能获得个案正义,出于对形式理性的尊重,就应当放弃个案正义,仍然遵守现行制度进行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