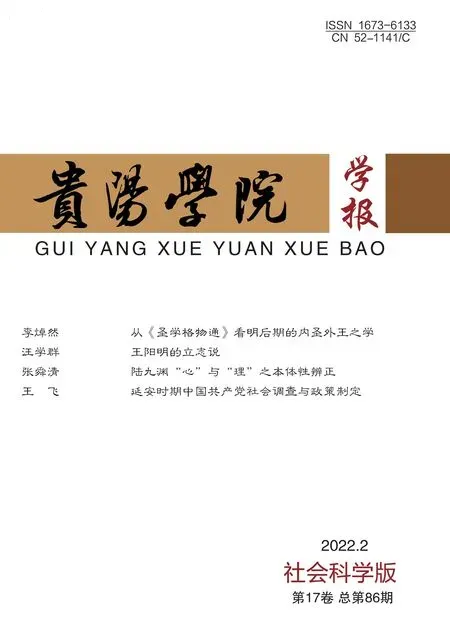戴震的人性论思想及其人文价值
李长绪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戴震人性论思想体系之建构,基本沿袭了宋儒所讨论的人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孟子的思想,以实现理论层面的实质创新。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也将矛头直指现实社会。他一方面阐释出人性是根原于天道的观点,为人欲的先天地位作出一个合理的证明,另一方面批判受到程朱思想影响进而产生的不良社会风气问题,揭示理学“以理杀人”之现状。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戴震人性论思想既有丰富的义理内涵,又有对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
一、戴震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戴震继承张载的思想,建构出一套天道气化生人生物的形而上宇宙图景,使得人性之成立是基于天道之气化、生生,这从形式上呈现为一种一元结构。同时又将人性中的心性解释为名实关系,以凸显心的理性认识能力。以上二者皆是为批判程朱理学作一个形而上的理论依据,指向的是人的伦理价值与学习能力。
(一)“性原于天道”的人性一元论结构
戴震人性论的一元论结构与程朱人性论的二元论结构有着内在的关联性,这点可直接追溯至张载。张载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与“气质”两种,其建构人性理论的思路影响到程朱。程朱用理、气解性,其人性理论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①程颐认为,影响人性善恶的除了“性即理”的天命之性,还有能够产生“才”的气质之性,这样就构成两种相对立且含义不同的性,形成了一种关于人性论的二元论结构。。但是,张载所说的两种性皆是原于“气化”,这为戴震建构自己的人性一元论思想提供了思路,使其将二性相对立的二元结构改为一元结构。
在程朱那里,程颐根据“性即理”的思想,将人的善性与绝对化“天理”相联系,把人的恶性归于气。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认为人之出生是“禀理成性,禀气成形”,“天理”在人心中便保证了人出生后所具备的善性,同时人又受到形气的影响以产生恶,故朱熹将人性直接划分为两种,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在戴震那里,首先否定了程朱对绝对化“天理”的界定,认为理就是分理、条理,而性则是天道之分理的体现,这在逻辑上构成了一种“性原于天道”[1]43的一元论结构。基于此结构,戴震深入分析性与人性的关系,认为: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咸以是为其本。[1]25
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1]37
性作为一种客观性的万物根本,体现为“血气、心知、品物”,而血气心知则专指人性。这样,性与人性之间就构成一种链条式的因果逻辑关系,有性才会有人性。
戴震所谓的阴阳五行被区分为血气、心知、品物,其实是对“性原于天道”的解说。天道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而戴震则用血气、心知、品物来说明天道变化后的具体形态,并在此变化中使人性之血气心知得以成立。因而,戴震的人性一元论结构内含一条从天道延伸到人性的单一脉络。而这种人性便是程朱讲的气质之性,故戴震才认为“人之为人”不能够“舍气禀气质”,这是戴震人性一元论的理论要旨。
在戴震的人性论中,弱化了“天理”在宋明理学中的绝对化地位,把气与人性直接关联在一起,否定了程朱思想中性与道德天理的直接联系,将绝对化的“天理”从人性中剔除,从而为人欲留出地盘。
(二)心与性的名实关系
对于人心与人性二者之关系,最早在孟子人性思想中被系统阐述。孟子将人的恻隐等情感之心,分别与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理性相连接,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性之开端,因而使得人之善性得以成立。这便是孟子对心性关系的阐述。
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2],直接赋予“心”以知觉能力,弥补了孟子心性关系中只讲情感与道德理性,而不讲知觉认识的缺陷。朱熹在讲“理在人心,是之谓性”[3]的同时,亦注重“已发”“未发”之心的意识活动性,这是对“心”知觉认识能力的细致化分析。此种分析直接影响到戴震,使得戴震在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中十分重视人心的理性认识能力。
张载与朱熹实际上是将心、性两者割裂,并赋予两者以实在性。而戴震对心性关系的阐述则是基于人性一元论,将宋明理学中的“性”作虚化处理,弱化“性”的实在性和本体意义性。如“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1]34,“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21,实际就将“性”与“血气心知”二者关联到一起,使得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名实关系。戴震完全消解“性”的道德内涵,将其作名称化的处理,意在强调“性”所具备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指心知的现实性功能。因而,他的心性关系理论最终要落实到心知所具备的理性认识功能上,旨在凸显人的道德理性在现实中的实际价值。
二、对孟子性善思想的发展与叛离
戴震承接孟子的性善思想,揭示出孟子性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道德的二重向度,并以人禽之辨阐释出道德理性在人性中的独特地位,最终达到了对孟子性善思想叛离的程度。
(一)对孟子性善结构的继承
孟子的性善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首先,“性善”体现在人心所具有的感性情感上,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4]259朱熹将孟子之四端解释为“情”,从此角度看,人所具备的善良感性情感是先天植根于人心当中的,故孟子才用孺子将入于井的比喻来说明先天感性情感的存在,从而说明人先天就具有一种本然之心,这是人的道德根源[5]。其次,“性善”体现在四种先天的道德理性上。这些道德理性是植根于人心当中亘古不变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4]80孟子认为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理性的开端,并且用人有四肢的比喻进一步强化论证人先天就具有道德理性。
孟子在逻辑层面上,从人的感性情感出发,进一步推进到人的道德理性,并认为能够生发出感性情感的本然之心又是道德理性的开端,所以孟子的“性善”是一种感性的本然之心与理性的道德之心的结合,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感性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戴震的性善思想在内容上与孟子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结构上却是继承了孟子。他所讲的人性专指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依然具备孟子性善结构中的感性情感和道德理性,而且两者依然是一种统一性的关系。戴震认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1]40,这说明血气心知在人身上体现为欲情知三者,这三者是人性之自然,是一种人自身应有的本然状态,而人的情感与理性就是通过欲情知体现。
从逻辑层面来看,欲情知三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不同的功能。首先,“欲”是“情”和“知”的根本,是第一性的。戴震引用《礼记·乐记》来解释,“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1]2。人性之欲通过“感物”得以产生。而“欲”的功能是通过“感物”而得到声色嗅味,即“给于欲者,声色嗅味也”,“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1]5。这在说明欲的功能作用的同时,也在把人性中的欲和血气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得欲本身转变成了血气对外界事物反应的结果。与此同时,感性的情也在“感物”中得以萌生,即“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故戴震将欲和血气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把情归置于血气之中,使得欲、情与血气关联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戴震又进一步区分了血气与心知的序列关系。他将二者的次序排列为血气在先心知在后,即“有血气,斯有心知”[1]61。这样,在欲、情之后便是心知,其功能作用是能够认识道德伦理,即“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1]37。戴震通过对欲情知三者的深入分析,挖掘出血气和心知不同的功能作用,从而能够清晰地发现人性之血气心知所具备的感性情感和道德理性,同时也能看出两者是统一于人性之中的,这种结构特征与孟子性善结构相同。
(二)对孟子性善思想的完善
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随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畏死矣。……心知之发乎自然如有是。[1]26-27
这说明人与禽兽之共性在于都有怀生畏死、趋利避害的本性,皆为血气使然。禽兽能够做到“知母”“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皆是“发乎自然”之心知的作用。
孟子以人禽之辨论证性善,戴震也是沿袭着这一思路将人与禽兽进行比较。一方面用来说明血气心知为人与禽兽之共有,另一方面则用来论证何为孟子之性善。其对于后者的研究实际上是弥补了孟子性善思想中的一部分空缺,所以这也是对孟子性善思想的完善。
孟子虽然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4]191,但没有明确说明“几希”于何处。其后,以“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4]255的疑问,驳告子“生之谓性”,此处他将人性与牛性进行比较,但并没有讲二者之间的差异。在随后的篇幅中,孟子只是单纯地对有关“性善”的观点进行论述,他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4]259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知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4]261
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4]263
以上所讲的都是“昆南”。昆曲北曲(以下简称“昆北”)虽然没有入声,但平上去的基本音势与“昆南”一样,字腔和过腔的由来也与“昆南”一样。
孟子以“人”“心”“仁义礼智”“理”等词语论性善,这是其性善思想的核心,旨在点明人先天具备的道德理性。同时,孟子认为“梏之反覆”会导致“夜气”不能存留,进而便会近于禽兽,此处表明人对先天道德理性的消磨必然会近于禽兽,甚至最终会等同于禽兽。也是此处才说明人的道德理性是人性与牛性之差异所在,同时也说明人所具备的道德理性是人与禽兽差异的“几希”。
人与禽兽有不同,但必然也有相同之处,这一点孟子没有讲出来,而戴震则弥补了这一空缺。在前文中,戴震已说明了人禽皆有血气心知与一系列的本能反应,这是性之自然。同时,又提出禽兽先天存在着理性认识方面的缺陷,其知觉认识达不到人性中心知的认识水平,或者说禽兽不能够知五伦关系、道德伦理。故,戴震说“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1]34。一般意义上的性只是对动植物的说明,以指出人与动物皆有血气心知,而“性善”则是专指人性,指人性当中蕴含着道德理性,此道德理性是要通过心知来体现,而将动物的心知与人的心知相比较来看,动物的心知只是功能不完整的知觉而已。
(三)对孟子性善思想的叛离
戴震的人性论虽以孟子之“性善”二字命名,但二人在有关性善的具体问题上实有不同。甚至戴震对一些问题的阐述已经严重违背了孟子思想的本义,呈现出一种叛离的姿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孟子性善论中,“心”既是恻隐等情感之心,又是仁义礼智的开端。这使得心既包含感性情感,又包含道德理性。而在戴震的人性论中,将感性情感归置于人性中的血气,将道德理性归置于心知。所以,二人的人性论结构相同,但具体内容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孟子是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理性归到了人心当中,使得人先天就具备仁义礼智,从而成为人的道德本质。而戴震则取消了“心”的这种先天道德本质,他所指的“心”则专指“心知”,心知并不具备仁义礼智,只具备理性的认知能力,即后天学习能力,其作用是要求人通过后天学习以获得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
戴震认为,人所具备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有它的认识指向,他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1]18。这心知的认识指向是“懿德”,以此来证明心知追求仁义礼智所具备的原发性。同时,这样的心知便是孟子所谓之“性善”。所以,戴震实际上就将孟子的人性本善改为了人性本知善。尽管是在凸显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但实际上是曲解了孟子的本义,这无疑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叛离。
其次,戴震的这种叛离更明显地体现在对“性善”二字的挑战上。他认为“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直以性善断之”[1]30。在他看来,孟子为应对告子等人的人性观点①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将告子等人的观点归结为三条,即“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便直接提出“性善”二字,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人性立场为“善”,故认为孟子这种用“善”去论证人性的做法十分武断权宜。而后世的强势者反而借助孟子的这一说法去欺压弱者,即“如古今之常语,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1]30。随后,戴震正本清源,认为“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无人性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1]30。从他人性论的论证逻辑来看,用“善”来说明“人性”是没有在讲人性,因为只有当人性之血气心知成立之后,心知才能够发挥其理性认识的作用,“善”才能够成立,所以是不能够用“善”反过来论证“人性”的存在。如果论证的话,反而便证明了“人性”不存在,而导致“见其禽兽”。
从戴震对人性本知善的阐发和对“性善”二字的挑战来看,能够看出戴震本人想要批判程朱理学的基本意图。孟子的性善思想实际上成了戴震手中的挡箭牌,甚至可以说《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是戴震本人借用孟子之名来阐述自己的义理思想,用以揭示出“后儒以理杀人”现象的工具。
三、对先秦儒学内在价值的发展
戴震的这一套义理思想,不仅重新定义了程朱的天理,更重要的是在对人性的研究中,挖掘出了人性当中潜藏的欲望、情感以及对善的追求,并认为这是现实普遍人性之共有。同时,他在理论的创新层面上有意识地避开宋明理学的义理诠释方法,而以考据法直接面向先秦时期的儒家文本,挖掘出其中内含的人文价值,这可视为是对先秦儒家人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提出的“君臣父子”的思想旨在构建一种合理秩序,这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社会。此思想之基础在于拥有每一种身份的人要履行自身所应有的责任,即君要履行君的责任,臣要履行臣的责任,从而使得君臣之间不相互僭越,进而地位得以稳固,社会秩序得以和谐。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6]这指的是君上践行自己应有的责任,而臣民百姓也是用情以应之,这便使得社会稳定。所以,两者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双方权利与责任相对等且合理的情感交流。然而,君上一方可凭借自身的权势地位,违背自身所应有的责任,当对他人构成实质性的灾难时,那么君臣父子的秩序就会被打破,受难的一方就没有必要遵循原有的责任与义务,故孟子才会讲“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42。通过孔孟的观点就能够看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君臣父子”的权责对等关系,是基于人的现实情感所建构起来的一种合理关系,在这种人与人的共情中才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秩序。孔孟所提倡的对等关系思想是指在道德层面君臣、上下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相协调一致,如果君上违背这一点,那么臣下一方便无须遵守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进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反抗。这种思想所体现的是弱势一方存在着合法的反抗意识,其论证基础只是基于现实情感所构建起来的社会道德关系,将社会的价值认定标准设定为人的先天情感,但并没有进一步引向天地自然之维,以深化其哲学内涵。不过,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反抗意识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对强势压制、体现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文思想,这足以说明孔孟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理念,足以证明先秦儒学中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内涵。
在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在作为官方学说的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强势者借用程朱理学之名为自己谋得话语权,站在“理”的高度对弱势者一再发难,弱势者却无权申辩,甚至认为这是理应如此。以史实来看,强势者已经打破了孔孟思想中通过人之情感所构建起来的人人之间权责对等关系,戴震则对弱势者抱着深切同情。他说: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10
戴震人性论的意义之一,是通过性之自然的“欲”推导出人性当中所蕴含的“情”,此处的“情”不单指人本性中的喜怒哀乐,更是指在人伦关系中所产生的共情。在戴震看来,每个人从自己的原始本性出发,将自身当中所蕴含的“情”发挥出来,在与其他人的交互中达到“以情絜情”,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会过分地责难和为难对方,达到“无过情无不及情”“情得其平”,这就是戴震所谓的“依乎天理”。通过这种情感的共鸣所构成的“理”具有人人之间相对等的特点,避免人与人在交互中出现因“情”不到位而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责难。这种思想其实是戴震对当时社会所出现的“后儒以理杀人”现象的批判,他以性之自然的“欲”“情”为基础,来凸显人性当中潜藏的反抗意识,在理论上为受难的弱势一方作辩护。
戴震所讲的人伦关系中的共情,是对孔孟所提倡的对等关系思想的还原。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通过性之自然推导出来的共情,是从自然主义的层面对人的本然之性的进一步引申,将人的本然之情确立为社会价值的普遍认定标准。其效仿孔孟,为弱者之反抗提供理论依据,所以也是对先秦儒家人文思想的一种发展。
在戴震的人性论中,人伦之情是通过血气心知的欲情知建立起来的,使得人伦道德成为了性之自然的延伸与现实体现。同时,戴震多次引用孟子的人之口耳目心与味听色理义相连接的观点,从人之“官器”的角度来说明人的耳目口鼻心对声色嗅味和理义的追求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功用,是性之自然的生发,用此说明人伦道德与人之“官器”的内在联系,即“明理义之悦我心,犹味之悦口,声之悦耳,色之悦目之为性。……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1]5。从具体的人体来看,人之“官器”是指血气心知,其分于天道,为天地自然之运化所成,戴震便用此证明“以情絜情”是性之自然的生发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更有意思的是,身兼考据家与义理家的戴震,在其古音学研究中,同样重视人之先天“官器”。其《声类表》的排布就是遵从人体的先天“官器”,即人体先天发声部位。他根据发声原理,总结出人的先天发声部位由深到浅的次序为:喉、鼻、舌齿、唇[7],认为“以此为次,似几于自然”[8],而其九类二十五部的《声类表》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排布的。
以上便能看出,戴震实际上是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将先秦儒家人文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一步推进,这不仅限于人性中的现实情感,而且进一步把人性之情感推进向天地自然之维,为现实人性中的情感作了形而上的证明,将现实之人性与自然之天性相关联,从而深化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