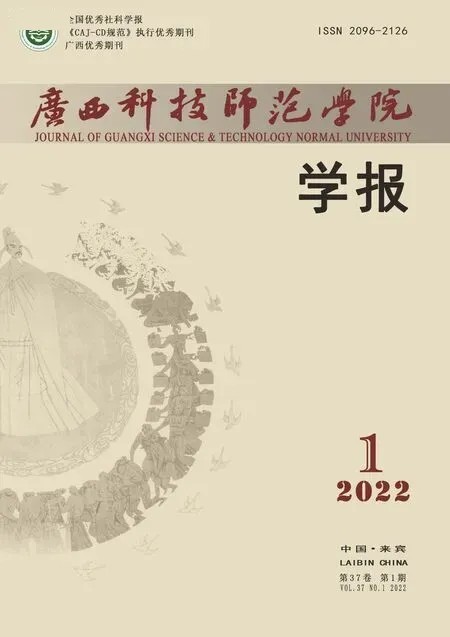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
张 明 月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文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外国文论作为依托的。加之特殊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俄罗斯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便成为一种可能,甚至一度成为主流,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思想更是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审美趣味。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欧美文论蜂拥而入,逐渐在中国文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我国逐渐走向式微。近年来,随着我国文论建设朝着多元化、纵深化的趋势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再次被中国文论界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进行了阐释,涌现出一批全新的成果。例如,王志耕、刘悦笛、田刚健、涂武生等学者就“美是生活”这一传统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然而,想要厘清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本质,首先必须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反思其文化层面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深入研究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所受到的赞誉并非一蹴而就。1902 年,岭南羽衣女士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该文中有三处提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①《东欧女豪杰》一文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为“渣尼斜威忌”或“遮尼舍威忌”。。瞿秋白在1921 年至1922 年旅俄期间撰写了《俄罗斯文学史》,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思想进行了论述。1942 年,周扬发表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专题论文,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成为文艺理论家们批驳论敌的武器。与此同时,国内掀起了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高潮,这种热潮一直延续至20 世纪80 年代。然而,一些学者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批评缺乏整体性的关照,对他的文论思想有一定的误解。“文化大革命”也对国内学者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形成了一定阻碍,甚至一度中断。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探讨逐渐深入,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可以说这段时期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研究的深入期。在1956 年前后的“美学大讨论”中,批评家们高频率地引用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对论敌进行批判。例如,朱光潜认为:“美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1]158但曹景元并不认同朱光潜的观点,为此他对朱光潜的美学观进行了强烈地批判,认为“朱光潜否认现实中有美的说法,全都经不起批判。现实中的美是朱光潜等所抹杀不了的”[1]158。曹景元之所以坚持此说,究其根本是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美的本质”是“‘美是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作出了这样的定义。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是反映了美的本质的,它给予什么是美的问题以唯一正确的解答”[1]160。由此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当然,其文论思想在当时声名鹊起也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它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当时批评家的革命性和激进立场,导致这些学者对其文论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甚至是断章取义,这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僵化。
这一时期,除了“美学大讨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进行了大量的援引,还有学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其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道看作“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其中,以周扬、汝信、朱光潜最为知名。汝信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中明确提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农民革命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是一个坚决的革命家,他是那种为了信仰可以贡献一切的人”[2],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性、社会性的一面被突出强调。在另一篇论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中,汝信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自然美与艺术美”“悲剧的本质”以及“艺术的社会意义、艺术的目的和使命”等方面的论述对黑格尔的观点展开批判,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去批判黑格尔美学的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他的不妥协性、彻底性、党性和理论勇气对我们有着莫大的教益”[3]。由此可见,此时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更多的是站在政治立场上予以肯定的,之后才是实用性。意识形态在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光潜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别林斯基思想的继承者与接班人。想要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思想,首先必须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关系以及他的哲学基础”[4],因为二者在文学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都主张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并对消极的浪漫主义予以批驳;其次需要厘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派美学观点的批判”[4],在这一点上朱光潜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与看法基本一致。我们唯有把握了以上两点才能够充分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思想,即他关于“方法论”“美的定义”“美学的对象”以及“艺术和现实的优劣的问题”等的理论。当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中的功绩与缺点,朱光潜同样予以了充分的讨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朱光潜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上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提出了关于美的三大命题和关于艺术作用的三大命题”,而其缺点就是对于“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艺术与现实,典型与个性,内容与形式这一系列对立面的关系都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的,即过分地强调它们的对立面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的辩证的统一”,“轻视典型化,因而忽视了艺术虽是现实的反映”[4],以及存在对艺术形象思维看法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更为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提供了路径与参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中国昔日的影响力一去不复返,其文论思想遭到连续不断地批判,相关研究也一度中断。“文化大革命”之后,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相关话题再次出现。但这些文章数量并不是很多,理论性也相对较弱,主要是将其作为批驳“四人帮”的辅助性材料。例如,龚翰熊的《“普罗米修斯”的书——兼评“四人帮”为何诬蔑〈怎么办〉》、雷光的《正本清源,还其光辉——驳“四人帮”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诽谤》等均是此类文章。由此看来,无论是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还是汝信、朱光潜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抑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相关探讨,这些论争既有优点亦有不足。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范本,为后人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多元阐释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工作基本完成。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已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那般狂热,在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如从前,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却向着多元化、纵深化的趋势发展。诸多研究成果既有对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成果的承袭,也有对新理论的挖掘与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学术期刊网上,1980 年—2000 年,篇名中包含车尔尼雪夫斯基名字的文章共计47 篇;2001 年—2020 年,篇名中包含车尔尼雪夫斯基名字的文章共计45 篇,其他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改革开放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美是生活”的辩证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与周扬美学之比较、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意蕴及当代价值等。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明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某种单一角度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关注较多的莫过于“美是生活”说,然而每位学者对于“美是生活”说的理解却并未取得一致性的看法。蔡仪和杨恩寰均认为“美是生活”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究竟为何而错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蔡仪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中认为“美是生活”这个定义“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主观决定客观,美感规定美,是由美的认识论倒向美的本体论的错误”[5]。而杨恩寰在《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兼与蔡仪同志商榷》中则认为,“美是生活”这个定义不完善是“由于他缺乏辩证观点,对生活、实践没有科学了解所造成的不完善”[5]。事实上,对于“美是生活”的讨论并不局限于蔡仪与杨恩寰,刘文孝在《“美是生活”: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辩》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把‘美’从神秘的、晦涩的抽象,转化成生动的、明朗的概念,还给‘美’的概念以生机勃勃的本色,使上自莫测高深的哲学家下至目不识丁的匹夫匹妇都能懂得并体验‘美’的内涵”[6],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定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上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错误,只是各位学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导致意见相左。这也表明,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还需对其著作进行全方位研读。
周扬作为国内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介绍者、推行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进入21 世纪,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与周扬美学观点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其中,较为显著的成果要数蔡同庆的系列论文,如《周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之影响研究》系统地梳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周扬的影响以及周扬文艺思想的流变。蔡同军的《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周扬》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周扬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突出地强调了周扬文艺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接受和推行过程中的局限性,可以说是论述翔实,见地深刻。黄金亮的硕士论文《一脉相承与变异发展——周扬早期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比较》就艺术与现实关系进行了论述,其论述的深度较蔡同庆而言稍显逊色。总体而言,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周扬的思想比较研究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并未有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更多的史料与成果有待进一步发掘。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向,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也愈加多样化,学者们更注重多视角、跨学科对其文论进行解读,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的解读、在我国传播影响的研究等层出不穷。虽然大部分学者依旧论及“美是生活”,但研究视角已经发生转变,“美是生活”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引子,学者们更侧重剖析其当代价值与启示。刘悦笛在《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主流线索》中以“美是生活”为切入点,提出“21 世纪‘生活美学’的整体转向”的课题,倡导“要超出实践美学及其各种后学的思维范式,再次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7]。而所谓“21 世纪‘生活美学’的整体转向”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可能,这将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也需要国内文学理论界长期的努力与坚持。田刚健在《“美是生活”抑或“美是生命”: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意蕴及当代价值再探》中对“美是生活”的译介历程与理论影响作了系统的探讨,进而指出“美是生命”的观点,“重申了其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资源的基本观点和参与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地位”[8]。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再到“美是生命”,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不仅显示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生命性,更彰显出当今中国学界的创新能力与理论阐释的多元趋势。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国内文学理论界的权威不断受到质疑,其“绝对”正确性受到了挑战,而对其辩证的考量成为新的趋势。进入21 世纪,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再度发生转向,各位学者主要通过文本细读、比较研究、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其理论中的诸多问题作了全新的阐释,这使我们不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更对其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明晰的认识。
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文化思考
回顾过去70 余年中国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接受与阐释,国内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确实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既有贡献也有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其理论为中国文论界的走向找到了外在的参照和支撑;“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由原来的被推崇的典型变成了遭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学者们通过撰写文章对其予以正名,重新评价和定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文论,但创新性不足;进入21 世纪,国内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提出了新的命题,但依旧难以摆脱传统文论的窠臼。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作出过突出贡献。首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参照,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将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他的人生信条贯穿其文论思想始终。他的唯物主义文论是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现实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总结,为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以及为历史的、审美的文论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思想不仅启蒙了中国当代文论,更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外来参照和支撑。其次,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其民主主义文论的特殊性对中国某些极左文论起到了纠偏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坛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周扬倡导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来为中国文坛纠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在文学创作中“写真实”,这恰恰抑制了庸俗的社会学批评的横行。
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而言,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已经明显弱化,这其中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就外部而言,西方多元文论输入的冲击显而易见,各种主义与文论纷纷涌入中国,使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论遭遇冷落的处境。如夏中义所言,中国“短短几年简直压缩了整个西方美学界花一世纪才走完的路程。极度饱和,当然也就无暇分心来顾盼别、车、杜了”[9]。从内部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其自身的不足难以适应中国文论的发展现状。就如韦勒克所说:“他这个人好像几乎没有审美感受力:一位疏浅严峻的思想家,即使谈论文学时也是偏重于眼前的政治问题。”[10]当然,这也给了我们重新考察和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机遇,有助于人们看清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原本面貌,并对我们已接受和理解的片面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作出应有的反思。
进入21 世纪,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再次面临转向。那么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究竟该转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也决定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研究的理论创新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走向阐释学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如何去阐释的问题?阐释的角度、思维以及阐释的模式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文论的进一步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研究在21 世纪的中国将更加走向式微,我们能否找到更新的角度重新进行阐释?例如,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等。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能否做到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例如,田刚健对“美是生活”的重新阐释,进而对“美是生命”的内涵进行挖掘,而不再是大而化之的笼统概括。这一系列的命题不仅关乎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中国的地位,更能够透过对其研究的现象见出中国当代文论的本质特征。
结 语
回望过去70 余年中国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接受与反思的过程,我们不免要带有挑剔的眼光,甚至批判的态度。但如果让我们回到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我们未必会比我们的前辈做得更好,只不过现在的我们受到中西方多元文论的影响,学术视野拓宽,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情况。事实上,在不同的时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研究出现的偏离与失落带有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仅存在于学者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接受与批评中,也同样存在于学者们对其他文论家观点的接受与批评中。然而,今天我们回顾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在中国70 余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其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去评判以往学者本身,而是透过这些学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论的研究去思考产生此种情形的文化因素,以及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弘扬哪些传统,从而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与转向提供一种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