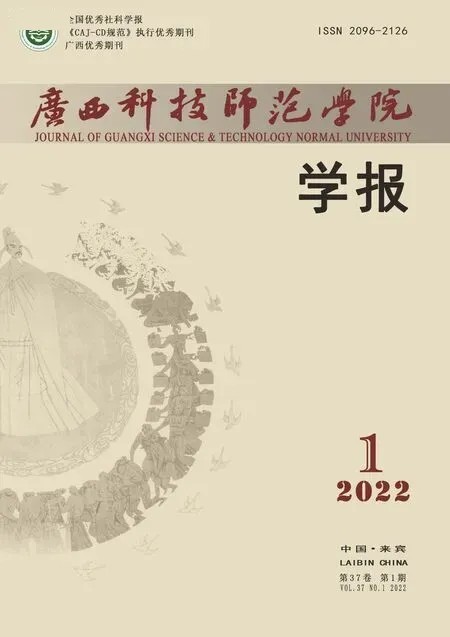快乐工业:文化工业视角下国内脱口秀的文化生产机制
强 佳 琪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不少互联网媒体习惯将2021 年称作“中国脱口秀爆发元年”。脱口秀文化的迅猛发展正是得益于其链条式的创作与分发机制。喜剧本着嬉笑戏谑的原则,可以揭开彼此的面具并享受自由人的快乐[1]267。然而嬉笑戏谑的创作背后是观众的失语状态、演员的苦行主义,二者的背后还有一双操纵的手——喜剧工业化的资本生产。
一、文化工业视角下的脱口秀文化
“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一词最早可能出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①为人名翻译一致的需要,在正文中所涉及的“Adorno”统一译成“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2]。在该书中,作者借以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指出其通过大规模的垄断、机械复制与传播,以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产出同一化的产品,从而将艺术转化至商品消费领域中。文化工业以娱乐的方式不断地影响着消费者。实际上,文化工业向消费者的“承诺”已成为其施行“谎言”的筹码,部分消费者也在娱乐中失去了自我控制力,失去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文化工业垄断下的“奴隶”[3]126。赵勇将文化工业理论还原到其原生语境中去考察,指出西方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具有拜物教的性质,艺术在逐步丧失自律性与反抗的冲动,开始与文化工业形成“共谋”的关系[4]。金元浦利用文化工业理论分析了我国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指出当时的文化工业以复制、包装、推销一连串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文化工业与艺术本性严重背离[5]。姚文放指出西方文化工业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它是资本驱使与操纵下的商品化、市场化、技术性的文化生产[6]。上述研究表明,文化工业生产与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资本控制部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以标准化机械复制的运作方式,让部分消费者在潜移默化的“娱乐”思维下,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文化本身易失去活力。
脱口秀被视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形式。郭子超指出当前国内脱口秀创作是标准化、伪个性化的文化生产,对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有潜在操纵作用并使他们丧失了自由思考的能力[7]。需要补充的是,脱口秀文化与文化工业之间的链接关键在于所谓“生产快乐”的喜剧产出机制。《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提到,快乐是一种逃避,意味着消费者会对商业提供而来的娱乐麻木不仁、点头称是[3]130。脱口秀正是这样一种“快乐工业”,它恰恰展示了商业与娱乐之间的亲和性。
脱口秀起源于国外,又被称作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最早可以追溯到18 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上的一种表演。20 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电视节目的发展,脱口秀从夜场、酒吧等集会场所转向公共电视节目,其表演形式也逐渐固定为“一个人,一支麦克风”,由脱口秀演员讲述各种笑话、段子,以引观众发笑[8]。作为舶来品的脱口秀传播到中国之后,从2010 年的《壹周立波秀》开始,一批基于单口喜剧形式的脱口秀节目在东方卫视播出,这使得脱口秀在中国出现了专门的、传播度较广的剧场表演和电视节目的形式。直到2017 年的《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网络综艺节目上线,国内脱口秀逐渐形成产业链,吸引了一大批脱口秀演员,并出现了本土化的创作风格与传播风格。近年来较热门的《脱口秀大会》,已经形成了综“N”代的节目矩阵,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IP 效应,有效提升受众黏性[9]。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8 月23 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仅更新两期就收获8.1 亿次的播放量[10]。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笑果文化”)的脱口秀节目已形成了产业链,旗下的《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冒犯家族》等综艺节目,正引领中国脱口秀在娱乐行业中独树一帜,以“嬉笑怒骂醉眼看世界”的方式,赢得观众的喜爱。
从本质上来说,脱口秀是关于“笑”的文化生产,实际上已成为当代文化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子目——“快乐工业”。当“逗笑梗”铺天盖地向观众袭来时,部分观众享受着直接挪用与复制演员的经典台词的便利,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亲自阐释自身生活的乐趣,久而久之便忘记了主动思考的能力。而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赢得“笑声”才是唯一的变现能力,通过技术层面固定化的语言机制以及内容层面对生活的苦涩进行挖掘与淘洗,脱口秀文化高捧起“快乐”来夺人眼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还依然是保留着娱乐的成分。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3]123脱口秀文化所曝光的“快乐”背后是有意的资本操纵和资本主导下工业化的内容生产,演员是生产领域的被迫害者,成为资本诱导下站在台上表演的“提线木偶”,承担着绞尽脑汁的观点输出,被卷入曝光的中心领域。观众是消费领域的被绑架者,体验着段子如同风潮袭来时的瞬时“快乐”,却也在无意识中逐渐失控。
二、快乐的工业:笑的工业生产与语言机制
“快乐工业”的娱乐效果源自于该文化本身的语言机制。随着脱口秀文化的不断发展,“脱口秀段子开始出现同质化,演员编写故事也开始遵循一定的公式和套路”[11]。当前的脱口秀文化正体现为一种标准化、模式化复制的创作产物。
(一)网络用语与潮流趋势
作为生产“快乐”的脱口秀行业,已经形成了其专有的语言、语法和词汇。首先,由于《脱口秀大会》的受众群体集中在青年一代,在他们之间有绝对的互联网普及率与潮流跟踪率。因此,网络用语的活用成为脱口秀演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比如,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的突围赛中,演员吴星辰在表演时运用了大量的网络用语,也专门指出了网络用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弊。脱口秀演员通常将网络用语融会贯通在演出文本中,或是作为引爆的笑点出现,或是将其作为常态化的叙述用语,抑或是直接讽刺网络用语的滥用。在现实生活中,网络用语不断更新迭代,过时的网络用语被遗忘在记忆深处,而新的网络用语层出不穷,甚至脱口秀也成为网络用语的制造地之一。
(二)讽刺吐槽与冒犯性
讽刺与吐槽是脱口秀演出的另一套语言运行规则。这原本是喜剧演出的一种叙述技巧。在伯格森看来,“笑也是不能出于善意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羞辱来威慑人们。如果自然没有……留下丝毫恶意,至少是丝毫狡黠的话,笑是不会达到它的目的的”[12]。脱口秀的讽刺艺术有其模式化的讽刺对象、讽刺原则、讽刺程度。表演者在讽刺时还会以自嘲或自黑作为“安全牌”,以此避免给被讽刺对象和其他观众带来尖锐听感与不适感。对于脱口秀而言,讽刺只是一种搞笑的手段,以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与认同为目的,一般达不到针尖对麦芒的激烈程度,可以称之为“温柔的讽刺”。演员带“刺”的语词或许只是一剂微痛的细针,其中的冒犯性是为迎合观众追求的刺激与宣泄,来满足观众解放天性和好奇的社会心理,由此争取观众的注意力。
(三)谐音梗与语词跨越
谐音梗也是一种常用的表演方式。谐音是指字词的音相同或相近。人们常常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来使用谐音代替本字,构成修辞格,增强表达效果[13]。在脱口秀表演中,表演者利用音近义不同的两个汉字,造成音指与所指之间的反差感与距离感,生成陌生化的滑稽效果。事实上,脱口秀创作中的谐音梗是一种微语言的超常搭配,利用了字音的置换思维,是一种便捷的创作行为[14]。事实上,过度模式化与技巧化的语词创作使得脱口秀创作变为一种“文字游戏”,这种人为牵连的文字联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语言的创造性与灵活性,机械式的字音联想使得语言的自由张力受到限制。
综上所述,网络用语、谐音梗、讽刺吐槽等语言技巧并不孤立存在,创作者通常会将其融会贯通在脱口秀文本,从而形成脱口秀独特的语言生产机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3]115-116《脱口秀大会》第四季节目以“所有人都可以说五分钟脱口秀”的口号作为营销策略。在这样的号召之下,“笑”的生产逐渐开始普及化。脱口秀节目将“笑”变成了一种文化理想,打着“尊崇理想”的方式将“有识之士”吸纳到本行业中,以此来稳固自己的“娱乐地位”。然而,看似低门槛的脱口秀行业,实际上却拥有已然刻板化的语言生产机制。每一场段子如同精密的锁链,一环扣一环。关键的笑点投掷、表现的收放自如与段落的自然过渡,考验着演员的文本能力与演出能力。与相声行业不同,大部分脱口秀演员的成长里程显然比相声演员更短。以笑果文化的脱口秀新人演员培养为例,笑果文化通过线下稳固文化基础、孵化新人,再通过线上扩大艺人知名度并提高脱口秀文化的影响力,四块业务统合组成一个人才的上升通道。脱口秀行业近年的增长速度,正是引证了现代社会商业与娱乐的紧密贴合。
三、失语观众:二次阐释与瞬时快感
观众是整个脱口秀行业的最关键的一环。在伯格森看来,笑需要有附和者的回声,需要有社会的力量来推波助澜[1]258。观众是否喜闻乐见是评判脱口秀质量优劣的首要标准,也是脱口秀文化得以发展的精神支柱。脱口秀的正式演出过程大致如下:台上的脱口秀演员说着预先设计好的文本,配合着与文本相适应的肢体语言,并在每个关键的位置“抖”出“包袱”,其表现力强弱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反馈。相关调查显示,“18 至29 岁的群体是喜剧受众的主体……大部分年轻态喜剧受众的家庭月收入在1 万元以上,收入可观,有一定的消费能力”[15]。因此,从受众的角度分析,与相声、小品等传统喜剧形式相比,脱口秀作为年轻态喜剧的代表,内容和形式都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豆瓣“脱口秀大会”小组2020 年发起的内部观众投票结果显示,与输出价值观相比,有将近80%的观众认为搞笑更重要[16]。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3]130。对于观众来说,脱口秀呈席卷之态势的“笑”向观众袭来,观众已然失去了思考的意识。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他人的思考来总结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躲避原发思考的机会。
(一)二次阐释与情感提纯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与第四季的主题赛中,脱口秀的创作主题大多都集中在都市青年的日常话题中,与他们的工作生活高度契合。《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主题赛的选题分别为“不就是钱吗”“我们,结婚吗”“保持距离,保持联系”。《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主题赛的选题分别为“没关系,我也有病”“不上班,行不行”“恋爱,我想和你谈谈”。以上选题说明,脱口秀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受众,讲述主题一般集中在都市青年较为关心的议题上,包括常见的恋爱婚姻、金钱消费、职场社交、心理健康等方面。因此,对于观众来说,脱口秀的文本恰好是关于自身生活的二次阐释,观众的日常生活借用演员之口传达出来。观众来到脱口秀的演出现场,就相当于从真实的生活走到另一片阐释生活的疆域中。观众将脱口秀文化视作趣味与幽默的观点发酵地,挖掘出无聊生活尚存有的幽默精华,尽情缓解生活的苦痛与无聊。然而,这一片阐释生活的疆域或许是使观众思考停滞与固化的一片疆域。脱口秀演员的讲述,替代了部分观众去实现从生活本身到观点投射的跨越式发展,直接替代他们进行生活的情感提纯,自动省略他们领悟生活的过程。在脱口秀演员的讲述中,观众能与之获得更高层面的情感认同。但是在一些广为流传的经典段子中,所谓“阐释生活的疆域”变成了观众进行惯性复制灵感与挪用观点的提取域,某一观点在更多场合被观众不断地进行套用,使得他们独立思考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
(二)瞬时的快乐与闭塞的思考
对于一部分观众来说,他们愿意在线上或者线下观看一场脱口秀演出,愿意为之消费,愿意与台上的演员配合,共同完成一场关于“笑”的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的逃避。快速行进的脱口秀表演并没有给这些观众留下多余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他们不得不快速地作出大笑的反应。转瞬即逝的理解,或许根本偏离了表演所要呈现的真正指向,而如同火车般呼啸而过的脱口秀表演,又使得部分观众不得不减少思考,顺着表演继续听下去。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反应是半自动的,但也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想象的空间。”[3]113在观看笑点连续性极高的脱口秀表演时,这些观众只会在意并期待着下一个“包袱”什么时候来到,下一个痛快的“笑”该如何配合,无法顾及上一个“包袱”究竟表达了什么含义,上一个“笑”究竟是为何而笑。观看表演的次数多了,观众也会在连续不断的“观看训练”下,学会如何分辨表演中的关键节点,学会根据演员抑扬顿挫的语气、恰到好处的停顿、巧妙的手势动作等具体细节,接收到何时该笑的状态提示。这时,观众便“学会”了自动地作出反应。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对笑的产生是这样论述的:“笑都是突如其来的,不假思索的,所以见到可笑的事物而发笑,自然可以说是直觉形象的结果。”[1]276脱口秀文化正是把握住了“笑”的产生机制,利用文化工业的逻辑进行文化扩张,观众已经成为被其裹挟的个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观众的意识“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3]112。人们似乎无法决定自己该笑还是不该笑,他们坐在漆黑一片的观众席间,如潮涌般袭来的笑声使得他们不得不笑。于是,在不经意之间,观众已经失去了作为观众不笑的权利,越来越难站起身来对抗这种固定化形式对自己的约束。“表演造成的情感刺激,使观众得以宣泄情绪,纾解压力;表演中的观点输出,可以让观众体会到‘顿悟’的快乐。”[8]与演员相比,观众所获得的不过是一个由他人代笔的情感文本,不过是一个观点输入再到情感认同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观众关闭了抒发原生观点的欲望触角。基于他人赋予的瞬时快感,观众自行偷懒,仅用笑声表达对他人思考的广泛赞同,用笑声替代了自身原创性的思考。因此,随着脱口秀的经典段子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规避了自身思考,被动接受他人思考的成果。于是,在脱口秀的文化场域中,演员与观众、演员之间、观众之间,所谓的“段子”不过是不断复制与引用的产物,观众失语的状态仍在不断持续。
四、苦行的演员:审丑效果与苦的情怀
作为“快乐工业”,脱口秀文化并没有在纯粹意义上将“快乐”贯穿始终。相反,在生产快乐的过程中,痛苦与麻痹却时常存在。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认为,“喜剧跟悲剧一样,都引起快感与痛感的混合”[17]。依据喜剧的逻辑,相对痛苦的事情才会令其他人发笑。比如,在《脱口秀大会》中,演员常聊的两类话题是“丑”与“苦”。这两类话题也最能博得观众的满堂彩,例如何广智关于“丑与穷的人生经历”、徐志胜的“长相优势”、邱瑞惨痛的“北漂租房经历”、呼兰的“屡跌的股票之路”、鸟鸟的“容貌焦虑”、赵晓卉的“车间女工身份”等。从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来看,脱口秀演员通常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共同展示了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从生活体验的方面来看,他们的生活经历极易与普通观众之间产生共鸣。
(一)审丑效果:打破常规与逆流视野
“丑”是脱口秀演员常用的人设标签之一。从容貌评价的角度来看,脱口秀文化或许与大众的审美体系恰恰相反。在一般的大众娱乐领域,演员需要有独特的颜值、过人的身体机能和优异的才艺表演。但是,脱口秀却恰恰相反。颜值高似乎并不能成为明显的加分项,脱口秀演员往往代表了生活中普通人的长相,甚至有时候会产生颠覆常规的审美原则。在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中,容貌与身材的自嘲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模式,成为一些脱口秀演员的常用人设之一。例如:《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新人演员张灏喆初次登台时,讲述了自己由于过重的体型引起的各种误解;《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演员王勉与豆豆都曾自嘲身高;《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靠长相走捷径”的演员徐志胜,凭借着他的挑眉与“逗号刘海”,提出了“暴力丑学”与“吾孰与城北徐公美”的经典段子;等等。这些特征由演员讲述出来之后,便成为演员自身的一个标签,给予观众特定的演员印象。
由此可见,反向审美成为脱口秀领域相对固定的形式,融会在脱口秀演员的个人段子中,通过自嘲的方式,让观众拥有微妙的优越感,使得观众的心理从紧张戒备变得松弛起来,缩短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徐志胜的“喜剧脸”就是如此,符合了喜剧的逗笑机制。徐志胜不遗余力地将其作为一个创作卖点,以调侃和自嘲的方式讲述出来,放下长久以来的自卑痛苦,去发掘背后辛酸的心理情绪。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脱口秀文化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原则,演员凭借着自身的口才与创作能力,展示了个性化的审美效果,与当代社会大众所认同的审美趋势形成反差与逆流,以批判的视野塑造了多样化的审美特色。
(二)苦的情怀:直面痛苦与精神禁闭
“苦”也是脱口秀演员常用的文本基调之一。由于脱口秀的受众大多是都市青年,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忙碌的生活间隙来观看脱口秀表演。此时的脱口秀表演就成为观众的情感发泄空间,他们渴望通过一场演出,驱散现实生活的阴霾与疲惫。演员们恰到好处的“苦”段子,代表观众讲出了心中部分愤懑已久的感受,观众也似乎在此“苦”与彼“苦”的比较中找到了内心平衡。“苦”同时也成为脱口秀表演的一种独特情怀,演员借此宣发自己的生活态度,讲述着普通人生活的痛苦与不易,在观众之间获得相似的情感投射。对演员来说,台上表演讲出来的“苦”需要成为能逗笑观众的“梗”。因此,他们的“苦”就成为一种“自嘲式”的人生之苦,带有几分“嬉笑怒骂醉眼看世界”的自我揶揄,以此来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
“容貌焦虑”“脱发危机”“理财失意”“内卷压力”“催婚催生”等是脱口秀演出常用的“苦”话题。脱口秀所探讨的话题,大多是小人物身上肩负的种种焦虑与压力的表现,“他们的自我挖苦和互相调侃,庸俗却不低俗,调侃缺点却不嘲笑缺陷,捧腹大笑之余,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18]。“丑”与“苦”是双向并行的生产机制。在演员这里,“丑”与“苦”暂时是专属于自己的负面情绪。通过脱口秀的文本创作,他们将这些痛苦的情绪包装上一层“糖衣炮弹”的外壳。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根据霍布斯的“鄙夷说”,“突然的荣耀”是笑的一种,产生于自己某优点引起的“荣耀感觉”,这样的笑是鄙夷的、奸险的,这种由妒忌作笑的动机是喜剧心理学的出发点[1]256-257。因此,“幸灾乐祸”“荣耀感觉”与“妒忌作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脱口秀文化生产的部分逻辑。
综上所述,反向解构是脱口秀的文化逻辑,它与大众娱乐略有不同,摒弃了颜值至高无上的审美效应,摈弃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的传播方式。事实上,脱口秀作为一种“快乐工业”,“它把笑声当成了施加在幸福上的欺骗工具”[3]127。演员与观众一样,都成为“快乐工业”的“受害者”,演员时刻面临着直面痛苦的过程,自我蒙骗式地将自我的痛苦转化为他人的快乐。他们被剥夺了逃避痛苦的权利,且要对生活强加而来的种种羁绊进行滑稽模仿。身处脱口秀表演中,演员是被“快乐工业”进行精神禁闭的“苦行僧”,为每一份生活的快乐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结 语
脱口秀属于喜剧的一个分支,本质上是关于“笑”的工业生产。具体来说,目前当代脱口秀文化已经形成其独有的语言生产机制,以潮流追踪、讽刺态度、真实性等创作原则进行语言生产。脱口秀文化已经具备相对完整的生产链条。比如,笑果文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脱口秀产业链,从上游的艺人培训,到中游的线上内容制作、线下商演与开放麦,再下游的营销推广,均日趋成熟。随着《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综艺节目的不断热播,同台竞技的脱口秀促使了更多新人的加入,用比赛的方式助推快乐工业的内容产出与技术提升。
脱口秀演员通过对观众的深度体察,助推形成了本质意义上的“失语观众”。一方面,脱口秀演员讲述都市青年所关注的议题,本身是对观众生活的二次阐释,将“糟糕”的生活视作搞笑创作的发酵地,从中不断地获得感悟,进行情感提纯。当脱口秀演员替代观众完成这一关键步骤后,观众就会无拘束地享受一场脱口秀带来的瞬时快乐,忘记负载思考的疲惫感与复杂感。另一方面,演员担任了“快乐工业”的“苦行”角色,通过“丑”与“苦”的情绪渲染,撕开自身的伤疤以博得他人的发笑。在文化工业的视野下,纵览整个脱口秀文化的生产机制,这如同一台巨大的商业机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有关“笑”的工业生产。正如《脱口秀大会》的节目口号“The show must go on”,在一场大秀过后,观众们继续投入原本机械复制的生活中,“快乐工业”仍在继续生产,人们翘首以盼,等待下一场秀的到来。在这个看似一派和睦的场域中,笑声被文化工业规模化地生产出来,导演、制片人与演员为了满足观众娱乐与轻松的需要,用“快乐至上”的工业标语,形成其独有的意识“控制”。而在一场大秀散去之后,观念“被搞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3]124。不禁质疑,一出引起观众阵阵大笑的脱口秀,是否也能像莫里哀[19]所说的“受到公众的哄笑”的同时还能“把他们的缺点刻画出来”与“打击恶习”呢?脱口秀文化——这种“快乐工业”,其展示出的种种文化特征,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值得被进一步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