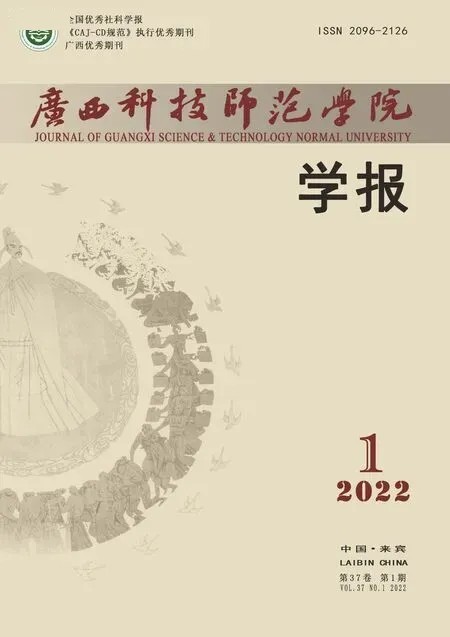杨映川儿童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刘蕙嘉,王 红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独秀女作家”杨映川于2020 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以《少年师傅》《千山鸟飞》两部新作跻身当代作家转向“小童书”的行列。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均具有鲜明的广西地域特色。在《少年师傅》中,杨映川讲述了成长在三江侗乡木匠之家的小主人公玉樟是如何从贪玩的小孩成长为一位建造大师的;在《千山鸟飞》中,她将严峻的环保问题直接呈现在侗乡儿童面前,如少年包森林在家人的支持下,以超乎寻常儿童的勇气去守护森林、保护鸟类。杨映川以童年故乡为叙事原点,透过儿童纯真的视角书写凝结着民族地域特色的文本。她的作品留下了若隐若现的地理痕迹,真实还原了桂西北地区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承载着侗族人民集体生命体验,显示了侗族族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散发着生命活力。与此同时,杨映川将儿童从城市中解放出来,让故事发生在有原始山林、河流、动物的大自然中。在乡野中自在成长的孩子们整日穿梭在山林中,与大地紧密相连,与动植物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促使儿童以热爱、尊重和关怀之心去认知整个世界。杨映川通过文学、地理以及童年三者的互动来实现重回童年发生现场和重构童年生活的目的。文学桂地的民族书写、地域书写以及童年记忆所蕴藏的生命经验,在交流互动中不断丰富着杨映川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具有诗性特质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并以此建构包孕地理之美、童年之趣的诗学,彰显了杨映川在儿童文学创作过程中独特的思想认知、创作模式以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一、童年、地理与文学经验:杨映川儿童文学的本色写作
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人地关系”是探讨核心之一。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1]。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是文学创作的地理故乡。作家写作方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源自无法抹去的童年经验。地理与童年对作家而言已经超越特定的名词概念,在其成长过程中早已升华为自身的精神归宿,并在作家反思中不断重建,从而形成带有历史性、时代性并超越自我个体的文学经验。显然,这一文学经验形成了杨映川儿童文学的本色创作方式,即回归自我、叩问本心,是一种鸿蒙天成、童心自然的写作方式。
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杨映川,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人。她的童年记忆中有秀美的自然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璀璨的民俗风情,多种文化形态都在桂地交汇、碰撞、融合,这为杨映川构筑了独特的文化空间。虽然杨映川的文学作品大多以现代都市环境为背景,但她仍将创作触角延伸到童年、故乡的每个角落。其小说贴近广西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南宁符号意象打造的逼真的生活环境”[2],作品描绘了以老友粉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邕江为代表的南宁生活场景等,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南宁人的生活轨迹,还原了南宁的本真模样。为了保持作品的地理与时间的真实性,杨映川在创作之前会进行实地考察,将小说发生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习俗、民族特质都融入作品中。正如她所说,文学创作“不仅要将口语化语言转化为文本创作,也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运用地方方言”[3]。无论是严肃文学作品还是儿童文学作品,杨映川灵活运用地方语言使作品氤氲着丰厚、质朴的南国气息,整体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此同时,广西密集重叠的文化空间使杨映川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北部湾海洋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4]。她的作品不仅有对人现实处境的全面审视,还有对未来生活的诗性憧憬,让读者与之一起“分辨生活,反思人生,叩问人性”[5]。
一直以来,杨映川的文学创作并非停留于对现实表象的描述,而是不断向内心世界拓展,直逼人的灵魂,有着生命的力度与韧性。童年的温馨与家庭的温暖伴随着杨映川成长。在《我的1972》中,杨映川记录小时候大病初愈的情形,“每想起那群身穿白大褂的人,我的心口处就像有茸茸的白云拂过,温暖而饱含柔情。也使得今天我在对许多人事刻薄唾弃之余,还带了点宽容之心”[6]。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反而让她对世界有了包容之心,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她的作品便呈现出一种宽容、乐观、向上的生命意识。在2021 年接连出版的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少年师傅》《千山鸟飞》中,以桂西北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正是杨映川笔下童年世界的再现,正如她所说的,儿童文学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把孩子的世界还给孩子,让他们的立场、态度自然而生,尽可能地让孩子用自己的视角来完成整个故事的解读[7]3。杨映川构建的儿童世界是以“风雨桥”“千年鸟道”为原型的边陲南国。“以儿童视角来书写侗族族群的生活,将主动权还给儿童”意味着杨映川试图还原儿童生命的纯粹,不断叩问追寻生命本质,并在带有乡土生活色彩的日常叙述中向读者传播侗族传统文化,为民族的认知与重建找寻独特方式。
正如侗族古歌吟唱的那样,“世间谁是主人翁/侗家祖辈教孩童/山河是主人是客”[8]。一直以来,“天地为大”的思想决定着侗族人的生存思维,侗族人与万物和睦相处、相亲相爱,造就了侗族人真诚、良善的品性,也体现了侗族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这一自然崇拜是侗族族群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侗族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思考,体现了侗族发展过程中的大地品格。因此,带有鲜明侗族文化气息的地理环境,成为杨映川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地理基因之一。在《少年师傅》中,“风雨桥”这一独特的地理意象贯穿杨映川的作品。在作品中,阿爸四处修桥积攒“功德”,小少年玉樟从贪玩的小孩成长为一位建造大师,故事结尾是侗乡众人合力修补风雨桥。侗乡地理空间的交流互动离不开风雨桥。风雨桥不仅是避风遮雨的工具,还是邻里沟通的社交场所,供来往行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在侗族社会的演变中,风雨桥已然成为侗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寄托着侗族人朴素、深厚的民族情感。杨映川笔下的风雨桥更是侗族人民团结力量的象征,这一鲜明的地理意象涵盖了侗族传统文化、民族情感认同等多种元素,积聚着侗族人对族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一座结构严谨、造型独特的风雨桥的建成离不开精湛的木匠工艺技术,而建造材料均取于大自然的苍天杉树。侗族人民生活的地方素有“杉海”之称,丰富的森林生态文化滋养了古老的民族。许多侗族村寨都流行“祖孙林”的习俗。在《少年师傅》中,侗族儿童就成长于“祖孙林”之中,他们能听得见树呼吸的声音,跟杉树“‘打老同’(即结拜兄弟)”[9]34,与森林、土地互相信任,大自然成为他们广阔、纯粹的游戏场所。同时,温暖而具有治愈能力的大自然也成为儿童在成长时期感到迷茫、伤心时的庇护所,儿童在与大自然温情脉脉的对话中共同生长。对侗乡儿童而言,他们自小对大自然就有敬畏与爱护之心,能自然而然地与大地建立亲密关系,从而建立独立人格,形成对生命的正确认知。在珍惜自然馈赠人类的同时,侗乡儿童将工匠技艺视为一种游戏,每一块木料都承载着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生活的感悟。在一刀一斧的刻画之中,他们聪明淘气的儿童天性得以释放,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也得到极大的开发。除此之外,杉树在侗乡工匠的手上不仅能从木材、木料变身为各种精美的家具、器皿,还能成为“一桶定终身”[9]13的定情信物。这些沉淀在乡土之中的生活实践,蕴藏着侗族人民的生命力量,显示了侗族人民通过实践性的生命体验来与自然形成良性的沟通与对话。
对广西文化的热爱、对童年生命体验的不断回望以及民族文化和生命经验的先在性影响共同组成了杨映川特有的文学经验,进而成就了杨映川的本色写作方式,即回归自我、叩问本心。在《少年师傅》《千山鸟飞》中出现的银兰村,在作品中被杨映川赋予了地方色彩与童真奇趣,成为一个动态的文学地理空间。在这里发生的神秘、温情、悲伤的故事,都来自杨映川对故乡和童年的文学想象。“地理空间是具有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的审美空间。”[10]杨映川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大地与山林、人与天地完美融合,呈现了一个干净、潮湿、质朴却充满童趣的南国边地,显示出她对儿童生命的体悟与认知。这正是杨映川创作的本色显现,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度。
二、儿童认知中的乡土世界:杨映川儿童文学的地理空间叙事
杨映川不断回望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在其儿童文学作品的虚构世界中打下乡土的烙印。作品的虚构世界与作家的童年现实世界彼此相通,这一本色书写方式表现出杨映川对生命的尊重与理解。杨映川儿童文学作品以桂西北少男少女的成长为主线,不断调动儿童生命的乡土经验,塑造了勇敢、坚韧的侗乡儿童人物形象,显示了南方少数民族延续至今并依然散发的生命活力。基于地理空间叙事方式的创作理念,杨映川的儿童文学作品反映了丰满而又情感氤氲的侗乡世界,也反映了杨映川对童年生命与文学创作的认知,呈现出诗的质地。
首先,杨映川透过儿童视角不断还原童年记忆中侗族乡土生活的场景,并以此为儿童文学的叙事原点,展现了原始、朴素、天然的侗乡社会。这样一种回归童年、回归本心的创作方式更能凸显杨映川对童年童趣的本色书写,同时保证了杨映川以童真的视角关注现实,直面生命的本真状态。文学世界有了现实基础与生命情怀的交融,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奠定了逻辑基石。例如,在《少年师傅》中,“祖传树林”和“林溪河”对侗族人具有特殊意义,风雨桥垮后侗乡人祈祷山神和树神的庇佑;在《千山鸟飞》中,包森林家有玉米糊、豆腐酿等各类手工制作的食物,侗乡少男少女经常参加坡会、以歌传情。侗族乡土社会所特有的风俗人情,属于杨映川个人的童年经验,独具地域色彩的侗乡原型符号在杨映川的作品中以艺术再现的方式显现出原始之美。同时杨映川关注了侗乡的环保问题。作品《千山鸟飞》刻画出了侗族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问题,并十分关心生态危机下儿童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的变化。乡土与现代社会嬗变,向往城市并走出大山的人越多,侗乡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变化得越快。例如,在《千山鸟飞》中,余鹏程也是在山野长大的少年,但不同于包森林的天真可爱,他喜欢时髦,善于算计,梦想是赚大钱;走出大山的农家女孩包百丽逐渐沾染了现代人功利和自私的习性,成为捕杀鸟类的帮凶,与乡土社会的善良、质朴渐行渐远。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沦为主客体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层次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为自然的开发者。在《千山鸟飞》中,包百丽、余鹏程是一部分乡村少年的代表,他们褪去童真的面貌,逐渐带有现代社会异化的影子。但在故事的最后,包百丽、余鹏程由于目睹鸟儿被虐杀而感到愧疚不安,加入了包森林的行列,成为银兰村的守卫者,他们找回了善良的初心与童真之心。杨映川通过这些儿童对自然和生命态度的转变来实现当代侗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构,引导儿童重新建立敬畏自然、保卫自然的观念。有的人几乎完全泯灭良知,用各种方式捕获鸟类获取利益的同时,他们眼中一切儿童“游戏”“淘气”“闹别扭”的行为正是儿童以童真的方式去抵抗成人世界功利的悲哀。儿童对自然生命的思考,与以工具理性和利益至上为主导的成人思维方式有着巨大差异。杨映川认为,我们要启蒙的就是孩子对生命的尊重,我们要保护的就是孩子的这一份纯良[7]3。因此,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艺术性刻画,不仅体现了杨映川对侗族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反思,还遵循着自然生命的自由意志,将生命深处的点滴置于读者面前。
其次,人类的生存发展都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文学的发生也离不开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文学审美经验在本质上是人类在空间内进行系列文学活动的主客生成体,是人—空间的交互性产物,这决定了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性质。”[11]而文学世界的构成也就是文学内部空间化的显现,即在人与空间的交往互动中构成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杨映川儿童文学世界的构成以独具地域特色的客观环境与人文环境为底蕴,以相应的侗乡人物形象塑造为表征,具有联动性与具体可感性的特点。如在《少年师傅》中,“三江侗乡”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地理空间作为文本叙事空间,具备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情节发展的静态背景和叙事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场景的功能。三江侗族自治县、风雨桥都是真实存在的,故事发生在“三江侗乡”这一地理空间中也合情合理。玉樟的父亲四处修桥铺路;玉樟勤学苦练最终修成“飞斧”神技;侗乡的男孩子喜欢聚集在一起斗陀螺,女孩子则喜欢在白布上绣花;少男少女定期在坡会上以歌传情……这些细节散发着些许侗族质朴、真诚的人文气息。作品透过儿童的视角书写了当地的社会变迁与侗族人的生存状态。这意味着叙事空间不仅是容纳情节走向的背景,而且在主体的实践下具有了“依据时代、社会、生产模式与关系而定的特殊性”[12]。在《千山鸟飞》中,银兰村作为现实与艺术相交融的产物,承载了幽美奇异的自然风光、包森林一家的衣食住行等,这同样是对当代桂西北少数民族生存状态的展现。杨映川的儿童文学世界在空间化的呈现下不断生成,也为在这方土地成长的少男少女提供了释放自然生命的场所。这些侗乡儿童都在万物有灵、万物和谐的自然地理空间中享受山野的滋润,不断丰富着自身与山水相融、与土地紧贴的生命体验。当传统与现代碰撞,原始乡野受到侵蚀,但这方独特乡土孕育的孩子们始终成长为如山般坚毅、如水般温润的人,这也是杨映川儿童文学世界最真挚的呈现。
文学世界的生成是空间化的内在显现,“空间通过具有某种实体意义的内存之物来显现;空间的构成是一种关系论;空间的连续性运动构成时间”[13]。在杨映川儿童文学作品中,具象空间的建构以故事情节设置为最小单位,最终形成以空间活动、人物成长为串联的叙事模式。在《少年师傅》中,每一章节都可以看作独立的故事。例如,“陀螺王”讲述了玉樟如何智胜斗陀螺;“龙山红的婚事”讲述了村民一起替受丈夫欺负的龙山红讨说法;“赚钱吃鸡”讲述了玉樟依靠精湛的技艺赚钱并请表哥杨盛年一起大快朵颐。作者塑造了不同的人物穿插在不同篇章,由小主人公玉樟的回忆来串联事件并丰富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从而构成整个完整的故事。例如,“丝瓜须很好看”与“龙山红的婚事”两章的女孩龙杜鹃表现出侗族少女聪慧、直率且泼辣的性格特点。杨映川的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完整呈现了以玉樟、杨盛年、包森林为首的少年们释放才华、走向成熟的过程,作品中自信、乐观和独立的少年形象十分凸显。而侗乡儿童的成长串联了不同空间下的人物活动,不仅体现了文学空间的地域特色,还体现了儿童生命的自然发生、发展。例如,在《少年师傅》中,作为侗乡人心中的母亲河——“林溪河”在文中多次出现,它同“风雨桥”共同构成侗族人心中无可替代的传统文化空间符号。对侗乡儿童而言,它更像是朋友、父母,无论是追溯自己的起源,还是离家出走夜宿的地点,“林溪河”永恒流淌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在杨映川笔下,通过儿童人物的成长串联具有流动性与跨越性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儿童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达到了重构自我、追寻自我、认同自我的目的,更好地展现了儿童纯真、自然的生命之美。
正如曾大兴所言,文学地理空间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审美空间[14]。童年生活与乡土记忆给予杨映川文学创作的本土文化选择,其儿童文学作品基于侗族的地理空间转换,串联起侗乡少男少女的成长轨迹,组成一幅幅鲜明的侗家人生活场景图。这是杨映川对侗族乡土生活的诗意书写,展现了作家童年经验内在的民族气质、质朴的童真以及乡野的美好。
三、“童年精神”与乡土气息:杨映川儿童文学的地理诗学
科技进步给自然与现实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人类面临着复杂的伦理困境。“人的主体性”消解使得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下的主题之一。因此,当代儿童文学多将生态批评纳入其中,把生态问题和儿童成长联系起来,“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15],试图在生态伦理和现实关怀中寻求平衡。杨映川以特有的地理空间为基础,为乡野儿童提供了实践、成长的场所,创造出诗意盎然的童年世界,童年精神与乡土气息在此被唤醒,儿童生命的自然、自由、自在本质得以呈现。杨映川的儿童文学在地理空间叙写之上建构起独特的诗学之维。
英国学者艾伦·普劳特曾提出童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任何一种童年观念都是长期历史建构的结果[16]。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商业化的特点,辨清和识别童年精神的内涵与方向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坚信,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17],向儿童传递道义感、情调和悲悯情怀是隐含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精神”。李利芳认为“童年精神”是一个生长在儿童生命内部的观念生成过程,其内核是社会之于童年的价值观念,即以儿童观为支撑的一种文化建构[18]。李学斌则基于“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所呈现出的不同时空维度的审美内涵提出“中国童年精神”,它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指引,以纯真、自由、乐观、勇毅、自信、超越等诗学范畴为依托的审美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可以将“童年精神”视为一种永恒留存的文化概念,有别于“童年”“成长”这一单线时间,“童年精神”在不同时代赋予童年经验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内涵。而杨映川的“童年精神”不仅包含着独特的桂地民族之韵,还彰显着回归大地的乡土气息,本质上是一种回归现实的精神,直指生命初始与文化根脉。儿童生命初始的“童年精神”,是儿童生命最原始的心灵状态,以自由、欢乐、愉悦、热闹等轻松的形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流露出来,同时蕴藏着传统文化下的生态智慧和生命哲学。例如,在《少年师傅》中,侗乡少年沉迷于打陀螺的游戏,他们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去竞争,少年们不再羡慕成人的高超技能,而是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在其中体味输赢的滋味,实现自我满足。对玉樟而言,成为陀螺大王不仅是游戏的胜利,还代表着他能赢得木耳、野菜、红薯等胜利品,实现他“养家”的愿望。除了打陀螺,阿爸教导玉樟木匠技能时还遵循自由、自主原则,让他在体悟与想象之中琢磨木工活。玉樟在游戏中体验到了纯粹的乐趣,同时也掌握了精湛的技艺,最终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位木匠大师。正如胡伊青加所说,“人是游戏者”,“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儿童从来都是秉持最本真的心去关照整个自然、整个世界,不带任何目的去实践、感受。杨映川笔下儿童游戏的场所和方式不是离奇古怪的,而是立足于侗族乡土社会,立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共同建构的自然世界。在自然场域中,侗乡少男少女本能地将实践活动视为设定好的游戏,无论是学习工匠技能,还是与盗猎鸟儿的外乡人抗争,他们始终从心出发,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与其他伙伴携手并肩共同完成游戏过程。儿童脱离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沉重获得游戏般的快乐,最终达到游戏目的,实现主体性的解放与扩张,也在与自然完美统一的游戏情境中获得一种愉悦的享受。
当今社会,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建构的基础之上,人类既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又要避免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保留对自然的好奇与探索的童真,同时也要更自信地应对生态问题,而非单一地呼唤保护大自然或远离大自然。在杨映川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以游戏的方式来完成日常实践,从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愉悦。“童年”不再只是一种批判现实的文化符号,而是儿童的自然与自我内在统一的真实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杨映川的儿童文学是以“童年精神”为逻辑起点,以朴实的乡土气息为底蕴的文学。儿童成长经验的欢快、适意、悲伤、勇敢、无畏传递了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蕴含在背后的是儿童对自我的调控和超越。出生在乡村的侗乡儿童始终与大地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性格也多是十分活泼、调皮,对一切充满着好奇。与此同时,在杨映川儿童文学作品中,侗乡儿童善于使用生存智慧寻找“天性”的快乐,不仰视成人秩序的权威,并以敬畏大自然的生态意识做出符合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颠覆了成人世界中人与自然是从属关系的传统,唤醒了成人世界遵循人与万物平等的伦理意识。
结 语
杨映川儿童文学的地理诗学是以杨映川回归自我、叩问本心的本色写作方式来呈现的。她的作品通过乡土与童真相交融的叙事方式,以自然地理空间与人文地理空间的构造重回童年发生现场。充满浓郁桂地气息的地理意象成为文本独特的民族符号。作者十分自然地刻绘了桂地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作品乡土气息浓郁。此外,杨映川儿童文学的地理诗学以“童年精神”为内核来传递一个民族对于土地的情感与认知,交融着作者在桂地的乡土体验,并在灿烂的民间文学养料中不断形成生命体验式的认知。杨映川的“童年精神”以纯粹、天真、素朴和去功利化的方式摆脱成人的惯习、成见和利益纠葛,让社会生活回到自身的起点与展演环境。杨映川以赤诚的稚子情怀关注现实,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寻根文化。她的作品建构了生命生存境遇与发展空间,形成了质朴无华、灵动通透、认知厚实的自然生命美学特色。同时,杨映川的儿童文学作品试图在儿童日常游戏中培育儿童的生态情怀,重建儿童视角下的生态伦理,重塑良性的生态价值观念,引导人们遵循生态规律。杨映川儿童文学的地理诗学显示了她独特的思想认知、创作模式以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时作为一种深沉、富有生命力量的自省性思考,或将成为杨映川作品中永久的闪光点。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