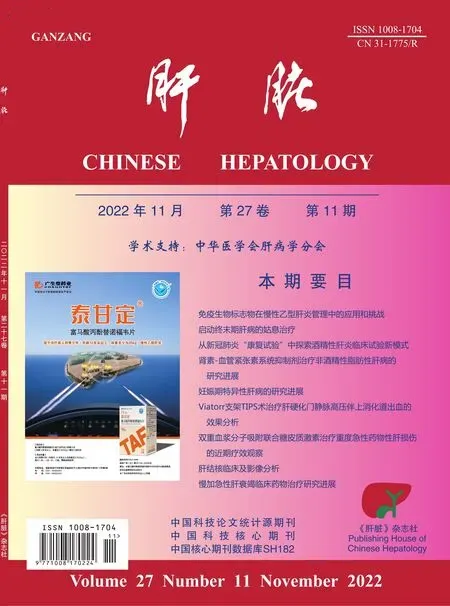免疫生物标志物在慢性乙型肝炎管理中的应用和挑战
赵彦达 钟师红 李咏茵
慢性乙型肝炎(CHB)是由免疫反应介导的肝脏炎症损伤疾病,因此,对其治疗方法和预后评估的研究中涉及免疫作用的生物标志物愈发增多,但肝活检定量肝细胞核内的共价闭合环状DNA(ccc DNA)和肝内乙型肝炎病毒DNA(HBV DNA)存在有创、取样误差等缺陷,限制了这些指标在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应用。因此,替代性的免疫生物标志物可以为预测CHB治疗的效果、深入了解新型治疗方法的作用机制以及指导评估患者预后提供重要依据。
一、免疫生物标志物在CHB管理中的研究背景
病毒性疾病的临床结局由病毒和宿主抗病毒免疫力之间的平衡所决定。在急性HBV感染后发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阴性的动物模型或临床患者中发现,HBV的特异性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与病毒学指标水平(HBV DNA、HBsAg)的快速降低相关[1-2];当动物模型或患者的抗HBV免疫反应缺陷时,则发展为慢性HBV感染[1]。HBV感染后的二分类结局为现有的抗HBV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直接或间接恢复抗HBV免疫反应来抑制HBV复制[3],这也为免疫生物标志物应用于评估宿主免疫反应和CHB患者的临床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免疫生物标志物在CHB管理中的应用
(一)病毒相关免疫标志物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Anti-HBc)是人体感染HBV后产生的特异性抗体,已在临床中广泛用于HBV感染患者的筛查和诊断。新型的Anti-HBc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检测法可以对血清中Anti-HBc水平进行定量(qAnti-HBc)。既往在多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中发现,CHB患者治疗前qAnti-HBc水平能独立预测抗病毒治疗诱导的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血清学转换,而且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的患者其基线和治疗各时间点的qAnti-HBc水平始终高于未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患者[4]。HBV DNA定量水平越低者,其qAnti-HBc水平越高,而HBV DNA定量与ALT水平之间不存在此种关联[5-6]。由此可见,qAnti-HBc水平是反映CHB患者体内针对HBV免疫控制能力的指标。此外,qAnti-HBc水平还与CHB患者对核苷(酸)类似物(NAs)治疗后的反应有关。较高的qAnti-HBc水平与停止NAs治疗后较低的肝炎复发风险相关联[7],提示qAnti-HBc水平对筛选适合停止NAs治疗的CHB患者具有指导作用。这些研究均表明,qAnti-HBc指标具有应用于CHB患者管理的潜在价值。
(二)免疫细胞亚群 慢性HBV感染者体内存在免疫功能紊乱,不同免疫状态的患者外周血细胞亚群有不同的变化,这对了解患者免疫状态、疾病进展有一定临床价值。在CHB患者免疫清除阶段,外周血CD8+T细胞表面的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表达显著增多,CD4+T和CD8+T细胞PD-1的表达水平与CHB患者体内病毒载量和肝功能有关,随着HBV感染进程发生改变[8]。HBV感染急性期未被完全清除继而转为慢性化感染,NK细胞活化性/抑制性受体发生平衡对调[9],分泌干扰素(IFN)-γ功能下降[10],使HBV持续复制。研究表明,阻断NK细胞的表面抑制性受体NK细胞凝集素样受体亚家族C成员A(NKG2A)与人类白细胞抗原-E(HLA-E)的相互作用也许会成为治疗HBV慢性感染的有效手段[11]。我们的研究发现,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滤泡辅助性T(Tfh)细胞频数增多,替比夫定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的CHB患者外周血Tfh 细胞频数增多,并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IL)-21,促进B细胞分化为浆细胞产生HBeAb,从而有利于HBeAg血清学转换[12]。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慢性HBV感染中,肝内CXCR5+CD8+T亚群比外周血同类细胞具有更强的抗病毒效力,提示该亚群可能作为CHB潜在的治疗靶点[13]。
(三)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 研究表明,急性感染中部分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与HBV特异的杀伤性T淋巴细胞活化相关;而在慢性感染中,抑制性细胞因子参与HBV特异性免疫细胞的耗竭,导致无法有效清除病毒,因此通过对各类细胞因子的研究有助于为抗病毒治疗提供潜在靶点。白细胞介素是一类能广泛调控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细胞因子。其中,IL-6是一种能影响各种淋巴细胞功能、具有多态性作用的细胞因子,HBV利用IL-6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癌的发生,同时IL-6也能通过多种机制对HBV复制发挥抑制作用[14]。此外,IL-21也是一种具有多态性作用的细胞因子,IL-21能促进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增殖能力,抑制PD-1和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等抑制性分子的表达[15],并通过抑制IL-10的分泌来抑制HBV的复制,但IL-21的过度持续性炎症反应会导致肝脏损伤和肝细胞癌的发生[14]。IL-21在HBV感染的发病机制和预后中具有多重价值,能够为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更多研究方向。IL-35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细胞因子,不仅具有直接抑制效应性T细胞反应的能力,还能通过刺激产生表达IL-35的诱导性调节性T细胞(Treg)亚群促进其调节作用[16],导致病毒的长期复制和存在。除了细胞因子,趋化因子也参与介导抗HBV的特异性免疫反应,部分成员具有判断停止抗病毒治疗后肝炎复发或HBsAg转阴结局的临床应用价值,并可能作为CHB治疗的靶点。我们团队研究发现,趋化因子CXC配体13(CXCL13)能募集CXCR5+细胞到肝内发挥抗病毒作用[13]。此外,CHB患者停止NAs治疗时高CXCL13水平和停药后获得HBsAg消失结局有关,表明CXCL13可以作为NAs停药后持续应答的预测因子,用于指导CHB患者的停药管理[17]。
三、免疫生物标志物在CHB管理中的挑战
CHB患者的抗病毒免疫力无法通过患者的肝脏生化或病毒学指标直接评估。例如,肝内HBV特异性T细胞水平与肝脏的炎症状态无关[18]。在HBeAg阴性的CHB患者中,虽然外周血中的核心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和聚合酶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频数与病毒载量成反比[19-20],但是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CHB患者外周中的HBV特异性T细胞总体水平接近[21]。抗HBV的免疫能力也和HBsAg水平无强相关性,HBsAg特异性B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与血清HBsAg水平无关[22],而HBsAg特异性T细胞水平则可能与感染时间呈反比,与HBsAg水平无关[21]。值得注意的是,HBV特异性T细胞的能力也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宿主抗原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23-24],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难以利用HBV特异性的免疫学参数来对异质性的CHB患者群体进行定义和分类。因此,CHB患者的免疫生物标志物水平在治疗中产生的变化仍然具有未知性,需要结合纵向研究和实际治疗病例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
此外,免疫生物标志物的检测需要高度专业化的人员和设备,检测方法的复杂性也阻碍了免疫标志物在慢性HBV感染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对此的解决思路可能在于开发更适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更容易和更广泛地测量CHB患者的免疫学参数,以减少所需的精度和特异性。最近针对SARS-CoV-2的研究表明,开发快速且易于操作的检测方法具有可行性,比如直接SARS-CoV-2抗原诊断试验使个人自我管理成为可能[25],在外周血中可以直接快速测量SARS-CoV-2特异性T细胞功能[26]。因此针对HBV感染开发快速、易于使用且标准化的免疫学标志物检测方法是未来的关注点。
四、 结语
免疫生物标志物已广泛用于预测慢性HBV感染患者的治疗效果和评估预后,也为探索HBV感染的免疫机制提供了参考,但免疫学检测的复杂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免疫生物标志物在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应用。因此,目前将免疫生物标志物标准化应用于临床CHB患者的管理仍是较为困难的工作。未来需要统一免疫检测流程,寻找简化检测试验的技术方法,减小检测的复杂和困难程度,降低免疫标志物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条件和门槛。此外,免疫生物标志物在HBV感染中的相关功能和机制尚需深入阐明。开发新型的免疫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疾病的进展和治疗的效果,也能助力新治疗药物的研发,实现慢性HBV患者的临床治愈。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