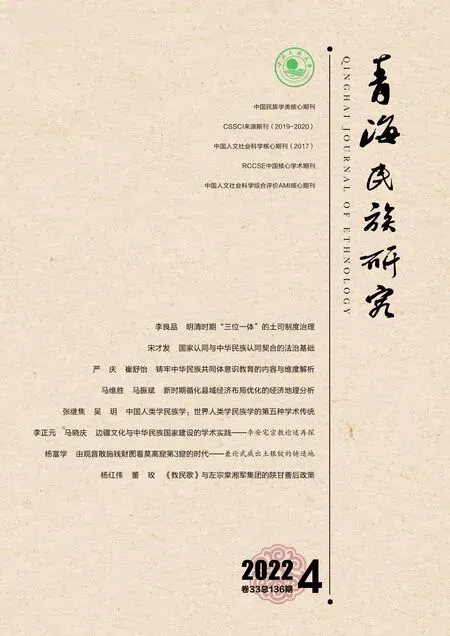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
——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吴金庭
(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清代“湖南苗疆”或者“楚南苗疆”的地理范围,与现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本一致,一般称之为“湘西苗疆”。①清代“改土归流”前后,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湘西苗疆,土司、流官、民间力量等多种势力在山箐相连、以高山深壑为屏障的特殊地理环境中长期并存,造成了这里解决民间纠纷的机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民族性。对于湘西苗疆这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学界主要是关注民族习惯法“苗例”与清政府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认为清政府在对苗疆实施“抚绥”政策时,基本上采用“苗例”来处理苗民内部纠纷,部分学者则主要探讨清朝法律在苗疆的运作情况。②显然,这些研究既未触及到清代湘西苗疆民间纠纷解决的机制,又没有深入到清朝在民间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渗入及其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有鉴于此,笔者拟区分“改土归流”前、“改土归流”到“乾嘉苗变”、“乾嘉苗变”直至清末等三个阶段,探讨湘西苗疆在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以及清政府如何加强对湘西苗疆的社会控制并稳定苗疆社会秩序,最后促使苗疆地区走向“化内”,③期望能对当今加强地方民族区域治理、促进民族团结提供必要的例证。
一、“改土归流”前:以民间力量与“苗例”解决民间纠纷
“改土归流”前的明代和清初,解决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侧重点存在着差异。具体而言,明代主要是借助民间力量解决纠纷,而清初则以“苗例”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
(一)明代借助民间力量解决纠纷
湘西苗疆习惯于“聚族而居”,这在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中有所反映。“散处山间,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者谓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1]在此,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湘西苗疆,不属于“熟苗”而属于“生苗”区。据苗族学者研究,“至明末清初,湖、贵、川三省‘红苗’中,仍被视为‘生苗’,弃之于‘化外’的,只是聚居于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地方,即今贵州松桃自治县和湘西自治州凤凰、花垣、吉首等县市及邻近地区的苗族。”[2]这一方圆数百里地方,在明代分属永顺、保靖两宣慰司管辖,永保土司对“生苗”的防范也有分工。“明时镇苗属镇溪所管抚,令永顺司担承;竿苗属筸子坪长官管抚,令保靖司担承。”[3]尽管永保土司对湘西苗疆具有“担承之责”,但“无论郡县时代,还是后来的土司时期,湘西‘苗疆’实际上均未进入有司的管辖之下”[4]。正因为如此,明代《教民榜文》和里老制在湘西苗疆没有能够推行,“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行头’,以讲曲直”[5]。
在这里,“行头”的身份当与百户、里老相似,在他们主持之下,理亏者以“牛马为算”进行赔偿,否则,民间纠纷往往升级为仇杀。“(苗)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仇,必报当而后已。否则亲戚亦齗齗助之,即抗刭不悔,谚云:苗家仇,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6]对于这种争斗仇杀,明朝流官政府也并非放任不管。据清人毛奇龄《蛮司合志》记载,万历年间,腊尔山草坪苗石篡禄与天星寨、龙集寨苗民吴天保等,斗殴杀人,官府虽然几次召集这三家苗寨解决争斗但都呼之不来,百户黄钟音等人前去询问,却遭到苗民抗拒,“黄钟音叱之曰:‘尔辈欲反矣!石篡禄杀吴顺保,不过输银五百两,贳其死。’”[7]从该记载可知,在土司的松散管辖之下,石篡禄在湘西苗疆杀人,只要赔偿五百两银子,就可以免死。正因为此,只要民间纠纷不涉及民人区域社会的稳定,官府几乎任由苗疆民间力量来处理。
(二)“苗例”成为清初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湘西苗疆先后建立凤凰、乾州两厅,其势力随着对腊尔山台地的不断征剿开始渗入苗疆腹地。由于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苗疆是新辟之地,因而,行政管理虽然纳入到了政府体系但政府势力尚未完全渗入。“其(保靖土司)所辖竿子坪、五寨二长官司虽名义上已于康熙中后期归流,改由厅官管理,但实质上仍受保靖土司控制,甚至为土司后援力量,清朝仍难以深入,无法如其他正常州县一样建立基层管控体系。”[8]这也就是说,这时的土司仍在军事上监控苗疆,主要承担镇压苗民反抗之责。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国家法律在融入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比较注重苗疆习惯法“苗例”的运用,“将正式审判与民间调解相结合,乃是清代乃至今日中国民事纠纷处理的一大特色”[9]。清政府在处理一般民事纠纷中基本上是遵从“苗例”,这在当时的政书中有所体现。“康熙四十年(1701年)覆准熟苗、生苗若有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10]所以说,“苗例”在苗疆纠纷解决机制中,成为维护苗疆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
由于纠众仇杀、伏草勒赎等命盗案件严重扰乱苗疆社会治安,危及清政府的苗疆治理秩序,因而,清政府有时严格按照内地“官法”处理类似案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戒苗条约》中规定:“尔杀内地一人,我定要两苗抵命,尔掳内地一人者,我定要拿尔全家赏还。”[11]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湖南巡抚赵申乔在《苗边九款疏》中奏称:“苗民盗窃及抢夺杀伤等事,俱应照内地州县命盗之例。红苗捉人勒赎之例宜严。”[12]雍正五年(1725年),湖广总督傅敏在上奏的《苗疆要务五款》中提出:“请自后凡有勾苗杀掘等事,务必将行凶之苗,严拿正法。地方官如有惮于拿苗,但据仇贴勒赎者,以不职例参处。”[13]从以上三则材料来看“官法”,清政府对苗人窜出苗疆杀掳客民,惩罚极其严重,对于“行凶之苗”随时潜入内地丢放仇贴勒赎、断棺取颅等恶习,不仅要求杜绝而且严令地方官务必督管。
由上可知,改土归流前,流官和土司对湘西苗疆的最初管辖几乎流于形式,王朝势力未能真正实现对苗疆的治理,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为主。到了清初,虽然清政府势力已经开始深入苗疆,建立厅行政机构施以管理,并借助土司力量加强对苗疆社会控制,但在民间纠纷解决中仍以“苗例”为主、“官法”为辅。“官法”对苗疆“捉人勒赎”等恶劣行为采取严惩态度,这就有效稳定了新辟苗疆的社会秩序。
二、从“改土归流”到“乾嘉苗变”:官法与“苗例”的结合
土司制度发展到清初弊端百出,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了清朝的国家一体化进程。“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14]为此,清政府从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在湘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永保土司地区被改设府县,湘西苗疆完全进入流官治理时代,社会控制被空前强化。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处理苗疆纠纷时,不断地将官法与“苗例”结合起来,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倒骨价”抑止“打冤家”,使“苗例”成为官法的重要辅助。
(一)以“倒骨价”抑止“打冤家”
“打冤家”是湘西苗疆中强势好斗性格的必然反映,这在田汝成《炎徼纪闻》中就有记述。清代改土归流后,当地《厅志》对之记载尤详:
红苗轻生善斗,好寻旧怨。睚眦之隙,动至操戈,非排解稍释,往往相寻不已。或强弱势悬,贫富不敌,蓄愤积怨,虽久必报;或暂时相避,俟势均力敌,怂恿有人,遂纠众持械,拼命穴斗,谓之打冤家。[15]
如有仇雠,则树木为志,累世不解,或现在强弱势悬,贫富不敌,蓄愤积怨,虽代更必报,或暂进隐忍,俟至势力敌,追忆前事,约集党羽,宰牲置酒,为所约者食,其碗酒块肉,虽致死杀伤,断无后悔。遂执器械,披牛皮,挨命穴斗,斗时无行阵队伍,彼此休土堆石块后,以鸟铳相击,执杆抢,持利刀,蜂拥豕突。倘前一人受伤,众皆奔散,故胜者欢旋,败者鼠窜,若正斗之时,虽官司差拘,莫能勾摄;既斗之后,败者犹再纠合别寨亲党,复往厮斗,迨力斗不胜,然后向官,其蛮劣如此,今此风亦渐杀矣。[16]
其实,在上述“打冤家”的场景中,乾隆朝记载的“今此风亦渐杀矣”未合历史事实。嘉庆七年(1802年),湖南巡抚高杞在《苗案请照例完结疏》中仍在提及乾(州)、凤(凰)、永(绥)三厅的苗人命盗之案,认为“打冤家”有三种情况:“一种则系确因彼家果曾杀害此家之人,互相报复......。又一种则系实有远年之仇,苗记刻木......仍图乘机报复,彼此互杀,亦复辗转不休。更有一种则或因利所有,或因忿成恨,戕杀之后,借口有仇。”[17]当时参与打冤家的“党羽”,又叫“帮兵”,人数较多,“亲朋或数十百至”。他们既有族人、亲戚,亦有一部分是欠账的佃户。“苗寨中富民放账,其息甚大。......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18]可见,带头组织“打冤家”的基本上都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有地位有实力的富民,不然是难以组织那么多人去充作“党羽”。
类似“打冤家”的仇杀难免会有人命案件发生,如果不给予妥善解决,则“往往相寻不已”,造成“常时出门辄挟刀枪以防格杀”局面。这不利于苗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各苗寨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此,其解决方式就通过“倒骨价”赔偿来实现。“其被伤死者,即行掩埋,不以告官;官知而往验,亦不告以葬所。两家战斗之后,计尸以相抵,除一命一抵外,多尸者为人命,则索牛马财物以偿,谓之倒骨价。其价则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则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其中老牛瘦马破衣旧物,俱可抵算。”[19]仇斗双方情愿用“倒骨价”来解决,原因是:“以为一经官验,则鬼反其室,举家俱有灾祸也。且其性贪鄙,只愿得财,不愿偿命,纵力凝招抵,彼以为又杀我一人,仇杀相报终无已时,必解释排结,方可相安。”[20]解决“打冤家”的办法,首先是通过讲和,然后是以财物赔偿了结。“仇杀相报,终无已时,必解释排结方可相安。故浼人解纷曰‘讲歹’,以财货酬死者之家,曰‘倒骨价’。其主盟之人,曰‘背箭’,和处之人,曰‘牙郎’,又曰‘行人’。”[21]可见,双方要“解释排结”实现财物的赔偿,离不开“背箭”和“牙郎”这两个关键人物。“排解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牙郎,也就是排解讲和之人,此人一般是苗目,在当地具有一定权威。”[22]也就是说,“背箭”和“牙郎”是当地苗寨有影响的人,否则无法召集仇斗双方坐到一起来谈赔偿最后达成协议。
“打冤家”固然是明显的凶杀刑事案件,但“杀人偿命”的刑律在清代苗疆却不能实现。在“背箭”“牙郎”的处理下,它最终以经济赔偿的“倒骨价”作为解决争斗的唯一方式。“倒骨价”赔偿的财物不菲,苗民赔偿后往往会倾家荡产,但这种惩罚相较于官法的制裁却是苗民情愿采纳的。通过“解释排结”后,苗疆“仇杀相报终无已时”的局面得到解决,苗区社会终于“方可相安”了。“这种自愿原则的确立,既立足于苗民对本民族这种风俗习惯的心理认同,又充分考虑到苗民文明程度的发展对其接受内地法制态度的影响,这是十分高明和有益的。”[23]
(二)“苗例”成为官法的重要辅助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湘西苗疆设官驻兵、编户课赋和开办义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强化了对苗疆的治理。清政府在处理苗疆纠纷时,不断将官法与“苗例”结合起来。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二十日,乾隆帝对贵州等新改土归流的“苗民”谕旨中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之以官法。”[24]如果说以上那些是针对贵州新开苗疆的话,那么,乾隆五年(1740年)正式颁布的《大清律例》中的有关“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之以官法,以滋扰累”[25]的规定,则是对全国范围内苗民争讼的法律规定。乾隆九年(1744年),湖南巡抚蒋薄陈奏抚苗事宜,要求在湘西苗疆处理民间争讼亦可按照“苗例”:“令苗人遇有户婚、田土、忿争细事,只令报官,许该处寨头甲长等,照苗例处理,乃以苗治苗羁縻之法。”[26]军机大臣等回复同意照此执行。可见,苗疆民事纠纷基本上都是以“苗例”为依据解决,“官法”很少介入。
由于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是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新开发的“新疆”,因而,清政府为加强湘西苗疆的治理,对于命盗刑案的处罚力度是比较大的。乾隆朝《大清律例》之《刑律·贼盗下》规定:“凡苗人伏草捉人,横加枷肘,勒银取赎者,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臂膊刺字。再犯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27]审判命盗案件,直接交由省级司法部门来完成,道一级地方官府只负责勘查案情。“湖南省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命盗案犯,由厅径行招解臬司审转,毋庸解道。其秋审人犯即责成不由审转之该管本道亲历复勘,遇有异同仍遵定例办理。”[28]案情出现“异同”,则遵“定例”。具体就是,命盗案件在实际操作中亦有折中处理方式,苗人双方如果情愿在经济上用“倒骨价”处理,官府不予干涉;苗人实在不愿以经济赔偿,则由官府按官法办理。乾隆二年(1737年)湖南巡抚高其倬上疏言:“乾、凤、永三厅,苗人杀死汉民,自应照例办理......嗣后苗杀民人,及苗杀苗,而苗不受骨价欲求追抵者,仍照例究抵正法,如两造情愿得价完结者,请准照苗情办理,得旨:依议。”[29]在这里,清政府首先依据的是“苗例”,以“苗例”解决方式为主,最后才是按照官法“究抵正法”。
综上可见,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这一时期,“苗例”之中,主要以经济赔偿的“倒骨价”抑止凶杀刑事案件“打冤家”。由于清政府在湘西苗疆建立厅县,实施流官管理,因而,“官法”开始在苗疆得到执行。尽管如此,清政府在处理民间纠纷甚至命盗案件时,还是充分考虑“苗例”的作用,“苗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法”处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在苗疆尚未被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发挥了稳定苗疆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三、“乾嘉苗变”直至清末:发挥乡约和神判的作用
“乾嘉苗变”后直至清末,湘西苗疆的社会自我约束力明显增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社会依据乡约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神判变成苗疆民间纠纷解决的最高形式,寨长、乡老和族长协助苗疆民间纠纷的处理同时,主要依托苗官制维护苗疆社会秩序。
(一)依据乡约处理苗疆民间纠纷
从顺治九年(1652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近240年期间,清朝共颁过乡约谕旨32道,足见政府对于乡约的热心提倡。[30]“乾嘉苗变”后,清政府为了推进苗区的儒化,加强对苗疆的治理,在苗地大力兴办义学、义馆。道光和咸丰两朝,绅士势力开始兴起和发展,苗疆乡绅群体开始出现,他们在乡约的制定上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道光三年(1823年)古丈坪厅的《蓄禁桐茶碑序》具有较大影响。
兹者公议,自今以始,当一体遵议款之条,共保地利:有私伐桐茶之木者,无论贫富,悉罚钱三串文;至于杂木果树有砍者,罚钱一千文,其所罚之钱充入公会,以修道路之崎岖;捡茶捡桐亦有定期,不准先后参差,若有暗行捡摘者,应罚钱二千文,与守桐茶杂木之人食用;故于桐茶将登之时,每派八人守之,一方二人,以锣击之,日夜严防盗窃;摘捡之期,必过寒露之后,乃准捡摘,盖取桐、茶子米内多油故也。[31]
湘西苗疆盛产桐茶,桐茶是苗民们换取盐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物品,故有保护桐茶树和防止过早捡摘、偷采桐茶之事发生。在当地乡绅组织下,“村人公议,学生杨延康抄呈”,制定上述蓄禁桐茶约并立碑以示。碑文内容详实,处罚标准体现了公平公正,罚钱的使用去向明了,防范措施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由乡绅提倡村民合作制定的乡约,以光绪三十年孟夏月(1904年4月)凤凰厅的《唐家桥修筑担水江水圳章程碑》具有典型代表性。该章程是由光绪年间考中秀才的乡绅龙凤翔倡导、苗民积极响应而制定的乡约。章程共有十条,主要为以下五条:
一、工程浩大,筹资实难。拟中田一挑,出小工一个,钱十文;下田一挑,出小工二个,钱二十文。计亩匀摊,以示均平。
一、圳水长远,架枧筑堤,朝盈夕涸,易致朽坏。每年议出理水谷七石,妥雇一人理水,以专责任,俾免朝盈夕涸之害。
一、田有中田,有下田。中田十挑,每年出理水谷六升;下田十挑,出理水谷一斗二升,以分中下,俾顺群情而惬众意。
一、所议理水谷,通盘合算,不止七石,且有荒地待开田丘,照章匀派数尚未定,除七石雇人理水,其余作为逐年修圳之资。
一、理水灌田,务要相匀,不得恃强欺弱,妄行滋事,违者共同率究,以平事端,俾沾实惠。
龙凤翔龙子福率同众业户立光绪三十年孟夏月吉日[32]
龙凤翔系凤凰厅上苗乡唐家桥苗寨人,平时“排难解纷,累息争讼,乡人德之”。[33]在龙凤翔的影响和组织下,这个章程将在修筑担水江水圳时可能出现的难易、贫困、丰歉、里水谷抽取等方面都基本上照顾到了,处处体现了“和谐”“公正”的思想。该章程制定出来后,必会成为乡民遵守的乡约。
“乡约制度是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制裁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34]“在乡村实行的一种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规约和组织形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可以填补法律与乡村习俗之间管理的真空,成为法律的必要补充。”[35]梁漱溟认为,乡约可认定为一个“地方治体”,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自治组织”。[36]通过前人的这些探讨可知,乡约属于苗疆乡村社会的习惯法,是湘西苗疆苗人解决争讼的规范,在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苗疆社会中可以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
(二)寨长、乡老和族长协助苗疆民间纠纷的处理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苗疆的控制,将各苗寨编入里甲,在苗寨内广设如同内地里正保甲的百户寨长。“乾嘉苗变”后,统辖苗寨的主要是寨长,“其尊者只寨长,否则曰头人。”[37]这些寨长的形成已有变化,主要依靠势力担任,它在严如熤《苗防备览》中记述详尽。“生苗各分寨落,在松、永、乾、凤交界地者,地势毗连,犬牙相错,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府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此一户一人,则又各自畏党。故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递变易,不能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38]可见,寨长不仅势力大而且会讲客话(汉话),与土民客人交往比较多,在苗寨里算是见多识广之人,故而其在处理苗疆民间争讼上具有很大权力。《古丈坪厅志》中记述:“遇有争斗之事,客总寨长可为之排难解纷,一涉讼庭,亦为之备质作证。此等人既无功名,亦非殷实,其贤否未可知,惟听乡人之爱憎而已。”[39]由此可知,寨长不一定是富苗,也不一定具有贤德,但是由于其在寨中负有威望,因而在苗疆处理民间民事纠纷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寨长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往往会有德高望重的乡(寨)老等人参加,并没有采用一言堂的独裁方式。乡老之中不乏有一部分是富户、读书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道光十三年(1834年)处理在凤凰厅落潮井发生的庸医杀人案,充分体现了乡老在处理纠纷中发挥的作用。
庸医孙仲吉,系宝庆府人氏,为自悔戒后事。情因予虽习痘疹医理,但辩方识症尚未精通,故以疑似用药,未免有与反症之弊。今有落潮井向姓之子国蕃出痘,先有胞弟孙仲祥调治,尚未平稳。后予于铜回家,未经向姓所请,遽尔自望送药,不意毒集于口,瘀肿益甚,续后命终。向姓不能无疑,即欲鸣官勘验药物。予恐庸医误人之罪法所不容,只得请动乡老、场头大旂稿公,于中排解,又幸得向婆恺恻,共息此事。自此以后,再不糊乱下药妄治,如有此情,任凭送官惩究。故愿立碑记,以悔前愆。以为后戒云。
道光十三年三月日立排解人陈自文聂明久韩秀韩仲榜吴廷栋[40]
该碑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将整个事件记述详细。这里的“庸医”孙仲吉,可能是受弟弟孙仲祥之托前来医治向国番,谁知向国番病情加重竟死掉了。向家准备告官,按照《大清律例》之“庸医杀伤人”规定,轻则“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重则“故用反症之药杀人,斩监候”。[41]孙仲吉害怕受法律制裁,只好委托乡老出面排解。向家没有告官,最后以孙仲吉立碑为戒告终。尽管碑记没有记载赔偿一事,但按照常理,估计孙仲吉的赔偿费和邀请排解费亦不菲。
与土家族、汉族地区普遍建有祠堂、修族谱相比,湘西苗疆的宗族制度不仅发展晚而且发展慢。④“至明中期,宗族制度已在苗疆土家族中得以确立。”[42]之所如此,是因为苗区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不高,而土家族地区一直处在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清初苗区虽有宗族观念,但宗族制度却未能建立起来。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同时要求在聚族而居地区设立族正,负责宗族内部治安。“这一法令立法原意是在保甲制不能施行的地方实行,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能有管制不到的村落。”[43]改土归流后,苗疆宗族权开始发展起来,“此时的宗族领袖(及管理人)凭借宗族的实力,逐渐在村社区里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当他们对内行使权力时被称族长(或宗族其他名目管理人员),与政府及外界交往或对话时,他们多被称为寨长、里(寨)老等等。”[44]乾嘉苗变后,清政府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湘西苗疆普遍设立义学,苗民开始具有宗族意识,宗族制度有所发展和加强。清中后期,出现了一部分苗秀才、苗举人、苗进士,他们中的大族开始纂修族谱,那些族长成为与寨长、里老一道处理纠纷的重要力量。清末,古丈、永绥两厅苗族大姓所修的《龙氏族谱》,制定了宗族间族人处理纠纷的族规:
解斗争:凡族间有因田水利钱谷之类互相争竞,许其人各具本情始末,开单赴投族长,不得任气角力,互相斗殴,经扰官司,援引他词以相罗织。族长体惜真情,从公剖决,毋得徇情颠倒,以淆是非。[45]
在这里,“解斗争”虽然寥寥几句,但是对于族人间的纠纷调解处理程序和要求,却说得明白清楚。它要求双方写清纠纷的始末,然后再到族长那里由族长秉公断定;断定时,纠纷双方不准因斗殴而引起官司,进而给那些讼师随意罗织讼词有可乘之机;解纷的族长,必须根据真实情况公平公正处理,不得徇情颠倒黑白。从《龙氏族谱》族规的内容可以看出,族长不仅掌握着宗法权,而且在处理族人间纠纷上具有一定的司法权,扮演着法官的角色,起着维系和稳定宗族间社会关系的作用。虽然宗族处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宗族在农村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能影响社会秩序:是稳定,抑或制造混乱。它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治理者努力与它处理好关系。”[46]
(三)神判变成苗疆民间纠纷解决的最高形式
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是清代湘西苗民的主要宗教崇拜方式,宗教往往与巫术掺杂在一起。“湘苗的巫术大多已进而为宗教的行为,巫术已失去实用的效力,而宗教尚带有巫术的色彩。故湘苗的宗教,可称为巫教。”[47]由于“苗人畏鬼信巫”,因而,很多巫教活动几乎都与鬼神有关。“苗乡鬼神类多,有谓三十六神,七十二鬼。此系约数,实尚不止矣”;[48]“苗人神鬼不分。......其惟一方法,便是乞灵于有超自然能力的鬼而祭鬼。”[49]
正是在“巫教”基础上,产生了湘西苗疆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神判”。“神判”主要有“诅誓”“摸油锅”“踩铧犁”“吃血盟誓”等类型。其中,“吃血盟誓”乃是“神判”中解决纠纷的最高形式,解决场所一般选择在天王庙。“天王神之庙院乃苗乡大理院。苗民两造争端,是非莫辨或遇冤不能自白,即至天王庙吃血设誓,无论大小讼案,当可立决。”[50]“吃血盟誓”时,原被告双方邀约亲朋好友前往天王庙,被请来的苗巫师主持仪式。对此,清中后期的苗疆各厅县志记载尤详,如道光版《凤凰厅志》:
遇有怨忿者,必告庙誓神,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谓之吃血。吃血后三日必宰牲酬愿,谓之悔罪做鬼,其入庙则必膝行,股悚莫敢仰视。抱歉者则巡不敢饮。其誓必曰:你若冤我,我发大旺,我若冤你,我九死九绝。犹云祸及孙也。远不能赴庙者,建拜亭于路前盟誓。舆骑边亭必下,尊之至也。事无大小,吃血便无翻悔,否则官断亦不能治,盖苗人畏鬼甚于畏法也。[51]
此种天王庙“神判”可以说是终审,具有无上的权(法)力。“诣神庙互誓以此为最终审,而依法上诉者寥寥可数。良以迷信特深,视神所决定为至公且允也。”[52]需要指出的是,“神判”一般用来解决无证据的纠纷,这种纠纷即使官府来断案亦无从下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王神”在苗民心中始终是极其威严且神力广大的,该“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53]“神判”一方面利用苗人“畏鬼信巫”的心理使理屈者不敢蛮横无理,另一方面杜绝人为断案所带来的偏袒,从而使苗疆社区秩序能长期有效地得到维持。所以有人说,“苗族神判”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法”的概念,这是苗族早期认识观上的一大进步。[54]
“神判”方式从心理上可以使理屈者屈服,为民间无证据纠纷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渠道,但因为不科学,必然会造成一些冤案发生。道光九年(1829年),清政府改定“苗例”,要求苗人命案均照民人例办理,但是直到民国初期,湘西苗疆地区一些村寨在处理民间纠纷时继续沿用部分“苗例”,人神结合依然是苗民首选的解决机制。

清代湘西苗疆设立苗备、苗弁
(四)依托苗官制维护苗疆社会秩序
“乾嘉苗变”之后,清政府为加强对湘西苗疆的社会控制,除了设卡修堡、屯田练勇外,还实行“以苗治苗”的政策,建立非世袭的“苗官制”。“苗官”又称“苗弁”。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上奏《苗疆善后章程六条》,首倡撤换汉人百户设立苗官;接着,部复《苗疆紧要善后事宜咨》的“苗疆百户寨长名目应酌量更定一款”,明确要求设立苗官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此次随同官兵打仗出力,给予翎顶之各降苗甚多。即于此内择其明白晓事、众所推服者,照各省土官之例,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惟土守备,守备之下酌设土千总、外委等员,俾令管束苗民。其额数照所管之寨落多寡设立,仍由督抚衙门给札点充,并归地方官钤束。如有苗民格斗、窃盗等事,即着落该土弁等缉拿办理。”[55]
苗官分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四个级别,最初是从降苗中选择那些“明白晓事、众所推服者”为之,设立之初的职责是统帅苗兵、管辖苗寨,又兼缉拿办理刑事案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朱绍曾在《详明屯守备经管事宜》中对苗备弁的职责做如下记述:“各厅县苗兵该备等照依详定,分管苗寨,管辖各处集场,务当好为弹压,毋许市侩侵款。倘有奸民擅入苗地,及不肖兵役,私入索拢,立即拿解厅县惩究。......其民苗户婚、田土、词讼及挑丁授田等事,该守备不得干预。”[56]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二十二日,刑科给事中陈岱霖奏苗疆屯防积弊四条中,亦提到苗备弁的职责:“其设立苗守备千把等官,不过令其催取苗租,传唤苗户,所有一切苗词,概不准其擅受,均归该管厅员审理。”[57]从朱绍曾和陈岱霖奏折中可见,苗守备、苗千总、把总等“苗官”主要是统率苗兵、稽查户口和维护苗疆社会治安,实行“湘西有屯七县”屯田后才负责催征钱粮、调派夫役,但对于苗疆民间民事纠纷是不能干涉的。这似乎可以从光绪七年(1881年)凤凰直隶厅同知汪明善陈禀苗疆积弊五端中得到印证:“严谕各营苗备,如遇苗民口角钱债细故,只准从中排解,不准私设公堂,擅作威福,免开索诈之门。倘若排解不下,准即据实申道赴厅,以凭传讯。”[58]
事实上,苗备弁等从道光朝开始,并没有认真执行清政府给予他们的职责,苗官干涉民间纠纷之事,时有发生。正如萧公权所说的:“因为居民没有为官府效劳的意愿,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不如官府期望的那么强,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积极利用基层政治治理体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而不是为皇家服务。”[59]苗弁们经常利用身份之便,干涉苗疆的民讼,趁机为己谋利。这就造成苗疆社会的不稳定,引起中央官吏几次上奏汇报,要求地方督抚等官加强督查和治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二十二日,刑科给事中陈岱霖奏陈苗疆屯防积弊四条中之“苗官宜严加约束,以恤穷苗”提到:“乃闻今日该苗备弁,妄自尊大,私役苗民,开垦田土,遇有苗词,先行收审,横加需索,并私设刑具,任意凌辱。”[60]陈岱霖所述苗官等人在苗疆干涉诉讼的现象,应该较为普遍。据此,湖广总督裕泰、湖南巡抚陆费瑔于八月初一日具折会奏:“嗣后该苗官等,如有擅受苗词,私设刑具,横索苗钱等事,由该督等饬属随时查拿,从严惩办。”[61]十月二十六日,道光帝批复:“依议。”由此,一批苗官遭到革职。“各苗备弁内,前有守备梁开科,千总吴老吼、欧通帼,把总龙老巴,外委龙隆景、石添荣、廖老仡等,因约束不力,不治舆情,俱经斥革另补。”[62]可见,这些苗官被革职,除了治安不力外,当中难免有干涉苗讼的原因。
综上,“乾嘉苗变”后,清政府在苗疆解决民间纠纷时,继续遵循“苗例”,发挥乡约的约束作用,重视寨长、乡老和族长等民间力量。由于苗民信巫好祀,心理上崇拜鬼神,因而,更愿意在解决无证据纠纷时融入神明来做裁判。加之,该方式富有成效,因而得到官方的默许得以实行。由此,“苗官制”成为流官制的重要补充,苗官成为苗疆社会基层管理者。为了稳定苗疆社会秩序,清政府对于苗官处理民间纠纷,执行的是严厉的管理政策,尽管准其排解,但严禁他们插手干涉诉讼。这样一来,民间调解机制相比官方渠道虽然程序众多、耗时长,但是更易成功、见效快,恰好是苗民和清政府双方都能接受的。在这种机制之下,苗疆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结 语
改土归流前,湘西苗疆名义上处于流官和土司的管辖之下,明代和清初在借助土司力量加强对苗疆社会控制的同时,对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这一时期,随着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建立厅县,实施流官管理,“官法”开始在苗疆得以执行。乾嘉苗变后至清末,清王朝加强了对苗疆的社会控制,但湘西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苗例”成为苗疆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清朝为了有效统治苗疆,既考虑了苗疆的民族习惯,又融入了国家法律,特别是在处理窃盗杀人等刑事命案上,清朝有时遵照“苗例”,但更多的还是按照“官法”来办理的。就清代湘西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考察,民间力量的强势要大于官府职能,民间调解机制相比官方渠道的程序众多、耗时长,更凸显其易成功、见效快特点,这恰好是苗民和清政府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三阶段历史表明:清政府治理苗疆既考虑了苗疆的民族习惯又融入了国家法律,官府在解决湘西苗疆民间纠纷过程中,充分借助了民间力量,表现出了官民结合的特色,它所形成的多元性机制在苗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苗疆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既有效地化解矛盾,维护家庭、家族、邻里之间的和睦,又分流案件,减轻国家司法机关的负担。清政府就是在“苗例”与“官法”的治理结构中,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的社会控制,使湘西苗疆完全融入到国家一体化建设之中。如此,“民苗为二以相安”局势得到保证,苗疆的“失范”得到有效纠正,苗疆社会在走向“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发展,苗疆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它无形之中,不仅促进了苗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又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
注释:
①编撰于道光年间的《苗疆屯防实录》(佚名氏)在《苗疆图说》中将“湖南苗疆”范围界定为:“湖南苗疆,沿边七百余里。凤凰、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四厅一县,控制东、南、北三面。其迤西一面,长二百余里,系贵州松桃厅管辖。统计周围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参见(清)佚名氏:《苗疆屯防实录》,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页。乾州厅、永绥厅、古丈坪厅即现今的吉首市、花垣县、古丈县。
②参见:施青:《试析苗族“神明裁判”与其原始宗教三大崇拜的关系》,《民族论坛》1993年第3期;苏钦:《“苗例”考析》,《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黄国信:《“苗例”:清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龙建明:《苗族解决无证据纠纷神判方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谢小辉:《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州县法律安排与司法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等。
③笔者认为湘西苗疆在清代以前虽然一直处于中央王朝治理版图之内,但其并没有向中央政府输役纳赋,中央政府也没有将其编户入籍,处于一种松散的控制状态,中原文化也没有对苗疆社会产生影响,故而可将湘西苗疆称为“化外”。
④根据笔者对五县市的田野调查,苗族仅有凤凰县千工坪乡通板村在清末时建有龙姓祠堂。据说是该村有两兄弟参加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由军功而为官,长期驻守在湘潭,老年回乡后建立此龙姓祠堂。民国年间曾经在此举行过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山江、腊尔山等地龙姓苗族都派有代表前来参加。此后随着龙家家道败落,未有任何活动开展。该祠堂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现无任何遗迹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