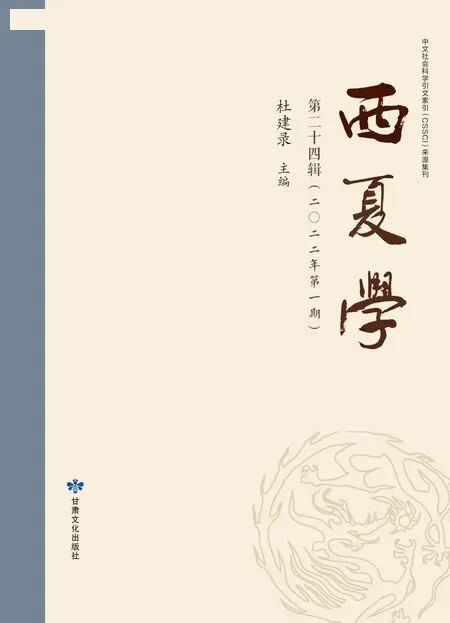文化交融视阈下的11—14世纪河西炽盛光佛信仰探析
张海娟
以往,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炽盛光佛信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唐、宋、明时期,对西夏亦多有涉猎,而于元代则鲜有关注。其中,西夏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相对丰硕,但总体上仍多就文献文物而言信仰,既缺乏系统论述,又欠缺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嬗变考察,以及背景原因探析,在研究维度与构架上仍有挖掘空间。本文即透过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等视角,以11—14世纪河西之地为切入点,采撷相关出土文献与石窟考古资料,希冀窥见这一时期河西炽盛光佛信仰历史面貌,探究其发展嬗变,辨析其信仰宏盛背后之历史文化原委。
一、出土文献所见炽盛光佛崇拜
就佛教典籍而言,与炽盛光佛相关者主要有:唐代失译《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唐代不空译《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唐尸罗跋陀罗译慧琳笔受《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又称《炽盛光佛顶仪轨》)、宋代遵式译《炽盛光道场念诵仪轨》等。迨至元代,高僧释性澄又校订了不空译本①黄璜先生指出唐代失译本形成于8世纪20年代至中叶前,出现最早;而目前所见“不空译本”与敦煌、西夏及大理之藏外经传本皆由其脱文而来,且所谓“不空译”乃是假托,其是最晚出经本,当形成于9世纪晚期至10世纪70年代(972)。黄璜:《〈消灾经〉考》,《敦煌研究》2018年第5期。为了便于论述,本文在此仍使用传统的“不空译本”一说。,且元刊《碛砂藏》又新见收录有《佛说最胜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目前,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相关炽盛光佛典籍主要有汉文《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Дх1390)、西夏文《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调伏诸星宿消灾吉祥陀罗尼经》(Инв.No 5402、Инв.No 7038)等。其中,西夏文本与唐不空译本存在依承关系,乃西夏仁宗校译本;而Дх1390文书概为流传于西夏的一个和不空本稍有差异的汉文本。另外,《英藏黑水城文献》之Or.12380/3182文书亦属于西夏仁宗皇帝校译本,而Or.12380/2845RV写本乃该经另一版本,但尚无法判定是初译还是校译本①张九玲:《西夏文〈消灾吉祥陀罗尼经〉释读》,《宁夏社会科学》 2017年第1期。。
与上述见于汉文《大藏经》收录的炽盛光佛典籍不同的是,在我国西北、西南还流行着另一种未见入藏的《〔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关于其与入藏的两种炽盛光陀罗尼经的关系,一说它是独立的敦煌藏外经②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一说是失译经的简本③陈万成:《景德二年板刻〈大随求陀罗尼经〉与黄道十二宫图像》,载氏著《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中华书局,2010年,第33页;黄璜:《〈消灾经〉考》,《敦煌研究》2018年第5期。。但参照真言格式类型、汉化程度来看,《〔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年代可能早于不空译经与失译经④廖旸:《〈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文本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显而易见,河西出土的炽盛光佛文献版本相对丰富,既有汉文原本,又有译自汉文本的西夏文本(初译本、校译本),以及目前翻译底本尚存争议的《〔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本。它们当为适应11—14世纪河西地区现实的宗教形势,社会环境及僧众需求的产物。
黑水城出土《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刻印本,包括汉文藏外经刻本三种(TK129、130、131)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7—81页;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8—160页。,以及相应的西夏文写本、印本各一种(Инв.No 809、Инв.No 951)⑥Е. И. Кычaнoв: Кaтaлoг тaнгутcких буддийcких пaмятникoв, Киoтo: Унивeр cитeт Киoтo, 1999, cтр. 414.。另外,1983—1984年,黑水城F9和F13遗址又出土了若干与《〔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相关的残页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735、1764—1765、1769、1790页。。就内容而言,上述西夏文诸本较之唐译本,于经文中新加入卷首七言偈、九曜下降日期、真言等内容,删减了正文内容,给人以方便实用之感。就文书年代而言,仅TK129于发愿文后书“乾祐甲辰十五年(1184)八月初一日重开板印施”,时值西夏仁宗在位,而其他文本则无明确年代标识。
另一件元刊西夏文本《〔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则与西夏文不空译本、西夏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译自宋法天汉文本)合刊一册,由斡巴法师于“大朝国庚午年十月二十五日”发愿刊刻①此经于2020年10月17日在北京泰和嘉诚“古籍善本·金石碑版”拍卖专场展拍,网址:httр://auction.artron.net/рaimai—art0091413038。,乃世存孤本。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亦保存有该合刊本之零星残片,惜无款无序,幸而由此可窥黑水城本之一面貌。此元刊本中之“大朝国”为中原汉人、汉地对成吉思汗肇建的“大蒙古国”之习称。忽必烈上位后改国号“大元”,但“大朝”一称仍未废用。推而论之,上文所及“大朝国庚午年”当为世祖至元七年(1270),抑或文宗至顺元年(1330),但又以前者可能性为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献在重新翻译梵文真言时,还加入了藏传佛教“梵文拥护轮”,汉传佛教之紫炁、月孛二曜真言等内容②秦光永:《中西交融与华夷互动——唐宋时代炽盛光信仰的传播与演变》,《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这无疑不昭示了11—14世纪河西地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融摄,西夏佛教文化与元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交融互鉴。
此外,黑水城出土的相关文献还有汉文《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TK—103、TK—107)、西夏文《圣曜母中道法事供养根》(Инв.No 4737、Инв.No 7122)、《圣曜母惣持中围法事》(Инв.No 2552)、《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Инв.No 571、Инв.No 572、Инв.No 577、Инв.No 2528、Инв.No 6484、Инв.No 6879、Инв.No 6541、Инв.No 696、Инв.No 699、Иив.No 705、Инв.No 706、Инв.No 5402)等。上述文献之内容多与密教坛城、经咒等关系密切。显而易见,11—14世纪的河西僧俗大众虽仍延续着前代设坛供养、诵持密咒等传统的炽盛光佛崇拜仪式仪轨,但是却摆脱了以往严格繁复的密宗程式的桎梏,宗教修习与实践日益简洁便利,更趋于功利化和现世化。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学者多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版本学比较研究,及唯一具有纪年的TK129文书,继而推定相关文书皆属西夏时期。然而,事实上黑水城既为元亦集乃路所在,又为元代西夏遗民聚居区,且元朝不仅继续行用西夏文,更曾刊刻、印施河西字《大藏经》。因而,对于没有明确断代标志的西夏文文献,我们不能仅根据其文字一概归入西夏时期。毫无疑问,上述文献当为11—14世纪河西炽盛光佛崇拜的产物。
另外,于敦煌莫高窟晚期石窟第464窟亦出土有炽盛光佛藏外经残片2件,为经折装,白麻纸刻本③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该文献尺寸袖珍,适于掌握,既方便随时礼颂赞叹,更可随身携持避祸趋福④廖旸:《〈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文本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同时,该窟还出土有未完工的二十八宿十二辰木雕板残件,以及元代文献多件。
由是可见,以敦煌、黑水城两地为主的河西地区出土了为数不少,时属11—14世纪的炽盛光佛典籍文献。其不仅数量相对颇丰,且版本、内容亦有所不同。这里既有源出中原本土的汉文传世文本,又有译自汉文本的西夏文本;既有写本,又有刻本印本。而其内容亦不断发生演化,既有删减节略,便于修习实践;又增补充实,广纳汉、藏等多元文化。尤其是鲜见它地的炽盛光佛藏外经文献频繁出土河西,它们可谓是11—14世纪河西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明体现。
二、图像资料所见河西地区炽盛光佛信仰
石窟壁画方面,莫高窟亦可寻觅到11—14世纪炽盛光佛信仰流行的踪迹。其中,有“文殊堂”之谓的第61窟虽开凿于曹氏归义军时期,但甬道却经后代重修,时属敦煌石窟晚期。
该甬道盝形顶,南北两壁皆绘炽盛光佛经变,南壁西端又画一尼像,北壁则绘诸星、僧人等。值得注意的是,甬道两壁炽盛光佛经变并非一致。孙博先生认为其分别描绘了作为主尊的炽盛光佛之出巡与回归的场景①孙博:《炽盛光佛图像的“祠神化”——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中心》,《艺术史研究》第2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沙武田先生则以为该窟为迎、送炽盛光佛的神祠,其甬道北壁为迎接炽盛光佛诸星曜回归,南壁则是送炽盛光佛诸星曜离开本尊道场巡行②沙武田:《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20年第3期。。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但同时也稍有异议。即北壁内容当为供养僧众迎请炽盛光佛前往作为临时道场的第61窟主室,与文殊菩萨一道消灾除障。及“行神”结束后,僧众则奉送炽盛光佛还归本处,此即甬道南壁之内容。对此,甬道南壁炽盛光佛像后西侧所绘的一身面向第61窟主室虔心礼拜的扫洒尼姑像即可为印证。她当负责此次礼拜活动前的洒扫厅堂,严净道场等事宜。于此,借由甬道南北二壁对称绘制僧众迎送炽盛光佛图,以及作为临时道场的第61窟主室,继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炽盛光佛巡行说法、消灾弥难的宗教礼拜空间。
同时,甬道两壁所画的带有显著民间色彩的扫洒尼姑像,以及颇具世俗意味的助缘僧众画像与所书题名则揭示出晚唐以降,不同以往恪守炽盛光佛密教仪轨的传统,举行斋会、图画神形等通行泛化的祈福方式更趋普遍③谢继胜:《扎塘寺壁画法华图像与11—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的重构文殊弥勒、释迦文殊与藏汉佛教义理的图像形成史》,《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且随着炽盛光信仰日趋世俗化,其为个人与地方消灾除祸、追福荐亡的现实宗教功用愈发凸显。由是,第61窟既成了炽盛光佛为敦煌民众与本土地方主除不祥,祈求福祉的临时道场,又满足了供养僧众彰显功德的诉求,继而映射出河西地区炽盛光佛信仰之世俗化、现世化倾向。
另外,扫洒尼姑像右侧榜题框内还书写有回鹘式蒙古文题记,就其字体、词句等观之,颇具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中期回鹘式蒙古文的特征。现据嘎日迪等先生的释读移录于下:
(1)对无边无际的宇宙诉说,放荡鬼怎能有诚心……
(2)出类拔萃的那些好汉们,坚强起来……肯定渡过……
(3)如果不被挑拨诽谤之词所迷惑,怀有信念的……我们
(4)如同镇降妖魔的佛爷那般更加坚强起来
(5)彻底熄灭炽盛的欲望①哈斯额尔敦、嘎日迪、巴音巴特尔:《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回鹘蒙文题记释读》,《敦煌究研》1989年第3期。据嘎日迪等先生所言,第61窟甬道北壁尚还有一则回鹘式蒙古文题记。惜未见有学者著录释读,不得其内容。
就题记内容而言,它确实与甬道所绘炽盛光佛及其护法神、诸星存在某种联系。题记书写者试图通过对炽盛光佛的祈愿,以达到消灾祈福、充实信念的目的。显而易见,元代某时,曾有崇奉佛法的元人前往第61窟顶礼膜拜,并于甬道南壁书写题记,祈求炽盛光佛庇佑。
同时,另一则重要的回鹘式蒙古文题记则书写于该窟甬道北壁助缘僧索智尊与持伞盖侍从之间,记曰:“寅年六月初八日亦仁真王子的使臣帖木儿卜花……僧格为这寺庙积善叩拜而返。”②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其中,“亦仁真王子”当为元代阔端系后裔亦怜真,他又见于《巩昌府城隍庙令旨碑》《元史·世祖纪》③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巩昌府城隍庙令旨碑》,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卷四,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0页;[明]宋濂、王祎:《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等文献,概驻守于瓜沙至哈密附近。至元二十七年(1290),亦怜真曾与诸王术伯、拜答寒共击章吉,当年正为虎寅年④[明]宋濂、王祎:《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恰与上述甬道题记纪年相同。是可推见,蒙古宗王亦怜真概因连年的战事征伐之苦,特令使臣帖木儿卜花前往莫高窟第61窟崇奉朝拜,祈求消灾弥难,避祸趋福。
以往见于莫高窟的炽盛光佛图像,以第61窟为独例,幸而谢继胜先生在对敦煌晚期石窟莫高窟第465窟进行考察时,于该窟再觅其迹。这铺炽盛光佛画像绘制于该窟主室窟顶东披,位于阿閦左侧⑤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上海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借由其手中八辐金轮,以及围绕着特征性眷属的十一大曜,是可断定其炽盛光佛的尊格⑥廖旸:《11—15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一)——以炽盛光佛为中心》,载沈卫荣主编《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炽盛光佛作为密宗神祇,多见于汉传佛教及其石窟绘画中,藏传佛教中鲜有所见。藏传佛教色彩浓厚的第465窟发现炽盛光佛图像,其价值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西夏佛教早期主要受中原汉传佛教影响,及中晚期藏传佛教崛起,影响渐深,但其最初主要流传于民间。且伴随着藏传佛教于西夏之地的深入发展,汉、藏佛教圆融趋势日显,继而对西夏佛教、社会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朝肇建,尽管藏传佛教已非常显赫,但它仍承袭了西夏显密圆融、汉藏融合的佛教传统。对此,莫高窟第465窟主室窟顶之金刚界五佛与炽盛光佛的图像绘制、神系重构即是有力的说明。其覆斗型窟顶斗心绘大日如来,西、南、北三披则为三方佛及其眷属,唯东披绘阿閦佛、炽盛光佛、药师佛三尊,从而构成了东方三佛体系,同时又与主室窟顶金刚界五方佛构成一种七佛体系。这无不体现了炽盛光佛的尊格抬升,信仰宏盛,以及汉、藏、印佛教文化的融合互鉴,正可谓11—14世纪河西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另外,作为西夏窟的东千佛洞第1窟亦保存有炽盛光佛图像,其东壁正中绘制炽盛光佛经变一铺。而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第1窟东壁也绘有西夏《炽盛光佛与星曜宫神图》一铺,壁画中炽盛光佛居中坐于莲座上,左手作禅定印,右手托金轮。佛的上部绘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神像,佛两侧及下部人物则漫漶不清,当是九耀星官①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绘画方面,据俄罗斯学者萨玛秀克介绍,现存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黑水城藏品中描绘星宿神的作品即有24件,按题材可以分为6组②萨莫秀克著,谢继胜译:《西夏王国的星宿崇拜——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黑水城藏品分析》,《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其中,绢质卷轴彩绘《星曜坛城》背面保存两处印章,系西夏文,文字漫漶,无法辨识。幸而借由黑水城西夏文《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可窥见《星曜坛城》之内容及意蕴。尽管炽盛光佛并未被绘于坛城主要位置,但整个祈祷活动却以炽盛光佛为中心展开③崔红芬:《从星宿神灵崇拜看西夏文化的杂糅性》,《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同时,它又借助藏传佛教曼荼罗,将炽盛光佛及其星曜眷属作为藏传密教日常修行的核心意象,以消灾除障。
概而言之,借由相关炽盛光佛出土文献、石窟壁画、绘画作品等,从中我们不难窥见11—14世纪河西地区炽盛光佛信仰的传播情况。是时,炽盛光佛崇拜业已突破了其本初传统的密教程式格套,宗教仪轨的闭锁性进一步弱化,同时还吸收了部分显教通行的祈福方式,展现出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炽盛光佛为国家消除星灾的功能日益退化,取而代之的则是为个人或地方消灾弥难、祈求福祉,世俗化与普适化趋向显著。同时,伴随着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于河西之地的并驱发展,以及西夏、元朝佛教尤重显密兼容,炽盛光佛信仰亦呈现出显著的汉藏交融趋势。
三、炽盛光佛信仰形成背景探析
诚如前文所言,11—14世纪,炽盛光佛信仰备受河西信众崇奉,其发展嬗变日新月异。是时,炽盛光佛法之所以如此流行,概因以下几方面:
其一,佛教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多民族交流交融。众所周知,唐宋以降,作为一种修行方式的炽盛光佛法借助密宗的活跃发展态势,逐步弘传开来。至辽、西夏时期,这一信仰仍十分流行,相关文物不断涌现,如宁夏宏佛塔及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之西夏文献与炽盛光佛变相绢画等。元朝时期,统治者对于炽盛光佛亦甚为崇奉,校勘、印施佛经时有所出。如至治元年(1321)释性澄奉召入京,被旨居清塔寺校刊《大藏》,他即对唐不空译本进行了删补疏解,校正改定①[元]释性澄:《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序》,《大正藏》第19册,CBЕTA,2009年,第337页。。另外,前文所述元刊西夏文本藏外经,其乃元代斡巴法师据西夏国师德慧译本发愿刊刻而来。与其合刊一册的还有西夏文《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西夏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其炽盛光佛崇拜的主旨显露无遗。因而,在这一佛教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共同推动下,纳入王朝疆域框架的河西之地,其地炽盛光佛崇拜弘盛自是情理之中。
另外,河西地区历经唐末五代、宋元以降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之裹挟,以及11—14世纪西夏、元朝的长期统治,其地族群种类与部众规模皆远超前代,成了多民族杂居相处、交往交流的大本营。加之,河西地区自古就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当地民众又保持着浓厚的炽盛光佛信仰传统。因而,入居河西的党项、蒙古诸族,身处崇奉炽盛光佛法的包围沁润之中,与其交往交流交融甚密,因而在佛教信仰上必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对此,前文所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书写的多位助缘僧众题名即为明证。尽管这些题名中有少数漫漶不清,但可辨识者亦为数不少②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页;[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2017年,第250页。。其中,“嵬名”“杂谋”“讹特”“播盃”等皆为载于西夏文《三才杂字·番姓》的党项姓氏,而梁、吴、翟、索则为汉姓③张玉海:《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所见人名姓氏浅析》,《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因而,尽管目前无法判定其真正的族属身份,但是无论是单纯的汉姓、蕃姓僧众,抑或兼具蕃汉两姓的僧众,他们皆助缘顶礼炽盛光佛道场,而该窟甬道所出现的两处回鹘式蒙古文题记及蒙古人名则再次印证了元朝时期,落居河西的多民族部众崇奉炽盛光佛法的历史。这无疑不彰显了西夏、元朝时期,河西多民族在日常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中交流交往之深厚,文化交融互鉴之深远。
其二,原始宗教信仰、道教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河西地区自古以降即为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于此,儒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原始信仰等根植发展、交流融合。其中,原始宗教信仰于河西地区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继而对其他宗教的发展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其更为河西地区的多民族部众所始终崇奉。它以萨满沟通鬼神与人间,主持祭祀仪式、占卜吉凶、禳灾驱邪,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活跃于河西地区的汉、回鹘、党项、蒙古等,其先祖时期就有自然崇拜,即使崇信佛法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仍颇为深厚。
另外,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它不仅囊括了儒、释、阴阳、神仙诸家学说,又融合了原始巫术、谶纬占卜等方技术数与民俗传统。关于道教于河西地区的传播,其当肇源自汉魏时期。隋唐时期,河西道教在官方的扶持下趋于兴盛。“安史之乱”爆发,道教因丧失官方支持,开始深入民间发展。归义军统治时期,佛教传播宏盛,地位不高的道教遂进一步走向民众,继而强化了与民间信仰的融合。及西夏、元朝时期,在统治者的大力优抚下,原始宗教与道教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以巫术星占、鬼神祭祀等为核心内容的原始宗教和道教崇拜在文化内涵、仪式仪轨等方面皆与佛教炽盛光佛信仰具有颇多相通之处。例如,炽盛光佛信仰通常与九曜、十二宫和二十八星宿的占星术相结合。又如,炽盛光佛逐渐演化为具有消灾避祸、追福荐亡功用的世俗化民间宗教信仰,而世俗大众的原始宗教信仰及道教崇拜中则存在对神秘莫测的星际天空的崇拜与恐惧。因此,当河西民众接触到与星占学关系密切的炽盛光佛时,这似乎为其解决心中的疑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找寻到了一把更高深、更权威的金钥匙。
毫无疑问,炽盛光佛信仰与原始宗教、道教在宗教文化、仪轨等方面的相通性和广适性,以及11—14世纪河西地区原始宗教崇拜与道教信仰历史悠久,皆为炽盛光佛信仰于河西之地的根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宗教思想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极大地促进了炽盛光佛信仰于河西地区的传播流布。同时,炽盛光佛信仰既包含高深的佛法,又融合了天命星象的神威,融摄了释教与道教数术,可谓具有双剑合璧之效,异曲同工之妙。河西民众对其大力吸收与利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三,现实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问题。炽盛光佛作为统摄星曜的密教主尊,其可教日月、星宿等天神降伏。因而,人们于天变地异、风雪灾祸时修炽盛光佛法,通过密宗法事及宗教献祭的方式,可排除和削弱来自上天星宿界的有害影响,以达到消弭灾祸、祈福禳难的目的。同时,晚唐以降,随着炽盛光佛信仰的日趋世俗化,其最初消除恶曜降临的功能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消灾与荐亡①秦光永:《中西交融与华夷互动——唐宋时代炽盛光信仰的传播与演变》,《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他不仅可以攘除灾星恶曜,兵燹暴乱,恶病缠绵等,更可保佑福禄永固,国祚绵长。西夏蒙古贵族统治河西时期,在那些灾乱不断的时候,崇奉炽盛光佛,受持陀罗尼经咒,更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西夏太宗德明、景宗元昊统治时期,以武力诸称,“尽有河西之地”②[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然而,盘踞河西的回鹘、吐蕃势力仍不容小觑,其地时陷于动乱。尤其是随着13世纪初蒙古部族的崛起与军事征伐,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河西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困苦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42—443页、496—497页。。元朝肇建后,河西地区又作为元廷对抗海都、都哇等西域叛王的军事壁垒,其地战乱频发,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衰落的景象。事后,尽管在以豳王家族为代表的蒙古诸王的镇戍与经营下,河西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但已不复往昔之盛。同时,西北之地僻在边陲,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常常遭遇天灾人祸,社会动荡不安。对此,《元史》所载元政府对河西地区的频繁赈济与支援即是有力的体现②《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卷二六《仁宗纪三》、卷三七《宁宗纪》都有相关事例。。
面对这种严峻而恶劣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具有浓厚佛教信仰倾向的上层统治者与河西民众必然求助于炽盛光佛法,以期消灾避祸,祈福添祉,保一方平安。目前所见11—14世纪,河西地区出土的炽盛光佛相关遗物遗存也多与其时各地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如以《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为代表的黑水城出土的佛顶尊陀罗尼刻印本中,即有不少是专门为祛灾、治病、祈雨、防雹、诛杀敌人等特殊用途而念诵的密咒和陀罗尼,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景观③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同时也揭示了人们如此崇奉炽盛光佛,必然与现实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肇兴于唐代的炽盛光佛信仰于11—14世纪的河西之地得以继续弘扬,其发展嬗变历久而弥新。这一时期的河西炽盛光佛信仰对前代既有所承继,又有所革新,从而在典籍文献、仪式仪轨等方面展现出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在宗教功用上呈现出以满足普通信众之消灾弥难、追福荐亡的世俗化宗教诉求为主旨的现世性趋向;在外部形态与内部意蕴上则显现出多民族交往交流,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倾向。总体而言,11—14世纪河西炽盛光佛信仰的宏盛既得益于其地佛教文化传统与原始宗教信仰、道教崇拜的融摄交汇,同时又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多民族交流交融,特殊的自然生态条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