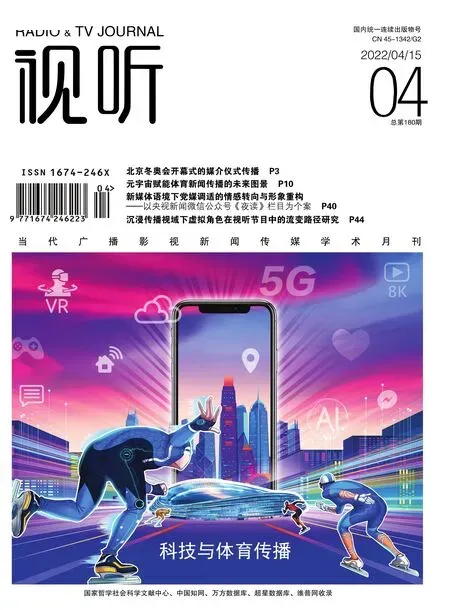想象“八十年代”的方式
——以电影《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为例
程振红
近年来上映的一些电影中承载了创作者对“八十年代”①的想象。尽管“八十年代”常作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而存在,但在这些电影中,“八十年代”本身其实也已经成为想象的客体,如《老师·好》(2019) 和《你好,李焕英》 (2021)。《老师·好》围绕师生关系,主要讲述的是高中班主任苗宛秋与班级学生之间的关系从冲突、对立到和解、融洽的变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和插曲。这些插曲和片段见证了学生们的青春岁月,也成为苗宛秋人生中最好的时光。《你好,李焕英》则是关于亲情的故事,虚构了贾晓玲“穿越”到“八十年代”后与年轻时代的母亲李焕英“相遇”的种种场景。无论是《老师·好》中被苗宛秋所怀念的最好的时光,还是《你好,李焕英》中电视里解说的“激情燃烧的时代”“拥抱世界的时代”,“八十年代”在这两部电影中显然都被贴上了“美好”的标签。这两部电影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但不管是《老师·好》中的“青春之歌”,还是贾晓玲在“白日梦”里所“看到”的李焕英的青春光彩,都镶嵌在“八十年代”的幕布之上。
一、曾经的流行歌曲:“八十年代”记忆的提取线索
正如陶东风所言:“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气候的写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因而也就有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它表达了社会想表达又表达不出的真实情感。”②电影中往往会插入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既能营造特定的时代氛围,也可以将其作为电影的叙事元素。《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中都“植入”了一些“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对电影的叙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老师·好》以一段舒缓的钢琴曲拉开帷幕,伴随这一段音乐的画面只是叙述者王海的现实。随着歌曲《金梭和银梭》 (1980) 响起,影片的主人公苗宛秋在王海的回忆中登场。满怀激情的男女声合唱《金梭和银梭》瞬间将故事从“优秀教师”王海的现实切换到他回忆中的高中生涯。作为有着强烈时代气息的歌曲,《金梭和银梭》既提示了“八十年代”的故事背景,也相当契合大特写镜头下南宿一中的校园环境。这首八十年代初的流行歌曲充满蓬勃昂扬的乐观情绪,对应高中生王海们的校园生活和青春岁月,“光阴快如箭提醒你和我,年轻人快发奋,黄金时代莫错过”的歌词更表征着八十年代的“青春之歌”。电影字幕提示故事时间是1985年9月1日——南宿一中新生开学的第一天,背景音乐却是这首1980年推出的歌曲。由此可见,影片精心挑选了《金梭和银梭》这首歌曲作为“八十年代”的主旋律。换言之,通过叙述者王海的回忆,这部电影所想象的“八十年代”是激情满怀、奋发有为的时代。
如果说《金梭和银梭》标志着对学生的规训或期待,那么《路灯下的小姑娘》 (1987)、《吉米阿佳》(1982)、《阿里巴巴》 (1981)、《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等歌曲则代表着他们对“压迫”的反抗。伴随着这些歌曲,电视呈现的场景是王海、蒋文明、关婷婷等人的“不务正业”——在舞厅、教师办公室、教学楼楼顶等场所跳舞的画面。相对于《金梭和银梭》站在高处的“召唤”,《路灯下的小姑娘》等歌曲显然更生活化,也更轻松欢快。可以说,《老师·好》中的八十年代歌曲体现了理想化和生活化的两种样态。
与《老师·好》将王海的现实轻描淡写而对其回忆中的“青春之歌”加以浓墨重彩的做法相似,《你好,李焕英》对贾晓玲真实的成长经历也只用了10分钟的叙述时间,而将故事的重心放在其“穿越”到1981年后的见闻上。伴随着欢快的背景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八十年代”在贾晓玲的视野中得以展现。《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都选用了这首歌曲,不同的是,《路灯下的小姑娘》在《老师·好》中表征的只是学生在“八十年代”的课外生活的一部分,这首歌在《你好,李焕英》中却意味着贾晓玲对“八十年代”的总体印象。玩耍打闹的小朋友,跳皮筋的女孩们,买冰棍的孩子,互相追逐的少年们,三五成群并肩行走的工人等,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这些画面都是对总体印象的佐证。换言之,《你好,李焕英》以《路灯下的小姑娘》这首欢乐活泼的小叙事歌曲作为八十年代的基调。“与现实中的个人遭遇不同,叙事中的遭遇是依照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编织起来的”③,虚构的穿越情节显然体现了贾晓玲的意志和意愿。她希望母亲李焕英安然无恙地活着,更想让母亲高兴,因而欢乐成为影片赋予“八十年代”的重要元素,这是贾晓玲想象中属于母亲李焕英的“八十年代”。
《你好,李焕英》中的另外两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980) 和《迟到》 (1980) 同样体现了欢乐元素。如果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与《金梭和银梭》一样明确地标识了“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那么《迟到》在《你好,李焕英》中的运用则是更加个人化的表达。与《路灯下的小姑娘》相似,《迟到》也属于小叙事歌曲。伴随着《迟到》,画面呈现的是贾晓玲与年轻的李焕英一起逛商店、买衣服、吃饭和去往电影院的日常生活场景,为两人单独相处的欢乐时光做了注解。整部影片其实就是以“我”的口吻讲述的“我”和“你”的故事,与歌曲《迟到》同步的故事情节承载了贾晓玲“穿越”的意图和意义。
无论是《老师·好》,还是《你好,李焕英》,这两部电影中所插入的以上歌曲都是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所耳熟能详的曾经的流行歌曲。电影创作者或从自身经历,或从历史资料,或从他人口中获得了“原材料”并建构了自己的“八十年代”记忆,同时通过影片呈现出对“八十年代”的想象。心理学认为,根据记忆保持的时间长短不同,人的记忆可以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④。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时,需要依据一定的线索,“提取线索可以激活有关的记忆痕迹”⑤。作为历史时间的“八十年代”早已远去,成为20世纪时间链条中的一部分,而“八十年代”也已经成为人们长时记忆中或苏醒或沉睡的影子。作为“八十年代”记忆的提取线索,电影中的八十年代流行歌曲不仅可以发挥叙事功能,还能瞬间激活人们对“八十年代”的记忆,对于想象“八十年代”具有独特的意义。
二、现代化想象:“八十年代”的时代话语
《老师·好》的片名特写字幕出现之后,画面快速切换到南宿一中的开学场景。班主任苗宛秋推着自行车正对镜头走进校园,在其身后校门外的宣传墙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在“八十年代”故事的讲述一开始就以正面镜头将主人公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中,可见,在影片的叙事中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时代标记。八十年代“占主导性的时代话语”可以概括为“对‘现代化’的欲望与诉求”⑥,现代化成为指引“八十年代”方向的精神航标。《你好,李焕英》中进入“八十年代”叙事之后,伴随着《路灯下的小姑娘》的背景音乐,首先呈现的也是现代化的符码——胜利化工厂内的墙壁上“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宣传标语特写镜头,着意凸显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
现代化承诺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景,也想象了一个时间开始了的“八十年代”。“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⑦,《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表明电影中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抢时间、抓效率、快步迈向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的标语不仅见于校园和工厂,也出现在大街小巷。《老师·好》中苗宛秋下班后到街头摊贩处买红薯,画面中的背景墙上写着“锻炼身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字样。能够锻炼的身体是具体的,也是个人化的。将身体纳入现代化的想象之中,意味着现代化话语意图通过对身体的规约建构起个体作为“八十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从而将其“召唤”成现代化的建设者。苗宛秋买菜的场景与现代化标语的并置也说明现代化想象所涵盖的不仅是社会空间,还有普通人的生活空间。
如果说以上标语口号在电影中都是出现在敞开、露天的公共空间,那么,这两部影片中的封闭空间里则体现了现代化话语的渗透。在《老师·好》的情节中,学校礼堂先后举办了学生文艺汇演和教职工表彰大会,礼堂舞台侧面悬挂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标语。在“三个面向”中,首要的是“面向现代化”,可见现代化在教育领域也是第一位的目标。现代化的标语出现在礼堂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封闭空间之中,表明现代化话语以仪式化的方式为空间赋予意义。礼堂可以看作剧场,而剧场“是一个物理空间、具象空间,也是一个携带符号、象征性符码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无意识、社会无意识的抽象空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图像和谱系”⑧。作为象征性符码,礼堂内现代化的标语承载着“八十年代”的“精神图像和谱系”,无论是对于参加教职工表彰大会的苗宛秋等人而言,还是对于参与文艺汇演的王海等人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背景。在这一仪式化的封闭空间之中,人的身体的空间性也得以凸显。“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⑨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其身体的空间性都反映了他们在学校礼堂空间中的处境——他们都处于现代化光芒的映照之下。
与《老师·好》中的学校礼堂一样,《你好,李焕英》中的工人文化宫也具有剧场的意义。它是电影院,也是举办文艺演出的场所。沈光林与李焕英看电影的片段,以及贾晓玲在文艺汇演上的表演都在这里展现。作为电影放映和文艺汇演的视觉背景,工人文化宫内舞台上方高悬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的醒目横幅。工人文化宫是胜利化工厂的工人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他们观看电影和欣赏演出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号召也无时不在。贾晓玲“穿越”前,医院电视机里的解说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们,成为了这个时代工人的主力军。他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脸上各个洋溢着时代的笑容”,正是对“贡献青春”的李焕英们精神面貌的生动描写。按照贾晓玲的“意志”和“意愿”,她“看到”了青春时期的李焕英。作为“八十年代”工人主力军中的一员,李焕英在与现代化的关联下显得更具青春光彩。换言之,现代化不仅表征《你好,李焕英》中“穿越”故事所发生的“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而且是塑造更符合贾晓玲期待的青春李焕英的重要元素。
现代化想象还赋予了人们对“八十年代”独特的时间体验。《金梭和银梭》“时光如流水,督促你和我”和“光阴快如箭,提醒你和我”的歌词,以及胜利化工厂“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宣传标语,表明“八十年代”的时间体验就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快速”和“加速”。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时间体验也是一种时间性,即“人的生活、感受、感觉所具有的时间特性,……指的不是客观时间,而是主观时间”⑩。电影中作为时代背景的“八十年代”不再是客观时间,而是体现影片人物时间体验和具有时间性的主观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中的现代化话语规定了“八十年代”,使其成为“美好的时光”和“激情燃烧的时代”。
三、日常生活空间的彰显:“八十年代”的微观肌理
《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分别讲述的是“八十年代”中学师生和青年工人的故事。无论是班主任苗宛秋,还是工人李焕英,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普通人,在他们的故事中,更多呈现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阿格妮丝·赫勒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⑪。《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中的日常生活空间主要是家庭、居住区和消费娱乐空间。
《老师·好》中着意凸显的首先是家庭空间,这与教室(学校)空间有很大不同。在教室里,苗宛秋以绝对强硬的姿态树立和维护他的权威,即便对最桀骜不驯的洛小乙也毫不手软。“掩藏在这一空间背后的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联合实施的柔性权力,旨在规训教室空间中所容纳的学生,驯服那些僭越传统课堂秩序的姿态与行为。”⑫可以说,教室空间成就了作为教师和班主任的苗宛秋。相比之下,家庭空间则展现了苗宛秋更真实的一面。师生之间的冲突、对立发生在教室,苗宛秋邀请学生们到家里做客则表明他们之间的和解。家庭空间中的苗宛秋面带笑容,与学生们举杯相庆、谈笑风生,逼仄的房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正是在家庭空间中,苗宛秋向学生们讲述了他的过往,其辉煌历史使学生们受到震撼和触动。那一刻,曾经被学生认为霸道专制的“苗霸天”变得真实、亲切和高大,成为指引学生前进方向的灯塔。教室里的“规训与惩罚”没能让学生们心服口服,家庭空间中的推心置腹却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可见,日常生活空间实际上发挥了教育功能。
《老师·好》同样展示了学生们的家庭空间。洛小乙家墙壁上相框里挂着他初中时参加体操比赛获奖的奖状,奖状右下角一张残缺的照片中只剩戴着军帽的父子俩。显而易见,洛小乙母亲的影像已经被他从照片中撕毁。这暗示着洛小乙不幸的童年,以及他加入“九龙一凤”混社会的原因。洛小乙与祖父相依为命,缺位的父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入团的动机正在于他想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军人。安静家同样简陋,室内摆放的缝纫机和随处可见的衣物表明母亲的职业,满墙的奖状则为“好学生”安静做了注解。与洛小乙家的情况相似,安静的父亲也是缺席的。相比之下,关婷婷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室内有序摆放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餐桌上丰盛的菜肴,围坐在餐桌旁看电视的一家三口,都表明关婷婷家优越的生活环境。在“八十年代”,电视不仅是现代的表征,也是“保持日常生活的连续性,获得自我认同的体验”⑬的重要工具。可以看出,这三个学生的家庭空间既烙印了他们不同的生命轨迹,也说明了他们迥异的性格成因。
与《老师·好》有所不同,《你好,李焕英》中“八十年代”的日常生活空间更多地呈现于消费娱乐空间和居住区,指向家庭空间的镜头并不多。前文提到,贾晓玲“穿越”的目的是让李焕英高兴,人多热闹的消费空间和居住区更有助于实现她的意图。不同于消费社会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和商场,影片中的消费娱乐空间主要是供销社和工人文化宫这样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定场所。《你好,李焕英》用了较多的叙述时间展现贾晓玲和李焕英在供销社购买电视机的情节,尽管大批顾客蜂拥而上竞购电视机的片段反映了“八十年代”物质相对匮乏的事实,影片却通过贾晓玲编造悲惨身世的剧情显出喜感,使得这一匮乏的消费空间充满欢乐。
居住区的情节在影片的叙事中也有独特意义。贾晓玲用策略帮助李焕英买回电视机后,职工们一起围坐观看露天电视。这个场景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的“风景”之一,也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场景。“日常生活的世界为人提供熟悉感、安全感、亲近感和‘在家’的感觉,是人的‘家园’。”⑭一起看电视的人们形成一个熟人社会,职工宿舍区的公共空间成为个人家庭空间的延展。影片巧妙地设置了电视中播放中国女排比赛的片段,再现了“八十年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不动声色地凸显“八十年代”的故事背景,也营造了李焕英们庆祝女排夺冠的愉快热烈的氛围,同时十分自然地为过渡到胜利化工厂职工排球比赛的情节做了铺垫。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日常生活空间中也有时代大事件的投影。
总而言之,在《老师·好》和《你好,李焕英》中,日常生活空间从微观层面彰显了“八十年代”的内在肌理。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⑮,这两部电影中的“八十年代”叙事也主要是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徐徐展开。无论是《老师·好》中的苗宛秋,还是《你好,李焕英》中“穿越”后的李焕英,他们都是“八十年代”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将他们融入“八十年代”,是人物塑造的需要,也是“八十年代”题中自有之义。
四、结语
《老师·好》中“八十年代”的故事时间从1985年到1988年,《你好,李焕英》中的“八十年代”则定格在1981年。尽管二者讲述的故事相去甚远,但它们想象“八十年代”的方式却是相似的。无论是《老师·好》中苗宛秋对学生的真诚关心和严格负责,还是《你好,李焕英》中李焕英与贾晓玲母女之间相处的日常,都令人感动。无论是王海的回忆,还是贾晓玲的“白日梦”,回忆和梦见的都是“八十年代”。由此可见,作为“美好的时光”和“激情燃烧的时代”,“八十年代”依然能为今天的观众提供情感抚慰。
正如洪子诚教授所说:“不仅是不同‘代’的人,就是同为‘这一代人’中有不同遭遇的,对‘历史’的了解和描述,都会有那么多的差异。”⑯“八十年代”对于其亲历者和并无“八十年代”经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即便曾经同为“八十年代新一辈”,不同的个体也可能感受各异。此外,“八十年代”“常常并不是作为‘历史’而是作为‘现实’,存在于当下的文学视野和历史意识之中”⑰。电影中的“八十年代”叙述不仅重塑“八十年代”,而且反射出电影创作的年代,反映的是电影制作发行时对“八十年代”的理解。不同时代的电影创作者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角度与方式,想象和呈现更加丰富、立体、多元的“八十年代”,重新激活人们对“八十年代”的记忆,并为现实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本文用“八十年代”指代20世纪80年代。
②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1.
③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
④刘益民,程甫,刘耀中.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8.
⑤张承芬 主编.教育心理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41.
⑥童娣.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 “80年代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⑦[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
⑧濮波.社会剧场化——全球化时代社会、空间、表演、人的状态[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2.
⑨[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7-138.
⑩刘彦顺.时间性——美学关键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4.
⑪[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 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3.
⑫潘跃玲,熊和平.教室空间的现象学之维[J].教育发展研究,2013(04):66-70.
⑬金玉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
⑭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
⑮[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概论)[M].叶齐茂,倪晓晖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0.
⑯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6.
⑰贺桂梅.打开六十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J].文艺研究,2010(0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