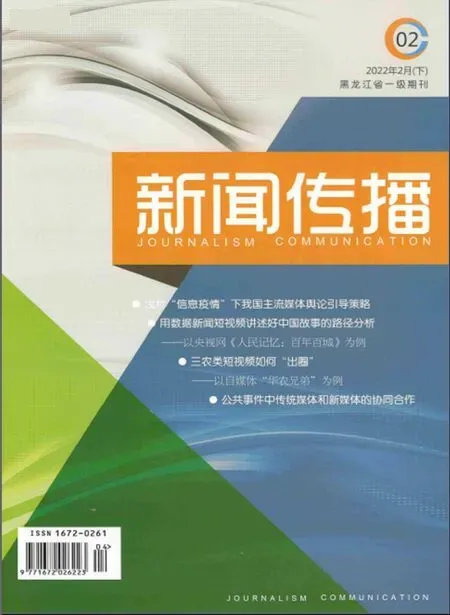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2020学术年会”综述
杨 惠 张瑞坤、2
(1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西安 710119 2 河套学院 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媒介技术渗透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形态,整个社会结构围绕新的技术逻辑发生了重构。一种由“媒介研究”而至“媒介化研究”的新范式已出现,为重新锚定媒介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开启新的理论想象之门,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2020学术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
一、学者主题演讲环节突出学术研究理论向度
“算法计算机科学用于解决某一问题方法的术语,也是对计算机发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指令。”[1]算法是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核心。计算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数据进行转换的过程,而文本、图片和音频都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以搜索和数据挖掘为主要形式的数据转换过程就是计算。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围绕《算法逻辑的知识考古学》进行发言。他认为,如果说世界主要由物理环境、人和社会构成,人类的计算也可分为人和社会的计算、物理环境的计算。前者研究人和群体的行为,包括过去和现在,有组合和无组织,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属于这个范畴;后者研究人类生活环境的状态,传统学科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属于这个范畴。在算法逻辑下,人类的思维还将面对哪些变化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数字媒介向城市空间的不断渗透,致使媒介突破符号化的仿真,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现实。复旦大学孙玮教授围绕《媒介变迁:从“仿真”到“全真”——未来城市空间发展》进行发言。她提到,空间化进程有三种方式:一是媒介界面与实体空间的嵌合——屏幕植入。二是媒介实践参与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基础性平台。三是智能身体作为媒介与空间的连接——主体营造复合空间。全真的媒介在时间层面:媒介与现实的时间间隔消失;在空间层面:媒介与现实的缝隙消失;在主体性层面:媒介通过抽象符号对意识的影响,转变为以智能身体主体感性的、场景的、物质化的体验,媒介即身体“我”。
中国修辞传播功能覆盖全面、智巧表现丰富、历史延续悠久、领域覆盖广阔,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丰富的智慧哲思、伦理道德、审美趣味、交往方式和生存策略。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围绕《重叙中国修辞传播的伟大传统》进行发言。他认为,中国修辞传播研究以交流为本位,以媒介为基础,以言谈话语为中心——落实于传播实效之“事”与“为”;重心在于传播的“伦理”与“智巧”。中国的修辞学应突破由日本“早稻田”学派建立起来的美词学传统的影响,回归到本土文化领域,这对于建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汉语中描述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词汇相当丰富。“君子之交”作为一种理想型人际关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教授围绕《浅谈“君子之交”》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君子之交”可以从相遇(先择而后交)、相知(道德为本)、相交(以诚相待)、相持(谦和礼让)四个方面进行实践,从而有助于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高尚人格;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任何学科的认识论都面临着一种研究起点上的两分法:着眼于体结构与功能的视角;着眼于个体行动和实践的视角。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围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种途径及当代发展》进行发言。他认为,经典传播政治学的结构性视角:媒介受到市场力量与公权力的双重约束。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都一定是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合谋,延展到新闻或传播内容生产中的权力规训。结构性视角的当代发展主要体现在空间的传播经济学、时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基于此,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代发展的背后需要重新认识媒介技术。媒介重新安排了时空,新的物质性终结了旧有的权力关系。所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重新上路了。
手机管理已成为中学校园管理中非常突出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管成云副教授以《农民工的孩子为什么还是农民工——基于农村中学校园新媒体事件的多点民族志考察》进行发言。他认为,学校教育在孩子发展轨迹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毁掉孩子的,手机并不是罪魁祸首,而是父母陪伴的缺失、教育不公平背景下学校生存状况的应试机制等综合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且彼此又相互强化,造成了农民工的孩子在教育上的弱势积累,由此丧失了向上流动的资本。
二、媒介的技术、文化与历史纬度
“语境是指说话时人们所处的状态和环境。”[2]语境信息为表演者提供了重要线索。河海大学张杰教授通过梳理社交媒体研究中“语境崩溃”这一概念的发展脉络,探寻这一概念如何将社交媒体中的互动与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区分开来,又塑造了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怎样的互动体验。研究发现,“情境”本身的理论和视角独立性已严重被削弱,情境崩溃成为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的必然结果。恢复情境的相对独立性和情境中行动者的相对独立性,而非仅从媒介可供性、技术结构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这一微观理论,或给予媒介理论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性。“传播”本身充满着多种角度和多种范式的理解。
广西大学李庆林教授、鲍精华研究生比较分析了传播的传递观、仪式观和交往观,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引领了传播的技术范式、开创了美国主流传播学学科,传播的仪式观回溯传播具有的文化内涵,而传播的交往观从实践论、主体论出发,回归传播的缘起,认为传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货币是生活风格的载体。南京大学王佳鹏助理研究员从关系主义和相对主义视角出发,将货币视为纯粹抽象媒介的“巅峰”形式,剖析货币经济学这一经验科学“之前”的“先验”和“之后”的“后验”,从而以货币为“范例”,透视现代客观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文化趋势。齐美尔的思想遗产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但却似乎缺乏明确的继承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张聪讲师对延安时期的影像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影像的“再现”模式理论背景下,通过研究延安影像的生产机制和延安影像产品的接受,来考察延安时期的电影和摄影图片作为一种在当时全新的媒介,是如何参与到新的政治话语的建构之中的;其次,从“地点制造”的角度,探究延安人以摄影活动作为平台,通过自身参与拍摄电影、拍摄照片或观看电影、观看影展的实践活动,构筑了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地方空间,并赋予此空间以新的意义。
三、媒介化实践与社会关系网络维度
媒介的现实性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新闻的客观性、社会现实的建构方式、社会现实与媒介的关系、媒介的建构过程与结果具有怎样的实在性等一系列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刘国强教授认为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媒介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独立存在,但相对其他社会领域,媒介又有着极为优越的地位。浙江传媒学院李欣教授基于“227”粉丝社群冲突的案例进行观察,研究了粉丝独有的社群组织化传播路径与集体行动动因。南京大学胡菡菡副教授则是通过对“227大团结事件”中网民话语的分析,提出我国网络公共话语受到族群冲突的挑战,正是因为“偏好”在包括技术、资本与主流话语在内的各行动主体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合理的扩张。未来,我国的网络治理需要强调“偏好共存”与“偏好妥协”的公共话语伦理原则。
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广告的投放可以依据消费者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定制。厦门大学王霏副教授认为,合意性诉求以及可行性诉求是旅游广告常用的两类诉求。将广告诉求与游客的心理距离相匹配有利于增强广告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南京大学吴志远助理研究员认为,大众媒介对城市空间正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扮演了建构城市空间正义的四道“墙”的角色,即区隔之“墙”:建构城市空间所有权的正当性;监护之“墙”:影响公共空间资源再分配的公平性;遮蔽之“墙”:通过“代言”或“标签化”扭曲不同社群在城市空间中的平等性;想象之“墙”:干预城市空间中异质空间的开放性。
四、媒介化传播的时空、身体与范式转型维度
“媒介化社会主要凸显的是媒介在社会中日益扮演更多和更重要角色的社会事实。”[3]四川外国语大学严功军教授提出“教育媒介化”这一概念,认为媒介在教育领域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从“中介化”的物质教育媒介与数字教学实践到“媒介化”云课堂情境的历史脉络变迁。福建师范大学连水兴教授认为,媒介时间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时间结构。如今我们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时间结构也发生了范式的改变,即时间并不是在加速,而是时间由于缺乏叙事重力和意义走向消散,成为一种不良时间,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加速只是时间消散的症候之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军芳教授探讨了媒介如何成为人类意识中介时所秉持的逻辑,以探索传播可能具有的新意蕴。山东财经大学张瑞瑶讲师以运动APP的使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运动APP的使用行为和规律运动行为的产生、维持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运动APP的使用对规律运动行为的干预作用,以劝服传播的视角解释运动APP的使用对规律运动行为动机的影响和转变作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付玉讲师认为,医学传教以身体为中介,利用生物学的物理治疗手段、医疗公共空间对身体的管理、西医学与宗教教育融合等手段形成了一整套世俗化的身体控制体系。
浙江传媒学院方兴东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对信息传播的构成、传播的主体、内容、速度、受众和效果等要素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科学理论、基础原理、基本技术、核心应用以及传播机制等层层推进的传播发展与变革进程进行深度剖析。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薛毅帆从当前党报传播活动若干合理性出发,认为党报活动更主要地是属于一种组织传播活动,而非人们惯常认为的大众传播活动,并将党报理论视为一种原生于党报自身实践的组织新闻传播学理论成果,是分析与评判党报活动的更恰切的知识框架。西安外国语大学展威震试图从唐·伊德提出的“人—技”四种关系的角度探析移动直播现象,思考这四种人技关系对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的启示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杨馨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种经典范式正逐渐式微,新的研究议题已经拓展到了对媒介技术的关切、对劳动概念的拓展、时间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的主体性及其实践。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型的方向正是媒介化,媒介技术应当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才能解放其理论的创造力与阐释力。
五、承续与超越: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圆桌论坛
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提出需要从概念的角度理解媒介化,媒介化是通过传统媒体的时空流程的格式化规律把人们传播过程中的流程概念意义放大,而不是一个机构强制性的刻意安排的流程意图。同时,媒介化概念正在慢慢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习惯。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媒介化反应于教育生态的,如今传统的传播学教材无法解释媒介化所要体现的意义,媒介时态发生了变化,专业教学上如何重整教育体系、如何提供积极有效的概念系统,对当前年轻一代的学者和老师们提出了挑战。
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提出,媒介在文明的进化中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唯物的规律,但并非纯粹的物质技术进化的规律。技术是运用和实践的结果,是在不断运用中进化,如从电视到互动媒体到网络化媒体、智能化媒体,媒介化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学派和重要研究方向值得肯定。媒介并非一个物化的工具,而是一个实践。在人的实践类型中,仪式中是有媒介因素的,但不完全归结于媒介。他承认媒介化研究是主流研究方向,但是人的交往实践是和人的内在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复旦大学孙玮教授提出媒介可以成为传播学研究转向中最重要的一点。她着重强调感知,技术怎么改变人的身体感知以及肉身对媒介的感知。她不赞成纯粹的物质性身体,肉身不完全构成媒介,身体一定是实践的。中介是最主要的,没有中介就没有主客体,把人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中介就是媒介。如今知识体系的发展是本体论向认识论、认识论向媒介论的转向。只有这样,传播学才能和人文科学对话。媒介作为未来的传播研究的中心,有助于建立新的人类文明并且可以重现人类文明思想史。
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提出交往实践基于媒介物质性之上,媒介可控性不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关于媒介物质性中物质性更重要还是实践更重要,他认为不能抛开媒介带来的物质性框架讨论实践。这个时代之所以被称为信息社会,是因为社会组织方式以信息资源的配置为核心来运转。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依靠媒介的一整套的逻辑来运转的社会。中国最前卫的学者的观念已经被媒介化概念的提出所重构,这个重构把西方理论体系生搬硬套来讨论中国问题,并没有站在新概念的基础上来看待中国本土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