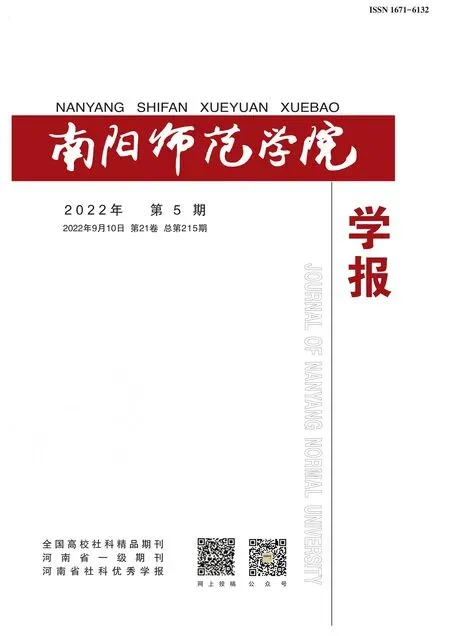北宋初期词学的传承与流变
岳淑珍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对于北宋初期词学的批评(1)此文北宋初期、北宋前期以及中后期的划分,同意刘扬忠先生在《唐宋词学流派史》中的观点,即初期指宋朝开国前六十年,前期指柳永、晏殊、欧阳修等活跃在词坛时的仁宗、英宗时期。,学界多就其词体沉寂原因加以阐述,而对其词学贡献探讨不足。可以说,北宋初期词学的发展在晚唐五代与北宋前期词学发展中架起了一座桥梁,北宋前期出现了宋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离不开北宋初期词学发展的重要铺垫。此期虽然被称为词坛之“沉寂期”,但在词的内容取向及情感内涵的抒写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影响着宋词风格流派的基本面貌”[1];不仅如此,词学理论方面也为北宋“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词集的编纂更是承上启下,为宋代词选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一、词学创作:突破花间传统,奠定宋词基本风貌
晚唐五代词体已经成熟,《花间集》的刊刻宣告传统词学观念的确立,即词在题材内容上的“艳科”取向,体性上柔婉艳情的抒发,风格上的香艳绮丽,功能上的娱宾遣兴。南唐词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花间词“娱宾遣兴”的功能,但由于国势衰微以致走向灭亡的形势,使南唐君臣在其词作中融入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尤其是李后主后期的词作蕴涵着无尽的亡国之痛,“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2]4242。因而,南唐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士大夫抒写性情的性质。
从《宋史》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可知,宋朝从立国的960年至1004年的44年间,内忧外患,还有自然灾害,这种环境与在歌舞筵席环境中成熟起来的词作格格不入,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少有心情创作单纯以“娱宾遣兴”为功能的词作。宋朝立国,将崇尚儒术、振兴文教定为基本国策,宋太祖时期,“治定功成,制礼作乐……道德仁义之风,宋与汉、唐,盖无让焉”[3]34。宋太宗即位后,非常重视经籍的搜集,因此到真宗景德二年时,经书已经比宋开国时增长了二十多倍。景德二年(1005),“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版本大备”[3]9998-9999。并且真宗亲自撰写“《崇儒术论》,刻石国学”[3]102。儒学思想统治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艳曲小词的创作。西蜀、南唐皇帝与大臣溺于声乐而走向亡国,孟昶与“五鬼”的小词供奉,南唐李璟与冯延巳的关于“吹皱一池春水”的切磋,皆使北宋初期三位皇帝对艳曲小词怀有深深的警惕性。如《西清诗话》载太祖语云:“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4]大臣们的家国意识也很强,以强国为己任,监督皇帝,避免重蹈西蜀、南唐覆辙(2)《宋史·蜀世家》云:“炯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也。’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不复召。”参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37页。。以致至仁宗时的田况还在《儒林公议》中指出:“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江南李煜时,近臣私以艳薄之词闻于王听,盖将亡之兆也。”[5]社会动荡、崇尚儒学以及君臣对艳歌小词的警惕,致使北宋初期词体创作不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词体亦然。
北宋初期流传至今的词作不多,仅有十二位词人的三十四首词。这十二位词人是和岘、王禹偁、苏易简、寇准、钱惟演、陈尧佐、潘阆、丁谓、陈亚、林逋、杨亿、夏竦。在十二位词人中,寇准、陈尧佐、丁谓、杨亿、夏竦官至宰相,王禹偁、苏易简皆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钱惟演为翰林学士、枢密使,和岘与陈亚曾在朝廷音乐机构工作,潘阆亦在朝廷做过官,后到地方任上,大中祥符三年为泗州参军,卒于官舍[7]。由此可知,此期填词者多为朝廷重臣及贵族官僚,还有隐士林逋。这个时期流传至今的词作虽然只有三十四首,但词作涉及面很广,不仅突破了花间词题材内容上的“艳科”取向,也基本奠定了北宋前期词体创作的总体风貌。
(一)闺情词
这个时期创作的闺情词有八首,占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但这些闺情词或是清新明丽、富有民歌风味,或是在渐变的景物描写中融入淡淡的离情,或是借药名陈闺情,皆一洗花间词香艳之态,对此后宋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林逋的《相思令》无疑是宋初闺情词的典型代表:“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整首词不仅用民歌中复沓的形式,而且把离别之情置于“吴山”“越山”所阻隔的钱塘江两岸。上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增加离别的痛苦;下片以“罗带同心结未成”暗喻离别的不得已,含蓄动人。词的最后以景作结,融情于景,韵味无穷。林逋富有民歌风味的词作显然对欧阳修的词作《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有明显的影响。寇准“性刚自任”[3]7773,而其词非如其人,闺情词写得“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如其《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8]3。
词中借助春天景物、闺房所用的描写一步步展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春雨潺潺,落红铺径,青春伤逝之情便油然而生;密约已过,情人未归,妆镜尘满,无心梳妆,幽怨的离别之情跃然纸上;登楼遥望,满目芳草,离人更在芳草之外,把黯淡销魂的离情推向高潮。整首词以景物描写开始,又以景物描写作结,情景交融,清丽雅致,无一艳俗之语。可以说,晏殊、欧阳修闺情词深得寇准词之风韵。
北宋初期陈亚的闺情词别具一格,以药名抒写闺情,如其《生查子》词三首:“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 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小院雨余凉,石竹风生砌。罢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 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 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这三首词以中药名贯穿,诙谐易懂,生动有趣。可以说,陈亚是宋代第一位创作俳谐词的词人,之后俳谐词渐成规模。
(二)写景词
此期所存三十四首词作中,潘阆的十首写景词《酒泉子》十分抢眼,词人用定格联章的形式,写了十首忆杭州风景的词作,并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百年后的黄静在《逍遥词附记二》中写道:“潘阆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9]708陆子遹亦认为其词“句法清古,语带烟霞,近时罕及”[9]708。杨慎在其《词品》中则指出:“潘阆……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词曲亦佳,有忆西湖《虞美人》一阕云:‘长忆西湖……’此词一时盛传。东坡公爱之,书于玉堂屏风。”[2]475(按此乃《酒泉子》,杨慎误此为《虞美人》)况周颐评价其第三首忆西湖词句“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为“语不嫌质,尤不显说尽”,第七首忆高峰词句“昔年独上最高层,月出见微稜”、第九首忆龙山词句“别来已白数茎头,早晚却重游”、第十首忆观潮后段“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为“句皆清新,境尤高绝,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道”[10]。夏承焘则高屋建瓴地指出潘阆此十首写景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在宋代,最早最著名写自然界风景的词,是潘阆的十首《酒泉子》又名《忆余杭》,也是写杭州西湖的(余杭就是杭州);但是前人还不大注意它在宋词里的地位。”[11]135“在词里连篇累牍以山水风光为对象的,潘阆这十首联章体算是最早的。他继承白居易三首《望江南》,而把它扩展为十首联章,所描写的又恰是新兴的大都市杭州、西湖的景物;当时人们很向往东南的山水、生活,也就自然喜爱这十首词了。”[11]136可以说,潘阆的十首《酒泉子》上承白居易的《望江南》三首,对北宋前期欧阳修的写景词《采桑子》十首以及柳永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皆有典范意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逍遥词》充分肯定了潘阆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宋初令曲,承袭唐余,渐易秾腴为清雅。阆之所作,颇似张志和之《渔父》,诚有如陆子遹所称,句法清古,语带烟霞者也。[12]
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宋初小令之风格,的确是承接唐五代词之余绪。从花间词到南唐词,再到宋初词,从创作实践来看,即是“渐易秾腴为清雅”,其间,潘阆词的创作可以说在这种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咏物词
在唐宋词的发展过程中,“诗客曲子词集”《花间集》中已有咏物词,但数量很少,所咏对象之特点描写亦不甚突出。而到宋初出现了较好的咏物词,典型的代表作是林逋《点绛唇·金谷年年》与《霜天晓角·冰清霜洁》,前者咏草,后者咏梅。林逋的咏草词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载:
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杆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一矣。[13]495
因为有人称赞林逋为“咏草词美者”,引发了梅尧臣、欧阳修等著名人物的好奇心、好胜心,他们也以咏春草为题材,分别写了《苏幕遮》和《少年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林逋和梅尧臣、欧阳修的三首词为“咏春草绝调”。魏庆之亦指出:“林和靖工于诗文,善为词。尝作《点绛唇》云:‘金谷年年……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乃草词耳,但终篇无草字。”[2]207可见林逋咏草词对梅尧臣、欧阳修词的影响。林逋的咏梅词对宋代咏梅词也有示范作用,正如张德瀛所评价:“南宋人咏梅词,谱《霜天晓角》者,仿自林君复。”[2]4162杨亿的《少年游》咏梅词、钱惟演的《玉楼春》咏竹笋词亦可圈可点。在宋代初期词人的影响下,柳永创作了《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咏梅词,晏殊创作了《瑞鹧鸪·江南残腊欲归时》《瑞鹧鸪·越娥红泪染朝云》《玉堂春·后园春早》《望仙楼·夜来江上见寒梅》等多首咏梅词,张先也创作了《汉宫春》“红粉苔墙”咏梅词,一时形成了咏物词创作的小高潮。北宋中期,苏轼继承咏物词传统,创作了三十余首咏物词,其词不仅形神兼备,且有所寄托。之后,咏物词逐渐兴盛,到南宋达到繁荣的景象。其间,北宋初期咏物词创作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四)抒怀词
北宋初期三十四首词中,抒写士大夫情怀者就有七首之多。这些词作用语清丽,意境婉美,不庸俗浮艳。如王禹偁的《点绛唇》“感兴”:“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词人先写江南佳丽地的水村渔市,袅袅炊烟的恬静风光,过片笔锋一转,目光转向辽阔的天际,征鸿成行,正展翅飞向目的地。词人从高飞的征鸿联想到自己虽少有大志,要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处贬所,无人理解的现状,于是逼出末尾一句“谁会凭阑意”,把无人领会自己理想的怅然心情借景物抒发出来。无论是景物描写还是内在情感的抒发,晏、欧词皆有此词风味。寇准的《蝶恋花·四十年来身富贵》一词之意境不仅被欧阳修出神入化地在创作中发挥到极致,而且对苏轼的旷达词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阳关引》更被广泛赞誉: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8]3
此词加入边塞因素,《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云:“寇莱公《阳关引》,其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14]《钦定词谱》卷十八在《阳关曲》调下注云:“此调始自宋寇准。词本隐括王维《阳关曲》而作,故名。”[15]315因而此词不仅对范仲淹豪放词《渔家傲》有影响,而且还开了之后隐括词的先例。
(五)宫廷词
宫廷词为宋代词人抒写内容之一,而开其先者为北宋初期词人,此期创作的宫廷词就有七首,涵盖宫廷祭祀、宫廷宴饮、颂圣、寿圣等内容。《全宋词》所选第一位词人和岘的三首词《导引·气和玉烛》《六州·严夜警》《十二时·承宝运》,即为开宝元年(968)朝廷举行郊祀时所填词作。和砚“建隆初,授太常博士,从祀南郊,赞导乘舆”,后“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3]10139-10140。在这三首词中,和砚不仅描写了朝廷祭典的盛况,抒发了对皇帝的赞美之情,还高度赞誉“诸侯述职,盛德服蛮夷”的大宋国威与“时清俗阜,治定功成”的清明富足景象,并对“混并寰宇,休牛归马,销金偃革,蹈咏庆昌期”给予深深的祝福。三首词写得富艳精工,雅致大气。苏易简也创作了《越江吟》一词,并且迎合皇帝崇雅心态:
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换玉》,三曰《峡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只名曰《贺若》。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改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词。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舆挽。玉麟背冷清风远。”[16]
此词以超脱凡世如仙境般的意境描写宫廷宴会,颂圣及歌舞升平的情感溢于言表,华而不俗,非常符合太宗求雅的标准(3)脱脱《宋史·乐志》云:“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44页。,也得到后代词学家的肯定,明代杨慎选此词入其词选《百琲明珠》中。丁谓创作的两首《凤栖梧》皆为寿圣词,第一首“十二层楼春色早”把皇宫京城比作蓬莱仙境,写了宫中在莺啭乔林、鱼游于藻、太液微波、王孙斗草祥和明媚的日子里,迎来皇帝的诞辰,京城万人瞻仰,祝颂皇帝万寿无疆。第二首“朱阙玉城通阆苑”亦把皇宫比作仙境,但在描写中只就仙境而发,不涉凡尘景象,结尾用“壶中日月如天远”祝颂主人公长命百岁、如天不老。两首词各有特点,丽而不俗。夏竦虽主要活动在仁宗时期,但其宫廷词《喜迁莺》作于真宗时期:
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新秋。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悦。[17]1660
词作用语华丽而典雅,比喻浪漫而贴切,整体呈现出一幅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宫廷歌舞场景,“富艳精工,诚为绝唱”[2]293。
宋初词人用小词写宫廷祭祀、宫廷宴饮、颂圣、寿圣等庄重的题材,且写得富丽堂皇、精工典雅,无浮艳之词,有求雅之趣,对北宋前期词人如柳永《送征衣·过韶阳》《倾杯乐·禁漏花深》《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永遇乐·薰风解愠》《醉蓬莱·渐亭皋叶下》、晏殊《喜迁莺·风转蕙》、张先《庆同天》等词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柳永同类词的创作影响尤大。之后,宋代词人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诸如描写时令节序、宫廷宴游等内容更加丰富的宫廷词,可以说北宋初期的宫廷词为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词学理论:提出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
由于时代原因,南唐词已经出现了抒写性情的倾向,但是没有留下有关论述词学观念的理论文章。而北宋初期这种局面得到了改观,词人不仅在创作中抒写士大夫意识,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呈现。北宋初期的潘阆在其《逍遥词附记》中明确提出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
茂秀茂秀,颇有吟性,若或忘倦,必取大名,老夫之言又非佞也。闻诵诗云:“入廓无人识,归山有鹤迎。”又云:“犬睡长廊静,僧归片石闲。”虽无妙用,亦可播于人口耶。然诗家之流,古自尤少,间代而出,或谓比肩。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岂可容易而闻之哉!其所要《酒泉子》曲十一首,并写封在宅内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唱,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其间作用,理且一焉。即勿以礼翰不谨而为笑耶。[9]708
此文不长,是潘阆写给一位晚辈诗人的书信,但内涵深刻。作者在文章开头鼓励年轻的诗人茂秀,指出其“颇有吟性”,即有诗人的性情气质,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并举出茂秀写得较好且广为传播的诗句。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怎样才能成为一流诗人时,作者提出了“诗词一体”词学观念。研读《逍遥词附记》,认为其诗词一体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体演化论
潘阆认为一流的诗人自古就很少,后代诗人要想超越前代一流诗人的成就,与其比肩并驾、闻名于世,非常不容易,要“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由下文作者提到自己创作的词《酒泉子》十首可知,此处的“变风雅之道”,不仅指诗歌,亦指词。郑玄《诗谱序》指出: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18]
显然,郑玄所谓的“变风、变雅”主要是指诗歌的内容,而潘阆的“变风雅之道”兼具内容与形式。他对于自己的《酒泉子》十首自视很高,认为这十首词即是“变”的结果。当时他以著名诗人身份由创作诗歌转而为填词,这是其形式之变;认为如果这十首词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创作,很难成为一代名家,因为大唐诗坛上写景诗数不胜数。就内容而言,花间、南唐诸君已把艳词唱尽,潘阆若继续写作艳词,一时难以超越,他就变香艳为清疏,用定格联章的形式,填写了十首回忆杭州的景物词,一扫晚唐五代词坛的绮艳风气,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使其在宋初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其内容体性之变。潘阆认为,诗词创作只有不断变化,才能超越前人、别出新意。这种“变”的观念,不仅对宋词创作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宋代的诗文创作。
(二)立意高远,意境深厚
潘阆在强调“变”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词立意的高远与意境的深厚,“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如此,才能把“盘泊之意,缥缈之情”蕴含其中。“盘泊”意谓滞留、盘踞,皎然《诗式》之“辨体有一十九字”云:“立言盘泊曰意。”[19]卷八林逋诗亦云:“时闲盘泊心犹恋,日后寻思兴必狂。”[20]此指含蓄婉转、迂回曲折之意味。“缥缈”指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的样子。皎然《诗式》之“辨体有一十九字”还说:“缘景不尽曰情。”[19]卷八此指深厚幽深、悠长绵远的情感。显而易见,潘阆在用诗歌理论阐释词中的立意、用情,可以说这是宋词诗化的最早宣言,其对宋词的影响亦不言而喻。潘阆在北宋初期诗坛十分活跃,“潘逍遥阆,有诗名,所交游者皆一时豪杰”[17]1423,“一时若王禹偁、柳开、寇准、宋白、林逋诸人皆赠答。盖宋人绝重之也”[21]。此非虚言。时人宋白赠其诗赞道:“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17]1664他把诗歌创作作为人生的主要意义,他曾在《叙吟》中写道:“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上李学士》诗云:“试把平生业,来投作者看。”《书诗卷末》诗云:“一卷诗成二十年,昼曾望时夜忘眠。”[22]可以说,潘阆是一个以诗为生命的人。其诗集中有《谢寇员外准见示诗卷》一诗,可知寇准早年曾将己作送于潘阆指正。欧阳修在《书逍遥子后》云:“熙宁三年五月九日,病告中校毕。时移太原,未受命。续得民间本,又添《无鬼》以下七篇。世传《逍遥子》多脱误,此本雠校虽未精,然比他人家本,最为佳耳。”[23]可见欧阳修非常欣赏潘阆的诗文,搜求其诗文不遗余力。因为潘阆精通诗道,并认为诗词一体,因而他认为词作应该如诗歌一样,只有立意高远、意境深厚,才能收到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词学观念被苏轼以及之后众多词人所继承,滋润着一代词人的创作。
(三)超逸脱俗,清丽雅致
自文人创作词以来,词体创作即朝着雅化的方向发展。刘禹锡在其《竹枝词序》中指出: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24]56
由此可知,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九篇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同屈原创作《九歌》一样,认为居官之地所歌《竹枝》“伧伫不可分”“词多鄙陋”,于是想把它改造为“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的雅致之作。
《花间集·序》的作者欧阳炯胸怀同样的理想,他有感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的创作现实,于是想编辑一部“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的雅致词集,以供歌舞筵席间之娱宾遣兴:“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25]1刘禹锡、欧阳炯提倡雅词,但不排斥香艳,即词可以是“狭邪之大雅”[26]295,这与晚唐五代词的创作实际相一致。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宋初潘阆的词学观念则大相径庭,他认为自己所作之词不是用来在“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歌舞宴席间演唱,而演唱环境须是“水榭高歌、松轩静唱”,即其词须在疏柳栖鸦、初月落霞的水榭“高歌”,而悠扬的歌声荡漾在疏柳晚霞间,这是何等的旷放飘逸!须是在四季林青、幽静雅致的松轩“静唱”,歌者之声与松风清音相应和,这又是何等的高雅脱俗!此与里中儿联歌《竹枝》歌、绮筵绣幌间演唱花间词判若两途。在这篇《附记》中,潘阆虽然没有提到花间词,但似乎句句针对花间词而发,或者说句句是在针对晚唐五代词风而发。潘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高雅脱俗,他在《赠道士王介》一诗中称赞王介“诗无入俗章”“出语芝术香”[22],虽是对王道士的赞誉,亦是自己诗学观的表现,因此,其诗词皆无俗艳之作。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载的柳永与晏殊的经典对话含蓄地表明晏殊在词体创作中求雅的心态(4)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这种追求与潘阆追求的脱俗清丽毫无二致。
由潘阆当时在诗坛上的地位可知,其“诗词一体”论不仅影响同时代的王禹偁、寇准、林逋等词人的创作,亦为北宋前期晏殊、欧阳修等词人树立了典范,甚至影响了苏轼“以诗为词”以及之后词人的创作。这一理论也影响了王安石的词学观:“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17]2091王安石的论述与潘阆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词集编纂:词学功能的秉承及词集编纂体例、观念的超越
晚唐五代词集《云瑶集杂曲子》《花间集》皆为时人歌曲唱本,为“应歌”而编。北宋初期,词集编纂者继承了这一观念,先后编撰了《家宴集》《金奁集》《尊前集》三种词选。
(一)《家宴集》对唐五代词学功能的继承
此期编纂最早的词选《家宴集》今已散佚,但从词集名可以确定此集的编纂目的在于宴饮佐欢、娱宾遣兴。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家宴集提要》中云:“序称子起,失其姓氏,雍熙丙戌岁也。所集皆唐末五代人乐府,视《花间》不及也。末有《清和乐》十八章,为其可以侑觞,故名《家宴》也。”[27]由此可知,此集编纂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其与《花间集》的功能相同,即歌舞宴席间的娱宾遣兴。所收词作已不可考,但在陈振孙看来,创作水平不及花间词。
(二)《金奁集》对唐五代词学功能的继承与编纂体例的创新
《金奁集》亦刻于此时,明正统年间吴讷《百家词》本《尊前集》在李王《更漏子》调下注云:“《金奁集》作温飞卿。”[26]120可见《金奁集》早于《尊前集》刻印。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著录,表明此集在南宋传播不广。《金奁集》选温庭筠(六十二)、韦庄(四十八)、欧阳炯(十六)、张泌(一)四人词作一百二十七首;还有十五首《渔父词》,题张志和撰,据前人考证,乃他人和张志和之作[28]185。也有研究者则认为,“这些作品与存世张志和《渔歌》风格一致、情调一致,精神神韵都相同,更大可能即张本人所作”[29],可备一说。此集共选词作一百四十二首,其所选词作除十五首《渔父》词外,其余均出自《花间集》;与《尊前集》重复者只有温庭筠三首《更漏子》,即“柳丝长”“金雀钗”(《尊前集》收录在李煜名下)“玉炉香”(《尊前集》收录在冯延巳名下),只是两个集子中三首词个别字词有所不同;还有在《尊前集》中拼凑韦庄两首《菩萨蛮》为一首而录入李白名下的“游人尽道江南好”(《花间集》作“人人尽说江南好”)。《金奁集》所收词作基本不出《花间集》范围,但编排体例不同于《花间集》的“以人而系词”,而是“依调以类词”,“估计是宋人为应乐工歌伎演唱的需要,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之词而成”[28]185。但是,词集最后录入题为张志和十五首《渔父》词与本集所选其他词作风格颇为不谐,今观十五首《渔父》词,尽写“五湖烟水”中渔人“不钓名”“乐性灵”的自在生活,没有求官的寄托,亦无借隐而求名的寓意,词中展现的是渔人的劳作与满足、从容与享受的真实生活,而这种生活还时时被人羡慕着:“水边时有羡鱼人。”《花间集》中收录和凝《渔父》词“白芷汀寒立鹭鸶”一首,顾夐《渔歌子》“晓风清”词一首,抒发其“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的时光如梭、无心逐名的恬淡心绪。收录孙光宪《渔歌子》二首,抒发其“谁似侬家疏旷”的心境。收录李珣《渔歌子》四首,抒发其“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的看淡荣辱名利的心情;还有“任东西,无定止,不议人间醒醉”的无所拘执。总体说来,数量不多,只有九首,而《金奁集》选录十五首《渔父》词,而不选《花间集》中同类题材的词作,不知何意。朱祖谋认为此集为“宋人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词,各分宫调,以供歌唱”[28]185,也没有提到十五首《渔父》词,难道是受当时词学观念的影响而选入词集?
《金奁集》的编纂体例是“以调以类词”,即按照宫调编选词作,可以说开创了宋代词集编纂的一种新体例。北宋前期按照宫调编纂的词集有柳永的《乐章集》、张先的《张子野词》,当皆受《金奁集》编纂体例的影响。
(三)《尊前集》对《花间集》编纂观念的超越
此期在词选编纂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是《尊前集》(5)朱彝尊《书〈尊前集〉后》云:“康熙辛酉冬,予留吴下,有持吴文定公手抄本告售……取顾氏本勘之,词人之先后、乐章之次第,靡有不同, 始知是集为宋初人编辑,较之《花间集》,音调不相远也。”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521页。萧鹏《群体的选择》云:“《尊前》所载不涉及北宋,当是宋初人编。”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其词集名告诉我们其编纂目的仍为“娱宾遣兴”。翻检其选词可知,它是《花间集》之后又一部唐五代词的总集,共收三十六家词人词作二百八十九首。《尊前集》的编辑体例与《花间集》同,按词人编排词作,只是人君之词编次在前,先后收录唐明皇(一)、唐昭宗(二)、唐庄宗(四)、李王(五)四家词十二首;而后是人臣之词,先后收录唐代词人李白(十二)、韦应物(四)、王建(十)、杜牧(一)、刘禹锡(三十八)、白居易(二十六)、卢真(一)、张志和(五)、司空图(一)、韩偓(二)、薛能(十八)、成文幹(十)等十二家词一百二十八首,从收录词人的编排顺序可以看出,编辑者没有严格按照词人所处时代顺序排列;唐代词人之后,收录南唐冯延巳词三首;冯词后,编者按照《花间集》收录词人的顺序,收录温飞卿(五)、皇甫松(十)、韦庄(五)、张泌(一)、毛文锡(一)、欧阳炯(三十一)、和凝(七)、孙光宪(二十三)、魏承班(六)、阎选(二)、尹鹗(十一)、李珣(十八)等十二家词一百二十首;花间词人之后,又重复编排收录李王(八)、冯延巳(七)、李王(一)等二家词十六首;之后又收录庾传素(一)、刘侍读(一)、欧阳彬(一)、许岷(二)、林楚翘(一)、薛昭蕴(一)、徐昌图(三)等七家十首。按照一般的编辑体例,李王(煜)、冯延巳词不应该在同一选本中重复编辑,尤其李王词还重复了两次;而花间词人薛昭蕴也应该按照《花间集》编排顺序置于韦庄之后。这种编辑现象的出现原因可能如舍之先生推测:“疑此皆后人增入,非原本次序也。”[30]这种推测很有道理,由此表明在当时《尊前集》不止一种版本。《金奁集》在《菩萨蛮》调下注有“五首已见《尊前集》”[28]165,好像表明《金奁集》在《尊前集》之后成书,但现在所见《尊前集》选温庭筠《菩萨蛮》五首、欧阳炯四首、魏承班一首、尹鹗二首、林翘楚一首皆不与《金奁集》同,此又表明,《金奁集》的编辑者看到的一定不是原刻本,可能是在《金奁集》之后的重刻本,从而印证了舍之先生的推测。
《尊前集》所选词作与《花间集》相同者凡十首;所选词调与《花间集》相同者也仅有《菩萨蛮》《清平乐》《江城子》《巫山一段云》《浣溪沙》《更漏子》《满宫花》《生查子》《南乡子》《西溪子》十个,加上被疑为后人增入的薛昭蕴所用《谒金门》词调,凡十一个,仅占《花间集》所用七十七个词调的七分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尊前》的编者曾见到《花间》,只因《花间》的时代和地域过于集中,有意要在花间之外增选温庭筠之先的唐人词以及前、后蜀以外的五代词,再补充被赵崇祚遗漏的花间词,总为一集,与《花间》并行不悖”[31],蒋哲伦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与《花间集》对比,《尊前集》显示出与《花间集》异趣的词选编辑思想。
其一,词史发展观。《尊前集》注意词体发生发展的进程,展示了文人依曲谱填写齐言词发展为长短句的变化过程。《尊前集》选有盛唐词人词作,如唐明皇、李白词,选取的李白词有齐言词句与长短句两种。晚唐李濬《松窗杂录》记载李白填写齐言词句的情况: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龟年俱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瓈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32]2261-2262
这是一幅词体初创时依谱填词的生动画面。《清平调》这支曲子原有配合的歌词,而唐明皇认为赏名花,对美妃,不能以旧词入曲,而应该依曲填写新词,于是使李龟年“持金花笺宣翰林学士李白”为这支曲子填词。李白一定是熟悉《清平调》的,他醉意未消,挥笔填了“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三首词作。因为是填写的齐言词句,但曲句不是整齐的,所以,“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梨园弟子的演奏要“约略调抚丝竹”,使整齐的词句更加贴合不整齐的曲句,而皇帝也要“调玉笛以倚曲”,“迟其声以媚之”,演奏时尽可能使不整齐的曲句与齐言词句做到水乳交融、协调一致。这应该是词产生初期常有的状态。但随着词体的成长,文人也在不断努力,不仅“依谱填词”,而且尽可能做到“以曲拍为句”,稍后李白所作的《清平乐》五首以及《忆秦娥》《菩萨蛮》词即为长短句。唐明皇精通音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时才士,始依乐工拍但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13]537到了中唐时期,“以曲拍为句”被明确提出,刘禹锡所作《忆江南》词题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33]晚唐以谱填词更为普遍了,唐昭宗时的苏鹗在其《杜阳杂编》中指出,咸通九年(868),“(李)可及恃宠,以无改作。可及善转喉舌,对至尊弄眉眼,作头脑,连声作词,唱新声曲,须臾即百数方休。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为之‘拍弹去声’”[32]2213。从《尊前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唐齐言词句入曲的情况占绝大比例,《尊前集》选中唐词人刘禹锡、白居易词作较多,选刘禹锡词作三十八首、白居易二十六首,其中刘禹锡齐言词如《杨柳枝》《竹枝》《纥那曲》《浪淘沙》有三十五首,白居易齐言词如《杨柳枝》《竹枝》《浪淘沙》有二十首,还有卢真《杨柳枝》一首。《尊前集》收录中唐词凡八十五首,其中齐言词就有六十四首,占收录词作的三分之二强。晚唐五代词的创作出现了新局面,长短句成为词坛主流。《尊前集》通过选词展现了词体成长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尊前集》的编选者应该是词坛上的内行里手。《尊前集》的编纂对其后意在存史的词籍编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二,客观反映了唐五代词体的创作风貌。欧阳炯《花间集·序》曰:“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以阳春之甲,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5]1欧阳炯编纂《花间集》的目的很明确,即集中所选词作,是让歌女歌唱以增加雅集中“西园英哲”的欢乐,使南国美丽的女子不再歌唱尘俗曲子;而《尊前集》的编者则打破这种局面,大量选取了富有民歌色彩的“莲舟之引”。
《尊前集》选取了很多如花间词一样的艳词,但比较而言,《尊前集》所选艳词更口语化,更俗艳一些,民间气息更浓。如《尊前集》所选欧阳炯的《更漏子》:“玉阑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怎生嗔得伊。”词中的“独自个”“叵耐”“怎生嗔得伊”皆是当时俗语。号为“曲子相公”的和凝以创作香艳词著称,《花间集》选取其词二十首,整体上还算含蓄有致,而《尊前集》选取和凝词七首则不然,其中有《江城子》组词五首:
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爇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
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
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
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
帐里鸳鸯交颈情。恨鸡声,天已明。愁见街前、还是说归程。临上马时期后会,待梅绽,月初生。[24]477-478
词人用定格联章的形式创作《江城子》五首,五首词之间联系紧密,描写一女子与心上人晚上约会的整个过程,从布置环境、急切等待、含笑迎接到相见温存、两情相悦之情景,跃然纸上。吴梅评价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后人凭空结构,皆本此词。”[34]《花间集》不选此组词作,显然编者有其选录标准,正如吴昌绶所言:“《花间》虽亦主词采,然唐人乐府之遗,仍以应歌为主也。”[35]《花间集》选词虽“以应歌为主”,但是“主词采”的,俗词艳曲则不被选入。《花间集》选孙光宪词六十一首,仅次于温庭筠,但如其《浣溪沙》“试问于谁分最多,便随人意转横波,缕金衣上小双鹅。 醉后爱称娇姐姐,夜来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长么”之类的词作,《花间集》亦不选,个中原因当如陈廷焯所言:“赠妓之词,原不嫌艳冶。然择言以雅为贵,亦须慎之。若孙光宪之‘醉后爱称娇姐姐,夜来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长么’,真令人欲呕。”[36]分析切中要害。
较《花间集》而言,《尊前集》的编纂者更多地选入富有民歌色彩的《杨柳枝》《竹枝》《采莲子》等词作,诸如选取刘禹锡《杨柳枝》十二首、《竹枝》十首、《浪淘沙》九首,白居易《杨柳枝》十首、《竹枝》四首、《浪淘沙》六首,张志和《渔父》五首,薛能《杨柳枝》十八首,成文幹《杨柳枝》十首,皇甫松《竹枝》六首,欧阳炯《渔父》二首、《春光好》九首,李珣《渔父》三首等一百余首,占其选词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花间集》选取《杨柳枝》《竹枝》《采莲子》等这些富有民歌色彩的词作则很少,尤其是极具民歌风味的皇甫松之六首《竹枝》词,一首不选,《花间集》编者的求雅意趣昭然若揭。另外,通过对比《花间集》与《尊前集》所选共同的词人词作可以发现,晚唐五代词人创作《杨柳枝》《竹枝》《采莲子》这些清新明快的曲子词大幅度减少,文人创作不仅在形式上多以谱填词,以曲拍为句,多填写长短句词,内容体性上也几乎集体转向了艳情抒发。因此,又可以清楚地看到盛唐、中唐、晚唐五代词作的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变化过程。
《尊前集》所选词作内容体性丰富多彩:言情、言志、边塞、山水等,不一而足,渔翁、采莲女、饮酒者、游乐者、游船者等皆可在集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歌曲。风格不拘一格:婉约、豪放、旷放等各放光芒。同时还可以使我们具体领略到咏题词的创作情况,如《杨柳枝》《浪淘沙》《潇湘神》《渔父》《临江仙》《巫山一段云》等,从而为黄昇所谓的“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题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做了很好的注脚[28]592。形式上小令、长调并举:《花间集》所选全部为令词,而《尊前集》则选取了一些慢词长调,如收录了唐庄宗词《歌头·赏芳春》、杜牧词《八六子·洞房深》、尹鹗词《金浮图·繁华地》《秋夜月·三秋佳节》等。《歌头》始见于《尊前集》,《钦定词谱》调名下注曰:“《尊前集》注大石调。”词后注云:“此词无别首可校。”[15]695《金浮图》亦始见于《尊前集》,《钦定词谱》在调名下注云:“调见《尊前集》。”在词后注云:“此词无别首可校。”[15]423因而《尊前集》保存了词学史上用此调创作的唯一词作。《八六子》始见《尊前集》所收杜牧词,虽与北宋诸家多有出入(如秦观《八六子》为88字,杜牧词为90字),而由《尊前集》的录入使宋代传世词调又多一体。《秋夜月》也是始见于《尊前集》,《钦定词谱》在词调下注云:调见《尊前集》,因尹鹗词起结有“三秋佳节”及“夜深窗透,数条斜月”句,取以为名。词后注云:“此调尹词、柳词大同小异,但柳词自注宫调,其平仄恐各中律吕,难以参校。今《词律》以前后段对校,酌注可平可仄,颇与柳词暗合。仍之。”在柳词后注云:“此即尹鹗体,然句读参差,恐有讹脱,故录以备一体。”[15]360因而,从《尊前集》中,我们可以知道宋前文人创作的慢调长词也为后人诸如柳永等提供了创作上的经验借鉴。
总之,北宋初期虽然词体创作不振,留存至今的词作很少,但在整个词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词体创作为北宋前期创作甚至宋代词学创作奠定了基本风貌;“诗词一体”词学观念的明确提出对宋代的词学创作与理论皆有指导意义;词集编纂更是承前启后,尤其是体例上的创新,对宋代及其后的词籍编纂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所有这些词学贡献,应该被肯定或客观评价,而不应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