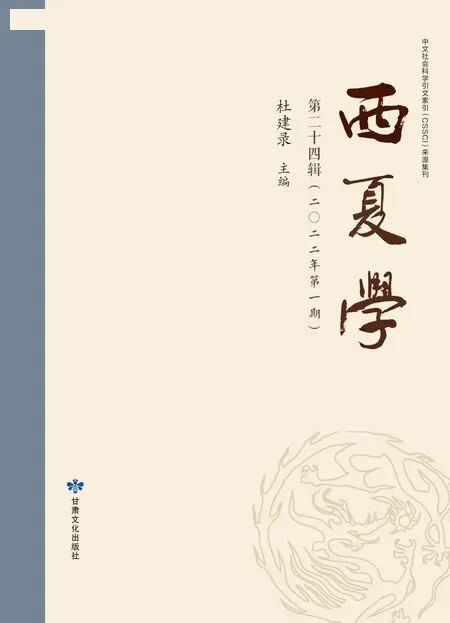延安何家坬石窟再研究
——兼论北宋沿边党项熟户佛教信仰特点
袁 頔
前 言
何家坬石窟位于陕西省志丹县旦八镇何家坬村,毗邻樊川河。在陕北石窟群中,该窟是唯一一座功德主主体基本全由党项人构成的窟室①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页。。透过这一佛教艺术遗珍,可以讨论宋夏战争、地区信仰及民族交流等诸多问题。前辈学者针对此窟已有集中研究,如姬乃军先生《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对何家坬石窟的建筑结构、造像题材作了基本介绍②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第18—26页。;段双印、白宝荣先生《宋代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③段双印、白宝荣:《宋代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91—99页。,李静杰先生《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④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3—115页。,杜建录、邓文韬先生《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志丹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⑤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等文皆关注到该窟内容丰富的题记,其中尤以杜建录、邓文韬之文对题记背后所反映的宋军军制、佛教结社、民族融合等问题探究得最为全面细致;石建刚先生《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一)——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①石建刚、杨军:《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一)——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7—29页。《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②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第68—78页。两文对何家坬石窟形制、题材、题记等基础信息进行了整体分析并就主要造像内涵、义理展开解读,同时检索出石窟营建蕴含的多民族文化交流因素。总的来看,学界已给予何家坬石窟相当的重视,但仍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如此窟主尊具体是何身份,窟室所承担的实际功能等方面尚无探讨,故笔者不揣冒昧,在前辈学者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再做分析,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校正。
一、窟室内容与相关背景简介
(一)窟室内容简介③该窟形制、造像等资料参考陕西石窟内容总录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石窟内容总录·延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
何家坬石窟的基础资料已经公布,为便于展开对窟室的进一步分析,兹在此简略概述该窟的形制与造像。何家坬石窟开凿于今志丹县旦八镇何家坬村西南,窟室坐南面北,由前廊和后室组成。前廊宽约4米,进深1.6米,高2.52米,现存天王、力士等造像内容。后室为中央佛坛窟,坛上主尊塑像现已不存,残有八边形仰莲座3个(图1);南壁雕刻小坐佛15排;西壁下部中央有一龛,龛内刻一倚坐佛并二弟子,龛外壁面刻14排小坐佛;东壁结构与西壁类似,亦是龛内一佛二弟子的组合并龛外十余排坐佛,此龛内佛为结禅定印的趺坐佛,依据陕北造像传统,窟室两侧壁佛龛内应分别为倚坐弥勒佛与禅定印趺坐阿弥陀佛;北壁题材较为丰富,雕刻有弥勒、罗汉、自在坐观音等内容(图2)。

图1 何家坬石窟后室中央佛坛现存仰莲座④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图2 何家坬石窟后室北壁⑤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3页。
(二)建窟功德主身份与窟室地理位置
何家坬石窟前廊后壁门上现存有内容详尽的建窟题记一方,且大部分行文清晰可辨(图3)。此处题记所涉内容颇多,不仅反映出何家坬石窟功德主的家族背景,还蕴含有关于北宋蕃兵编制、佛教结社组织形式,以及民间蕃汉融合等各方面宝贵历史信息①何家坬石窟题记录文及校正信息以及关于题记内容所涉历史、军事、民间活动等方面的相关解读,详见段双印、白宝荣:《宋代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96—98页;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石建刚、杨军:《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一)——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22—25页。。最为关键的是,题记当中对窟室营建的主导者“首领吃多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如开头“维南瞻部洲大宋国修/罗管界保安军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挥施主惟那头/首领吃多遇等壹佰壹拾人……”“首领三班吃多遇小胡行者”、结尾“绍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八日,惟那吃多遇/本族巡检胡”等。根据题记所述内容,杜建录先生、邓文韬先生曾指出吃多遇其人兼具多重身份:他既是佛教社邑的维那头,小胡族蕃众的酋长“首领”,还是宋朝任命的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挥,并带有“三班”职衔②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9页。。在旷日持久的宋夏战争期间,久居于宋地边境的党项熟户是宋西北防御体系中颇为倚重的一支力量。由于双方连年不断拉锯,宋朝在数次野战败绩后采取修筑堡寨、坚守耗敌的作战方法以应对夏军攻势。受制于重文轻武的政策,许多边地驻防宋军战力低下,难与夏人匹敌,但土生土长的熟户却“习知山川道路,知西人情伪,材气勇悍”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四,治平二年二月丙午,中华书局,1992年,第4949页。。他们“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斗”④[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4页。,对生存居所的保护意识较强,并敢于同来犯敌军作战。故富弼等重臣曾上表,支持招徕沿边蕃族,防御西夏犯边。所以居住于鄜延、泾原一带的党项、吐蕃等族得以大量加入宋军并被授予各级军职。据《宋史》描述,在西北蕃兵群体中:

图3 何家坬石窟编号T1题记拓片局部④此图由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副教授提供,特此感谢。
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次为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以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检者,奉同正员。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番兵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4751页。
故吃多遇是在此背景下被吸纳为边军中的党项军官,担任“本族巡检”职务,率领蕃兵保卫沿边堡寨。同时由窟室题记可知,信奉佛教的吃多遇亦是族内地位较高的“惟那头”,其顺理成章地成为佛教活动领导者,积极组织家人及其他数个小型佛教社邑,在本寨辖区内合力修建起何家坬石窟。
另外,从窟室坐落的地理位置来看,何家坬石窟位于今陕西省志丹县,建成时该地为鄜延路德靖寨所辖。德靖寨①关于北宋时期德靖寨的相关记载,可参考古籍有[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陕西二》,中华书局,1977年;[宋]王存撰,魏嵩山,王文楚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永兴军路》,中华书局,1984年;[宋]曾公亮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上》,商务印书馆,2017年。涉及德靖寨历史地理、军政状况研究的相关专著有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彭向前:《党项西夏名物汇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日]前田正名:《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是宋西北边境一座防御要塞,其地扼咽喉“北控洛河川,入西界金汤镇大路,旧号建子城,天圣中赐今名。东至军六十里,西至金汤镇六十里,南至保胜寨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②[宋]曾公亮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上》,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87页。,并且这一地区始终受到宥州嘉宁军司的大军威胁。《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录有“贼三十万众”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中华书局,1992年,第7927页。进攻鄜延,由史料分析可以发现,德靖寨作为一处沿边堡寨,不仅居于要道,还随时处在战争爆发边缘。
经由对吃多遇身份以及何家坬石窟地理位置的了解,我们已知此窟营建领导者是宋军蕃兵军官、任职为“本族巡检”的党项族人,且窟室区位堪称四战之地,常年笼罩在战争氛围当中,面临着外部敌人进犯的险境。通过这些背景分析,我们明确了何家坬石窟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这是下文进一步讨论洞窟造像内容选择、具体功能等问题的出发点与现实依据。
二、窟室主尊身份判定
就何家坬石窟造像来看,其题材、布局都较为清晰:前廊主要以镇护窟室的天王为主;后室为整座洞窟的核心部分,室内中心佛坛上主尊为三佛;东、西、南壁面皆大量雕刻千佛;北壁则有弥勒、观音、罗汉等神祇的出现。石建刚先生曾撰文对该洞窟后室内容组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何家坬石窟的营建受到末法思潮的强烈影响,窟内千佛变相、十六罗汉等造像均反映出末世度人、护佑正法的意味,这样的题材选择同石窟所处艰难残酷战争环境、民众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息息相关①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第70—71页。。关于何家坬石窟的落成带有明显末法烙印,彰显出身为军人群体的功德主渴望消灾除难、顺利往生的心理这一观点,笔者基本赞同,但其文中虽提出了窟内主尊即中央佛坛三佛身份的几种可能,却并未给予明确的判定,因而也无法进一步分析整窟总架构。在末法思潮盛行的大背景下,结合此窟现存造像与同时期可参考案例,笔者以为何家坬石窟后室佛坛上应是法身佛毗卢遮那、报身佛卢舍那、应身佛释迦所组合形成的三身佛,该窟整体呈现出法身统摄十方三世的宏观结构。
陕北宋金石窟中以三佛作主尊颇为流行,前辈学者已将不同类型的三佛组合归纳为数种模式,如竖三世佛、横三世佛、三身佛等②三佛组合归纳以及相关材料的梳理、讨论详见齐天谷:《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39—40页;孙修身:《陕西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内容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60页;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第10—17页;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第25—29页;胡同庆:《陕西钟山石窟3号窟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文博》2010年第1期,第57—67页;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一辑,第92—120页;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针对何家坬石窟主室内的三佛,笔者判定其身份为三身佛有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何家坬石窟内主尊造像虽已不存,但根据早年间的照片显示,窟室中央佛坛上留有三尊趺坐佛像(图4),它们对于判断此组合的身份极为关键,因在陕北石窟中,凡弥勒佛造像基本采用倚坐姿势表现,这一点可以在延安众多出现弥勒题材的窟室中得到印证,如富县大佛寺第3窟主尊倚坐弥勒佛;清凉山第11窟、王家坪石窟、红庙沟石窟、新茂台石窟等处主尊均为二跏趺坐佛并一倚坐弥勒。何家坬石窟后室西壁亦有倚坐弥勒雕刻,而佛坛上三尊佛却均为趺坐,故其中应无弥勒佛的存在。另外,观察坛上遗存的佛座能够较为直观地看出,三处莲花台形制近似、截面较小,难以支撑倚坐造像,说明佛坛三佛营建之始便未有弥勒佛的设置,因此包含弥勒在内的竖三世佛,以及“释迦+药师+弥勒”“释迦+阿弥陀+弥勒”等组合非何家坬石窟主尊。

图4 何家坬石窟主室旧照片①此图由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副教授提供,特此感谢。
第二,作为精心设计的统一体,窟室四壁设置自然与主尊有密切关联。从题材布局上来看,该窟内主室东、西、南壁均以千佛为主,北壁则主要是十六罗汉、观音等神祇的组合,此种题材选择与配置在同期各地佛教造像中颇为盛行。如山西双林寺罗汉殿现存宋代十八罗汉并观音,罗汉安放于观音两侧形成“十八罗汉朝观音”结构;敦煌西千佛洞五代、宋第19窟内东西二壁面绘制百余身罗汉;瓜州榆林窟第39窟属回鹘窟室,内部壁画营建时代约与北宋相当,其主室内南、北两壁绘制罗汉与弥勒,主室甬道处则绘有千手观音菩萨。值得注意的是,榆林窟第39窟主室内设置有四面开龛之中心柱,昭示了此窟室各壁题材与法身信仰的密切联系,而罗汉、观音、弥勒的组合在何家坬石窟内同样出现,这对思考何家坬石窟主尊身份起到重要参照作用。
早在北朝时期,由于华严思想体系的不断发展与相关理论的完善,代表法身的卢舍那佛信仰愈加勃兴,不仅将佛法推向更高地位,还使得法身不灭的观念流行开来。卢舍那佛的神格化与末法背景下众生期盼佛法永恒的心理两相契合,加之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接踵而至,令末法氛围更为浓重。在此环境下,突出护世护法思想就成为佛教造像的重要目的,故佛教造像的内容也随之变化,北朝晚期作为释迦法身的卢舍那佛大规模流行就是末法时期人们渴望佛法永存的表现之一,而三身佛概念在6世纪出现即与末法思想相关联②郑炳林、吴荭:《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北周石窟造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同样,11世纪左右整个中国北方均受到“法难将至”思潮的影响,且与陕北十分接近的西夏、辽朝地区末法思想尤为强烈①这一点从现存辽、西夏佛教遗迹可见一斑,在朝阳北塔中出土辽代文物中,有许多关于“末法”的直接描述,如“像法只八年”“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西夏石窟中则骤然兴起自中唐以来几近消失的涅槃图像。这些实物均反映出末法思潮的深刻影响。相关文物资料与研究参考自孙进己主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一、二、三),北京出版社,1997年;常红红:《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因此人们对法身的崇拜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存有辽代写经、藏经等文物,是辽人安置“法舍利”的行为②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藏经之研究》,《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12期,第175—211页。;敦煌西夏石窟中大量绘制的千佛变相亦是敦煌教界意图通过千佛信仰振兴佛教、护持法身不灭的图像表达③张世奇、沙武田:《历史留恋与粉本传承——敦煌石窟西夏千佛图像研究》,《西夏学》2016年第2期,第271—272页。。在此种时代思潮的波及下,陕北石窟之营建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末法烙印,何家坬石窟也并不例外:护持正法的罗汉(图5)、禳灾除难的观音(图6),以及未来佛弥勒均现身于此窟中。在释迦涅槃后、弥勒未成佛前,罗汉作为受佛嘱托常驻世间的护法者,其题材本身蕴含着无佛时代守护正法的强烈意味;观音与弥勒二者的组合则更加直观地体现出信众期盼得到救助的渴望,构成完整的“现世——未来”救度体系,令信众从末世苦难中解脱,并在未来往生至衣食无忧的净土世界。更应提及的是,遍布何家坬石窟主室内东、西、南三壁的千佛极有可能是受敦煌风格影响而创作的贤劫千佛,展现了佛佛相续的理念,传递出强烈的末法意味④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第70页。。故洞窟主尊必定是能够含摄四壁题材且于末世中彰显佛法的存在,再结合中央佛坛上“三佛”的形制设定,那么凸显法身尊格的三身佛即是最契合整窟氛围的主尊选择。

图5 何家坬石窟后室北壁罗汉造像⑤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图6 何家坬石窟后室北壁自在坐观音造像⑥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最后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陕北石窟群中出现三身佛造像的有不少案例,如万安禅院第1窟主室南壁中部三座立佛大龛(图7),三佛中右端一身结智拳印,佛龛上方及龛内佛像间有题记“毗卢……周永舍钱二十贯……”“逯清舍欠三十贯足,作报身佛一尊记”“施主王义……同发愿造三类化身佛一尊……”等内容,由此可见此龛内三立佛为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的组合;更为典型的案例还有城台石窟第2窟,其后室后壁即刻有三身佛。该处造像保存完好,三佛皆跏趺坐于三层仰莲座上,中间一身佛结智拳印(图8),身份尊格一目了然。从细节上观察,何家坬石窟中央佛坛现存三佛座与城台第2窟三身佛座几乎一致,均为须弥座承托的三层仰莲座(图9、图10)。必须重视的是,城台第2窟落成地点同样属于北宋德靖寨管辖区域内,与何家坬石窟相距不远,窟内题记“华州保捷第三十一指挥都头冯□全共力施造”等字样表明此窟功德主中亦包括军官群体。两座窟室的地理位置相互毗邻,开窟功德主身份相同且在三佛造像细节上高度相似,城台石窟第2窟为何家坬石窟主尊身份的判定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依据。

图7 万安禅院第1窟主室南壁中部三立佛大龛①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7页。

图8 城台2窟后室后壁中龛毗卢遮那佛②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图9 城台2窟毗卢遮那佛佛座②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图10 何家坬石窟中央佛坛佛座③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
基于末法大背景的影响,笔者将何家坬石窟造像内容意蕴与同期毗邻窟室进行比较,认为何家坬石窟中央佛坛上主尊之身份非三身佛莫属。由此,该窟的整体结构也得以明晰:首先,代表法身思想的三身佛为全窟核心,统摄着四周各壁。其次,两侧壁配置有阿弥陀佛与弥勒佛,阿弥陀佛不仅为西方极乐净土教主,更具有过去定光佛以来世自在王之后第五十四位成佛的终极过去佛的双重身份,故阿弥陀佛既身居西方净土,又为过去佛之一①[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266页;白文:《图像与仪式——隋唐长安佛教艺术》,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9页。;而弥勒佛被视为未来世界的救主,且常在四方佛等体系中扮演东方佛的角色。因此何家坬窟内两侧壁阿弥陀佛与弥勒佛的设置既有着东、西方净土的横向对应关系,亦在时空上延展出过去至未来的纵向时间概念。加之东、西、南三壁刻有大面积千佛,营造出十方诸佛境界。诸多内容最终皆由佛坛上的三身佛所统,寓意着法身拥有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地位,含摄着过去未来、十方三世诸佛土。
三、窟室具体功能的讨论
通过上文对主尊身份的分析,我们基本厘清了何家坬石窟的整体结构,也为继续挖掘其具体功能奠定了基础。佛教石窟不仅彰显出信众对诸佛菩萨等神祇的虔诚供奉,传递出种种义理、内涵,亦是现实中人们践行宗教活动的实际场所。因此,探寻一座窟室的功能,即是审视此期佛教信仰状况及体会功德主心理的不二法门。
(一)践行佛教仪礼的空间
借助何家坬石窟中内容详细的建窟题记可知,在吃多遇的领导下,不仅他的妻子三娘、儿子李三、卧怡等家人参加了窟室营建,其同宗族人员也积极投入到此项活动中,题记里“吃多嵬、吃多怡、吃多宁”等人名便是明证。另外,数个“惟那头”的出现也反映出该窟室乃是许多佛教结社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观之,何家坬石窟俨然是以吃多遇一族为主、多个社团共建的邑义窟,带有鲜明的公共神圣场域之意味,故服务于佛教实践应是何家坬石窟所必备的功用。
从主室形制来看,中央佛坛的设置表明此窟可作仪式空间,佛坛四周留出廊道以便信众活动。室内造像题材上文已述,包含弥勒佛、阿弥陀佛、千佛等内容且窟室主尊为三身佛。如此配置基本能够满足相关佛教仪礼的进行,如根据敦煌写本、黑水城文献等文字资料均有记载的寅朝礼程序可知,完成此项仪式大致有如下步骤:礼三身佛(敬礼毗卢遮那佛、敬礼卢舍那佛、敬礼释迦牟尼佛)→礼未来佛(敬礼下生弥勒佛)→礼十方佛(敬礼东、南、西、北及上下方一切诸佛)→礼三宝→所为→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寅朝清静偈→六念→三皈依→和南①相关普礼忏仪及程序研究详见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4—165页。。寅朝礼作为常见的礼敬诸佛的仪式,包含礼敬三身佛、未来弥勒佛、十方一切诸佛等,而何家坬石窟造像题材较为丰富,基本囊括了十方三世诸佛,亦有东西方净土的对置,兼及观音、罗汉等现世救度色彩浓厚的神祇,完全可以作为举行此类敬佛礼忏,以及其他佛教活动的道场。该窟落成仰仗于数个佛教结社的合作,发心施舍钱财者达一百余人,如此众多的出资者显然会产生极大的信仰需求,因此何家坬石窟必定具有佛教实践空间的功能。
(二)祈福荐亡的殿堂
时至宋代,人们更加重视眼前的现实利益,故其到寺院佛窟往往出于世俗目的,并制定出各类仪轨和佛事活动以便超度荐亡、孝养父母等②赵瑞娟、赵志策、马凤娟:《世俗性的宋代佛像雕刻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第37页。。无独有偶,何家坬石窟内相关题记也展现出该窟蕴含有功德主利用窟室神圣空间为亡去亲人祈福的意图:位于后室北壁编号K9-1罗汉造像左上方有楷书阴刻字样“一佰一十人惟头/吃多遇,父遇兀,/母马□,愿早/生天界,/记之”。此处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这条题记由吃多遇发心刻写,吃多遇为何家坬石窟营建的领导者,他的行为与想法无疑是众多功德主心理的代表,最能真实直观地反映出窟室开凿的目的;其次,题记清晰表达了吃多遇为亡去父亲遇兀、母亲马氏祈祷,企盼他们往生天界的愿望,由此也印证了窟室带有超度荐亡、孝养父母的功能。前文已述,何家坬石窟修筑于宋夏鏖战的边界,主体营建者为军人群体。吃多遇为宋军军官,他的父亲遇兀也极有可能是效力于宋军的蕃族军人。身处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殒命疆场难以避免,加之末法思想的不断侵袭,以家族为单位营造一方属于自身的净土便尤为重要。在何家坬石窟这座乱世的佛国殿堂中,功德主为亡故亲人祈福发愿,助其往生,也以此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同时,吃多遇为父母悼亡所写题记的位置也较为特殊,刻于罗汉造像的下方。十六罗汉既具有鲜明的护法意味,又扮演着人间导师的角色,故设计者将十六罗汉镌刻于信众刚刚进入后室的北壁位置,希望罗汉能引导他们进入佛国圣境①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第70页。。吃多遇将发愿题记写在罗汉下方也应是出于这一考虑。需注意的是,在该壁面还刻有自在坐观音题材,宋代常常以罗汉与观音二者搭配,举办荐亡祈福的法会仪式。如苏轼曾撰文记述自己贡献出观音画像一幅,同十六罗汉组合以为亡者追福灭罪:
兴国浴室院法真大师慧汶,传宝禅月大师贯休所画十六大阿罗汉,左朝散郎集贤校理欧阳棐为其女为轼子妇者舍所服用装新之。轼亦家藏庆州小孟画观世音,舍为中尊,各作赞一首,为亡者追福灭罪。②张春林:《苏轼全集》(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705页。
可以看出,观音与罗汉同时出现带有明显的度亡意味,而何家坬石窟后室北壁K9-1罗汉下方题记也正是吃多遇欲纪念已故父母所写,故该壁造像着力凸显的主题即是祈福消灾、度亡往生。另外,题记中希望父母最终“往生天界”,这与同壁面弥勒造像完美契合。此处弥勒以菩萨装形象示人(图11),表明其尚居兜率天宫,属于弥勒上生信仰的体现。题记与壁面造像题材呼应,展现了吃多遇希望故去父母在罗汉、观音的接引下前往兜率天弥陀净土的虔诚心愿。

图11 何家坬石窟北壁弥勒造像③图片选自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编:《延安石窟菁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饶有趣味的是,同宋朝鏖战数十年的强劲对手——西夏军队中亦有以石窟作为荐亡圣地的行为:瓜州东千佛洞第2、第5窟中皆绘西夏供养人像(图12),通过题记释读、服饰细节辨认可知他们均是西夏武官,担任官职有“边检校”等。由他们主导营建的窟室中出现汉传佛教释迦涅槃、行道药师、水月观音、地府鬼卒,以及密教题材如顶髻尊胜佛母、绿度母等,其共性即是彰显出浓厚的消灾除难、度亡往生的色彩①常红红:《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同德靖寨情况相仿,瓜州的位置也极为重要,该城为西夏西平监军司的驻所,地处丝路要隘,毗邻西域地区并常常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②西夏曾“虏略于阗(黑汗)人畜”,为打击西夏,黑汗王朝则向宋廷上书“请讨夏国”,并于绍圣年间进言已“遣兵攻瓜、沙、肃三州”。详细记载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197册,中华书局,1957年,第7722页;[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692页。。历史的物事,可以将它们当作当时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方式③Мichael Baхandall, patterns of intention: 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 Yale universitу рress, 1985, р. 35.。何家坬石窟、东千佛洞第2、第5窟均由久居战火中的军人群体发心营建,德靖寨与瓜州虽远隔千里,但于动荡时局中修筑禳灾祛难、抚魂荐亡的佛教石窟竟成为宋、夏武官冥冥中共同的选择,这既是石窟强大度亡功能的体现,亦从侧面反射出绵延战火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与冲击。

图12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像④此图由敦煌研究院提供,版权归敦煌研究院所有。
四、由何家坬石窟看陕北党项熟户的信仰特点
上文多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对何家坬石窟的主体结构、宗教内涵、实际功能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因该窟是现存陕北石窟中仅有的以党项人为主体功德主营建的窟室,在群体族属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代表意义,故有必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借此个案管窥陕北地区党项熟户佛教信仰的特点。
(一)传统大乘佛教信仰的延续
从何家坬石窟造像题材的选择来看,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群体中依旧盛行大乘佛教信仰。无论是窟室主尊三身佛的设置,两侧壁阿弥陀佛、弥勒佛的组合,以及大量千佛图像的出现,基本都使用了大乘佛教中的常见题材。三身佛及其蕴含的法身思想等上文已有述及,此不赘言。两侧壁面配以阿弥陀佛、弥勒佛的组合方式也属常见,此二者对置的历史颇为悠久,经典案例如灵裕于隋开皇九年(589)主持修建的大住圣窟,内部正壁、东壁、西壁均设佛龛,正壁佛像头光左上侧榜题标明此身为“卢舍那佛”、东壁佛榜题为“弥勒佛”、西壁佛榜题为“阿弥陀佛”。另外,窟内大面积千佛也正是大乘信仰延续的标志,因千佛本身即是大乘佛教“多佛”思想的产物。
由此观之,何家坬石窟的题材选择及思想体现,基本是按照大乘佛教的传统体系。根据前辈学者的详细梳理、调查,陕北宋金石窟群中大乘造像占据绝对主流,题材集中在三佛、文殊普贤、涅槃、千佛与万菩萨等①陕北宋金石窟总体题材的详细梳理参见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一辑,第92—120页;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而密教题材鲜有出现,仅有万安禅院石窟第1窟、钟山石窟第3窟等寥寥几处。因此,浸染在此种信仰氛围之中的党项熟户也必然顺应地域风气,以大乘造像题材作为开窟建寺的不二选择。
(二)对实际利益的关注
何家坬石窟在营建过程中对于功德主的实际利益十分关注,如建窟题记开头便有“风调雨顺,天下人安”的字样,结尾更直观点出希望“舍财施主增福增寿,合家安乐”,还有K9-1罗汉像下方题记表露首领吃多遇祈求亡父母能够“往生天界”,这些内容均揭示出众人期待通过建窟造像功德以增益自身。我们已经对何家坬石窟所处的时代、宗教背景,以及特殊地理位置进行分析,以吃多遇一族为代表的沿边党项熟户笃信佛教,加之族中许多人效力于军队,因而此窟带有浓重的实用意味,是当时历史与环境所决定的。
再从具体题材上看,全窟中最能凸显功利性色彩的无疑还是北壁的观音与罗汉。首先,自阐释观音信仰的重要经典《法华经》传入并盛行于中国之后,以救难为核心的观音信仰便成了日后中国观音信仰的主流②谢志斌:《中国古代汉地观音形象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82—83页。。故观音也被塑造成禳灾除病、帮助信众解决现世苦难的救主,其形象已然成为一种标志性符号,观音救八难、十五善生与十五恶死等具有鲜明实际功用的情节常伴随观音形象出现。甚至西方净土在和观音内容搭配时,所包含现实利益部分也被观音强烈的济世救苦特质所吸收③杨明芬(释觉旻):《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70—271页。。在陕北石窟中观音形象数量很多,自在坐观音、千手观音、观音救度八难等皆有雕琢,可以说这些造像正是广大信众渴望平安、息灾避祸心理的真实写照。
罗汉作为另一种流行题材,在陕北石窟中也以多种形式呈现,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组合,何家坬石窟北壁即为十六罗汉。玄奘《法住记》中阐释到罗汉可以“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④[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第4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12页。,由于罗汉在佛涅槃之后常驻世间,在观念中同百姓距离更加贴近,故罗汉信仰很快风行于世,形象亦广受崇奉。在宋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罗汉信仰处于“惟灵是信”的实用氛围,这样的信仰观念“提拔”了一批原本身份稍低的神祇,还使信众人为地赋予这些神灵新的法力或功能,就十六罗汉而言其图像常被用于祈雨抗旱、祈仕途、超度等⑤张凯:《五代、两宋十六罗汉图像的配置与信仰》,《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9页。。如名僧贯休归隐豫章西山后,所绘的罗汉图被当地宋人在祈雨仪式上供奉。随着佛教日益世俗化,人们更加倾向于满足自身需求的神灵崇拜,护持正法、久留世间的罗汉正契合信众渴望现实利益得到保障的心理。而陕北石窟对罗汉题材运用十分普遍,并独创地域性特征极强的“罗汉奏乐”图(图13),以突出罗汉造像①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32—435页。。与绝大多数窟室一样,何家坬石窟的营建基本符合陕北地区石窟选材喜好及组合样式,因此也给予罗汉主题相当的重视,并以之为寄托哀思、助人往生的引路者,窟室首领吃多遇为父母荐亡的题记题写于罗汉下方正是最好的证明。而同样获得党项人资助开凿的樊庄石窟第2窟、城台石窟第2窟等窟室内也均刻有罗汉,说明此地域党项熟户的信仰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图13 钟山第4窟罗汉奏乐图②此图由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副教授提供,特此感谢。
总的来看,观音与十六罗汉在宗教功能、象征意义等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且均属于陕北地区十分流行的造像题材。二者在何家坬石窟中的搭配相得益彰,不仅共同承担起救难度亡、助人往生的责任,还能够护佑功德主现世生活安稳,这样的造像偏好也直接显示出以吃多遇一族为代表的陕北党项熟户在佛教信仰方面具有重视自身实际利益的鲜明特点。
(三)以佛教信仰作为族内团结的纽带
前已提及,何家坬石窟的营建是多个佛教结社合力的结果,德靖寨辖下以吃多遇为首的一百余名党项人按家庭单位结成了约10个小佛教社邑,共同参与到窟室修筑中。实质上,正是对于佛教的虔诚,使此支党项小部族在乱世战火中依旧努力完成开窟造像这一需要全族上下群策群力、鼎力互助的事业。何家坬石窟的营建过程即映衬出其族内帮扶合作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建窟题记中标明修造石窟的有首领吃多遇等“壹佰壹拾人”,但文内所列出的人名远超一百一十之数量,杜建录、邓文韬先生认为该处“壹佰壹拾人”指的是实际意义上的出资者①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5页。。而笔者在阅读题记时,发现有许多功德主姓名出现数次,如“吃多嵬”之名有三次、“怡遇”两次。那么这些人是否为重名之人呢?借助题记所载信息,加入何家坬石窟建设的小型家族佛邑数量约10个,在如此小范围族群中频繁重名,显然不太合乎常理。故笔者推断这一现象应是部分功德主参与了多个结社的反映,所以造成了发愿题记中刻写的姓名数大于“壹佰壹拾人”。若该推断成立,则在此族群众中一人可与不同结社和小家庭产生关联,从而加强了各小社、亲属间的联系。结合吃多遇等人的身份与所居住战区环境相关,他们凭借佛教结社、开窟造像来巩固亲缘、守望相助的举措是颇为有效且顺应时势的。
另外,还有一位功德主身份相对特殊,此人为出现在建窟题记中诸功德主题名末尾处的“地主吃多香”。“地主”的称谓说明吃多香原是石窟开凿处地权的拥有者,他的名字未见于诸小佛社,但仍以施舍土地的方式参与了这次开窟活动②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5页。。可见,吃多香作为族内较富裕者,基于自身的佛教信仰,将私产土地支持宗族事业。这一善举为众人提供了落实精神寄托的物质基础,不仅大大方便何家坬石窟的落成,亦使全族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结 语
诚如巫鸿先生提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考古证据并将其“语境化”“历史化”,进而探究背后的意义是十分有必要的③[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25页。。我们将何家坬石窟置于宏观的宋夏战场与末法世界中,再结合吃多遇一族信众的身份与处境,不难发现其渴望避免灾祸、获得现世安稳的心理皆可以透过石窟中的蛛丝马迹得以反映。
就窟室造像而言,何家坬石窟整体结构较清晰。主尊三身佛明确了法身崇高地位,诸壁面配置以阿弥陀佛、弥勒佛及大面积千佛图像,营造出法身统摄十方三世诸佛的格局,凸显正法永驻之意味。而罗汉与观音组合又密切关注着现实利益,不仅为亡者往生增添助力,亦成为功德主身边的护佑者。
审视何家坬石窟的营建过程,可体会到明显的功利性特征,百余名功德主合力建窟,展现的是普通百姓在末世与战乱环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企求。佛教作为一种精密复杂的宗教,其经典浩繁、义理深邃,大部分寻常信众难以理解个中奥妙。但当这种教义不是以抽象的教条,而是以朴素感性的形象、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同广大信教者包括宗教美术家的向善愿望和为人准则是相一致的①徐建融:《美术人类学》,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何家坬石窟是利用佛教艺术来直观表达民众内心情感的绝佳案例,此窟的营建也恰恰是宋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平民化的一个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