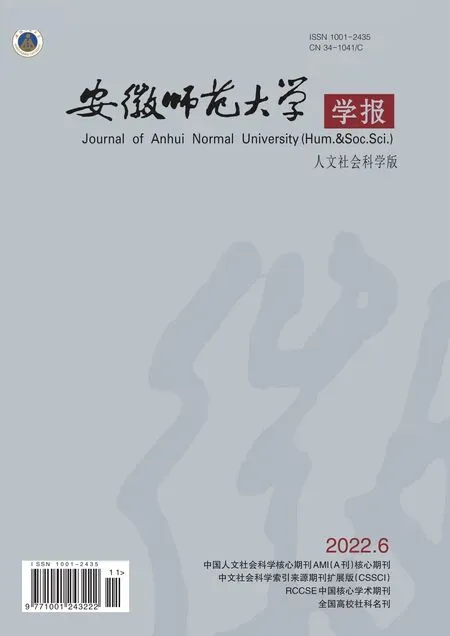境界与诠释:中国经典诠释中的境界的诠释循环*
余亚斐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读者在阅读和理解古代经典时,常能感受到其中圣人高远的境界,文本内蕴的圣人境界既构成了经典之为经典的内在根据,又反映了人性普遍具有的理想形态。读者与经典之间在境界上时常存在着较大距离,正是境界上的差距使得读者产生出经典“不可得而闻”或不可思议的感叹。在对经典的理解上、在与圣人境界的对比中,读者自觉到自身境界的狭小,“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通过经典诠释,感悟圣贤境界,读者的境界伴随着理解得以提升。在中国经典诠释中,境界贯穿经典诠释的始终,其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境界标志着经典的思想高度,代表着人性所可能达到的悟境,读者具备一定的境界是经典诠释的必要前提和准备,经典诠释在一定意义上是读者与经典之间境界的互动与交融。在经典诠释中,读者与文本的境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经典境界被揭示的程度取决于读者的境界层次,读者境界是经典诠释的前见;另一方面,在经典诠释中,读者的境界得以扬弃,不断趋向于经典中的圣人境界,体现了经典诠释的教化功能。不管是对经典境界的诠释,还是读者境界的提升,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由境界到诠释、由诠释到境界的双向循环中相续渐进,由此构成了经典诠释中境界的诠释循环。
一、将“境界”引入“诠释循环”
“诠释循环”是西方诠释学的概念,“境界”是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的概念,把“境界”引入诠释学之中,并提出境界的诠释循环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凸显中国经典诠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进诠释学的实践和价值功能的实现。
在西方诠释学中,不管是侧重方法论诠释学的施莱尔马赫,还是作为从方法论诠释学向哲学诠释学过渡的狄尔泰,抑或是哲学诠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把诠释循环当作诠释学的重要问题加以探讨。在施莱尔马赫那里,诠释循环是指对文本的某一部分的诠释要根据它与整体语境及其他部分的关系来进行,而对整个文本的诠释又必须参照其各部分的意义,由此构成了部分与整体的理解的循环。狄尔泰把诠释活动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精神的互动与交融,诠释过程既拓展了自身个体的生命,也延续了人类整体的生命,于其中形成了生命个体与人类整体生命的循环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诠释活动是展现此在历史性的方式,“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①[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页。,文本诠释作为此在生存方式的展现,同时又作为前结构规定了诠释的范围与意义,二者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伽达默尔认为诠释是读者带着当代的理解视界进入历史,并将历史融入当代,效果历史的运动构成了历史与当代的诠释循环。由此可见,诠释循环虽然是诠释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但对它的不同理解也构成了诠释学的内部论争,展现出各自的思想特点,并推动着诠释学的发展。同样,当诠释学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经典诠释传统相遇时,诠释循环也突破了西方形态,展现出经典诠释中境界的诠释循环这一中国特色。在正式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对“境界”一词的内涵进行分析。
在汉语中,“境界”原指疆界,如《列子》曰:“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②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页。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境界有了新的内涵,具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十八界”中的“六境”,即色、声、香、味、触、法,此六者是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的感知对象;二是指有情众生的思想层次或心灵状态。按照唯识学的理解,对“六境”认知的主体是阿赖耶识,此识在“六根”“六境”之因缘以及宿业的作用下产生对世界与“我”或染或净、或真或妄的认识。所以,认知的对象实质上是心灵的映照,而对对象的不同认知,或是烦恼尘劳,或是菩提自在,皆反映出心灵的不同状态,所观之境与能观之知非一非异。如此一来,作为认识对象的“境界”便转化为认知主体的心灵层次,这便是境界两种意义的内在关系。境界的两种意义是一体的,一方面,境界作为精神活动的对象,必然受到精神的作用,是心灵净、染两面的反映;另一方面,精神活动的对象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心灵的状态,如“六境”被称为“六尘”,此“尘”犹如落在明镜上的尘埃,具有遍染六根、昏昧真心的作用。所以,境界虽有主体境界与客体境界的区分,但是,“能”“所”一体,精神在领悟客体的同时领悟自身,境界是人与世界的一体显现。境界的两层意义犹如两镜相照,在经典诠释中表现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经典之间的相照关系,读者依据自身境界之“此镜”去理解作者、经典之“彼镜”,而“彼镜”也伴随着作者的理解过程融入“此镜”,成为“此镜”的一部分,以此达到两境之间的对话、融合与循环。
西方诠释学以语言为基础,语言包含着逻辑结构、语法规则、历史视域和生存方式,而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成己、成圣是主要目标。语言,尤其是经典中的文字还蕴含着圣人所体悟到的宇宙—生命的真谛,即圣人之意,并呈现为境界。所以,作为中国哲学发生之动因的经典诠释,与其相关联的不仅有语词、语义、语境,更重要的乃是境界,语词的分析、语义的理解、语境的再现最终都是为了通达圣贤境界,而有所自得。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知之”是知识层面上的学,相当于对文本语词和语义的理解,“知”的对象是外在于己的,见闻再多,也无关乎己,如若要化外在为内在,体验到作者之“乐”,以此成就“为己之学”,还必须经过“好之”,即通过身体力行去真切地体验。刘宝楠在解释此节时说:“乐者,乐其有得于己也。”②[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5页。境界是内在的,惟有自家受用,所以,“乐”所达到的是心通圣贤的境界。王守仁说:“乐是心之本体”③[明]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李泽厚也将此“乐”理解为“融理知、意志于其中的本体感悟”④李泽厚:《论语今读》,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7页。,之所以说是“本体”,是因为境界作为心灵状态既是人们理解生命—世界的根源,也是觉悟的展现。宋明两代的儒家从周敦颐开始“寻孔颜乐处”,所寻者正是圣人境界,只有当读者从自身心境、心地上契合圣人,才能通达经典中的圣人之意而成己、成圣。因此,境界虽为两镜相照,但又以心灵为根本。正如张世英说:“‘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⑤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蒙培元也说:“谈境界必先谈心灵,因为境界说实际上是心灵哲学。境界是心灵的境界,即‘心境’之同异或高低,不是在心灵之外有一个与心灵相对的境界,更不是心灵对外部世界(对象或实体)的‘认识’。”⑥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成己、成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在自家心性、心灵上自得,而“境界就是心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⑦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87页。。所以,在成己、成圣的目标指引下,作为通往圣贤心灵之途径的经典诠释也需要关注境界。
诠释学关怀“他者”问题,需要解释的文本是他者异己性的表现之一,而诠释学的任务正是要克服作为异己存在的无法理解的文本,而化为自家的东西,而克服异己首先就要分析异己性产生的根源。他者之所以成为异己的东西,如果不是文明的冲突和知识的障碍,可能就是由境界的差异所导致的。由于境界构成了经典异己性的原因之一,同时又是经典诠释的重要目标,所以需要把境界引入诠释循环中。境界的诠释循环之所以提出,是在中国经典诠释的语境下,当把理解的对象返回到理解得以被构成的准备之中,即思考性与天道何以被理解、何以不可得而闻的问题时,把境界作为理解必不可少的前提和目标加以考虑时所产生的结果。境界的诠释循环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经典是圣人境界的流露,基于人之心地的境界既表现为生命之间的共有,又存在着现实中的距离,这些构成了经典诠释循环的基础;其二,境界有高下、真俗之分,具备一定的境界是读者理解经典、通往圣人之意的必要前见,而理解的困难又源自于境界上的差距,即读者进入经典所需境界的缺乏;其三,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为读者提供了重要启发,借助于经典诠释,读者的境界得以提升,这也是经典流传之意义所在。总之,经典中的境界与读者的境界相互牵制和作用,两者既互为中介,又相互转化,构成了经典诠释中境界的诠释循环。境界既是理解之因,也是理解之果。作为理解之因,境界在经典诠释中处于“先有”地位;作为理解之果,境界展现出经典诠释的实践目标与价值追求。可以说,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学就是人生境界之学。
二、境界的共有与距离
在当代建构中国诠释学的背景下,之所以需要将境界引入诠释学,并提出境界的诠释循环问题,不仅在于经典与圣贤境界存在着内在关系——经典是圣贤境界的流露,没有高远境界的文本谈不上经典,而且还因为境界构成了经典诠释循环的基础。一方面,境界是人性普遍的存在状态,人人皆持有一定的生命境界,境界是读者与作者的共有之物;另一方面,读者与作者的境界既在现实中存在着距离,又存在着超越的可能,人人皆可感悟并成就圣贤境界,在经典诠释的启发之下,读者可以跨越时空的距离与作者产生生命间的共鸣。
经典诠释的最终目标不是把握经典中的语言,而是领会语言中所内蕴的圣贤境界。经典作为一种文本,自然表现为“言”,但对于具有高境界的经典而言,语言的作用在于明象、尽意,即展现圣贤境界。正如王弼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①[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4页。这段话是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精辟论述,旨在破除汉易象数对易理的遮蔽。王弼所谈论的“言”是经典中的语言,依照他的思路来看,语言的阐释来自于明象和尽意的需要,而由语言构成的经典的目的也在于明象和尽意,意是本,言是末,象为中介,虽然“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②[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页。,但不可以本末倒置。由于境界是圣人之意的体现,而经典是圣人之意的载体,所以,经典诠释的重心在于对境界的揭示。在《庄子·天道》篇中有关于“轮扁斫轮”的故事。齐桓公于堂上阅读经典,着重于“圣人之言”,而在作为工匠的轮扁看来,语言文字则是“古人之糟魄”,借用老子的话来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③[汉]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0页。若要由迹寻履、循指见月,则必须要透过语言,深入圣人之意,把握经典中的圣人境界。
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只有当读者与经典或其作者产生一定的共鸣,而非无动于衷,诠释活动才算真正开启,对经典中境界的自得也才有可能。伽达默尔说:“阅读是一种纯粹内在性的事件”④[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4页。,又说:“理解总包含一种内在的言语活动”⑤[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234页。,其“内在性”便是读者扬弃对语言对象性的理解而转为自心中的领会与受用,而境界正是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的基础,是建立读者与作者之间生命关联的纽带。境界的共有是经典诠释得以展开的基础,境界虽有高低之分、圣俗之别,但人人皆有境界。孔子把人分为小人、善人、君子、圣人等境界,因材施教,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老子把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境界,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⑦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3页。不管是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还是老子所谓的上士、中士、下士,皆涵盖了一切人,由此可见,境界是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中国佛教有判教理论,判教虽是判定佛陀说法之先后与教义之深浅,但又源自于众生基础境界的高低,众生皆有境界,因为不同的根机与境界,所以需要施设不同的教化方法,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正如宗密所言:“若约各为一类之机,善巧方便,广开门户,各各诱引,熏生生之习种,为世世之胜缘,则诸宗所说,亦皆是诸佛之教也。”⑧[唐]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诠集教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认为这四个层次具有普遍的意义,并称这种普遍性为“大同”,正如他说:“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①冯友兰:《新原人》,《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页。张世英把境界理解为人的“在世结构”,以此角度提出了“人生四境界”: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认为这四种境界不是直接对应某一种人,具体的人往往是四种境界兼而有之。正是因为境界是人兼而有之的,读者才可能在面对经典中的圣人境界时产生共鸣,并进而对自身境界有所超越。
境界虽然人皆有之,但境界亦有高低之分,境界的高低层次是造成经典诠释中读者与作者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这也为经典诠释之必要以及诠释学的实践性提供了可能,因为对境界之间距离的超越是经典诠释的主要任务,而境界的超越所带来的读者人生境界的提升也体现了诠释学的价值目标。境界是人处在世界中对待自我与世界万象之间关系的态度,表现为一个人的生命层次与界限,正如冯友兰说:“境界有高低。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②冯友兰:《新原人》,《贞元六书》,第557页。具体来说,境界的高低存在着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来说,境界作为生命的界限,体现为一个人的眼界、视域、胸怀等心灵状态。在《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篇中有关于楚人、孔子和老子三者境界对比的故事。有一位楚人丢了弓箭却不愿找回,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闻后说:“去其荆而可矣。”老子听闻后说:“去其人而可矣。”这位楚人能超越私利,将自我融入于国人之中,可谓境界之高;孔子认为,局限于一国范围,其境界仍不免有些狭隘,应扩大到全体人类之中,孔子的境界比之楚人又高了一层;老子认为还应该突破人与万物之间的界限,把自我融入于万物之中,其境界更加广大。在这则故事中,楚人、孔子和老子之所以对“遗弓”一事有不同的态度,所体现的正是境界在广度上的差距。从深度上来说,境界体现在人对心物关系的处理上,即人在受到世间诸事反作用于己时心灵所展现出的自由程度。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士君子的心灵不受外物束缚,在心灵上更加独立与自由,所以比一般人的境界要高。在《庄子》中有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④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0页。的三等境界,此划分也与心物关系有关,境界依照心灵受到外物与知见的束缚程度而有高下之分。大乘佛教追求超越真、俗两边的中道境界,心灵随缘而不变,不变而随缘,所表现的也是境界的深度,正如《楞严经》曰:“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能含受十方国土。”⑤刘鹿鸣译注:《楞严经》,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页。在佛教大自在的理想境界中,心灵既周遍法界、与物相接,亦不会遍计所执,不受随缘而来的尘劳系累,于一真法界中,随缘自在。
不同境界之间虽有距离,但境界的距离又是可以克服和超越的,或者根本无需克服和超越,因为境界并非外在于心灵,哪怕是再高的境界,也是心灵本有之物。就其主流来说,中国传统中的儒、道、释三家都对人性的先天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依靠人之本性,皆可达到圣贤境界。儒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9页。,认为人人皆有达到圣贤境界的先天基础。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⑦[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7-238页。圣人是仁、义、礼、智的统一,作为此“四德”起点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则人人先天本有,不假外求。道家和道教皆以得道之真人为理想境界,认为道性人人皆备,只要返璞归真,人人皆能知“道”、行“道”、得“道”,所以,圣人境界“甚易知,甚易行”⑧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274页。。初唐道教经典《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曰:“众生道性,不一不二,究竟平等,犹如虚空,一切众生同共有之。”⑨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中国佛教认为佛性人人本有,无始以来的有情众生本具如来藏性,果觉不离因心,所以与如来法身无有异处,正如六祖慧能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①尚荣译注:《坛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页。众人之性与圣贤之性平等不二,当孔子闻道时,天下人皆可闻道;当佛陀觉悟时,众生皆可觉悟。境界的距离是非时间性的,觉与迷只在一念之间。此非时间性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生命关联搭建了桥梁,也为境界的诠释循环奠定了基础。
“道不远人”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页。,每一位读者都可能具备经典中的圣贤境界,这是人性所具有的可能性。而现实的生命境界又存在着高低之分,读者与圣贤之间在境界上存在着一定距离,并造成读者在理解经典上的困难。然而,境界又并非不可超越,经典诠释正是读者超越自身有限境界而通往圣贤境界的重要途径,这便赋予了经典诠释一个重要目标,即在经典诠释中获得生命境界的提升,这既是经典诠释的意义所在,也是诠释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的根据。
三、境界是经典诠释的前见
经典的意义是开放的,从诠释学的视域来看,并不是经典具有多意性,而是读者按其自身境界对经典加以理解时所表现出的开放性。清代学者沈德潜在论诗时说:“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③[清]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读者的生命境界表现为心态、性情、涵泳、品味、器量等因素,它们对作品理解的影响体现了境界作为理解的前见在经典诠释中的作用,这也构成了境界的诠释循环的第一个环节,即从读者的境界到经典的境界。
在对经典的理解中,经典首先要被理解,虽然经典有其自在的境界,但是经典境界的揭示又取决于读者在理解的此时所具有的境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被揭示出的经典的境界就是读者此在的境界。读者此在的境界作为前见在理解中发挥作用是常见的。在《论语》中记载了一则子贡卫道的故事。孔子死后,鲁国有位叫叔孙武叔的大夫欲贬低孔子,抬高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也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2页。子贡以围墙为喻,围墙比喻境界,两者皆有界限之义,境界有高低,故有理解上的差距。在子贡看来,叔孙武叔抬高子贡,是因为子贡的境界尚在叔孙武叔的理解范围之内,即两人的境界相当,依照叔孙武叔的境界,可以透过子贡家的等肩之墙而窥见其室家之好,而孔子的境界犹如数仞之墙,远远超出了叔孙武叔可以理解的境界范围,所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黄侃在解释此节时说:“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浅,深者难见,浅者易观。”⑤[梁]皇侃撰,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1页。器量是境界的体现,不同深浅程度的境界作为理解的前见影响着理解,其理解也展现了此在的境界。《庄子》中望洋兴叹的寓言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河伯见黄河之水宽阔汹涌,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汇聚于此,后来河伯顺水东流,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望洋兴叹,方知自己贻笑大方。河伯拘于自己的空间与视界,所以陷入所知的偏见之中,而读者亦不可避免地深陷自己的境界,依照自己的境界去诠释经典,所诠释者亦是读者自身的境界,而难以通达经典中的圣贤境界。
经典中的境界只有被读者领会才能展现其境界,因为境界的展现基于被理解、被揭示,而理解又以读者具备与经典作者同境界为前提,当两者的境界距离较大时,便会造成经典意义的晦涩、隐蔽,乃至于神秘、不可思议的理解结果。所以,经典之所以难以理解,以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9页。,重要的不是语义、语法上的障碍,也不是由于历史的时空距离,抑或是理解的技巧问题,而是读者境界的缺乏。当性与天道不能被相近的境界所接近和理解时,便只能作为物自体而存在,因为不能成为被认知之见和被给予之物,不能成为直观上的现前,也就不能成为真的或可理喻的。诚然,“‘以作者的精神’来进行历史解释的必要性来自于内容的晦涩暧昧和不可理解性”①[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261页。,不过,经典诠释却不能因为境界的缺席而走向读者中心,只要读者将经典作为经典来对待,并以教化己身为目的,读者自身的境界就不应成为理解的目的;如果理解的目的仍然停留在读者此在境界的显现和表达,那么经典的理解就可以判定为有缺憾的。所以,读者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弥补境界上的距离,带着一颗诚敬之心,通过自我扬弃,来通达圣人之意。圣人之意从未遮蔽,而是读者境界的自蔽。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8页。圣人之意一直置于光亮之下,由于读者缺乏与圣人心通的境界,所以不能通达圣人之意,并在自我境界的理解中被遮蔽。在经典诠释中,当出现“不可得而闻”的情况时,可能就是经典对读者境界不达的重要反馈,读者以此体会到境界作为理解前见的作用,并进而为自己提出提升境界的要求。
相对于读者来说,境界所展现的不仅是读者此在的生存状态,更是相较于圣人来说的境界的距离,鉴于境界作为理解的前见在经典诠释中的作用,读者只有超越自我境界的局限,弥补与经典在境界上的差距,才能走进经典,领会圣人之意。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圣贤境界以“无己”为特征,走进圣贤境界也要以“无己”为前提。庄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③方勇译注:《庄子》,第3页。圣人之心游乎无穷,其境界无待而圆融,读者若要体验圣贤境界,也需要做到“无功”“无名”乃至“无己”。因为经典以及经典中的圣贤思想是对宇宙—生命之大全的探讨和体认,经典不是为个人所写,经典所展现出的境界也不仅仅是基于个体而求索的人生出路,而是对整体世界与生命的关怀,体现了对人类乃至宇宙万物的大爱,如孔子“天下归仁”、老子“以辅万物之自然”、张载“民胞物与”以及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等;反之,若仅从自身的情感欲求、知识见闻、功利目的出发,所展现的只能是“自我”的狭隘性,并以偏盖全,遮蔽经典。程子曰:“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④[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冯友兰也把天地境界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圣人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⑤冯友兰:《新原人》,《贞元六书》,第644页。。在天地境界中,自我融入于天地万象之中,既打破了主体观念中的对待,也消解了客体间以及主客体间的对待。在冯友兰的“四境界说”中,相对于天地境界而言,自然境界是原始的本能运动,自我的观念尚未形成,更谈不上无我之境了;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虽是自觉的,却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我”的主体性,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对待。张世英依据“在世结构”把人分为四层境界,而“在世结构”又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主—客关系的在世结构,一种是天人合一的在世结构。其中,作为最低境界的欲求境界所对应的在世结构是“原始的不分主客”;然后是求实的境界和道德境界,此两者的在世结构都是主—客的对立;最后是审美境界,其在世结构是主客融合、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正是“无我”境界的表达,它既是心通经典的境界准备,也是经典诠释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西方诠释学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议题时,就已经进入了“主—客”的关系之中,然而,如果以“主—客”对待关系的在世结构来从事经典诠释的话,经典中的圣人之意或者被此在的主体性所取代,或者无法被全然领会,如此一来,经典的存在意义也将丧失。因为圣人是处天地境界的人,圣人境界正是对“主—客”对待关系的超越。因此,在境界的诠释循环的第一个环节,即从读者的境界到作者的境界中,读者需要自觉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观泰山而小鲁”,并实现自我的超越,以此建立起进入经典所需要的天地境界这一前见。天地境界作为读者进入经典的前见与门槛,既是经典存在的意义所在,也体现了经典诠释的实践目标。这是因为,经典虽然等待着读者前来揭示,却不为拙工改废绳墨,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中道而立,能者从之”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2页。,经典正是由于其天地境界被读者一次次地体验到并运用到具体的生活世界中才延续着生命。读者想进入经典,必须先提升其境界,而经典诠释又为读者境界的提升提供了启发。经典诠释既以天地境界为前见,其本身也是重构读者境界的过程,在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中,读者的狭隘性得以超越,境界得到升华。
四、经典诠释为读者境界的升华提供启发
在中国经典诠释的境界诠释循环中,从读者的境界到经典的境界是第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读者的境界作为理解的前见影响着经典境界的展现;从经典的境界返回到读者的境界是第二个环节,读者境界的提升有赖于经典诠释,经典诠释为读者境界的升华提供了启发。经典诠释需要读者境界的拓展和升华,而读者在经典诠释的活动中也伴随着境界的提升,两者相互成就,构成了循环关系。
提升读者的境界是经典存在的意义所在。经典的境界不是抽象的历史的他者,圣贤境界作为本体永远向着现时的读者敞开。经典包含着某种期待与弘扬,它总是等待着被揭示、被体验,而且,只有在被读者一次次体验到并促使其境界的升华时,经典才能活在当下,其意义才能持续流传。虽然境界总在历史中被显现,犹如以“用”显“体”,意以象成,但是境界的本质却不是历史性的,历史性只是境界借以表达的条件以及境界的提升所需要冲破的界限,境界的存在意义不是显现其历史性的象状,而是冲破一切历史性,在现时中直显本真,并接受现时读者的追寻。虽然经典的境界等待着被理解,但仅当其境界能够进入读者理解的范围时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只有当读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境界,经典的文字符号才能转变成意义被读者领会,否则,宝山在前,也只能空手而归。这正是境界的诠释循环在经典诠释中的体现,而克服这一矛盾的关键仍然在于经典诠释,因为经典诠释能够为读者境界的提升提供启发。
经典诠释之所以只能发挥启发的作用,是因为经典诠释并不能完全承担起读者境界提升的全部任务,而只是给已经有所准备的读者提供一个自我突破与自行前进的契机。“启发”由孔子提出,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方法。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愤”是指学有所至而未能上达,“悱”是指心有所得而言之不出,学者必待“愤”“悱”之后才能启发。“愤”“悱”是境界提升前的准备,境界的提升是目的,启发是途径,经典诠释正是读者提升境界的重要途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是在说启发的目的,启发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智慧的开显,不在于模仿,而在于自得,只有自得,才能在一隅的启发下自行开启其它三隅。正如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既然境界在于自得,根源在读者内在的“愤悱”,所以,经典诠释所提供的只是启发。
经典诠释只能是启发,还因为境界的获得不只是思维上的知,更在于生活中的行,境界只能通过读者的实修、实证才能真正习得。《易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④[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0页。从境界的诠释循环的视角来解读,“穷理”是去路,即读者通过经典诠释来获知圣贤境界;“尽性”是回路,是在圣贤境界的感召下,通过自己的修行来变化气质、超越自我,逐渐迈进圣贤境界;“命”则是读者境界的生成与成就。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学与习,是境界提升的两种方法,“学”即“穷理”,是从经典诠释中获知新境界的方法;“习”是“尽性”,是在经典诠释之外,从生活世界中自行领悟;而“说”(悦)则是经过“学”与“习”之后所达到的生命的状态与境界。生活是智慧之源,境界的体认不能离开生活,犹如慧能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⑥尚荣译注:《坛经》,第58页。境界不仅是经典诠释的对象,还是自我生命的环节,生活世界对于境界的创生与领悟来说具有本原性。所以,读者只有将其生命的经历实际参与到所知的境界之中,并通过“习”的持续积累与反复地切己体察,才能将对象性存在的所知内化于己而成为自身的境界,进而体验到内心之“悦”。佛教将戒、定、慧三学作为自己的实践纲领,主张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慧是所达到的境界,而慧的生发离不开戒与定的实修和实证的工夫,只有在生活中恪守戒律才能摒除杂念、摄散澄神,入三摩地,也才能进而见性悟道,联通佛的境界。由此可见,在境界的诠释循环中还包含着知与行之间的循环,或者说,中国经典诠释本身就不只是一项理解的理论活动,还包含德行修养的重要一环。
此外,读者在经典诠释中所获得的境界的启发还需要在“习”中稳定,并最终实现自得。启发是举一隅而反三隅,也是“温故而知新”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7页。。“知新”是境界的获得,是“一种独特的现在”②[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181页。。“知新”在于“温故”,对“故”有所知又依赖于经典诠释,而“温”却不限于见闻觉知,还包含了行与习在内。正如《论语正义》引郑玄注曰:“谓故学之孰矣,后时习之,谓之温。”③[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第54页。“温”是通往“熟”的途径,闻见之知尚显肤浅且易流于表面,只有稳定于心、见之于行才算得上自得。周敦颐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④[宋]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可见,境界的自得需要将对象性的所知内化,然后油然而生,外化在万物之上。颜回问孔子“仁之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2页。视、听、言、动皆是生活中实修、实证的工夫,是在自己身上持续地存在并发挥作用,此之谓“体验”。伽达默尔说:“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⑥[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93页。当读者进行经典诠释、面向圣人境界时,可能暂时性地与圣贤共时共在,圣贤境界可能一时成为读者的境界,而使心地一下子豁然开朗,然而,读者一旦回到生活中、面对事情时,又会回到原有的境界,难以稳定境界。就像人们在看一部悲剧电影时,会暂时带入悲剧之中,当剧场结束,又迅速从悲剧中脱离,只有当人们长期浸染于悲剧中,久而久之,才能形成稳定的悲剧心理。这表明,经典诠释只能发挥见闻觉知的作用,通过带给读者暂时性的境界体验而完成境界的启发,读者如果只是停留于、满足于经典诠释所获得的一时感受,圣贤境界便只能作为对象性的存在,而难以令读者自得。“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⑦[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9页。读者在经典诠释中“有闻”,还必须在“有闻”的启发下经历长时期的“格物”工夫才能“致知”。
经典诠释之所以能够为读者境界的提升提供启发,是因为在经典诠释中,读者与圣贤能够在境界上展开对话,并在此过程中,读者反躬自省,实现对自我境界的超越。经典中蕴含着人类共同拥有的崇高精神的发现,而不是某种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世界观,圣贤境界虽然通过经典中的文字表达出来,但文字中所蕴含的境界却可以在心灵中相通。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灵魂内在感受的符号,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对所有人来说文字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人来说,口语也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文字和口语原本都是内在感受的标记。”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刘叶涛等译:《工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灵魂的内在感受可以穿透语言的表象而进行内在的交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境界也伴随着经典诠释得以理解。经典诠释不是将作为异己的境界直接转化为理解了的东西而被读者直接占有,而是彼此之间的融合与同化,在此过程中,已经改变了的既有理解中的经典,也有读者的境界,经典在读者境界的观照下获得意义的重估与创新,而读者也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经典的同化。一个人经常阅读某一类书,自然就会受到这一类书的影响,经常阅读境界比他低的书,境界就会被拉低,反之,境界就能得到提升。经典是高境界的文本,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以提升境界为目标,而经典诠释的过程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读者接近这一目标。就好像《易传》这部经典,当读者“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①[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第342页。,在吉凶的引导下适时安排当下生活时,就是在接受其境界,“感而遂通”,改变自身。
境界既是心灵的自得,又是人心之所本有,只因遮蔽故,所以,读者可以在经典诠释中获得境界的启发,以此展开对自身内在的精神资源和潜能的开掘,激发境界的重现。在经典诠释中,读者的境界与圣贤境界双向开显,并在两者的互动中相互同化,可以说,经典诠释发挥着接引读者通往圣贤境界的功能,为读者境界的提升提供启发的契机。
五、结语
境界的诠释循环包含着去路与回路,去路是此在境界的展现,回路是圣贤境界的应用。伽达默尔说:“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②[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235页。,经典诠释的再创造在于对圣贤境界的当下应用。经典中的圣贤境界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这是经典的未来视域。每一个时代基于当下的需求都会问道于经典并产生经典的注疏,经典的注疏既延续了圣贤境界,也表现出其特有的历史特征,如孔颜的“安贫”境界、庄子的“逍遥”境界、郭象的“独化”境界、张载“民胞物与”的境界,以及近代“人间佛教”的境界等,这些都是对圣贤境界的崭新的体认、诠释与应用,并以此推进经典意义的延伸。虽然经典的圣贤境界是自在的,但经典的创新不是境界的创新,而是应用的创新,从应用性上来说,经典的境界是效果中的境界。然而,经典的境界又需要在经典诠释中不断地展开其历史性,在境界的应用中创生当代价值。在如今的时代,传统哲学中的境界虽然被人心所普遍地向往,但在其应用中所呈现出的历史性又远离当代人的生活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经典诠释时,不仅要回顾、追寻古代圣贤境界,同时还要与新时代的社会状况和生存方式相结合,在历史的继承中开创符合当代生活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