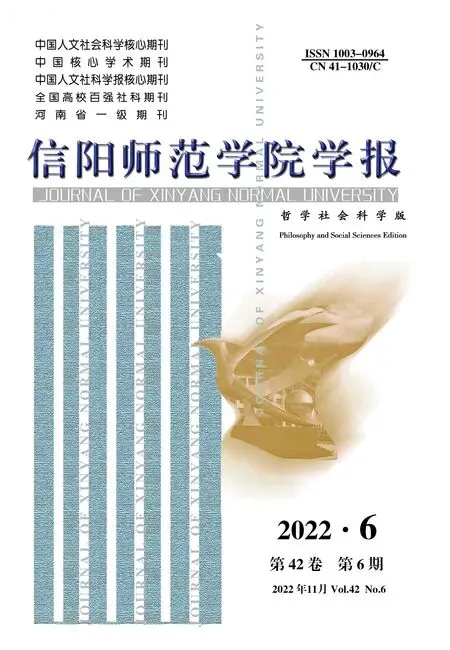戈迪默《伯格的女儿》空间书写中的“异托邦”研究
姜 梦,王 娟
(1.皖南医学院 外语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南非白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年)因真切而深刻地反映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而著称,其小说除了展现种族隔离政策下不同肤色人民的生活、精神和内心世界,更以其独特的空间书写而别具特色。戈迪默小说的空间书写既涉及流亡、家园、世界这样的宏大主题,又对个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等微观空间甚为关注。宏观与微观的空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无形的异质空间网络,“向我们展示了竞争的、偶然的和不断变化的充满了抵抗和同谋性质的场所。这些场所被文化地理学家们称作异托邦”[1]85。戈迪默在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伯格的女儿》中便构建了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一系列异托邦空间。
《伯格的女儿》因语言风格晦涩且仅有一部中译本,国内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仅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叙事研究[2]、文化身份解读[3]和伦理思想[4]上,对小说的空间书写,尤其是异托邦的建构鲜有涉及。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无论是社会空间还是个体的精神空间都受到“深刻的扭曲和重压”[5]3。在这种非常态空间中的个体是异托邦中的“不正常的人、偏离的人”[6]147。主人公罗莎一直设法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压制,寻求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这是戈迪默的小说创作不断探讨的主题——“逃离父母的家以及找寻到可以安身的家”[7]121。可以说,罗莎的每一次重要成长都和空间密切相关。罗莎在寻求独立精神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过程中顿悟,并最终在反种族隔离的共同体中找到自我的定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件自己的房间》中便强调了“空间诉求与女性独立生存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关联”[8]149。那么,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如何影响并塑造了主人公罗莎的行动和认知?什么样的家才是可以安身的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家”的母题与当下中国话语和价值体系中的“家”又有什么相关性?本文拟从空间批评角度,结合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之。
一、禁锢与规训的偏离异托邦
小说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段题词“我是一片发生过大事件的土地”①开启了整个篇章,由此点明了小说空间书写的基调。主人公通过视角转换,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着客体的“自我”——“自我”成为“各种矛盾影响的空间”[9]38。在福柯看来,“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消逝于其中的空间,我们的时间和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空间,吞噬和磨平我们的空间,也是一个自在的异质空间(即异托邦,笔者注)”[10]21。也就是说,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个体在被历史和时代塑造的同时,也被置于南非这个巨大的异托邦之中不得脱身。
1. 自由意志的缺失
罗莎的父亲莱昂纳尔·伯格是忠诚的反种族隔离的斗士和白人共产主义者,母亲追随父亲的信仰,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自从罗莎出生后,她的行动和意志就牢牢地和革命、政治绑定在一起。在罗莎对家庭和父亲的回忆中,出现最多的词就是父亲的“房子”,“房子”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
莱昂纳尔·伯格在世的时候,那所房子是他生活和革命活动的中心,凝聚了伯格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坚韧的革命斗志。因此,房子象征了伯格作为革命领导和家族之长的权威。与此同时,“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1]13-14。“房子”作为封闭的空间,将个体限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通过权力的运作对其进行规训。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房子成了束缚和规训自由意志的牢笼。在对空间转向的研究中,苏珊娜·辛克在论及女性旅行者和固定家宅之间关系时指出:“女性在父权框架之内实现自我定位的困难性。”[7]158对罗莎来说,那所房子不仅是他们的家,更代表了父亲的权力意志。
十三四岁本应是少女天真烂漫的花季,罗莎却在家庭和革命活动的熏陶下变得超出年龄的成熟、冷静和隐忍。从青春期开始,罗莎就没有享受过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所谓的恋爱不过是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她服从父亲的安排,“在那所房子里”和革命者诺埃尔·威特假订婚;在她还不懂得爱情是什么的时候,也不得不“在那所房子属于我的房间里”写着自己也不懂的情书,以未婚妻的身份去探监的同时传递消息;在别的女孩还在无忧无虑讨论八卦和无聊话题的时候,她已经长期奔波在学校、警局和监狱之间,忍着初潮带来的生理疼痛,在监狱门外给被捕的母亲送棉被和热水袋。从她生长的环境和经历来说,作为“伯格的女儿”,放弃自我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在那所房子里,我们为了革命活着,革命将会改变黑人命运”。而自我的情感和感受,“我们家任何人——那所房子……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
罗莎的第一个恋人康拉德曾清晰地指出:
“在你父亲那样的家庭中长大就是在一个虔诚的家庭中成长。也许没有人反复灌输马克思或列宁主义……可是他们就萦绕在你们家……在每个人的心里——家庭圣经。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感动你、什么不感动你,所有这些尺度都已经被预先设定。……而不是你个人的欢乐和微不足道的内心痛苦。”[5]38-39
在康拉德看来,罗莎“是在别人的期望中长大的”。在这一切行为的背后听不到“罗莎”的声音和诉求,她的自我是喑哑的。在“房子”这个权力意志的空间,“人或者主体的认同和角色在空间权力中被规训出来,肉体不断被空间权力锻造出来”[6]116。罗莎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出于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主观意愿,而是在房子的权力空间被规训后的顺从,“我伴着我父亲的存在而活,但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她在父亲的房子中被规训成了父亲所希望和需要的“伯格的女儿”,而并没有思考过真正的“罗莎”是谁,又是什么样的。
2. 对自由的渴望
随着罗莎不断成长,她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她开始意识到政治与革命并不是她内在的意愿。因为父亲在世,她“只不过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情”,“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对她来说,那所房子凝聚的是父亲辉煌和令人尊敬的一生,是他坚定的意志,但这些都与她无关。因此,父亲一去世,康拉德便告诉她“现在你自由了”。她卖掉房子,以期父亲的光环和控制力也将随之消失。然而,父亲去世、房子卖掉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文学空间研究专家罗伯特·塔利在论及存在主义哲学时认为,自由既是存在焦虑的根源,也是克服焦虑的方法[12]84,“焦虑与行动的自由相伴而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异化感。这是一种‘暗恐’体验”[12]84。尽管罗莎连父亲的骨灰也没有,房门上标志身份的黄铜铭牌也被拆除,对那栋房子回忆和记忆却始终萦绕在她心头。父亲生前的同事和朋友们依然将罗莎当作伯格的延伸,希望她能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她对自己被承载的期望不堪重负,“充满了逃离的渴求,就像逃离某种污秽的东西一样”。罗莎渴望获得自由和独立精神空间的焦虑便造成了她对那栋房子的暗恐感受。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个人的生活空间与属于这个空间、但已经不在场的那些人交织在一起”[13]345,“在场与缺席、感性的当下与历史的过去交织在一起”[13]393。房子出售了,但地点和空间还在,一起生活的回忆还在。此时,父亲是缺席的,但他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场:罗莎因为父亲的身份而被监视和限制行动,无法从事法律工作。她既难以租到房子,又无法获得护照,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一次当罗莎经过曾经的房子的时候,“与其说她走进了曾经的家,不如说她看到了自己的壳。——我想在那所房子里有愤怒”。她把这种愤怒解释为“对血统、基因的怨恨,对生我养我的精液和躯体的怨恨”。父亲的房子在囚禁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房子既是居住的空间,又扮演了精神病院和监狱的角色,福柯将这类空间称之为偏离异托邦,而在其中的个体“就与中庸或所要求的常态的关系而言,其行为乃是偏离性的”[10]23。父亲的影响由此处(房子)辐射到她生活的各个角落,房子成为她无法言说的创伤之地。
《空间的诗学》对家宅的最宝贵的特质做了以下描述:“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14]5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莎的家宅并没有起到庇护的作用。父亲的房子既是对黑人和有色人种开放的空间,是打破种族隔离藩篱的象征,又是规训身心、束缚自由的封闭的空间。房子由此成为叠加了各种矛盾和复杂关系的异托邦。尚处于青春期的罗莎对世界并没有全面的认知,在这样的偏离异托邦中,精神与心理不断被撕扯,她迫切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重新定义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
二、顿悟的危机异托邦
小说第二章开篇引用了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句——“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引言暗含了该章节的主旨,即在探索中求真,知行合一。对白人身份和隔离制度的愤懑、对无法继承父亲政治遗产的压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使罗莎得出结论:“我不知道怎样生活在莱昂内尔的国家。”换言之,罗莎不知道该如何才能真正成为父亲的女儿,“她必须先成为罗莎·伯格,然后才能成为伯格的女儿”[15]87。但她对于如何成为罗莎·伯格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于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和位置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迷惘和矛盾的,尚处在内心的“知”与外在的“行”无法统一的焦虑状态。为了摆脱这种思想危机,罗莎在幼年、青春期和成年后三个阶段分别进入了不同的看似可以逃避和摆脱危机的“房间”。福柯称这种提供庇护的“房间”为危机异位(异托邦),“一些享有特权的或神圣的或禁忌的场所,它们服务于那些处在与其生活的社会和人类背景相关的危机状态中的个体,诸如青春期的男女、排经期的妇女、劳动妇女、老人等等”[10]23。这些空间不断塑造着她的认知,她也在探索求真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自我的身份和责任,逐渐统一思想与行动,走向知行合一。
1. 童年—农场旅馆的房间
罗莎小时候在维尔玛姑妈家的农场暂住时就萌发了对独立私人空间的渴求:“她越来越多地待在旅馆门廊尽头的那两间标有‘私人房间’字样的房间里。”“那两个不允许客人进的房间正如罗莎所期望的,由她自己安排……让人感觉安全又舒适。……但她能感受到它们(指房间的摆设,笔者注)引发的种种联想与她内心世界的关联”。这样的私人空间极具异托邦功能:首先,这是连接着非异质空间的真实位所,但是却又是“外在于常规空间的空间”[6]145,因为这两个房间不同于普通旅馆房间,是没有编号的。尽管这两间房是属于旅馆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在那两间‘私人房间’过夜”,也就是说,空间既存在又不存在。其次,这个空间“假定了一个开放的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异位(异托邦)孤立起来,并使之同时具有可渗透性”[10]26。只要房门上挂着留言的便签本,便不会有人知道她在房间,也就不会打扰她,“没有人进入这些房间,但是罗莎可以随意出入”。尽管她因父母入狱而暂住在此,旅馆的私人空间对于长期处于规训和被监控状态的罗莎来说是重要的空间转换,“通过转换空间,通过离开习以为常的感性空间,我们开始和心理学上全新的空间发生交流”[15]266。在这样的异托邦空间里,罗莎的内心得到疗愈,她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保持独立而不受干扰。
但就在罗莎得以沉浸在这样私密的自由空间时,她忘记了“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16]124。种族和身份决定了黑人白人无法共享同一个空间。在白人孩子回到屋里享受食物时,她才惊觉和她一起来到农场,被伯格收养的黑人孩子巴塞尔被留在了屋后。那一刻,罗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顿悟,她开始明白为何巴塞尔抗拒这里,即使两人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黑人和白人之间依然有不可逾越的空间鸿沟,这种鸿沟是用肤色来定义的。而这也成为两人日后分道扬镳的预演。罗莎的名字的后半部分继承了祖母的名字“玛丽·伯格”,名字所蕴含的秩序、特权也在这个农场深深扎根,不可撼动。白人制定的秩序让罗莎感到被“包围着、覆盖着、捆绑着……这一切像洪流一样将她淹没”。戈迪默在评论种族隔离对于黑人与白人的关系的影响时说:“你的正义感被激发,你的良心感到不安,你的友谊收到种族歧视的限制……你的美好感情被羞辱……所有这些沉重地、不由分说地横在黑人和白人朋友之间。”[17]107因此,由顿悟引发的不安和羞辱让罗莎选择逃离这个曾经带给她自由的异托邦。
2. 青春期—康拉德的小屋
一直以来罗莎都生活在他人的凝视之下,是被监控、被谈论、被安排的。这种“被凝视”的状态剥夺了个体生活和情感的私密性,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也忽略了她的个人感受。伯格去世后,悲伤孤独和众人的期待所带来的压力让罗莎无法宣泄,走投无路之下住进恋人康拉德的小屋。首先,罗莎选择康拉德的小屋的首要原因是“那是一个陌生人的地方”。小屋位于城市边缘一片旷野之上,是远离人群和闹市的独立空间。在这样无人知晓的处所,罗莎才在长久的沉默和压抑之下,头一次放下戒备,敞开心胸,“他们在黑夜中低语,讲着自己的秘密。……欢乐、节奏明快的音乐在房间回旋。……他们起来在黑暗中跳起舞来”。小屋作为危机异托邦,为此时手足无措的罗莎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其次,康拉德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与罗莎截然相反,两人因为巨大的反差而好奇,继而互相吸引。康拉德是罗莎追求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启蒙者。在这个小屋里,康拉德给了她完全的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空间,此外,还有追求个人主义和虚无的价值观,除了“性和死亡,其他一切都在逃避”。这种将自我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恰好契合了罗莎当下想要寻求独立思想空间的需求。
然而,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并存的,不能脱离责任和义务而存在。康拉德对罗莎并没有恋人之间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不被任何人或事束缚,始终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住进康拉德的小屋后,罗莎离群索居,生活变得琐碎、虚无、毫无意义,只是“沉浸在自我陶醉的亲密中,没有保留任何成人的责任意识”。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评论这种自由主义者时指出:“独立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获得其日常意义上的应得。”[18]201尽管小屋给罗莎提供了暂时的自由与空间,在父亲的房子里的成长经历让罗莎无法忽视“他人遭受的苦难”,她的内心依然被关在外面的现实所牵动,无法平静,于是她选择离开小屋。当罗莎再度驱车回到小屋的时候,她发现已经“辨认不出瓦楞锡皮小屋的位置,那里已经被推土机推为了平地”。小屋在时空的存续上出现了断裂。与此同时,康拉德为了追寻所谓的自由而去航海,茫茫大海上的航船始终杳无音讯。小屋的消失与康拉德的失联暗示了盲目追求完全自我的自由人生终究不能脚踏实地,“对个体权利的过度强调只会进一步加剧业已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疏离”[19]84,其最终结果是“走向历史的虚无”[19]84。
3. 成年—欧洲的生活
因父母革命者的身份,罗莎一直无法离开南非去世界其他地方。父亲去世后,她托关系终于获得了去往欧洲的护照,而逃离南非去欧洲的目的,如她自己所说“我想知道如何摆脱他”,即摆脱她的父亲莱昂内尔·伯格。由此可见,农场旅馆和康拉德的锡皮小屋都无法让她摆脱父亲的影响。
罗莎启程出发去欧洲的第一站直奔伯格在法国南部的前妻巴格内利夫人,即卡佳。卡佳在罗莎这段法国之旅中,扮演了一个亦友亦母的角色,而“最初将罗莎吸引到卡佳的世界的是她从孩童时期就被剥夺而从未感受过的自由”[15]91。当罗莎来到卡佳的住所时,她被卡佳给她准备的房间惊呆了。房间的描写一改之前的阴霾色调,刻画了一个光线明亮、色香味俱全的花园空间,“灯照得十分明亮。灯光洒满天花板……一大罐子紫丁香,碗里的毛桃散发出香气……读诗歌和高雅杂志用的长藤椅……这是一个为想象中的人准备的房间。……埋在鲜花中的鼻子……桃汁顺着下巴淌下,揽镜自顾,心醉神驰,飘飘欲仙”。以这个花园般的小屋为缩影,整个法国南部都被塑造为一个甜蜜安详的感官世界,与南非的苦难现实形成强烈对比。这里“灯光柔和斑斓”“鲜亮的黏黏的”“敲打金属棒般的音符”,有“温暖寂静的夜晚。……琶音一样的笑声……新叶婆娑的葡萄架”。她沉醉在这个风光旖旎、如梦如幻的极乐世界,既没人监视也没人认出她,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她不惜牺牲伦理道德,成为有妇之夫沙巴利耶的情人,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爱与真理,在伊甸园一般的空间与情人仿佛亚当夏娃一般享受极乐,“狂野奔放、及时行乐、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不顾及任何对意愿的阻挠甚至背离”。她甚至接受了情人的安排去往伦敦一个公寓暂住,以方便两人偷情。
卡佳、沙巴利耶等人引领罗莎走进一个她渴求自由的理想空间,这是“实现对所在现实的补偿”[6]144的异托邦空间。这种异托邦“有某种创造幻觉空间的作用,这种幻觉公然排斥所有真实的空间”[10]27,它将罗莎同南非的苦难现实割裂开来,使她成为柏拉图洞穴里的囚徒,误把虚幻的影像当作真实的世界:她沉浸在两人的浪漫之中,却不想这是一段既不贞又没有名分、偷偷摸摸的恋爱,此乃伦理上的虚幻;她聆听着沙巴利耶关于政治的高谈阔论,充满了诸如“‘压迫’、‘反抗’、‘背叛’,他和其他人一样说着这些空话套话,并不知道他们代表些什么”,此乃思想精神上的虚无;她的周围围绕着被包养的人、对婚姻不忠的人、被抛弃的人、神经错乱的人、劝她忘记家乡忘记父亲的“友善的人”,此乃社会环境的虚无。这些都暗示了罗莎在欧洲的生活是荒诞的,缺乏真实的归属感。
真正将罗莎唤醒去看“洞穴”外真实世界的,是与她青梅竹马的黑人巴塞尔。他们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偶遇,出乎意料的是,巴塞尔在多年后的重逢中表现得相当冷淡。当天晚上,罗莎接到了巴塞尔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控诉了两件事:一是他真正的坦桑尼亚名字是“兹维林兹玛”,意即“受难的土地”,并不是白人家庭给他起的充满讽刺的名字“巴塞尔”(意为“小主人”,笔者注)。二是凭什么白人伯格的死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和他父亲一样的黑人革命者被捕后却只能在监狱渐渐老去,或者被杀,悄无声息?巴塞尔的电话给罗莎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和伤害,巴塞尔怒斥罗莎“我不知道你是谁”。儿时的青梅竹马如今反目成仇,正印证了戈迪默在《参照:文化的符号》中所说:“种族隔离之下的孤独,超过了任何百年孤独。”[17]44南非的种族主义和隔离制度远未结束,怨恨与苦难还在继续。而罗莎又如何能远走他乡逃避现实呢?
John Cooke指出,一个人不应缺乏“连续性”[15]94,因为忘记过去就只能活在“孤立的当下”[15]93。然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个人无法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个体不可能脱离集体,个人更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否则对自由和身份的追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仅如此,在多种族共存的南非大陆,白人与黑人的关系不应该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而应该是互相补充、彼此共建的和谐合作、相互成就。对罗莎来说,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作为白人,她应该在南非这样的国家如何发挥自己作为公民的主体性,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在不平等的社会,个人成就感也无从谈起。罗莎只有最终接纳自己的政治责任并作为个人信仰,才能真正成就圆满”[20]131。
三、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异托邦
罗莎逃离了种族隔离的生活,在不同的异托邦中获得了顿悟。但若要将“知”与“行”真正的结合起来,只有接受自己的使命并将自己投入创造南非新历史的进程中去,才能真正达到知行合一。罗莎践行知行合一的第一步便是回到祖国南非,献身革命。在此过程中,她投身两个典型的异托邦空间:医院和监狱。从福柯的空间理论来看,医院和监狱作为封闭的规训空间,是对病人和犯人实施关押并剥夺自主和自由权利的场所,被束缚和规训的主体并非没有获得自由的可能。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指出,“个人是历史和政治话语作用的地方,是接受者也是创造者”[21]112。罗莎选择在医院和监狱中实践个人信仰,既是在明确革命信仰和责任担当之后的抉择,也是对关押空间的反抗,对其原有秩序的解构和创造性重构。
1. 医院—医患命运共同体
福柯在其空间理论中将医院描述为典型的偏离异托邦,收治的个体“与常态或者被建构为常态的个体不一样”[6]134,医院是对病人进行训诫的权力空间。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医院规训空间的性质被颠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主人公罗莎回到南非后,成为约翰内斯堡一家黑人医院的理疗师。这家医院收治了许多天生残疾的孩子,他们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走路。罗莎通过不断引导这些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帮助他们重燃生活信心。随后,1976年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爆发了血腥的索韦托惨案,南非白人政权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枪杀数百名黑人学生。白人政府将黑人的生命弃置于法律和秩序之外,再现了二战集中营的“例外状态”,即“合法的非法权力空间”[22]94,黑人的生命沦为阿甘本所述的“赤裸生命”,他们“被一种既不渎神也不违法的暴力杀死。……这一暴力正是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最本真的形式”[22]90。大量伤者,尤其是青少年,被送往罗莎所在的医院。罗莎目睹了每一个黑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创伤,“哀痛和愤怒是融合在一起的”。罗莎和所有医护人员一起,救治和照料这些受伤的人们。她虽然“没有孩子,但他们经过她的手,那是她的工作,把他们尽可能地集合在一起,在医院里”。
在此之前,罗莎逃离南非,不断寻求可供逃避危机和焦虑的异托邦,试图让自己从创伤中恢复。欧洲的经历和国内的现实让她看到个人痛苦之上整个民族和国家内部的巨大裂痕与创伤。回国后,她开始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人疗愈创伤。她在帮助他人重建人生的同时,也在重建自己的人生。此刻罗莎考虑的已不是过去和当下的自我,而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那就是未来,父辈无法预见”。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浪潮的感召下,她的关注点由自我转向他人,转向南非的未来。当下,医院作为规训空间的性质已被改变,它脱离收容异类和边缘人群的偏离异托邦,对需要救治的人群进行治疗、提供安抚和庇护所。医院已然成为所有医护人员包括病人在内的命运共同体。他们之间除了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更是完全相同的群体。她所救助的是同属于南非家园的同胞和家人,她所工作的医院成为暴动混乱局势下的方舟。
Andrew Ettin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家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家人们是塑造我们最初也最深的力量。……‘家’的意义还包括了家园,‘家人’也意味着所有我们认同为亲人的人们”[7]121。对于罗莎来说,父亲的房子和祖国南非,是她一直想要逃离的“家”。然而又是“家”的力量让她依然选择归来。戈迪默曾说:“家不一定是民族归属感,而是你生长的地方,是你每日一睁眼在你身边的面孔,是在你的整个人生中同你一起在政治上、个人或艺术上挣扎奋斗的同胞们。”[23]34罗莎不仅仅是经历个人苦难的小写的“人”,更将自己视为这片历经磨难土地上的大写的“人”当中的一员。
2. 监狱—反种族隔离共同体
在《伯格的女儿》中,罗莎所经历的最后一个异托邦是监狱。监狱作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为最典型的异托邦,是“被隔离起来,成为孤立的不被许可进入或者有条件被许可进入的空间”[6]142。小说的结尾与开头做了两处呼应:一是开篇主人公站在监狱外面,给监狱里面的妈妈送东西;而小说结尾是罗莎因参加革命,自己被捕入狱。二是小说初始,罗莎最想要逃离的便是父亲的控制以及他所选择的道路;而小说结尾,罗莎也最终认同父亲,走上和父亲一样的道路。此刻,她没有任何被迫与愤怒,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女子监狱内部呈现出与传统监狱截然不同的状态。观念中的监狱应该是隔离分区明确,然而这里不同肤色、不同地方的人却混杂在一起。不同于福柯在《监狱的诞生》中所描绘的边沁全景敞视监狱的严苛管理,这里“是如此破旧,事实上,那些防止内部交流的实际屏障形同虚设”[5]305。在罗莎和她的黑人朋友玛丽莎的带领和影响下,狱警不仅无法阻止信息交流,而且监狱里还飘荡起优美的歌声。歌声一响起,所有的黑人妇女都跟着唱和起来,监狱里时常传出欢声笑语。整个监狱形成了一张沟通和交流的网络,所有的人都串联在其中。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里说:“一些对于空间的非常规使用,就会变成挑战社会秩序的手段。”[24]116监狱作为实施关押、监控、规训和惩罚的国家机器的性质被逐渐解构,成为不同肤色和种族人群的同盟,形成了一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体。监狱共同体的形成挑战了白人国家机器的权威,隐喻了对西方二元对立价值体系的颠覆。
在这个同盟形成的过程中,罗莎既影响和带动着别人,也被他人改造着。此时的罗莎在一系列异托邦空间的塑造和影响中,脱离了曾经不断追寻的空洞的自我,也摆脱了父权阴影笼罩之下压抑的自我。“罗莎·伯格”取代“伯格的女儿”,变成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己,获得了真正的主体性。当伯格生前的朋友去狱中探望罗莎后,回来评论道:“她很好,状态很好。……不过她不知何故比过去更活泼了,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含蓄。我们说了好多笑话。”在罗莎邮寄给卡佳的信中,她提到了在狱中看到了父亲说过的反射到墙面的阳光。这束光象征了她与父亲最终的和解,更是她对父亲的信仰的领悟和接纳。与此同时,这束光也象征了南非大地在苦难和灾难中孕育的建立种族平等共存的家园的曙光和希望。
四、结语
罗莎从逃离父亲的家到最终融入反种族隔离的命运共同体,最后才发现,无论是卖掉父亲的房子还是逃进各式各样的异托邦空间,她依然无法逃离的是源自内心的对“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一方面对她来说,“从那所房子出来的人”,若是以追求自由和自我为目的,“那是真正的孤独:没有社会责任地活着”。此时的她已经从被迫逃离到主动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也给出了她对生活和时代的回应:个人的主体性不应超越他所归属的社会、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个人是属于自己的,但他也是属于他所生活的家园和世界的。倘若没有这样的根基,自我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层面上看,罗莎对家园和祖国的回归非常贴近中国人观念中“家”和“国”交融的家国情怀。这种依恋与归属感“让人们不管身在何处,也不管遭遇怎样的危难,都把‘家’作为自己的生命母体、把‘国’作为自己的社会母体,都把‘家国’作为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依归”[25]70。作为同样经历了百年艰苦卓绝反帝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伟大国度的人民,中国人对独立、自主、强大的祖国也有着深情地向往,并义无反顾地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中去。这种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在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而现实的意义。在文学作品创作中,这种意义即表现为“在后现代视角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如何讲述一个同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故事?”[26]134
另一方面,父亲的房子从不曾消失,它一直都在。在那所房子里“白人的该隐和黑人的亚伯融合在一起,这种全新的手足之情为走向最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铺平了道路”[5]110。黑人也好,白人也罢,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戈迪默在《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中写道:“分开生活,黑人和白人都在败坏自己道德的国度。共同生活,我们才有可能越过白人控制、黑人控制,以及其他一切让我们彼此漠视的妨碍,从而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人。”[17]109作者在小说结尾描绘监狱里不同肤色和种族的狱友们欢声笑语的场景,正蕴含了戈迪默对于南非各种族人民共存的希望,这也印证了巴什拉对艾吕雅《生活之必要》的引述:“当我们的天空连成一片,家宅就有了屋顶。”[14]46小家、大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大的“家宅”至关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和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戈迪默建构异托邦空间所希望达到的题中之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世界和平充满挑战的后疫情时代构建一种更美好的相处模式和共同体的可能。
注释:
① 文中引用纳丁·戈迪默《伯格的女儿》的内容,均出自李云、王艳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