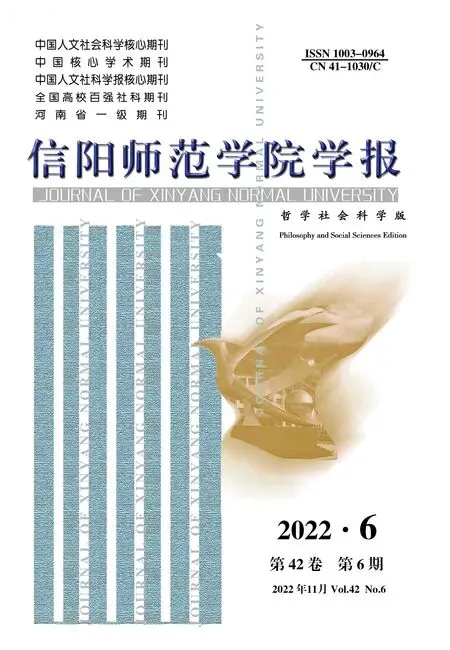剧本创作视角下的戏曲文本音乐性构建
李 娜
(沈阳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从戏曲起源开始,就包含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成分[1]28,由此“综合性”就成为戏曲艺术的“天然基因”,并在其此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巩固强化。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以歌舞演故事”来概括戏曲艺术,指出戏曲的完整意义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2]32。由此可见,戏曲具有将歌、舞、叙事文学等多门类艺术形式融于一体的综合性特质,这也使戏曲文学具有了区别于一般性文学样式的诸多特点。张庚把戏曲文学称为“剧诗”,认为戏曲是以诗写剧,把剧写成诗[3]8。他的观点,更强化了戏曲的中国艺术美学气质,使戏曲文学的独特性得到进一步强化:戏曲文学在叙述性、“言志”和“意境”说等文学特征之外,还蕴含了另一个重要内容——由诗化而产生的音乐性。基于此,在戏曲剧本的文学创作中,既有一般戏剧所共同的“故事”层面的叙事创作,又蕴含了戏曲综合性中对音乐性的要求和呈现,成为戏曲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创作面向,是戏曲艺术本体性得以完整实现的戏曲文本的深层设计与构建。
一、戏曲文学的音乐性构建
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使文学自古就有对文字音韵美的重视和强调。无论是诗、词,还是曲的创作都表现出文学的音乐之美。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很早就出现了对文学的“声”“音”“韵”“律”的论述与主张。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4]320“刻镂声律”[4]326等观点,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需要对音节格律进行雕琢修饰。他还在《文心雕龙》中从《声律》到《练字》共7篇里,分3个层次集中论述了声律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声律问题。此后,随着戏曲的逐渐成熟,在传统文学中对音韵美的追求,发展成为戏曲中的音乐性特质。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出对戏曲曲词的艺术要求:“句子长短平仄,须调停的好,令情意婉转,音调铿锵。”[5]220以达到“美听”的目的。 其中,“音调铿锵”就是对戏曲文学音乐性的概括,通过对句式和音韵的安排设计,体现戏曲文学的音乐美,使其能够完成戏曲所承担的“情意婉转”和“美听”的艺术目标。
(一)声韵的音乐化
戏曲文学的音乐性首先是指戏曲语言在声韵上的音乐化,主要表现为戏曲文学中唱词、念白所具有的音乐性。这既来源于戏曲文学的诗化传统,也和戏曲文学必然要通过舞台来呈现紧密相关,这两者综合起来就要求戏曲文学要可歌、可演、可读。因此,戏曲文学的语言文字和曲式结构都有着严格的音韵规定性,要求在戏曲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时时关照戏曲唱词、念白的声韵使用、音乐结构的安排、声调节奏的设计等,其目的是使戏曲文本通过音乐化的语言文字,提供舞台表演较强的音乐性语音韵律、句式节奏,以及符合戏剧表达的音乐结构形式,在文学性之上以更立体、更形象的多元方式塑造人物、表达情感、营造氛围、反映社会。戏曲文学正是以文学性与音乐性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戏曲“剧诗”化的舞台美感。
一是韵辙的使用。所谓韵,是指音节的收音。把同韵字按一定规则排列在曲词句尾,即为押韵[3]109。戏曲的唱词和念白(主要是韵白),在创作中都遵循着合辙押韵的语言规则。近现代广泛使用的十三辙,是根据北方语音,合并了中州二十一韵后,形成的十三个韵部的戏文用韵规则。在戏曲曲词的创作中,通过诗、词、对句等语言形式,遵循韵律规则,选用适当的韵脚辙口,通过戏曲文本语言的音乐构建,形成了韵辙相适、节奏变化的音乐美,形成发音或响亮或婉转或激荡或细腻的语言音乐性变化。比如,京剧《黛玉葬花》中林黛玉的唱词:“花谢花飞飞满天,随风飘荡扑绣帘。手持花帚扫花片,红消香断有谁怜!”通过诗化的语言,将意象美与音乐美相结合,充分表现人物的情绪情感,强化人物性格塑造。
二是声调的设计。声调指字音的长短高低,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戏曲文本的创作中,声调分为平仄两类,平声长而舒缓,仄声短而多高低变化。在曲词创作中,剧作者通过遵守和使用上下句的平仄规则,如每句平仄声交替相间、上下句间平仄相对、连句韵上仄下平等,对字或语词进行声音方面的新排列组合,使其声调发生变化,形成句段语音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旋律感,实现曲词独特的音乐性声调。在戏曲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剧作者需重视戏曲剧本的文学语言与戏曲音乐的协调一致性,即通过妥当的曲词文字的平仄设计和句式安排,使戏曲的音乐性得以充分实现。例如,明代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归纳昆山腔的音乐特点时所说:“声则平上去入之宛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6]198他在道出昆山腔音乐美的同时,也指出了昆剧的文辞与音律的关系。语言字声的“平上去入”要与曲调之间相互协调,昆山腔的乐音也充分照顾文辞中的字音,唱腔以字音为主。例如,阴平字多平出,阳平字则由低转高,这样唱出来它的旋律走向就和字的声调是一致的。只有戏曲文学中的字与声、词与律相互“宛协”了,才能形成抑扬回环、收煞适宜、字正腔圆、声调和谐的戏曲韵律之美。戏曲的众多曲谱和曲牌就是为了方便剧作者把握戏曲文本语言与戏曲音乐的关系而逐渐形成的成熟范例。
三是语音修辞的运用。语音修辞是通过对戏曲语言的音、韵、调的设计安排,如使用押韵、叠韵、叠字、双声、衬字等方法,打破一般性曲词较为规整的句式,让语言更加鲜活多样,加强语词的音乐感,使语言的句式、节奏更加灵动,风格富于变化,使戏曲文学在声音层面产生特别的效果或产生独特的情感意义。比如,《长生殿》中李龟年的唱词:“早则是喧喧嗾嗾、惊惊遽遽、仓仓促促、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就是语音修辞与情节叙事相结合的典型用法。再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一句唱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其中的“春色”原词是“春天”,但句中“迎来春天”形成了四个平声的连用,“迎来春天换人间”整句则仅有一个仄声字,大大削弱了曲词的音乐变化性。于是剧作者在反复斟酌之后将“春天”改为“春色”,使“色”和“换”构成两个仄声连用,增加了全句的音乐性。在戏曲文本的创作中,通过字与字、词与词的组合安排,形成新的语音关系,来改变语词原有的响度、力度和流畅度,形成适宜演唱的曲词语音起伏、声音错落、语词多姿的戏曲语言效果,产生具有意义的情感表达,形成戏曲文学音乐性和文学性的融合构建,为戏曲音乐、戏曲的戏剧性创作提供声音和情感连接的基础。
(二)句式结构的音乐节奏化
宋祖光认为戏曲曲白有“三性”,即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3]106。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是戏曲剧本创作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在戏曲文本的创作过程中,剧作者要清晰地把握住戏曲文学不同于一般性的、以阅读为目的的文学样式的特点。尽管戏曲文本仍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和呈现形式的,但戏曲文本中的文字、语言始终都是非完全文学化的,甚至在一些时候还要调整和节制文学性,而让位于语言的音乐性。可以说戏曲文学的语言是高度音乐化的语言,是需要基于戏曲“三性”特征而精心设计的,通过符合音乐声韵的词语使用,具有鲜明音乐节奏感和流畅性的句式结构安排,形成独特的音乐效果,与戏曲的舞台表演、音乐曲调、演唱节奏相契合,以极具形式感、表现力、情境性的文本形态,使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始终保持一致,实现戏曲文本的文学性与音乐性的高度融合。
一是音乐结构的强调。戏曲的音乐结构体制主要分为曲牌体结构、板腔体、综合体和山歌体四种,在创作中,会由剧种不同、剧目风格和容量不同而进行不同的选择,常用的是曲牌体和板腔体。曲牌是填词制谱用的曲调调名之统称[3]107。若干支曲牌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一组曲牌音乐,若干组曲牌音乐又组成一个剧目的音乐,就构成曲牌联套。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目前仍是昆曲、高腔主要采用的音乐结构体制。而板腔体则是以板式的安排和变化作为音乐的基本结构方式,通常板式可分为三眼板类、一眼板类、有板无眼类、散板类等。这些板式的自由组合和变化,其前提就是戏曲语言的诗化特征,再辅以声腔的转换,来完成不同情绪、不同氛围的戏剧任务。戏曲剧目的音乐结构系统的选择,决定了剧目音乐的主体样态,成为剧目曲词创作的基础和遵循。基于戏曲音乐结构的样式即曲牌体、板腔体、综合体和山歌体等艺术特性和规定,戏曲曲词的创作需要严格遵守相应戏曲音乐结构的“规矩”。但戏曲曲词的创作却不是僵化的,它和戏曲表演的程式一样是戏曲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构成部分。戏曲独特的音乐结构,表现在曲词上就是诗化的语言,来自传统诗化语言的音乐特质使曲词能够与音乐相配合,通过声腔演唱,在塑造人物、传情叙事、描绘世界时,具有诗化的、自由的审美气质。
二是句式节奏的音乐性。戏曲的曲词从句式、用韵到声调都严格遵循戏曲音乐性的需求,因其是配合音乐而歌唱的,所以曲词的创作与曲调、演唱高度契合。例如,板腔体曲词句式的变化,无论是七字句,还是十字句,或是五字句、四字句、三字句、二字句,都是通过对句式节拍的划分,来创建不同的音乐节奏。字数不等,节拍不一,这些诗化文字语言节奏的变化带给音乐、演唱以丰富多样的二度创作空间,能够表达多种不同的情绪和起伏变幻的剧情,形成戏曲独特的节奏感、音乐感和寄寓于此的中国文化特殊美感。通常一个唱段的句式并不拘泥于单一节拍,而是富于变化的。用长句可以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如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中李奶奶唱革命家史时,用了多个长句来表达坚定而热切的革命情感。更多的时候,唱段的句式会根据需要而相间排列,将二二三或三三四等不同节奏的句式交叉使用,还可以穿插短句,其目的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是为了避免节奏的单调,通过设计句式的参差错落、变化多姿,增加文本的动态美和音乐性。
二、剧本结构的音乐性
戏曲剧本创作中的音乐性建构,除了语言文字的音韵、声调、句式、节奏、修辞等音乐化之外,其实还有着一种更深层面的音乐逻辑安排,主要体现为戏曲结构的整体布局、核心唱段的构思和程式化的配置。
(一)整体布局
在戏曲剧本着笔之前,要对所创作的题材故事、人物事件、主旨高潮、开头结尾等进行布局设计,这是对剧作整体性的思考,让戏曲文本的各个部分在比例、相互关系方面协调、平衡、流畅,使戏曲剧本为戏曲舞台表演提供故事情节和音乐化空间。同时戏曲文本的主旨、人物也通过戏曲音乐来更好地彰显和推动,以多元化表现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与表达情感,实现戏曲文本的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双重美学建构。
戏曲剧本创作的整体布局是对剧作的集中,特别是对中心人物、中心事件的确定。在戏曲的北杂剧时期,剧本体制和演剧体制规定只一人主唱,或是旦或是末,以此确定中心人物。到了南戏、传奇时期,尽管剧本篇幅增加,演唱的人也不止一人,但剧作的中心人物仍只有一个。到今天,现代戏曲无论是剧本内容,还是舞台表演艺术都要比传统戏曲复杂丰富,但把冲突和情节集中在中心人物身上仍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戏剧冲突的集中化,不会把戏写散。更重要的是,中心人物往往居于人物关系和情节冲突的中心而贯穿始终,其精神和情感通常是剧作主旨的体现,把握和构思好主要人物,剧作的大体轮廓也就确定了,中心思想、情感和高潮也基本明晰了,而此后剧本创作都是在朝着这个最高点努力的,这其中不只有文学性的建构,还有音乐性的设计安排,所有的创作都向着这个中心而来,这是剧作的关键所在。
(二)唱段安排
戏曲表演综合了“唱念做打”,而唱居首位(指一般情况)。在剧本创作中唱词的创作是重中之重,唱词写得好不好,常成为评价戏曲剧本的重要标准。有不少戏都是因为其中著名的唱段而久演不衰。但评价唱词唱段好与不好,除了考察其文辞是否优美、音韵是否和谐之外,还要看唱词唱段是否在最合适的戏剧点把人物的内在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中佘太君的一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的唱词,以一腔正义之情诉说杨门的赤胆忠心,将人物的激烈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看得感动、听得过瘾而产生共情。这其实已进入戏曲艺术本色的问题。
戏曲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下,戏曲现代戏更是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其中有着不少与其他戏剧样式相互学习借鉴与融合的成功案例,但从戏曲剧本创作角度来看,与创新戏曲适应新的审美文化相比,在发展中传承戏曲特色,突出戏曲艺术本色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剧本创作部分的特色传承,就是要把唱段创作好,这既有对戏曲文本音乐性的考量,又有彰显戏曲剧作本色的讲究。戏曲剧本重“唱”,是由戏曲艺术的“抒情”特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戏曲在情节矛盾、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搭建等方面的创作努力的最终指向都是为了“传情”“抒情”,从而“唱”的内容就成为戏曲剧本的核心。由此可见,戏曲唱段的设置,不仅仅是音乐性的演唱,更是为“情”,为剧作主旨而唱。也就是说,戏曲的唱段安排,是在语言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在人物情感爆发的时候、在矛盾冲突到达高潮的时候,为了人物情感得以充分表达、为故事情节更好推进而设置的。因此,当下,很多戏曲作品被评价为“话剧加唱”,其实质就是没有把握好“唱”在戏曲剧作中的价值和意义。戏曲中的“唱”,是戏剧性与音乐性的双重需要,有着剧作内在结构的情感需求和发展逻辑的,不是文本的平均主义,而是来自于剧本情节结构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歌唱和表达的需求,与人物的情感发展、矛盾冲突、舞台情境等紧密相关,是“不得不唱”的必然表达。
戏曲剧本中唱段安排,要从整体结构层面出发,安排在情节的重要转折点或者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时刻,呈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巨大变化,以及为了表达需要为舞台表演所创建的音乐性、舞台性、文学性交融的空间。因此,戏曲的唱段的铺排创作总关“情”,如人物间有着重要情感交流时的唱段,像京剧《四郎探母》中“坐宫”一场,秦腔《窦娥冤》中“婆媳刑场诀别”一场;再如人物面临重大转折时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像京剧《杨门女将》中“惊变”一场,越剧《红楼梦》中“哭灵”一场;还有特定情境下人物深层内心独白,像京剧《失空斩》中“空城计”诸葛亮与司马懿城上城下的独唱独白,祁剧《王昭君》中“出塞”的意投黑水一段,都是戏曲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唱段。以音乐的形式将剧作中最“紧要处”,形成了表达的高潮,并“重着精神,极力发挥使透”[5]206技巧,使情节与抒情、音乐与文学、舞台与文本间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三)与程式相配置
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舞台艺术,悠长的历史发展积淀,形成其多层次的动态结构特点[7]。其中戏曲表演的程式性、虚拟性特征影响着戏曲剧本创作的始终。一个不懂戏曲舞台美感和戏曲表演程式意味的编剧很难写出好的戏曲剧本。这是因为戏曲的多层次动态结构决定了戏曲文本与舞台表演的紧密结构,这直接决定了戏曲文本的多层次动态结构,即包括故事结构、技术结构、美学结构等多个层次,它们相互协调,形成戏曲多样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构成戏曲剧本创作的重要规律。戏曲表演的程式化隶属于技术结构层面,是戏曲艺术的突出特征,指由“唱念做打”综合而成的歌舞形式。
戏曲的表演程式化,对剧本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表演程式是不同于生活的真实样态,而是对生活自然状态的凝练和艺术化,是有格律、有节奏的表演技术格式。其次,这种表演技术的格式化被一代代戏曲艺人通过舞台实践,不断完善而固定下来,成为被普遍采用的表演规范,被严格的遵守和传承。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要求戏曲作者从构思到落笔,必须充分了解和熟悉戏曲表演的程式化,把剧本创作与戏曲舞台程式的形象思维联系在一起,在剧本创作时就为舞台表演设计出“无声”的节奏感。也就是说,要把剧本的情节故事与戏曲的“唱念做打”各个程式相配置,形成最恰当的组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戏曲剧本能演。戏曲剧本不能写得“太满”,要给程式化表演留出空间。戏曲剧本还不能让演员只说不动,而是要在唱词和念白的创作中为表演的动作性创造可能。这就需要剧作者有统筹兼顾的本领,在文本的创作中,重视曲白的动作性,使各种程式表演能最佳地发挥其特点,在文本中为表演提供空间、留白和节奏。只有这样的戏曲剧本,才是属于舞台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案头文学。
三、戏曲剧种、流派、演员对戏曲文本音乐性创作的影响
剧种、流派和演员的风格特质也是影响戏曲文本音乐性创作的关键要素。戏曲剧种、流派和演员舞台表演的审美独特性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音乐的独特性来展现的。这除了需要戏曲作曲家的精心设计和编创之外,也需要戏曲剧作家戏曲文本创作的支持,在文本中突出剧种亮点,给出音乐创作的特色空间。因此,戏曲剧作者较之话剧、影视剧作者,要有更高的专业素养,要“懂戏”,要“了味”,更要“有情”。只有剧作者充分了解和把握所创作的戏曲剧种、流派和演员在艺术表现上的独特气质、“味道”和样态,如剧种的音乐个性、流派的唱腔技法、演员的表演特色、适合的题材领域等,才能在文本创作时将剧种的独特性彰显出来并融入整体剧目的创作之中,使每一段唱词写作、剧情设计、氛围烘托、人物语言等都能为舞台表演提供恰当的基础,为二度的音乐创作、导演构思、演员表演等提供全方位的文本支持和情感表达空间。
(一)剧种
中国戏曲有300多个剧种。各个剧种因不同的发展历史、地域文化和声腔演唱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剧种特色。戏曲从成熟之始,就有北杂剧和南戏之分。两者由于地域特征、社会风俗、人文审美、情感表达等方面的不同,使北杂剧多豪迈慷慨之气,而南戏则多细腻温婉之声。戏曲的民间性又决定了戏曲剧种与地域历史文化、百姓生活紧密联系,它在扎根地域与兼容人生百态之间不断生发、丰富、流变,并逐渐形成形态多样的剧种,而各个剧种经过一代代艺人的潜心创作,兼容并蓄,呈现出稳定且独具特色的审美气质和音乐特色,如京剧、评剧、梆子剧等,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韵味和风格。
每一个剧种的音乐都有其独特的基本调式,成为该剧种艺术特色的显著标志。在戏曲剧本创作视角之下,由于剧种音乐所独具的基本调及剧种所蕴含的丰富地域文化特殊性,使不同剧种的戏曲文本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就是大家常说的剧种的“味儿”,特别是在文本内容题材、音乐结构、语言韵辙、唱词数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今天,很多传统剧种的音乐创作,仍保留着“以字生腔”和“以腔就字”的音乐创作方式,即为唱词选择适合的传统唱腔,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修饰、创新,力求保持剧种基本调,也就是核心艺术特征的保护与传承。由此可见,戏曲剧本创作对剧种基本调性规则的遵守,对保持剧种音乐的风味特色,传承剧种传统音乐美,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戏曲剧本的唱词写作,要求剧作者根据不同剧种所特有的基本调或特征调的板式变化来进行创作,使唱词文字符合剧种调性对于语言节奏节拍和句式长短的要求,让剧种的基本唱腔创作得以顺畅开展,并保持剧种所独有的风格,从而让观众可以通过戏曲剧本曲词所体现出的音乐性和美学气质就能判断出一个剧本的剧种或是地域。比如,昆剧、越剧、黄梅戏等江南剧种,在曲词方面就体现出流丽悠远、典雅隽秀的音乐美感。而另一些地方小剧种,如关东喇嘛戏、江西采茶戏等,因剧种根植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曲词和念白都更加的口语化,充满民间趣味。
当下,戏曲剧本创作出现了一种“泛剧种化”[8]现象,就是剧作者为高效、快速、通用的出作品,在戏曲创作中运用一般性的剧作方法来创作戏曲地方戏的剧本,而忽视或放弃了戏曲剧种对剧本文本的音乐性的独特需求,使剧种的艺术风格、表现方式、情感风貌、方言乡音等诸多独特性都被模式化的剧本文本创作大大削弱,造成“千戏一面”的局面,损害戏曲多样性的发展,不利于剧种独特风格和审美特征的保护和传承。
(二)流派、演员
戏曲流派和演员风格也是影响戏曲剧本创作音乐性的因素。中国戏曲剧本创作一直有“为演员写戏”的传统。这是由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特征所决定的,也是受中国传统戏曲长期以来“演员中心制”的影响。尽管随着戏曲改革,“导演中心制”的深化,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剧体制在不断被弱化,但演员对于戏曲艺术的重要性却从未减弱。余秋雨说:“站在剧本立场上,演员只是角色的载体;而站在宏观演剧的立场上,各种角色只是梅兰芳、俞振飞、严凤英、常香玉们发挥自身魅力的载体。”[9]这充分表明优秀的戏曲演员对戏曲表演艺术的重要性。
为演员写戏,其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演员的特长。在戏曲中只有演员的艺术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剧本故事才能更好地被演绎,戏曲的魅力才能得到更好地彰显,才能更吸引观众。同一个剧目由不同的流派和演员来演出,会有不同的舞台效果,甚至产生“一体万殊”的样态。这就需要剧作者根据流派、演员的不同特质来创作和调整剧本文本的细节,使唱词、唱腔、板式等内容更符合流派和演员的特点,有利于戏曲灵活多变的表演形态的形成。例如,评剧经典剧目《杨三姐告状》被改编为豫剧版,其部分唱词的尾韵被改成了更适合豫剧声腔特色的韵辙,如“尊厅长”一折唱词中“发”“答”“查”等字尾韵、“容”字的高腔、“专程”的发声等,都为豫剧剧种声腔特色的发挥提供了文本空间。同时,桑派的唱腔特色也为豫剧版“尊厅长”一折戏增添了抒情感,呈现出与评剧不同的审美风貌。
戏曲观众欣赏戏曲有着明显的多元化需求,而这种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也影响着戏曲剧本的创作。他们一方面在看故事,另一方面在欣赏演员的表演,所以戏曲剧本绝不是单纯的文本创作,其中蕴含着创作者对于戏曲艺术的舞台表演节奏、音乐唱腔、程式安排、时空构建等要素的统筹安排与思考。剧作者在戏曲文本故事层面的创作中,不能只写情节矛盾、发展高潮,还要考虑演员的声线、行当、表演,以及观众审美习惯和欣赏期待等因素,来综合完成剧本创作。这些综合因素使戏曲剧本超越了剧本的文学范畴,进入戏剧剧本所关涉的舞台表演和音乐层面的艺术创作。为“角儿”、为名家写戏,为流派唱腔代表性人物写戏,根据他们个人所具备的在“唱念做打”方面的艺术特长来进行创作,如京剧《大探二》“唱”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剧目的大多数篇幅,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演员来充分地“唱”,让观众尽情地“听”。这种在剧本中对某一特殊程式的侧重,是编剧基于对演员表演的充分熟悉而在创作中为突出其表演特点而特别选用其擅长的程式完成的构思和创作,这样的“量身定做”让演剧充分发挥演员的优势与长处,是戏曲文本创作的一个重要方法。特别是在旧时的戏班时代,戏曲名家梅兰芳与齐如山、程砚秋与罗瘿公、荀慧生与陈墨香、尚小云与清逸居士等组合,都是表演名家与编剧长期合作的典范。他们共同创作,编剧了解演员的特点,演员与编剧分享对舞台表演和构建的意见,从而实现了戏曲文本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的直接结合,进而产生了众多好戏,又因为剧目带有鲜明的演员表演特征,而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特色。观众在欣赏名家流派表演之时,其聚焦点已经不再是熟悉的剧情,而是表演所呈现出的流派声腔之美和艺术之魅。在京剧中,杨派的全本《伍子胥》、梅派的全本《生死恨》、程派的全本《窦娥冤》都是充分彰显流派个性、演员风格的剧本。在这样的作品中,剧本的文学性已经相对不重要了,剧本创作成为为演员表演提供故事空间的基础[10]。
戏曲剧本的文学创作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结构,既有一般戏剧所共同的故事层面的文学性创作,又有着以舞台表演为指向的技术层面的创作,同时还通过文学方式来构建戏曲艺术独特的美学特征。坚持戏曲剧本创作的多元面向,是戏曲艺术本体性得以完整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也是戏曲文本在文学性、音乐性、舞台性等方面的“多重美学建构”。戏曲剧作者应关注戏曲艺术的独特性,在文学创作上传承和创新以音乐性为代表的多元舞台构建方法,以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的方式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创设情境、反映现实,通过文本创作的多层面艺术融合,为戏曲舞台表演提供文本支持和审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