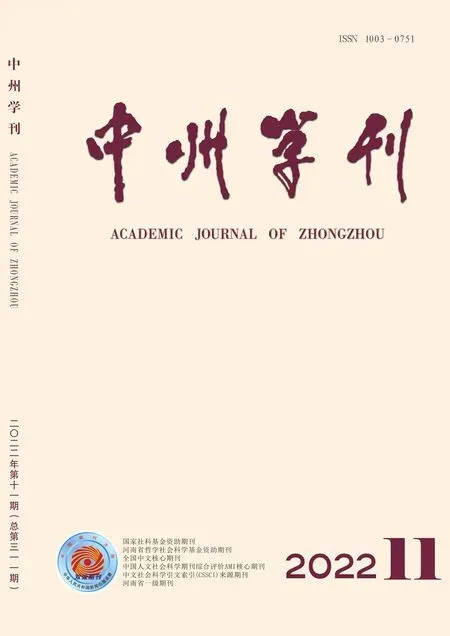杜甫华州去官是弃官还是流放?*
张 起 邱 永 旭
一、问题缘起
华州去官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关捩,诗人遭遇的苦难无不由此而起。经历这一事件后,杜甫的诗风也为之一变,由明丽直截变含蓄隐讳,许多事在诗中不能直说,只能寄托遥深,被迫沉郁顿挫。自宋代出现“去官说”后,递相祖述至于今,影响深远。比如在学界影响较大的陈贻焮、莫砺锋,在各自的《杜甫评传》中也以“弃官说”为圭臬。但笔者越认真读杜诗,越觉得这种说法令人生疑。此事关涉诗人事君交友、生平出处大节,甚至可以说它影响了诗人后半生的运程,对解读杜诗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一疑案加以考证很有必要。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杜甫华州去官,是因关中饥荒主动请辞,还是肃宗进一步加责免除?到底是弃官,还是罢官?他入陇蜀,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被迫流放?从他与肃宗的微妙关系看,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华州去官,古今学者几众口一词,认为是他主动弃官。但笔者认为杜甫并非这种人。他很忠君、很重传统,“奉儒守官”,报效朝廷,是其家族传统。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作《进雕赋表》自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祖父文采风流,“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天下学士到如今而师之”[1]2172。杜甫家族门风清华,儒学传家,世代官宦。奉儒守官,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传统道家的逃逸、魏晋名士的个人解脱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迂拙,都与他无关,家族传统中无这些基因。他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自比“稷与契”,述志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已表明其人生态度。莫砺锋认为:“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绝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2]如果没有外力逼迫,他怎会无端辞官?
杜甫华州去官之前的行为已表明,他是一位忠君爱民的诗人。天宝十五载,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奔蜀,肃宗灵武接位,杜甫迁家鄜州,北上勤王,途中陷贼军,困于长安,作《哀江头》,有“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之语。后来,他冒死窜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如此危境,忠勇的诗人都经历了,怎会因饥灾弃官呢?在华州他作有批评肃宗的《洗兵马》、描写战乱和百姓苦状的“三吏”“三别”,他怎可因饥荒便弃华州百姓独自逃荒?杜甫刚到华州,即埋头工作,作《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代州牧写《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分析形势,仇注云“经国有用之文”。这一时期他还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写李嗣业安西兵马过境讨安庆绪,“竟日留观乐,城池未觉喧”为王师讨贼而高兴。《夏日叹》《夏夜叹》记录了邺城三月兵败后关中久旱无雨的景象,人祸天灾,生灵涂炭,满目萧条,诗人“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化用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诗》“对食不能餐,临觞不能饭”,忠君忧民之状溢于言表,毫无辞官之志。从其价值观与道德人品来看,他不可能弃官逃荒。所以,“弃官逃荒说”纯属无稽之谈,颇不合诗人家庭传统、人生理想及为人处世。
翻检近年研究杜甫的文献,杜诗研究虽为“显学”,但相比而言,对于华州去官问题却鲜少追寻,囿于定说。早期如20世纪80年代郑文《杜甫为什么弃官》、冯钟芸《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到近年丁启阵《论杜甫华州弃官的原因》、安志宏《“少陵弃官之秦”探因——关于杜甫弃官流寓秦州的补充意见》、陶成涛《杜甫弃官奔秦州原因再探析》、师海军《杜甫离职华州西行论稿》均从宋人之说。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多是就弃官原因分析,未能上升到罢官这一层面。如冯文史料运用非常详尽,可惜仍在旧说里转圈子。郑文既有退隐之志分析,又有罢官猜测,惜无结论,便有些模棱两可,在文末说明:“由此可见所谓诗人的弃官,并非由于天灾饥饿,而是由于人事排斥,本诗自道明甚。以上所举,理由还不够充分,证据还不够切实,请候高明,作进一步之探索。”陶文则把杜甫说成忧惧战争而逃亡,将诗圣视为偷生之辈,而无视其忠勇。文中将杜甫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在蜀中所写的《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中的“不关轻绂冕,但是避风尘”之句,肤浅地理解为字面的“躲避战争风尘”,不明白诗人为尊者讳的苦心,说“杜甫担心叛军再次攻入潼关,担心华州再次沦陷,故而提前弃官西逃”。师文是新近的研究成果,却又回到宋人弃官旧说,进一步分析了“主动辞官”的原因,认为诗人离职华州西行及其在秦州的经历是去找人,是为了去凉州投奔河西节度使杜鸿渐。这属于主题先行式写作,完全不可取。
21世纪初有人提出“华州罢官说”,如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王勋成《杜甫罢官说》、李宇林《杜甫罢官华州原因探析》、韩成武《解说“罢官亦由人”之“罢官”——对杜甫离开华州任原因的讨论》,但在分析原因时,要么牵强附会,要么与弃官原因大同小异。如李文虽然说华州“罢官”,却认为是因为杜甫身患重病,难以应付繁重的公务而遭“顶头上司”罢官。韩文认为“罢官”有两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二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离职属前者,是对肃宗政治失望而自己罢自己的官,实际上仍等于“弃官说”。阎文虽认可罢官,却说诗人是因“荒怠政务”中途擅离职守跑回河南“触犯职律”而遭遇罢官。这种看法没有理解诗圣之心,与历代对诗圣的认知严重不符。王文认为杜甫罢官是因为唐代考官制度,秩满罢官,是“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的一项措施”。这里把杜甫看成普通平民士人,与杜甫家世身份不合。王文看似另辟新路,实际上却不可取,此时是盛唐而非中晚唐,官路未见堵塞,只有中晚唐科举放开,平民士人大量出现,才使得进身之路十分拥挤,而朝廷提供的岗位又不能满足需求。
“罢官说”虽然比“弃官说”有所进步,但仍然未能看清杜甫遭遇流放的真实遭遇。研究杜甫,都知道“华州事件”对解读诗人后期诗歌的重要性,但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如果上升不到“流放”的程度,则难以解释透彻杜诗,难以解释清楚杜诗前后诗风的重大转变。不知杜甫遭遇流放,导致今人对其草堂诗的误解。不少人对诗人经历丧乱之后,在成都获得表面平静生活的诗歌作闲适写景解读,完全低估了草堂诗的价值。比如《草堂即事》,就并非写景诗,其中“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之句埋藏着诗人对朝廷、对君王的深切眷恋。杜甫在草堂诗中大量引用《离骚》《诗经》中的典故,即可知其自比屈子之难。又如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在成都所作《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表面在写风雨摧拔楠木之景象,实则在写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暗示了诗人对失势玄宗的同情。读者如果不知诗人介入的深浅,便不知诗人心中的滴血。《读杜心解》说“深痛摧埋失色”,叹楠树,亦是诗人遭遇流放的自叹。
二、多种典籍对杜甫华州去官的误载
关于杜甫华州去官之事,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仇兆鳌考订朱鹤龄《杜工部年谱》中所说:“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3]16二是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所说:“乾元二年己亥(759),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4]69三是王士菁《杜诗今注》中在《立秋后题》下注:“这首诗约为乾元二年盛夏已过,立秋后辞去华州司功职务,即将前往秦州时所作。”“罢官二句”下注:“这是说去官之意完全由自己决定,心不为形所役。反陶诗之意而用之,以明去官之志。”[5]以上不同时期的说法皆从主动“去官说”,均把“华州事件”简单化,殊不合诗人的理想抱负。
追本溯源,杜甫华州“弃官说”出自两《唐书》。《旧唐书》文苑本传记载:
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6]3193
《新唐书·杜甫传》记载: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书,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庭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畿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7]3588-3589
但两书均距杜甫生活的时代较远,不能说最权威,并且两史杜甫本传皆有重大缺漏。《旧唐书》言“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文义不连贯,从华州参军直接跳到寓居成州同谷县,中间有重要信息脱漏,故意漏言杜甫“寓居成州同谷”之因,似有隐情。《新唐书》则径直言“关畿饥,辄弃官去”,明确说杜甫为饥荒弃官,去过不受约束的自在日子。比较两书,《旧唐书》并无“弃官”二字,100多年后编纂的《新唐书》中添加“弃官”二字,让人殊难理解。危急关头,一贯为苍生号寒啼饥的杜甫会抛弃自己一直关心的黎庶,不负责地弃官逃跑,去过“负薪采橡栗自给”的生活?这不仅严重违背他“奉儒守官”的家训,而且与他后来在成都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展现的儒家情怀相悖。从杜甫一贯的立身行事来看,他不会如此前后人格分裂,“华州逃荒”几不可能。
追而溯之,《新唐书》的“弃官说”盖源自宋人王洙《杜工部集〈记〉》介绍杜甫生平时所说的“属关畿饥乱,弃官之秦州”。“逃荒说”则是王洙根据《旧唐书·肃宗纪》中关中灾荒的记载,增补杜甫弃官的原因是“关畿饥乱”。王洙的记载误导天下人千年,并引起后人对华州之后大量杜诗的误读,至今未得到匡正。
三、杜甫华州去官的真相
杜甫华州去官之因是什么?《旧唐书》不便写出,直接略去;《新唐书》说是“弃官”;杜甫自己也刻意回避。从杜甫自身而言,他具有忧念百姓的情怀和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并且这种志向老而弥坚,他无论如何不会坐视人民苦难主动辞官。天宝十四载(755年)他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年后,回奉先省亲,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充分表达自己坚定的志向与抱负: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仇兆鳌注曰:
(第一至八句)此自叙生平大志。公不欲随世界立功,而必朝圣贤事业,所谓意拙者,在比稷契也。甘契阔,安于意拙;常觊豁,冀成稷契。[8]259
(第九到二十句)此志在得君济民。欲为稷契,则当下救黎元,而上辅尧舜,此通节大旨。江海之士遗世,公则切于慕君而不忍忘;廊庙之臣尸位,公则根于至性而不敢欺。此作两形,以解同学之疑。浩歌激烈,正言咏怀之故。明皇初政,几侔贞观,迨晚年失德,而遂生乱阶。曰“生逢尧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复为令主,惓惓忠爱之诚,与孟子望齐王同意。[8]259-260
(第二十一句到第三十二句)此自伤抱志莫伸。既不能出图尧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负稷契初愿矣。居廊庙者,如蝼蚁拟鲸,公深耻而不屑干。游江海者,若巢由隐身,公虽愧而不肯易。仍用双关,以申上文之意。放歌破愁,欲藉咏怀以遣意。[8]260
杜甫要求自己向稷、契看齐,为了此志,即使落得一生勤苦、一事无成,也不愿转移志向。虽然他惭愧没有像许由、巢父飘然世外,但不愿改变节操。所以,杜甫不可能辞官逃跑,其华州去官另有原因,笔者认为是他与肃宗的君臣关系出现了问题而被罢官。《旧唐书》不记去官原因,是受为尊者讳的史传传统约束。杜甫自己避而不谈,也是在为尊者讳。
综观杜诗,杜甫仅在《立秋后题》这一首诗中非常隐晦地提及华州罢官之事: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次日作。杜甫此前所作忧国忧民的《夏日叹》《夏夜叹》均无辞官的迹象。立秋次日即言“罢官亦由人”,可见罢官是在立秋日。“节序昨夜隔”,暗示昨日还在官,隔夜就被罢免。“日月不相饶”,除时序更迭外,背后还有日月力量。日月代表着谁,诗人没有说。他是别有一番痛楚不能说,此乃春秋笔法。我们联想这一时期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十》中的“双悬日月照乾坤”之句,可以推知,日月分别指玄宗和肃宗。“日月不相饶”不能单纯解为化用鲍照诗句“日月流迈不相饶”,而是一语双关,还隐含着鲍照下句“令我愁思怨恨多”,由此可知诗人对罢官多么痛苦不堪。
《杜诗详注》中朱鹤龄、王嗣奭、仇兆鳌对这首诗的解释皆失误,所谓“此诗盖欲弃官时作”“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9]544,均是不解诗人之遭遇。其实杜甫在诗题中直接点明这首诗立秋后作,是别有深意的。古代设官立制、刑杀赦免均要依节序,应四时。《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用始行戮。……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10]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下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11]杜甫在立秋之日被罢官,隐晦地道出肃宗迫不及待地对他秋后算账。
翻检杜诗,可以发现杜甫对于涉及自己重要人生关节的诗全有自注,唯独《立秋后题》这首没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在为尊者讳。这种良苦用心,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乾元元年(758年)杜甫由长安出华州途中作《题郑县亭子》,也在“为尊者讳”,诗中有“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之句。诗人为谁伤神?他苦楚难言,自己的遭遇不可留于“青竹”。又如五年后他在蜀中写的《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中有“不关轻绂冕,俱是避风尘”之句,谈到当年被驱赶出朝、华州罢官时,也是十分含蓄隐讳,完全把责任归于自己。尤其是“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两句,既隐含安史之乱,又映射肃宗擅自接位、架空父皇的不孝行为。晚年他在总结性长诗《壮游》中也刻意回避关涉自己人生大节的华州罢官事不记,仅言“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前句暗指诗人当年任左拾遗时激烈批评肃宗的行为;后句暗示华州之难及流放陇蜀的遭遇。担任左拾遗却不能进谏,反而被放逐边荒之地,诗人故意跳过其中的原因与过程不言,只能“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中有许多带“病”字的句子,这往往并非指身体之病,多数情况下应当理解为君臣之病。他所“病”之人,是罢官背后的强大势力,也就是诗人“为之讳”的唐肃宗。我们从“罢官亦由人”之句可知,杜甫不是简单贬谪,而是被革职。因政治打击而直接罢官,惩罚过于严重,之后像永贞之变这样扰乱朝纲的重大政治事件,当事人也仅是被长期贬逐。由此可见,杜甫与肃宗之间的恩怨已超越房琯事件。
四、杜甫与肃宗的君臣关系
杜甫与肃宗的君臣恩怨,我们可结合史料梳理出二人交集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一是杜甫与肃宗二人的关系始于天宝十三载(754年)。
《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7]3588天宝十三载十月杜甫守选期满,授河西尉。河西县属同州(陕西渭南),为春秋时期游牧部落大荔戎进入洛水建立的戎国之地。这与诗人的正统观念不合,他并未像一般寒士考选出来那样去就职,于是再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自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左右卫率府参军为太子武官,掌兵仗羽卫,设仓兵胄三曹参军,从八品下,官阶不高。《新唐书》称杜甫“胄曹参军”有误,《旧唐书》称“兵曹参军”是准确的。杜甫在这个岗位履职一年余,有多首与官员交往的诗可以为证。这一年他还得到休假,多次往返奉先(陕西蒲城)探亲。从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一诗可知,太子曾委派家令李炎去看望杜甫,从中亦可推知杜甫与太子的关系比较密切。
杜甫做了一年率府参军,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他又从京城赴奉先探家,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笔者细致阅读杜集,发现杜甫履职一年多后才回奉先探亲。不少学者读书时误将天宝十三载这年省去,认为天宝十四载杜甫官定后即回奉先探亲。如果按今人观点,至少有11首杜诗无法编年,杜甫北上勤王,而不追玄宗入蜀的行动,也不能准确解释。
二是至德二载(757年)春,杜甫自长安亡走凤翔,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遗,受到肃宗器重。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述怀》注:
唐授左拾遗诰:“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黄纸,高广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今藏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12]
宣义郎,散官衔,从七品下;左拾遗,职事官,从八品上。杜甫由兵曹参军改左拾遗,属升迁。左拾遗虽为从八品上,却是天子近臣,“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13]。肃宗把如此责任重大的职位交付于杜甫,可见对他充分信任。杜甫左拾遗的任命由中书、门下二省奉皇帝敕诏颁授,比吏部铨选授官更为尊荣。左拾遗为敕授官,由皇帝授予;旨授官由吏部铨选上报,再下旨颁授,人选并非出自皇帝。可见此时肃宗非常器重杜甫,君臣关系融洽。
光复后杜甫回到长安,肃宗曾给予他很大恩遇。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载,“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上亲享九庙,公得陪祀”[4]68,可谓荣显。仇兆鳌注:“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这种莫大的荣耀给杜甫留下美好记忆,晚年他还在《往在》中述此盛事:“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耿金钟。侍祠恧先露,掖垣迩濯龙。”至德二载五月,杜甫作感恩诗《端午日赐衣》,可见君臣之间往来密切。
三是至德二载闰八月初一,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遣返鄜州省家,君臣关系开始疏远。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记载:
至德二载丁酉,公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4]65
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六月,房琯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4]69
《旧唐书·房琯传》记载:
上由是恶琯。……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6]2076
房琯五月十日被贬为太子少师,杜甫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遗。因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之交,杜甫向肃宗“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甫谢,且称:‘琯宰相子……酷嗜鼓琴,庭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然帝自是不甚省录”[7]3588。
“墨制”是指皇帝避开中书、门下二省用墨笔亲书诏令。肃宗不经外廷盖印就直接向杜甫下达亲自书写的遣返诏书,说明他对杜甫非常生气,很有可能在廷上匆匆草就。杜甫对这一突然下达的诏命毫无思想准备,感到茫然失措。但他在被遣送鄜州省家路上作长诗《北征》,仍在忧虑国事、忧君失误,东坡称赞“《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3]406。在杜甫看来,只要正义就要坚持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在肃宗看来,这种做法不仅违背圣心,更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了。
乾元元年,肃宗出贾至汝州,贬房琯邠州,下除高适太子少詹事,刘秩、严武等均被逐。朝中发生这么多大事,不少旧臣受到处理,身为谏官,杜甫感觉自己有谏诤的责任。正如其《题省中院壁》所云:“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他认为,如果谏官无忠言以补天子,便是愧对皇恩。
杜甫初为谏官,便以房琯罢相之事上疏,这触犯了肃宗内心的禁忌。肃宗先登基再通告玄宗的做法有违儒家血缘伦常,他要借贺兰进明谗毁房琯之故罢免房琯以平息非议。房琯罢相是肃宗对玄宗旧臣有计划的清洗,杜甫却抓住此事上疏力抗,由此得罪肃宗。这并不是杜甫迂腐,而是他看清了肃宗面目后的深思熟虑之举,是其一贯的忠勇正义的行为。他知道房琯恢复相位已不可能,但他偏要不可为而为之,这并非不合时宜,而是要表明态度,阻止肃宗继续迫害大臣和上皇。广德元年(763年),他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仍说“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委婉批评太子继位违背伦常。《旧唐书·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也就是说,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玄宗八月才知情,有一个月的时间天下有二主。杜甫的清醒,正是肃宗惧怕的。因此,在同年闰八月初一,杜甫被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由此开始,他与肃宗渐行渐远。从《北征》“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之句看,他内心对皇帝的疏远感到惶恐不安。
杜甫直言极谏的执着,让肃宗烦恼,因为这样对自己清除旧臣、树立权威不利。当时上皇还健在,旧臣与之多少有瓜葛往来,这是肃宗心病,必须处理。乾元元年杜甫出华州后,同年八月肃宗又将李白流夜郎。当时被处理的官员基本上不是玄宗旧臣,便是永王李璘之人,唯有杜甫出自东宫,但他却没有站在肃宗阵营。他去京时作《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时值朝廷用人之际,自己却遭受贬谪,由此更可看出他内心的无限悲凉。此诗仇注引元人赵汸《杜诗选注》:“公虽遭谗黜,而终不忘君,……岂为一身计耶?”又引清人顾宸《杜诗律注》:“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处之大节。曰‘移官岂至尊’,不敢归怨于君也。当时谗毁,不言自见。”[3]481杜甫一生遵从君臣大义,无只字怨君,只能自嘲“不怪君王,怪我才不合道”。诗人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长安。
四是至德二载十一月杜甫自鄜州归京,继续任左拾遗,至乾元元年六月突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君臣关系恶化。
杜甫出京前,作《酬孟云卿》,“但恐天河落”之句暗含被贬的原因。是年肃宗处理大批旧臣,笔者推测他又会上疏阻拦。他在朝廷目睹肃宗对上皇不孝的做法,刚到蜀中便以春秋笔法写下《杜鹃行》,微言大义对肃宗进行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可见他立场之鲜明、态度之坚决。
君臣关系是封建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左迁华州后杜甫也可能托人做过疏通,努力修复君臣关系,但没有成功。杜甫有《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特意注明“冬末以事之东都”,至于何事,诗人没有详说。杜甫诗集是诗人自编,他在编订时对自己重要的人生关节,都有“自注”,由此可见“之东都”一定不是小事,如仇兆鳌所言“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节也”[3]25。按人之常情推测,当时诗人内心最焦虑的应该是修复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有《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为证。杜甫在冬至怀念同事及左掖生活,流露出对过去朝中生活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当前处境的愁闷。怀念同僚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朝廷。此时,杜甫被贬华州已有半年,但君臣关系没有缓和的迹象。在湖城(河南灵宝)刘颢宅宴上,他醉酒作诗“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款曲”须互通,“艰难”尚努力。他期盼“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但只有“天开地裂”才能沟通长安之路,这实在太难。“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时过境迁,合辙难求,暗喻君臣关系难以修复。但当他从洛阳转回华州不久,却被无情地罢官了。估计肃宗得知有人求情后,更为发怒。
乾元元年冬末,他急于往东都见何人?依笔者推测,很可能是高适。刘开扬《高适年谱》记载:
758年,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高适五十五岁。贬官为太子少詹事,赴洛阳。适后有《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五月,过睢阳,有《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夏日,在洛阳,有《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章甫)所居》诗。又有《送崔录事赴宣城》《送桂阳孝廉》,似亦洛阳之作。
759年,己亥,肃宗乾元二。高适五十六岁。五月,出为彭州刺史,有《赴彭州山行之作》。于蜀山中为乱军劫夺。九月,史思明入洛阳。十月,引兵攻河阳城,李光弼率诸将败思明将周挚,擒徐璜玉等,思明遁去。十一月,适有《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又《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亦是年冬作。至彭州,有《谢上彭州刺史表》。十二月有《赠杜二拾遗》诗,时杜甫初至成都,寓居草堂寺中。[14]
由上可知,杜甫去洛阳时,高适正以太子少詹事的身份分司东都。他有可能是去求高适帮忙,去之前特意写了《寄高三十五詹事》,中有“时来如宦达,岁晚莫情疏”之语,但从“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来看,他还没有收到高适的回信,所以他直接去洛阳求见。在洛阳,高适很可能答应帮助他,故乾元二年年底,杜甫一到成都便收到高适的《赠杜二拾遗》,得到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这相互形成的锁链,或可解“冬末以事之东都”之谜。当然这仅仅是根据杜甫与高适关系的推测,能否成定论,尚待新材料进一步考论,此处只是抛砖引玉。
五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杜甫毫无征兆地去官。
杜甫华州去官,后人皆言“公有高蹈之志”,因其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但笔者认为,“高蹈之志”与他不符,杜甫不是道家人物,也没有杂家思想,他是纯儒。即便流放秦州,他仍有《蕃剑》述志:“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趠,龙身宁久藏。风尘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是年,贬邠州一年的房琯被召回,“诏褒美之,征拜太子宾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15]。贬巴州的严武也在上元元年(760年)迁东川节度使,次年擢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可见,肃宗对琯党的处罚并不严,是给了出路的。
但杜甫则不同,这一年他反而彻底失官了。为什么?因为在华州他坚守初衷,仍在含蓄地批评肃宗。如《洗兵马》作于邺城大战前,当时王师已扫清外围,诗人对未来河清海晏充满期待。但我们仔细品味相关诗句,可以发现,诗人并不止于“赞”,而是明“颂”暗“刺”,明“赞”暗“讽”。经历华州之贬,遭受切肤之痛,杜甫已经深知肃宗为人。由“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蛇晓”之句,开始转向“刺”。实际上玄宗自蜀还京后从未有如此待遇,诗中故意这样描述岂不是“讽”?“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之句再提房琯事,又是明“赞”暗“讽”。萧丞相、张子房分别代指房琯、张镐,二人都有辅宰之才,但都被罢相了。“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之句,更是在讽刺肃宗不明忠直之臣,随意刑罚。此诗虽然是颂诗,但诗人没有“空颂”,对肃宗有美有刺。“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与“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形成鲜明对比,揭示肃宗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肆意赏赐自己人,处理父亲旧臣时却十分残酷。末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表达了对肃宗治国的强烈否定。《钱注杜诗》云:“《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感受到了诗人之心,明确指出:“此公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16]67肃宗显然也感受到了《洗兵马》中诗人的良苦用心,因此很快将其罢官。环视琯党成员,尤其是朝廷高层,唯有杜甫坚守君臣大体,秉持忠义之气,容不下破坏人伦秩序的事。所以,称杜甫是唐代的孔子,称杜诗是“诗史”,皆是中肯的评价。
六是上元元年(760年)杜甫被流放成都,作三首“杜鹃诗”谴责肃宗。
在蜀地时,杜甫罢官已过数月,仍不能释怀,作《杜鹃行》,借古蜀神话追记肃宗不尽人子之道:
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跳枝窜叶树木中,抢佯瞥捩雌随雄。毛衣惨黑貌憔悴,众鸟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华屋,短翮唯愿巢深丛。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饥始得食一虫。谁言养雏不自哺,此语亦足为愚蒙。声音咽咽如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口干垂血转迫促,似欲上诉于苍穹。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教学传遗风。乃知变化不可穷,岂知苦日居深宫,嫔嫱左右如花红。[12]636
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再作《杜鹃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12]116
《钱注杜诗》云: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迁居西内。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皇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诗云“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移杖之日,上皇惊,欲坠马数四。高力士跃马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又令辅国拢马,护持至西内。故曰“‘虽同君臣有旧礼”,盖谓此也。[12]117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在云安(重庆云阳)再作《杜鹃》。此时代宗已即位,努力纠正父亲错误,拨乱反正,以工部员外郎召还杜甫。《杜鹃》乃是杜甫还京途中写给代宗的颂诗。杜甫之所以去蜀,是因为他要赴京受职。《年谱》此处说严武暴卒后杜甫失去依靠去蜀,完全错误。全诗如下: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12]168
这三首“杜鹃诗”均采用了“诗史”笔法,深含春秋隐意,以蜀人悲杜鹃啼血,杜宇禅位传说,托寓上皇与肃宗之间的恩怨。作前两首时,肃宗在位,杜甫虽在流放中仍坚持批评。他即使远离政治中心,也心系朝廷,堪称唐代屈子。最后一首作于代宗时期,诗旨已完全不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762)建巳月:“甲寅(五日)上皇崩于神龙殿。……丁卯(十八日)上崩。”[16]由此可知,大历元年的《杜鹃》是写给代宗的赞美诗。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沉郁顿挫”是一种贵族情怀,“顿挫”即上下有序、尊卑错落的儒家社会秩序,如“行飞与跪乳,识序与知恩”。诗人此时已获代宗启用,正还朝接受郎官,遗憾“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一片忠谨之意。此诗写于去蜀后病阻云安,不能进京报天子恩遇,正是“顿挫”之诗。可惜,国内学者对“顿挫”的理解存在不小的误解。
对比前两首,第三首“杜鹃诗”在赞美代宗的同时,也是在谴责肃宗,一褒一贬,诗人多么深婉顿挫。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能得出如下逻辑:杜甫疏救房琯是表象,反对肃宗清洗旧臣才是目的。他以疏救房琯表达对玄宗的支持,也就引发对肃宗擅自继位的质疑。杜甫最重儒家血脉亲情,将违背伦常看作“乱源”,在华州他以《洗兵马》批评肃宗不孝,这些做人原则,无论是杜甫担任左拾遗期间,还是在华州参军任上,都是他实现“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所要坚持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肃宗步步迫害。杜甫忧心如焚的“乱世”,包含两方面:一是安史之乱,二是人主不尽孝道。百善孝为先,讲的是秩序;万恶淫为首,说的是乱的根源。这两条肃宗与安禄山都触犯了。大逆不道与忤逆不孝,皆是违背天下秩序之祸首,这是杜甫终身批判的,所以他自然也不会见容于肃宗。但杜甫又特别尊崇君臣礼义,不能直接谴责皇帝。即使肃宗强逼玄宗退位的事实也不能提,只能将一腔忧愤化为疏救房琯的抗颜直谏。杜甫之心,别人不知,肃宗却会感知,故有罢官处罚。诗人之苦,“后世罕有知之者”。这就是肃宗对所有“琯党”都予平反,唯独不放过杜甫的根本原因。在华州,他“独立万端忧”,却讳言不能述。
五、华州罢官后杜甫遭遇流放
杜甫华州罢官后,他去往何处,为何不能回长安呢?这又是一个关节问题。他不能回去,一如“罢官亦由人”那样无奈,这是流放,去哪里由不得他,自然未能再回长安。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其中“因人作远游”已隐讳道出他遭遇了类似屈原那样的放逐,这是关乎他日后成为“诗圣”的重要内在因素。
关于流放的去向,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样分析:“是时东都残毁,既不可归,长安繁侈,又难自存。”并举杜甫在秦州时所作《寄高岑三十韵》中的诗句“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为证,认为居秦州是因其侄杜佐居东柯,那里雨水充足,“秋禾有收”,“因携家徙居焉”[4]169。闻氏延续《新唐书》的“辞官逃荒说”,故有“惟秦州得雨”适合居家的认识。这种认识将诗人遭遇放逐简单化地理解为为了生存,没有明白“无钱居帝里”乃诗人采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得雨”,真是秦州有大自然之“雨”吗?真是为了生存去秦州吗?这只是字面意思,笔者以为必须回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看问题,从君臣关系分析中找到隐含的答案。
杜甫华州罢官后,皇帝为何不让归京?原因很简单,怕他回京生事端,议论自己清洗旧臣、稳定政权的策略。长安不准回,杜甫只能流去秦州,故才有“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之叹,一种无奈莫可言述。杜甫的流放是被指定去处的,秦州自汉代以来即行役戍边的苦寒之地,羌戎杂居,杜诗称其为“天末”,指中原之外,即为天边,有惩罚之意。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形容秦州“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和杜甫一样被放逐秦州的,还有长安高僧赞上人。二人交往频繁,相互慰藉。杜甫写过三首诗送他,其中《宿赞公房》自注“京中大云寺主,谪此安置”,诗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被“谪”呢?仇注引赵汸《杜诗选注》:“赞,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9]592-593两相参证,二人均“因人”“因事”去秦州,或为肃宗的统一安排。
到秦州不久,杜甫又被迫前往两百里外的同谷。他在《别赞上人》中感慨“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他不愿再流,可肃宗迫害又至,不知何时会停止。他在《发秦州》中说“生事不自谋”,“惘然难久留”,这些奔波都不是自己的本意。在同谷他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其中“中原无书归不得”之语感叹命运难自主。入蜀也是肃宗的安排,杜甫有《发同谷县》,“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深含微意。诗人由华州到秦州转同谷再到蜀中,故言一年“四行役”,离京城越来越远。谁役使他?诗人没有说,我们不难推测应是肃宗加害。以上推论可知,华州去官非本愿,秦州流放属无奈,入蜀也非他自主决定。此时正逢国家多事之秋,用人之际,不反对肃宗的王维、岑参均在数月内得到迁升,杜甫却一步一步远离政治中心。由此可见,他与肃宗的君臣关系不是一般糟糕,这是导致他被罢官的根本原因。
后来,杜甫又补京兆府功曹。《旧唐书》载:“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新唐书》载:“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朝廷召补杜甫京兆府功曹在何年?从肃宗对他的态度来看,应在肃宗驾崩后,代宗宝应元年征召。杜甫有《奉寄别马巴州》自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宝应元年(762年)七月杜甫送严武至绵州,严武还朝任京兆尹,即为他请此官。因吐蕃滋扰,杜甫应召阻滞阆州,无法出川。广德二年(764年)正月,严武再督川,改请节度参谋。杜甫十分欣慰,写下《奉待严大夫》,从“一生襟抱向谁开”之句看,只有严武最了解他的志向。
杜甫虽然遭遇流放,历经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怨君失志。在同谷,他有“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的号呼,声明自己不弃理想,不做清流。流放蜀中时,他不怨天尤人,反而诗思壮阔。《赠蜀僧闾丘师兄》中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他对皇恩只有感激,无个人怨悱。在苦难中,他没有颓废,从“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的诗句中,可见少陵旷怀。
杜甫遭遇罢官流放,千载无人言述,无论钱谦益还是仇兆鳌,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许故意疏忽。我们抽丝剥茧发现其中真相应该是:在古代血缘伦常政治中,人伦忠孝是执政之基,杜甫对于肃宗不敬上皇、违背伦理,及由此引发对肃宗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戳中了肃宗的痛处,导致他受迫害,在所有琯党平反后,他反而被罢官流放。但《新唐书》与《旧唐书》均为尊者讳言,使“诗圣”之痛苦千古沉冤。
综上,杜甫华州去官实为“罢官”,再流放陇蜀,直到肃宗驾崩,代宗继位,他才在严武的大力举荐下得以复官,相当于获得朝廷正式平反。这期间,杜甫有四年时间无官职,以后又经幕府参谋、蜀中军功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入朝就职。终因途中消渴病发,被阻夔州,但他仍赤心不改,期待还朝。诗人因糖尿病销蚀身体,不能还朝履职,最后在一条孤舟中带着无尽遗憾与忧伤离世。
杜甫的不幸遭遇,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正是因为华州罢官,流放陇蜀,杜甫后半生诗歌转入春秋笔法的隐讳,成为“诗史”。诗人的不幸遭遇强化了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这里说一下笔者对“诗史”的理解,“诗史”决非文学史泛解的现实主义诗歌,而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具有四个标准,一是言王事,二是语词曲折意含褒贬,三是让乱臣贼子惧,四是为尊者讳。我们理解杜诗中称为“诗史”的诗,当围绕这些标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华州罢官,陇蜀流放,成就了“诗史”,成就了这位五百年一遇的伟大诗人。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