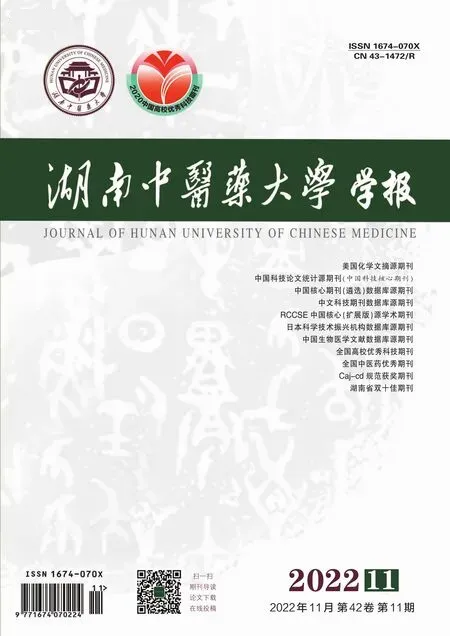蔡连香教授“扶正祛邪法”治疗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经验探赜
史宇思,黄欲晓,蔡连香,方庆霞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 100091)
宫颈癌发病率位居妇科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第二位[1],严重威胁女性健康。 持续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HR-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最重要因素[2-3]。 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是与宫颈癌密切相关的一组宫颈癌前病变,可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病变。 因此,积极阻断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感染、合理有效地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可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宫颈癌变[4-5]。
由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发展为浸润癌需经历长达10 余年的时间[6]。 目前,对于单纯HPV 感染及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以随访观察为主[7],但随访时间长、且过程中仍存在一定进展的概率,给患者身心带来巨大压力。持续HR-HPV 感染是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持续和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一旦进展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则以手术治疗为主(环形电切术、冷刀锥切术等)[7],虽疗效显著,但是对于那些病情反复、需要多次治疗的患者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8]。 因此,近年来探寻阻断HPV 持续感染、逆转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药物引起了广泛重视。
中医药对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各个阶段均可开展治疗,意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多项研究已证实,中医药对HR-HPV 感染及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防治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9-13]。蔡连香教授是第三届首都国医名师,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妇科学术带头人,是第二、三、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业医60 余载,在中医药治疗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笔者有幸师从蔡教授,受益匪浅,兹将其诊疗宫颈癌前病变的经验择要浅述如下,以飨同道。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中无“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一词,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多表现为白带增多、色质异常、外阴瘙痒、异常阴道出血、宫颈肿物等症状及表现,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将此病归属于“带下病”“阴痒”“癥瘕”“崩漏”等范畴。 《女科证治约旨·带下门》载:“若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酝酿成病,致带脉纵弛,不能约束诸脉经,于是阴中有物,淋漓下降,绵绵不断,即所谓带下也。 ”《傅青主女科·女科上卷》中论治带下病时云:“夫带下俱是湿症。 ”根据带下颜色将其分为青带、赤带、白带、黄带、黑带,强调青带核心病机是“肝经郁火,下焦湿热”,赤带核心病机是“肝阴亏虚,肝不藏血”,黄带核心病机是“肾阴虚火旺,任脉虚损”,黑带核心病机是“火热之极”。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四·阴痒候》载:“妇人阴痒,是虫食所为。 ” 《景岳全书·妇人规》提出:“瘀血留滞作癥,惟妇人有之。 其证或由经期,或由产后,凡内伤生冷,或外受风寒,或恚怒伤肝,气逆而血留,或忧思伤脾,气虚而血滞,或积劳积弱,气弱而不行,总因动血之时,余血未净,而一有所逆,则留滞日积,而渐以成癥矣。 ”综上认为,病因多与外邪、劳逸、情志、饮食等有关,从而导致脏腑气血失调、冲任受损,气滞、血瘀、痰湿、毒邪侵袭少腹、胞中,相互搏结,日久积结不解而成。
蔡教授认为,“湿毒”是导致本病的重要原因。湿者指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所产生的内湿,亦可为外湿入侵所致。 毒者,即“毒邪”,是一种致病性毒性物质,此处即指HR-HPV。 湿性重浊黏腻停于下焦,与毒邪共同为患,感染阴器缠绵难祛。 究其病机特点,可概括为“虚、湿、毒、瘀”。人体感受湿毒后,若正气充足则可抗邪外出,HR-HPV 可在短期内被宿主免疫系统清除,几乎不存在恶变风险[6],不会进展为宫颈癌前病变或宫颈癌。 当机体正气亏损且无法及时恢复时,正不胜邪,则出现HR-HPV 持续感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日久气机升降失司,津液代谢失常,致正虚邪聚,瘀血阻滞。 究其致瘀原因可细分为以下几种:(1)气虚血瘀。“气为血之帅”,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血积脉中成瘀。(2)气滞血瘀。毒邪壅阻气机,或久病脾虚肝郁,导致气滞血瘀。 (3)寒凝血瘀。 “血遇寒则凝”,寒湿凝滞血脉,则寒凝血瘀。(4)热毒致瘀。 湿毒化热,煎熬津血,如王清任《医林改错》所说“煎熬成块”,可致血瘀。(5)毒邪伤络。如毒邪直伤络脉,血溢脉外成瘀,即“离经之血,便为瘀血”。 随着疾病进展,机体不断形成新的病理性毒邪——湿毒、热毒、寒毒、瘀毒甚至癌毒等,导致宫颈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的发生。可见“虚、湿、毒、瘀”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疾病恶化进展。 宫颈癌前病变多属本虚标实证,机体自身正气不足为本病发生的内在条件,使湿毒有机可乘,体虚无力驱邪,致瘀久成毒。
2 诊疗特点
《灵枢·逆顺》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治未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 《素问·皮部论》云:“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脏腑也。”说明了外邪的传变途径是由外到内,由皮肤腠理到经脉脏腑的过程。
蔡教授运用此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传变过程。当HR-HPV 持续感染宫颈鳞状上皮,进而发生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此时病变范围仍局限在宫颈上皮内,尚未突破基底膜形成浸润性宫颈癌,正是应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理论来指导治疗的关键时机,在此正邪交争之时,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驱除邪气(消除HR-HPV 感染),可防止疾病恶化,逆转病情。 蔡教授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原则,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机特点,制订恰当有效的个体治疗方案,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是整体虚、局部实的疾病,“正虚”与“邪实”贯穿始终,故以扶正与祛邪并举为治疗总则。补益脾肾以扶正,除湿、化瘀、解毒以祛邪。 在攻补药物的选择上,亦应全面考虑,有时补重于攻,有时攻重于补,蔡教授辨治遣方用药颇具特色。
2.1 补益脾肾以扶正
正气,代表了宿主的免疫系统,体现了机体的抵抗力。 正气“虚”提示着机体免疫力下降,是造成HR-HPV 持续性感染的重要根源。 《素问·痹论》云:“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膛。 ”可见卫气行走之处,正是机体免疫系统的产地和战场。 且卫气具有“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等抗御外邪的作用,可见卫气亦代表着宿主的免疫力。 因此,提高患者免疫力即扶助正气,可以从扶助卫气入手。 卫气生于水谷,源于脾胃,脾虚者则卫气化生无源,故扶正气就要从补脾处着手。蔡教授常用党参、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白扁豆、薏苡仁、砂仁等药补益脾气。现代研究证实,补脾药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14-16]。
蔡教授认为脾旺则气血化源充足,肾气得到滋养才能更加充盛。 肾阳充足,则全身之阳气亦足,脾得其温煦,才能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 正如《傅青主女科·种子·胸满不思食不孕》曰:“人以为脾胃之气虚也,谁知是肾气不足乎……无肾中之水气,则胃中之气不能腾,无肾中之火气,则脾之气不能化。 ”“补肾而不兼补脾之品,则肾之水火二气不能提于至阳之上也。 ”因此,蔡教授在补脾的同时,兼顾补益肾阳。 常用补肾阳的药物有巴戟天、鹿角霜、菟丝子、肉苁蓉、杜仲、桑寄生等。 在温阳药中可酌加滋阴之品,如女贞子、山茱萸、熟地黄等,以期“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
2.2 除湿、化瘀、解毒以祛邪
针对“湿”邪,蔡教授认为无论内、外,虚、实,均应尽早去除。 脾喜燥恶湿,若湿邪困脾,则妨碍正气恢复,故治疗中离不开化湿运脾药,如苍术、厚朴、广藿香、砂仁等;“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湿聚成水时,如出现白带过多、水肿、小便不利、泄泻等水湿病症时,可酌情加用利水渗湿药,如茯苓、生薏苡仁、泽泻;出现湿郁化热之象,如黄带、口干舌红时,可酌情配伍清热解毒药如败酱草、忍冬藤、蒲公英、黄柏、金银花、连翘等。
针对“瘀”邪,既是病理产物,又是疾病后期致毒的病因,是成瘤、成癌的关键。《血证论·男女异同论》云“瘀血不行,则新血断无生理,故凡血证,总以祛瘀为要”,所以治疗时应酌加活血化瘀药,使气血运行通畅,正气随血运到达病灶发挥作用。因瘀血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治疗侧重也有所不同。气虚血瘀者,应用健脾补气来化瘀,常加生黄芪、白术、山药,化瘀的同时,也可适时加用理气药物,如陈皮、香附等,使补而不滞;气滞血瘀,往往采用行气化瘀之品,常用药物有柴胡、川芎、三棱、莪术等;寒邪凝滞者,可通过温补脾肾,以达通利血脉的效果,如肉桂、干姜、吴茱萸等;热毒伤津,血液煎熬成块者,可加用凉血化瘀药,如丹参、牡丹皮、赤芍等;血溢脉外导致血瘀,如出现白带带血、接触性出血等症状,可加生蒲黄、五灵脂、三七、茜草等化瘀止血。
针对“毒”邪,现代研究发现,牛蒡子对宫颈癌Hela 细胞的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蛇床子素抑制人宫颈癌Hela 细胞增殖并促进细胞凋亡[17-18];从苦参中提取出来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具有抗病毒、抗肿瘤、抗炎及抑制免疫等多种药理作用[19-20];体内抗肿瘤研究表明,薏苡仁有明显抑癌效应[21];故以上药物在治疗中均可酌情加用。 又因毒瘀胶结日久可酿生热毒,因而临证时可酌加穿心莲、黄芩、知母、金银花、鱼腥草、桑白皮等清热解毒之品。
2.3 内外合治
在口服药物的同时,蔡教授提倡适时应用阴道上药及外洗中药治疗。
阴道上药方面,蔡教授针对反复出现下生殖道感染的患者,除了给予甲硝唑、氟康唑等药物外,还建议给予益生菌改善阴道微生态环境。蔡教授认为,恢复患者阴道微生态环境,可改善宫颈局部免疫功能,对清除HR-HPV 及逆转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大有裨益。 近年研究显示,阴道微生物群(cervicovaginal microbiome, CVM)的特征与HR-HPV 进展相关,在HR-HPV 自然史中有重要作用[22]。 意大利一项针对患有细菌性阴道病或阴道炎并伴有HPV感染的女性研究[23]显示,117 名女性被随机分为两组,均在标准治疗(甲硝唑或氟康唑口服)的基础上加用益生菌治疗,短期益生菌治疗组为期3 个月,长期益生菌治疗组为期6 个月。结果发现,长期益生菌治疗组获得的宫颈脱落细胞涂片异常清除率和HPV 清除率明显高于短期益生菌治疗组。 证实了对HPV 感染和伴随细菌性阴道病或阴道炎的女性,长期使用阴道乳酸杆菌可能有助于重新建立健康生态,从而清除病毒感染。
刘化勇等[24]通过对102 例患者的研究发现,随着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升级,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上升、宫颈局部免疫功能下降,说明阴道菌群失调(包括HPV 感染),宫颈局部免疫功能低下是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所以,及时调整和恢复阴道微生态环境的平衡及宫颈局部免疫功能对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蔡教授利用外用药直达病所的优点,给予患者中药汤剂熏洗外阴,发挥解毒止痒的功效,药物多由苦参、黄柏、白鲜皮、土茯苓、蛇床子、苍术等组成。 国内多项研究证实,联合中药外治法可降低HPV的病毒载量,促进HPV 的清除[25-27]。
2.4 精神疏导及健康指导
持续感染HR-HPV 的女性容易表现出多种负面情绪,导致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28]。所以临证时要耐心听取患者倾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病情、缓解患者紧张情绪、增加其安全感和信任感,其目的是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也”。 此外,指导患者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配合营养支持和功能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达到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
3 验案举隅
杨某某,女,32 岁,已婚。 初诊:2019 年4 月12日。主诉:患者因HR-HPV 感染2 年,宫颈病变3 个月。 患者2016 年2 月因白带异常于外院就诊,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y test, TCT):中度炎症,HR-HPV(+),予干扰素治疗,半年后复查结果同前。 患者近2 年间白带反复异常,偶伴有外阴瘙痒,自行购药阴道上药,未予重视及正规治疗。 2019年1 月TCT 示: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R-HPV(+)。2019 年1 月阴道镜下宫颈活体组织检查,病理示:宫颈3 点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P16(-)。 刻下症:白带量增多,色淡黄,乏力身重,腰酸痛,纳差,大便质黏,夜眠梦多,易怒,舌淡暗体胖,苔微腻,脉沉细。 既往贫血病史,末次月经:2019 年4 月5 日,8天干净。月经量多,色暗,少量血块,经行小腹坠胀,平素周期规律5/26 d,无痛经。 孕4 产1,人工流产3次。 妇科检查:阴道充血,黄色泡沫样分泌物,宫颈充血,接触性出血。 辅助检查:白带检查提示细菌性阴道病。 中医诊断及辨证:带下病,证属脾肾亏虚,湿毒瘀结;西医诊断: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高危型HPV 感染。 治则:补益脾肾,兼利湿解毒化瘀,具体方药如下:黄芪20 g,生薏苡仁20 g,肉桂6 g,熟地黄15 g,茯苓15 g,炒白术10 g,当归10 g,川芎10 g,山药15 g,生甘草6 g,白扁豆10 g,砂仁6 g,醋香附10 g,黄柏10 g,炒麦芽15 g,车前子10 g(包煎)。 14 剂,每日1 剂,水煎服,1 日2 次;外用甲硝唑栓阴道上药10 d;坐浴中药如下:苦参20 g,黄柏15 g,白鲜皮15 g,土茯苓15 g,蛇床子20 g,苍术15 g。14 剂,每日1 剂,水煎,趁热熏洗外阴,药液温度适中时坐浴、清洗,每日睡前1 次。
二诊:2019 年4 月28 日。 服药14 剂后带下量减少,乏力明显好转,食纳增加,舌淡质嫩,苔薄,脉弦细。守上方加白花蛇舌草15 g,陈皮10 g,守方再服2 个月。
三诊:2019 年8 月21 日。 复查TCT 正常,HRHPV 转阴。 此后半年随访,患者复查宫颈癌筛查:TCT 轻度炎症,HR-HPV 阴性。
按:患者为育龄期女性,一诊时患者已持续感染HR-HPV 病毒2 年余,近期宫颈活检病理提示宫颈3 点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面诊时患者心情抑郁、焦虑,迫切希望得到有效治疗。 因此,鉴于未病先防的治疗原则,并综合考量患者的精神状态,决定给予患者积极治疗方案。 此患者房劳多产、房事不洁,多次人工流产和反复生殖道感染,加之工作奔波、忧思劳倦,最终导致脾肾亏虚,湿毒瘀结。 具体从临床表现来看,脾肾亏虚者可见乏力纳差、腰酸疼痛;脾虚湿困者可见身重,大便质黏,白带量多;脾虚肝郁者可见急躁易怒;脾不统血者可见月经量多;气血亏虚,心神失养者,见夜眠梦多;气虚血瘀者可见经血色暗,兼见血块,腹部坠痛。 HR-HPV 病毒感染生殖道后,因正虚不足以抗邪,导致正虚邪恋,湿毒留滞下焦,出现反复的白带异常,日久化热,出现黄带。患者舌脉亦是佐证。 患者此时病情正处于正邪交争难分胜负之时,治则上应以扶正为主,驱邪为辅,待正气恢复之后再加重驱邪力度。治疗以补益脾肾为主,兼利湿解毒化瘀。方中重用黄芪、白术、白扁豆、山药健脾补气,熟地黄、肉桂补肾温阳,通过补气温阳药物的应用,同时促进血运消除瘀血。茯苓、薏苡仁、车前子淡渗利湿,砂仁芳香化湿,并同炒麦芽一样具有醒脾开胃的作用,川芎、香附疏肝行气,当归补血活血,黄柏清热解毒。 同时,针对细菌性阴道炎及外阴瘙痒,给予阴道上药及中药熏洗对症治疗,内外合治消除病毒。 二诊时正气已渐复,加用白花蛇舌草、陈皮解毒行气之品驱邪外出。 治疗同时注重心理疏导,使患者正确认识该病的严重性,告知生活调护的具体细节,增强其治疗疾病的信心。 最终,不仅达到清除HPV 的目的,也改善了患者其他不适症状,生活质量有较大提升。
4 结语
随着宫颈防癌筛查的普及,将会有越来越多持续性HR-HPV 感染的宫颈癌前病变女性得到关注,及早清除病毒、逆转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对此病本质的认识,是蔡教授制定治则的关键。 本病的发展过程是邪正相争的过程,单纯使用扶正或祛邪之法断不可取,当令二者相辅相成,即使疾病日久错综复杂,也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因此,蔡教授确立了扶正祛邪法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基本原则,把握“虚”“湿”“毒”“瘀”之间的关系,在疾病不同状态,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 在患者正气尚足时,驱邪重于扶正;若正气已亏,邪正交争难分胜负,应以扶正为主,驱邪为辅,待正气恢复后,再行攻伐;及至元气大伤,不耐攻伐,宜固护正气为主。 此外,在治疗中及时指导患者饮食起居及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酌加阴道上药及中药坐浴治疗,以期尽快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蔡教授认为唯有谨守病机,辨证论治,方可妥善处理扶正与祛邪的关系,此亦是中医辨证治疗宫颈癌前病变优势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