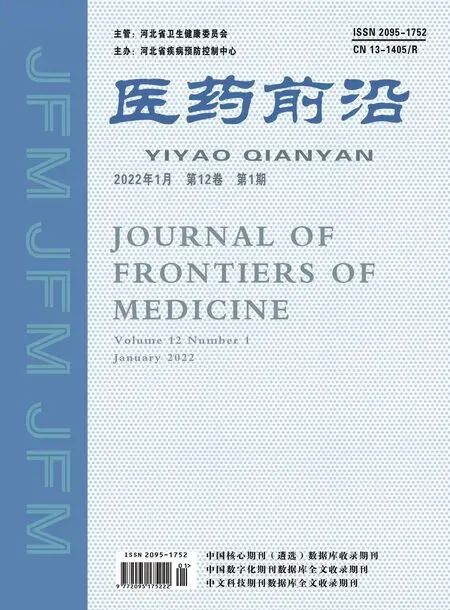“六位一体”静脉血栓栓塞防治模式在神经外科ICU 中的应用效果
刘彩凤,王金明
(1 长江航运总医院重症医学科 湖北 武汉 430010)
(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质控科 广东 佛山 528315)
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与肺血栓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1],是全球性的医疗保健问题[2],有发病隐匿,高发生率、高病死率等特点。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由于本身疾病的特殊性,如存在多种并发症、手术前后脱水治疗、止血抗凝治疗、偏瘫、卧床时间长等危险因素,发生VTE 的概率较大,一旦发生,后果严重[3]。有报道显示,我国外科手术后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可高达50%,而神经外科术后卧床患者血栓发生率是其他类别外科手术发生率的2 ~3 倍[4]。因此,建立和完善神经外科ICU 患者VTE 综合防治管理体系,进行积极预防非常有必要。长江航运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于2021 年1 月起采用“六位一体”的VTE 防治模式,对患者实施规范化的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现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长江航运总医院神经外科2021 年1 月—5 月术后进入本科ICU 的患者为观察组,选取神经外科2020 年1 月—5 月术后进入本科ICU 的患者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患者在入院后均接受神经外科手术治疗;②患者家属同意参与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入院前已患有DVT 或PET、正在使用抗凝药患者、合并手术禁忌证者、经保守非手术治疗患者。观察组52 例,其中男35 例,女17 例,年龄28 ~85 岁,平均年龄(58.94±18.50)岁;疾病类型:急性颅脑外伤24 例,脑出血16 例,脑肿瘤7 例,其他5 例。对照组47 例,其中男29 例,女18 例,年龄31 ~76 岁,平均年龄(58.09±12.50)岁,疾病类型:急性颅脑外伤22 例,脑出血17 例,脑肿瘤5 例,其他3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本院常规护理方法预防VTE,包括下肢抬高、气压泵或弹力袜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
1.2.2 观察组 采用“筛查、预警、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六位一体VTE 防治模式。首先科室内成立VTE 防治管理小组,小组成员由科主任、护士长、医疗及护理骨干组成。管理小组主要职责是制定本科室VTE 防治体系和实施方案,编制VTE 医生/护士工作手册,进行全员VTE 知识培训,督促科室医护人员落实各项防治措施,收集本科室VTE 疑难或死亡病例、关键数据指标、监测指标,定期在科室进行讨论,及时进行反馈并持续改进。
1.2.2.1 筛查阶段 正确的血栓风险评估有利于VTE的早期预防[5]。目前,较为成熟的评估工具主要包括Caprini 量表、Autar 量表、Padua 量表,不同量表应用范围各有侧重[6-7]。本研究由管床护士使用2011 年修订版Caprini 量表[8]对患者进行初步风险评估,评分0 ~1 分为低度风险,评分2 分为中危风险,评分3 ~4 分为高危风险,≥5 分为极高危风险。对于中高风险患者由管床医生确认评估并签名。评估时机包括:患者入院、手术前、手术后、转科、病情变化、出院时。鉴于抗凝预防本身潜在的出血并发症,由管床医生对所有需要预防的住院患者进行出血风险评估。患者入院、转科、手术前、手术后、病情变化、出院时需进行动态评估。
1.2.2.2 预警阶段 筛查出来的中高危患者,在HIS系统医生、护士工作站患者一览表进行黄色标识,床头悬挂“VTE 预防”标识牌,每日早晨交接班时,特别进行交待。
1.2.2.3 预防阶段 由管床医生和护士共同制定预防策略,一般选择个体化预防措施,并根据动态评估结果调整预防策略。出血风险低的中危患者,采取药物预防或物理预防措施,出血风险高的中危患者,采取物理预防措施,出血风险低的高危患者采取药物预防或药物联合物理预防,出血风险高的高危患者采取物理预防。一般药物或机械物理预防至手术后7 ~14 d。管床医生开具预防处方,管床护士落实执行预防措施,并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1.2.2.4 诊断与治疗阶段 该阶段主要由主管医生负责,一旦发现疑似VTE 患者,需请相关科室会诊,进入规范诊治程序。对于疑似DVT,首先借助Well’s 量表进行临床可能性评估,根据风险评估进行相应的实验室和血管超声检查,邀请血管外科进行院内会诊,指导诊断和治疗。对于疑似PTE,首先结合临床可能性评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根据临床情况选择相应的影像学检查手段邀请呼吸内科进行院内会诊,进一步明确诊断;一旦明确诊断,即应该给予相应的治疗,同时寻找其潜在的病因。
1.2.2.5 康复阶段 患者在转入普通病房或出院后,由管床护士负责提取患者基本资料,填写《VTE 病例随访表》,进行电话随访,指导患者及家属进行预防措施干预和药物调整,获取患者的不良事件和终点事件,督促按时来院复查。
1.3 观察指标
包括风险评估和预防类指标、治疗类指标、结局相关指标。其中风险评估和预防类指标包含,VTE 风险初始评估率:指入院24 h 内接受VTE 风险评估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出院患者例数之和的比值;VTE 风险动态评估率:指接受VTE 风险动态评估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出院患者例数之和的比值;出血风险评估率:指接受出血风险评估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VTE 风险评估为中高危患者例数之和的比值;采取VTE 预防措施率:指采取VTE 预防措施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VTE 风险评估为高危和(或)中危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的比值。治疗类指标有住院患者实施抗凝治疗率:指执行VTE 抗凝治疗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出院确诊VTE 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结局相关指标有VTE 发生率:指出院确诊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出院患者例数之和与同期出院患者例数之和的比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各观察指标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VTE 风险初始评估率、VTE 风险动态评估率、出血风险评估率、采取VTE 预防措施率和实施抗凝治疗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者患者VTE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n(%)]
3.讨论
有证据显示,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发生DVT 的风险可以降低50%~60%,发生PE 的风险可以降低近2/3[9],因此建立完善的VTE 防治管理体系,制定规范的防治流程,早期进行中高危患者筛选,及时进行有针对性个体化的干预,能有效降低VTE 的发生率。傅丽琴等人通过在风险评估、分层干预、教育培训、质量监控以及信息化建设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后,护理质量得到明显提升[10]。VTE防治管理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工作,需要领导层、医务管理人员、信息、临床、医技、护理以及患者和家属共同推进[11]。2016 年6 月,中国VTE 院内护理预警联盟提出了VTE 防控需要医生和护士共同协调工作,包括筛查、预防、预警、诊断、治疗和康复六个阶段。护士在筛查、预防、预警和康复中起主导作用。区洁芬等人研究也显示,护士主导的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控管理能够推动院内VTE 防治的科学化、规范化[12]。本研究采用“筛查、预警、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六位一体VTE 防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了神经外科ICU 患者VTE 综合防治管理体系,并从风险评估、预防、诊断、治疗和结局相关等维度对患者VTE 防治成效进行量化评估,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VTE 防治和护理效果成效明显。
相关研究显示,应用脱水药物、高龄、卧床时间长、心肺功能差、血液凝结、糖尿病、肢体瘫痪及静脉置管是静脉血栓发生的独立和高危影响因素[13]。作为护理人员,对于此类患者要运用预见性和前瞻性护理,及时介入并进行筛查,筛查出中高危患者是防治的关键,只有找出中高危患者才能进行精准预警和个体化的预防。对于此类患者要运用前瞻性护理,而筛查出中高危患者是防治的关键。国内有学者调查显示,临床工作中存在护理人员对于患者深静脉血栓缺乏系统有效的评估[14],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六位一体”的VTE 防治模式,不仅明确了管床医生、护士的职责,医护人员还能熟练运用筛查、评估工具去甄别中高危患者,给予患者个体化的预防措施。患者VTE 风险初始评估率、VTE风险动态评估率、出血风险评估率、采取VTE 预防措施率和实施抗凝治疗率均明显得到提高。由于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对静脉血栓形成认知不足,对其重视程度不够,患者转科和出院后对VTE 防治的依从性不高,对患者及家属开展健康教育也非常重要[15]。在康复阶段,护理人员通过使用《VTE 病例随访表》,对转科或出院患者进行定期电话随访,并指导患者继续进行预防措施干预和药物调整,能保证护理的延续性,提高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ICU 患者采用基于“六位一体”的VTE 防治模式,可以改善VTE 防治效果,提升护理质量。但由于本次研究时间短,研究样本小,在以后的研究中将扩大样本量,并增加成本效率相关维度的评估,进一步优化“六位一体”VTE 防治体系,发挥护士在防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降低VTE 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