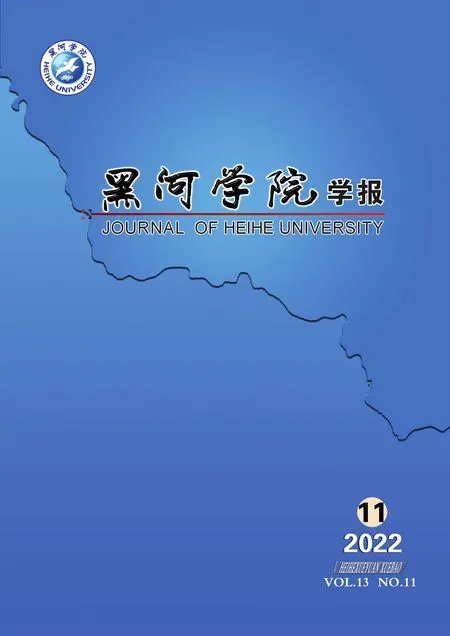认罪认罚案件中法、检权力的博弈与平衡
王大为 韩 瀚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加之新刑诉法对量刑建议采用“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量刑成为了控审双方的博弈重点。2019年的“余金平案”,一、二审法院均拒绝采纳检察院的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力图通过裁判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框架的实践,反映了司法中法、检权力博弈之过程。权力的冲突最终会造成司法资源的重复与浪费,与立法原意相背驰。为缓解冲突,法、检双方应当在新刑诉法框架下,探求量刑的平衡路径,即在“审判中心”“检察主导”相互尊重基础上,构建权力的调和之道。
一、结构性冲突——控审关系新样态
我国的诉讼模式具有职权主义的色彩,强调“犯罪控制”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相应的诉讼程序及证据规则体系。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极具控辩协商色彩的认罪认罚制度,改变了我国传统构造体系中的控审权力配置模式。实践中,控审关系呈现出新样态,检察机关在此类案件中主导责任更加凸显。
首先,在“认罪”方面,检察机关需就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态度及所采取的行动来判断其是否构成制度意义上的认罪;其次,在“认罚”方面,犯罪嫌疑人需接受精准量刑建议中对其指控的罪名、适用的刑罚种类、刑期及刑罚执行方式后方可被认定为制度意义上的认罚。最后,在量刑方面,新刑诉法对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的立法表述使得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诉机关的求刑权对审判机关的量刑权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主导责任延伸至审判阶段。
对于新型控审结构,法院在认罪认罚制度入法之初并不能较好适应,且在部分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就量刑问题产生较大争议。法、检权力的阶段性冲突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由“规范”到“实践”改革方法的必经之路。在认罪认罚制度改革过程中,立法机关先行制定法律规范,而后司法机关加以执行,这种“规范——实践”的司法改革模式与域外认罪协商模式的形成完全相反,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督促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做法,在相关配套制度与程序有待完善时,必然会引发控审矛盾[1]。
二、观念的博弈—法检权力冲突分析
“认罪认罚”制度的引入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控审关系,引发法、检量刑权与求刑权的冲突。控、审双方有关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背后的原因是多维的,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一)量刑建议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之争
传统理论认为,量刑建议权系公诉权的下位权能,与实体审判结果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无涉,诉讼中仅具“请求职能”,属于程序性权利[2]。但这一观念受到了新刑诉法中对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冲击。
在检察机关看来,新刑诉法的“一般应当”规定使得量刑建议具有左右案件审判的效力,量刑建议权不再是单纯的程序性职权,而是检察机关践行司法公信、有效制约法院量刑权且具有实质约束效力的实体性权力。认罪认罚制度的关键在于从宽,刑事被追诉人基于从宽的预期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这种预期集中体现于量刑建议之中,从“检察主导”视角出发,量刑建议应被采纳是践行司法公信,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应有之义。
在审判机关看来,新法中“一般应当”的规定是对控辩双方“合意”的尊重,人民法院不应“照单全收”,量刑建议权仍属程序性职权[3]。此司法观点具备一定的理论支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仍属于量刑活动的范畴,量刑建议的采纳规则不能与量刑的有效性规则相违背。依据刑事实体法罪刑相适应原则及刑事诉讼法236条的规定,量刑应适当,即量刑适当是量刑有效性的实体性标准和底线规则。基于上述论述和《指导意见》第49条“量刑建议的适当性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的规定可知,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可采性”的前提是具有“适当性”,且人民法院对“适当性”拥有完全决定权。而新刑诉法中的“一般应当采纳”规则应当作为促进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效率性规则,对法院不具备约束力,量刑建议权仍属于程序性职权。
控审双方对量刑建议权性质定位的不同是引起控审双方权力博弈的原因之一。
(二)法条释义——不同司法环境下的分歧
对于法条“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解读,法、检看法不尽相同,而笔者认为,法条的释义可以回归于立法初期的司法实践。立法者修改刑事程序法之时,法、检系统对量刑建议的适用已达成合意,即“以幅度刑量刑建议为主,确定刑量刑建议为辅”,而法条的“一般应当”用语应当依附于此种司法环境。而《指导意见》33条的固定使得司法实践发生变化,在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精准刑量刑建议的情境下,仍结合量刑建议的采纳规则稍有不妥。不同司法环境下条款的结合使用强化了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作用及强度,使法院陷入以采纳量刑建议为原则,不采纳量刑建议为例外的困局,法官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有被“不当僭越”之嫌。但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现行立法是司法实践最重要的依据,因此,立法中“一般应当”的具有约束力的表述是引起控审双方权力博弈的原因之二。
(三)诉讼理念——“检察主导”抑或“审判中心”
审判中心论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刑事诉讼法则,其是指在诉讼中庭审应居于核心地位,该法则的核心要求在于形成裁判结果的依据来源于法庭。“检察主导”的理念是检察系统基于司法实践提出的刑事诉讼法则,其初始思路为“审前主导地位”,无论是制度启动、程序适用还是审前分流,检察机关均可以发挥较大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审判系统看来,检察机关基于逮捕和公诉阶段的案件信息而形成的量刑建议尤其是精准量刑建议,对案件具备“潜在”的实体性约束力,与“审判为中心”理念是相违背的。但在检察机关看来,“检察主导”并不天然的侵犯“审判中心”,更不代表量刑建议权入侵量刑权,检察院提出精准化量刑建议后,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但也存在法定情形下法院有权拒绝采纳并依法判决,此拒绝采纳仍是源自法官在庭审中形成的心证,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仍贯彻“审判为中心”的理念。法、检双方诉讼理念的差异是引起控辩双方权力博弈的原因之三。
三、法、检权力的平衡之道
认罪认罚制度具有浓厚的控辩协商色彩,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缓解诉累,提高诉讼效率,在优化司法资源的同时减少社会对抗。但刑诉法中“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却改变了控审双方的司法权力配置,从而引起双方的司法量刑冲突。法检系统的零和博弈在恶化双方福利的同时有违立法原意,基于合作才是最优解,量刑建议权和量刑权应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形成动态平衡,两者相互制约,以推进认罪认罚制度的良好实施[4]。
(一)“检察主导”下检察行为的规范
1.检察机关的合理抗诉疏导
抗诉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的法定权力,权力设定的目的在于监督法院裁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该权力似乎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最高检在其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第三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而直接作出判决的,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依法提出抗诉。”该条款的合理性值得商榷。诚然法院未优先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而径行改判的行为属于程序违法,有违程序公正的要求,但不可否认诉讼效率在认罪认罚制度中亦举足轻重,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衡量。以河南省郑州市某盗窃案为例,一审人民法院未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而对刑事被告人宣告缓刑,并代为退赃退赔,检察机关认为上述行为程序违法并可能影响审判公正,依法向郑州市中院提起抗诉,建议发回重审。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未经向公诉机关提出建议而直接宣告缓刑,程序上确有不当之处,但其量刑结果、缓刑适用与刑事被告人的罪责、认罪情节相适应,亦未造成“影响公正审判”的后果,故驳回抗诉,维持原判。①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刑终724号裁定书。案例中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与二审法院裁判的依据均立足于行为本身是否有“影响审判公正”之嫌。
对此笔者认同二审法院的裁定。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框架下,基于效率的考量,检察机关应当尊重法院的量刑权,并对法院不采纳精准量刑建议而合理改判的轻微程序瑕疵负有一定容忍义务,不得因此轻易抗诉。
2.检察机关精准量刑能力的提升
精准量刑建议应当包含确定的刑种,精确的刑期及具体的执行方式。在更加凸显检察机关主导责任的认罪认罚案件中,鉴于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法院采纳率同步提高的实践要求,提出内容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挑战性。在传统控审模式中,准确量刑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能范围,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为主的司法实践对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能力要求并不高,但这种能力短板在《指导意见》及新刑诉法的规定下渐露端倪,法、检双方量刑能力的差距会体现在精准量刑建议的采纳中,而量刑建议中的确定刑罚与法官基于心证而形成的内心确信不同是法、检权力于司法中博弈的逻辑起点,因而有必要从检察机关自身出发,提高精准量刑能力。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可以尝试逐步推广智能化量刑辅助系统的适用。在信息化时代,各地司法机关开始摸索开发智能化司法辅助系统,如上海市的“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重庆法院的“智慧E审”辅助系统及全国检察系统通用的“智慧检务”系统等,智能辅助系统已在司法中取得一定成效。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辅助平台提取类案的量刑要素,分析法院量刑尺度,为本案提供帮助,使得精准量刑建议的提出兼具效率性和可采性。以笔者调研的A省F市①F市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不属于认罪认罚试点区域。检察机关为例,2021年,全市提起公诉的认罪认罚案件共439件559人,在智能司法辅助系统的帮助下,精准刑量刑建议适用率达到100%,法院采纳率为98.50%,效果显著。
(二)“审判中心”下量刑权运用的完善
1.新型诉讼结构下法院量刑权限的定位
我国认罪认罚制度具备职权性与协商性的色彩,其职权性是指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程序的启动、量刑建议的形成等方面具有主导作用,且程序开展非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而进行,刑事被追诉人仅为有限度的参与;而协商性是指控辩双方达成合意的刑期应当精准,合意对于各方诉讼主体具有外在形式上的约束力[5]。认罪认罚制度的协商性是审判机关诉讼定位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但因协商性本身具有践行司法诚信、提高诉讼效率等诸多重要现实意义,人民法院对此应理性接受。
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尊重检察机关的诉讼裁量权,接受其制约,在庭审中着重审查制度适用的自愿性、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及证据的合法性,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不应“赌气式”拒绝采纳量刑建议。同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判机关在尊重检察机关诉讼裁量权的同时,应当保持自身理性。审判机关不应当充当消极的“确认机关”“盖章机关”的角色,庭审仍应采取实质化的审查,尤其是对制度适用之自愿性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审查。另一方面,对于不合理的量刑建议应先行建议检察机关调整,调整无果,依法改判,实现最终意义上的实体公正。
2.更加精准量刑指南的制定与贯彻
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行)》,确定了由“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量刑步骤及影响量刑情节的刑期加减刑幅度,并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要按照规范、实用、符合司法实际的原则要求,共同研究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以确保量刑指导意见正确实施。该意见有效促进了法、检系统在量刑问题上达成共识,但部分规定仍过于宽泛,因而基层、中级司法系统可以在各地实施细则规定的框架下,结合本地司法实践,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实务要求、更为精准的量刑指南以缓解权力博弈。
量刑的不同是法、检权力博弈的逻辑起点。而精准量刑指南作为法、检量刑共识的产物能够平衡因量刑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控审双方在两高指导意见及各省高级法院实施细则的框架下,对实务中常见的犯罪类型、量刑情节,结合司法经验予以更精准化的明确。其精准化程度越高,量刑建议适当性的争议余地就越少,双方权力博弈的空间也就越小。
四、结语
精准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全面适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案件的控审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法检定位的转变引发了实践中的权力博弈。但公正应当始终贯穿于诉讼制度的改革中,在现有制度下,“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应相互尊重,法、检权力亦在调和下才能实现共赢。当然,对法、检权力的调和路径及如何应用于司法实践并发挥效用的问题,仍值得继续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