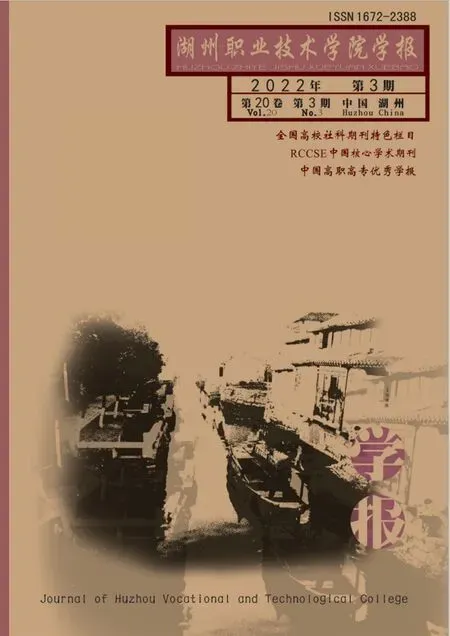薇拉·凯瑟《一个迷途的女人》空间叙事分析
徐 明 丽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与商务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6))
《一个迷途的女人》是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于1923年发表的一部小说。她此前的作品《我的安东妮亚》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而《我们中的一员》在助她荣膺普利策文学奖的同时,也给她招来了多种批评声音。《一个迷途的女人》发表后,批评家们颇感欣慰,认为凯瑟终于将写作中心又转回到自己擅长的题材上来了,并认为这是一部“没有瑕疵的杰作”[1]。凯瑟对于拓荒题材早已驾轻就熟。但是,与以往的拓荒颂歌不同,《一个迷途的女人》被认为是美国拓荒时代的最后一首挽歌。
《一个迷途的女人》通过美国西部小镇青年尼尔的视角,讲述了西部拓荒者福瑞斯特上尉破产没落后,他的年轻美丽的太太玛丽恩·福瑞斯特背离了拓荒人的为人处世原则,认同了坐享西部开发成果的新兴资产阶级(如艾维·彼得斯之流)的价值观,走上了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迷途的故事。小说篇幅相对简短,结构严谨。第一部有九个章节,故事时间延续了九年,叙述主人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上尉在丹佛破产回到甜水镇告一段落;第二部也有九个章节,同样由代表性事件组成,以玛丽恩每况愈下的生活为主线,完成了小说叙事和对故事人物的刻画。
薇拉·凯瑟曾说,世界在1922年的时候一分为二了。她本人多次声明,无意对福瑞斯特太太进行道德上的谴责。福瑞斯特太太的原型是红云镇创始人,内布拉斯加州前州长塞拉斯·加伯的妻子。她的优雅和活泼给少女凯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凯瑟对加伯一家怀有温暖美好的回忆,她力图恰如其分地将真实的“福瑞斯特太太”刻画并展示出来。这种刻画本身就是对一个时代的描摹。她创作《一个迷途的女人》时,像福瑞斯特上尉这样的拓荒者们已垂垂老矣,主宰社会的是艾维·彼得斯之流的新兴资产阶级。整个社会将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物质主义、金钱主义甚嚣尘上,虚荣攀比之风大行其道,拓荒精神日渐衰微,拓荒者的光辉几近消失。《一个迷途的女人》代表着凯瑟的创作主题由“精神力量胜过物质力量与自然力量”转为“物质力量、金钱力量可以战胜任何崇高理想和伟大精神”。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这部小说“标志着以天真、优雅、充满希望为核心的美国梦的失败”[2]2。
本文拟从空间理论的视角,解析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象空间。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身份来探析其人格特征,通过解析人物摆脱困境的努力与尝试,来探究时代更迭中人物的选择,通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来阐释意象空间对叙事的有效拓展。
一、地理空间:构建角色身份
贯穿凯瑟小说的地理空间——西部大草原的小镇和乡村,大多是作为人物“感觉—体验”的地理背景出现在主人公的回忆中。凯瑟本人有着丰富的空间经验:儿童时期移居红云镇,青年时期在林肯市上大学,毕业后到匹兹堡工作,最后移居纽约,其中,童年时期在红云镇的经历对她影响至深。《一个迷途的女人》以甜水镇作为背景空间,因为这里既是凯瑟熟悉的西部小镇,又能最直观地反映拓荒时代的历史变迁。凯瑟未对甜水镇做整体性的描述,只用了一句颇为传神的描写一带而过:“三四十年前,勃林顿铁路沿线有不少灰暗的小镇,这些镇现在是越发灰暗了。”[3]265
这一句用的是传统的全知叙述,力图客观地概括甜水镇的全貌。甜水镇作为一个空间,规模不大,但鞋店、裁缝铺、杂货铺等应有尽有,旅馆、租车行、法律事务所等也一应俱全。小镇的基调是“灰暗”,它的发展得益于铁路的新兴。后来,随着铁路行业的不景气,再加上农业的连年歉收,人们纷纷离开。因此,失去活力的小镇显得更加“灰暗”。这也寓意着整个拓荒时代由盛转衰。但是,在福瑞斯特上尉眼里,小镇所在的草原地区却是风光无限:“天天都是好天气,可以打猎,有许多羚羊和野牛,天空一望无际,阳光普照,草原也无边无垠,青草随风荡漾,长长的大湖,水流清澈,开遍了黄色的花朵,野牛换季迁移的时候到这里来喝水、洗澡,在水里翻滚。”[3]284
福瑞斯特上尉是拓荒者中的佼佼者。他身材高大,做事果敢,从部队退役后,做过长途货车司机、铁路承包商以及银行家,从看到甜水镇的第一眼起,便对它念念不忘。正如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所说:“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评价依据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4]94在上尉看来,乡野不是不毛之地,而是处处彰显着美与活力。“他恰恰喜欢小河这样曲曲弯弯地流过草地,两岸还有薄荷、节连节的草和闪闪发亮的柳树。”[3]267他拒绝抽干沼泽地里的水改种庄稼,严禁在林子里打鸟打猎。对于大草原,对于甜水镇,对于被称为“福瑞斯特之家”的土地及其周边地区,他发自内心地热爱。他对工作伙伴真诚相待,宁愿自己破产也要维护银行储户的利益。他是老一辈拓荒者的杰出代表,是凯瑟讴歌和赞美的对象。
作为拓荒者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小镇青年尼尔一直寻求拓荒时代的火热与美好。他本应该看到丰饶的大草原和宜居的甜水镇,然而,现实是:在他眼中,冬日寒冷萧瑟的图景是甜水镇的常态。
“马儿不用指示方向,沿行人不多的寒冷的大街驶去,跨过冰冻的小河,跑上两边栽着杨树的小道,奔向山上的别墅。晚霞映照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杨树又高又直,在冬日萧条的景色下显得冷清而又肃穆……”[3]277
“雪下了三天三夜,三十英寸厚,刺骨的寒风又把雪卷积成大雪堆……路上的积雪齐他的腰,有时候没到他的腋窝。路边的篱笆都被雪盖住了。”[3]292
“阴沉的天色黑了下来……大风夹着雪花吹过山与镇之间宽阔的草地,房子周围高大的杨树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3]321
小说此时从尼尔的视角进行描述。作为故事中的人物,他不像第三人称叙述者那样客观,而是倾向于从自身感受出发,对自己所观察的对象寄予同情或表现出其他情感[5]217。这个西部小镇对于尼尔来说,粗粝单调,缺乏温度。在晚间,尼尔出门拜访福瑞斯特上尉一家,感受到的是冰冻的道路,死寂的街道。尼尔对“福瑞斯特之家”无比依恋。这种依恋并非出于要“守护”优雅、迷人的玛丽恩,而是出于对上尉等老一辈拓荒者的敬佩。他试图亲近仅存余辉的拓荒时代。他认为,玛丽恩应该无条件地对上尉忠心耿耿。因此,当他发现玛丽恩违背了这一设定时,他对玛丽恩的“着迷”立刻转化成了鄙视和厌恶。因为彼得斯对上尉缺乏起码的尊敬,他愈加厌恶彼得斯。他赶走闯入上尉家聒噪的小镇妇女,维护了上尉的尊严。他休学一年贴身照顾上尉,让上尉得以在平和安静中离开人世。福瑞斯特上尉与尼尔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上尉高洁的人品吸引了尼尔。尼尔对上尉的临终护理是惋惜整个拓荒时代的隐喻。上尉的去世,预示着整个拓荒时代的终结——“这里的人们,这乡间本身……将来是没有什么值得他回来看望的。”[3]330没有拓荒光环笼罩的甜水镇,更加“灰暗”了。
二、社会空间:摆脱人生困境
甜水镇是一个代表美国历史又反映典型美国文化的社会空间,固执地蕴藏着传统的价值观。它的社会维度是它的等级观念:“在这些大草原的州里有两种显著的社会阶层:一种是分得土地迁居来的和干手工活的,他们到这里来为的是谋生;另一种是银行家和办大农场的绅士,他们从大西洋岸边来,为的是投资,或者用他们常用的话说,为的是‘开发我们伟大的西部’。”[3]266
简言之,甜水镇居民分为两类人:一是有产阶级,一是普通劳动者。这两类人群之间有着鲜明的界限,无论是小镇居民,还是外来访客,对此都熟谙于心并遵照执行。如拜访“福瑞斯特之家”的人,都是银行家、铁路负责人、医生、法官等,其他小镇居民虽然对福家好奇万分,但从不涉足,就连十来岁的孩子们,也知道福瑞斯特太太属于社会上“幸运的特权阶级”。恪守阶层划分已成为甜水镇人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他们以此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孩子们怂恿尼尔向福瑞斯特太太恳求,要她允许他们进入沼泽地野餐,只因为尼尔的舅舅是法官。尼尔从树上摔下来后被送入福瑞斯特太太的卧室,其他孩子也只是谦卑地待在厨房外面等候。在小镇空间里,福瑞斯特之家是独特的私人领地,代表着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
这种局面在上尉第二次中风的时候被打破。此时,上尉经济拮据,甚至开始入不敷出。在甜水这样的小镇,人们按部就班地生活,总体上人们的生活是单调平淡的。凯瑟曾在《小镇生活》里谈到,西部小镇人民生活的贫乏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上帝、铁路或天气与他们作对[6]85。为了在单调的生活里寻找一些乐趣,人们热衷于说别人家的闲话,乐此不疲地将各种消息散播出去。上尉第二次中风以后,镇上的主妇们以照看上尉为名,公然出入福家,翻遍屋子的每一个角落,蓦然发现福家既不神秘也不高贵,到处都是过时的家具和老朽的陈设,并公然诟病玛丽恩酗酒无用,不守妇德。至于上尉能否尽快恢复健康,以及玛丽恩如何重整旗鼓,她们并不关心。在热情助人的表面现象之下,小镇居民实则自私又冷漠。“为什么那些使得生活一帆风顺、多少能弥补其中的更大失望的起码礼节,在小镇里就那么难做到,比石头里挤出血还难?”[6]87这样的社会空间令人愤懑、窒息,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凯瑟还是少年尼尔,最终都选择了逃离。
小镇妇女让玛丽恩原本私密的私人空间暴露在公众眼光之下。以前的老朋友们认为她“误入歧途”“背信弃义”。玛丽恩从人人仰视的迷人贵妇变成被人鄙视的风流寡妇。人们对于玛丽恩的情人艾林格却宽容很多。玛丽恩与艾林格保持通信联系,时而秘密幽会,但艾林格最后娶了“可以做他女儿”的康斯坦斯,彻底抛弃了玛丽恩。玛丽恩被斥责为荡妇,但人们却只记得艾林格是个孝子,认为他是“大好人”,即使他年轻时放浪不羁,“在光天化日之下带妓女骑马”。可见,无论是相对闭塞狭小的甜水镇还是丹佛等大城市,人们对男性宽容、女性苛刻已经成为社会风气。上尉破产后,出身富裕之家、一直以来备受爱护的玛丽恩不再享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并没有指责上尉,在接受现实的同时,不忘告诫尼尔:“尼尔,你得抓紧,做一番事业……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开始就得看准这一点,要好好对付这个问题,不要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弄到最后出洋相。”[3]308
玛丽恩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要生存下去就要顺应社会变革,这样才能摆脱人生困境。她将这一人生感悟传授给尼尔,希望尼尔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玛丽恩清楚地知道,正视现实才能走出困境。面对流言蜚语,玛丽恩不屑一顾,我行我素。她把草地租给彼得斯。尼尔曾问玛丽恩是否怀念沼泽地,玛丽恩回答道:“不太怀念。我永远没有工夫到那里去了,再说,我们也需要这笔租金。”[3]308为了增加收入,她把上尉的业务都转移给彼得斯,她因此遭到“老朋友们”的批评。上尉去世后,她和彼得斯继续来往,并把钱财交给他打理。即便这样,玛丽恩的状况仍很糟糕。直到她将房产卖给彼得斯,离开甜水镇,再婚嫁给一个富有的英国人,才走出人生困境,并且一直到死都受到很好的照料。凭借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玛丽恩重回有产阶级,重新成为“幸运的特权阶级”。
在尼尔看来,艾维·彼得斯是“下人”,是龌龊下流的代名词,不配和玛丽恩平起平坐,更不用说与上尉相提并论。实际上,彼得斯处于甜水镇的“谋生”阶层,但他的理想和行为都是爬向甜水镇等级结构的上层。他甫一出场便声明,自己的“地位”和玛丽恩“一样高”。这一言论让恪守阶层划分的在场听众觉得“荒唐可笑”。彼得斯想从处于“谋生”阶层的普通劳动者跃升为有产阶层、“投资”阶层的理想,是他各种行为的动力。而他抬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是践踏曾经的有产阶级如上尉等人的骄傲和尊严。如,他租下草地后马上将上尉喜欢的沼泽地改为农田,废除打猎禁令,从波梅洛埃法官手里抢业务等等。艾维·彼得斯代表了一类人:他们没有拓荒情怀,只热衷于敛财,无视自然生态、社会规则甚至法律法规,坐享老一辈拓荒者的财富积累,最终,实现了阶级跨越,一跃成为主宰操控社会的新兴资产阶级。
三、意象空间:拓展叙事意蕴
凯瑟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描写了丰富多彩的意象,如树林中的啄木鸟,玫瑰花园中的日晷和上尉家的客厅,这些意象反复出现,隐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同时,这些意象有专属于自己的空间,勾画出与描绘一样的视觉效果,并突破意象本身单一、孤立的形象,营造出与周围空间或和谐统一、或冲突对抗的意象空间。
故事开篇,尼尔和镇上的几个孩子正在小树林里玩耍和野餐。小树林在上尉家房子的后面,是坐火车进入甜水镇的人第一眼能看到的风景。树林里野花盛开,蜂飞蝶舞,啄木鸟、野鸭子随处可见。孩子们吃着福瑞斯特太太送来的甜饼,非常快乐,直到被孩子们称为“毒”艾维的艾维·彼得斯出现。艾维·彼得斯用铁弹弓打下一只啄木鸟,并残忍地用小刀把啄木鸟的眼睛挖了出来。然后,任由小鸟在林子里左右乱撞,在阳光下打转,慌乱而又绝望。这让原本清凉静谧的树林变成了危险与邪恶的所在。在这里,失去方向感的小鸟象征着玛丽恩。玛丽恩漂亮、迷人,善于交际,极富魅力。她在福瑞斯特上尉破产后不知所措,“误入歧途”。恰如被剜去双眼的啄木鸟最终躲进了自己的洞里一样,玛丽恩没有被动地任凭命运摆布,没有放弃对生命的尊重与渴望。她还举办了一次宴会,希望为镇上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文明的去处”,并教会他们做文明人。虽然宴会惨淡收场,但身处逆境的玛丽恩却展示了她不屈不挠,在现状中挣扎,对时代反抗,不会轻易被生活打败的一面。从“迷人”到“迷途”再重回“迷人”,玛丽恩完成了自我蜕变。日晷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出现在被福瑞斯特上尉称为“玫瑰花园”的地方。玫瑰花园属于上尉的私人空间,他有时可以连续几小时坐在那里看日晷 。对于上尉来说,日晷记录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时代的渐渐消亡。福瑞斯特上尉是探险家,也是征服者,有着属于拓荒者的骄傲与自豪——每个拓荒者的血液里都流淌着自豪感。“在美国大平原边缘地带的农场上,农民必须坚持不懈地与干旱和沙尘暴抗争。那些无法坚持下来的人纷纷离开了,而留下来的人们则在心中产生了一份源于坚守的自豪感。”[4]144这种自豪感是彼得斯之流无法体会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恰恰又是彼得斯这类唯利是图、精明小气的年轻一代摧毁撕碎了上尉这样的老一辈拓荒者们的骄傲和尊严。福瑞斯特上尉参与了拓荒者的全盛时期,同样也不幸见证了拓荒时代的黯然落幕。上尉代表了拓荒者们牢固不变的价值观。然而,在时代变革和经济变革面前,他变得无奈又无助。可以说,终日坐在花园里看日晷的福瑞斯特上尉,已经先于拓荒时代老去了[7]51-62。福瑞斯特上尉去世后,玛丽恩提出将日晷呈放在上尉墓前作为墓碑,日晷因此被赋予了纪念性的意义——纪念所有曾经火热战斗过的拓荒者们,以及渐行渐远的拓荒时代。
综上,薇拉·凯瑟从来没有因为远离故土而在情感上背弃家乡,从而使其作品失去根基和给养。相反,她的拓荒主题从来没有离开过西部,离开过让她魂牵梦萦的大草原。她的作品是想象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完美融合。在拓荒时代行将结束、拓荒精神日渐衰微之时,凯瑟正视这一历史趋势,冲破狭隘的传统价值观的束缚,拒绝悲观地吟唱时代挽歌。她力图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弘扬拓荒精神,勉励人们将对拓荒时代的缅怀转化为适应社会变革的动力,在时代更迭中走向新的人生。
———金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