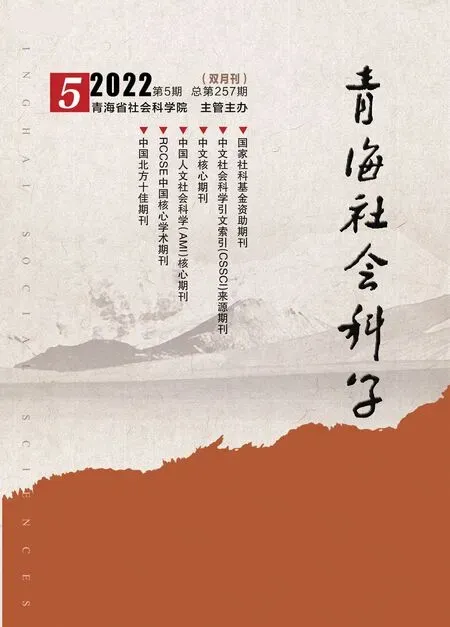从微博到微信:社交网络可供性对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
◇吴新奇
基于苏格拉底的观点,道德并非是天生的,也不是单纯的认知习得的,而是由个体持续且反复地参与特定活动逐渐积淀形成的。因此,考察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应该更多地聚焦其促成美德形成的行为。个体行为总是跟特定的情境密切相关。而技术是构成情境的一个核心要素。当前,以微博与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业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组成部分。社交网络对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的关键并非其功能,亦非其带来的使用体验,而是其可供性(affordance),即社交网络应用提供的行为可能性。
近几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伴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演进,大学生用户逐渐从微博迁徙向微信,且趋势日加显著。微博与微信,因为其可供性的差异,大学生用户在其中的迁徙意味着某些线上行为受到促进,而另有一些线上行为则受到阻抑,这必然会改变他们的道德发展的图景。当然,这并非即时或短期的效果,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本文基于“可供性”的视角来探讨大学生从微博转向微信的变迁中,其道德发展可能受到的微妙但深远的影响。
一、可供性
Gibson提出的可供性概念近年来成为探索人机互动的一个重要视角。可供性的理论发端于格式塔心理学的效价(valence)概念,强调事物潜在地提示且邀请着人们该用它们来做些什么,如同苹果在宣告着“来吃我”,而水在宣告着“来喝我”一般。Gibson称之为环境或物件的可供性,即:环境或物件提供或配给于有感知能力的人或动物的价值与意义,或是有利的,或是有害的。在其经典的《视觉的生态取向》中Gibson[1]强调,人的知觉不只是被动的过程,而是通过他与环境的互动去获得环境之于他的可供性的意义。比如,对于有寄信需求的人而言,看到邮筒时感知到的是其“邀请人来投信”的可供性。正是因为可供性,人类(以及动物)才能适应、应用、探索并试着去调整和改变周遭的环境。在社交网络环境下,可供性意味着用户基于其理解以特定方式参与该环境的行为可能性。
基于可供性的视角,技术与人或社会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理解技术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个体与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台湾学者曹家荣[2]指出:
技术并不只是被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实际上几乎所有我们的生活体验,都是在与技术的关系中产生的。我们的生活世界,正是由我们与技术物共同构作而成……这些技术物既提供亦限制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与它说明技术物本身的价值取向,亦同时揭示了淀积于我们心中的价值图式。
就社交网络与用户的关系而言,可供性理论强调追问社交网络如何促成用户的行动,亦即优先考虑社交网络的工具特征与其可被使用之间的关系,因为工具特征是影响特定行动的关键要素。“物件被觉知的以及实际的特征,决定物件能被如何使用”[3]。可供性意味着促进了特定行为发生的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行为机会的限制。比如,Boyd[4]认为社交网络的可供性让用户有更多的机会与他者建立链接并且维系链接,因而相对于受到物理限制的现实世界,用户在社交网络里可以建立和维系更庞大更复杂的“朋友”群,而与此同时,基于社交网络的交往让深沉的情感纽带逐渐淡化。
社交网络应用有着迥异于传统媒介的可供性,它们不再让用户被动地对着相对比较静态的网页,而是允许用户之间、用户与线上内容之间实现良好的互动。有研究指出,社交网络的核心可供性在于:链接/社会关系、协作性信息挖掘和分享、内容创作、知识和信息聚集和内容调整[5]。微博和微信,作为中国大学生当前两款主流的社交网络应用,也有着特定的可供性,以促成或阻抑相应的行为。从大学生逐渐从微博向微信迁徙的趋势来看,他们业已对微信的行为可供性具备了较好的觉知和运用。本文试图基于可供性的视角,比照分析微博与微信提供给大学生的线上行为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大学生从微博迁徙进入微信,其道德发展的图景可能受到的影响。
二、微博与微信的“可供性”差异
在本文中,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清晰比较微博和微信之于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可供性,笔者忽略两款应用中包含的游戏、会话、收藏、线上支付等情境,而聚焦于与“发布”(微博与微信的核心功能)相关的特征,包括朋友列表、发布、转发、评论、@昵称和点“赞”等。
朋友列表是用户的社会关系图谱,它允许用户管理和控制其关系结构与信息传播。在用户发布动态时,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列表有着巨大的可供性差异。微博的朋友列表让其动态发布可以“公开”“好友可见”以及“仅自己可见”,而微信的朋友列表则让其动态发布能够“公开”“私密”“部分可见”(选中的朋友可见)以及“不给谁看”(选中的朋友不可见)。微博的朋友列表的可供性指向于信息的公开与分享。微信的朋友列表则具有非常强大的目标对象的分类管理功能,允许用户让其动态仅仅被特定类别的朋友看到。总体而言,微博的“朋友列表”促进了用户的动态发布是相对公开而且透明的。而微信的“朋友列表”则鼓励了用户基于特定圈子来分享信息,表现为强关系条件下的封闭性与私密性。
微博“发布”强调“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字”“相册”(图片)和“拍摄”。而微信朋友圈的“发布”有两个选项“照片”和“小视频”,倘若用户需要发布纯文字信息,则需要长按“发布”按钮。这意味着微信的“发布”更有利于图片和视频信息。因此,从“发布”(以及与先前所述的“好友列表”相结合)的可供性来看,尽管微博和微信都指向于文字与图片/视频的分享,但用户更容易觉察到在微博中是文字优先的,在微信中则是图片/视频优先的。“文字”意义在于说明或描述某个事件、经历、想法或观念,蕴含其中的核心可供性是“告诉”。而图片相对于文字而言更适合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6],蕴含其中的核心可供性不是“告诉”,而是“展示”。
微博具有转发功能,微信则没有,这导致了两者之于人际互动以及自我表达上的可供性的明显差异。微博的转发功能让信息传播的指向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微博的转发可以附加评论,这些功能的组合让信息的传播在快速扩散的同时,也允许更多的对话与互动。微博因此超越了单纯的社交属性,而带上较为明显的媒体属性——强调消息的传播与扩散。微信朋友圈并没有设置“转发”功能。用户之间无需因为转发的存在而特别去关注某个强影响力的节点,从而让用户彼此之间表现出平等的关系。这符合微信以社交为核心的定位,换句话说,没有转发功能促进了微信基于关系建构人际网络。此外,没有设置转发的另一个重要的可供性是对私隐的保护。
“@昵称”在微博与微信都有提醒的意思,意指“向某某人说”,但两者对用户的线上行动具有显著不同的可供性。在微博,用户发布动态或对他者动态进行评论或转发时,可以通过“@昵称”将相应的用户“邀请”进来卷入某个共同的议题。“@昵称”在微博里的可供性指向于人群的聚拢或“围观”。在微信朋友圈中,“@昵称”的可供性则简单许多,用户在发布动态时通过“@昵称”提醒特定对象的留意并作出回应。微信朋友圈的“@昵称”强调的是发动彼此的互动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微信的“评论”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叠加性,即用户对原动态作出评论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群组内其他人的评论的一次叠加性的评论。与之相对,微博的“评论”则是针对动态或其他评论的一次单向的行动,更多的是表达看法或者提供信息。微博的评论是公开的,可见于他者,但不具有叠加性,因此对于引发用户之间的多向互动而言显然不及微信里的叠加性设计。微博的“评论”可以附带“@昵称”功能,用户在评论的同时可以邀请更多的用户参与进来,关注或参与某个特定的话题。
在微博和微信中,点“赞”有着类似的可供性,它强化和引发更多的人际互动。Turkle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社交网络里更希望以类似“小啜一口”的方式来进行交往[7],而点“赞”正是实现这种交往的最佳途径之一。微信的点“赞”被设置为所谓的“叠加赞”——用户对某个动态点“赞”的同时也实现对同个群组内的其他业已作出回应的用户叠加地点“赞”。因此,这种叠加“赞”让群组内的用户实现了持续的自我强化。
基于以上分析,微博与微信在六个方面的可供性的差异比照如表1所示。

表1 微博与微信的可供性比照
三、从微博到微信: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危与机
(一) 微博与微信的空间属性
从表1可见,微博的相关设计指向于基于话题的人际网络建构。由于好友列表、转发、评论以及“@昵称”的可供性,让微博的信息分享与流转趋向于公开透明,并且更为快捷便利。这有助于形成某些热点话题,从而聚拢起相当规模的人气。微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分享、传播与获取的平台,是线上的公共空间。确切地说,它是Lange所谓的“私隐的公共空间”(privately public space),用户尽可能多地与其他用户形成链接关系,让其发布的信息最大化地进行推广和流转——但与此同时,用户无需公布其身份信息,从而保证其私隐属性[8]。
相对而言,微信是基于关系而建构的人际网络,强调根据好友列表的管理和分类的互动。而叠加性的“评论”以及“赞”的设置,则凸显了微信基于“强关系”的社交网络的封闭特性,让用户的线上行动及其嵌入的价值观不经意得到持续的自我强化。这造就了微信作为私密化与个性化的场域,类似于Lange所谓的“公开的私隐空间”(publicly private space)——用户的身份信息是公开的,与此同时,由于其信息的指向是特定的圈子,其流通的范围和程度都是私隐和封闭的[8]。
(二) 微博之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意涵
微博是适合人群聚拢的公共场域。在微博,某个话题或现象能够得到快捷和充分的关注,引发无数用户作出线上行动,发布信息、评论、转发以及“@昵称”等,从而表现出信息洪流、舆情鼎沸的现象,并且相当容易促成群情亢奋激昂,出现许多非理性的言辞。而当话题得以平息,用户则一哄而散。这反映出微博这种基于“话题”为中心的围观现象以及与之相符应的作为“乌合之众”的用户汇聚形态。在微博,大学生可以根据其兴趣、价值、目的以及想象的观众进行选择和分析信息,因此表现出较大的自主性。他们不再是像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那样被动地、消极地接纳信息,而是参与性地进行相关资讯或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流通和再流通。
微博能够迅速地聚拢起相当旺的人气,从而让特定事件成为公共话题。在微博,负面消息更容易抓住用户的眼球,其流通也更为快捷与广泛。这是微博之于大学生道德发展最大的风险所系,亦即:基于可供性而形成的中心化的关系网络对处在传播结构底层的大学生的误导或者教唆。处于中心地位的用户通常制造和控制着相应的话题资源,因而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用户的话语权力,并藉此而操弄微博里的舆情与其他用户的行为[9]。大学生囿于其心智发展水平,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处心积虑的影响。而且,微博里的用户行为也更容易导向情绪化的表达。大学生对特定事件所形成的广场式的围观,往往表现出“去个性化”、漠视责任与后果,从而更容易导致舆论暴力[10]。
从资源取向的视角来看,在微博的可供性条件下,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在以下三个方面获得一些机遇:(1)微博拓展了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让他们有机会接触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元的道德话语和行动反馈。这有助于大学生内在观念的协商、对话以及重构,从而养成更加开放包容的道德情怀。(2)微博让大学生参与性地在其中习得相关的知识和情感模式。比如“@昵称”,虽然表面上传递了某种提醒或邀请,其实也是Althusser意义上的“召唤”[11],即那些动态或评论所蕴含的价值或理念,以“非强迫的运作方式……呼喊着个体(to hailing a person)”[11],参与其中,进行互动。(3)微博也允许大学生对其道德发展内容进行试验与抵抗。微博的众声喧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作为既有的声音以及各种各样的言语在戏谑中混搭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声音和意义。大学生混迹其中,甚至可能挑战社会主流的价值准则,表现有意无意地试验性和抵抗性。而这是其道德自我建构得以完成的机会所系。
(三) 微信之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意涵
作为私密的空间,大学生在微信的行动基于彼此的情感纽带来展开。他们互粉而成为特定的群组。大学生在群组里存在的关键是沟通生活、交流琐事、传播八卦。这种私密的空间里,同样容许(可能的)道德议题的出现,但在微信的可供性条件下,这些议题往往并没有发生如同微博情境下的“围观”效应。相反地,话题本身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事件里面某些戏剧化的要素被迅速放大,并成为互动的聚焦。原本严肃的话题被转化为令人欣快的娱乐事件。借用Deumert[12]的观点,微信实际上是大学生的“嘻乐的自我”(ludic self)得以展现和建构的地方。大学生用户在微信里以好玩的方式与自己和他者建立关系。他们的聊天主题常常旨在于让大家觉得有趣,并且预示着无限的自由——说任何想说的。涉及道德生活的严肃主题偶有出现,但它们会急速地沉落而被新的轻松的主题替代,或在好友们的互动中被戏谑而转化为好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直面严肃的道德议题时,大学生在微信群组内的行动似乎难以涉及深刻的反思或体验,而更多地停留在有趣或好玩的层面,并以此来维系或强化彼此的关系。
微信的可供性也更加促进了用户的自我展示行为。在朋友圈里通过分组,大学生热衷于向特定的观众发布照片或视频。朋友圈是他们能够定制舞台或选择观众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更多地促进了社交网络里原本彰显的自恋[13]。大学生用户在其中的发布往往蕴含着其被关注、被聚焦和被认可的内在诉求。大学生在乎自己展示了什么,也更在乎在其展示之后别人的回应。
在朋友圈里,尽管大学生有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但微信的各种机巧的工具或设置却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对同伴的依赖,或准确地说,是对群组之内趋同的价值观的依赖而非对那些异质的、替代性的价值观的依赖,因为后者给他们的信念系统带来挑战。大学生习惯将这些携带不同信念的用户刻意地划归到不同的“朋友列表”中,比如教师,或者“关系疏远者”。微信有别于家庭或学校这样受监视的空间以及街头巷尾那样的公共的空间,是属于大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私隐空间。于此,大学生喜欢跟自己的同学或朋友混迹在一起,分享着相似的观点或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对微信的日益卷入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跟他者建立链接和展开互动,却可能从他者身上学得更少。他们努力在其中寻求各种各样的反馈,但在好友列表设置、叠加“赞”、没有转发功能等可供性的条件下,微信类似那种摆满镜子的厅堂,让大学生只能在其间获得他们所观照的同伴带来的反馈。
基于密切关系而建构的空间可以让微信(群组之内)里每个人都彼此注视,并有可能形成Foucault意义上的规训性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14]。比如,大学生被要求在微信中表现出起码的尊重、得体以及礼貌等,而倘若表现出伤害或欺凌行为,则需要担受来自群组其他成员的潜在社会压力。由此,大学生可以在其间操练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并将其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指南。这或许是微信为大学生带来的最为起码的道德发展意涵。但是,这远远不够,如前所述,微信内在的可供性导致的大学生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以娱乐化为导向、鼓励集体式的自恋、排斥不同的声音等,从而让他们的道德建构缺乏必要的资源。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对微博和微信里动态发布相关的功能(包括好友列表、发布、评论、转发、“@昵称”、点“赞”等)的可供性进行比照分析,认为:大学生使用微博“告诉”或叙述事件,形成“话题”,并以此为纽带而建构起嵌套式的人际网络,它具有媒体的属性;在微信情境中,大学生则根据好友的性质来设置特定的圈子,因此是一个基于“关系”建构的私隐空间。大学生在其中可以相对自由地“展示”自我。大学生从微博迁徙至微信,意味着他们逐渐从公共空间遁入私隐空间。如今,微信相对于微博,由于其可供性的特征,对大学生道德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威胁日益彰显。
基于可供性的视角,对大学生道德发展而言,网络技术本身并不是重点,网络技术提供或带来的行动可能性才是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启示之一:在社交网络应用的开发过程中,政府的立法或行业的规约应该采取介入的立场,基于其可供性的预见充分地检视和评估该应用蕴含或导向的价值要素及其对用户(尤其是大学生)带来的潜在影响,并且在该应用后续的流行中进一步检视和评估其可能的无意导向的行为或情感后果。同时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也应该组织或敦促社交网络应用的开发者担负用户教育和培养的相关责任,以避免强有力的技术被强有力地加以滥用的局面。
本文的启示之二在于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对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通常滞后于大学生,因而往往处于“数字鸿沟”的劣势的一端。非但如此,大学生遁入微信时,更是运用其内在的可供性,设置了秘而不宣但又坚不可摧的藩篱,将教育者排斥在外。教育者对大学生道德生活的介入,受到双重阻隔而鞭长莫及。因此,教育者需要重新定位其在线上的角色以及影响模式。教育者如何微妙地介入大学生的微信空间中,且不显山露水地实施道德教育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议题。
本文的启示之三在于网络技术不再仅仅被视为工具——拥有道德知识的教育者藉此而更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教学。网络技术关键在于其可供性,这跟Heidegger关于“技术”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Heidegger认为“技术不只是手段。技术更是某种揭显(revealing)的模式。”[15]“揭显”在他看来意味着部分现实经由技术被带到这个世界并且得以存在。不过,这个过程并非是单一的,因为部分现实得以“揭显”也意味着另一部分现实得以“隐蔽”。当前,微信正日益成为大学生线上生活的关键的“栖息”场域,其内在的可供性之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而言,确实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威胁,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也同时在“隐蔽”着某些尚未清晰界定的机遇和资源。而未来之于社交网络(尤其是微信)与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关系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聚焦于这些机遇和资源,为将来的教育实践和大学生成长提供基于经验或实证资料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