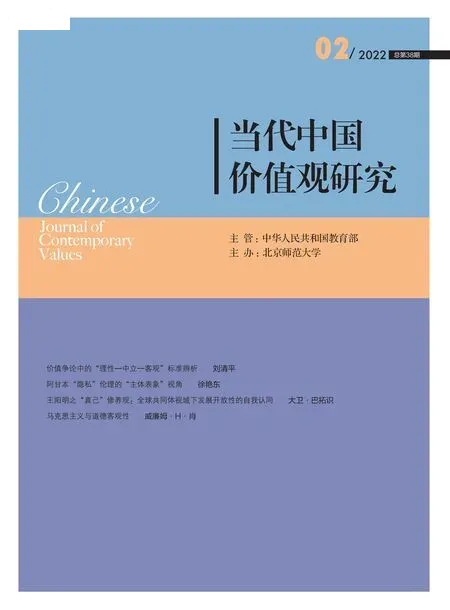阿甘本“隐私”伦理的“主体表象”视角
徐艳东
阿甘本曾受邀去美国讲学,然而由于他坚决抵制指纹采集,便中途主动放弃了这一出国计划,这与他极其看重个人“稳私”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阿甘本所理解的个体“隐私”并非简单等同于个人“秘密”,它更多指向生命的自主性与整全性。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而来的“非潜能”概念始终贯穿于阿甘本的思想体系,使得他一开始便非常重视生命的“晦暗性”,尤其是人作为主体的“幽深性”。透过“潜在性”和“晦暗性”,这位思想家从中明确看到了人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的全部可能性。大概是受海德格尔区分“现象”与“显像”等概念的启发,阿甘本始终重视对“表象”与主体关系的分析探讨。他还致力于探讨综合景观阶段人该如何在表象装置的密集围捕中求取生存空间这一现代性问题。他深刻意识到,在“辩证影像”完全为“景观表象”所取代的现时代,每个人都完全成为了机器装置的凝视对象。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下,以往的“社会主体”首先演变为“影像主体”,继而变为“数据主体”,经过层层抽象化,现代主体从“空无”再次跌回“空无”。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隐性”与“私性”皆被“显性”与“抽象性”所取代,“内部”为“外部”所占领,原本可能的“内在性平面”坍缩成了僵化的“外在性平面”。由此,“隐私”与“暴露”问题构成了当代第一伦理问题。对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数据主体”与“隐私”伦理的二重维度
阿甘本注意到,在现时代,每个人都不再能以实在的本来样子在世,而是要借由各种光学或感应介质(扫描仪、数据跟踪app、成像装置、感应仪等)的显现来存在。他在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由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光学扫描仪可以迅捷地获取指纹、视网膜或虹膜信息,这使生物识别系统逐渐超出警察局和移民局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中学的自助餐厅入口,甚至在某些国家是小学的校门口(生物识别产业近年正蓬勃发展,他们建议民众最好从小就习惯这种控制模式)都已经配备了光学生物识别仪,学生们心烦意乱地在上面按下指纹。”①[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5-96页。
在目前的大数据发展态势下,我们无可避免地进入数据状态,成为一名“数据主体”,这已然构成了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结构性事实。个体不仅有可能被动地遭遇信息泄露,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主动配合提供信息数据,否则就无法达成一些事实性的社会交换。伦理学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他们关注的是隐私及其泄露的问题,其研究范式是“客体—泄露”式的,这是隐私伦理的第一维度问题,其关注对象主要是数据的掌控者——各种大小形态的数据装置。关于这一维度的相关限制,通常包含四个具体的阶梯式原则:一是如无必要,不收集任何信息;二是若有必要,即当信息收集不可避免时,数据装置应尽可能少地收集隐私信息;三是如果因为社会运转需要不能实现少收集信息,那么要尽可能不让数据掌握者之外的任何人得到这些信息;四是数据掌握者要在契约或者事先同意的条件以及范围内谨慎使用已采集的信息,且过期后应尽可能在约定时间内将这些信息删除,以免给当事人造成任何信息性的伤害。
由上可见,第一维度隐私伦理的提出者们面对的是,数据是否应该收集、收集方式、收集范围以及使用范围等主要问题。毫无疑问,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这样的研究与呼吁对于人的自由及其基本权利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如果人的生存连基本的隐私自由都不复拥有,其生活质量以及尊严定将会成为一种奢望。“客体—泄露”式的伦理探讨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近些年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已然对各国推进相关立法以及隐私保护措施的出台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然而,阿甘本侧重的却是第二个维度——隐私伦理的“主体”维度,其研究范式是“主体—存在”式的。这一维度同样重视隐私的泄露问题,不过却将泄露看成是非基础性的,认为更加基础性的探讨应该集中在其他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下,泄露是结构性的、难以免除的,正是这个科技时代的总体特点让阿甘本最终改变了批判方向。他将批判的矛头从隐私伦理第一维度所针对的客体目标(摄取者的伦理),扭转向主体——被泄露者本身。在这种逻辑之下,我们谈隐私伦理,关注的将不再是“对方将我的信息拿走然后泄露了什么具体内容”,而是“拿走使用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我们的整全性造成了什么伤害”,这一维度更加看重人整个的生存论结构。也就是说,阿甘本更多关注的是隐私攫取的形式本身所带来的后果,而非强调泄露具体内容的后果。他注重的不是普遍性的生物识别手段“让人少了的部分”,而是“让人本身少了什么”。由此,阿甘本的隐私批判走向了“形式生命”以及人本身的维度,而为了抵达这一深层论述,阿甘本借用了基础存在论和影像伦理这两个强有力的批判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从他的思想导师海德格尔那里发展而来的,第二个工具则综合了德波、马克思与本雅明的相关见解。
阿甘本注意到,在进入到居伊·德波所述的“景观的第三阶段”,即“综合景观”之后,一切都被表象化,当然,被表象化最严重的则是人本身。阿甘本提醒我们要留意影像统治这一时代趋势,他说:
资本的生成影像不过是商品的最后变形,通过这种变形,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吞噬净尽,并在篡改了全部社会生产之后,终于达到了支配全部生命的最高绝对主权的地位①[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综合景观时代,影像为表象完全取代,或者以“影像—表象”的最终模式出现。在这个表象胜利的时代,人再也不能以本来的“姿势”面对面存在,他必须跃进扫描与摄像装置的波段里,借着外物才能走入“此在”自身的生存结构之中。影像带来了主体的第一次抽象化,我们被迫作为影像而存在,数据加工继而让主体遭遇了二次抽象化,每个人最终都只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成为“数据主体”。
此外,阿甘本还注意到另一个更加深层的现象,即各种成像以及数据采集技术不仅让主体被动地暴露在装置下,而且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现实后果——主体对于成像技术以及生物识别方式的主动依赖症。在他看来,现代的虚无主体已然无法告别被动的影像存在方式,他必须让自己成为一种影像,否则便无法体认自己活着并天然富有个性价值这一原始事实。这导致了现代主体不仅不回避,甚至还渴望机器装置对其进行各种精确识别。其思考逻辑是:
如果机器识别出了我或者至少看见了我,我就在这里;如果既不知道睡眠也不知道清醒,却时刻保持警觉的机器确认我还活着,那我就还活着;如果大机器记录了我的数字或数码信息,那我就不会被遗忘。②[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总之,“数据主体”存在的感觉依赖于机器的记录,他们对于数据采集不仅不主动进行拒绝或抵抗,反而会有意识地在机器光谱里寻求确认与满足。机器成了真正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大他者”,数据主体时刻需要“被凝视”。在机器的介入下,我们与他人一切原初的交往欲望都被冲淡了,交流再也不是通过微笑或姿势,也不是通过和蔼或沉默,而是通过一种生物身份进行信息传递①具体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在这个时代,机器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人的“目光主人”,我们需要随时随地被看到、被听到、被触摸到。虽然到不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愿意主动泄露自己的大部分隐私给机器”的程度,但是我们却“经常性地愿意将自己泄露给机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便涉及到阿甘本所重视的“隐私伦理的第二维度”,即技术对“人本身”的影响维度。这也造成了从隐私伦理的第一个维度——“给看不给看,看到什么东西”,到“不得不给看,主动给,给出自己的全部”的第二维度的深度转向。
在第二维度中,隐私侵犯不再单纯看重所泄露的内容,而是关注我们的存在方式,即我们必须向机器存在以及我们喜欢向机器存在这一事实。这对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更根本意义上的侵犯。数据主体欢迎“侵犯”、欢迎机器,在他们看来,一切没有被数据机器“侵犯”的自我部分都可以与自身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有一些极端人士会选择主动在网络上散播自己的丑闻,以此实现自我存在的幻觉式认证。当我们将“整个自我”都献给数据时,强调自我的“哪个部分”不要被采集或者被发现,将是一个严重的逻辑悖谬。主体不是将部分隐私,而是将整个自我都作为隐私呈现给了机器他者。可以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根本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私,因为隐私首先涉及自我与他者的私人性差别,然后才涉及隐藏自己的部分私事。然而,在数据政治之下,一切都是无差别的信息,人也是无差别的,人所有的活动最终都要被还原为数据。我们的自我已然是数据化了的,成为数据才有自我,而数据机制必然会侵犯隐私。数据必然拥有内容,否则就不叫数据。数据装置不仅要通过吸收人的内容,还会通过吸收人的形式本身来“喂饱”自己。
人们愿意泄露自己的全部私人性,是与影像时代的总体特征完全一致的。以公共性影像曝光促成最终的私人性确认,其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到处自拍并传播到社交媒体。通过费神的自拍动作让自己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对自我不要任何隐藏,或者以唯一方式——暴露来实现隐藏。与自拍的影像景观密切配合的是各种化妆崇拜以及修图拟真技术。过度的化妆让脸与形体完全几何化和数据化,并最终全部服从于美学专家提出的统一人造标准。这一标准为个体深度信服,仿佛越是统一化,越“不是”自己,才越“是”自己。美学、数据和影像彻底颠覆了真正属于自身的原始私人性,生命被数据最终俘获。
至此,隐私伦理的内容以及涉及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动与被动、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人与物本身的关系都发生了结构性的颠倒。我们与我们的信息摄取者们的关系变得复杂微妙,后者不再像过去一样明显地被视为我们的敌人。在两个维度的综合作用之下,我们甚至连“隐私”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关于什么是隐私感的体认都出现了重大的主观性分歧,以至到了“人们更愿意保护还是更愿意泄露隐私”都不得而知的极端程度,人们自己也不太清楚“泄露”与“守秘”的界限。在阿甘本看来,这是由于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语言和概念本身已经彻底混乱了,巴别塔的隐喻在如今已经彻底具备了其现实性。这也恰恰印证了他的诊断:“如今资本主义的瞄准目标不仅是对生产活动的征用,而且首先是对人类语言本身进行异化,对语言性质和人的交流本性(della stessa nat ura linguistica e co municativa dell'uo mo)的异化”②Giorgio Aga mben,Mezzi Senza Fine:Note Sull a Politica,Bollati Boringhieri,2013,p.67.。
二、从“面具主体”到“无人格身份”
为了达成对主体隐私性的深刻辨认,阿甘本对“人格”一词进行了详细的概念与历史考古。persona(人格)一词最初的意思是“面具”,在古代罗马,贵族们除了通过自己的名字,还通过存放在正厅中的祖先的蜡质面具得以确认其个体性,每一面具和每个个体为社会所认可的人格与个性之间是正相吻合的①具体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7-88页。。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具、人格与家族他者的辩证关系。面具表象(人格)个体,同时(人格)个体也在表象面具,这是一种双重关系。面具不仅是个体的象征,还指向家族的其他人,尤其是曾拥有显赫地位的祖先。由此,面具既隶属于个体,同时在古代西方还是家族所有成员的表征物,隐藏着历史的经验与价值。阿甘本认为,“人格—面具”在古代西方不仅具有法律意义,而且对于伦理主体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加基础和重要。
除了历史考古,阿甘本还从斯多葛哲学那里印证了古代主体和人格面具的复杂辩证关系②阿甘本之所以追溯斯多葛关于演员与角色的“分离性认同”思想,大概也是受到其思想引领者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在讨论史诗剧时,援引布莱希特的理论,强调演员在表现角色的时候也应该同时表现自己,即保持借助艺术手段跳出角色的可能性。(具体请参见[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4页。)。按照斯多葛派的说法,古代个体与人格面具的表象关系是十分丰富的:“伦理个体通过既佩带社会面具又与这一面具保持距离来建构自身:他毫不犹豫地接受它,同时又悄悄地与其保持距离”③[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0页。。在此,尽管面具和主体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分离,却又在分离中黏合得更加紧密。面具隐去了主体的面容与表情,却生发出更多的属于面具与主体的共有表情。与之相似,在《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中,阿甘本再次提到角色中面具和主体之间的丰富关系,他将其称为“二者的幸福感染”。在他看来,在其中“演员不是戴上面具那么简单,而是二者同时被召集于一个领域,在那里,真实生命和舞台场景模糊不清并丧失了一切同一,个体和其面具跳出了一般性和独一性的日常逻辑区分,同时迈入了一道无区别的门槛”④具体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0-71页。。阿甘本还考察了意大利传统即兴喜剧,认为“这些面具不是角色,而毋宁说是作为类型而被形象化了的姿态,是姿态的星丛。在这种情境中,角色同一性的瓦解与演员同一性的瓦解联手而行……面具使自身迂回地进入了剧本和演绎之间,从而使权能与行动实现了难以区分的混同”⑤[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除了具体的图像面具,阿甘本还提到另外一种古代的“精神面具”——“守护神”形象。阿甘本笔下的“守护神”不只是一个宗教概念,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词源学的概念考察结果,这一形象来自于他的直观体认。在他看来,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证实,然而守护神的存在又是可以被明晰地直观到的,它具有普遍的确实性。按照阿甘本的描述:守护神指的是我们身上一切非个人的部分,它又真正的是我们自己的亲密生命。它是推动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或使我们陷入睡眠的力量,是身体中温柔地调制和分配它的温暖或那放松或紧缩肌肉纤维的未知的力量。它真正的是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最陌生的,不会属于任何人。它离我们最近同时又最远,不受我们掌控①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守护神是“我”的“外部”,描画“我”又分离“我”,同时“他”也是“我”的“内部”,如同“我”的私人面具。阿甘本认为,恰恰是与保护神的这种融合又分离的辩证关系,让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主体。主体因此不再是实体性的,它同时被两个相反方向的力所贯穿,这两种力既分离又交叉,一个指向个体,同时另一个指向非个体②具体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伦理主体建构过程中的“非主体”部分,确切说是个体同他身上固有的“非个人”部分之间复杂的“联结—分离”关系。“我”和“非我”的部分始终并存,这同我们与原始人格面具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阿甘本还注意到,古代人极其重视面具,古代演员凝视面具时,是认真而严肃的,其中表达着深深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他在表演时同样也要表达“非面具”的部分,这也是其真正独特的隐私部分,正是在服从与反抗的绝对悖论关系中,他们体认到了完整的自我认同。不仅是演员,古代社会的人更是如此,古代的人格认同在自身自由以及同社会他人的张力空间中拥有持续稳定性。但阿甘本指出,随着近代监控技术的发展,最初应用于罪犯身上的数据采集技术被推广到众多生活领域,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无人格的身份和无限倍增的面具③[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页。。在这种新形势下,尽管身份面具与人格的关系表面变得多重化,然而却最终只是化为死板的表象,变成了“越多越空,越多越少越呆板”;“多”丧失了所有“内容”,其中的主体失却了经验,仅有经历,不再储备真正的历史记忆。
在这种僵硬的关系之中,人格主体与面具的关系不再灵活生动:要么主体完全皈依于面具,要么是让自己彻底告别面具。面具不再如“守护神”一般被视为绝对的“自我—非我”成分,而是人的目的性工具或者个体的精神镣铐。阿甘本看到,在数据科技时代,当个体被归结为纯粹生物性的非社会身份时,他可以戴上各种面具,可以在网络上过第二种或第三种生活,尽管所有这一切都不真正属于他。他们不再需要承担那种原初的社会人格带来的道德重负,不再直视对方的眼睛,完全逃离了人格的重量以及道德情感的压力④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页。。在其中,个体可以借着影像的隐匿性随意进行各种网络社交,而对自己的言语与行为不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正如阿甘本所指出的:
在人类历史上,身份第一次不再有社会人格和他者认同的功能,而只有生物数据功能,它可以和人格没有任何关系。人类摘下了数千年构成其认同基础、从而赋予其身份的面具,转向隐秘地绝对属于其自身、但又无法认同的某物。我的认同不再由他人、同伴和敌人来确认,甚至也不由我的伦理能力来确认⑤[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网络上“隐”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个体在虚拟世界中的隐匿性,正因为在其中获得了隐蔽的畅游体验,个体才彻底深陷其中,患上了上“隐”症。借着“隐身”不一定展开什么具体行为,仅仅是“隐身”本身就能让现代人充分体验到足量的“剩余快感”。这种上“隐”症表面上维护了赛博主体的隐匿感觉,使其可以在暗处畅快淋漓,然而从根本上看,其“隐”性的获得却是以“私”性的彻底丧失为根本代价的。
曾建基在稳定性人格面具之上的古代个体认同被网络数据认同所取代,个人不再自由地立足于和他自己的守护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中,而是成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私性”不再存在于与“他性”的辩证关系中,而是游走于过分极端性的两极之中。面具从与自身极其丰富的“人格—表象”关系中脱离了出来,完全成为了僵硬的“假象—表象”。“无限倍增的面具”让“无人格的个体”广泛地存在于世界中,可以凭借各种身份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存在,然而他又“从不存在”,因为不再有“他”,或者说,“他”成为了绝对的“无”。没有“他”的“私”,当然不会有“他”的“隐”。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隐”的,不需要在阳光下与他者进行具体交往,然而“他”的“隐”在终端的意义上又不是“私”的。在数据洪流的席卷下,“他”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完全在生命权力的掌控之下。网络监控技术有能力让一切都被记录和看到,只是必要性的程度问题。这其中呈现的逻辑是:如果必要,就必然会被发现和提取。由此可见,“隐”实际上也是表象化和虚假化的,大数据让一切的“隐”都处在随时的“显”的控制之下,可以说“隐”是暂时且偶然的,“显”才是必然与根本的。过去可以隐藏某些私人事件,而在当下与未来,隐藏任何事物都变得不再可能。显露不仅是技术装置的绝对能力,而且还经常是我们强烈的私人要求。在这种局面下,隐私伦理将变得不再可能,至少其所指与内涵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面孔”主体与“归隐”策略
以上通过对于“数据主体”以及“面具主体”的还原分析,可以清晰看出阿甘本思想的敏锐与独到之处。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将自己逼入一种分析的“绝境”,而主动遭遇绝境却恰好构成了他一贯的思考风格。先行于“失败”之中,在思想的绝境中求生恰恰是阿甘本最擅长的文字策略。
尽管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与科技现代主义无限悲观,在看清了“我们必须在数据下生活,否则寸步难行”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之后,他却并没有简单走回复古主义的旧路。在他看来:“遵从历史规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我们必须为寻找人类的新形象做好准备,既不满怀歉疚,也不满怀希望,这一新形象应该既超越个体认同,又超越无人格的认同。或者说,我们必须寻找的可能只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因为超越了面具的脸和超越了生物数据的脸是一样的。我们仍然没有尽力去看清楚这一形象,但对它的预感会突然惊醒我们,有时是在我们的困惑中或梦里,有时是在我们的无意识中或完全清醒的状态下”①[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页。。阿甘本并非要致力于恢复到过去的某种样子,而是倡导在数据科技的阴影下进行“不可能”的突围,进入“形式生命”本身,成为无法采集的真正主体。然而这样的道路仿佛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鉴于此,除掉遁世主义与拒绝主义,阿甘本还能为我们提供出何种有效的逃逸策略?
阿甘本给出的答案是,重新“恢复”和“构建”自我。然而,这里的“构建”并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构建并非是要树立或者恢复一个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主体自我,而是去把握“面孔自我”,阿甘本将其称为“把握面孔的真相”。尽管阿甘本批评僵化的影像及其虚假性景观效应,然而他仍然不会轻易放弃影像的激进有效性这一面向,这也是造成其反抗策略最终导向对“面孔”进行分析的根本原因。通过承接列维纳斯关于“脸”与他者关系的深度思考,阿甘本发展出了独特的面孔学理论。尽管面孔并非个体单纯的肉身部分,无法被定义,但他还是对其进行了描述:面孔(volto)不完全等同于面庞(viso)。凡是在某种东西达到暴露的水平又试图自身免被暴露的地方,凡是在某个存在者即将沉入这种外表又试图找到摆脱的出路的地方,就会有面孔存在”①[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相较于古代面具与象征主体关系的丰富性,同时相对于数据罗列对于现代主体的抽象性,面孔和主体的关系在阿甘本的笔下变得更加复杂。面孔可以构成表象,也可以由表象单独构成;面孔可以表象主体,也可以表象主体的“外部”;面孔可以暴露主体,同时也可以隐藏主体。它具有天然的张力结构,在人身上,面孔集隐匿和暴露于一体,正如阿甘本所说:“面孔只因其隐藏而揭示,只因其揭示才隐藏。通过这种方式,理应使人得到显露的外表对人来说却成了这样一种外观,它使人泄露自身,但人在其中又辨认不出自己……人的真正所是无非就是外表之中的这种伪装和不安”②[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阿甘本反复提及面孔表象的复杂性:
人的面孔总是呈现着它自身结构内部的那种二元性,即真与假、交流与可交流性、权能与行动之间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也是人的面孔中构成性的东西。人的面孔的形成,有赖于一个消极的背景,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上积极的表现性特征才能浮现出来。③[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2页。
不仅如此,阿甘本还敏锐地看到了由面孔所开启的关于“暴露”与“隐藏”的政治与主体的双重维度。人作为一个主体,天然注重控制自身的暴露程度,这也招致了政治的在场,对此阿甘本总结道:“暴露是政治的场所,如果说不存在动物的政治,那或许是因为动物从来都是开放坦白的,从来都不会试图控制它们自身的暴露;它们就居于暴露之中,从来不刻意为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镜像、对作为影像的影像没有兴趣。而另一方面,人则使影像与事物分离,并为之命名,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要辨认自身,也就是说,他们想把握他们自己的外表。这样一来,人也就将开放的外面(l'aperto)改造成为世界,改造成政治斗争没有边界的战场。这场以真理为目标的斗争,则被称作历史。人与动物不同,他想控制自己的外表”④[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正因为“暴露”关乎政治及主体性确认等基础问题,它天然构成了人的核心区域。政治与生命的复杂性问题完全可以在面孔的二元张力属性中找到答案,前者亦可以为后者提供答案。
通过阿甘本的分析,我们发现,面孔的复杂性直接导向的是两个相反的面向。
一方面,面孔构成了自由的绝对机遇。首先,“我”必然与“我的”面孔“相交叉”,面孔并非人刻意争取到的避难所,每个人本身即处于“有我”与“无我”之间的面孔的绝对位置之上,从而天然就构成了“面孔—姿势”。影像采集到的关于“我”的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的面孔,它不仅代表了“我”的实在,同时代表了“我”的虚无。透过“面孔自我”,“我”的本质与表象合一,却同时又相距遥远。“我”被机器捕捉到的永远是“面庞”,而非“面孔”,这二者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按照阿甘本的描述,“面孔不是单一的,而是形形色色的面庞的并立,在其中没有哪张面庞比其他面庞更真实。把握面孔的真相不是把握各种面庞的类同性,而是把握其同时性”①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4-135页。。阿甘本将其描述为“将诸种面庞汇集并团结在一起的一种不安静的力量(l'inquietà potenza che li tiene insieme e acco muna)”②Cf.Gior gio Aga mben,Mezzi Senza Fine:Note Sull a Politica,Bollati Boringhieri,2013,p.80.。面孔既属于“我”,又不完全归属于“我”:
我的面孔即是我的外面,它是一个模糊点,在这里不再有我的全部专属属性的区别,不再有属于我与共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在面孔上,我是带出了我的所有属性(我一头棕发、身材高挑、苍白、骄傲、易动感情……),但这些属性当中没有一个是专门属于我并能使我借以本质地辨认出我自己的。③[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5页。
从这种面孔哲学的视角来看待隐私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隐私不是产生在主体之后,也不是在其之前,甚至与主体亦非同时发生。与其说是“主体”产生隐私,不如说是隐私生产“主体”。主体全部都由“脸”这一隐私基础立基,主体只是“脸”,正因如此,“主体”自身全部都不是隐私,“他”永远不是作为“部分”而存在。在面孔的天然构成下,即使“我”被还原了,被泄露了,然而“我”又完好无损。这是在“泄露”之前的“泄露”,伦理之前的“伦理”,也是纯粹形式的伦理,而非内容的伦理。当自我如面孔,真实生动与模糊昏暗混搅在一起,“自我”与“非我”同处于一个空间,隐私的摄取与泄露才对“我”完全无效。面孔同时与语言有关,“它”呈现的不是固定化的内容和信息,而是语言的纯粹可交流性本身。由面孔构成的主体性是一种绝对的空洞,它本身即符合阿甘本所强调的“示例”类型。在其对“示例”的特殊分析中我们看到:其中的存在物“既非特殊,亦非共相,而是一个别物”④[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而作为人的每个个体应该是“示例化”的,在理想的意义上,“示例”的东西,除了可以被称呼之外,不可由任何属性界定。而数据则是按照某些特征属性将人进行分类划定的。信息与数据切分皆不符合阿甘本提出的“同名(o moni mi)却异其是者”⑤Cf.Giorgio Agamben,La ComunitàChe Viene,Bollati Boringhieri,2001,p.57.的未来个性理念。他重视的是逃离所有简单划分的“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是个别性,但又是多出了某个“空的空间”的个别性,这些个别性连续不断地由其自身的式样而生成自身⑥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页。。这里所述的“任何一个”当然包含由面孔所反映出的主体意象。总之,在阿甘本的思想体系里,面孔天然构成了人的避难所。
另一方面,阿甘本看到了“面孔表象”对主体带来的灾难性面向,也即面孔处处被危险使用的当下处境:面孔、真理和展示如今都是一场全球内战的争夺目标,这场内战的战场就是全部的社会生活,而其突击队则是媒体。政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面孔,装置的首要基础是对表象的控制①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由于面孔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一空间在为人提供绝对的隐私自由的同时,也让主体时刻处于被侵入和被控制的危险之中,从而使得面孔沦为他人的工具。正是因为面孔的表象不含任何实际的内容,有一种自身和别人都未知的东西深藏其中,它便构成了隐私的天然优势。面孔的非真非假性如同影像自身的缥缈性,这个真正中空的大空间还天然会导致各种奇怪性的扭曲:影像的“真实感是与其展露自己弄虚作假的程度正好相符的(proprio nella misura in cui esibiscono la falsificazione,essi appaiono piùveri)”②Giorgio Aga mben,Mezzi Senza Fine:Note Sull a Politica,Bollati Boringhieri,2013,p.76.。在景观社会下,经常性出现的问题同样印证了鲍德里亚的判断——表象社会之下,“超真实”(假)本身比“真”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这种境况下,面孔主体的结局将是惨淡的,原本的隐私性优势反而构成了其他目的的利用工具,而且这种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面孔自我”的使用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面,无法为个体带来真正的隐秘感,阿甘本便讨论了其他的归隐方式,尤其是艺术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具体呈现了如何以作品或实验的方式让自己处于隐蔽且绝对私人性的状态。当然,艺术和实验只是阿甘本的阐述手段,其本质是对语言的重新改造与利用,具体说来便是放弃意指性语言的直接性,转而利用语言的“非潜能”(阿甘本将其称为“声音”)去实现对于装置的根本性逃离。“声音的语言”与作为信息的现代科技语言是正相对立的,“声音”从产生之日起就摆脱了能指与所指的双重枷锁。
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一书中,阿甘本通过瓦尔泽的作品向我们呈现了语言的另一种使用策略,即用“托名”或“假名”(pseudoni mo)的变形方式来展开陈述③Cf.Giorgio Aga mben,La Co munitàChe Viene,Bollati Boringhieri,2001,p.49.。阿甘本称赞瓦尔泽,认为后者以“某某”的托名或者假名的方式从一开始就让作品产生了“伪装”与“隐匿”的特质。主体开始即以另一个名字的方式现身,对“他”的描述越是铺展,读者离“他”的距离就越远。这种手段通过“愈显愈隐”的方式,在叙述的量与质二者之间“挑拨”出了永恒的悖谬结构。通过假名称,主体在词语的处处暴露中安稳地实现了真正的隐藏。除了对主体和名称的特殊变形方式,阿甘本还注意到瓦尔泽笔下的“词绝不强装严谨”,而是“疲倦得要死”,而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字未来主义。瓦尔泽不仅不像古代作家一样追求意指的精确与优美,反而故意选择疲倦的词汇,并且有意利用疲倦的连接方式。正是借由诸词语的瘫软及昏昏欲睡性,瓦尔泽或者带领主体从意指性的监禁中逃生,或者选择让主体一直隐匿在“睡着的词汇”中,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全之所。
除了瓦尔泽,阿甘本还列举了傅里欧·泽西的技术。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神话学机器(la macchina mitologica)的创作方式,在其中,“言说‘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一同出现,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我’的模拟或者我的面具(un calco o una maschera dell'io),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主体的两个声音以夸张化和戏剧化的形式并列上演”①Giorgio Agamben,La Potenza del Pensiero,Saggi e Conferenze,Neri Pozza,2010,p.111.。此外,阿甘本还通过专著《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向我们展示了他独到的艺术归隐方式。他对其中非同寻常的故事主人公进行了描述:普尔奇内拉一直变换着样子,没有固定的身份与性格特质,然而他却又一直是普尔奇内拉自己。普尔奇内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副词:他不是一个什么(che),而是一个如何(co me)。他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糅杂②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2页。;他是一个集合,然而同时又是自身,这是一种居于特别和一般之外的不可能的类型。既是独一无二又不单在个别性之中。他活在死亡“旁边”,他既不属于死者,也不属于生者③具体请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2页。;“普尔奇内拉是对一切性格的正式告别,他只是成功地亲历了未亲历者,而不将之作为一种命运承担下来。他在一切生活(bios)的彼岸过着一种生活”④[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2页。。正是通过身份的非稳定性与生活的彼岸性,普尔奇内拉始终存在于暴露与隐藏自由张力中,我们读得越多,他离我们反而越是遥远。普尔奇内拉的形象真正符合了阿甘本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中所设想的个体的绝对独一性,正是这种绝对的个体“孤独性”让这个共同体根本上是“破碎的”。这是由于:“任意独一无二的个体不可能组成景观社会的一个societas,因为他们并无任何可兹证明的身份,也无可借以寻求承认的社会纽带”⑤[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在他看来,恰恰是这种“破碎的共同体”才是真正坚实且充满人性化的,它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态。
除了文字与类型艺术的方式,阿甘本还在作品中多处提到即兴喜剧和滑稽模仿,认为这种古老的方式逃离了任何固定的叙述类型,它本身即是影像的和独一的。在即兴喜剧或滑稽模仿中,完全的瞬时性以及主观性让表演者打破了舞台的常规剧情,原本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类型被这种“突然性”撕碎,一切开始由原初完全的“明显性”转成晦暗不明的隐匿性,让人难分真伪。当然,“意大利即兴喜剧的面具在登上舞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拥有生命而演员只能钻入普尔奇内拉的生命和身体——而不是台词——并让自己被它们所占据”⑥[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3页。;“普尔奇内拉不满足于舞台上即兴表演;他在生活中也即兴发挥”⑦[意]吉奥乔·阿甘本:《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这种影像的戏剧方式让原本的艺术与生活预期发生了结构上的根本变形,从而让笑声构成了“厚重的帷幔”,主体才能隐遁其中。阿甘本大概认为即兴喜剧与德波提倡的情景主义方式遥相辉映,后者通过情景实现了主体的“姿态”性存在,“姿态是生活与艺术、行动与权力、普遍与特殊、剧本与演绎之间交叉点的名字。它是被剥除了个人生活史语境的生命瞬间……它是商品的反面”⑧[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页。。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阿甘本维护主体隐私的典型策略手段。但这恰恰构成了阿甘本的独特策略,从悲观中寻找希望的可能前途。他寄希望于那些真正的“面孔主义者”:若能仅是着他们各自个别的外显性,仅是着他们自己的面孔本身,则可能实现一种无预设、无主体的共同体。解开差异性与共性的薄膜,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任务①[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1页。。也许恰恰是在这层“薄膜”中,富于“生命姿势”的主体才能成功发掘并守护其最后的“隐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