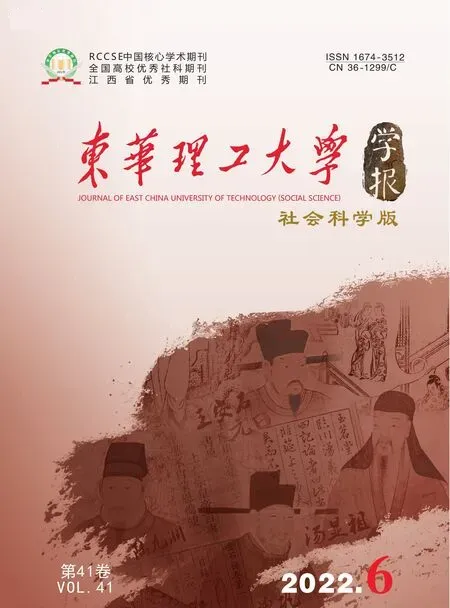家坤翁:宋代临川文化的承创者
赵军伟, 刘卫涛
(1.东华理工大学 抚州师范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2.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家坤翁(1213—?),号颐山,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以户部郎中知抚州,在任期间厘奸剔弊,颇有政声;著有《抚州图经》(已佚)、《景定临川志》三十五卷(今存残卷,收入《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宋诗纪事》录其诗一首,其散文多被《宋代蜀文辑存》收录。然而,学界对家坤翁的研究颇少,本文拟从《景定临川志》的编纂、抚州诸多名迹的修葺以及纪事散文创作三个方面来探讨家坤翁对临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承前启后的《景定临川志》
临川设县始于汉朝,历史悠久,县志编修源远流长。在家坤翁编纂《景定临川志》之前,众多临川县志版本的原本大多已经失传,不能深入考证。《景定临川志》的编纂在临川县志修订史上具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搜集了大量文字材料,使得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免于失传;另一方面,相较之前,《景定临川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例,为后世县志的修订提供了基础框架。
临川县志的编纂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时临川太守荀伯子收集临川当地山川、风土、民情等资料,编纂《临川记》六卷,为临川修志之始。此书现已失传,其相关资料散见《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且看以下几例:
荀伯子《临川记》曰:岩内有石人,坐盘石上,体有尘秽,则兴风雨。洗讫晴日,遍体洁朗,如玉莹净,民以为准焉[1]236。
荀伯子《临川记》曰:五章山绝岩险峭,有蜜蜂依之为房,其形如笠,采者皆悬磴数十丈然后获之[1]236。
荀伯子《临川记》云: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东高坡名曰新城,傍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2]2527。
隋唐时期,临川县志的编纂工作并未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延伸,仅有两部专题著作,一是《临川圣贤名迹传》三卷,撰者不详,且已失传;二是甘伯宗所撰《临川名士贤迹传》三卷,亦失传。两书以临川名人名迹为主,并未涉及临川当地风土人情,未形成系统性的著作体例。
宋朝之前,临川县志修订的次数并不多,体例亦不完备,且均已散佚。临川县志的修订在宋朝迎来了第一个小高峰。如,南宋重臣李壁作《临汝闲书》五十卷、邑人汪大经作《临汝耆旧传》、张贵谟作《临汝图志》十五卷、徐天麟作《临川志》,等等。宋淳熙二年(1175),赵善誉始撰《临川县志》。嘉定四年(1211),屠雷发在赵本基础上重新编纂,且更显条理性,初步具有分卷立目的意识。赵、屠二志并见《永乐大典》。但令人惋惜的是,二书原本亦亡佚不可考。
景定五年(1264),时任抚州知州的家坤翁感临川“群公先正萃焉,文献可谓足矣。郡乘顾无成书,先后草创,乃不足证,来者慊焉”[3]96。文中提及乐史有作《太平寰宇记》,晏殊作《类要》,却不曾对临川当地的风土文化作相关著作。《太平寰宇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地理总志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必读书籍,记载了北宋时期地理、历史、风俗、人物和艺文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开创撰修地志书的先河[4];《类要》遍及天、地、人、事、物各部的知识体系,共计一百余卷,涉猎广泛,独成一家[5]234。家坤翁称二者皆可谓“举天下郡国之纲”[3]96,然二位名士皆着眼于天地四方之志,不曾对乡里的地理人文进行详细搜集考证。在其位,谋其政,“坤翁以景定壬戌被命来守,岁余少事,属同志收揽载籍,考订耆旧,退而相与裁之,合为三十五卷”[3]96。成书后,交予周君彦查对阙误。家坤翁认为,县志实时编修,则事可具备,若百十年来不曾缉续,便有散佚的可能。
《周官》自川泽丘陵、坟衍原隰、都鄙土地、官府次舍,讫于士庶民物、风俗、生齿、财用器械、九谷六畜,各有所掌,岁时比之辩之,稽之登之,盖不徒考校其数,常修治其籍,惟恐一日失所纪也。懿哉!我后之人,尚有意焉,愿毋忘《周官》之法度,时取而附益之,庶乎此书可传也,可继也,可悠久而备足也![3]96-97
家坤翁以继“《周官》之法度”为志,对临川川泽丘陵、坟衍原隰、都鄙土地、士庶民物、风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探究,辨伪去妄,形成了临川县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修订临川县志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及参照体例。嘉靖《抚州府志》徐良傅后序载:“郡故有荀伯子《临川记》与淳熙《志》,虽不可考见,而家太守坤翁所为《景定志》,首末图经皆在,上下数百年文献,开卷了了,无采摘缀辑之难。”[6]56
元朝无临川县志的修订。直至明朝,在《景定临川志》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临川县志》。如,明朝临川人傅占衡作《临川志》三十卷,拾遗补缺,结构和材料也基本以《景定临川志》为蓝本。又如,《弘治抚州府志》序曰:“凡若干卷,其例一承家氏之旧而少加损益。”[6]19家氏,即家坤翁。清朝修临川县志,亦多在《景定临川志》的结构上加以修补,且大量引用其中文献。如《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二抚州府卷,称抚州“二水绕郭,五峰镇城”,便是引用《景定临川志》。又如,清代同治年间童范俨主修的《临川县志》所引:
宋景定志云:旧名秋声斋,在治事厅后,仁寿堂西,偏丛竹间。淳熙二年,州守赵熠重修,易其名曰拙斋,晦庵朱子为之记[7]670。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此后临川县志的编纂,不但在材料上多引用《景定临川志》,而且在体例上也不曾有较大改变。在清朝诸多县志中,甚至以《景定临川志》作为临川修订县志的开端。如,康熙乙巳年《抚州府志》云“考郡志之所自始宋景定”[6]23。《景定临川志》集先人荟萃,开后世体例,对后世临川县志的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
2 重修抚州名迹
家坤翁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厘除奸邪,奖励农桑,在百姓中颇有威望。在此之余,他还着手修葺临川大小名胜古迹。名胜古迹是历史过往的见证,更是先贤们的精神象征。然而在历史的风雨中,多处古迹毁坏崩塌,年久失修,早已不复往日风采。家坤翁感临川先贤风骨,亦不想前贤们的雅正之风与古迹一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是,家坤翁对失修的古迹重加补葺,才使得众多象征临川文化的名迹至今得以保存。
第一,修补抚州主城墙。抚州在东汉名为临汝县,六朝始至隋为临川郡,唐代改临川郡为抚州郡。唐中和五年(885),危全讽将抚州州衙向东迁往羊角山,光启三年(887)开启了抚州历史上第一次的城墙修筑工程,历时三年竣工。南唐升元四年(940),周弘祚再次修葺,浚深其池。宋绍兴年间,太守张混因城墙简陋曾修补之。绍定年间,太守黄炳复浚池,悉力创治,这次规模是自中和年间以来不曾有过的。再至景定年间,城墙摧颓、荒翳,望楼损坏四处,十二处城门倾斜不支。家坤翁抚念今昔,不免发出慨叹:
盖自唐讫今五百年间,守土者不知其几人,其能兴废者才四人而已。大率敌国外患之来则城兴,燕安逸豫之久则城废,俯视一辙,不谋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应,故理相通。城复于隍之象,虽着于上六道穷之后,无平不陂之兆,实基于九三道通之际。信乎!废兴成毁,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国有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则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长保。岂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砻者不见其损,积累者不见其益也,况斯城久于否[3]102。
家坤翁用《易经》中的“泰”相来比喻抚州城墙兴废之状,说明事物鼎盛之后,必然迎来衰落,然阴阳循环,盛衰往复,太平盛世也会有不平之事的发生,逢凶亦可化吉,其中蕴含着古人阴阳交泰的哲学观。内忧外患之时抚州城墙固若金汤,太平之时城墙破败荒翳。家坤翁以城之小见天下之大,阐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理,并希冀后人勤加建设:“然念人情终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来不可常,书用识之,以勿忘于心,亦以望后人,非徒记其事求自衒,将以致吾城于坚高悠久也。”[3]102
第二,修葺五峰堂。“景定志云在治事厅前之西偏,旧名见山堂,后改名见远。绍兴中,州守张滉重修,复名见山,黄次山记淳熙三年州守赵熠重修,后废。至景定四年,州守家坤翁重建,改名五峰堂,久废。”[7]569家坤翁在《重修五峰堂记》中,记叙并考证了五峰堂的修葺历史,表达自己重修五峰堂并非仅仅为了愉悦心志,而是抒发心怀天下之愿,希冀后辈再达此地时能够有所感悟:
孔子登东山、泰山,小鲁、天下者,何也?小大一理,远近一本,推而致之,同此观也,同此心也。今吾隐几默坐,寻丈千里,小而一心,大而四体,近之一州,远之四国。吾视此身,如视此邦;吾见五峰,如见五岳。此理此中,随寓随着,其所以矩上下前后左右者,乃所以准东西南北四海也,非曰能之,愿学焉。至若孜孜于美景,眷眷于赏心,则非吾志也,非吾事也。乃记其说于堂上,以此自达,复以此贻同志[3]98。
第三,重修鲁公堂。“郡治旧有堂,曰王谢,曰康乐,曰鲁公,盖王右军、谢康乐、颜鲁公皆尝守郡,后之人歆慕之,以是名堂。”[3]101鲁公堂原为康乐堂,后又改为王谢堂,最后转为鲁公祠堂,因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皆曾任临川太守。如今鲁公堂早已在风雨中毁塌,相比王、谢二公,家坤翁对颜鲁公忠烈气节更为推崇与钦敬:
公以大历元年忤元载,自尚书左丞别驾峡州、司马吉州、刺史抚州、湖州,十二年召还,距今五百有余岁。人民非矣,堂之弃而碑之仆矣。公英姿义概,摩荡人耳目,尚凛然如存。盖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谓公久于此,政教入人者深欤!计公留临汝,乃不二三载,公之名字,所以震撼今古者,固出于治郡之外,天理人心,亦随所寓而长存[3]101-102。
家坤翁言鲁公任抚州刺史仅两三年,然“政教入人者深矣”,盖其英姿忠烈,不只限于其治理郡县的功绩。家坤翁于景定四年(1263)“扶筑其堂,新其甃,汰其梁柱之挠且腐者,作室于后”[3]101,书匾“鲁公堂”,并作《景定重修鲁公堂记》一文表达人应“守谊居正光明卓荦”[3]102,希望同辈慎重选择,心中应长存鲁公忠烈之节。
第四,重建瀛洲亭。宋嘉定中,州守林岊建瀛洲亭,并书有《瀛洲亭记》。该亭后逐渐破败坍塌,危稹重建之,沿其旧名。家坤翁不仅重修瀛洲亭,并以瀛洲之名,引出宇宙中诸多“名存义失”的现象:
碑志云:始嘉定间,郡守某、仓使某后先从三馆来,既成斯亭,遂扁斯名。吁!有是哉。故老云:夙有此亭,忘其所始,久而圮,君实兴之,名则因其旧。当时好事者游台郡间,相妩媚有此言,其然乎?自列子驾其说于夏革,蓬、瀛之名遂著。其山凡五,在渤海东,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根无所著,随波上下,将流西极。帝使十五鳌举首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五山乃峙。有大人一钓连六鳌,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北极。此夏革所为说。瀛洲盖五山之一。城中有五峰,州始占其一,又居城西,瀛洲之义,当起于此。嗟夫!宇宙间名存义失,岂惟斯亭![3]105
家坤翁警戒众人,凡事不可听之即信,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世间万物的真伪要有质疑之心,不可人云亦云。
第五,修葺三清殿。景定癸亥(1263)秋八月,连日高温,太阳暴晒,稻苗枯槁。家坤翁忧百姓之忧,登坛祭拜,百拜叩头,祈求上天降雨。果然“礼成而雨”,家坤翁便率州中文武群官集于三清殿敬谢上天。他环顾四周,殿内梁柱腐蚀毁坏,亦不能遮风避雨,十分破败,于是便从财政拨款,重新修整了三清殿。
第六, 重修州学大成殿。大成殿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建成的祠庙。家坤翁对圣人之功极为推崇,在“周辙东,王迹熄,天所畀,圣所膺,分裂晦,莫知所主,纲沦法斁,天人始二”[3]109之时,孔圣人匡扶伦理纲常,使得秩序井然,“躬天道,无天位,以有其事,退而阐明至教,述作圣经,用宗主三才,用范围有极,用迓续帝统。然后君臣父子以定,天地万物以位有,山川河岳以流峙,日月四时以代明错行,天经地纬,帝德王功,以昭明不坠”[3]109。然临川虽为江西声名文物之首,文人辈出,大成殿却“梁柱屏障,牖户几席,黝然凝尘,惧弗称命”[3]110。家坤翁为之心痛,遂将大成殿重新修缮布置,愿临川后世之人感圣人恩德且怀圣人之心:“今而后博五氏之文,归约于夫子之礼,浚临汝之流,以通乎洙泗之源,明此之理,渺彼之欲,敬此之义,羞彼之利,典章贵,防范尊,人文兴,天象应,千载一日,去圣一心。”[3]110
第七,修建明润阁。临川地理位置高峻,四周皆是低平之地,丽谯楼可以东望,瀛洲亭可以西望,五峰堂可以南望,皆一览无余。北面原为望楚台,长久废弃,成为摆放兵器的废阁,视野阻塞,与其他三处不能相通。因此,家坤翁将其中杂物安置他处,将此处加以补缀缮治,命名为明润阁。修葺后的明润阁,“晦光窒通,上著下察,如寤如醒,曰明曰旦,藩篱洞彻”[3]111。明润阁之名起源于郡志“是邦上应于文昌,质诸史,其星在北斗魁前,大小明润齐,则天瑞臻。嗟乎!此政理也。今吾阁位乎北,文昌斗魁实在其上,宜遂扁曰‘明润’”[3]111。家坤翁亦通过明润阁阐述了为政之道,“夫为政,未有弗烛厥理能施其泽者,明有窒则润不能溥”,为政只有去“心欲”,而存“忱静”[8],“莫之为而为”,才可达到“无求于星象而象自应,无求于天瑞而瑞自臻”[3]112的境界。
3 临川名迹散文小记
家坤翁十分热衷于临川的文人雅迹,并常日流连,以散文记之:或考证源流,对其名号加以梳理;或托物寓理,通过眼前之景抒发人生哲理,厘清妄言。他的散文纪事论理,逻辑严密,富含哲思,才情动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3.1 《玉茗亭记》
玉茗,原是山茶花的美称。据《临川县志》记载,玉茗花最早被发现乃是在北宋雍熙年间。当时,郡守周申甫在东园发现一支白色山茶花,大为赞赏,称为奇花。待崔仁冀接任郡守,对周申甫所言之奇并未深信,及其观之视若琼花,取名为“玉茗花”,并作《玉茗花赋》。黄庭坚撰有《白山茶赋》,赞其圣洁[9]311。曾巩也有《以白山茶寄吴仲庶见贶佳篇依韵和酬》之诗,用身体官能的感受表达景观审美的愉悦感[10],称玉茗花“山茶纯白是天真,筠笼封题摘尚新。秀色未饶三谷雪,清香先得五峰春”[11]。陆游亦有《眉州郡大燕醉中间道弛出城宿石佛院》一诗提到玉茗花。
玉茗亭,正因玉茗花而得名。家坤翁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与玉茗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玉茗亭记》:“玉茗亭,在府署西。亭前种玉茗花大如山茶,而色白黄心绿蕊,人以比之琼花。亭前有石耸立如笋,呼笋石亭。北有横秋阁,阁下为春草亭,皆宋嘉定中建。”[6]640玉茗“薄有香气,貌近薝卜,远于山茶,繁秾而幽野,如逍遥肥遁者”[3]99。“得乎乾坤之清体”,赞赏玉茗花不争不抢的特质;“不与诸年少争春风”,抒发与世无争、安然自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追求。“琼花者,与此花媲美。彼处康庄,有闻于世。此居遐远,人遂忘之,若有所歉。是不然。琼花困于采掇,根非其故,此花退然自安,至今无恙。”[3]99家坤翁通过二者的比较,阐释只有长怀清净隐逸、超然恬静的人生态度才能够独善其身,保持本性初心的哲理。
3.2 《羊角石记》
《临川县志》中记载:“抚州谯楼前,左有一卷石,长三四尺,高二尺许,郡人谓之羊角之洞天。相传有人自青城山来,扣石暂开,得入见洞府。云所谓羊角者,郡城形势南来东行而转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所以有角之名。宋绍兴中,守王秬覆以小亭。后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视之,未数尺,大风起穴中,惧而止。”[7]530
家坤翁考察碑志,对太守危全讽迁抚州郡城至羊角山,将州门和谯楼并列面向东且门在右侧、楼在左侧之布置产生怀疑:“戟门直南地甚夷,可达康庄。何州门转而东,谯楼不遂为门而别为台?”[3]100他否认危全讽因洪水之故而将谯楼地势拔高,认为如此布置的真实原因是抚州城中“包络丘坟,其脉南来,东绕西出,渐起为子城,又西突起为州治,势昂如首,州门谯楼位焉”[3]100。“为台不门,欲培养其生意也;鼓角临之,欲鼓动其生意也。求之天地间,阳气鼓动则成雷,在地中为复之亨,出地上为豫之利。”[3]100即州门、谯楼和羊角石的布置,皆是为了促进抚州阳气、生气的产生与繁衍。而唐人深谙此道,因此“始疏剔之,寻绕以墙,阑以石”[3]100。
3.3 《金石台记》
金石台,又称金石山,处于崇仁河和抚河交汇处,两岸水道险峻,山峦耸峙,与五虎山相连,与玉石山遥相对望,是隋唐时期临川旧址。古人迷信金石台,认为其能去凶避邪,将之视为游览胜地。
关于金石台,民间有“金石台分宰相出”之谶语,言王安石与晏殊皆是因为金石台的祥瑞而能拜相。家坤翁对此大为谴责:“夫山川钟秀,人物挺生,有开必先,理气之常,何必诬以为谶,念此恍惚怪神语哉!”[3]104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家坤翁先以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说明凡事皆有迹可循,无迹可查的“化神”之妙皆存在于“形气”之中:
化神之妙,存乎形气中。化神无其迹,形气则有其先,惟情明不汩者,能静而得之。盖天地之形气即吾之形气,天地之化神即吾之化神。在躬在两间者,同乎清明,则二气五行之良知良能,交举而互发,四体之动,庶征之若善不善,必先知之。然非有惊世骇俗之事,语其近要,其凡亦夫人与知与闻者。故风雨霜露,春秋冬夏实先之;庶物露生,神气风霆实先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实先之;生甫及申,嵩岳降神实先之。化神密运之理,气形相因之用,著察呈露,昭昭莫掩[3]104。
在家坤翁看来,天道的“化神”与“形气”和人体的“化神”与“形气”运行机制一致。在天地之间和自身形体之间,阴阳五行所存在的运行之道皆有其先兆,“化神”的规律与“气行”的轨迹相通,故而得出结论“是知至诚前知之道,不出于日用躬行之间,万事万物之变,不外乎一心一身之常也”。一切有预见性的事情都出于“日用躬行”之间,万物万事的变化,也不过是心与身的日常运行。家坤翁以金石台为引,阐述了“化神”与“形气”、“天地”与“人体”之间的关联,希望通过圣人之言破除虚妄迷信,引导民众多读儒家经典,切勿迷信神鬼之书。
3.4 《书拟岘台记后》
拟岘台,位于江西临川抚河之畔,古与河北幽州台、山西鹳雀楼、赣州郁孤台等齐名,始建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
至景定年间,家坤翁再次修缮拟岘台,并作《书拟岘台记后》。家坤翁首先提出“事物万殊,理则一致,耳目异趣,心则同归”[3]107的观点,认为世间万物形态各殊,以物观物,东南西北各地山川乃至风土人情都是不一样的;若以理观物,大到日月星辰的运行,小到草木昆虫的生息又都是相同的,“盖理之所著,心之所察,通天地等一胜慨,合人我共一胜实,非彼疆此界可得而私其同异,非管窥蠡测可得而囿其广狭也”[3]107。
最后,家坤翁言明自己的主张:修缮古迹文物本身,不如将精力用在政治开明与民众教化中去;欲要传承其精神,与其仿照其游玩观赏之迹,不如仿效其治理民众之道,只有这样才不会受耳目事物的束缚,而能与天地造化一同生生不息,千百年后,亦能长久为人所传颂怀念。家坤翁进一步提出,不必局限于岘台,亦不必局限在豫章大地,天下大夫师长,凡适宜民众学习其精神的,均可效仿,即“吾之扶植斯台者,不以畚筑,不以陶瓦,不以户牖矣,愿相与心领而意会”[3]107。
3.5 家坤翁的记文之道
家坤翁深谙记体散文撰写之道。第一,立意高远。所谓“必有一段万世不可磨灭之理”,无论是《金玉台记》抑或是《书拟岘台记后》,都颇具宋代散文之风,借题发挥,纵横议论,同时融入强烈的自我主观意识。第二, 兼重学术考证。如《羊角石记》,考证县志,以驳论前人观点发端,进而提出自己观点,复以议论收尾。记体散文实际成了其考察论证的过程,逻辑缜密,思想博大精深,论据合理,观点鲜明,与苏轼《石钟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12]。第三, 兼顾文采。家坤翁虽注重说理议论,但却十分注重文采,所作长篇短章,皆具有优美的节奏和旋律,而且善于将抽象的事物或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如,“故风雨霜露,春秋冬夏实先之;庶物露生,神气风霆实先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实先之;生甫及申,嵩岳降神实先之。化神密运之理,气形相因之用,著察呈露,昭昭莫掩”[3]104。这是以自然界的现象说明“化神”与“形气”之间的关联,深入浅出,通俗形象。
4 结语
家坤翁虽然不是临川人,但与王羲之、颜真卿、陆游等诸多曾在抚州(临川)为官的外籍名人一样,为临川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为政期间不仅厘清奸邪,更是在民众教化与精神传承等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心力。《景定临川志》的修订使得众多临川文化典籍与历史记载并未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对临川古迹的修缮更是彰显了临川文化与精神;其托物言志的散文亦抒发了其对临川文化与治国理政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