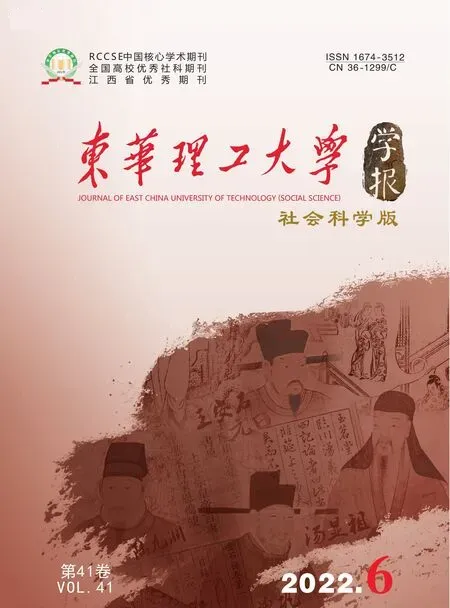老庄“道”论本体及其美育启示
王英娜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道”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最早由老子提出,并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话语,其本体涵义指向了对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庄子在继承老子“道”论基础上,使“道”论本体呈现出从宇宙本体向个体存在的推进与探求,体现了其对生活中有限性、规定性等现实的超越与探索。在西方,本体被认为是一种通过抽象思维而获得的超经验存在,其往往把本体与对象放置于对立的结构中,因此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属性”等本体论思想,都具有在主体或客体中偏执一端的本体特点。老庄思想不同于西人思维(1)由于文化思维的差异,中西方对本体论的认识明显不同。如果说西人对本体的认识往往偏执于主观或客观一端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越主、客的合一性特点。如张岱年认为老庄本根论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不以唯一实在言本根,不以实幻说本根与事物之区别。二,认本根是超乎形的,必非有形之物,而寻求本根不可向形色中求。三,本根与事物有别而不相离,本根与事物之关系非背后实在与表面假象之关系,而乃是原流根枝之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8页。)孙正聿指出本体论有三重内涵:“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孙正聿:《简明哲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老庄的“道”论本体即是如此。,其具有以“道”为核心消解对立与偏执的道家文化特质。“道”的本体理念不仅是对宇宙存在的终极探索,而且亦包含了对人的理性关怀,其旨归是实现人与世界、他人、自我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家本体内涵亦为当下的美育本体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资源。
1 “体用合一”的老子“道”论本体
关于老子“道”论本体的讨论,在历史上主要有以王弼为代表的“无”本论思想和以裴頠为代表的“有”本论思想,后人分歧大都沿承于此。随着老子出土文献的问世,一些新的且较可靠的古本材料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依据,于是对于古人讨论的传统话题也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老子通行本文献与古本文献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老子的“道”论本体并非单一性存在,而是潜含着一种“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从世界存在的角度,他对其展开了有、无一体的讨论;从行为实践的角度,他则突显了人道与天道、自然的一体。可以说,老子的“道”论本体思想不是纯粹的思维理念,而是具有兼顾宇宙论与社会论的“体用合一”的本体特点。
《道德经》第一章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1-2
此篇是理解老子“道”论本体思想的重要文献。在通行本中,老子开篇言“道”。河上公将此篇命名为“体道第一”[2]1。对于“道”的理解,从造字法来看,它是一个会意字,金文从行从首,本义是在路上行走之意。《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3]76“道路”是其最基本涵义。这种本义在先秦时具有较普遍的使用,如:“履道坦坦,幽人贞吉。”[4]90“道之云远,曷云能来。”[5]47“行道迟迟,载渴载饥。”[5]219在本义基础上,它还有多种引申义。段注言:“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3]76这是由行走的道路引申至思想领域,在思想中可明理、通达的路径,即“道理”。当它引申为万事万物在生成运行中所应遵循的轨迹时,便具有了不可言说的规律之意,而这种规律之道,既可指向宇宙万物,亦可指向日用伦常。如“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人道恶盈而好谦”[6]116“顺理而不失之谓道”[7]557等。对于这些思想的表达,“道”亦可引申出言说之意,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5]66“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8]315在老子笔下,“道”则被赋予了贯通天地人的世界存在理念。“道”的涵义突破了文字训诂所规定的释义局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范畴,并成为道家文化的核心理念。
老子开篇对“道”的界定呈现了“道”论本体的认知内容。他将“道”和“名”对举,明确指出“可道”“可名”者并非“常道”“常名”。对此,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1]1王氏理解侧重表现“道”的无形特点,但实际上“道”并不仅限于此。高亨言“此二语实为其全书而发”[9]1。老子正是通过对“道”与“名”的讨论展开了世界的整体以及本体的世界。对于世界的认识,人们往往始于具体的名象,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可表述的名象与言说是否能恰切地表现出世界真实的存在?老子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他进一步探讨了“无名”与“有名”关系,其对“名”的辨析即是对“道”的诠解。可以说,“道”统摄的范围含纳了天地万物。
为了恰切呈现“道”体的复杂性,老子对“道”亦给予了多视角的阐释,如“道”作为宇宙存在的描述;“道”与事物变化之间的关系;“道”与人的处事方式、政治经验、个体修养等之间的关联,等等。对于老子“道”论本体,人们往往习惯将之与“道”所指向的宇宙本体直接等同,认为“道”的本体仅是一种超越实体的本源性存在,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体用合一”的本体存在。如《道德经》第十四章对“道”的描述是夷、希、微的混而为一,它是一种“无物”的状态,即“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同时,它亦具抽象的规律性,即“道纪”,可发挥“御今之有”的作用。第四章则更为明确,“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直接从“用”和“宗”的视角对“道”展开状态化的呈现。二十一章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是其对“道”论本体的概述。在这里,他提出了与“道”相应的“德”的概念,此处之“德”与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不同,它与“道”相似,亦属于宇宙自然的抽象范畴。“德”在天地万物的生成、生长中具有与“道”相辅相成的作用。正因为“德”的存在,无形之“道”在恍惚中呈现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等存在状态。“德”亦被老子赋予了本体地位,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136-137。由此,我们亦可推知,老子的“道”论本体其实是“道德”本体,而老子的“道德”正如刘恒健所说:“乃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即一种超越伦理道德的本源性的真正的道德。”[10]在老子思想中,“德”兼具本体和功能,并直接关系到生命的本质与意蕴。老子对“德”的思考超越了周以来以伦理视域进行界定的局限,“德”有了“玄德”的重要内涵,“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168。“德”将外在的礼仪道德引申至内在的心体,最终使人或物返归的是真朴与自然的存在。在老子笔下,“德”作为本体,呈现出了其义涵的多层次性,正如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1]93在此,老子“德”的心体最高层次与“道”境相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是万事万物依循于“道”的理想状态。高亨言:“上德之人,但求反其本性,不于性外求德,而终能全其本性。”[9]85也就是说,上德之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通过顺其自然而实现一种合于本性的存在。除“上德”外,老子亦提出了“下德”,而下德“无为而有以为”的特点,意味着其从“圣人”转向对普通人的关注。因此,有德者亦包括具有崇高品德的普通人,而他们与上德之人的区别即在于其是“性外求德”,故而执守于外在“德”的形式。如果说上德之人是身、德合一,那么下德之人则是身、德为二。老子给予“德”的本体地位是“失道而后德”,这看似在说“道”与“德”的先后关系,但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体用关系。老子把道德修养分为六个层次,即道、德、仁、义、礼、智。其中,“道”“德”可成为万物与人的存在本体与生命本体,而后四者则是对具体人道思考的层层推展。可以说,老子通过对“人道”的讨论与展开,使之与“天道”相和谐,体现了“道”不离人、天人和谐的认识与理想。
总之,老子的“道”论本体体现了与经验现象的关联与超越,同时,它亦试图通过理性直觉去把握万物存在的本体与生命存养的本体。老子对“道”论本体的思考拓展了儒家以伦理为主的人的视域,并将之溯源至天地宇宙的自然之“道”。这种本体意向性的拓展,不仅体现出老子对人与世界终极存在的探求,而且体现了他对生命存养世界的关怀。他试图通过“道”体的确立,在生活世界的多样性、矛盾性中寻求恰切的平衡与张力。老子的“道”论本体不是纯粹抽象的客体存在或主观理念,而是一种具有体用合一的至善性指向,因此这种本体包括了存在论与实践意向性的统一。
2 庄子“道”论本体的发展及审美内蕴
“道”在庄子思想中是一个内蕴丰厚且意义深邃的专有理念,因此学界对于“道”论本体的理解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道”是对物质存在的超越,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的学者则认为“道”侧重的是对主体精神的超越,应是主观的存在;也有学者认为虚无是“道”的本体,等等(2)冯友兰认为“道即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1页。)侯外庐认为庄子的“道”的学说,“完全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它是“超空间的绝对,它超乎物际,在一切物质之上而又似乎在到处显其幽灵。这种‘道’是人们不能言说的泛神”。(侯外庐:《侯外庐及中国思想通史学派论庄子》,见胡道静:《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123页。)张文勋认为庄子“道”的本体是虚无。(张文勋:《庄子思想的现代解读》,《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可以说,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对“道”论本体的认识。对此,笔者以为,庄子的“道”论本体继承了老子“体用合一”的本体理念,在内涵结构的建设上则具有了存在论、认识论、审美实践论相统一的本体论特点。
关于宇宙本体之“道”,庄子继承了老子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它既是一种终极的存在,同时亦为万物生成之源与存养的根据,这种“体用合一”的理念即体现在庄子对“道”的描述中。如《庄子·大宗师》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1]225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道”自为根本的存在性、永恒性,以及无形的超越性,而对于“道”作为万物之源的探索,庄子的阐释也更为形象与生动。在思考理路上,他也突破了“有”与“无”较概括性的单一层次展开,并尝试运用逻辑思辨推衍出可绵延至无穷的终极预设。如《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1]76,即体现了其对万物存在的逻辑性溯源,这种方式也呈现出庄子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特点。在“道”“物”关系上,如果说老子重在从生成论的角度追溯“物”以“道”为本源,那么庄子则认为无形之“道”与世界万物有形的存在同为一体,道与物共存于有形之中。《知北游》中东郭子曾问“道”于庄子,庄子言“无所不在”,并通过“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等可感知的最卑下的物象,指出“道”亦在其中,从而说明“道”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平常处。与老子相较,庄子使“道”与“物”的关系更加密切,如果说老子“道”论本体的“体用合一”主要是以“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展开,那么庄子则将这种体用关系进一步下行,即明确指出“道”与“物”之间的体用关系。可以说,这种“道”与物象的直接关联为“道”体在实践论层面的存在与价值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认识论层面,老子“道”的提出,扩大了人们对本有世界的理性认知,对于万物本源的抽象存在,老子以“道”作为思维中可通过逻辑推理而援取的概念性表达,使之成为认识论中的最高层级。“道”论本体的探索使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也达到了更为抽象而深刻的程度。庄子继承了此思想,并在其基础上以“道”的视角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继而提出解决知“道”之难的理论设想。从“道”的本体特点而言,它是不可言的,因此在《庄子》中,有不少寓言故事都设计了问“道”的情节,而其回答无外乎“有”与“无”两种极端方向,或者是寓于万物而无处不在,或者是“不答”“不知应”“吾恶乎知之”等,看似矛盾的两种回答其实在庄子这里具有内在的统一,即道、物为一的“道”体存在。因此,对于“道”的认识,我们要突破人本有的认知局限,对此,老子亦曾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王弼注:“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1]178可以说,人由于天赋、阅历、环境、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其认知能力的差异与局限,因此每个人的认知都具有较强的主体性特点,不免对本体之“道”构成遮蔽,庄子“梦”与“觉”的一系列相关寓言即是针对于此而展开。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对“道”的本体认知呢?庄子指出认识“道”的根本在于把握“道枢”。何谓“道枢”?庄子言“彼是莫得其耦,谓之道枢”,也就是说通过消解万物之间彼此存在的差异、对立,才能实现认识的最高境界。与此相似,庄子亦有多种表达,如“齐物”“两行”“天钧”,等等,可见庄子对于“道”体认知的深刻思考。“道”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从内容上看是不同的,但如果从最根本的性质看,两者则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一致性。具体而言,“道”论的本体存在决定了认识论终极解释的方向,道、物合一的“道”体特点决定了对常识认知方式的反思及如何实现超越的探索。
道、物合一的“道”论本体不仅在世界存在论、人的认识论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庄子亦将之拓展至人的审美实践之域。如果从实践的视角解读老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本体之“道”作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应当依循的原则,因此体现出人的言行应与“道”相合的自然、无为、真朴等特点。他要追寻与执守的是人所本有的真性情,这实际上是欲将本体之“道”落实在“人之道”的生命与生活的本体价值中。虽然老子对人道的关怀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但他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关怀在庄子这里得到了发展。同时,庄子亦将“道”的本体探求与人生中的审美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人的个体生存与生活预设了一个理想的存在境界。正如李泽厚所说,庄子与老子大不相同之处是“他第一次突出了个体存在”[12]145,尤其关注了人的生命与精神。其实,除了内在境界之外,庄子亦强调了其与生活合一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因天人合一而具有实践美的艺术世界。有一些学者认为老庄的“无为”主张是消极的,远离实践的,其实不然。“无为而无不为”即是老庄所主张的生活实践方式。“无为”的精神状态并不妨碍人“无不为”的实践行为,正是这种“无为”的精神状态使人的实践生发出美感,而精神与实践的合一使人的现实生活转变成为一种艺术生活。如果说,老子是这种精神与实践相合一的实践论的提出者,那么庄子则对其给予了实践方法、路径的探索,并使之呈现出充满美感的实践过程与实践境界。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美的、艺术化了的实践中,人实现了生命与生活的自由。
庄子审美实践论的关键在于他将对“道”的本体认知与实践对象融合为一体,而这种审美实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人的本体精神境界;二是对实践对象的本体认知与实践行为合一的状态。两者在“道”体层面的交融将会使实践主体具有一种达至理想与自由的审美实践境界,而主体所呈现的实践行为亦是一种美的活动,是生活艺术化了的实践。在《庄子》中,关于道、技结合的寓言最能体现出这种实践理想的审美境界与价值。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看似是一个关于解牛的技术实践,但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技”的问题,正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庖丁已将解牛的技术实践上升至“道”的境界。对于从技至道的提升,他通过学习解牛的过程给予形象说明。初学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这说明他对于实践对象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现象,并未有深入的了解。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可知他对于实践对象已有透过表象见其肌理的能力,较之于初学时,已有对客观对象认知上的进步。当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之止而神欲行”之时,其已达至“纵心而顺理”的合“道”之境。这则寓言所呈现的不同阶段,虽同为解牛实践,却有着技能与技艺的差别,其关键在于是否达至“道”境。在实践中实现“道”境,一方面需要解牛者能够达至与“道”相通的心境,或者说作为人的主体要有一个最高程度的自我本体体认的境界。另外,对于客体对象的理解,也要达到对其本体的认知,从而实现解牛时“依乎天理”的“道”境。可以说,庄子的实践论实际上要实现的是人的自性本体与实践对象本体的合一,通过两者在“道”的本体层面的交融,继而达到现实世界中主观审美境界与客观审美实践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根本自由与生活的艺术化。
总之,庄子在继承老子体用合一的道德本体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呈现出道物合一的特点,同时在存在论、认识论、实践论方面亦有新的开拓。他尤其重视对人的终极关怀,不论在精神世界,还是实践领域,都给予了更深刻的思考,并发展出以“道”论本体为核心,宇宙存在论、主体认识论、审美实践论融为一体的“道”论本体思想。这种承扬不仅蕴含着对世界、生命的深刻思考与体认,而且对于人的生活实践亦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3 老庄“道”论本体对美育建设的启示
“美育”一词,早在徐干的《中论》就有提及,即“美育人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13]115。他认为“美育”与人之“艺”具有直接关联,并强调了文、质兼备的重要,如此才可达至“体全”,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思想。虽然汉魏时就已有了“美育”的说法,但在当时并未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的美育思想。我国美育理论的自觉建构始于近现代学者,他们欲通过美育国民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而他们的理论来源即是西方的美育理念。在西方,“美育”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德国理论家席勒。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次将“美育”界定在情感教育范围内,并进一步提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14]71。同时,他亦指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14]4。在席勒的美育思想中,最关键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情感”与“自由”。他所说的情感是一种愉悦的心境,其所说的自由则是与当时人性异化相对的人性的解放与自由,而实现途径则是“使他成为审美的人”[14]325。在中国,道家思想多言“自由”,但其与西方不同,有着中国人独特的体悟和探索,这对于西方人所言的美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启示。尤其在美育本体论建设方面,老庄的“道”论本体思想,将对我国美育本体理论内涵的建构提供重要借鉴。
在老庄“道”论思想中,均谈及“美”。如《道德经》开篇明“道”之后,就言及了老子对“美”的认识,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6老子将“美”放置于具有相对性、辩证性的事象之中,而其对美与恶关系的态度,正如帛书本老子所言:“美与恶,其相去何若?”(3)郭店楚简本:“美与恶,相去何若?”傅奕本:“美之与恶,相去何若?”(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4页。)这其中蕴含了老子以超越对立的“道”论视角认识美。因此,他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191虽然老子直接论述美的内容并不多,但其中却蕴含了“道”与美关系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刘纲纪所言:“老子的美学同他的哲学是不可分地互相渗透在一起的。在老子看来,‘道’的自然无为的原则支配着宇宙万物,同时也支配着美和艺术的现象,是美与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15]195在老子对美的认识基础上,庄子则有所继承和发展。如《知北游》:“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即是对老子美丑对立关系的进一步阐发。此外,庄子亦将美与天地大道构成关联,并明确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成玄英疏曰:“夫大圣至人,无为无作,观天地之覆载,法至道之生成,无为无言,斯之谓也。”[11]649对此,叶朗亦指出:“‘道’是客观存在的、最高的、绝对的美。……天地的‘大美’就是‘道’。‘道’是天地的本体。”[16]111可见,美与“道”之本体的相通,而“无为”是美的本质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的“道”论并不仅仅指向宇宙天地的最高存在,而是将宇宙存在论、主体认识论、人生实践论融为一体的“道”论本体思想。庄子之“美”并不仅仅是以“无为”作为与“道”相通的“大美”,它还包括了对个体自由之美的无限追求,其中既有精神上的追求,亦有实践上的追求,庄子的美育思想亦是如此。可以说,庄子的自由思想是其不同于儒家美育思想的关键处,而“自由”作为庄子“道”论本体的旨归,正是其对美育思想建设最具启发之处。
席勒曾说,美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的感性能力和精神能力的整体达到尽可能有的和谐”[14]63,而老庄思想中实现“道”境的体认亦是对这种“和谐”状态的探求。对于如何实现至美“道”境,老子主张“自然”,万物的生成有其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人的返璞、归真也要合于自然。这种自然并没有已规定的运动变化轨迹,其主要指向的是不受外物与他人的干涉与束缚,它是自生、自发、自由的状态。在庄子思想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合于自然而归于“道”的思想,但庄子更侧重的是以人为主体对万物、社会的关注。他以“道”体为核心融通物我,使人从外在的分别、局限、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的生命本体与对象本体在“道”体境界中相遇,这种物我合一关系的“道”境,为美育本体内涵的建构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启示。为了与本体“道”境相通,庄子提出了“体道”方式。如在《知北游》中,庄子言:“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11]665可见,“道”不可论,但可体悟。体悟“道”不仅是一种虚静、冥思的状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亦可通达体“道”之境,而后者恰恰是前者在现实境遇中的应用与延伸。它将本体之“道”从一种实体化的存在,丰富为一种具有立体结构的关系,从而将外物内化,将主体物化。在“道”境中,人实现了超越现实的分别与束缚,达至身心和谐与行为实践的审美与自由。主体本性、客体存在与“道”境审美经验的融合,共铸了道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审美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了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而美育的旨归也蕴含其中。因此,从道论本体视角审视美育,其根本在于实践与“道”论本体的融合。具体而言,在践行中,既要有对世界本体存在的认知,也要融入对自我生命本体的体悟。体认“道”境,不仅是纯粹抽象的终极理念,也不仅是对实践对象客观存在的终极认知,而是需要将之运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在物与我的关系中实现齐等的交融与和谐。生活实践、艺术实践本自蕴含着对实践主体提升自我修养的内容,而当其将内在的精神境界与外在的实践技能合为一体时,实践便不再是单一的现实行为,而是成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实践对象之间的关系行为,其被赋予了具有哲学性、审美性的艺术至境。这种思想理路将“道”论本体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继而增强了生命存在的质感。因此,如果从本体论角度对“美育”给予重新审视,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美育是在生活实践中学会对美的认知、体悟与追求。具体来说,即对美的客观艺术对象的本质认知,对美的主观本体“道”境的体悟和对美的实践自由“道”境的追求。老庄的“道”论本体对美育的重要启发,即在于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实践中达到这种本体性的至美“道”境,并以此获得人的真正自由。
总之,我们一般所说的审美,指的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而老庄思想中体“道”境界的美育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即人的生命本身蕴含着美,实践对象潜藏着美,实践活动呈现着美。在“道”的层面上,人的自性本体的对象化,发掘了物与我美的真谛,并在实践中构成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审美体验。在现实生活中,体“道”的过程既是行为实践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生命本真的体认不断展开的过程,其中的审美体验超越了外物刺激下的喜怒哀乐,进入了一种本性自由的精神愉悦与超脱。老庄对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是审美的、诗性的,这种美感是物我交融后自然的生成。马克思曾说,理论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人的根本而言,就是“人本身”[17]10。可以说,老庄体用合一、物我合一的“道”论本体思想即体现了对“事物的根本”、对“人本身”的探索,而且不离生活,寓于实践,以此获得人存在与实践的自由。同时,对于人格的塑造亦可开拓出具有崇高天性之美的生态化追求[18]。在美育方面,老庄的“道”论本体启发我们应超越工具理性,增强对客观事物及人本性认知的能力,并将之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突破现象,在本质的层面实现更具深刻性的审美教育。
4 结语
老庄的“道”论思想一脉相承,他们的“道”论本体并不仅仅指向宇宙万物之源的本体性存在,而且还与经验现象融为一体。如果说老子的“道”论本体具有体用合一的至善性指向,其包含了存在论与实践意向性的统一,那么庄子则在其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尤其在对人的终极关怀方面,不论在精神世界,还是实践领域,都给予了更深刻的思考,并发展出以“道”论本体为核心,宇宙存在论、主体认识论、审美实践论融为一体的“道”论本体思想。他们对“道”的论述使“道”体呈现出无限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其敞开的视域既有对宇宙客观存在的探索,也有对内在无限丰富情感空间的思考,并将其提升至终极理念的世界。更使人欣喜的是,其将“道”体下行至人们的实践生活,为人生的艺术化、实践的审美化提供了理论根本,并通过“道”论本体思想体现出其对生活世界的多重关怀。老庄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厚的“道”论本体内容,启发我们在美育实践中应超越物质现象看到内在本质,超越工具理性看到人的自然本性,超越生活的种种束缚达至审美实践的自在自由,这无疑对当下美育本质的思考具有重要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