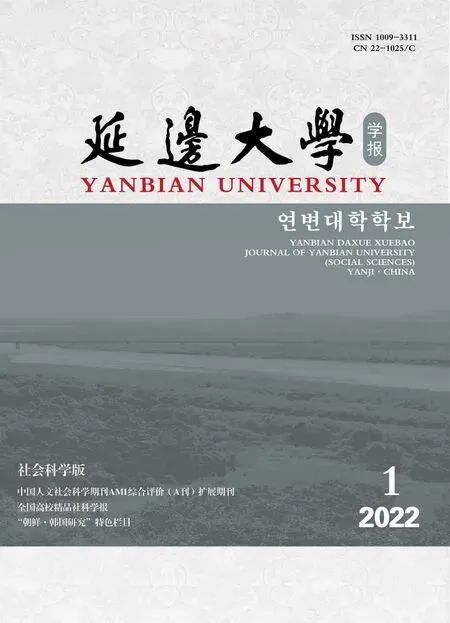试析韩国近代启蒙语境下的韩汉文混用体翻译
——以梁启超著作译文为中心
韩 银 实
日俄战争以后,受日本控制的韩国开始了以恢复国家主权、开启民智为目标的爱国启蒙运动。为启迪民智、唤醒民众觉悟,启蒙期(1)本文中的“启蒙期”指1894年至1910年间韩国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的时期。韩国的各大报纸杂志开始大力宣传进步思想,为民众介绍近代文明。1910年以前,韩国主要通过中国文人翻译或撰写的文章来学习近代先进知识,其中梁启超的论著占相当大的比重。启蒙期爱国志士们争相译介梁启超的文章,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翻译热潮,启蒙期也因此成为了韩国翻译史上罕见的“黄金期”。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8页。通过“翻译”行为应为读者呈现“另一种”语言文字,即源语种与目的语种应为两种不同的语种。但在19世纪末的近代启蒙期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韩汉文混用体翻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是因为这种翻译策略下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仍保留着汉文原文的语言文字,并未完全以目的语语种呈现。显然,这种“翻译”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翻译”不同。但正是这种混用源语种与目的语种的翻译方式成为启蒙期的主要翻译体,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为当时的韩国社会注入了近代的新鲜血液,加快了韩国启蒙的步伐。
事实上,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是与当时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翻译方式。进入近代启蒙期,韩国开始了“脱离汉字,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进而实现言文一致目标”的运动。即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选择用韩文体译介汉文书籍的文人也仅占极少数,绝大多数文人选择用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外文书籍,为民众译介近代新知。这一事实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这种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翻译方式为何能够承担起翻译重任,甚至影响了启蒙期的整个韩国呢?本文将以语言学视角考察梁启超著作译文的特点,并以此为事实依据,分析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方式得以盛行的原因。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在韩国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之前被称为“方言”“谚语”的韩国语被注入本民族与国家精神,成为了真正“国语”的起始阶段便是使用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阶段。而在韩汉文混用体文章中占较大比重的梁启超著作译文是研究这种翻译方式的特点及发展过程的重要资料。
一、梁启超论著在启蒙期韩国的译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接触到了大量日译西书。他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汲取了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并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著述工作。梁启超的进步思想以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为载体在中、日、韩三国风行一时,广为流传。
梁启超的论著自19世纪末传入韩国,一时掀起了译介热潮。1899年,韩国报刊《皇城新闻》率先连载了梁启超的文章《爱国论》。其后,《大韩自强会报》《独立新闻》《时事丛报》《新韩民报》《大韩每日申报》《太极学报》《朝阳报》《帝国新闻》《共立新报》《大韩协会报》等报刊与《西友》等杂志也陆续连载了梁启超的文章。
在近代启蒙期,韩国共有15家报纸杂志连载了梁启超的原文或韩国文人译文,文章共达50余篇。到了20世纪初,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已无法满足韩国读者对梁启超进步思想的渴求,于是,玄采、周时经、李相益、全恒基、张志渊、申采浩等人又相继翻译、出版了梁启超的《清国戊戌政变记》《越南亡国史》《饮冰室自由书》《伊太利建国三杰传》《中国魂》《匈牙利爱国者葛苏士传》《新译生计学说》《民族竞争论》《十五小豪杰》等10余本单行本。这些单行本在当时受到了韩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越南亡国史》一书被多位文人翻译,又被多次印刷、发行,为启蒙期的韩国社会指明了救国方向。此外,韩国文人全恒基翻译的《饮冰室自由书》一书收录了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64篇文章,为韩国学习社会进化论,树立自强思想、新民思想、民族主义历史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梁启超论著在韩国风靡十余年,一个外国人士的论著被如此大量、频繁地刊登在韩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又被多位文人编译成书并出版,在韩国启蒙期仅梁启超一人。
二、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
启蒙期文人翻译梁启超著作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韩汉文混用体翻译,第二类是韩文体翻译。在传入韩国的梁启超著作中,除个别文章是直接以汉文原文形式出版外,其绝大多数是通过韩国文人翻译、加工后才得以出版发行的。在当时,用韩文译介梁启超文章、书籍的译者仅占少数,大多数译者都选择了韩汉文混用的翻译方式。
(一)韩汉文混用体翻译
韩汉文混用体翻译顾名思义就是混用汉文与韩文的翻译方式。在近代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承担起翻译重任,作为供应“近代新知”的载体,为启蒙期的韩国注入了近代文明的新鲜血液。启蒙期的韩汉文混用体与早期韩汉文混用体虽都是汉文与韩文的混用体,但二者存在显著区别。早期韩汉文混用体为翻译汉文书籍而生,除个别固有名词、动词词根使用了汉字以外,其他一律使用韩字韩文,语序也完全实现了韩国语语序,译文中无任何汉语语序的词组或句子出现。而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仍保留着大量汉语语序的词组或句子,呈现出汉语语序与韩国语语序掺杂,无规律可循的特点,对“问、有、知”等实际语言生活中的高频词,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也选择了避开本国语言中现有的“-,-,-”等固有词,而是选择了“问-,有-,知-”等汉语词附加韩国语语尾的形式。
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又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留了较多原文语句,仅在句末或句中添加少量韩国语助词、语尾等成分的翻译,因主要以汉语语序为主,可称之为“汉主韩从”式翻译。这类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中仍存在大量汉语句子或词组,被转换成韩国语语序的句子仅占少数,但对原文中的哪些句子采用仅在句末添加韩国语语尾的翻译策略,又将哪些句子转换成韩国语语序,并无规律可循。闵贤植(1994)、(3)[韩]闵贤植:《对开化期国语文体的综合研究1》,《国语教育》1994年第83卷,第113-152页。李秉骐(2013)、(4)[韩]李秉骐:《饮冰室自由书的国汉文体翻译》,《语文论集》2013年第54辑,第351-376页。洪宗善(2016)(5)[韩]洪宗善:《近代转换期开化文人对“国文/谚文”的认识与口语体文章的形成》,《我们语文研究》2016年第54辑,第589-620页。等研究中也指出,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复杂多样,很难将其进行完整的分类、总结。第二类是将汉文原文中的大部分句子进行句子成分重组,基本实现韩国语语序的翻译。译者将原文语句分解成词语或词组,其后紧接韩国语助词或语尾,用以表示该词语或词组在句中所充当的角色。这类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其翻译规律有迹可循,译者的翻译策略明确,与第一类韩汉文混用体翻译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翻译的特点
在译介梁启超著作的韩国文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玄采等。本文将分析以上几位文人的梁启超著作译文,并以此为事实依据探讨在启蒙期承担起翻译重任的“汉主韩从”式与“韩主汉从”式韩汉文混用体翻译的特点。(6)比较、分析各译者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原则上应选择同一译文进行比较,但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玄采等人分别翻译了不同的文章或书籍。因此,本文以译文句子的语序为分类标准,将以上几位文人的译文分为“汉主韩从”与“韩主汉从”两大类。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等人的译文汉语成分所占比重较大,应视为“汉主韩从”式翻译;而玄采的译文则与之相反,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应视为“韩主汉从”式翻译。
1.“汉主韩从”式翻译的特点
如前文所述,“汉主韩从”式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保留了较多的原文语句,仅在句末或句中添加了一些韩国语助词、语尾等成分,或仅将少量句子转换成了韩国语语序,译文中的翻译策略复杂多样,并无规律可循。
第一,仅添加少量韩国语成分。例如:(7)本文将所有例文中出现的古韩国语字母全部转换为现代韩国语字母,具体请参见译文原文。以下所有例句中的a句为梁启超原文,b句为译文。
(1)a.抑學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實施,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2)a.我中國人之善於經商,雖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權所以遠遜於人者……(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页。
(3)a.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回答一夕話耳……(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汉主韩从”式韩汉文混用体译文最显著的特征是“忠实于原文”。这里所说的“忠实于原文”是指这类翻译策略下的译文与原文几乎没有区别——仅在原文中添加了若干韩国语成分,语序也自然以汉语语序为主。从上面的例文中可以发现,译者将梁启超原文以句子、词组、词语等为单位进行分解,其后紧随“”“”“”“”“”“”“”“”“”“”“”“”“”等韩国语成分。被分解的句子成分并未发生语序上的变化,仍以汉语语序为主。至于原文中的哪些句子被分解成词组或词语,哪些直接在句末添加了韩国语成分,并无规律可循。
第二,个别句子转换成韩国语语序。例如:
(4)a.西人每歲創新法,制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页。
(5)a.故日日議瓜分,逐逐思擇肉,以我人民為其幸下之隸,以我財產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為其版內之圖,揚言之於議院,勝說之於報館。(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页。
(6)a.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勵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1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汉主韩从”式译文虽主要以汉语语序为主,但也有少量句子被转换成了韩国语语序。从以上例文中可以发现,梁启超原文中“V+O”结构的“創新法”“制新器”“著新書”“得新理”“議瓜分”“思擇肉”等被译为“O+V”结构的“新法創”“新器製”“新書著”“新理得”“瓜分議”“擇肉思”等,即在宾语后添加了“/”,在动词后添加了“-”,以表示该词或词组在句中所充当的角色。
在例(5)中,对于梁启超著作原文中的述补短语“揚言之於議院”“勝說之於報館”,译者选择去掉处所补语“於議院”“於報館”中的介词“於”,添加韩国语助词“”,并将其前移,使之成为表处所的状语“議院”“報館”,从而转换成了韩国语语序。
在例(6)中,原文中的“創建焦靈銀行”被译为韩国语语序的“焦靈銀行創建”。首先原文中的“創建焦靈銀行”被分解为“創建”“焦靈”“銀行”,为转换成韩国语语序,译者分别在这三个词语后添加了动词词缀“-”、目的格助词“”、表处所的格助词“”,以表示被分解的各词语在句中所充当的角色。原文中的因果复句“皆干預之,獎勵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被译为“莫不干預之獎勵之彼特們農會組織”。译者选择不译原文因果复句正句中说明结果的“遂”字,而是在说明原因的偏句中加入韩国语成分“(由于)”,即意在不改变因果句原意的基础上,对句子进行了进一步加工。
第三,翻译策略不一。例如:
(7)a.故其勢渙散,其心耎懦,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8)a.泰西人之1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2性質。(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9)a.故欲觀其國民之1有愛國心與否,必當於其民之2自居子弟歟自居奴隸歟驗之。(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0页。
“汉主韩从”式译文的特点之一是没有固定、统一的翻译策略,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呈现出翻译策略不一的情况。以上三组例文均出自朴殷植的译文《爱国论》,我们以“之”为例来探讨译者对该词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
在例(7)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对“之”采用了保留不译的翻译策略,译者仅在句中或句末添加了若干韩国语成分,其他保留汉文原文不译。而在例(8)中,原文“主之谓”结构中的“之1”被译为“”,而该句后半句中的“之2”则保留不译。可见,译者对句中出现的两个“之”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韩国语的“”相当于汉语的“的”,精通汉文的朴殷植将“主之谓”结构中的“之”错译为“”的可能性并不大,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源于译者“之即”的机械性翻译策略。在例(9)中,译者同样对句中出现的两个“之”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该句的两个“之”都在“主之谓”结构中,“之1”被机械性地译为“”,“之2”则被准确地译为韩国语主格助词“”。
2.“韩主汉从”式翻译的特点
启蒙期文人玄采翻译的《清国戊戌政变记》《越南亡国史》等译本是“韩主汉从”式翻译的典型。“韩主汉从”式韩汉文混用体译文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其翻译规律有迹可循,译者的翻译策略明确,与第一类翻译方式有着明显区别。
第一,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例如:
(10)a.酒稅,亦與鹽稅同,亦由法人自煑,業賣酒者,亦向法人領買酒紙牌,但只兩重稅耳。(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
在例(10)中,译者将汉文原句分解为“酒稅”“鹽稅”“同”“法人”“業”“者”“向”“領”“両重稅”“賣酒”“自釀”“賣酒紙牌”等词语或短语,之后将其按照韩国语语序进行了语序重排,并在这些词语或短语后添加了“”“”“”“”“”等韩国语助词来表示该词或短语在句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帮助读者理解句子的意思。“同”“業”“向”“領”等单音节词语在韩汉文混用句中被视为词根,通过与后缀“-”结合成为韩国语动词,而“亦”“只”等副词则并未以汉字词形式出现,而是被译为“”“”等韩国语副词。
第二,实词保留不译,虚词译为韩国语。“韩主汉从”式译文中的实词大多不被译成韩国语,而是以原文中的样子出现在译文中,其后紧随韩国语助词或后缀。而虚词则被翻译成了韩国语固有词。例如:
(11)a.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2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丁酉重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17页。
(12)a.宋代之稱姪稱子,猶天上矣……(30)梁启超:《外史鳞爪·越南亡国史前录》,《饮冰室丛著第九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
(13)a.此種野蠻法律,且幾廢不用,曾是靦然以文明,人道自命之法蘭西,而有是耶而有是耶。(32)梁启超:《外史鳞爪·越南亡国史前录》,《饮冰室丛著第九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6页。
由例(11)-例(13)可知,原文中的诸如“惟”“將”“猶”“幾”等汉语副词,在玄采的译文中被译为“”“”“”“”等韩国语固有词。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将句子成分重组实现了韩国语语序,而且将原文中的副词译为韩国语固有词,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韩国语的特点。这一点与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汉文原文特点的“汉主韩从”式翻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汉主韩从”式译文中几乎没有韩国语固有词出现。
第三,个别句子意译。“韩主汉从”式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一般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大部分句子直译,对个别句子进行了意译。这一点与忠实于汉文原文的“汉主韩从”式译文明显不同。例如:
(14)a.客容憔悴,而中含俊偉之態,望而知為異人也。(34)梁启超:《外史鳞爪·越南亡国史前录》,《饮冰室丛著第九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页。
(15)a.僕之行,改華服,冒華籍,偽為旅越華商之傭僕者,僅乃得脫耳。(36)梁启超:《外史鳞爪·越南亡国史前录》,《饮冰室丛著第九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
在例(14)中,原文“望而知為異人也”中的“異人”在汉语中是多义词,可作“他人”“不寻常的人”“怪人”“神人”等义,在这里作“不寻常的人”之义。译者将该词译为“凡常人”,“望而知為異人也”被意译为“凡常人知”,这种翻译策略避免了歧义的产生,降低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在例(15)中,“改華服,冒華籍”中的“改”与“冒”为单音节词,单音节词具有一词多义的特点,“改”可作“改变”“改正”“重新”“另行”等义,在这里作“改变”之义。“冒”的意义更加丰富,可作“帽子”“戴帽”“贪求”“不顾”“假冒”“侵犯”等义,在这里作“假冒”之义。译者在译文中将“華服”译为“淸人衣服”,将“華籍”译为“淸人屬籍”,虽未将“改”与“冒”译为“改变”与“假冒”,但将“改華服,冒華籍”意译为“淸人衣服着淸人屬籍作”,这种翻译策略在降低了译句难度的同时,又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句的意思。
第四,翻译策略统一。例如:
(16)a.美人首以兵艦欲搗菲島以牽班力,而自懼其力之不達也。(3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8页。
(17)a.俄人之亡波蘭也,非俄人能亡之。(4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页。
在例(16)、例(17)中,在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的“韩主汉从”式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中,译者将位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的“之”准确地译为韩国语主格助词“/”,并实现了韩国语语序,其翻译策略统一,与“汉主韩从”式译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综上,“汉主韩从”式译文与“韩主汉从”式译文在翻译策略上有着明显区别:首先,前者基本保留汉文原文的汉语语序不变,仅在句中或句末添加了少量韩国语助词或语尾;而后者则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虽仍保留原文中的汉语实词不译,但原文中的虚词均已译为韩国语固有词,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韩国语的特点。其次,前者忠实于原文,译文几乎与原文并无区别;而后者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将原文中难译的词句,以难度相对较低的词、句进行意译。最后,前者的翻译策略不一,难寻其翻译规律;而后者的翻译策略统一,其翻译规律有迹可循。
然而,这两种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并非毫无共同点,不管是以汉语语序为主的“汉主韩从”式翻译还是以韩国语语序为主的“韩主汉从”式翻译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汉语成分。
三、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成为主要翻译体的原因
进入近代启蒙期,韩国开始了“脱离汉字,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进而实现言文一致目标”的运动,用本国文字进行翻译或著述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使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纯韩文体翻译才是响应时代号召并有利于实现言文一致目标的翻译方式。但在启蒙期,韩文体翻译却并未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大多数文人选择了混用汉文与韩文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貌似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它却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翻译体,启蒙期的大部分文人也正是用这种韩汉文混用体译介了梁启超著作。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时代要求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各国脱离汉字,用本国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成了历史总体趋向。19世纪末,韩国开始意识到摆脱他国文化统治,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进而实现言文一致目标是步入近代国家行列的必备条件。同时,当时的韩国又认识到西方先进国家无一不使用表音文字,比起上层文人使用的文字——汉字,简单易学的表音文字才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于是,全国上下开始了大力倡导使用本国的表音文字——韩字的运动。
1894年11月21日,朝鲜高宗发布了敕令第1号《公文式》,在这条敕令的第14条,高宗明确命令:“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并于1895年5月8日的敕令第86号《公文式》第9条中再次强调了此命令。从此,官报、法律条文等都加入了韩文成分。韩汉文混用体成为当时反映“国语国文”精神的重要形式,推动韩国社会向实现言文一致目标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
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倡使用本国文字”,第二阶段“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第三阶段“按发音记录文字”,第四阶段“制定拼写规范”。(42)[韩]白采媛:《20世纪初资料中“言文一致”的使用情况与意义》,《国语国文学》2014年第166期,第78页。而1910年以前的言文一致运动还仅停留在第一阶段。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便是第一阶段言文一致运动的产物。
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应时代要求而生,这是它在当时成为主要翻译体的重要原因。首先,文体演变的规律要求文体一定要适应时代需求,否则就要发生变化。在推行言文一致运动并大力倡导使用本国文字的特殊时期,启蒙期韩国面临着从汉文到韩文的过渡,但是从使用了数千年的汉文中脱离出来,统一使用韩文,并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其次,韩国的“启蒙”分不同时段,先是上层文人士大夫,再是普通民众,需由小范围逐渐扩大到大范围。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小范围内文人士大夫的“启蒙”期。他们是当时韩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启蒙类文章的主要读者群。由于当时的启蒙教育尚未扩散到未受过汉字汉文教育的一般民众群,因此,这一时期的报纸杂志及书籍的出版主要考虑的是上层士大夫的阅读需要。对从小学习汉字,且具有深厚汉学素养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汉字与汉文成了知识与身份的象征,韩字只是妇孺与底层阶级的文字。因此,文人们一时难以接受从汉字汉文到韩字韩文的转变,很多文人甚至并不具备用韩文写作的能力。但是,他们又比谁都清楚只有实现“言文一致”才能普及近代知识、教育韩国民众,从而实现救国目标。在这种艰难抉择中,启蒙期韩汉文混用体应运而生,它既给了文人从汉字汉文转变为韩字韩文的缓冲期,又没有完全背离“言文一致”的时代要求,是适合当时韩国社会的“最佳选择”。
(二)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阅读需求
启蒙期的“汉主韩从”式与“韩主汉从”式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其翻译目的各不相同。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引导全部的翻译活动。“汉主韩从”式译文的主要读者群为精通汉文的上层人士,这种翻译的目的是在顺应时代要求的前提下,迅速地翻译汉文原文的内容并将其传播出去。这一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原文中仅添加少量代表“国语国文”精神的韩国语助词、语尾等成分,并将这种仍保留着大量原文语句的译文快速地传播于上层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的读者精通汉文,并不需要这种与原文并无区别的译文,原文中的韩国语成分存在的意义在于顺应时代要求而并非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这也是为何在“汉主韩从”式译文中出现大量“之即”机械性翻译的原因。“韩主汉从”式译文的主要读者群并不仅限于精通汉文的上层人士,其翻译目的是在保留汉文原文精髓的前提下,实现韩国语语序,并扩大读者群,以达到启蒙开化的目的。这一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成分,从而满足上层人士对汉文的需求;而基本实现韩国语语序的翻译行为,又满足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这一阶层的读者可以借助《注解千字文》《儿学篇》等工具书理解文中的汉语成分,进而理解全文内容。
(三)韩文体的弊端
当时的韩国语并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导致语言文字使用混乱。韩国语的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元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等形式。当“辅音+元音+辅音”结构的音节后紧随元音,那么,发音时充当韵尾的辅音便移到后续音节上,与其拼成一个音节,即发生连音现象。例如,“”一词发生连音现象,应读“”。在未形成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启蒙期,同一词语在文章中形态不一,按读音记录的“”类词语与按音节形态记录的“”类词语共存,严重阻碍了读者对词义的准确理解。
此外,韩文体并不利于传播近代新词。爱国启蒙运动以开启民智、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急需汲取近代新知,学习近代思想,而近代新词所承载的便是启蒙期韩国迫切所需的近代精神。近代新词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日本为译介西方文明,翻译了大量的新词新语,这些近代新词滋养了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为其完成从封建国家到近代国家的跨越输入了近代的新鲜血液。日本之所以选择用汉字翻译近代新词,其原因在于汉字为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其意义,汉字词能够以简单、直观的方式准确地传达信息。表音的韩字则不然,如将“权利”“法律”等近代新词译为“”“”,很难让第一次接触这些新概念的民众准确地理解其义。
(四)梁启超文章的特点
1910年以前,韩国主要通过中国文人翻译或撰写的文章来学习近代先进知识,其中梁启超的论著占相当大的比重。韩国文人通过梁启超的文章来学习近代知识,为韩国民众传播进步思想,而传达梁启超精神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语句,使读者能够直观、准确地理解文章精髓。这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句的保留与梁启超在文章中大量使用的近代新词有着密切关联。如前文所述,在译文中只有保留近代新词不译才能保证准确地为读者传达近代新知。
此外,梁启超独有的犀利、辛辣的写作风格深受韩国文人赞扬,保留原文的文体风格才能更有效地传达其思想感情。这也是韩国文人在翻译梁启超著作过程中选择韩汉文混用体翻译方式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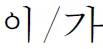
四、结语
在近代启蒙期,韩国不同文人翻译梁启超文章的方式虽呈现出不同特点,但大多数文人选择了以汉文与韩文混用的方式来译介梁启超的文章。启蒙期的韩汉文混用体翻译又可以细分为“汉主韩从”式与“韩主汉从”式两种,两者在翻译策略上有着明显区别。这两种翻译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启蒙期韩国的主要翻译体是因为:第一,这两种翻译方式应时代要求而生;第二,这两种翻译满足了不同阶层的阅读需求;第三,当时的韩国语并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导致语言文字使用混乱,严重阻碍了读者对词义的准确理解;第四,梁启超文章的特点。
梁启超著作韩汉文混用体译文是研究近代韩国语的重要资料。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梁启超著作韩汉文混用体译文,将为中韩两国学者从多角度研究近代韩国语发展史、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影响等课题提供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