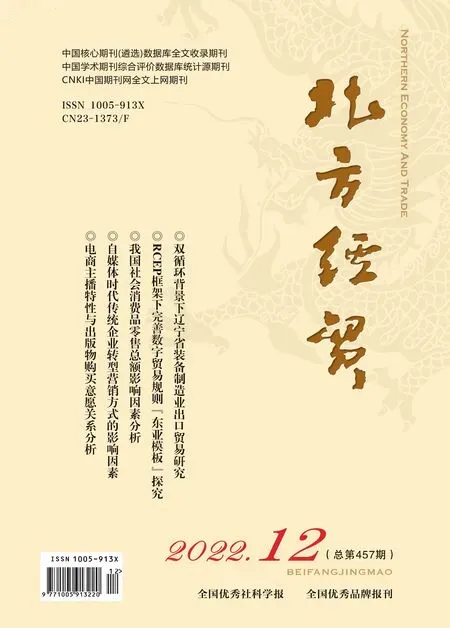《民法典》合伙合同的规范解释
周丽丽
(黑龙江五伦律师事务所,哈尔滨 150077)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合伙合同预设的规范目标为未成为组织的合伙,即合同型合伙,从而区别于《合伙企业法》所规范的组织型合伙。然而,合伙合同一章仅由12 个条文构成,条文的概括、笼统、简略与内容、形式多样的合伙实践的客观需要相去甚远。在合伙合同的司法实践中,在缺少当事人约定而法律又欠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类推适用《合伙企业法》的可能。《民法合同编(草案)》曾于第537 条规定“本章对合伙合同的内容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尽管此后的草案及正式的立法文本将该条删除,但依然难掩作为民法中的合伙合同由于规范供给不足而参照适用作为商法的合伙企业法的客观事实。此种一般法没有规定而参照适用特别法规范的法律适用方法,与常见的作为特别私法规范的商法缺乏规定时参照适用作为一般私法的民法的法律适用方法相异,因而值得关注与研究。
二、合伙合同的规范地位
我国制定《民法典》时接受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首次将“合伙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范,规定于“合同编”之“典型合同分编”。但是合伙制度在《民法典》之前便已存在,仅是对其存在不同的认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公民(自然人)”一章中规定了“个人合伙”,在“法人”一章中规定了“联营”即“法人合伙”。唯一可脱离民事企业概念解释合伙合同关系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 条,其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将对合伙企业的法律规定辐射至非企业的合伙合同关系。[1]从规范形式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试图从民事主体的角度规范合伙关系,但就规范实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又根本就没有把合伙作为民事主体对待,而仍然将合伙视为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合同。[2]
《民法典》在“总则编”民事主体部分将“合伙企业”作为“非法人组织”,使不具备组织体性质的“合伙”彻底在形式上退出主体制度,而回归到其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有学者指出,《民法典》规定“合伙合同”的意义在于,为商事合同以及商事组织体的相关制度提供基础,特别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发起协议或出资协议,可以适用合伙合同的规范。[3]但由于我国的民商合一体例的现实存在,传统大陆法系对于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的区分,似乎无法在我国民法的语境下继续发挥原有的功能。尽管有学者将《民法典》中的合伙合同称为民事合伙,《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为商事合伙,但是合伙合同中的“共同事业目的”并不以非营利目的为限,[4]当事人缔结合伙合同的目的仍然可以基于商事目的。因此,《民法典》语境下合伙的民事性或商事性已经无法进行区分。唯一有意义的区分在于是否形成接受《合伙企业法》调整的商事组织及合伙企业。
在合伙制度的体系上,尽管合伙合同并未形成组织体,但合伙合同仍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不过其具有的组织性强度与合伙企业的组织性强度位居合伙制度的两端。《民法典》规范上的合伙合同的组织性最弱,而《合伙企业法》规范上的组织性最强。当事人之间基于各异的交易目的与交易安排,约定组织性各异的合伙合同关系。而约定的合伙合同的组织性越强,对于《合伙企业法》的参照适用的范围也就越广。具体在制度规范上,例如合伙财产的归属、合伙财产的确定等事项,均存在由于自身规范供给不足而需要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空间。
《民法典》虽然将未形成组织的合伙作为一种合同类型,然而合伙的当事人之间基于“共同的事业目的”而形成合意,与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互异且对立而形成的双务合同即契约存在相当的差异。而我国民法向来很少区分契约与合同,且《民法典》无论是“民事法律行为”还是“合同编通则”均是以双务合同为原型进行制度设计,因此作为“共同行为”的合伙合同能够在何种或多大程度上适用“双务合同”的一般规则,则不无疑问。在理论上,合伙合同所具有的组织性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非互换性,决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与合同的一般规则,于合伙合同场合应当限缩适用而非全部一概适用。
三、合伙合同的规范性质
合伙合同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共同行为”的属性,从而构成合伙合同与其他十八种有名合同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共同行为区别于契约行为,目的不在于实现“对待给付”的交换关系,而在于形成一定程度的共同体对外部实现当事人追求的“共同的事业目的”,合伙合同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团体组织功能。因此,合伙合同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团体性与组织性。正是由于合伙合同的这一特色,合伙合同在对合同法一般规则的适用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限缩性,即对于以对待给付为制度典型性的契约行为制度须进行一定的限缩适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民法典》与《合伙企业法》在立法时间以及立法内容上存在错位,在“一般法—特殊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上,将突破特别法欠缺规定时适用一般法的规则,而可能存在一般法如无规定时适用特殊法的“倒序”现象。此外,合伙关系中存在的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其中蕴含的共有关系,因此合伙合同中还外溢出物权关系的相关问题。
(一)合伙合同的共同行为属性
根据德国法系的传统理论,依法律行为实施人之单复数或曰意思表示之单复数,法律行为可分为单方法律行为(einseitige Rechtsgeschäfte)与数方法律行为(mehrseitige Rechtsgeschäfte)。数方法律行为的成立需要数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又可划分为双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与决议。其中双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最为重要,也是合同法中主要涉及的法律行为类型。双方法律行为即为我国民法上之合同,亦即传统民法上之契约(Vertrag),是指双发当事人形成方向相对的意思表示之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例如买卖、租赁等。唯我国大陆地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来对于该类法律行为不再使用传统民法上的契约而改称合同,而我国台湾地区依然遵循大陆法系传统的契约概念。多方法律行为虽然同样为复数当事人之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与双方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相互对立、需互为对待给付不同,各方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方向相同或内容一致。大陆法系传统上将之成为“合同行为”(Gesamtact),以与“契约行为”相区别。在我国由于合同概念的变异,民法理论上称之为“共同行为”以与“合同行为”相区别。[5]
纵观《民法典》总则编与合同编,无论是民事法律行为一般规定、合同编通则还是合同编第九章至第二十六章的典型合同,概莫以标准的互为对待给付的双方法律行为为典型模式与制度原型,因此于术语上区分合同与契约意义有限。但恰恰是第二十七章的“合伙合同”殊为不同,合伙合同中不存在以交换为目的的对待给付关系,当事人之间订立合伙合同是以实现共同事业为目的,与社团法人设立、因合并之公司成立等相同,属于传统民法中典型的“合同行为”、我国民法中的“共同行为”。[6]因此,在合伙合同的法教义学分析上,应当重视其共同行为属性,而对于以契约行为为制度预设的合同法律制度,应存在适当限缩适用的必要。例如,作为合同一般规则的合同撤销、合同履行、合同变更与转让以及违约责任等应当加以限制适用。
(二)合伙合同的组织法属性
合伙合同的组织法属性来源于其共同行为属性。尽管《民法典》合伙合同预设的规范目标为未成为组织的合伙即合同型合伙,从而区别于《合伙企业法》所规范的组织型合伙,但是订立合伙合同在于实现共同的事业目的,当事人各方的意思表示与实际行为均指向共同的方向。与成立合伙企业的合伙合同、成立公司的出资合同类似,当事人各方均意图通过该合同明确各方共同出资后、共同运营过程中作为共同财产之一部分的权利义务,其组织性相当明显,仅仅是在组织性的强度上无法与合伙企业相提并论。有学者甚至指出,合同法在现代社会既是交易法也是自治法,不仅在单次的交易中发挥着规范功能,在关系性、合作性活动中也发挥着与法人等社团一样的组织复杂经济活动的功能。[7]那么,作为共同行为的合伙合同的组织性更是尤为显著和突出。
从规范构成与规范内容上,《民法典》合伙合同一章仅由12 个条文构成,笼统性地规定了合伙合同的定义、合伙财产、合伙事务管理、合伙与第三人关系、合伙终止五个方面的内容。条文的概括、笼统、简略与内容、形式多样的合伙实践的客观需要相去甚远。在合伙合同的司法实践中,当缺少当事人合同约定而法律又欠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存在类推适用《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则的可能与必要。此与传统大陆法系中的情况正为相反。在立法顺序上,德国、日本等均是先制定包含合伙合同的民法典,再制定包含合伙企业的商法典。由此反映在立法内容上,《德国民法典》共使用36 个条文,《日本民法典》共使用22 个条文,全面、详尽地规定了民事合伙“从出生到死亡”的完整过程的各项规则。其规范内容之完备程度,完全可以与我国《合伙企业法》相媲美。正是有了民法中的坚实基础,《德国商法典》与《日本商法典》方可基于事物相似性的原理,并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适用顺序规则,仅规定形成商事组织的合伙的特殊问题,并明文规定商事合伙未予规定者参照适用民法中合伙契约的规定。我国《民法合同编(草案)》(2017年 8 月 8 日民法室室内稿)曾于第537 条规定,“本章对合伙合同的内容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尽管该条草案曾受到关于一般法与特殊法适用顺序上的非议,此后的草案及正式的立法文本也将该条删除,但依然难掩作为《民法典》中的合伙合同由于规范供给不足而存在参照适用作为商事特别法的《合伙企业法》的客观需要。从现实角度而言,这也反映出我国在已经制定了规范较为完备的《合伙企业法》之后无须再为重复规定合伙合同规则的客观情况。此种一般法没有规定而参照适用特别法规范的法律适用方法,与常见的作为特别私法规范的商法缺乏规定时参照适用作为一般私法的民法的法律适用方法确实相异。
《民法典》合伙合同规范所体现的组织性,其强度与合伙企业的组织性强度位居合伙制度的两端。《民法典》合伙合同的组织性最弱,而《合伙企业法》合伙的组织性最强。当事人之间基于各异的交易目的与交易安排,可以约定组织性各异的合伙合同关系。而约定的合伙合同的组织性越强,对于《合伙企业法》的参照适用的范围也就越广。具体在制度规范上,例如合伙财产的归属、合伙财产的确定,尤其是合伙合同终止后的清理与清算等事项,均存在由于自身规范供给不足而需要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空间。
四、结语
关于合伙合同,无论是从历史与比较的视野,还是民商事交叉与融合的角度,合伙合同均具有联结民事与商事关系之间关系的独特价值。合伙合同不同于其他典型合同或有名合同,其具有的非交换的共同行为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团体性与组织性,在其法律适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具体而言,立基于共同行为属性与团体组织属性,合伙合同对于以对待给付的契约行为为制度原型的合同解除、履行抗辩等合同法一般规则应当予以限缩适用,以保证合伙人订立合伙合同所欲实现的共同事业目的,以及对于合伙组织性与团体性的维持。另一方面,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存在不同于传统大陆法系合同型合伙与组织型合伙关系的独特性,《合伙企业法》的立法时间与立法内容相较于《民法典》合伙合同具有优越性与有限性。《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合伙合同的规范容量上有意无意地以《合伙企业法》为来源与基础,因此在《民法典》合伙合同出现法律漏洞时,例如合伙的退伙、合伙的清算等,存在类推适用《合伙企业法》相关规范的可能性,从而在民事一般法与民事特别法的使用顺序上存在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