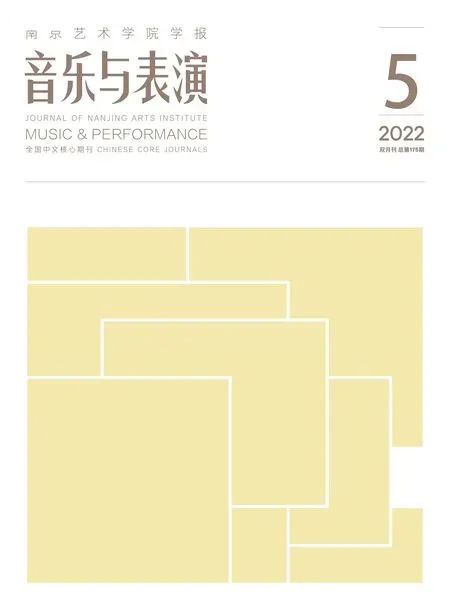动见观瞻,寸心史诗①
—— 为居其宏先生八十诞辰而作
钱庆利(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居其宏1943年4月生于上海,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及本科,后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硕士研究生。1981年,居其宏获硕士学位,并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直到2002年。在此期间,《中国音乐学》创刊,他多年担任常务副主编,为推动中国音乐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后,他调入南京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艺”),担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及“音乐与舞蹈学”首席学科带头人。
众所皆知,居其宏的研究广涉歌剧音乐剧史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音乐评论、音乐美学、音乐编辑学等诸多领域,每个领域都成就斐然。在晚学看来,先生最大的品格便是勤勉,其研究成果均由勤勉生发而来。2022年,先生步入耄耋之年,作为其授业弟子,特撰小文以道贺,对先生调入南艺后的点滴进行回顾。之所以摘取这一时段,是因为在此期间我与先生交往甚密,多蒙亲炙。
一、学科领衔:“南下”始末与其人、其文
1986年,南艺首次获批美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1世纪初,为使学科建设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南艺着意引进一批在全国音乐学界有影响力的旗帜性学者,居先生成为意向引进对象之一。双方经过了多轮磋商“谈判”。最终,南艺于2002年5月将先生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南艺,同时聘任伍国栋先生为特聘教授。自此,居先生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20余年的首都,正式“南下”投入到南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洪流之中。从学校层面而言,引进居、伍二老的终极目的不独是推动自身音乐学科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力保音乐学专业“申博”成功。在居、伍两位“外援”及南艺原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南艺于2003年获“音乐与舞蹈学”博士授予权,并于2004年开始招生首届博士研究生。这对南艺的学科发展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与幸事。后来南艺在全国艺术学科排名靠前,与两位先生的引进及丰厚的学术成果有直接关联。正如南艺原院长刘伟冬教授所言,引进人才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我与先生结识,是经由冯效刚教授介绍。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工作节奏突然慢了下来,也有了些闲暇时间,冯老师推荐我报考居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记得与先生初次见面是在南艺东门旁古林公园入口处的“圆缘园”餐厅(现已改作他用)。那天中午,冯老师因事没能参加,“媒人”未到场,我的忐忑之心可想而知。然而短暂聚会中,先生的亲切态度将我此前的恐惧一扫而空。自此,我便与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师、后友、再同事,受其教诲、滋养已近20年。人生之路,不仅靠“独立行走”,更受到他人及周遭环境的影响。在笔者的学习过程中,若问受谁影响最大、最广、最深?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是惠我良多的业师居先生。
我是居先生调入南艺后招收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之一。2007年,我硕士毕业留在南艺音乐学研究所工作,同时学校批给所里2间办公室(原先只有1间)。因办公比邻,我得以亲眼见证先生的勤奋。除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讲学、观摩演出,先生几乎都在办公室写作。从2008年至今,先生所坐的办公椅子就换了好几个(且都是椅子的表层被“坐烂”),先生也常自诩“坐功超强”(对电脑写作的人来说,一“座”难逃)。值此文撰写之际,先生的新凳子表皮又已破损,正待更换。
先生为人随和、谦逊,从不以著名学者、长辈自居,生活中自由洒脱、不拘小节,与不同年龄、性别的各界朋友均可打成一片。有个自身的例子可证,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一次与先生等众朋聚餐,席间因多喝了几杯,略带醉意,竟搂着先生的脖子直呼“其宏兄”(现在想起来都汗颜)。此外,还有诸如郭克俭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乔邦利教授曾与先生小酌,推杯换盏、相谈甚欢之时,乔竟称呼先生为“居克俭”。如此等等,先生丝毫没有生气,反倒留作日后师生交流、活跃气氛的“佐料”。
尽管先生平日里待人亲切、宽容,可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却是另外一种风格,其笔下威严之辞令所有学生不寒而栗。先生给学生辅导论文方式方法与其他导师不同,他从不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而是均以书面形式指导。每每学生将文稿发与先生审阅,都是在忐忑中等候回复。先生回复的指导意见十分详细,字数常多于原文稿字数,这全出自先生自嘲为“一指禅”的单指敲键指法。正是师生间如此多轮“交锋”,才使得学生们的文章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居先生其人、其文真挚赤诚,面对波诡云谲的中国音乐界,不虚美、不掩过,在其涉及的各个领域总能追踪热点、透视焦点、思考难点,取得层见叠出的学术成果。居先生的写作分析入理、表达机趣,体现出强烈的反思与责任意识,达到了融古今于一体、汇中西于通篇的醇熟境界,以渊博学识、辛辣文风和敏锐的音乐洞察力闻名音乐学界。
二、学术思想:南艺任职期间的学术成就回塑
居先生在南艺工作期间(2002—2013),是南艺音乐学事业发展的高峰期。先生超前的学术思想首先体现在弥补学科不足上。如在南艺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增设当代音乐方向,在原有目录古代音乐史方向基础上,使中国音乐通史研究有了立足之地。其次则体现在抢占学术高地上。先生在全国率先开创了歌剧音乐剧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先河,自觉开拓教学新领域,贡献卓著。10余年来,相继培养出冯效刚、卿菁、范晓峰、张少飞、屠艳、乔邦利、郏而慷、王冬、戈晓毅、朱艳、徐文正、张强、钱庆利13位博士,以及王艺蓓、赵玎玎等当代音乐与歌剧音乐剧史论方向的硕士。他们分布在全国各音乐院校,并逐渐成为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居先生对南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创新等诸多方面,可谓厥功甚伟。
值得注意的是,当艺术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2011)后,因国务院新修订的学科目录未将综合舞台艺术学纳入,先生当即撰文指出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单科制的专业艺术教育, 令各专业学者在精通本专业之外,对其他艺术门类知之不多、认知更浅;即便在综合性艺术院校,各专业之间亦每每‘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其系科设置、深层办学理念和实际教学效果仍与单科制无异。学者队伍普遍存在的这种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非但导致他们无法驾驭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和立体化审美这类宏大的学术命题,而且久而久之便在艺术学界沉淀为一种思维定式, 居然对这种单向的孤立研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1]这一前瞻性观点的提出,虽未得到官方回应,但其思想内涵与当下新文科、跨学科教育思维不谋而合。
先生为南艺学科布局与长远发展殚精竭虑的同时,其自身学术研究再度迎来爆发期。作为首席学科带头人,先生亲力亲为、勤奋当先,总是领跑学术“第一棒”。据粗略统计,在南艺工作的11年间,先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既有学科基础理论,亦有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还有关涉学术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等。这些见解均是先生多年教学、研究、实践心得,实属有感而发,对当代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和当下学术规范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发与警示意义,充分体现出一个史学家与批评家的责任担当。
除文章外,这一时期,先生著作的出版也迎来高峰期,先后出版的著作(含合著、论文集)共21 本。窃以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歌剧美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与修订版的《音乐学文论写作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先生早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将毕业论文的选题聚焦于歌剧问题。事实上,几十年来,歌剧始终是先生倾注心力最多的一大重要研究领域。《论纲》是有关歌剧元理论的重要文献,其内容关涉歌剧创作的方方面面。正如郭克俭教授所言:“《论纲》的篇章结构和内容呈现是匠心独运的,兼具美学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总结的双重品格——既有理论的凝练与精湛,又有大量中外歌剧实践的厚实支撑;密切关注中国歌剧(音乐剧)现状,联系舞台创作与表演实践展开学术批评,则是《论纲》又一重要的美学品格。”[2]
《教程》一书是目前国内较少面世的有关音乐学论文写作的专著。关于本书的重要性,作者在出版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做了说明:“文论写作事业不仅被专业学者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而且举凡从事音乐创作、表演教学和编辑出版的音乐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论文写作打交道,特别是在强调学术创新,而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的当下,编写一本专门探讨文论写作的种种奥秘与操作技巧的教材,显得尤为必要。”[3]给人印象最深的应当是《教程》中论及的“三性”问题,即对象第一性、资料第一性与研究第一性。事实上,论文写作的广度、深度、高度与成色,都与“三性统一”有关。《教程》的出版与修订,对多年来苦于没有音乐文论写作参考书的研究者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除论文写作与著作出版外,先生在南艺工作期间还主持申报多项课题,已完成的有:国家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歌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江苏省人文社科重点课题“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与乔邦利合作)、江苏高校人文社科重点课题“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等。其中有些论文、教材与课题成果颇受社会认可,这从其所获诸多奖项中可见一斑。如《教程》曾被评为江苏省高校精品教材(2005)及江苏省高校精品课程(2010);《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获江苏省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0);《当代乐坛的消费主义和浪漫主义》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10);《共和国音乐史》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2011),并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2);《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铜奖(2014)。最具含金量的奖项,当属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的结项成果——《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9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该项成果获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8)、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0)。
上述教学、科研与获奖成果,不仅体现了居先生自身的学术成就,也为南艺赢得了荣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果为南艺历次学科评估提供了充实且有分量的支撑。
在南艺工作期间,居先生除在学术研究的百花园辛勤耕耘外,还多次主持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其目的是带动音乐学学科发展、提升南艺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有2007年4月召开的首届“全国音乐学博导论坛”。这次会议通过分析我国音乐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历史与现状,围绕全国音乐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等展开讨论,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有关音乐学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达成若干共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是2008年12月召开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学术会议,具有显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性质:
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与会代表向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所做的大会演讲或小组发言,从各自所熟悉的领域和独特视角畅论新时期以来我国音乐学及相关二级学科繁荣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对30年来所取得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主要业绩以及在各学科自身建设方面已实现的历史性跨越做了系统回顾和热情肯定,深刻阐释了改革开放国策对于推动音乐界拨乱反正、解放音乐艺术生产力、促进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批评实践走向多元繁荣的巨大影响力。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于我国当代音乐学发展之推动伟力这个总前提之下,许多学者怀着高度责任感和问题意识严肃指出,最近30年来,在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并对其主要表现、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围绕这些不足的解决途径提出了各自的设想和建议。[4]
会议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前文提及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论文集》便是此次会议成果的集中展示。
除长期默默耕耘在基础研究领域外,居先生在创作领域亦有一定收获。由他担任编剧的歌剧、音乐剧有《月上盖头岭》《中国蝴蝶》《杜十娘》等,其中以中央歌剧院创排并于2006年上演的《杜十娘》影响最大。
为南艺做一部歌剧,也是居先生由来已久的念想。一来可以检验南艺的教学成果,二来可以彰显南艺优势。但是,怎么才能体现综合性艺术院校的特性?通过怎样的形式来体现?时机来了,201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协同创新”理论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南艺作为国内学科门类齐全、办学能力位于同类高校领先水平的综合性百年老校,在践行高校职能上已取得一定的成就,面临此次协同创新的发展大潮,更应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有所作为。2014 年3月5日,南艺党政领导召开校内协同创新项目策划论证会。
“居其宏教授作为中外歌剧史论资深学者,提出以复排歌剧《秋子》作为全校践行‘协同创新’理论突破口的创意,其理由有三:一是从项目本体来说,歌剧作为高度综合的艺术形态,其创演本身必须经历协同、合作的复杂过程,复排歌剧《秋子》是对南艺综合办学实力的整体性集中检验,是衡量‘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一把标杆。二是从政治角度考量,20 世纪40 年代初创演的歌剧《秋子》在战时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当时文化艺术界的一大盛事;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巨变,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复排反战题材的《秋子》是对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的最好纪念,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三是《秋子》故事发生地就在江苏,且当时的主创力量均与南艺有诸多人缘、地缘、艺缘之连。因此,由南艺来复排该剧,可谓上合天时、中享地利、下有人和,最为合适不过。”[5]
居先生“复排歌剧《秋子》”这一具有前瞻性与敏锐性的提议,得到时任院领导与论证专家的一致认可,创演团队迅即成立。居先生任此次《秋子》复排的总策划、艺术总监,担纲剧本整理、修订与编创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复排歌剧《秋子》的所有演职人员均为南艺师生。复排是对南艺办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南艺的一次大型艺术实践活动,还是对南艺前辈们的一次意义深远的纪念。该剧在2014年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上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5年8月26至29日,该剧又以音乐会版的形式亮相爱丁堡边缘艺术节,这是南艺原创歌剧作品首次走出国门,为南艺赢得了国际声誉。
三、寸心史诗:学术续航与提携后学
如今,居先生已界耄耋之年。从南艺正式退休之后,他本该像同龄人一样颐养天年,但实际上先生却是退而不休,依然奋战在学术一线,坚持论文写作与课题申报。退休后的居先生先后被河南理工大学、郑州西亚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聘为特聘教授,继续为南艺及其它院校奉献余力。其学术激情与退休前相比丝毫不减,大有将勤奋进行到底之势。
从南艺退休的第二年(2014),先生以南艺为主体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获准立项。以此为立足点,从该项目立项至结项,先生先后发表了7篇文章,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进行交融性论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中所论及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核心思想。在该项目的结项的那一年(2018),由先生负责的文化部横向课题“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现实题材创作课题研究”落户南艺。此外,先生作为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领衔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研究”也于2018年获批立项。该项目分设六个子课题,居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的又踏上了学术研究的新征程。
在紧锣密鼓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的同时,另一项工作也在推进,那就是重新修订2002年出版的《论纲》。该书由原发表在《歌剧艺术研究》(现为《歌剧》)上的系列文论裒辑而成。本次修订幅度最大的地方,“是根据近年来我国歌剧发展的新进展、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相关章节中“结合具体剧目的实例,增写了若干分析和论述文字,尤其在第一编第六章为民族歌剧增写了第六节,在第二编增写了第五章‘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分别对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题材选择和处理、剧诗创作等视角出发,从近年来创演剧目的具体实践提取论题、发现并分析问题,找出症结所在,提出解决建议,或者就其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展开美学阐释”。[6]修订版《论纲》于2021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原来的27万字增加到45万字左右,可见此次修订绝非匆忙间可以草就的重大工程。凡此等等,都足以说明先生勇毅前行、毫不懈怠的学术品格。
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先生承担了2019年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主体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的子课题“新时代中国声乐发展战略与学派建设研究”的写作任务,并对该院博士研究生雷佳等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辅导,为帮助他院、提携后学继续奉献余力。
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奔忙是居先生矢志不渝的志向。作为中国民族歌剧发端的《白毛女》(1945),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的产物。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新时期文艺座谈会,其核心精神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脉相承,深刻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此为契机,2015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决定复排歌剧《白毛女》,号召民族歌剧创作应向《白毛女》传统学习。作为这项工程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已越古稀之龄的居先生长年奔走于全国各地,对新创剧目进行跟踪指导,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艺》栏目民族歌剧讲解嘉宾并乐此不疲。除此之外,先生还积极参与新剧创作。比如,作为第一编剧,创作出原创歌剧《松毛岭之恋》,作品描写了红军长征前夕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长征后一名革命烈属用30年时间、30套衣裳等待一份爱的人间真情。2017年,该剧由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排上演,经过多轮巡演,其震撼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业内人士与一般观众的广泛认可,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滚动扶持和重点扶持剧目。
从2013年退休至今,先生先后在各类期刊(主要是核心期刊)发表文论近80篇。这些文章涉及领域广泛而多元,既有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系列论述(如《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思考系列之四: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方法论述要》,《音乐艺术》2014年第4期),又有关于音乐院校音乐学教学问题的意见与策略(如《对我国音乐教学若干问题的反思和建议》,《音乐探索》2016年第4期),更多的是有关中国歌剧音乐剧创演实践的思潮及评论文章(如《当前歌剧音乐创作若干紧迫问题刍议》,《音乐研究》2020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涉及学科理论、教学研究、思潮评说,充分体现出一个当代音乐学家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上述研究、创作等成果的产出对居先生而言,不是退休而是无休,是永不停歇的学术续航。
余 论
罗素曾言:“最好的生活是建立在创造活动的基础上。”此话用在居先生身上恰到好处。自读研开始,先生便行走在学术创造的苦旅上,40余年来潜心学术研究与写作、绝少旁骛。他用笔尖描绘出一幅幅综合多元的知识图景。从先生的诸多学术成果,足见其贯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独擅的方法以及发人之未发的新见。先生总能在切中肯綮中纵横捭阖、收放自如,以磅礴恣睢之气韵,给后辈学者带来无限的精神滋养与阅读美感。40余年来,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无不是默默耕耘所得。40余年来,先生不仅有“望断天涯路”的精神追求,且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冷清。先生基本上常年无休,不是在办公室做“五指键盘侠”,就是奔波在观摩、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的途中。其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而这种“冒险”始终与“独守”“自处”相生相伴,其勤奋程度令吾辈晚学汗颜。
总之,居先生作为中国音乐学界的领军人物,为南艺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其他学校的科研贡献了一份力量,为中国歌剧音乐剧事业付出了极大心力,为年轻的后学们树立了立学、成家的榜样。居先生的学术品格可集中概括为“勤奋、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