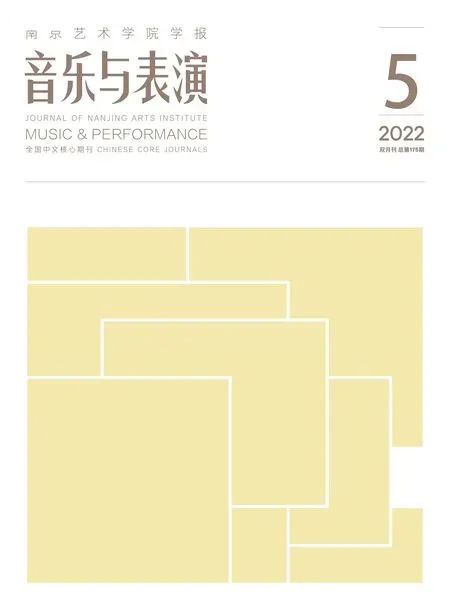师法承继 百变传神①
—— 当代戏曲艺术家李鸿良昆丑表演艺术
郭克俭(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袁 锞(浙江开放大学 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丑行是中国传统戏曲舞台表演中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角色之一,其表演诙谐幽默,往往一出场便能引人捧腹,笑而不止。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言:“丑以科诨见长,所扮备极局骗俗态,拙妇呆男,商贾刁赖,楚咻齐语,闻者绝倒。”[1]由此足见,丑角在戏曲演剧中的重要地位。丑角行当要求演员有全面的艺术素养,不仅要念、唱、做、打技艺精湛,塑造好自己的角色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性化的表演映衬而托举起戏中的生、旦主角,即业内俗称的“合得严”。基于此,梨园行亦有“无丑不成戏”之谓。
在古老昆曲漫长的舞台表演艺术发展历程中,不乏优秀的丑行表演艺术家。但至清末,随着伶人业已年老力衰,昆曲却落入后继乏人的窘境。幸有苏州、上海昆曲家贝晋眉、徐镜清、张紫东等富有远见卓识的先贤,于1921年8月在苏州城北桃花坞五亩园创办“昆曲传习所”,“传”字辈50余位学员不失时机地将昆曲表演艺术原汁原味地承传了下来。王传淞、华传浩、周传沧等表演艺术家便是其中昆丑学员的出色代表,为新中国昆剧表演艺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作为苏州“昆曲传习所”之苏系第四代“弘”②现代昆曲表演按“字”排辈始于1921年秋创办的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弟子,其中有谨严的择取“艺名”规则。新中国成立后,江苏昆剧院在“传”字后依次以“继、承、弘、扬、振”五字排辈,浙江昆剧团在“传”字后则以“世、盛、秀、万、代、昌、明”排辈,其蕴含着老一代昆曲艺术家对昆曲传承弘扬的美好祝福和期盼。字辈传承人,江苏昆剧院昆丑表演艺术家李鸿良先后师从周传沧、范继信、姚继荪、刘异龙、王世瑶、张寄蝶、周世琮等昆剧名师,矢志不渝地追求丑角特征中的丑行之美,舞台表演自然流畅而无过分修饰,幽默中包含着超凡脱俗的文化底蕴和恰如其分的艺术效果,逐渐“形成了自己细腻传神、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2],赢得南昆正宗、“江南名丑”赞誉。本文拟从李鸿良戏曲演艺人生、表演艺术风格和昆丑审美特征等三方面,探讨李鸿良舞台表演艺术成就。
一、李鸿良舞台戏曲人生
1966年7月15日,李鸿良出生于昆曲发源地——苏州昆山,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昆剧的缘分。1977年10月,江苏戏剧学校恢复建制,停招了10年的昆剧科重新招收小学生,11岁的李鸿良幸运地被录取。像许多小小少年一样,李鸿良怀揣着英武帅气舞台形象呈现的梦想,渴望像师兄柯军那样学习昆剧大武生;入学伊始,便在戏曲基本功练习方面非常勤勉刻苦、自觉自愿。当时武生组的主管老师名叫张金龙,其对学员练功要求之严格是全校乃至全江苏省都是闻名的,李鸿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的惰性,也从思想上认定“只有张老师的教鞭才能够治理身上的‘堕虫’”[3],于是便主动请求加入张老师的训练小组,留下了江苏戏剧学校校史上一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佳话,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舞台角色人物塑造打下了扎实的武功基础。
就艺术学习而言,年少的理想往往带有某种盲目性,它与先天条件的现实之间并不能达成恰切的一致性;当二者抵牾之时,特别需要一位睿智的内行引路点拨,幸运的李鸿良就遇到了这样的恩师。在入校第二年分配行当时,李鸿良古灵精怪的外表下所透露出的幽默天性,被著名昆剧“传字辈”名丑周传沧先生一眼相中,遂将这位聪明机灵、活泼可爱的小鸿良收入门下,从此开启了崭新的昆丑舞台艺术生涯。
1985年,李鸿良从戏校毕业进入江苏省昆剧院工作,舞台实践的积累使他的表演日渐成熟。正当李鸿良跃跃欲试、意欲大显身手之时,受通俗文化和港台流行音乐的影响,传统表演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演出市场急转直下、骤然萧条。为了生存,他只能惜别挚爱的昆剧舞台,回到家乡昆山创办礼仪公司,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公司办得红红火火。但离开舞台的他任凭物质生活多么富庶,因为没有精神上的依托,依然找不到生命的家园;闲暇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练习唱、念、做、打基本功,仿佛只有在与昆曲声腔相伴时,才能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不恋世间的灯红酒绿,独爱梨园的古韵留香。
1996年底,李鸿良怀着对昆曲的初心和依恋,独自一人回到南京,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昆曲舞台。因为个人能力使然和单位工作需要,从2004年开始,李鸿良被任命担任江苏省昆剧院的行政管理工作①2004年,李鸿良开始担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助理;2006年,担任副院长;2013年9月,担任院长;2019年1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责任重大、繁忙琐碎的行政工作之余,依旧坚守着那颗恒定不变的舞台艺术初心,坚持每日练功不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的勤奋精神及对表演基本功的执着追求,于无形中也带动了昆剧院乃至整个演艺集团的争相练功的热潮。艺谚云:“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江苏省昆剧院之所以能够取得“‘梅花’香飘芬芳”的骄人成绩,与剧院领导的率先垂范和对戏曲舞台表演艺术的执着痴爱密不可分。
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理念深入人心。江苏省文化主管部门为实现昆剧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最为有效的便是大力挖掘抢救传统折子戏,倡导和鼓励在职高职称戏曲演员举办“个人专场”演出,通过“个人专场”优化院团管理机制,打通院团生产传承中枢,激发演员登台表演的积极性,在相互帮衬配合中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风华正茂的李鸿良应时而动,不辞辛苦地积极投身到传统昆剧折子戏的复排搬演的创作之中。《孽海记·双下山》《跃鲤记·芦林》《幽闺记·请医》等40余出折子戏得以重现舞台,李鸿良个人传统昆剧折子戏专场演出举办了15场;大量的舞台演出实践、各种不同风格的角色人物塑造,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李鸿良的表演艺术体验,舞台演唱技艺愈发娴熟,角色特点把握更为精准,人物性格塑造日趋成熟。传统戏基本功的充分锤炼、表演演唱技艺的日渐精湛,为创演正本大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精华版《牡丹亭》中的石道姑、改编本《绿牡丹》中的车尚公,还是新编昆剧《小孙屠》②《小孙屠》系根据宋元南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同名剧目改编,其中《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先后由“永昆”于2000年、“北昆”于2003年搬上舞台;《小孙屠》系以丑为主角的剧目,编演难度更大。中的屠夫孙必贵等角色,李鸿良的舞台人物形象呈现都是那么至臻至美、得心应手。
2011年6月10日,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在四川省成都市揭晓,李鸿良凭借《西厢记·游殿》《水浒传·活捉》《红梨记·醉皂》等三出昆丑折子戏的优异表现,成功捧得“梅花奖”。在名家云集、人才辈出的江苏省昆剧院,这迟来的荣光是他个人34年昆曲艺术生涯勤劳汗水艰辛付出后的喜获丰收,更是对一位承继600年昆曲文化之根脉魂灵的传承人的认可和赞誉。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在迈向花甲之年的艺术征程中,李鸿良想做的要做到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作为江南名丑,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做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把个人丰厚的舞台表演积累传授给青年一代,做好传帮带的传承工作。他曾说:“人的生命有限,50岁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所有的昆丑戏恢复到我身上,50岁以后我会把自己学到的剧目整理好,带几个学生;最重要的是,我要努力去做一个有文化、有抱负又会演戏的艺术家。”[4]以现代审美意识和观念为指导,李鸿良将昆丑表演纯粹化、艺术化,让观众在审美感受的愉悦中体悟昆丑舞台演唱表演的声律韵味和艺术魅力。
二、李鸿良表演艺术风格
李鸿良拥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基本功,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几十年来精心研习、刻苦磨炼,他的舞台表演艺术体现在传统剧目的原汁原味传承和新编剧目创新性转化,在不断地自我突破和超越中破茧蜕变,他以表演形神兼备、唱念字正腔圆、人物塑造百变传神、心理刻画精微细腻,逐步养成适合自身特点的表演艺术风格特色。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丑副兼擅、深得精髓
昆剧丑行分小丑和副丑,“丑角应行的,基本上是好人;副角应行的,基本上是坏人。或者说,丑角演的好人多,副角演的坏人多”[5]3-4。的确,传统昆剧行当分类严格细致,小丑以好人居多,往往扮演平民阶层及以下的角色,以短打扮相为主,动作节奏相对明快;副丑以反面角色居多,往往扮演位高权重的官生或财大气粗的地主恶霸,此类角色穿着官袍长衣,动作沉稳、节奏平缓。因为两类角色形象反差很大,常见的昆丑演员中一般只能二者得其一,较少能够二者兼擅;而李鸿良以其非同寻常的天赋和后天勤奋钻研努力,练就一身兼通两路的过硬本领,二类角色表演切换得心应手、恰到好处。著名戏剧家张寄碟先生观看了“臻丑臻美——李鸿良个人专场”①2010年11月5日于江苏南京紫金大戏院隆重举行。的现场演出之后,不无感慨地赞叹道:“他真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昆丑演员!”
在李鸿良应工的丑角戏中,经其精雕细刻,塑造了许多形态迥异的人物形象。比如折子戏《孽海记·双下山》中天真机灵的小和尚本无;《渔家乐·相梁》中心地善良,救人于水火中的相士万家春;《红梨记·醉皂》中醉酒后出尽洋相的皂隶陆凤萱;《袖褥记·教歌》中落魄潦倒的苏州阿大等。其中,经典剧目《十五贯》之《访鼠测字》②讲述的是苏州知府况钟觉得尤二命案另有隐情,故假扮测字先生到高桥暗访,在城隍庙巧遇真凶赌棍娄阿鼠,内心惶惶不安的娄阿鼠在况钟的巧言探询下供出实情的故事。一折中娄阿鼠的形象则尤为出色、令人记忆深刻。李鸿良扮演杀人逃逸的娄阿鼠,一出场便采用屈腿缩胸的姿态踮步上场,面部时不时地抽动,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慌张与害怕。起初与况钟交谈时,娄阿鼠弯腰站立,双手盘于胸前,心情放松,毫无戒备。当被测字先生测出那家人姓尤时,他又如同受惊的老鼠,紧张地向后仰去,跌倒在地,紧接着慌慌张张地钻过长凳。这一连串连贯且紧凑的动作,将娄阿鼠心慌意乱而手足无措的内心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副丑戏,李鸿良演起来更是令人拍手称奇。如他扮演过折子戏《西厢记·游殿》中爱吃酒肉又具英雄气概的和尚法聪;《跃鲤记·芦林》中唯母命是从的书呆子姜诗;《鸣凤记·吃茶》中为登高位、趋炎附势的奸徒赵文华;《水浒记·活捉》中难改风流本性、沉迷女色的平民小生张文远等。其中,《鲛绡记·写状》③此剧讲的是临安恶讼师贾主文见钱眼开,贪婪成性,人前假装信佛,人后却做尽伤天害理之事的故事。中恶讼师的形象与小丑戏中的形象反差较大,表演更具挑战性。舞台大幕拉开,一位口念佛经,手拿佛珠的老人步履蹒跚出场,一声声冷笑,听得人不寒而栗。李鸿良在设计这一人物时将其整体表演节奏有意识放慢,一是为了符合人物年龄,二是为了凸显人物内心的城府。当剧中刘香玉拿出银子时,二人为了银子的摆放几经拉扯,贾主文更是多次寻找理由借机将银两收入囊中。这表演来源生活,却又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也正是通过这一举动借机嘲讽了贾主文的见钱眼开。他为了拿更多的银两多次推脱,甚至拿菩萨来做挡箭牌,当事成之后,奸诈的嘴脸又与开头静心念佛的场面形成强烈的对比,更显人物狡诈。这一出折子戏内心情感十分丰富,李鸿良曾说这出戏他藏了20多年,只为在40岁之后将其搬上舞台,以更加臻美的舞台形象地呈现给观众④2018年9月5日上午9点—12点,李鸿良应邀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厅作题为“至美的昆丑——昆剧丑行表演艺术”讲座;在现场聆听与观赏的过程中,被李鸿良惟妙惟肖、趋于化境的示范表演和演出所深深打动。。无疑,20多年等待中的积累非常值得。
无论是演绎心地善良,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还是外表斯文、内心奸诈的文人,李鸿良均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丑与副之间,通过演绎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丑角人物让人们感知世间百态。
(二)基功精湛、以技表艺
中国戏曲中有一个专门扮演滑稽风趣、性格爽直或品行奸刁底层女性的角色,被称为“彩旦”⑤川剧称“摇旦”,秦腔谓“媒旦”。,年纪较长者则称为“丑婆子”。彩旦角色唱少白多,重在做工,演员装扮和肢体表演都十分夸张,擅长调剂舞台气氛,烘托喜剧效果。昆剧“传字辈”名丑华传浩曾说:“其他剧种有彩旦一门,专演相貌丑陋、行为不正的中年、青年妇女,昆班统归丑角应行,代表人物是《风筝误·惊丑》里的詹爱娟。”[5]38李鸿良在《风筝误》中不仅能够成功在《前亲》中饰演自己的本行詹爱娟的相公、纨绔子弟戚友先,同样能够点上大黑痣,在《惊丑》中演活容貌丑陋的大小姐詹爱娟。《惊丑》是清代大剧作家李渔名篇《风筝误》中的第十三出,伴随着音乐响起,一个扭捏作态的背影走向舞台,只是一个出场而未从开口念唱,台下观众便已发出了阵阵的欢笑,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詹爱娟的整妆、碎步、兰花指充分调动丑旦的表演特点,对女性动作的模仿虽然少了一些女性的优雅妩媚,多了几分夸张巧拙的肢体摇动,却恰到好处地把詹爱娟粗鄙放荡、急色难耐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彰显人物独特的喜剧效果。当【渔灯儿】曲牌即出,李鸿良扎实唱功更是得到充分的展现,真假声区转换是那样的自然妥帖、不露痕迹,唱出了詹爱娟内心对异性欢愉的迫不及待,将一个刁蛮任性的詹家大小姐形象塑造的入木三分。李鸿良擅长采用丰富的表情和灵动的肢体语言,从形态和神态上两个方面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活灵活现、引人入胜。他曾成功塑造了《牡丹亭》中的石道姑、《白罗衫》中的小尼姑等多位男扮女装的角色,还计划专门举办男扮女装的演出专场,足见其喜剧性功力之深。
丑行表演以幽默谐谑为特色,表演上追求以技表艺,优秀的丑行演员大都不仅仅满足于获得观众的笑声与叫好声,他们在表演上追求独特的技巧性,并创造特有的“绝活”来吸引观众。李鸿良在学戏的四十多年中勤奋刻苦,不耻下问,已学习传统昆丑折子戏45出,大戏十余本,演绎的昆丑角色高达149个。在此过程中,他注重加入自己的思考,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再度创作,为舞台上角色的塑造增色不少。在《孽海记·双下山》中,李鸿良饰演的小和尚本无向往世俗的居家生活,在私逃下山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从庵中逃出的小尼姑色空,便有了戏中“衔靴蹚水”的一幕。他扮演的小和尚本无口衔一双厚底靴背着小尼姑色空涉水过河,途中调皮的色空突然开口道:“有人来了。”本无吓得赶紧甩掉了口中的靴子。这一“甩靴”的动作,前人有将两只同时甩向一边的,也有先后甩向舞台两侧的,而李鸿良则练就“一口开双花”的甩靴绝技,只见他一个甩头,一双靴子几乎同时掉落到舞台的两端,创造了意想不到的舞台美感。但李鸿良为了练习这一绝技,整整花了7年时间并咬破了17双靴子方得成功。而今,李鸿良早已将这一绝技传授给了下一代,昆丑绝技将继续在第五代传承人身上放射出耀眼的艺术光芒。
(三)文戏武演、自成一格
“文戏武演”就是指以唱、念为主要表演手段的文戏中,加入精彩的做打表演。李鸿良“四功五法”基本功扎实,专业素养全面和艺术造诣雄厚形成了“文戏武演”的表演艺术风格。《义侠记》是昆剧著名的“五毒戏”①通常系指模仿壁虎、蟾蜍、蜈蚣、蜘蛛、蛇五种动物的造型所表演的五出剧目,但“五毒”之“五”只是概数,也有蝎子等说。之一,丑角武大郎要模仿蜘蛛形态,呈现“矮手矮脚矮子步”的特点,非常考验演员的基本功。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需全程蹲下表演,手脚向内收缩,胸前用棉絮垫起,极力模仿蜘蛛的外形。在《游街》一折中,李鸿良扮演敦厚老实的武大郎,在技术形似的基础上,努力追求神似上的超越。只见武大郎上身着一件蓝色棉稠茶衣,下身穿一条白色百褶裙,全身几乎包于衣内,只有肚子处鼓起,活像一只大腹便便的蜘蛛。当他从郓哥口中得知打虎英雄就是自己的小弟武松时,得意地说道:“我们兄弟两个从小没有爹娘,是靠我武大郎卖卖烧饼,把他抚养成人,就是他打老虎的本事,也是我教他的。”一个是威武健壮的打虎英雄,一个身材矮小的卖烧饼郎,想到这二人的差距,郓哥则嫌弃道:“又在吹牛了。”为了打消郓哥心中的疑惑,大郎急忙为自己解释:“那么,我打两记(下)给你看看。”随后,他抓起水袖,利落地转身,踮步走起圆场,并打了一套动作利落而颇具特色的“矮子拳”。他忽而悄然行走,忽而快速往返,在慢走时,抬腿亮鞋底,展示稳健的“矮踹脚”;快步时则相反,追求行走的平稳性,最后的“飞脚”加上360度的转身,整个过程动作行云流水,样态可掬,一气呵成。
因为在《游街》中“矮子拳”的出色表演,李鸿良获得了第五届江苏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有了这次成功的舞台实践经历,在李鸿良心里又悄悄地萌生了创造新角色的想法。2005年江苏省昆剧院创演《小孙屠》,李鸿良以小丑应工率真耿直屠夫孙必贵成了领衔主演。虽然《小孙屠》剧本尚存,但舞台演艺形态早已绝迹,舞台演唱表演、人物形象塑造全靠个人揣摩和创造。李鸿良从全剧的整体着眼,在细节上下功夫,将一个爱憎分明、幽默善良的市井底层小民形象极为成功地立于舞台。特别是根据剧情发展和角色心理变化需要,将“矮子功”②张继超在《昆剧丑脚研究》中对“矮子功”的基本动作、剧目、出处等进行了整理叙述,他认为此身形的特点是缩手缩脚,使演员变成“三寸丁”的矮子。技艺给予适当调整与合理变化,三次运用“矮子功”,犹如行云流水,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在第一幕中,他因哥哥娶风尘女子进门与母亲观念上产生分歧,故生气地跳上椅子,拖着椅子跳跃前行,以此来躲避母亲的打骂。这一次“矮子功”的运用是将日常生活给予喜剧化夸张,体现母子二人之间浓郁的亲情。在第二幕中,为探听嫂子在房中与陌生人的对话,他运用“矮子功”踱步至窗前,洞悉房中的一切,体现小孙屠的谨慎;在第五幕还魂中,见到仇人分外眼红的小孙屠用“僵尸跳”与“矮子步”结合的方式与之打斗,表现他内心的愤恨之情。李鸿良通过不同的展现方式来表现不同场景下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将一位心地善良、爱憎分明的下层市民屠夫成功展现在舞台。戏曲理论家俞为民对此亦有中肯的评价:“李鸿良在扮演小孙屠这一人物时,既借鉴了传统昆剧丑行既有的程式,又结合小孙屠这一特定人物,作了创造性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幽默淳朴、疾恶如仇的下层小人物屠夫的形象。”[2]
三、李鸿良昆丑审美特征
丑行从舞台的装扮形象而言,的确算不上俊美帅气,但内在的品质却同样是值得尊崇的;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多是阴险狡诈、猥琐奸猾之流,但也不乏刚正不阿、正直善良的人物。昆丑“传”字辈大师王传淞一再强调:“戏曲的表演,里外都应讲究一个‘美’字。”[6]作为一个行当的代称,“丑”并非与“美”相对立审美范畴,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作“子丑寅卯”之中性的序号词来看待。所以对于任何一位丑行演员来说,“丑”只是其舞台上诠释中国传统戏曲艺术魅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通过这种脸谱化的模式、充分调动程式化的表演手段,让观众在对舞台上“丑”的人物形象的欣赏,获得艺术上的审美享受和满足,这正是作为昆丑表演艺术家的李鸿良最本真的艺术追求。
李鸿良曾说:“我既不做复古派、保守派,我也不做肢解昆曲的创新派,我既做继承者,又做创新者,保守和探索并行。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保证传统不走样、汲取昆曲传统百分之百养分的前提下,做一些让现代人更能接近昆曲本体艺术的小改动。”[7]李鸿良转益多师,在承继师辈舞台表演艺术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与体会,锐意创新与发展,从而形成了凸显个人特色诙谐奔放、生动传神的表演艺术审美特征。
(一)清晰流利、即兴风趣的念白
戏曲表演非常讲究“四功五法”①“四功”即指“唱、念、做、打”。“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但程砚秋先生认为“五法”系指“口、手、眼、身、步”五法(参见《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载《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而昆丑“四功”中的“念”则独具特色。华传浩将对昆丑念白的要求概括为“语言洁净,方言熟练,咬字准确”[5]13,字数虽不多,但却承载着念白的技巧。例如《鲛绡记·写状》一折,它以念白、表演为主,是传统昆剧中只“说”不“唱”的经典剧目。因为念白时没有乐器伴奏,音高韵律上没有参照借鉴之处,只能通过改变音量高低、语速缓急、音调的抑扬、顿挫来塑造贾主文这一人物,将内容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让其感受到念白之美。李鸿良自身具有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自入行伊始便深知学习掌握各地方言语音之于丑角演员的重要性,在方言音韵的声调语义上细心辨识,在吐字发音上苦下功夫,这样长此以往就熟练掌握了多种地方语言,为人物形象鲜活塑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在《西厢记·游殿》中小和尚法聪和在《绣襦记·教歌》中的阿大,说着一口标准的苏州方言;而在《红梨记·醉皂》中的扮演陆凤萱,则是念着一口纯正的扬州话白,其发音之精准几近于乱真,极大地增强了角色人物插科打诨的喜剧功能。舞台表演过程中,还常常根据人物角色所处的场域,穿插运用不同地域方言在念白中作即兴发挥,展现昆丑在语言道白上的独特魅力。
(二)生动活泼、幽默滑稽的表演
丑角多扮演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动作通常是缩手蹲脚、手舞足蹈,看起来风趣幽默、生气勃勃。如在《孽海记·单下山》中李鸿良饰演天真可爱的小和尚本无,全出表演夸张,身段灵巧,深得观众的喜爱。一出场,小和尚以袖遮面,抬腿登步上场,手持佛珠,先是背对观众,随后分别向右向左转身亮相,并伴以张嘴缩颈等动作,极力模仿蛤蟆形,这一连串的出场动作展现出本无的机灵可爱。小和尚在回忆自己刚上山拜师的情景时,念道:“我那日进了山门,见了师父,我就深深作个揖。”说着便向地上趴去,同时顺势将双手双膝缩于胸前,后脚向上翘起,活似一只生动的蛤蟆。他经历一番思想斗争,依旧决定下山,在拜别菩萨时,又连续两次纵身扑下,重复上述动作,将蛤蟆蹦跳时的场景模仿得惟妙惟肖。下山途中,本无看到远处走来一位小尼姑,为与其搭话,又在此展示了可看性极高的“转佛珠功”,整段表演较好地体现了昆丑表演的神韵。
(三)以小见大、凸显品性的人物塑造
丑角常扮演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不完美但整体善良,身上有着独特的闪光之处。演员在诠释这类人物时需要精准拿捏角色本性,站稳民众立场,凸显最真实的人物品性。如在《牡丹亭》中,李鸿良饰演因天生缺陷被封建社会抛弃的石道姑,她虽惨遭夫家抛弃,但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相反,她不忘帮助杜丽娘,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在“回生”一折时,她说道:“我虽落得个红鱼青磬,也蛮高兴见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管他人话鬼话,我也要帮他一把。也不怕盗墓挖坟砍头。”[8]可见,石道姑外形虽丑,但她的内心热情善良且有情有义。在《小孙屠》中,李鸿良饰演的小孙屠虽只是不起眼的市井小人物,但他心地善良、爱憎分明、颇有孝悌之心,最终用正义战胜了邪恶。昆剧丑角的表演暗含对是非的明辨,对好恶的判断和对人性的考验,其表演内涵十分丰富。
结 语
在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百花园中,丑角虽然只是调节气氛的配角,但要演好却是难上加难,甚至比生、旦更难应工。李鸿良深知其中三昧,他苦修勤练“内功”,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在原汁原味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独到的见解,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丰富了昆剧丑行的表现手段,赋予昆曲新时代的生命力。正如戏剧评论家孙书磊所言:“丰富的阅历与心得,自然是李鸿良昆丑表演能够达到炉火纯青境地的重要保障。执着而刻苦的精神及其对生活的明透洞察,正是推进其昆丑艺术一步步走向更高境界的动力。”[9]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鸿良的执着和付出终于获得了认可和回报,他先后获得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表演奖”、中国昆曲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促进昆曲艺术奖”②此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共同颁发。和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奖项,2015年获得国家授予的“艺德楷模”称号等诸多荣誉,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昆剧表演人生的绚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