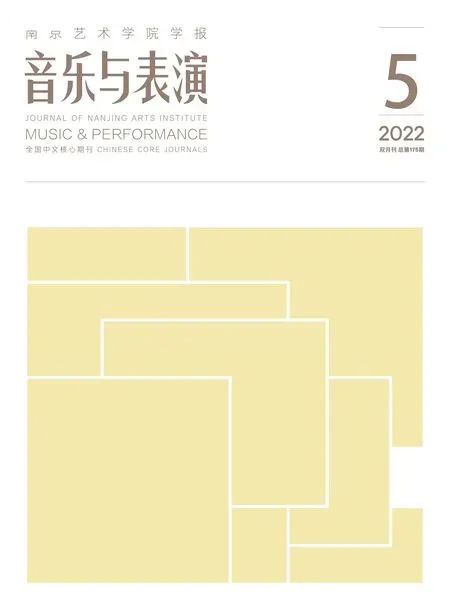王阳明的戏曲观及晚明传奇对阳明形象的塑造①
张婷婷(江苏开放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6)(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自明代嘉靖年间以来,中国艺术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呈现出新的气象:从程朱理学僵化的束缚中,涌动出一股反思传统、个性解放、自由率真的艺术思潮,掀起绘画、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风气的共同转向。艺术作为晚明社会思潮的审美表现形式,始终保持着与心学理论契合一致的发展态势,不仅体现了特定的时代风尚和审美旨趣,同时也凝聚了心学的思想资源与智慧精神。
阳明心学并非仅仅于哲思理论形态上的自足,当时甚至延至晚明各门各类之艺术思潮亦多受其沾濡,影响巨大。“心学”成为文人突破传统,寻求内心光明所依托的哲学思想,他们以艺载心,视艺术为“心灵的光明”,追求发端于内心最为本真的自然美,以怪诞、奇异、梦幻、脱离藩篱等艺术形态,张扬个性、表达自我,通过“异端”的审美表达,打破传统僵化与禁锢的艺术风格,形成晚明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表现风格。
这一时期,绘画、书法、琴乐、戏曲等各门类艺术,都呈现出艺术表达与艺术审美的相似性。尤其是戏曲艺术,从明初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教化剧,转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浪漫主义风格。以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为代表的剧作家,掀起戏曲舞台“至情”与“至性”的浪潮,以“性情化”的浪漫主义创造舞台形象,以对“本色”风格的追求,扭转文人“雕饰”的虚假文风,使得中国戏曲艺术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王阳明本人对充满生机的民间戏曲大为激赏,认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艺术,通过舞台演绎人生,“将高高在上的天道、天理直接转化为日用伦常中的普通行为,以戏剧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指点观众当下自觉自悟的人性”[1]。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戏曲观,对晚明的曲学观念与创作实践均产生了影响,尤其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本就是一部“传奇”,被晚明曲家剪裁、编创,出现了多部描写阳明的剧作,蔚成晚明戏曲艺术的一景。
一、激人恳切 触动良心:王阳明的戏曲观
如果说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灵魂,那么阳明心学就是扣响晚明的时代之音。阳明对“师门学问接力式的再继承和再发扬,不仅在工夫或实践方法上丰富了个人心性体证的经验内容,而且也在民众接受或传播的范围上扩大了心学思潮发展的社会空间”[1]。哲学与艺术,并非完全相隔的两个领域,心学思潮通过艺术化的形式载体得以呈现,艺术又以不同的物质媒介呈现文人内在的哲思。
在王阳明心学系统中,生命的本体的实践功夫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例如,他“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的原因时,便强调:“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2]既突出了亲证亲历直入生命本体的要求,又依体活泼,发用流行,不仅要“明明德”,也要“亲民”,内外兼顾并重,浃然合为一体,才谈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践之功”。因此,在心学思潮的影响下,晚明时期的传统艺术走向了注重内心的体验,强调源自真性、发自本心、一派生机活泼的艺术表达。文人艺术家将内心的般般意绪注入作品,在世俗的生活中营造一片艺术的“理想国”,寄景于画、托情于乐,借此抒发“一念之本心”的善美,表达内心压抑、超脱、自由、洒脱的多重心境,从而获得生命的安顿。无论书画观念、琴乐思想、戏曲主旨,均体现出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人格独立精神的宣扬,以此反拨艺术创作僵化而教条的风气。
王阳明本人对戏曲的认识,从他的诗歌便得以窥见:“处处相逢是戏场,何须傀儡夜登堂?繁荣过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线长。稚子自应争诧说,矮人亦复浪怨伤。本来面目还谁识?且向樽前学楚狂。”[3]
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受阉党刘瑾迫害,被贬至贵州修文龙场,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难,但这又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龙场悟道、创办书院、开设讲坛、传道授业、昌明圣学,使贵州文教大兴。在此期间,阳明得见当地的戏曲演出,有感而作《龙场傀儡戏》,诗中透露出当时傀儡戏在夜晚演出的情景:艺人以绳丝操纵木偶进行表演,男女杂坐,随意谈笑。乡闾小戏充满小传统的民俗风情,也展现出一方人文风俗的景观。阳明感悟人生如戏,被名利牵绊的人们,如同戴上面具的偶人,失去了本真之心。然而,戏剧虽是小道,但通俗易懂、生动鲜活,易于被民众接受,尤其是将“善”的内容融于“美”的形式,可以化民善俗。
在《传习录》中,阳明有言:“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4]
王阳明对戏曲并不否定,甚至认为周代的《大韶》与《大武》均是诗、乐、曲、舞结合的“戏”, 包含一定的叙事因素。虞舜“作《大韶》之乐”[5],是为了歌颂舜帝治国的明德;《大武》则叙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其德行一经艺术化的方式演绎,具有贤德之心的接受者,自然能明辨其中的艺术之“美”与道德之“善”。戏曲艺术本就通俗,尤其民间戏曲“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6]。浅白易晓的艺术形式,最容易感染愚俗百姓。若寓于美善道德,沿袭《韶》《武》古乐传统,演绎圣人事迹,给予观众相应的情感体验,使其感同身受,激起内在本有的良知,便能厚民德、正风俗。
阳明本人亦有多首散曲作品留存于世,例如正德二年(1507)创作南曲套数《归隐》,以【南仙吕入双调】连缀【步步高】【沉醉东风】【忒忒令】【好姐姐】【喜庆子】【双蝴蝶】【园林好】【川拨棹】【锦衣香】【浆水令】【尾声】等多首曲牌,首尾相接、结构工整。曲中“对邻翁野老,饮三杯浊酒村酸,醉了还歌笑”等曲句,一方面表达出阳明赴谪贵州龙场途经杭州时,内心对阉党的不满与归隐山林的向往,一方面亦可见出他喜以时调俚曲咏叹抒情。尽管从曲律的角度看,套数《归隐》不甚完全合律,但曲中的真情与豁达,足以弥补曲律之不足。诚如曲家王骥德评价:“【步步娇】‘宦海茫茫京尘渺’,又儒先大老之笔,不得以曲道绳之耳。”[7]该曲亦被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收录于《曲选》。又据《年谱》记载,阳明初到贵州龙场,自然环境恶劣,“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8]1395,加之跟随阳明的仆童陆续染疾,生死未卜,阳明则入厨亲持炊事,又歌咏家乡越调,安抚病人,“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8]1395。正德三年(1508),阳明又作南曲套数【仙吕·甘州歌】《恬退》,以诙谐的笔调,咏唱困居偏远山区村庄,终日“心底宽”“枕书眠”的阔达与不羁:
【南仙吕·甘州歌】归来未晚,两扇门儿,虽设常关。无萦无绊,直睡到晓日三竿。情知广寒无桂攀,不如向绿野前学种兰。从人笑,贫似丹,黄金难买此身闲,村庄学,一味懒。清风明月不须钱。
【前腔】携年傍水边,叹人生翻覆,一似波澜。不贪不爱,只守着暗中流年。矗盐岁月一日两餐,茅舍疏离三四间。田园少,心底宽,从来不会皱眉端。居颜巷,人到罕,闭门终日枕书眠。
【解三醒犯】把黄粮懒炊香饭,凭教他恣游邯郸,假饶位至三公显,怎如我野人闲。朝思暮想人情一似掌样翻,试听得狂士接舆歌未阑,连云栈,乱石滩,烟波名利大家难,收冯铁,筑傅版,尽教三箭定天山。
【前腔】叹浮生总成虚幻,又何须苦自熬煎。今朝快乐今朝宴,明日事且休管。无心老翁一任蓬松两鬓斑。直吃到绿酒床头磁瓮干。妻随唱,子戏斑,弟酬兄劝共团圆。兴和废,长共短,梅花窗外冷相看。
【尾声】叹目前机关汉,色声香味任他瞒,长笑一声天地宽。①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补编[M].束景南,查明昊,辑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4-55.此套曲是否为王阳明所作尚有争议,《吴歈萃雅》《词林逸响》《南音三籁》《古今奏雅》等曲集,均题作“恬退”,俱注王阳明作。而在《三径闲题》中无题,署王尚书撰;《群音类选》题作“闲情”注王思轩撰;《新编南九宫词题同类选》,署王思轩尚书著;《乐府先春》无题,属罗念庵;《乐府争奇》无题,不注撰人。未知孰是。但该曲被《王阳明全集补编》收录,又被多部研究王阳明的专著反复引述,兹姑以为王阳明撰。(参见谢伯阳.全明散曲[M].济南:齐鲁书社,2016:459.)
从曲子的结构看,王阳明深谙南曲的曲牌联套规则,用南仙吕宫中的【甘州歌】连接【解三醒犯】并加尾声的形式组成一套,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语调,操词觚曲。其中“妻随唱,子戏斑,弟酬兄劝共团圆”等词曲,亦可见阳明的生活世界中常常以曲怡情,快乐自洽。
纵观王阳明的戏曲观,不论是以戏触动人心,达成感化性的教育理念,还是以舞台人生的演绎移风易俗,都体现出他的致良知之教以及以心性为本的思想特征。艺术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艺术的情态是一种“活”的情态,它像一扇窗口,又如一道透视镜,创作者总是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的品评融入其中,用作品聚集起不同时空的在场者与不在场者,透过作品显性或隐性的意涵,去贴近创作者的心理世界,发现性灵世界本有的纯真。如同海德格尔所言:“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了。”[9]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中,“致良知”作为一种实践性工夫,一方面自能自觉其是善还是恶,另一方面也能为其善而去其恶,恢复重现其纯然至善之心体,也就是让最能代表人的主体性的内良知彻底敞亮。无论是圣人还是愚夫愚妇,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胸中各有个圣”,只是被遮蔽了。一旦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开启观者的本心,便能刮垢磨光,令其豁然敞亮。如果以戏曲编演忠臣孝子的故事,并使其在民间广泛流传,那么愚俗百姓的“良知”就会被激起,这是有益民风民俗的。
二、动人最切 移风易俗:戏曲的功能
阳明认为戏曲能“感激良知”“有益风化”的观点,对晚明戏曲影响较大。历来被视为“小技末道”的戏曲,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被晚明甚至清代文人所重视。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融入戏曲创作,在传奇剧作中构筑起理想的世界,寓于人物的善恶美丑以褒贬,以戏曲艺术为载体,在民间进行有效传播,通过生动活泼的剧场效应,激起“愚夫愚妇”心中的良知,达到净化风俗的目的。例如堪称宋明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有明三百年学术之殿军的刘宗周(1578—1645),开创了蕺山学派,其学脉滥觞于甘泉学,受阳明学影响颇深,他在《人谱类记》中,引述陶石梁的观点曰:
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废。但其中所演传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从此设法立教,虽无益之事,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也。先辈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至于《渡蚁》《还带》等剧,更能使人知因果报应,秋毫不爽,杀盗淫妄,不觉自化,而好生乐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则虽戏而有益者也。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独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可不深戒哉!”[10]
刘宗周看到戏曲正方两面的作用,戏曲自起发端之始式,便与祭神等宗教仪式密切相连,融合在民间风俗中,具有“娱神”功能的祭祀表演,常融入“娱人”的世俗戏剧内容,在宴饮娱乐的场合表演。就内容而言,既有忠臣义士的题材,也有男女私媟之事的表演,前者具有“移风易俗”之功能,后者则有伤风害俗的危害。戏曲舞台空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三教九流的观众群体聚集在公共性的演出空间,暂时消弭身份差距,“离开”现实生活,最容易被“带入”舞台构筑的情景,被引发情感上的共鸣,内心受到触动。如果戏曲内容淫谑亵秽,逗引观者淫靡之心,不能不为刘宗周等儒者所不齿。反之,若融于孝悌忠义的内容,激发人心的良知,能让观众走出剧场之后依据内心的感发践行良知,戏曲便能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
阳明“致良知”理论,不是空洞僵硬的理论说教,不是抽象刻板的教条训练,而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理论。艺术创作实践必然离不开主体能动的“心”的运思行为及方式。特别是受到心学影响或根本就是心学人物的文人群体,他们大多将艺术本体的活源追根溯本地归为人之本心,源自心性有体有用的“良知”往往便成为审美判断的标准。诚如阳明所言,良知就是无人不具的“定盘针”,是判断是非的最本源亦最重要的本体论依据。
戏曲演出具有一种剧场效应,观众在特定的观演空间观赏角色的喜怒哀乐,甚至将自身融于角色之中产生“共鸣”与“共情”。观众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便能激烈悲苦;观流离患难,虽村妇、孩童立即涕泗横流。从本质上看,戏曲是“人”的艺术,表达人的情感、展现人的世界、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贴人情、关怀人心,以至诚感人的唱念做打形式,直抵人心、感化观众。相较于照本宣科地讲经说法,戏曲更能激发起人的好生乐善之念,激发观者心中的良知,生发真善之念,自化贪嗔之欲。如果人人都能依据心中敞亮的良知, “行良知”,就可以起到净化风俗、淳厚民风的作用。因此阳明及其后学,均重视戏曲的功能。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就曾言:“市井之愚夫、愚妇,看杂剧、戏本,遇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触动良心,至悲伤泣涕不自禁,卒有敦行为善者。吾辈士夫自幼读圣贤书,一得第后,即叛而弃之,到老不曾行得一字,反不若愚夫、愚妇看杂剧者,虽谓为市井之罪人可也。”[11]乾隆时期,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的陈榕门,将刘宗周的戏剧观作为规范,在《训俗遗规》中评价道:“《人谱类记》一则,与阳明先生之意相发明,均为近时良药,故附录于此。更有演戏不以邪淫为戒,偏以悲苦为嫌,以姓名为讳,则其惑尤甚矣。”[12]戏曲以通俗易懂的舞台形式,激发人的为善之心,为心学者所重视,也引起晚明文士对传奇表现真心、真情以及独抒性灵的创作探索。
三、精忠正直 平定宁王:王阳明形象的塑造
阳明心学思想对晚明戏曲观念的影响甚大,又因其传奇的人生经历,本来就具有戏剧性,成为晚明曲家热衷创作的题材,出现不少以阳明事迹为情节的剧作。例如徐渭在《南词叙录》著录“本朝”传奇中,就有《王阳明平逆记》。明末殷启圣选辑的《尧天乐》一书,为弋阳腔、青阳腔剧本单出选集,在下卷中收录《娄妃谏诤》《点化阳明》两折,题《阳春记》。故事围绕王阳明平叛宁王朱宸濠而展开,《娄妃谏诤》剧写娄妃劝谏宁王,勿生谋反之心,宁王不听劝谏,一心要攻占南京。《点化阳明》剧写时任南赣汀漳巡抚的王阳明,从赣州顺水而下,去福建处置兵变之事,行至楚江渡口时,无桥无舟,难以渡江。许真君扮成渔夫载其渡江,王阳明向其打探宁王消息,许真君暗示宁王朱宸濠叛乱,以谶语勘破:“急水滩头着一篙,浪涌舟儿不见梢;水里寻剑剑不见,海里捞月月难捞。”[13]阳明参透机关,将计就计,转回吉安,领兵大败宁王。《点化阳明》又被《乐府菁华》卷五收录《真君点化阳明》一出,题作《护国记》。可见阳明的故事,随着弋阳腔、青阳腔等民间声腔的流行,已家喻户晓。晚明曲家吕天成,撰有传奇剧本《神剑记》,以阳明一生事功为情节,晚明曲坛盟主沈璟在《致郁蓝生书》中对此剧评价道:“《神剑记》,为新建发蕴,可令道学解嘲。”[14]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则评价该剧:“以王文成公道德事功,谱之声歌,令瞋笑皆若识公之面,可佐传史所不及。曲白工丽,情境宛转。”[15]只可惜《神剑记》全剧已佚,未能窥见其貌。①戏曲学者周育德认为:“《南词新谱》收《神剑记》之【正宫·半阵乐】曲外,其余均不传。” (周育德.汤显祖论稿[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87.)此后吴书荫等学者都依周说。但核查《南词新谱》卷四【正宫·半阵乐】一曲,题为“《神镜记》吕勤之作”,《神镜记》为吕天成所作传奇之一,剧写剑侠聂隐娘之事。从【正宫·半阵乐】曲文内容来看,也与聂隐娘故事相关:“蝶翅巳催花信,鹊声暗送春晴。怕说词章,懒评诗酒,忽觉客窗孤另。”(词隐先生,编著;鞠通生,重定.南词新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5:214.)据此推断,该曲非《神剑记》之曲文,也非有关王阳明道德事功之故事。(吴书荫.汤显祖及明代戏曲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43.)
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曾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撰传奇《玉搔头》,此时距离甲申(1644)明亡未远,剧中叙写明朝正德皇帝与妓女刘倩倩的爱情故事,将王阳明塑造成精忠报国的形象。遗民诗人杜溶(1611—1687)为该剧作《序》云:
《玉搔头》者,随庵主人李笠翁所作。其事则武宗西狩,载在太仓王长公逸史中。其时则有逆藩之窥觊,群邪之盗弄,王新建(守仁)之精忠,许灵宝父子之正直,及刘娥之凛凛贞操,无一不可以传,而惜未有传之者。乙未冬,笠翁过萧斋。酒酣耳热,偶及此。笠翁即掀髯耸袂,不数日谱成之。[16]
李渔对历史进行裁剪与虚构,着力刻画晚明正德皇帝荒淫无度、耽于欢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宫廷糜朽、政治黑暗、奸臣当道、国家倾危。剧中特意将宦官刘瑾(1451—1510)逐利腐败、朱彬(江彬)图谋篡位以及宁王朱宸濠叛乱(1519)等情节剪裁在同一时间发生,塑造了王阳明、许灵宝等忠义之臣,他们辅佐皇帝、力保社稷、平定叛乱,正所谓:“力保金瓯无缺陷,许灵宝的担荷非轻,削平藩乱定家邦,王新建的功劳最大。”[17]219-220剧中表现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沉重的忧患意识,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王守仁这一角色。他登场便唱道:“自从纱帽笼头,这身躯便非我有。又何待位高贵重方眉皱,少不得拼性命奠金瓯!朝内的事,有贤乔梓主持,分明是鼎开三足防倾覆,外面的事,晚生虽然不才,也做个柱立孤峰抵急流。各自把肩承担也,便做道山穷水尽,也难忍丢手”[18]阳明赤胆忠诚的形象跃然纸上。李渔以《分任》《讲武》《极谏》《避兵》《止兵》《擒王》等六出戏,演绎了王阳明的形象。尤其在第十出《讲武》,阳明一人独唱一套北曲,叙述了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赣州,平定宁王的经历:
【鹊桥仙】(小生带冠,引众,末扮中军随上)弭奸无策,养痈贻悔,忧国丹心如坠。一方有事万邦危,患不止东南半壁。
庸儒个个说修身,大事临头辨始真。若使力行无实效,从前讲学尽欺人。下官王守仁是也。自蒙圣恩,特简授以副都御史之职,巡抚江西等处地方。自从到任以来,且喜删清政肃,吏辑民安,富舍清闲,可称卧理。只有两件事情放心不下,阕得下官出京之后,皇上即为奸人所惑,早已微服私行,至今未曾旋驾。还亏得许季升父子,在朝中竭力弥缝,还不致有非常之变,这也罢了。宁王宸濠,久怀异志,终日招兵敛饷,非谋不轨而何?此下官肘腋之患,即国家心腹之忧也。故此到任以来,日以讲武练兵为事。又曾差有细作,不时打探军情,所以宁王一举一动,无不周知。他有作乱之才,下官也有定乱之略,若使朱宸濠得遂奸谋,今日的朝廷要俺王守仁何用?已曾传谕各营将领,今日披挂过堂,趁这平安无事的时节,把兵机将略与他们讲习一番,好待临期运用。[19]250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前往福建平定叛乱,然而行至位于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时,突然得知宁王朱宸濠叛乱,他立即返回吉安,发出檄文,招募义兵,带军征讨。王阳明一生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事功,在哲学思想上大有突破。李渔在剧中塑造的阳明,一登场便批评程朱理学,穷理格物、重学轻行,“穷理”而不落实在实践之上,变成了空洞的“假道学”。因此王阳明提出要变换气质,这是生命自我改造的活动,通过修养功夫的变换,要养出圣人气象。王阳明要把良知之知转化为意识活动,又将其转化为道德实践活动,所以他倡导行良知,也就是致良知、行良知。诚如睡乡祭酒在该段眉批所言:“惟阳明先生可以讲学,以其未尝藏拙故也。四句道尽一生。可称二百年知己。”随后王阳明以两首曲子,批评程朱理学的弊端:
【小梁州】阵势坚牢不怕窥,子为着“义”作藩篱。不知邪正视尊卑。但是居尊位,不怕少军威!
【幺篇】纲常二字谁能废,便是倒乾纲也终凛天威。况有那提得起抹不煞的人心忠义,怎能勾,把帝业扫成灰![19]250
程朱理学主张“理”在人心之外,“即物而穷理”,而阳明倡导的致良知,“致”就是到达良知之境,也是行良知。行良知就是实践良知,即良知的实践化。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其在社会关系中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德目,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又根据不同的对象,有不同道德德目的开显。比如见父知孝、兄弟之间悌、朋友之间信、对国家尽忠,都是伦理德目,虽有所不同,但归到本体,就是良知。从实践的方式来看,这也是良知的流行发用,如果人人心中有“忠义”,那么国家纲纪伦常就会被守护。也如杜溶的眉批所言:“此时宸濠逆势已成,乱形未著。虽饬诸将预防,又不便明言其事,但于讲武之中字字影射,发人忠义之心,杜人反侧之念。此从来院本中第一篇细密文字,读是剧者不可不鉴其苦心。”[19]250李渔以王阳明的“忠义”之“心”而践行的“忠义”之“行”,刻画了“忠义有为”的人物形象,进而思考明亡的社会历史原因。从中也不难看出晚明戏剧中的阳明形象。
王阳明不仅成为李渔剧中的人物形象,其心学思想也被李渔借用于戏曲理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阐述戏曲中的“机趣”时说:
“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因作者逐句凑成,遂使观场者逐段记忆。稍不留心,则看到第二曲,不记头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当。是心口徒劳,耳目俱涩,何必以此自苦,而复苦百千万亿之人哉?故填词之中,勿使有道续痕,勿使有道学气。所谓无断续痕者,非止一出接一出,一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时,先长暗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才知作茧之精,此言机之不可少也。所谓无道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则得词中三昧矣。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讯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词,则离合悲欢,嬉笑怒骂,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止矣。[20]
李渔以阳明“良知”论道比附“机趣”之说,认为机趣是编剧的“灵魂”,是作者心中之灵感与天地合一而生发的灵感。人的灵性生命本来即有的秩序感和价值感,实际为宇宙秩序与价值的内在化与凝聚化。“机趣”不是学来的“道学之气”,而是人心中自然而然生发的。任何人为地、刻意地、造作地、生硬地编剧,都会使戏曲走向“板腐”,使人乏味。只有“心”的体验,以真听、真看、真感受创作,抒发情感,才能得曲中三昧。戏曲创作必须要有“机趣”,过分直白则显笨拙,需以“似与不似”、富有意味的动作、唱词、表演,使观者触机领悟。李渔诠释并引申王阳明对“乐”的看法,可谓将本真之理融于舞台表演,通过艺术的观演,通达接受者的人心之本。戏曲艺术不仅仅要实现世俗层面上的情感共鸣,还要道德层面上的追求至善,在艺术的践行活动中激起“良知”,这才是高级的创作。
结 语
心学在晚明社会生活中迅速风靡,尤其是对艺术实践与观念影响巨大。在创作中从“师古”转向“师心”,出现大量表现出抒写真情、崇尚“知行合一”的艺术实践。文人从内心中寻找“理”,又通过艺术的形式避俗求真,展露心灵的生机与灵气。阳明的心学思想吸引了不少文人群体的主动认同,实际已成为晚明士大夫内部儒家价值传播的重要思想内容。徐渭、冯梦龙、祁彪佳、孟称舜等人,无论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心学观念的影响,并以自己的戏曲创作验证了戏曲本色论的实践价值,从而提倡颇有心学意蕴的戏曲本色论。晚明时期,戏曲的创作出现了对主体的张扬和对压抑人性的反对,出现了肯定欲望、人性,出现冲破藩篱的倾向。一时间,能表现“真我”的“俗”成为被戏剧批评话语系统广泛使用的概念,戏剧审美观念逐渐从对“雅”的膜拜转向对“本色”的倡导。
王阳明从本体来解释情,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因此体用合一,发乎良知本真的情,才是纯净光明的。将“真情”关注于艺术的实践,并通过艺术思想的传播,会对社会的治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在晚明心学思潮影响下,艺术创作重“情”,“主情”成为时代之风气的文化哲思原因。阳明心学对于艺术观念的形成与艺术实践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可挖掘的空间。尤其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如何发掘完善自己的内在生命,以心为师,创造出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阳明的心学理论亦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来说,心学理论亦具有历史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