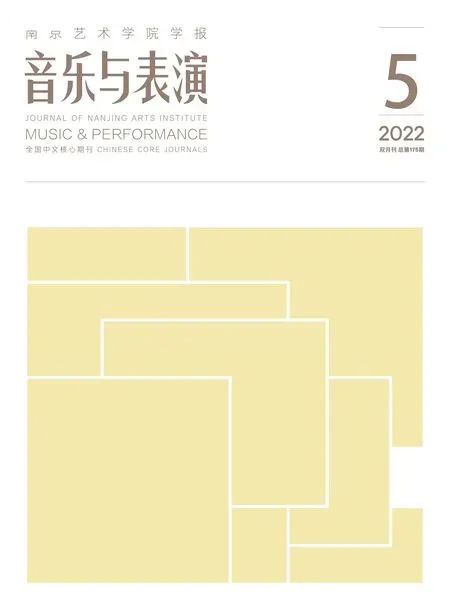元电影溯源及其精神内核探析
章云清(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龙迪勇(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引 言
“元”(Meta)作为一个英语前缀,源自希腊语介词和前缀meta-(μετά-),意思是“之后”或“超越”,表示从另一个概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一种艺术叙事的元,元叙事最早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实践。早在美国作家威廉·加斯(William.H.Gass)提出“元小说”概念之前,元小说的实践已有历史。在《荷马史诗》《堂吉诃德》中都可以找到元叙事的踪迹,18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纪德(André Gide)的《伪币制造者》也都属于典型的元小说。虽然元小说作家并未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纲领的文学集团或流派,但这些小说本身具有相同的特征,即在叙述上表现出“自我意识”的求真,或者“反身指涉”的批判,试图揭示叙述文本构建出的世界具有非真实性,在叙述中反思文本建构的过程。元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实践,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其强调的“元意识”,即作者本人的自我意识,引起了学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研究热点,围绕“元政治”“元语言”“元绘画”“元戏剧”“元批评”等术语形成一种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动能,也传导至电影艺术形式上。
电影具有再现世界完整性的特征,使观者不自觉去认同由色彩、声音、空间构成的影像世界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元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的最显著特征,即超脱出了其再现世界的使命。正如元小说作者常用揭示写作手法等方式揭示故事内容的虚构性,元电影导演常常揭露电影是如何运用镜头的运动制造幻觉,甚至通过打破连续的传统叙事结构,直接对电影本身进行评论。换而言之,元电影是内容指涉电影本身的电影。因此,学界通常称元电影为“关于电影的电影”。基于此,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元电影的内涵界定为,内容基于电影本身的具有真实性与批判性精神内核的电影。
一、元电影溯源
(一)西方元电影溯源
西方元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记录电影奠基人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电影眼》(1924),通过运用定格、多次曝光等手法来展示了电影时间的逆向流动。美国“冷面笑匠”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在《摄影师》(1928)中饰演了摄影师,围绕这一身份戏剧化地展开爱情故事。影片中,为了接近爱慕着的莎丽,基顿成为米高梅公司的新闻摄影师,无论是同莎丽第一次约会的失败、拍唐人街帮派械斗场面的失败,还是英雄救美遭受误会,最后都被电影中的摄影机所真实呈现。影片开始一个人站在巨大摄影机上的超现实画面,更意图明显地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在影片中无处不在。
维尔托夫在1929年拍摄的《持摄影机的人》是元电影又一早期实践。影片记录了城市中来自不同阶级与职业的市民,从富有的女士到贫穷的工人,从沧桑的老者到稚嫩的幼童,详尽展现了当时的城市生活。而这部影片有别于其他影片的最重要特征,便是影片中的摄影师本身就是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即维尔托夫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Mikhail Kaufman)。他在幕后安装起胶片,为即将播出的电影做着准备。而后幕布拉开、座席放下,观众们慢慢进入影院,随着乐团的演奏响起,这些观众们所观看的影片作为正片开始播出。《持摄影机的人》完整地向观影者呈现其本身拍摄、剪辑到放映的创作历程,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给观众信息。即,影片最终呈现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带有造影者思考、取舍的产物与美学思想,是创作者与社会现实的互动结果,其理念是电影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从电影艺术表达上也强调了元电影的批判性。
(二)中国元电影溯源
在早期中国电影探索中,便有作者在电影中嵌入话剧与戏曲等其他形式的艺术,随着电影语言和叙事的演进,这逐渐形成了一种导演主动为之的叙事策略。
中国元电影始于20世纪20年代,一些电影开始表现拍摄现场的情形。例如《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中滑稽大王前往明星公司参观,遇见演剧人员正在拍摄电影的场景,这是早期元电影启蒙的叙事手法。
真正基于电影的电影,我们可以通过张石川导演《可怜的闺女》(1925)戏园场景中得以体验。影片里台上表演者和台下观看者两组男女关系的同向变化形成呼应,人物在戏内戏外有多个身份,通常和所演角色在某一点产生关联,或引发人物主动代入角色抒怀,或暗示人物的宿命,相似之处合于一体,深入塑造立体化的人物。另一种是片中引用另一影片段落,例如程步高的《银幕艳史》(1931)中女演员,参观电影公司“看到”《火烧红莲寺》的云中特技镜头。这些均是中国元电影的早期探索。
1931年《银汉双星》和《银幕艳史》两部元电影在技术上达成突破,史东山执导的默片《银汉双星》,不仅再现了银汉电影公司拓展电影艺术语言的艰辛努力,也展示了无声电影时代表现声音的潜能。《银幕艳史》暴露的电影机器说明其物质性存在,肯定电影制造幻想的力量,契合造影者对电影批判性的论述,将电影中的想象、幻觉、梦境作为更复杂的戏中戏。这种方式使观影者混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元电影通过制造现实的幻象,在解构经典结构的同时思索电影与现实关系。在片中呈现拍摄电影,不需实体舞台框定虚构空间,只需利用镜头运动和景别变化即可完成戏内戏外的转换,片中片让观影者形成更广阔的美学体验与现实联想。
早期元电影在形式上也有不断探索。导演卜万苍在《三个摩登女性》(1932)中嵌入男明星与爱慕者合演的影片。唐煌执导的《银海幻梦》(1949),引用18部已映中电影片,串联起剧中18个人物的梦境,影片人物与已映电影中的人物形成银海幻梦。
早期元电影利用生活空间的真实来模糊电影场景的假定。如朱石麟执导的《艺海风光》(1938)中龙套女演员顶替罢工女主角试演“救火戏”。史东山执导《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再现战时抗敌演剧队走街串巷,深入难民区、农村等地的演出情形。其隐形舞台消解了戏中戏的表演属性,扮作真实以警示大众识别侵略者的真实面目,调动人们的抵抗热情,从而在真实的电影拍摄中完成了观看者和表演者两种角色的统一。
(三)元电影理论溯源
元电影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梅恩·朱迪斯(Mayne,Judith S)1975年发表的论文《元电影的意识形态》中。作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持摄影机的人》《一切安好》《我略知她一二》等影片,将实践理论的元电影与元电影实践进行区分。[1]这篇论文宽泛地定义,作为实践的元电影的目标是分析电影形式、功能,以及意指的方式,关注电影是如何生产的,拒斥把电影和绝对真实等同,并指出元电影探索了真实和虚构间的关系。
威廉·西斯卡(William C.Siska)1979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元电影:现代性之必须》,专门讨论了元电影,试图整体性地定义“元电影”这一概念。他将关注电影和电影人的反身性电影置于传统和现代主义两种语境中理解,并认为现代主义反身性电影才能称之为元电影。[2]现代主义反身性电影往往指向思考电影本质和结构,以不连贯的叙事引起观众关注;传统反身性电影则希望即使电影制作过程被暴露,故事也不会使观众产生疏离感。他将元电影实践和作为实践理论的元电影等同。元电影实践,早在人们有意识去讨论元电影这一概念之前就已诞生,随着时代发展,以及一代代电影人的反思突破,元电影理论在批判中不断完善。有学者认为:“元电影是指关于电影的电影,包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在电影中关涉电影的电影,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涉另外的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本身的那些电影都在元电影之列。”[3]元电影往往包含其制作者本人的形象与生活内容,以及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属于具有双重结构的艺术作品,其展现方式在于反映自己。[4]71
二、元电影精神内核
(一)真实性表达与表达真实性
元电影往往有作者自我扮演的特征,影片作者有意暴露自身,将现实身份带入故事空间。例如巴斯特·基顿本人出演《摄影师》一片,影片的内容也与他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关。热奈特认为,关于元电影的这种倾向,“他在影片中出现也是为了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事实上这就可能将故事外一种个人魅力引入到了虚构的故事情节之中”[5]。这种创作者直接出现在虚构故事中的叙事模式,往往不会给人以越界之感。反之,这种自我扮演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使得观众将其叙事内容与真实生活进行无意识的联结。就像《日以作夜》(1972)里的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本身扮演了一位电影导演,使观众从心理层面更加认同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元电影另一种特征是以套嵌叙事表达真实性,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八部半》(1963)是这种类型的经典元电影。影片对真实的反思体现在探讨电影这一媒介本身。片中的导演这一角色,事实上就是作者在影片中的化身,他真挚、自我、优柔寡断又自鸣得意。不同于很多典型的元电影,这部影片中的角色“导演吉多”所想要拍摄的影片,作为观众甚至一个镜头都没有看到,但结合影片对真实的追问,不难发现吉多梦想拍摄的电影就是费里尼最终呈现给观众的这部影片——其内容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内容。观众虽然看不到吉多如何剪辑加工他录制的素材,但费里尼把这些素材放在了自己的影片中,消弭了电影这一载体与观众之间的隐形屏障。[4]72
真实性表达与表达真实性还同时在元电影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的《偷窥狂》(1960)中完成。男主角马克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连环杀手。马克在童年受到生物学家父亲虐待,被当作研究的实验品反复恐吓,并被记录下惊恐万状的状态。这种对人格的侵犯贯穿了小马克的整个成长历程,因此他形成了特殊的癖好,总是拍摄下谋杀女性的过程,并以欣赏她们惊恐的面容为乐。然而,这个冷酷的杀手被一个他爱慕的温柔善良的女子海伦感化,他无法下手杀死海伦,于是在镜头前完成了最后一次“自我谋杀”——以自己面对死亡前的惊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影片通过展现父亲的录像,直接向观众展现了年幼的马克遭受了何等的虐待。观众被迫承担着观看小马克承受的痛苦的视角、偷窥的视角、观看马克自杀的视角。导演通过建构如同委拉斯凯兹的《宫娥》一样的视觉套层迷宫,通过一种类似于偷换概念的方式,把影片中的某一视点与现实中观众的视点合二为一,使得观众在真实表达与表达真实的张力中进行自我意识的哲学思考。结合《八部半》中导演的自我扮演与《偷窥狂》观众的偷窥视角,这种企图将影片中的真实投射于真实世界的“越界行为”,往往使电影不再是纯粹的真实世界再现,模糊了电影故事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一一对应的指代关系,在一种互相关联对照中深化了电影对真实世界的表达与呼应。由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Peter Weir)导演的《楚门的世界》(1998),讲述了普通男子楚门从出生起就被导演置于摄影棚中生活,生命中的分秒都暴露在隐藏于各处的5000多部摄像机镜头面前,同步通过卫星技术24小时在全球范围电视直播。影片通过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对元电影真实性的表达与表达的真实性进行了哲学的思考。
真实性表达与表达真实性同样贯穿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电影叙事中。影片通过“自我扮演”的方式,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故事空间与真实空间的互相映射中,完成对电影真实性的建构与解构。譬如宁浩《疯狂的外星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步之遥》等影片,同样以虚拟与真实的嵌套为基础,通过剧中人物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再叙述,使视点在故事与“故事中嵌套的故事”之间反复切换,实现不同叙事层面的转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故事的视点在各个人物中来回穿插,这种叙事方式除了展现故事的情节,也同样隐含了叙事者与观众间的对话。叙事者对观众以“你”相称,又使用“我”叙述故事,仿佛叙述者本人正与观众促膝长谈,又强调“千万别相信这个”来暗示故事的虚构性。一方面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由现实空间进入故事空间,将观众的视点拉入故事中,又或者让叙事者从故事空间超脱出来,增进了影片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又反复暗示自身叙事的不真实性,消解了自身建构的真实感。影史上有意通过元叙事的方式建构与消解真实感的例子不在少数,如影片《花眼》的电影院引座员,常常以遇到的观众为主角去幻想与构思故事,提醒观众去注意故事的虚构性,但观众最终从黑暗的影院走出时,却又清楚地被告知此前所述故事的真实性。[6]元电影中的这种越界行为与自我扮演所产生的叙事效果,超越造影者的个人体验,强化了造影者真实表达与观影者参与表达的真实。
(二)形式:批判与超越
元电影超越自身形式,不但具有大众文化易于传播的通俗性,亦可从自我反思、自我解构中产生批判之力,继而酝酿出广泛而深厚的诠释可能。
元电影首先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电影的改造意识。造影者试图通过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扬弃,用新的叙事模式来启发观影者,可以说这是一种大胆的、批判性的尝试。如前文所述,按照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造影者倾向于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来再现一个由影像与声音构成的、与现实别无二致的空间,让观众能借助叙事空间的提示,尽可能沉浸在故事中。而元电影试图将电影的制作过程,对画面的剪裁、角度的挑选以及对片段的组合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如《电影眼》《持摄影机的人》;也可能展现电影创作中遇到的精神困境,如《八部半》《蔑视》,让观众觉察电影只是制作者通过对现实取舍后建构的产物,使读者对认同电影创造的空间产生批判性美学体验与思考。
元电影的诞生便伴随着批判性,它是对传统电影叙事的革新与挑战。早在1919年,电影眼睛理论的创始人维尔托夫就对当时的一切电影提出反对,他不断通过影像艺术实验的探索,去寻找心目中更有表现力的表达内容,他的思想遭到包括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在内的电影理论家反对。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元电影对叙事内容与形式的批判,让观影者在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生活环境中,获得与现实同频共振的审美愉悦。
作为一部因其特有的元电影套层结构,在当时称得上形式革新的电影,《八部半》糅合了导演费里尼对人生观与审美观的批判性思考。在谈及这部影片时,费里尼称之为一部“杂乱无章的自我反省”[4]68。影片在内部放映时,有一位在场的人物说这完全是导演自己的生活。影片中的导演吉多正如费里尼本人,他将人生的反思与艺术生涯的总结糅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只有采用“戏中戏”的嵌套,导演才得以把他真实生活中的思考、人们对他影片的批评,融合在自己的作品里,并如数呈现在观者面前。
(三)内容:批判与互动
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阶梯,慕尼黑,放映》(1995),在慕尼黑放置百余块银幕,用以代表电影的百年历程。[7]观众在这些银幕间行走,象征着走过电影的历史,突破了电影的时间序列,对电影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彼得·威尔导演借助电影媒介在《楚门的世界》空间中营造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真实,让造影与观影同步在元电影拍摄过程中,形成艺术内容与生活情景嵌套式批判,突破了电影的空间边界。诸如此类的元电影,通过对其自身的批判性思考,推动了造影者与观影者在电影艺术与社会生活同步批判中思考。
关锦鹏执导的电影《阮玲玉》(1992)同样属于造影者的反思。这部元电影包含套嵌叙事,即阮玲玉本人出演的故事叙事与张曼玉所演绎的阮玲玉生平的叙事。影片叙述的既是阮玲玉感情生活,也是扮演者张曼玉内观阮玲玉的生活经历过程。从中观众可以看到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与包括导演关锦鹏在内的众多电影录制人员的互动。影片将这些层级的叙事相互穿插套嵌,通过视点的不断转换,构建了中国影人对电影艺术回溯与思考,完成了经典元电影的演员、角色与导演之间批判性反思。这一拍摄的过程,镜头不断将景框外的空间拖入的形式,造就了故事空间与拍摄现场空间的影中影套嵌,形成“虚构场景—电影拍摄场景—虚构场景—影场”的元电影的场景架构,在镜头的切换之间完成元电影叙事。片中,有关阮玲玉所出演的《新女性》内容呈现出元电影的批判性。演员张曼玉完全参与到所扮演的阮玲玉生活中——采访研究阮玲玉专家沈寂及与阮玲玉同时代演员黎丽丽,保存阮玲玉出演的电影影像。影片内容复杂套嵌,如沈寂、黎丽丽接受采访的真实内容与阮玲玉自身出演的电影虚构内容相互嵌套、相互补充。虚构故事中再现真实的电影内容,虚构场景与真实内容互相映照,促使观众对比互相嵌套多层叙事的内容。片内与片外故事之间的套嵌,形成对故事内容的反讽与评论,有效地引发人们对不同层面的电影内容与形式的批判反思,使影片充满丰富而动态的内在张力。
结 语
早期元电影展示了真实与再现之间的区别,其批判是保守的、无意识的,让观众接受固定的影像关系、被动接受电影的叙事。现代元电影则是对真实与再现提出了疑问并进行批判,拒绝被动接受,转向引导观众介入思考,颠覆电影语言秩序,与电影机制产生批判性的对话,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批判性精神。当代元电影的探索延展了电影边界,一方面对于电影的形式与其生产机制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对其内容进行深刻的反思,深入其精神内核,兼顾美学深度与批判广度,使造影者与观影者既能得以创新艺术与革新观念,又能在造影与观影过程中思考电影与现实的关联性。